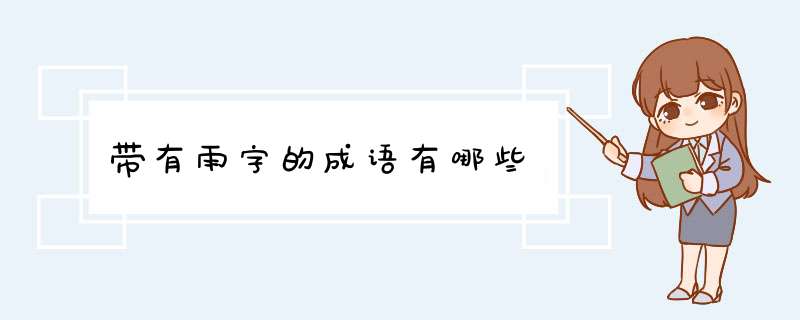元朝诗人刘秉忠和姚广孝有什么关系

很久以前,就想写写刘秉忠与姚广孝的事儿。此二人有很多共同之处:第一,一个元初一个明初,这里的共同点是“初”;第二,都是和尚,而且是大和尚;第三,都是政治家,而且是大政治家;第四,都是文豪,而且是大文豪;第五,在当时人看来,都辅佐了实在不该辅佐的人或集团;第六,都受到皇帝格外敬重和极度褒奖,死后前者谥“文正”,后者谥“恭靖”……刘秉忠生于1216年,活了58岁,姚广孝生于1335年,活了83岁。他们的政治生涯都在北京,死后也葬此地,坟墓至今还在,成为旅游景点。
刘秉忠是河北邢台人,汉族。蒙古人忽必烈欲取中原,刘秉忠主动上门,得到高度信任,官拜光禄大夫兼太保,领中书省事。姚广孝也是汉族,生于江南苏州,他倒是为汉族服务,但在当时人看来,聪明才智理应属之“建文”皇帝,不该属之“燕王”逆贼。姚广孝少时,尝游河南嵩山寺,不期而遇“相者”袁珙。袁珙一见大惊:“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据说袁珙看相很准确, “所相士大夫数十百,其于死生祸福,迟速大小,并刻时日,无不奇中。”照常理说,姚广孝听到此言应该不高兴,恰恰不是,后来教唆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他特意请来了袁拱“指点迷津”。
刘秉忠少时,宋、辽、金、夏胶着混战,他言:“男儿若逢乱世,应先隐之,伺机而动。”他先在武安山当道士,未几,再入天宁寺当和尚。道士也罢,和尚也罢,出家是假,伺机是真。1242年,高僧海云前往“和林”觐见忽必烈,途中听说刘秉忠博才多学,邀之同行。忽必烈召问:“佛法里有没有安天下的办法呢?”海云答:“应该在天下大贤硕儒中求问古今治乱兴亡之理。”刘秉忠对天文地理,遁甲之术烂熟于心,接过海云话头一番鸿论,忽必烈大为赏识,留之幕府,“情好日密,话必夜阑,如鱼得水,如虎在山。”忽必烈欣然命令刘秉忠还俗,不用原名“侃”(字仲晦),赐名“秉忠”,并聘太师、魏国公窦默之女为妻。至此,所谓“秉忠”之意,就不在“大宋”,而在“大元”了。
“和林”之行,刘秉忠得遇“明主”,彻底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蒙古帝国的命运。在忽必烈帐下,刘秉忠干了这么几件漂亮事情:一是上万言策,提出:“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二是采用“汉法”,总政务曰“中书省”,握兵权曰“枢密院”,司黜陟曰“御史台”,中央有寺、监、院、司,地方有行省、行台、宣抚、廉访以及路、府、州、县;三是订立朝仪,使未建国的元蒙政治秩序有了章法;四是减轻赋税差役,劝农桑,兴学校。特别重要的是,刘秉忠建议定都燕京(今北京),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确定政权名称“大元”。这样,既使得蒙古政权迅速完成了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蜕变,也使得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与继续,表明元蒙统治下的国家,不仅属于蒙古一个民族,而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这一招实在厉害呀!
姚广孝14岁时,怀抱“为学有成则仕于朝,荣显父母,不则就学佛,为方外之乐”思想出家妙智寺。朱元璋洪武年间,他赴京城(南京)求官,未果。回乡途中,于北固山前,感怀千载以来这里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吟道:
谯栌年来战血干,
烟花犹自半凋残。
五州山近朝云乱,
万岁楼空夜月寒。
江水无潮通铁瓮,
野田有路到金坛。
萧梁事业今何在?
北固青青客倦看。
同行的和尚宗泐反诘:“此岂释子语耶?”姚广孝报之一笑。显然,他虽身处佛门,却别有怀抱。多年后他曾言:“余少为浮屠而嗜于文,凡昔浮屠之号能文者之文,无不遍求而博览也。”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诏取高僧,姚广孝因病失机,痊愈后与友人檐下小憩,一只五色雀飞鸣于庭,友人戏言:“此雀五色,文明之象,子病起而遇之,异日文章当有大进矣。”姚广孝听后,赋诗云:“野田饱粟纵高飞,他年伫看栖琼树。”抒发了自己的鸿图大志。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再次诏录高僧,分予皇子作导师。姚广孝走到燕王朱棣面前,悄声说:“贫僧能为王爷奉上一顶白帽子。”朱棣何等聪明,当然明白其意:“王”戴“白”帽,就是“皇”呀!到北平不久,姚广孝急不可耐介绍“相者”袁珙给朱棣“纵论天下”,又在城墙四周埋下许多缸瓮、饲养鸡鸭遮掩声音,打造兵器,操练将士。从事后看,没有姚广孝策划,朱棣未必敢举事;没有姚广孝筹划,朱棣未必能成事。“靖难之役”成功后,姚广孝因为“首赞密谋,发机决策”,“论功以为第一”。朱棣也够意思,一如忽必烈对待刘秉忠一样,令姚广孝还俗,赐名、赐宅,并天仙美女若干。晚年的姚广孝,既厌惧官场斗争凶险,又不甘心放弃毕生事业追求,遂承担太子、太孙辅导讲读,及主持《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修纂工作。当年,刘秉忠去世时,元世祖悲痛不已,特命厚葬大都,赠太师。姚广孝去世时也一样,“帝震悼,辍视朝二日”,依僧制安葬京西卢沟河畔,镇远侯顾兴祖奉旨祭灵,宣读御笔祭文,追忆“靖难功绩”。刘秉忠、姚广孝这样双重性格、双重身份的成功人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元、明两朝各一,其他未闻。
刘秉忠早年曾在紫金山讲学,王恂、郭守敬、张文谦、张易等为弟子,这些人后来均成为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在教授学生中,刘秉忠因材施教,针对各人特点和兴趣加以引导。譬如:王恂善于计数,则教之九章算术等,使之成为数学大家;郭守敬勤于动手,幼年曾自制观天仪和计时器,则教之理学与工学,使之在天文、水利方面尽展才华。教育上的成功,给刘秉忠官场的作为巨大借鉴,使他在为朝廷选拔、培养、使用人才方面高人一等。他认为,“君子所存者大,不能尽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狭,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饱学之士,还是凡夫俗子,都可能是某一方面的人才。以此出发,刘秉忠先后为朝廷举荐数十人,后来均为元朝重臣。刘秉忠曾给忽必烈上书,“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随其巨细长短,以施规矩绳墨”。这是元朝初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得到较快发展的根本原因。
帮助蒙古人“顶层设计”建立国家的刘秉忠,还有一件大事更值一提,这就是他主持建造,至今还金碧辉煌的明清两朝皇城——北京城。以汉代以来统治者先进建都思想为主导的工程,这座城市建造历时18年,建有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有384条火巷、29条弄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欧洲人马可波罗在其《行记》中对之作了详细描述,引来西方人对美丽东方帝国的“无限神往”。当然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不怪刘秉忠。
永乐初年,姚广孝又以钦差身份前往苏州赈济。衣锦还乡本是大喜,但对他而言,却也伴随怅然之感:“垅墓既无,祖业何在?岁时祭扫,曾不可得。”回京后,他畜养一只雄鸡,每晨闻鸡而起,忙碌工作。这期间,他所干最大事情,是主持了《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两部大书的编修。《永乐大典》原由解缙总编纂,书名《文献大成》呈上御览,皇帝看后很不满意,复命姚广孝重修,姚广孝花费数年时间完成了任务。其后,77岁的姚广孝再度出山,主持《明太祖实录》重修,直至他去世。这部《明太祖实录》就是今天所见“三修本”,所用时间和内容修订大大超过了前两次。但当永乐十六年(1418年)书成,朱棣设宴赏赐有关人员时,为此耗尽余生的姚广孝已在两月前与世长辞了。
刘秉忠还是元代杰出诗人。他的七律《云内道中》,就是放在唐人作品中,也一点也不差:
远水平芜开野花,
塞云漠漠际寒沙。
闲禽向晚无投树,
倦容逢秋更念家。
万里经年走风雨,
一身无计卧烟霞。
来朝又上居延道,
怀古思君改鬓华。
是啊,“闲禽向晚无投树,倦容逢秋更念家。”这是一个极度入世之人的极度出世佳句,读来很是好笑。“靖难之役”后,姚广孝至长洲看望其姐姚须钬,须钬痛骂不见,访友王宾,王宾亦不见,到这时,他才体会到功业虽成,却众叛亲离的滋味。其后,他在朝堂上尽可能多行善缘,把好事做实,把实事做好,以买人心。闲暇之际,姚广孝或习禅打坐,或游山玩水,曾写“五丈石边琴一曲,桃花三月鲤鱼飞”妙句,人与境和谐,物与我俱融,属天然妙合之景。姚广孝诗作,较之传统文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内心世界,他兼合儒、释之学,而且融儒于佛,借政治之途,往之理想,宽阔、豁然之心于历史及自然,既有系民之热忱,亦有禅思之空寂,读来入心之深,于史少见。
1、中文名:李昊翰,国籍:美国,身高:178cm,出生地:中国上海,出生日期:1974年4月1日,职业:演员,毕业院校:上海戏剧学院隶属海政歌舞团。
2、代表作品:《英雄无悔》、《苍天有泪》、《大明宫词》、《大武当》、《新水浒》、《精忠岳飞》、《萧十一郎》、《边城浪子》、《新猛龙过江》、《旋风少女》、《云巅之上》、《战神2》、《父子》。
姚广孝,小时候名字叫天僖,后来被赐名才叫广孝,出家后的法名是道衍,他有两个字,一个是斯道,一个是独暗,号独庵老人、逃虚子,通称姚道衍。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江路(明为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中国元末明初政治人物、禅宗僧人、诗人,明太宗靖难之役的谋臣之一。就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经常出现在小说,戏曲,影视作品中的重要历史角色,为什么会被人称呼为:“黑袍妖僧”呢?
姚广孝生于医生世家,十四岁剃发为僧,先后学习天台、密教,最后改宗禅门,修持临济宗,法名道衍,号独庵,人称独庵道衍禅师,并拜道士席应真为师,得其阴阳、占卜之术。曾经在嵩山寺游学,有名叫袁珙的相命大师说他说:“怎有这么特异的僧人!眼眶三角形,体态像病虎一般,天性必然嗜好杀戮,是刘秉忠一样的人物!”道衍听后反而大喜,可见姚广孝志向远大,不似一般僧人。
朱元璋死之后,明惠帝朱允炆刚刚继位,就开始大范围的削藩行动,周王、湘王、齐王、代王及岷王纷纷获罪、或被罢黜为庶人、或被迫自杀,情势险峻。于是早就因为诵经祈福认识燕王朱棣的道衍和尚密劝朱棣起事。朱棣说:“民心都支持他们朝廷,我们能怎么办呢?”道衍曰:“臣只知天道而已,何必讨论什么民心!”于是朱棣渐渐下决心,并私下选派军官,勾结部队,并招募勇敢异能的人。之后燕兵起义,姚广孝辅佐世子防守北平,为转战各地的朱棣出谋划策,朱棣攻下南京后,论功道衍为第一。
朱棣攻占南京后,即位称帝,授道衍为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四月,拜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后恢复其姚姓,并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明成祖与其交谈时,称其少师的官名,而不叫名字,表示敬意。朱棣又命其蓄发还俗,道衍不肯。朱棣又赐房屋与宫女给他,道衍都不接受。道衍则住在佛寺中,穿官服入朝议事,退朝后一样继续穿袈裟。之后,出巡赈灾苏、湖等地,在抵达长洲的时候,把自己获赐的银两跟布料都送给宗族与同乡。
智多近乎妖,因为姚广孝实力强大,胸有大志,不惧权势,以一个和尚的身份在天下翻云覆雨,谋划造反,所以有“黑袍妖僧”的称号。
古代儒家和佛教一直是不相容的状态,在儒家知识分子眼里,皇帝信佛奉道无可厚非,但是将佛道信仰和朝政挂钩,则是儒家知识分子所万万不能容忍的。
而且姚广孝到晚年后,写了一本《道余录》,专门抵制程朱理学,引起当时人们的鄙夷。当其回乡省亲访友,至长洲拜访其姐,但姐姐闭而不见;访其友王宾,王宾跑走,远远喊著:“和尚错了啊,和尚错了啊。”于是姚广孝又跑去见其姐,姐姐又骂他。广孝体会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为之惘然。但是姚广孝一生功勋卓著,地位很高,当时没有人敢动他,死后也是。只能是在野史记载中给他取个名字叫“黑袍妖僧”了。我想这就是妖僧称号的由来。
《关于诛十族及其他》
第一版《明史》中记述方孝孺等人之夷族诛死仅用了“丁丑,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十五字。
而在“四库”版《明史本纪》中则改为了这样的叙述:“丁丑,召方孝孺草登基诏,孝孺投笔,且哭且骂。帝大怒,泰、子澄亦抗辩不屈。遂与孝孺同磔于市,皆夷其族”。
很显然,无论是原本还是四库本的《明史》,都没有明成祖夷方孝儒十族的记载。
(关关这里插一句:永乐帝登基的日子是己巳日,之后隔了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整整七日才是丁丑,永乐帝都当了七天皇帝了,又怎么会在七天后逼着他奸佞榜上第一人的方孝孺给他写登基诏书呢?《明史》四库版替前版增加的这个情节,可疑乎?)
《明史》从头到尾都由满清皇帝终审定稿。清廷的几位皇帝对《明史》修撰的重视可谓到了离谱的程度,《明史》每完成一部分,康熙、雍正、乾隆无不仔细审阅,乃至事无大小地就每个自己所“关心”的细节提出自己的“建议”并让书写者照办。
朱元璋修《元史》只花了两年多时间,蒙元修《宋史》(二十四史中规模最大的一部史书)也只花了两年多时间,惟独满清,修一部明历史竟然花了几代帝王近百年的时间,其处心积虑之深由此也可见一斑。
清人修完《明史》后毁弃了大量明朝史料。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下令再次修改《明史》。过程中对明朝的皇帝和人事进行了改编和丑化,更刻意贬低了对明朝皇帝的评价。
比如,原《明史本纪》中的“英宗赞”称英宗“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经改修后的“英宗赞”则这样评价英宗说:“前后在位二十四年,威福下移,刑赏僭滥,失亦多矣,或胪举盛德,以为无甚稗政,岂为笃论哉?”
再如,原本评价明世宗为“中才之主”,而修改后的评价则变为:“且倚任权奸,果戮直臣,以快其志,亦独何哉!”
就是这样不断修改黑明的清编明史,尚且没有诛十族的说法。明史是清朝人所修,为了某些政治需要,明史对明朝的皇帝多有贬损,可是,就在这样一部史书中竟然没有任何关于方孝孺被株十族的记载,想象一下,如果方孝孺真的被诛十族,那么明史的编纂者怎么会放弃这样一个描绘明朝皇帝“暴虐”“残忍”的情节?
有关明朝的正史有两部,一个是清朝人修的《明史》,还有明朝官方自己修的《明实录》,明朝人的官修正史《太宗实录》里面的记载:丁丑,执奸恶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至阙下,上数其罪,咸伏其辜,磔戮于市。
跟《明史》一样,没有任何关于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记载,试想一下,当时成祖刚刚打下南京,如果方孝孺真的被诛十族,此时应该大书特书,用来威慑降官,巩固统治,可是明朝官修的实录却和明史一样,在有关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记载上全部哑火。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成祖本纪中的记载,方孝孺的死期能精确到丁丑日,方孝孺传中不具备如此精确的时间概念,也只能根据所发生的事情来定一下位,即南京城破以后,永乐登基以前。
再看这两段行文。成祖本纪简单,直接,明了,甚至近乎流水帐。方孝孺传则曲折,生动,渲染力强。两相比较,不论辞彩,只说记述事情的笔法,明显方孝孺传的文学性更强。比如说,先是姚广孝交待云云,做一伏笔,然后,就要正面描写方孝孺与永乐帝之间的冲突了,这一段极富戏剧效果。
于是,我们不难从其中发现问题。第一,为何成组本纪可以精确地以六十花甲日来定位时间,方孝孺传中却含糊带过?第二,既然姚广孝交待过不要杀方孝孺,而且还要厚待,燕王也答应了,为什么永乐还要钦定他为奸臣?钦定的奸臣,不杀,还要厚待,还要令其草拟登基诏书,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所以,如果真有姚广孝交待,燕王答应这件事,那么,方孝孺就不会被钦定为奸臣,并一进南京就索要。
方孝孺什么时候死对于永乐帝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总之无非是一个钦定奸臣,早死晚死都没关系。但是对于方孝孺来说,就影响大大了。因为,南京城破,殉节自杀的大臣不是没有,而且也不只一个,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是方孝孺。那么,做为江南士人精神领袖的方孝孺,如此份量的一个人,怎么可以不殉节呢?在某些人的思想意识里,他是不应该活到永乐帝登基以后的,他们无法容忍这个事实。
此外,民间资料里,《玉堂丛语》里,只写到方孝孺“不屈死”,连那段对话都没有,“成王安在”倒是也有,不过那书里写的是练子宁说的。被“灭十族”的方孝儒,其堂兄和嫡长子活蹦乱跳的出现在永乐年间及之后的地方志上面,方家还有侄子华丽丽的出现在仁宗朝!方孝复方琬被赦是官方文件!还有《史迹考》说方克浩改母家姓得免。(令人疑惑,如果真的诛了十族,他母舅家不算十族里面的?)
在后面,明史中有“孝孺有兄孝闻,力学笃行,先孝孺死。弟孝友与孝孺同就戮,亦赋诗一章而死。妻郑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只是说了方孝孺本族的人被杀的信息,并没有提到方孝孺母族,妻族等人被杀的任何消息
更搞笑的是,明史后面竟然还有方孝孺第十族---门人和朋友的信息:“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门人王稌潜录为《侯城集》,故后得行于世。”可见,方孝孺的门人和朋友在永乐年间并没有被杀,至少在正史---明史中没有任何有关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记载。
还有,“明朝万历年间,万历下诏为方孝孺平反,并赐给祭田,将孝孺公次子中宪后人从松江府华亭县寻回,世居浙江宁海至今。该支系以克勤公(孝孺父)为一世祖,传今约25世,后裔约500人。此事明清两代《宁海县志》均有记载。
据《松江府志》载,方孝孺的挚友原刑部尚书魏泽不但没被杀,反而收留了方孝孺的九岁儿子方德宗。
方孝孺刚死,其门人廖镛、廖铭、王稌在方孝孺被杀后,偷偷收了方孝孺的遗骸,并将其葬于聚宝门外山上(今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东麓)。
民国《鄞县志》述:方孝孺长子中愈之后方九成,自明万历年间,由慈溪迁至鄞县,居于白岳乡方家。在慈溪时姓朱,到鄞县后复姓方,方九成为此始祖。
方孝孺有一嫡亲叔叔,叫方克家,其子方孝复于洪武二十五年被流放到庆远(今广西宜山一带)充军,以军籍获免。方孝复的儿子方琬,后来也得释为民。
既然这样,那么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记载出自哪里呢?据我的考证,最早记载方孝孺被诛十族的着作不是在永乐年间建文遗臣书写的文章中出现,也不是仁宗宣宗年代为靖难翻案之后文人的作品出现,而是在靖难发生100多年后的正德年间,由祝枝山所着的《野记》中第一次出现!
首先,通过野记的名字就可以知道,这本书主要是通过民间渠道记录的一些杂文野史,里面记录的内容也非常符合野史的定义,经常出现什么神仙下凡,皇帝微服之类的没有一丝历史价值,但却有着强烈的八卦意味的记载。
最可笑的是,祝允明在野记一书的开头就说:“允明幼存内外二祖之怀膝,长侍妇翁之杖几,师门友席,崇论烁闻,洋洋乎盈耳矣。坐忘无勇,弗即条述,新故溷仍,久益迷落。比暇,因慨然追记胸膈,获之辄书大概,网一已漏九矣。或众所通识,部具它策,无更缀陈焉。盖孔子曰“质则野,文则史”,余于是无所简校焉。小大粹杂错然,亡必可劝惩为也,大略意不欲侵于史焉尔。”
可见他写此书的意义就是“可劝惩为也”,资料来源也不过是“幼存内外二祖之怀膝,长侍妇翁之杖几,师门友席,崇论烁闻”的内容,没有什么史料价值。到了清朝初,有关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记载在严肃史料中还是没有,比如民间史学家谈迁的《国榷》
等到清朝一统天下之后,有关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记载顿时出现,比如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在本书中,忠臣孝子的形象跃然纸上,形象彻底饱满了。此公好像是顺治年间人士,即至雍正年间修《明史》的诸位末学后进、张献忠屠戮四万万人都写得活灵活现的诸人,都不敢继承此公的学说。
到后来那个“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的清朝学者赵翼不厚道地把诛十族和其他正史并列收入他的《廿二史札记》,由于《廿二史札记》流传较广,一些大学者如鲁迅等人深受影响,于是,诛十族的故事慢慢流传开来,以致现在几乎每本关于方孝孺的书都记载了“诛十族”一事,今日作者费了一些心思对其进行考证,希望能够还历史以真实面貌,揭露对明朝的污蔑和贬损。
※※※※※※※※※※※※※※※※※※※※※※※※※※※※
再比如铁铉女儿入教坊司的故事,到处都传得很热闹,可根据建文旧臣茅大芳的说法,他压根没女儿,就一个老婆,还自杀了。茅大芳是建文忠臣,铁铉的好友,他记载的东西应该比《国朝典故》之类的可信一些。
《国朝典故》中的一本:《立闲斋录》。书里是这么写的:“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劳大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旋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还有,《南京司法记》:“永乐二年十二月教坊司题:卓敬女、杨奴牛、景刘氏合无照,依谢升妻韩氏例,送洪国公转营奸宿。又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妇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作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贱材儿。又奏,黄子澄妻生一小厮,如今十岁,也奉钦都由他。”
《奉天刑赏录》引《教坊录》,记载和这个差不多。这些笔记故事十分猎奇,宣传效果明显,什么*贱材儿啊,着狗吃了啊,语言新鲜而且生动形象,但是否真实?
在这些故事里面,甚至提到了铁铉的两个女儿沦落妓女后做的诗,铁铉长女写的是“教坊落籍洗铅华,一片春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空有恨,故园归去却无家。云鬟半馨临青镜,雨泪频弹湿绛纱。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为赋琵琶”
经考证,此乃吴人范昌期《题老妓卷》诗作,范昌期,字鸣凤;诗见张士瀹《国朝文纂》。
同时杜琼用嘉亦有次韵诗,题曰《无题》,则其非铁氏作明矣。次女诗所谓‘春来雨露深如海,嫁得刘郎胜阮郎’,其论尤为不伦。皆好事伪作。
再说这乐户,乐籍制度始于北魏,犯罪者妻女为乐户,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惩罚制度,明代沿袭传统作法,籍没犯罪者妻女入教坊,明太祖朱元璋便“禁锢敌国大臣之孙妻女,不与齐民齿”,可见这是一种传统制度,并非成祖首创,也不能说明他特别无耻。
其次,教坊司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部门。在上面引用的笔记记载中,我们仿佛可以很容易的得出一个“妓院”的结论,但明代的教坊司,实际上是掌管宫廷礼乐的官署。《明史。志第三十七乐一》中记载:“太祖……又置教坊司,掌宴会大乐。设大使、副使、和声郎,左、右韶乐,左右司乐,皆以乐工为之。后改和声郎为奉銮。……及进膳、迎膳等曲,皆用乐府、小令、杂剧为娱戏。”
明代对于宫廷宴乐和戏剧的重视当然来自于元代杂剧的繁盛,所谓唐诗宋词元曲。受其影响,明代戏剧和宴乐都有极大的发展。教坊司作为国家礼乐机关,“统一负责天下乐籍的调配、教习与审核。明代以礼部祠祭司辖教坊司,以教坊司辖天下乐司及所在乐户,从京师到藩国到地方,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礼乐制度,教坊司也正式成为朝廷上宣下化的礼乐机构”。(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概述》)
而教坊司中的女性,主要的职能是“女乐”,而非娼妓。经后世演变,“妓”和“技”,“倡”和“娼”概念上渐渐开始重合,使得后人对教坊司的看法掺杂了一些想当然的成分,其实当时,此“倡”非彼“娼”。
明初官妓其实并不归教坊司管理。刘辰《国初事迹》中记载:“太祖立富乐院,令礼房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员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
而直到永乐十九年,富乐院失火焚烧,才又重新起十六楼安置官妓,官妓的管理才又移回教坊司(徐子芳《明初剧场及其演变》)。由此可见,永乐初年的教坊司还比较单纯,应该只是宫廷掌管礼乐外加唱曲演戏的机关,承办各种宴会演奏。此外,禁止“文武官员”入院的法律规定,也不禁使人对“转营奸宿”、每日“二十余条汉子”轮奸的说法大为怀疑一般研究戏剧和教坊司历史的学者们也多半认为,罪臣妻女入教坊,是作为“在官”女乐存在的,只是卖唱而已,在当时看来当然比较羞辱了,尤其是在我国历史上存在了多年的良贱制度之下,但和那些强暴之类的恐怖故事还是有区别的。
而且,明朝的乐人也并非如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地位低下,比如成祖就经常召“京城名倡”入宫表演(《坚瓠集》:“齐亚秀者,京师名倡,常侍长陵宴”),宁王朱权也得意洋洋的描写“良家子”演戏的情景(《太和正音谱》)。
就算是明初,教坊司中的乐工队伍也应该比较庞大,如果每个女人的事情朱棣都要亲自批示,他未免也太闲了一些。尤其是时间分别在永乐二年和永乐十一年,都不是靖难发生的时候,过了这么久了皇帝还要关心这些,实在是匪夷所思。再说黄子澄妻生了孩子,干嘛早不报晚不报,一定等到十岁了才报呢?
而且,就在那个“*贱材儿”记载的几乎同一时间,《明通鉴》上却有一条完全不同的记录——“永乐十一年正月……是月,倭寇昌国卫,诏宥建文诸臣姻党”。几乎在同样的时间里,难道朱棣会一边写着赦免“建文诸臣姻党”的诏书,一边又批什么“依由他”?实在很难想象。由此可见,关于建文旧臣妻女遭遇的故事,其实并不完全可信。
关于铁铉妻女的故事,清人写的明史中也只有这样一句:“燕王即皇帝位,执之至。反背坐廷中嫚骂,令其一回顾,终不可,遂磔于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并安置海南。”
几个版本之后,就变成了割其肉、下油锅,人都死了在油锅里照样翻不过他身子的神怪故事。《鲁迅全集》第六卷《病后杂谈》中写到,“俞正燮《癸已类稿》据茅大芳《希董集》,言‘铁公妻女以死殉’;并记或一说云,‘铁二子,无女。’那么,连铁铉有无女儿,也都成为疑案了。……”
看起来,认为铁铉妻女都挂掉了的,有一个出处,认为铁铉没女儿的倒有两个出处,《国朝典故》里也只提到铁铉的妻子杨氏,并没提到他有女儿。而这个杨氏,在茅大芳《希董集》说的又是张氏。
另考,铁铉后人于永乐元年(1403年)避难至山海关,隐居今锦州地区,成为沈阳铁氏的祖先。如今,铁姓已成为辽沈地区望族。明末清初铁姓迁到沈阳的有铁福、铁仲、铁魁、铁桂、铁元等祖辈几代。有六人为官,其中铁奎、铁桂及其子铁范金,皆为清代较为显赫的军政官员。现存东北最大清真寺——沈阳南清真寺,为其后人铁魁所建。
※※※※※※※※※※※※※※※※※※※※※※※※
关于对黄子澄的处理,逃过满清篡改的《国榷》是这样写的:“家僇六十五人,戍姻党四百余人”(《国榷》卷十二,第854页),翻译成白话就是:家里被抓了65人,亲戚被流放了400多人。
有人会说“僇”是杀的意思,是指杀了65人。“僇”这个字确实有“杀”的含义,但通常是指惩罚、逮捕的意思。在明朝史书中,“僇”的用法有严格的规定,与表示杀头的“戮”字有明确的区别。
如《国榷》在讲黄子澄下场时,对黄子澄本人用了“戮”字:“及被戮,彦修(黄子澄儿子)解役至京,收骸骨”,而对黄子澄被抓的家人则用了“僇”字:“家僇六十五人”,可见是有明确区别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僇”字在明朝史书中的用法,我还可以举出袁崇焕的例子。袁崇焕在崇祯二年下狱后,其部将祖大寿率关宁军出走,阁老孙承宗派人追上关宁军,想把他们劝回来,《崇祯实录》记载当时关宁官兵的回答说:“主帅已僇城上,又以火炮歼我,故逃避至此!”
而在《国榷》中,亦有“但主帅已僇,又火炮歼我,故遂至此!”的记载,这里的“主帅”,当然是指关宁军的主帅袁崇焕,按袁崇焕被杀是崇祯三年,祖大寿出走时才刚刚抓起来,但明朝史书就已用“僇”字来描述袁崇焕的遭遇,可见“僇”这个字在明朝史书确实是指逮捕,而并非杀头。
那黄子澄的家人被抓后,有没有被杀呢,很可能是没有。首先、如果其家人被杀,那史书中应当有明确记载,而不会仅仅用一个表示逮捕的“僇”字。
第二、今天黄子澄嫡长子黄升的后人已经公开站出来,证明其祖先没有被杀,同时他还证明黄子澄次子黄旭也没有被杀。(按黄升21代后人黄修刚已公开站出来,拿出家谱证明黄子澄长子、次子都没有被杀。并指出现在江苏丰县范楼镇黄坝村几百口人,都是黄子澄的后代。)
刘基:大明开国第一帝师
朱元璋:倾元建明的平民皇帝
徐达:功贯古今的开国将军
傅友德:戎马倥偬建功业的开国名将
姚广孝:和尚军师第一人
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英魂
郭登:忠君爱国守北疆
杨一清:出将入相的四朝元老
王守仁:疆场犹显儒将风
戚继光:平定倭患的民族英雄
李成梁:镇守辽东的抗倭虎将
孙承宗:誓死忠于明廷的辽左英魂
袁崇焕:“功到雄奇即罪名”的悲剧
史可法:梅花伴忠臣
郑成功:驱荷复台名垂青史
元朝诗人刘秉忠和姚广孝有什么关系
本文2023-10-05 17:26:46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100893.html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