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娘、韩女」源考。附华佗狱中托书事件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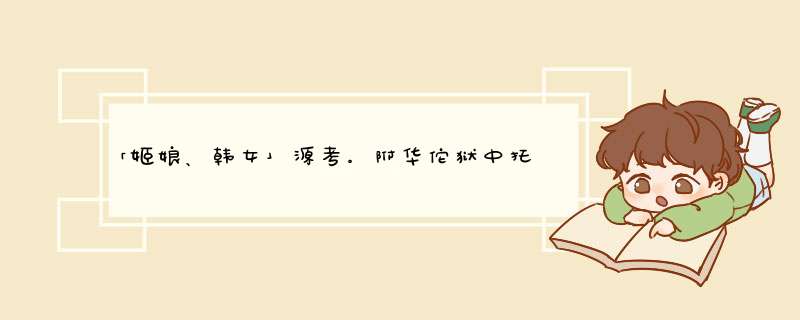
历史上有姬娘和韩女这两个人么?这是出现在话剧《商鞅》里的两个人物。
原回答内容 已由本人精简修缮,并大幅扩充
卫鞅初为姬娘收养,后被魏国公孙痤收为家臣。为绝鞅之后顾,姬娘自盲双目,誓不再见鞅。后卫鞅虽名显当世,却终未能伴姬娘左右以报恩。
韩女,青年卫鞅之红颜知己。其初为魏相公叔痤家妾,后为秦孝公庶夫人。鞅入秦,虽改革有功,却终不能再与所爱慕之人厮守。
「姬娘、韩女」二人,罕见于小说戏剧,而未见载于史书。
史上或确有其人,大抵因不值得记载、没必要记载,遂湮没历史长河。
毕竟历朝史书 较少收录女性人物之生平与事迹,很多古代女性名人都被轻描淡写 甚至一笔带过。加之列国战乱、始皇焚书,以及历朝大小战乱,不少典籍保存至今,自是难上加难。
历朝都不乏古籍善本失传,且其中不乏学术名著和大部头,如《连山》《归藏》《青囊书》《黄帝外经》《永乐大典》等,其或内容精深,或卷帙浩繁,可惜都散佚殆尽或所剩无几。此憾则憾矣,去者难回,往事弗追。
《连山》《归藏》,夏商两朝之易学经籍也,地位曾比肩周朝之《周易》。
《青囊书》亦称《青囊经》,东汉末华佗所著之医书也。华佗曾欲为曹操做开颅手术,所凭之医理医术,必见载于此书。奈何此书早佚,不然必振奋华夏之外科医学于千余年前也!
按,华佗,约公元145~208年在世,迄今已近两千年矣。
据资料,华佗与董奉、张仲景并称「建安三神医」。其少时游学行医,足迹遍及皖、豫、鲁、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医术全面,尤擅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晚年因被曹操怀疑,下狱拷问而死〔非下狱即死,而是历经一年多,待华佗将医书写成 并托付给狱卒,方才与世长辞〕。
据前文「尤擅外科」四字,可知《青囊书》中 必有华佗总结的 关于当时外科医学的尖端成果。毕竟华佗发明过麻沸散和五禽戏,前者乃外科麻药鼻祖,惜已失传 ;后者是中医著名导引疗法之一。
试想,中华外科医学,若果经千余载之发展历程,其理论与实践之造诣 必使近代西医望尘莫及,亦必使当世之西医汗颜矣。
遥想美国国父华盛顿先生垂危之际,一度呼吸困难,身边医生束手无策,惟放血耳,更无药可依。那是在1799年12月,距今不过220年。 〖请参考篇末所附资料〗
近代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重病手术,主刀医生是哈佛博士、经验丰富的外科医师,奈何其竟操作失误〔具体细节请查阅资料〕,手术失败,孙先生不日病逝。弥留之际,孙先生强令家人及知情者 务必隐瞒其手术真相,以免舆论哗然,更务要力保方兴未艾之中国西医,使之不至于方才引进,即告夭折。
《黄帝外经》,载上古外科医疗之经验、成法。一如《黄帝内经》载上古内科医疗之经验、成法。因此书成于华佗《青囊书》之前,且全书专论外科诊疗事宜,故其所涉外科内容之深都广度,或将在《青囊书》之上。
曹操以狠辣多疑著称,且曾弑杀曹父故人吕伯奢一家〔此事存疑,或为各本虚构〕。华佗为曹操诊病,理应避其锋芒,华佗也确实如此行事。奈何命数不顺,其平生虽救济贫病于四海,却仍于晚年逢大难,被下狱而终。
然观史书所载,推览华曹二人言行经过,盖非曹操之罪也,实华佗之失。华佗心怀天下苍生,有生之年欲云游四海以行医问诊。此间心迹,大可与丞相推心置腹,一表苦衷。操乃一世枭雄,未必不能明大义。
再说丞相头疾,乃慢性发作。华佗可舍数月之光景 集训丞相御医,务使其人人精于用药、针灸,以备丞相疾发之苦。丞相或将欣慰甚,遂准华佗离开,以成其善行。故华佗需谋此双赢之策,方能继续四海行医,又保丞相不再畏疾发作,则何祸之有耶?且华佗一旦重获自由,则其著书乃至授徒诸事,便悉得保障。则其道法不怕不传,其术业亦后继无忧矣。
故其若果为天下苍生谋,进退必求审慎稳妥,安能行史载之激进荒唐事耶?故愚推测,华佗之死,或另有蹊跷。只是时人迫于无奈,才封锁消息,临时编造个故事,以掩事实真相。史载此事,符合曹操本性,但于华佗处则说不通。
且曹操初因「华佗欲归家照料夫人」一事被骗,虽怒但未有行动。后疾发再召华佗入宫,华佗竟挑战时人之心里耐受力,直言需开颅方可治愈。如此狂言,换作董卓、袁绍,则华佗必获罪问斩。然曹丞相在身边小人谗污暗谤之前提下,仍决定网开一面,虽觉其居心不良,仍只是「不敢再问诊于他」。而后华佗不知收敛以保身,竟当众奚落曹操,后者甚为恼怒,才将华佗下狱。下狱而未问斩,此已算忍让有加。
故兹事观乎始末,都不应问罪于曹操。而华佗如此行事,亦不合常理,其究竟意欲何为,怕已成恒久之悬案、永世之谜团。
史载华佗初为曹操诊治头痛,扎针服药,病症消失。曹操大喜,欲留华佗当侍医,期常伴左右,以备不时之需。华佗心怀天下苍生,拒辞不受,操令禁其足,不准其返。两月匆匆过,华佗再难忍受,遂以「夫人久病,需人照料」为由,请归乡里,并称「待夫人病愈,即来侍奉丞相」。曹操允,差人送其归。差人返禀,称华佗夫人生病是假,不愿侍奉丞相是真,曹操大怒。後操头痛又犯,召华佗。华佗诊后沉思,曰:「 丞相之病若欲根除,须先饮“麻沸散”,再剖开头骨,取出颅内风涎,方能彻底治愈。不然,则还会再犯。」
操疑而未决,加之小人暗谤华佗,进献谗言,操便疑华佗居心不良,遂不敢再问诊于华佗。等华佗察知内情,索性当众将曹操奚落一通。曹操大怒,将华佗下狱。
入狱后,华佗病,自觉获释无望,遂决意整理一生行医治病之经验,使启后学,兼利苍生。华佗狱中著书 计一年零三个月。书成,其病愈重。
一日,有狱卒曰张明三者来探视,华佗取所著医书于枕下,含泪曰:汝常善待于我,我无以为报,此有所著医书一部,曰《青囊经》。此书载我一生行医所得,此赠予汝。汝若愿习学之,便可如我般治病救人。张明三听罢,感激涕流,稽颡叩拜,收下药书。张明三纳藏华佗著作,怕丞相闻讯怪罪,便连夜携书返家,请其妻暂代保管。
华佗于狱中著书,尽述平生行医所得。书成,嘱一狱卒,唤张明三,为报其平素善待之恩,愿以此书相赠,请其务妥善保存!狱卒感其诚,连夜携书返家,请妻暂代保管。
其送书未归,华佗逝世。操闻讯,甚惋惜,令厚葬。华佗逝,张明三悲甚,誓苦学医术,广济黎民,以慰华佗在天之灵。未几,张明三即负囊高歌,辞职返家。然方入家门,即大惊失色!其妻正在焚烧《青囊经》。张明三悲愤极,扑上去抢救,惜已晚,得剩半本残卷。明三怒斥其妻:尔缘何烧吾书?!
其妻含泪曰:只欲让汝多活几日罢。汝未见那华佗 即因精医术而下狱死乎?
明三慨然语曰:人行于世,上无以报国,下莫能济弱,纵百有余年又何益哉?
其妻闻而触动,奈何书已焚坏,卷已残缺,悔之晚矣。
虽原书仅存半部,张明三亦刻苦研读,后果成乡里名医。
关于华盛顿总统之死
『 后来,克雷克和迪克起草了公开声明,向国人交代他们为总统治疗的全部过程,试图消除人们对他们有意治死总统的怀疑。但是,不论他们如何解释,在很长的时间里,学者们都认为放血治疗导致了总统的死亡。
事实上,在最后的关头,迪克曾考虑用气管切开手术来解决呼吸困难问题,可是他没有做过此类手术,也不敢在国父身上做这个试验。
莫伦斯认为,考虑到当时缺少麻醉药和抗菌剂,人们应该认识到在那种情况下,医生无论如何也无法救活华盛顿。
然而,人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威廉·桑顿医生的办法是最可行的。他第二天才赶到,当时他看到的只是华盛顿的身体已经开始僵硬,于是他建议将还有一口气的华盛顿浸在冷水中,对他施行按摩,渐渐使他体温回升。然后,朝肺开个通道,用导管使他吸气。
对于这些建议,(华盛顿的夫人)马莎一概予以否决,她只是认为,华盛顿是遵悉上帝的安排而死的,自己过不了多久也会随夫而去,他们团聚的时刻是最幸福的,何必再多此一举呢?』
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一诗诗题曾在1949年后引起过许多学者的关注。从1959年学界对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讨论开始,到七十年代程千帆先生和施蛰存先生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分别提出各自的意见,至今未有定论。学者关注此诗题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诗题于流传中异文颇多,不知哪个更接近原貌;二是题目中某些字词意思于今难懂,不知应作何解。笔者在此提出一个新的可能,与学人共同商讨,并望方家予以指正。
一中华书局最新版王锡九先生《李颀诗歌校注》中对此诗诗题的注解主要引述了程千帆、施蛰存两位先生的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在今天看来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下面就此一一进行分析。
(一) 施蛰存先生认同《河岳英灵集》版的诗歌标题,认为《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这是李颀自己写下的原题”,“《唐文粹》《唐诗纪事》《唐音》都照录原题,可知编者都了解题义”。诗题标点应为“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而其他版本的致误之由是:
《河岳英灵集》的编者殷璠在评论李颀时,引述这首诗说:“又《听弹胡笳声》云……”他把诗题简缩为五个字,而在“声”字上读断,这是第一个读破句的人。后人跟他误读,下文的“兼语弄”云云就无法理解了。
施先生解释“声兼语弄”,认为“声”的意思是声音,“语”的意思是胡语胡乐,“唐人对西域来的音乐或歌曲,都比之为胡语”,“弄”则是琴曲,所以此四字是在形容董庭兰弹奏的《胡笳十八拍》“兼有胡笳和琴的声音”(施蛰存《唐诗百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这一解读有两个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李颀此诗作于天宝年间,《河岳英灵集》编纂于天宝末年,前后相差至多不过十余年,不应存在编者读破诗题的情况,除非殷璠看到的诗题已令他感到不解,也即是说此诗题传至殷璠已出现讹误。试想,若同为天宝人的殷璠尚且读破句,后来《唐文粹》《唐诗纪事》《唐音》的编者们比殷璠更了解题义的可能性有多少?
其二,将“语”解释为“千载琵琶作胡语”的“胡语”实在有些牵强。检唐诗中若有“胡语”意者,必按一“胡”字。因为琵琶属于胡琴就将琵琶诗中的“语”都解作胡语,进而将其所咏乐曲皆视为胡曲,又以此证明其他音乐诗中出现的“语”也皆为胡曲之意,这样的推断恐怕不妥。随便拿几首诗就可以证明:“小弦切切如私语”(白居易《琵琶行》),“昵昵儿女语”(韩愈《听颖师弹琴》),一是琵琶一是古琴,难道二者所描写的都是胡曲?况且在古代音乐文献中,能否把“胡语”跟“弄”相连并用也值得考虑。以此看来,《唐诗百话》中对此诗题的解释较难成立。
(二) 程千帆先生在《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诗题校释》中认为李颀此诗诗题流传有误,并做出相关校释:
一是“弄”字指琴曲,但是与“声”字并见不可解,因此“弄”或为释“声”字义混入正文的衍文;二是“寄语”及“兼寄语”应当为连文。“寄语”在诗歌中常见,“兼寄”在唐人诗题中常见。同时“语”和“语弄”并非音乐术语。因此程先生认为此题目应为《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房给事》。题目传抄错误的步骤可能是《十家诗集》系统先衍出“弄”字,《河岳英灵集》系统又在此基础上乙“语”与“寄”。《唐诗品汇》系统讹误最大,先衍后乙再缺“声”字(程千帆《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诗题校释》,《程千帆选集》,辽宁古籍出版社)。
程先生的校释也有三点值得商榷。
其一,“寄语”一词的色彩义及其使用习惯。“寄语”一词字典义概括为“传话,转告”,但从感 彩上看,它通常有一种语重心长的、或较凝重或类似传达经验的、犹有深意的味道。如:
寄语后生子,作乐当及春。(鲍照《代少年时至衰老行》)
寄语同心伴,迎春且薄妆。(刘希夷《晚春》)
寄语边塞人,如何久离别。(孟浩然《同张明府清镜叹》)
寄语何平叔,无为轻老生。(刘禹锡《寓兴》其一)
寄语双莲子,须知用意深。(李群玉《寄人》)
包括程先生文中引到的杜甫《驱竖子摘苍耳》“寄语恶少年,黄金且休掷”等也是如此。这其中杜诗“寄语杨员外”(《路逢襄阳杨少府入城戏呈杨员外绾》)有些不同,但此诗题既已标明是“戏呈”,这种“寄语”当属朋友间的诙谐口吻。所以从用法上看,李颀似乎不该因为听了董大的美妙琴曲就犹有深意地“寄语”房管,纵观全诗也并无一丝戏谑之意。此外,检索今存《全唐诗》《全宋诗》,尚未见诗题中有“寄语”二字者。
其二,程先生说“弄”是琴曲术语,可能最初是“声”字释文,因此而衍。但在古代音乐领域,“声”和“弄”的内涵外延并不相同,不当出现以“弄”解“声”的现象。
“声”有时特指五声,有时指某乐器发出的声音,如琴声、笛声、琵琶声、胡笳声等,在乐曲中也指某种声音或情境的表达或再现,比如说琴曲中有凤凰声、胡笳声,“声声犹带发冲冠”(贾岛《听乐山人弹易水》)等。
“弄”在器乐中有两义,动词为演奏音乐,名词为乐曲。《说文》:“弄,玩也。”玩乐器就是演奏乐曲。《世说新语·任诞》中桓子野为王子猷吹笛篇说,桓“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即是。后来应是由动词派生出名词义,所以乐曲也叫“弄”,于是出现以“弄”为曲名者,如同乐府中的“歌”“行”“引”之类,如嵇康《琴赋》:“改韵易调,奇弄乃发。”《南史·隐逸传》载:“宗少文善琴,古有《金石弄》,为诸桓所重。桓氏亡,其声遂绝,惟少文传焉。”等等。再后来其成为古琴的一种专用曲式,如刘宋谢希逸《琴论》:“和乐而作,命之曰畅……忧愁而作,命之曰操……引者,进德修业,申达之名也。弄者,情性和畅,宽泰之名也。”(《乐府诗集》卷第五十七《琴曲歌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而大概正是由于最后一个涵义,让之前的学者们习惯于把目光集中在诗题中的“语弄”和“弄”上。
但是由此可见,“声”绝不是“弄”,“弄”也绝非“声”,二者不应互释。岑参有《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起二句曰:“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是很明显区分了“歌”与“声”。郭茂倩《乐府诗集》引唐刘商《胡笳曲序》说:“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许健解释这段话说:“他(笔者按:董庭兰)是把‘声’加工成‘弄’的。”(许健《琴史新编》,中华书局2012年版)可见“声”是“声”,“弄”是“弄”。观岑参此诗诗题与起句跟李诗有相似之处,而李诗起句“蔡女昔弹胡笳声,一弹一有十八拍”也正是刘序里的意思。
其三,程先生所见《十家诗集》《河岳英灵集》《唐诗品汇》三个系统虽都是明刻本,但《十家诗集》系统所出最晚,《十家诗集》刊于万历年间,其系统中最早的《唐诗二十六家》也刻于嘉靖年间。《唐诗品汇》却成书于明初,最早刻本出于弘治。为何晚出的反而讹误最少?
二由于李诗流传最广的几个版本诗题意思确实难解,笔者顺着程先生的思路认为此诗题在传抄过程中产生讹误的情况是极有可能的。在此,笔者提出一个新的讹误可能,与学人共商:“语”字或是“调”字之讹,“语弄”应是“调弄”。“声”字或为衍文。理由如下:
(一) “语”与“调”讹误可能性:形近而讹。
“调弄”二字或本应是连文。从题目传写看,常见四个版本的差异主要在“声”“兼”“语”“弄”“寄”五个词素顺序或者有无的不同上。但不论如何调换,“语弄”两个词素总是连在一起的。说明很可能此二字在原始版本中就相连: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河岳英灵集》等)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十家唐诗》《全唐诗》等)
《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唐诗品汇》等)
《听董庭兰弹琴兼寄房给事》(《文苑英华》)
“调弄”成词,且是音乐术语,运用广泛。“调”和“弄”本各自有义,合为一词在音乐上有两义。做动词时“调”音阳平,指演奏音乐,特指弦乐,如方干《听段处士弹琴》:“几年调弄七条丝,元化分功十指知。”做名词则读去声,泛指乐曲、曲调。如宋代《张协状元》戏文第二出:“适来听得一派乐声,不知谁家调弄?”钱南扬校注:“谁家调弄,犹云‘甚么曲调’。”(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中又进一步说明这里的调弄指弦乐:
所谓调弄,当不同于“吹”曲破断送,应为琵琶之类。(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调弄”可以用来称呼各种弦乐曲。如唐诗中白居易有诗题《带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此是琵琶;宋太宗《缘识》其二八:“阮咸初立意,偷得姮娥月。……堪听诸调弄,勾锁无休歇”是写阮;欧阳修《三琴记》“其他不过数小调弄,足以自娱”,陶宗仪《说郛》载宋僧居月《琴曲类集》“凡诸调弄,诸家谱录尽分三古”,则都是写琴。从琴的领域看,“调弄”跟“弄”意思相似。
若从“弄为古琴术语”这一视域中跳出看,诗题写作“调弄”也是完全合理的。
以“胡笳”为名的琴曲在唐代很是流行,今见至少有“大胡笳”“小胡笳”“胡笳弄”“胡笳引”“胡笳曲”等几种不同称呼。而董庭兰在历史上也确实以整理、演奏胡笳曲闻名。除了前引刘商《胡笳曲序》:“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还有元稹《小胡笳引》“哀笳慢指董家本,姜生得之妙思忖”等可为证。“董家本”即指董庭兰整理的《胡笳》谱。
综上所述,可以说刘商《胡笳曲序》中的《胡笳曲》《胡笳弄》正是李诗题目中的“胡笳调弄”。若此说成立,则“调”讹为“语”的时间应该很早,因为今见最早的宋刻《河岳英灵集》就已如此。因此很可能是先有此讹在前,导致后人对此诗题模棱两可,于是有了后来各种版本文字顺序上的调换。
(二) 关于“声”字是否为衍文衍文可能性:衍诗歌第一句“蔡女昔造胡笳声”中的“声”字。
统观唐代音乐诗,尚未发现“听某人弹某声”的用法。李颀有《听安万善吹觱篥歌》,王昌龄有《听弹风入松阕赠杨补阙》,白居易《听弹湘妃怨》,贾岛《听乐山人弹易水》,顾况《李供奉弹箜篌歌》,李贺《听颖师弹琴歌》等等之类,结构均是:
听+(某人+)弹/吹……+某曲(+赠/寄)(+某人)
其所表述的听弹音乐都是完整乐曲,而非某“声”。且一首诗题中有“声”有“调弄”也略显繁琐。
《唐诗品汇》无“声”字。《唐诗品汇》完成于明初,且被学者公认为“精审”之作,保留了许多前代珍贵文献遗迹。高棅独在此书中于诗题未加“声”字,应该不是漏刻,而是有其他更早版本为依照。
但是“声”字究竟是否确为衍文还值得思考,因为今见宋本《河岳英灵集》中殷璠已简称其为“《听弹胡笳声》”(影宋本《河岳英灵集》,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若为衍,则或者此处与诗题皆衍,如此则很有可能殷璠看到的诗题已经有此衍文。若不衍,则或者因为“声”与“调弄”毕竟不同,因此用一“兼”字,胡笳声不成曲调,展示过后再弹完整的《胡笳》。
三据此,笔者提出还原此诗题的三种可能:
第一种:《听董大弹胡笳调弄兼寄房给事》。这是于文义而言最顺畅的诗题。若如此,则各家在讹“调”为“语”的基础上:《唐诗品汇》乙“兼寄”“语弄”;《河岳英灵集》衍“声”字,又乙“兼”“语弄”;《二十六家》衍“声”字,又乙“兼寄”“语弄”。
第二种:《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调弄寄房给事》。这是最符合奥卡姆剃刀原理,兼顾可见最早版本和讹误最简的诗题。“声”指琴奏出胡笳乐声,“调弄”指作为完整曲子的胡笳曲。若如此则《河岳英灵集》只讹“调”为“语”。
第三种:《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调弄房给事》。若如此,“调弄”当指调弄谱,与白诗《带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题目相类似。诗人听了胡笳曲顺便把曲谱寄给房给事。“声”字若衍,则“胡笳”指胡笳曲;“声”字不为衍,则胡笳声指奏出胡笳味的琴音。若如此,《唐诗二十六家》只讹“调”为“语”。
以上三种可能的来源或许分属三个系统,且都有更早本子可依。
一个是《唐诗品汇》系统,上文已有分析,此不赘述。
一个是《河岳英灵集》系统。上文提到的宋刻《河岳英灵集》是迄今可见载有此诗的最早本子,明本诗题文字与之相同。
一个是明刻《唐五十家诗集》系统。《唐五十家诗集》中此诗题目与前文提到的嘉靖《唐诗二十六家》及之后《十家》《百家》等各多家诗题文字相同。今学者考证认为该书刻于弘治前,其中收录的个人诗集与可考之宋元本诗集间有密切关系(影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其中《李颀集》收诗109首,与今见最早的正德刘成德刻本《李颀集》(87首)很是不同,与记载中存诗118首的陆涓本或其他别集刻本来源应该也不同,很可能亦另有宋元本可依。而后来的《二十六家》等多家诗诗集对李颀诗的选刻很可能源出此本。
因此,仅从版本上看,虽然《河岳英灵集》为宋刻,依然很难说明哪个系统文字更接近作者原著,也无法由此断定“声”字究竟是否为衍文,这一疑问还需求教于方家了。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院)
新书架《李太白全集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精装全八册)是李白研究大家郁贤皓教授毕生治学经验之结晶。在前贤和今人研究的基础上,郁教授用“竭泽而渔”的方法搜集资料,以认真审慎的态度,通过实证研究的工夫,对李白的全部诗文重新整理编集,删除伪作,补入遗诗逸文,并进行校勘、注释、评笺,从而为学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李白全集校注本,堪称当代李白研究的最新总结。这个总结建立在版本、考据、义理之上,继往开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献意义,将对开创李白研究、唐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提供极大便利和裨益。
《李太白全集校注》,精装十六开,全八册,凤凰出版社2015年12月版,定价880元。
本文2023-08-04 11:56:50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10190.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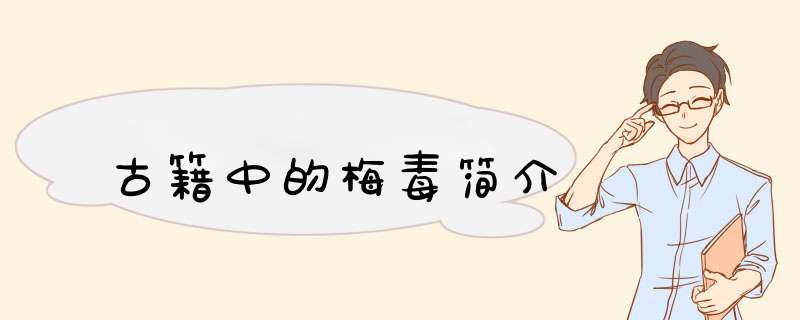
简(青斋书局出的)有收藏价值吗,知道的能说说吗,大概多少钱呢.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