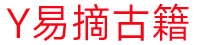藏族的相关资料?

藏族是主要生活在青藏高原上、使用藏语的民族,自称“博巴”(藏文:བོད་པ་;威利:bod pa)。主要分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西藏、川、青、甘、滇,境内人口约630万余人(2010年);在尼泊尔、印度、不丹、巴基斯坦等青藏高原周边国家亦有分布;另有从中国境内移民出境的藏族及其后代近20万。
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帝国。公元11、12世纪,藏民族开始逐渐形成。藏族使用藏语,通用藏文。主要从事畜牧业、农业。主要信奉藏传佛教,宗教气氛浓厚。常着藏袍。以糌粑为主食,多吃牛羊肉,喜饮酥油茶、青稞酒。牧区多住帐篷,城镇多住碉房。多行天葬。藏历新年为重要节日。
藏族文化悠久、灿烂而独特,文献众多,藏医药、藏历、歌舞、唐卡、金铜佛像等都独具特色。史诗《格萨尔王传》、热贡艺术、藏戏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族源
藏族民间有关民族起源的传说中,流传最广、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猕猴与罗刹女交配繁衍藏人的传说。有学者猜测,“罗刹女”指的是藏地土著,“猕猴”指来自横断山区的种群,二者结合的传说隐喻远古时期两地氏族之间的联姻。
藏族的基因有94%来自现代人种,6%来自已灭绝的人种。其现代人种的基因中,有82%与东亚人种相似,11%与中亚人种相似,6%与南亚人种相似。根据藏族特有的基因,藏族距今62,000-38,000年前就来到青藏高原。关于藏族的族源,历史上存在多种“外来说”。
考古发掘则表明,在距今39,000-31,000年前,青藏高原上就有原始人类居住。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分别是藏东地区和西藏腹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代表。现代研究多认为,藏区的种族和文化,是以藏区本地的土著居民和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南下的氐羌部落为主体融合而成。
另一部分古羌人向东发展,参与了汉民族的形成,即汉文文献中的西羌部落;一部分南迁云贵高原及东南亚,发展为藏缅语族各民族;留在青藏高原的部族,逐渐发展为今天的藏族。
藏民族,是吐蕃王朝灭亡后通过吐蕃部落在原吐蕃王朝征服 地域(青藏高原范围),尤其是甘青及川西高原地区与原吐蕃王朝征服的各族居民经五代、宋、金长达几个世纪的相互杂处、共同生活及血缘上的彼此混同,尤其是通过“后弘期”藏传佛教在整个青藏高原地区的广泛传播和普及之后而最终形成的。
扩展资料:
一、族称
自称
在藏语中,称藏区为“博”(藏文:བོད་;威利:bod),称藏人为“博巴”(藏文:བོད་པ་;威利:bod pa)。此外,不同地区的藏民又有不同的自称:阿里地区自称“堆巴”,后藏自称“藏巴”,前藏自称“卫巴”,康区自称“康巴”,安多地区自称“安多哇”。
他称
汉族地区多以“藏”为词根。在藏语中,“藏”本是满盈、纯净、清澈的意思,后来用来指称雅鲁藏布江(“藏曲”),再后来又引申指雅鲁藏布江的发源地——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地区。康熙年间,汉文文献开始用“藏”“西藏”来指称包含整个青藏高原在内的地区,并根据地名,将居住于“藏”的民族称为“藏人”“藏民”等,19世纪末开始用“藏族”一词做为藏民族的称呼。
此外,根据藏语中对藏区的称呼“博”和对藏人的称呼“博巴”,汉文文献中也称藏人为“番族”“番人”“濮”“番巴”“博巴”“百巴”“北发”“发羌”等。
唐代称当时藏地的政权为“吐蕃”。“吐”在藏语中指“上方”“高处”。“吐蕃”即“生活在高处的蕃人”,最初是西藏高原周边地区的藏族先民对雅鲁藏布江流域的蕃人的称呼,在被蕃人部族征服后仍保留了这一说法。蒙古语和满语中都采用这一称呼,蒙文汉译为“土伯特”,满文汉译为“图白忒”。西方语言对藏区、藏人的称呼,也多译自此类,如英语中称西藏为“Tibet”。
民族关系
藏族与中原汉族长期以来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松赞干布时期,唐朝与吐蕃之间开通了长安—西宁—唐古拉山口—那曲—拉萨的道路。此后,藏汉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汉族的陶瓷、丝绸、印刷等技术传入藏地,藏族则向汉地传输了大量宗教文献。
藏族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也有着密切来往。同样是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开辟了从拉萨至泥婆罗的道路,并通过泥婆罗与天竺来往。赤松德赞当政时,从印度迎请寂护和莲花生入藏弘教。印度传来的佛教给藏族的精神文化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藏文书写体系也深受梵文影响。
藏族通过藏传佛教,对周边地区的统治民族产生影响。元朝时的蒙古族上层,清朝时的满族上层,丽江地区的纳西族上层,都接受了藏传佛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化等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交融。
藏族与青藏高原上的门巴族、珞巴族、夏尔巴人等民族长期共同生活,交流密切。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就是出生于门隅的门巴族人。藏族用来记录藏语的藏文,也被不丹、锡金等地的人们用来记录自己的语言。
在甘青川滇藏交界处的藏彝走廊,分布着一些深受藏族影响的民族,大多在外使用藏语,在内使用本族语言,被大陆官方认定为藏族,如嘉绒人、木雅人等。
参考资料:
1、历史悠久
据考古发现,早在4000多年前,藏族的祖先就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生息繁衍了。
2、地域性和多样性
藏区以地域主要分为卫藏、康区、安多、阿里四地,各自的文化呈现不同的特色。以地理环境而言高地、平地、山谷、林区等所处的地域文化有所不同。以劳动产业不同而言牧区、农区、农牧结合以及少数的渔业区的文化不同。
3、完整性
藏族文化主要以藏族聚居的地域文化为主,解放前藏区处于几乎封闭的环境,保持着较完整的原始状态,保留着的文化较完整。
4、宗教性
藏区的文化几乎全部都跟宗教有关联或受宗教的影响,藏传佛教是佛教与藏区土生土长宗教“苯教”结合而成,因此它的宗教有一定的独特性。
藏族的史前文化特点
一、史前藏文化的本土特质
1、石器——狩猎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象征。
2、半地穴、圜地式房屋——藏族碉房建筑的源头。
3、石棺葬——远古藏族先民本土的丧葬习俗及宗教情怀。
4、大石遗迹——原始风俗及宗教现象的文化遗存。
5、岩画——远古藏族先民生活及精神的写照。
二、史前藏文化呈现出的多元性特点
三、史前藏文化是人类古文明的象征
1、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可以说明远古时代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具备了猿和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在藏族口承文学中,大量的藏族神话、民间故事和传说等,记录了史前藏族人民的思想意识、信仰观念、行为方式,以及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初始形态。
因此,考察史前藏文化的文明史,不仅可通过考古,也可通过对藏族民间文学作品的分析,从而总结出史前青藏高原历史文化的形态,说明在史前的生态环境和文化背景下,本土族人的物质、精神、制度三方面的传承和变迁的起始过程。
2、藏族文明史有5千年以上的历程。具有5千年历史的卡若文明、曲贡文明、象雄文明,以及雅隆部落文明正是以游牧、畜牧兼农业经济为主的,以既本土又多元的文化特性构筑了藏族5千年的文明史。
史前藏文化不仅具有悠久古老的历史,而且有着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是人类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民,在远古、在史前一直不断地创造着藏文化的远古文明,构筑了藏文化史前的本土性、多元性和变迁性。
西藏佛教,主要是密宗,或称为”真言宗“,藏族佛教徒念诵的主要是真言。比如六字真言、文殊心ZHOU、百字明ZHOU、药师灌顶真言……等等。另外也有上师口传的密法。虽然念诵的经文与汉传佛教有别,但藏传佛教的宗旨和义理,完全与汉传佛教相同。
传统观点认为,藏文是松赞干布时代由吞弥·桑布札仿照古代梵文创制的,距今约1300余年。然而,一些专家从目前的考古成果和史料记载中发现,藏族有文字的历史很可能早于1300年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负责人、副研究员赵慧民介绍,考古工作者曾在距今已有1275年历史的西藏朗县列山墓群中发现长1米左右的条形木构件,其上书有墨写的单个字母,字母与现代藏语中的元音字母相似,字体较为成熟。
赵慧民认为,木构件上的文字应该是区别吞弥·桑布札所创文字的另一种成熟文字,这证明早在吐蕃时期,藏族就有了自己的文字。
西藏文献中多有吞弥·桑布札创造文字的说法,而《善逝佛教史》记载:“参据蕃语实际,乃创三十字母及四元音”,这段记载似乎暗喻早在吞弥·桑布札之前,人们已经在使用一种“蕃语”了。
赵慧民推测,吐蕃王朝初期,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域生活的人们已经广泛使用文字,而且那时的文字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他还认为,藏文字母的发生、发展是勤劳、智慧的人们在长期大量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并非个人的伟大行为。早在吞弥·桑布札创造现今通用的藏文前,藏族文字可能就已发展到一定水平,到了吐蕃时期则在字体、文法、发音上经历了较大变化,后世人们出于“英雄崇拜”心理,才演绎出“创字”的说法。
与赵慧民有着同样观点的还有西藏著名民俗学家、西藏大学客座教授赤烈曲扎。据赤烈曲扎介绍,在西藏苯教徒撰写的大量史书中,藏文起源被认为距今4000年以前,当时人们使用一种叫“玛尔文”的文字。另外,象雄文也是西藏原始宗教苯教使用的文字,而据苯教典籍记载,苯教的创立至少已有8000年的历史。
他认为,“玛尔文”当时仅在王室成员间和祭祀中使用,由于缺乏群众基础而导致了该文字的最终消亡。松赞干布时期崇佛灭苯,几乎烧掉了苯教所有经文,使象雄文字成为千古之“谜”。
另据考古发现,吐蕃时期的石碑、敦煌出土的藏文史书、钟文中有很多文字与吞弥·桑布札创造的文字书写法不同。
赤烈曲扎说,如果吞弥·桑布札之前没有文字,那么仅靠口头相传,史书对吐蕃时代前苯教、42个部落以及松赞干布之前32代赞普的历史不可能记载得那么详尽。而且语言和文字的形成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吞弥·桑布札创字的说法“不符合社会发展的事实”。
青稞酒与藏族酒文化
以酒为载体的酒文化,源远流长,纷繁多彩,是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的杰出创造。一个民族的酒文化不仅是这个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一定反映,而且更充分体现了这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因而不同的民族大都具有各自独特的酒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以曲酿酒的国家,有着悠久灿烂的酒文化。生息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我国各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经过文化的交流、整合,逐渐形成丰富多姿的各自的民族酒文化。以青稞酒为主载体的酒文化,就是我国酒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绚丽的奇葩。
一、藏族酒史
一个民族的酒文化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酒俗、酒具、酒歌等文化表征,都建立在酒这一物质基础之上。因而一个民族的酒文化,实际是以造酒为发端的。
藏族造酒的历史,民间传说是从唐代文成公主把汉地酿酒术带到吐蕃时开始。但考诸史实,藏族造酒的历史应远比此早。众所周知,藏族是古代生息于青藏高原的若干民族和部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藏族的先民与我国汉文典籍中称为“羌”的民族系统有很深的渊源。羌,意为“西方牧羊人”,原是殷周时中原华夏族人对其西部地区的以游牧为主的民族部落的泛称。考古和文献资料证明,古羌人的最初生息地即在青藏高原,以后逐渐迁徒,分散形成许多的种落,有一部分改为从事农耕生产。古羌很早就创造了灿烂的高原文化,据有的专家考证,早在中原华夏人有麦种之前,古羌人已在高原上成功的培育出一种稞麦,即今藏族的主要粮食青稞。①羌族的一支神农氏后来进入中原与黄帝族相融合形成为华夏族。夏代开国的大禹,也是“长于西羌”②西羌的中心原在青海的河湟地区,公元前四世纪时受强秦之逼而向西南方迁徒,进入四川西北部和甘肃南部、青海西部和东南部,以及西藏等地,形成许多部落。到了南北朝和隋朝时,高原上已有苏毗、党项、白兰、吐谷浑、附国、嘉良、东方等较大的部族。当公元七世纪崛起于藏南雅鲁藏布江河谷的雅隆部落相继征服诸羌部,统一高原,建立强大的吐蕃王朝时,这些羌部中的许多羌人均被融合,成为了藏族。因此,藏族酿酒的历史应追溯到吐蕃王朝建立以前的古羌时期。古羌嗜酒,“饮食以酒、乳、牛羊肉为多。”③晋人王嘉《拾遗录》曾记一羌翁九十八岁仍嗜酒如命。羌人不仅嗜酒,而且很早就会酿酒。晋初善酿好酒的尚书张华,其酿酒所用,“蘖出西羌,曲出北朝。”④西羌人既有蘖,当已会造酒。《新唐书·党项传》记载党项人不事农耕,但“取麦他国以酿酒。”吐蕃统一高原过程中,除一部分党项人内徙外,留居原地都入于吐蕃,显然党项的酿酒术亦会入于吐蕃。《旧唐书·吐蕃传》记吐蕃旧俗有“接手饮酒”(《新传》作“手捧酒浆以饮”义同。)藏文史籍《王统世系明鉴》记松赞干布制定的吐蕃法律二十部中亦有“饮酒要有节制”的规定。可见早在文成公主入藏之前,吐蕃已有酒,并已能造酒。不过,此时吐蕃造酒尚未掌握中原地区先进的复式发酵法。《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中记载吐蕃贵族韦氏年老时惧自己死后子孙不能继续享受爵禄,因而设宴请松赞干布与其盟誓的故事。这个重大的宴会都仅“以半克青稞煮酒,捧献饮宴”。半克仅合七公斤,量是很小的。这种“煮酒”是用青稞发芽酿造的,颇似啤酒的制法,与后来藏族传统的青稞酒制法有很大不同。
公元641年唐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为唐蕃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开辟了道路。特别是文成公主为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不遗余力,不仅随嫁带去中原各种书籍、食品、工艺品,而且极力协助松赞干布学习先进的唐文化、技术和典章制度,推动吐蕃社会的发展。据藏文史籍记载,公主随带去的书中有“六十种讲说工艺技巧的书籍”和“各种食品、饮料配制法”,其中即有造酒的技术。公主还十分注意吐蕃农业和产的发展,专门带去了吐蕃所没有的蔓菁种子。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像《齐民要术》一类的农技书籍,亦必然在公主带进吐蕃的书籍之中。
但是,酿酒是一复杂的工艺,极不易熟练掌握。酿酒的成败和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操作人员的的经验。公主入藏九年后,松赞干布又向唐朝请派“造酒、碾、石岂 、纸、墨之匠。”可见当时吐蕃虽已输入内地酿酒法,但尚不能完全掌握。此后,随着唐蕃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藏,随带大批内地工匠;公元755年后吐蕃在占领陇右诸州、北庭和一度攻占唐都长安中,又俘获大批汉族工匠,内地先进的酿酒技术才逐渐被吐蕃所真正掌握。
必须指出,藏族古代社会中,并不像现在一样普遍饮青稞酒。事实上在吐蕃王朝时期,藏族饮用的酒的种类甚多。在敦煌出土的写于公元九-十世纪的《笨教殡葬仪轨书》中,人们所使用的酒类饮料有小麦酒、葡萄酒、米酒、青稞酒等五种。其中提到干布地区小王向吐蕃赞普奉献的“酿酒粮食”为“青稞、大米任何一种均可。”在一些藏文史籍中,还记载吐蕃佞佛普热巴金“饮米酒酣睡”,被臣下扼杀的事。⑤可见,在吐蕃王室和贵族中,当时比较盛行饮米酒。这一习尚,很可能是受唐之影响。众所周知,唐代饮米酒之风甚盛,宫廷中更是如此。现今西安宴席上必备的一种乳白色米酒,传即唐宫之酒。文成、金城公主入藏和吐蕃“豪酋子弟入(唐)国学”学习,势必将此风尚带入吐蕃上层社会。
吐蕃早在公元670年就占有西域的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并与波斯、大食、印度、尼泊尔等有交往,葡萄酒当即从西域输入,葡萄酒色红,而吐蕃人尚红,故葡萄酒在祭祀与宴饮中一度较盛行,在康区的三江流域(澜沧江、怒江、金沙江)酿制葡萄酒有很长的历史,《明实录》记载:洪武七年(1374年)康区谷日地方酋长以所造酒来献,其地“旧有造葡萄酒户三百五十家”⑥可见,这一藏区曾有酿制葡萄酒的专业户,而这些酒亦主要是供上层所需而生产的。
西藏东南部林区盛产蜂蜜,蜜酒是当地人很早就会生产的一种酒,藏文史料中说:“在工布地区,杂日山王曾于十五世纪向唐东杰布奉献过蜜酒和小麦啤酒。”⑦在藏族社会中蜜酒是较珍贵的酒,一般用于献于贵人。数量不多。
小麦是藏族主要粮食之一,量虽不如青稞大,但易采用内地传入的麦酒酿制法生产,故早期吐蕃多有酿制小麦酒的。
二、青稞酒及藏族酒俗
任何一种文化的整合,都经历了一个选择、适应的过程。一定的文化,都必适应于主生这个文化的社会经济基础。吐蕃社会饮酒的多样化,反映了吐蕃对外部文化的广泛吸收。吐蕃王朝在汲取外来的先进文化方面是十分开放的。据波斯文古籍《世界境域志》载,八世纪拉萨已有西域和波斯、印、缅商人。至于唐朝的手艺人、商贾、学者、僧人等更为数众多。佛教文化、儒家文化及本地的土蕃文化彼此激烈竞争,佛教的印度中观派与汉地的禅宗也互争短长。在这样的氛围中,西域的葡萄酒、内地的米酒被作为“时髦”饲料而流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藏区平均海拔三千公尺以上,干寒,无霜期短,除极少数地区可产稻米外,绝大部分地方不产米。吐蕃强大时期占有陇石和川滇的一些地方,有较多的米源,但当吐蕃于九世纪崩溃后,已不能再从这些地方获取稻米。米酒的酿造便难以为继。同样的原因,西藏产葡萄之地不多,葡萄酒自吐蕃失去对西藏的占领后,来源亦日趋减少。自产量十分有限,只能供上层享用。小麦虽藏区多有栽种,但产量远较青稞为少。这样,以青稞酿酒,便自然而然成为藏族人民普遍采用的制酒方式。青稞酒亦成为藏族酒文化的主载体。
前已述及,早期青稞酒的酿制是先将青稞(大麦的一种)发芽,经糖化后加入酵母菌(蘖),使其酒化而成酒的。自内地的复式发酵酿酒法传入后,青稞酒的酿法已类似内地黄酒的酿法。关于青稞酒的酿造法,著名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有非常生动具体的描绘:
要说酒是怎样造,造酒先要有粮食。
青稞用来煮美酒,花花的汉灶先搭起,
铜锅用毛布擦干净,青稞放在铜锅里。
倒入清洁碧绿的水,灶火膛里火焰升。
青稞煮好摊在白毡上,再拌上精华的好酒曲。
以后酿成好美酒,一滴一滴滴进酒缸里。
酿一年的是年酒,年酒名叫甘露黄。
酿一月的是月酒,月酒名叫甘露凉。
只酿一天的是日酒,日酒取名甘露旋。
学术界认为《格萨尔王传》的产生年代不早于十一世纪或十三世纪前后,以后在流传过程中继续增补而成。因而,它反映的藏族古代社会多为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社会生活情况。我们从中可知,至少在那时酿酒原料已是青稞,其酿法亦完全是复式发酵法。
近代由于藏族的发展和汉藏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加强。藏族青稞酒的酿制技术和所酿酒质均有所提高,首先是用曲方面已绝少用自制的土曲,多采用内地输入的质量较高的酒曲。其次,在控制酿造温度方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近代康区藏族酿酒,煮好青稞后,“晾干放凉,和以曲末,入釜中,以青稞麦桔杆覆之,数日酿成,渗水入釜沃之,便得多量之酒。”⑨复式发酵法是糖化与酒化同时进行,但二者对温度的需要却相互矛盾,高温对糖化有利,但却对酒化不利,易于导致酒酸败。青稞酒质量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要让其酸味减至最小最小。藏族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掌握了把煮好的酒粮晾干放凉,再入曲酿制的低温投缸法,能使温度慢慢升高,容易控制,避免杂菌入侵,达到对糖化、酒化均较有利的酿造条件。在酒的酸度和出酒率方面均较前为优。现代藏族家庭所酿的青稞酒,一般能达到15~20度,味微酸而回甜,性平和,不燥烈,男女老幼均能饮用。
上面所说的酿法,多用于宴会等用酒量较大的时候。至于平常藏民家中自饮的酒,则多是将青稞煮好后,晾晾,和入曲末,然后装入特制的木桶或陶罐中,用泥封口,盖上一些毡垫、皮袄或麦杆。两三天后放封,渗入一定数量的清水,再封好,等一两天之后,酒便酿成。只要拔去桶下的木塞,就有清冽的青稞酒流出。
在藏区东部一些喜饮“咂酒”的地方,还有一种“干酿”法,即酿制青稞酒时先不渗水或渗少量的水。在“吃咂酒”时,才从上而冲入温开水,饮酒的人将竹管(或麦管)插入酒罐的底部,便能吸到酒。这种酒可随冲入水的速度大小、数量多少而调节其浓淡。
由上述可知,青稞酒的酿造法基本是学自祖国内地的黄酒酿法,但藏族人民在长期的酿酒实践中,又融入了民族的、地区的特点,以使其更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和民族习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青稞酒既是汉藏文化交流的结晶,又是藏族的创造。
青稞酒藏语呼作“酉仓 ”(chang),藏语康方言呼为“穹”(chong)。我国古代习惯泛称酒为“酿”。“ “酉仓 ”与酿音极近,可能即“酿”的借词的音变。清代以来一些汉文书籍中常将青稞酒称作“蛮冲酒。”“蛮冲”实际“穹”的音译。青稞酒酿造过程要冲水,青稞酒是用麦管、竹管吸咂,故又称为“咂酒”。
青稞酒对于藏族来说,是喜庆的饮料,是欢乐、幸福、友好的象征。绝非“消愁”之用品。藏族豪放、热情,男女老幼均爱好喝青稞酒。但长期的佛教思想的影响,又使藏族人养成了“饮酒有节制”的传统,平时一般是不随便酒的,但在喜庆、欢乐的时候,则总是要饮得来酣畅尽兴方休。因青稞酒性平和,吃醉的人较少的。尽管有饮醉者,藏族绝少有酗酒者。
藏族的婚礼中离不开青稞酒。提亲时要带上“提亲酒”,女方如允则要同饮“订婚酒”;迎新娘时,半途要设“迎亲酒”,新娘辞家时要饮“辞家酒”;婚宴中要共饮“庆婚酒”。
藏族极好客,对客人敬上一碗青稞酒,是表示主人好客之心如酒力一般热烈,友情如酒味一样浓厚悠长。
藏族过年过节都要饮青稞酒,以示庆祝。就象汉族大年初一早上吃汤元,以祝全家这一年团园、园满一样,藏族大多地方都在年初一早上喝八宝青稞酒“观颠”(将红糖、奶渣子、糌粑、核桃仁等放入青稞酒合煮的稀粥样的食品)。以祝全家新年中丰收、幸福、吉祥。
青稞酒具有罈、壶、碗、杯等,以杯、碗盛饮为普遍。西藏仁玉县的绿玉酒壶、酒碗、酒杯是珍贵的藏族酒具,畅销于各藏区。江西景德镇的彩绘小龙瓷碗也是藏族普遍使用的酒具。其余多为木质酒具。就罈饮酒是在喝咂酒时,其饮法是,先烧开一大锅水,放在火塘边温着,然后将一罈酿好的青稞酒插入两支或数支竹管(或麦管)放在火塘边的客位上,客齐后,主人先请最年长的客人坐于酒罈边,诵经和以指拨点酒洒向四方后,即开始饮。饮时请另一位或几位年长客人与先前那位长者对坐,各吸一根竹管,主人掐起一瓢水慢慢从罈上部浇入,水流经罈中已酿熟的酒粮而浸入罈底便成为酒了。竹管深插在罈底,故吸酒而不会吸入糟。第一轮酒毕,又以长先幼后的顺序换上另一轮客人。主人始终在旁渗水,一罈酒吸出已无味时,又新换上一罈。
藏族善歌舞,饮青稞酒时少不了唱酒歌、跳锅庄。歌助酒兴,舞借酒力,这样方饮得淋漓酣畅。
青稞虽然受到藏族人民的普遍喜爱,但由于其至今仍停留于家庭手工酿造水平,消费上亦是自酿自用,未能成为商品而流通。因而其酿制技术难以提高,消费范围也有很大局限。藏族牧区因不产粮食,过去饮用青稞酒都是从附近农区的人家手中以畜产品交换。由于交通不便,藏族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和青稞酒不能长时间保存等原因,藏族牧民得到青稞酒颇不易因而牧民饮青稞酒的数量大大少于农民和城镇人。近代以来汉藏贸易有较大发展。许多牧民已习惯购买汉地输入的白酒、啤酒来取代传统的青稞酒。
另一方面,由于青稞酒技术沿袭家庭祖辈口传身授的方法,各家所酿质量有较大差异,一家几代人所酿也往往悬殊很大。加之设备简陋、缺乏现代检测手段,只能依靠个人经验来掌握,酿制质量难以稳定,时有失败。因而现今一些家庭的青年一代已不太愿费时费力的自酿酒,转而以啤酒之类的性味极近似青稞酒,而又随时可以方便购得的商品饮料来替代。传统的家酿青稞酒技术有面临失传的危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藏族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面临日益增长的藏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青稞酒势必只有走出家庭酿制的窠臼,转入现代化工业生产,方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目前拉萨已有现代的青稞酒厂,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现代化生产的青稞酒也将会崛起于高原。
藏传佛教与藏族酒文化
众所周知,藏族是几乎全民信仰喇嘛教(藏传佛教)的民族,宗教深入社会的各个方面和人的心灵深处。因此,有人把藏族文化称之为“佛教文化”或“喇嘛教文化”。但是从酒文化来看,藏族文化实际上并非全属佛教文化范畴。佛教是主张“出世”的,它要求人们戒除“三毒”(贪、嗔、痴),摈弃一切欲望和追求,皈依于“三宝”(佛、法、僧)。饮酒作为一种物质欲,无疑是应当摈弃的。酒还易“乱性”,影响修行的虔诚,佛教入门的最初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语、不饮酒)即要求戒酒。因此酒与佛教本当是不相容的。但奇怪的是笃信佛教的藏族人民都喜爱饮酒。深受佛教影响的藏族社会都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酒文化。
为什么在藏族社会中佛教文化能与酒文化并行不悖共同发展呢?我们知道,佛教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宗教。就象佛教传入汉族地区后,为适应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环境,遂吸取儒家文化,发展形成了禅宗这样的佛教宗派一样,佛教自七世纪传入西藏后,亦经过三百年左右的适应过程,形成了融藏地原有的土著的宗教笨教与佛教中的带有藏区特色的佛教喇嘛教。中其教义、经典仍是佛教,但在某些仪轨和神祗方面都来自笨教,而且在修习上偏重于密宗。自元代开始,喇嘛教不仅在宗教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取得在藏区的统治地位。出现了政教合一制度。“出世”的僧人却管理尘世纷繁的事务,卷入政治的勾心斗角之中,这本身即与佛教宗旨相矛盾。但喇嘛教的领袖却能处之泰然,自圆其说,因此,它能包容酒文化,并让它发展,就无觉为怪了。
酒,“天之美禄也”。“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⑽藏族居住地区大都自然条件严酷,高寒多风。藏族社会由于长期停滞于封建农奴制阶段,生产力低下,人民的物质享受处于相当低的水平。由于物质贫乏,人们的嗜好亦极少。酒作为自古传下的一种生活品,不仅能增加藏族人民抵御劣气候的能力,更能给生活增添丰采和乐趣。尽管茶是藏族的第一饮料,但茶作为糌粑、酥油相伴的生活必须品,实际上成为了主食品。酒在诸如喜庆场合作为一种烘托气氛的饮料,亦是茶所不能取代的。藏族人民笃信佛教,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热爱生活,追求幸福。适度的饮酒并不影响他们对佛教的敬奉。因此,佛教在藏族社会的传播过程中,不能不对藏族人民传统的饮酒习惯表示某种认同。另一方面,世俗的上层亦有饮酒的嗜好,佛教要取得他们的支持,亦不能不迁就他们。在一份古代藏族文学作品《茶酒仙女》中把茶和酒分别作为高僧大德和国王、大臣各自的理想饮料,并说:国王和大臣们饮了酒,“智谋会象春潮澎湃,荣耀如旭日东升”;将军和勇士喝了酒,“胆量会象烈焰腾空,入阵时如同猛虎下山。”而茶则适宜高僧大德饮用,“使他们神智清醒,勤奋修行,增进智慧。”⑾这种把世俗与宗教人员相区别的态度和对酒的功用的肯定,反映了喇嘛教对酒及酒文化的现实主义态度。
当然,由于佛教戒酒,藏族在向神佛教敬献和祭祀时是不能用酒的,而是以净水代替。这与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习惯以酒作祭祀品是不同的。
应当特别说明,喇嘛教僧人实际上也并不都是戒酒的。在一些宗教书籍内,反而对饮酒的事津津乐道,承认酒对修行者有所脾益。如著名的《米拉日巴传》中写道:米拉日巴的师父、喇嘛教噶举派(白教)的祖师玛尔巴不仅自己爱饮酒,还叫米拉一起喝。后来米拉在深山苦修,节制饮食,却一直不能“摄界归脉”。一天吃了妹妹送来的酒和未婚妻送的美味食物后,功夫陡然大进。打开师父所赐的秘卷一看,才知道修行到一定程度后,“要全靠好饮食”“多少喝一点酒”,才能把全身脉结打开,生出乐、明、无分别的境界,到达“涅槃”。米拉由此领悟到修习最上乘的密宗,要“以妙欲为道”的奥义,终成正果。
由上述可知,喇嘛教最上乘的密宗是允许饮适量的酒的。酒对修上乘密宗的僧人是一种“方便”(即手段)。事实上许多密宗大师都是饮酒的。著名的喇嘛教宁玛派(红教)祖师莲花生就是个极爱饮酒的僧人,传说他曾在一个酒店连饮了七天七夜。
不仅以密宗为主的宁玛、噶举等派饮酒,就连以“戒律精严”“着称的喇嘛教格鲁派(黄教),亦有僧人饮酒的”。如六世达来喇嘛仓央嘉措便是“耽于酒色”的。但虔诚的宗教徒们并不因此而减少对他的尊崇。就是创立格鲁派的宗喀巴,也“认识到最好是强调饮酒和吃肉的象征意义。因为,否认它们的价值只会使自己在追求的范围内达到有限的目的。”⒀因为藏族的主食品是肉和粮、乳。在广大的牧区更以肉、乳为粮,故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喇嘛教,虽然反对杀生,都不得不吃肉,否则即难以生存。这种情况极好地说明佛教的社会适应性。在某种情况下,它不得不迁就于所处的环境,即使社会使其与某些戒律相悖。一位著名的格鲁派僧人,曾任塔尔寺住持,并且是十四世达来的哥哥的土登美诺布活佛对此有一精彩的阐释:“吃肉本身并不是坏事。要说坏的话,就坏在你心里的想法:如果你认为吃肉是件快乐的事,那你就是以索取别的生命来寻欢作乐,这就成了坏事了;如果你吃肉仅仅是因为没有别的食物,或没有肉吃就难以维持生命,那就不是坏事。”⒁推及于酒,也是同样道理,在某种非吃酒不可的环境时,饮酒亦不算是坏事,只要不影响对信仰的坚定。当然,对藏区来,酒毕竟与肉在“生存必需”这点上,不能相比。因而格鲁派戒律,不戒吃肉,但仍戒酒,僧人饮酒的事例是极少的。
还要指出的是,佛教的四大“根本戒”中并不包括戒酒(四根本戒即入门五戒中除酒以外的四戒)。可见酒并非在佛教深恶痛绝之列。只不过对出家人加以酒戒,防止其贪杯乱性,不能致志于修行,对于广大的信教群众来说,仅要求信仰教义,并不苛求戒律。自然在四根本戒之外的酒戒更不会施之于群众了。因而,尽管寺庙中戒酒,民间的造酒、饮酒照样兴盛发展。事实上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兼容和涵化,使得藏族的酒文化更具特色。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L A怀特有一句名言:“文化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⒂藏族的酒文化正是在满足雪域高原人们的需要中诞生、形成的。它也必然会随着藏族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需求的提高而向前发展。
藏族的起源如下:
1、藏族,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古老成员之一,分布在西藏、青海、甘肃、 四川、云南等省、区,有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藏区已发现和发掘出新旧 石器时期和铜石井用时期等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遗址多处。1979 年,考古发掘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是距今四五千年的历史遗址、在聂拉 木、定日、申扎、林芝、墨脱等地区也发现和发掘了不少古文化遗址。说明 西藏地区在七千年至两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
青海、甘肃等 地区发现的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新石器及彩陶文化遗存物。阿坝州 境内已发现的古人类生活居住过的聚落文化遗址就有19处,其中有的 属新石器时代至汉代文化遗址,有的愿唐宋时期的文化遗存;古墓葬类, 则有石棺葬、砖室墓、石室墓、屋基、大石墓、灵塔等多种形式文化遗存。 古籍史料中所载的“累石为室,高至十余丈”的“碉楼”建筑,至今可见
2、嘉绒在州内金川、小金、马尔康、理县、黑水和汶川部分地区,以及甘孜州、雅安地区、凉山州等地,居住着讲藏语方言嘉绒话,并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藏族,为嘉绒藏族,藏区称这地区的藏民为“绒巴”(农区人)。“嘉绒”一名因嘉莫墨尔多神山而得名,意指墨尔多神山四周地区。
3、据汉文史料记载,古代生息、活动于今州境地区东南部河谷一带, 称之为“嘉良夷(嘉梁)”、“白狗羌”、“哥邻人”、“戈基人”等部落,为这一地区的土著先民。唐时与吐蕃移民及驻军融合后,成为藏族。嘉绒地区解放前的地方土官常说自己的祖先来自西藏,汶川县境内的瓦寺土司、金川县境的绰斯甲土司、雅安地区宝兴县境的穆坪土司等都有渊源于西藏的族谱记载。杂谷土司、梭摩土司祖先是唐代吐蕃大将悉坦谋。
4、《安多政教史》载:“多麦南北的人种大部分是吐蕃法王(按:指松赞干布)安置在唐蕃边境驻军的传人,……”。在公元5—6世纪时,嘉绒地区人户很少,为措巴首领割据称雄时期。7世纪初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吐蕃,嘉绒地区也统一于吐蕃之中,由赞普的将领充任嘉绒各地首领。
嘉绒地区在《安多政教史》一书和讲藏语安多方言的藏民中称‘查柯”。其因是:“历史上吐蕃赞普曾派遣大臣柯潘前来嘉练地区担任首领和武将,他的官邸在松岗以北,吐蕃王室在圣谕和公文中称他为‘嘉木查瓦绒柯潘’或‘查瓦绒柯潘’,简称‘查柯”’。柯潘是从西藏四大家族之一的扎族中招募来大批士兵的指挥官,主管唐时吐蕃的“西山八国”。
5、 古代称之为“嘉良夷”、“白狗羌”、“哥邻人”、“戈基人”等的“羌、氏、夷”部落,实为“皆散居山川”的土著居民。在吐蕃第九代赞普布德贡甲时期,即大约东汉顺帝时期(126年),吐蕃地区的原始宗教——本波教,就由吐蕃传入了州境,并逐渐兴宏起来,吐蕃文化的传入和对嘉绒藏族古代先民的影响始自东汉,佛教则晚于8世纪吐蕃王朝赤松德赞时期才在州内发展起来、由于宗教文化为中心的吐蕃文化的长期影响。
佛教(早期是本波教)逐渐成为上述部落全民的信仰,加上吐蕃大量移民和军事占领与统治,经过一千多年的融合、同化,与吐蕃长期的相互交往,从而形成今日统一的嘉绒藏族。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汉藏两种文字的作家比翼齐飞,涌现出了擦珠·阿旺罗桑、江洛金·索朗杰布、高平、汪承栋、杨星火、徐怀中、刘克等诗人与小说家。他们的作品里呈现的是一个时代的变迁,记录了西藏社会、经济、思想观念发生的深刻变化,成为了映射一个时代发展的一面镜子。作家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讴歌者,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抒写了青年人建设新西藏的豪情壮志和他们的爱情生活,反映了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社会变革;刘克的小说《央金》《曲嘎波人》《嘎拉渡口》等,歌颂了党和人民解放军与西藏人民的血肉关系。开启了当代西藏文学的先河。
民族作家走向创作前台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益西单增创作的长篇小说《迷茫的大地》《幸存的人》的问世,使西藏文学得到了全国的关注,益希丹增的长篇小说《幸存的人》获得了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长篇小说奖。这一时期西藏文学的最大特色是民族作家走向文学创作的前台,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具有较大反响的作品,班觉的《绿松石》、扎西班典的《明天的天气一定会比今天好》、旺多的《斋苏府秘闻》、德吉措姆的《漫漫转经路》等,其中《绿松石》获西藏自治区优秀创作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长篇小说奖,《明天的天气一定会比今天好》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他们的作品里呈现了旧西藏的黑暗,农奴的悲惨生活;解放后的藏族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韧性。这些作品紧贴西藏的现实生存背景,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摹了社会政治生活变化,在作品内蕴上显现了藏族文学独特的民族风貌。真正让藏族文学成为一个重要力量,被我国文坛所重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因扎西达娃、马原、色波、通嘎等人对文学叙事的不断探索与创新,使得藏族文学迈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沿阵地。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马原的《叠纸鹞的三种方法》《喜马拉雅古歌》,色波的《竹笛·啜泣和梦》《圆形日子》等作品显现了极强的先锋勇气。洋滔、加央西热、闫振中、诺杰·洛桑嘉措等诗人,在诗歌领域内的“雪野诗派”创作独树一帜,引起了国内诗歌界的关注和认可。马丽华的大型纪实散文《走过西藏》《灵魂像风》《西行阿里》等也为西藏文化热推波助澜,对推动西藏文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时期的西藏文学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和青春活力。
藏族的相关资料?
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