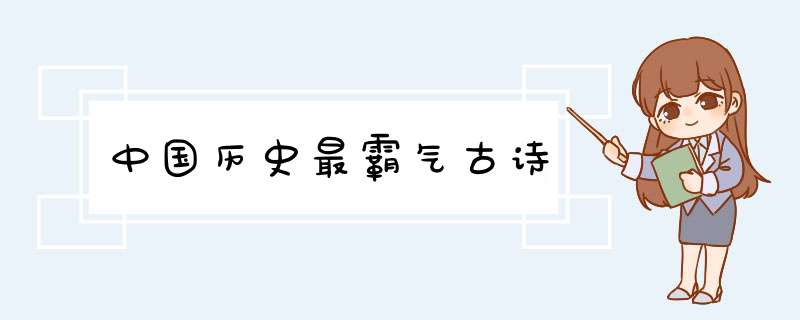中国古代提到天文学的典籍是哪一本著作

我国古代天文学有非常高的成就,自然会有浩如烟海的专著。提问中特制某一本著作,是不合理的。
就我一名理科生浅薄的见解,至少有以下几类:
《二十四史》对天文志,五行志,律历志等等。当然,名字可能会略有不同,比如大名鼎鼎的《史记》的天文志就叫做《天官书》。
天文历法专著,古代历法精度有限,一般用上十几二十年就要重修。比较有名的往往是在历算中有所突破的精品,比如《三统历》、《乾象历》、《皇极历》、《大衍历》等等。
天文星占著作,最有名的是两部,《甘石星经》和《开元星占》,诚然其中很多占卜的内容今天不值得提倡,不过其中对于星表的记录,五行的运动规律这些资料是弥足珍贵的。
天文仪器的使用注释,比如汉代的《浑天仪注》,宋代的《新仪象法要》,清代的《灵台仪象志》都是比较有名的。
科学专著,比如沈括的《梦溪笔谈》就有不少涉及天文学或者天文仪器的内容。
类书,类似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之类的官修大类书不可能没有天文学的内容。
那叫蟒袍
蟒袍
蟒袍,又被称为花衣,因袍上绣有蟒纹而得名。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蟒袍,一名花衣,明制也。明沈德符《野获编》云:蟒衣,为象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趾)耳……凡有庆典,百官皆蟒服,於此时日之内,谓之花衣期。如万寿日,则前三日后四日为花衣期。
《钦定大清会典》卷四十七:蟒袍,亲王、郡王,通绣九蟒。贝勒以下至文武三品官、郡君额驸、奉国将军、一等侍卫,皆九蟒四爪(趾)”。文武四五六品官、奉恩将军、县君额驸、二等侍卫以下,八蟒四爪(趾)”。文武七八九品、未入流官,五蟒四爪(趾)”。
封建社会的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朕即国家,一言九鼎,因此,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具有征信作用的皇帝宝玺,尤其是国宝,则是这种最高权力的标志。清朝政权作为中国封建制度最后也是最高阶段的政权,曾大量吸收了历代统治方略的精华,其中也包括国宝制度。综观清代国宝制度,既有满族统治的特点,也有对前代制度的继承。前者如御宝宝文中增加了满文,后者如御宝数目及宝文内容等。清代国宝制度从肇始、确立到消亡,也正是清朝统治由盛到衰的过程。 清代的国宝始制于满洲入关以前。努尔哈赤时期只有一方“天命金国汗之印”,皇太极天聪年间也是一方老满文的“金国汗之印”,至1636年皇太极国号改“大清”,改元“崇德”时,见于记载的国宝起码有“皇帝之宝”等五种(见皇太极国宝五种),此时清代国宝已初具规模。 顺治元年(1644),清室定鼎燕京(今北京),清朝许多国宝应是在这一时期创制的,但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康熙二十九年(1690)《钦定大清会典》修成,其中记载当时共有御宝二十九方(参见康熙朝《钦定大清会典》载御宝二十九方),与皇太极时期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至雍正五年(1727)重修《钦定大清会典》时,所载的国宝数目及内容仍然没有变化。可知康熙至雍正年间清代国宝制度相对稳定,为乾隆皇帝重新厘定国宝奠定了基础。 乾隆帝认为皇帝治理天下,应充分重视国宝的征信作用,制定一套严密的制度,对皇帝行使最高权力标志的国宝的宝文、形制、保管、使用等做了基本规定。乾隆十一年(1746),针对过去对国宝记载失实、宝文重复、用途不明、认识错误等情况,乾隆帝对交泰殿所藏的前代三十九方国宝重新考证排列,将国宝总数定为二十五方(参见二十五宝玺),仍旧贮存在交泰殿中,并制成宝谱,以流传后世。 乾隆厘定二十五宝之后,剩下的十四方御宝中,有四方乾隆认为“于义未当”,其余十宝送到盛京皇宫中珍藏,这就是“盛京十宝”。这十方御宝于乾隆十一年(1746)入藏盛京皇宫凤凰楼,乾隆二十七年(1762)又对盛京十宝作过一次调整,将“丹符出验四方”改刻为“制诰之宝”,改刻原因则史载不详。 另外,在故宫藏品中,有四方檀香木交龙纽宝玺,皆汉文篆书,制作的年代当在光绪末宣统初年,似应钤用于新政或立宪后向中外颁发的文书上,但迄今为止还未发现钤用以上诸宝的文件。抑或是预先制作,还没有来得及使用,预备立宪便宣告破产,这些御宝也就被束之高阁了。故将其列入清代国宝的范围。
碧玉盘龙纽“皇帝奉天之宝” “皇帝奉天之宝”,清早期,碧玉质,盘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玺书体。面14cm见方,通高152cm,纽高115cm。附系**绶带。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交泰殿宝谱》记此宝“以章奉若”之用,以示皇帝对上天的尊崇和礼敬。但这只是一种象征,实际上,迄今还未发现钤盖此宝的档案文书,表明此宝极少使用。关于此宝的含义,乾隆帝在乾隆十一年(1746)厘定国宝时曾有过如下考辨:“至谓‘皇帝奉天之宝’即传国玺,两郊大祀及圣节宫中告天青词用之,此语尤诞谬。大祀遵古礼,用祝版署名而不用宝。圣节宫中未尝有告天事,或道箓祝厘时一行之,亦不过偶存其教耳,未云命文臣为青词,亦未尝用宝。且此玺孰非世世传守,而专以一宝为传国玺,亦不经。盖缘修《会典》诸臣,无宿学卓识,复未曾请旨取裁,只沿用明时内监所书册档,承伪袭谬,遂至于此。”指出康熙朝和雍正朝《大清会典》对此宝的认识错误及其原因,并最后将其确定为敬天之表征物。乾隆十三年(1748)诏改玺印中的满文本字为满文篆书时,该宝未改刻而保持原貌。 金交龙纽“大清嗣天子宝” “大清嗣天子宝”,清早期,金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本字。面79cm见方,通高76cm,纽高5cm。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也是清代二十五宝之中唯一的一方金质宝玺。《交泰殿宝谱》记此宝为“以章继绳”之用,是皇位传接承递的象征。但实际上却很少使用,只在宫中殿堂内的御笔匾额上偶尔钤用。乾隆十三年(1748)诏改玺印中的满文本字为满文篆书时,该宝同样被乾隆帝认为是“先代相承,传为世守”的旧物而未被改刻。 栴檀香木盘龙纽“皇帝之宝” “皇帝之宝”,清早期,栴檀香木质,盘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篆书。面155cm见方,通高166cm,纽高11cm。附系**绶带。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是清代二十五宝之中唯一的一方木质宝玺。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为“以肃法驾”之象征物,故凡清帝行围及驻跸圆明园或避暑山庄时,都要以这方“皇帝之宝”随驾。此外通过对清代皇帝诏令文书中宝玺使用状况的统计分析表明,二十五宝中用得最频繁、范围最广的也是这方木质“皇帝之宝”,诸如皇帝登基、皇后册命、皇帝大婚、发布殿试金榜及其他重要诏书上均钤用此宝。可以说此宝是清朝皇权的重要标志,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白玉盘龙纽“皇帝尊亲之宝” “皇帝尊亲之宝”,清早期,白玉质,盘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篆书。面68cm见方,通高61cm,纽高43cm。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据《交泰殿宝谱》,用此宝“以荐徽号”,主要是为前朝后妃上徽号或尊号时钤用。据《大清会典》记载:“凡加上尊号、徽号,册立皇后、皇太子,册封皇贵妃、贵妃、妃、嫔……其应给纸册诰命,中书科缮写,送阁用宝。”其中的加上尊号、徽号时所用之宝就是“皇帝尊亲之宝”,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记载上徽号情况的清代档案中也钤盖有此宝。 青玉交龙纽“制诰之宝” “制诰之宝”,清早期,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篆书。面13cm见方,通高147cm,纽高85cm。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据《交泰殿宝谱》,用此宝“以谕臣僚”,但实际上多是在册书或诰命上钤用。按清朝定制,覃恩封赠五品以上官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则颁发诰命,诰命因发放的对象不同名称也不同,官员本身受封称为“诰授”,封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生者称“诰封”,死者称“诰赠”。但不管是“诰授”,还是“诰封”、“诰赠”,都要钤盖“制诰之宝”。据《大清会典》记载:“凡给功臣世袭罔替诰命,分别世次敕书,由该衙门开载功绩,移送内阁,交中书科缮写,送阁用宝,仍行该衙门给发。其子孙承袭时,令该衙门将原给诰敕送阁,中书科填写承袭人名年月,仍送阁用宝。”这里所用之宝,绝大多数是这方“制诰之宝”,此宝是二十五宝中使用较多的一方。 碧玉交龙纽“敕命之宝” “敕命之宝”,清早期,碧玉质,交龙纽,汉文篆书满文篆书。面113cm见方,通高9cm,纽高55cm。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据《交泰殿宝谱》,用此宝“以钤诰敕”,而大部分是在敕书上钤盖。清代的敕书分为敕命和敕谕两种。敕命用于敕封外藩、覃恩封赠六品以下官员及世爵有袭次者,为卷轴形式,六、七品二轴,八、九品一轴。敕谕则有敕任官员、敕谕臣民、敕封或谕告外藩之别。敕书最后都要书明颁发年月日,并加盖“敕命之宝”。 “敕命之宝”是二十五宝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方。 金交龙纽“天子之宝” “天子之宝”,清早期,金质,交龙纽方形玺,满文篆书。面119cm见方,通高83cm,纽高51cm。附系**绶带及牙牌,牙牌两面分书满汉字“天子之宝匮”。 “盛京十宝”之一,用于祭祀祖先及百神。据《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崇德八年(1643)十二月二十八日遣大臣阿拜代祭清帝列祖,其祭文中钤有“天子之宝”,所钤极有可能就是这方宝玺,制作当在清太宗崇德时期。此宝的交龙纽及满文篆字的印文风格也与这一时期的金质“奉天之宝”一致,是清前期十分重要的典章文物。 墨玉交龙纽“奉天法祖亲贤爱民”玺 “奉天法祖亲贤爱民”玺,清早期,墨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玺书体。面156cm见方,通高98cm,纽高49cm。附系**绶带及牙牌,牙牌两面分书满汉字“奉天法祖亲贤爱民宝匮”。 “盛京十宝”之一。据成书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当时共有御宝二十九方,其中内宫收储六方,内库收储二十三方。此方“奉天法祖亲贤爱民”宝即为内库收储者之一,其制作当在康熙二十九年之前。 白玉盘龙纽“大清受命之宝” “大清受命之宝”,清崇德,白玉质,盘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本字。面14cm见方,通高12cm,纽高82cm。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位列二十五宝之首。据《交泰殿宝谱》所记为“以章皇序”之用,即表明清王朝受天之命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又据乾隆帝《交泰殿宝谱序后》,此宝原是太宗皇太极以来“先代相承,传为世守”的旧物,故乾隆十三年(1748)诏改玺印中的满文本字为满文篆书时,该宝得以保持原貌。其材质洁白温润,盘龙纽线条简洁流畅,技艺纯熟,显示出清前期玉石雕刻的水平。 檀香木交龙纽“大清皇帝之宝” “大清皇帝之宝”,清晚期,檀香木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56cm见方,通高98cm,纽高49cm。附系**绶带。黑漆木匣承之。 光绪末年到宣统年间,新政与立宪成为国家政局的一大至要。清政府国家机构围绕着君主立宪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制度的转化。光绪三十四年(1908)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明确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此方“大清皇帝之宝”便制作于这一时期,似应钤用于新政或立宪后向中外颁发的文书上,但迄今为止还未发现钤用的文件。而此宝本身也无使用痕迹,刻宝时所着墨迹如初,抑或是预先制作,还没有来得及使用,预备立宪便宣告破产,故而被束之高阁。
在康熙、雍正两朝《大清会典》及记事截止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中,北京僧录司的僧官职位只有上述“八座”。再看《清朝文献通考》与《清朝通典》。根据它们的《凡例》,前者于“乾隆十二年奉敕撰”,后者是“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但均未说明记事的截止时间。不过,在《清朝文献通考》中有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资料,而《清朝通典》中有乾隆四十八年(1783)乾隆帝幸金山的详细记载,并且《清朝通典》中还有如下按语:“臣等谨按:乾隆五十一年,皇上巡幸五台,恭俟续纂寸敬载,谨识于此”。据此,可以认定这两本书的成书时间已到了乾隆末年。这两本书关于北京僧录司僧官的记载也没有正印、副印之说,而记事截止于嘉庆十七年(1812)的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中,却赫然有了正印,副印二职:“-京师僧官曰僧录司,正印一人,副印一人。左右善世二人,阐教二人,讲经二人,觉义二人……]”这样,正印、副印产生时间的下限可以确定在嘉庆十七年(1812)。不过,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的一条资料值得注意。乾隆四十一年(1776)奏准: “裁道录副印一缺”。清王朝对佛、道二教的管理措施相同点很多,在僧、道官的设置上也不例外。既然当时道录司有了副印一职,北京僧录司同样应该如此,这种推论站得住脚。不过,这里涉及的毕竟是道录司副印,而且该资料并不载于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所以确定正印、副印产生的下限时间仍需其他旁证。根据上述《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的记载,似乎可以得出结论:正印、副印产生时间的上限应当在乾隆末年。不过,这种说法可能有误,因为正印、副印不载于上述史籍并不能证明它们成书之前该僧职就一定没有出现。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现实中出现了正印、副印,而史籍的记载滞后。
古籍蝴蝶装订方法图解如下:
1、把打印好的小册子对折起来,一个对折叫做一台,一本书可以分为好多台,这里我把5张A4纸对折成一台,厚度比较合适,可以根据纸质的不同,尝试把不同张数的纸对折为一台。如下图:
2、把每台折页均匀的打上六个小孔,以方便穿针。对了,还需要折叠两个“蝴蝶页”,也叫“衬页”。我用的的厚一些的纸,比较结实,也都打好孔。如下图:
3、以蝴蝶页为最下面一台开始穿线。像图示一样,留出一个绳套,装订下一台的时候,针线需要穿过这个绳套。末尾要留出一段线绳。如下图:
4、像图示穿线一样,装订下一台。把线绳拉紧,在末尾打结,这样两台折纸就装订紧了。如下图:
5、打结之后穿入第三台,像前面一样穿线,但是从孔里穿出后,要穿过下面两台之间的锁线处,在穿回孔里,像下图这样。
6、每台都装订好后,到末尾线绳穿出以后,穿过下面两台之间的锁线处,然后打结,再穿过下一台的锁线处,再打一次结,就可以了,如果书籍比较厚,可以以此类推,多打几次结。如下图:
7、装订好以后,先下图一样,涂抹白胶,沾上纱布,再沾上和纱布同样大小的衬纸。等胶水干了以后,可以用壁纸刀,把书边裁切整齐。如下图:
8、接下来准备硬纸板和牛皮纸,准备制作硬书壳,如果有条件,也可以用布料和皮革来制作书皮,可以尽情发挥想象力,制作自己喜欢的风格,当然前提是比较结实、耐用。如下图:
9、涂上白胶,将书皮和硬纸板粘结实。把前后蝴蝶页跟书皮粘贴牢固,大功告成。书的封面,是一个发挥想象力的地方,开动大脑,做出你最喜欢的风格吧。
蝴蝶镶:蝴蝶镶在现存古籍中,只能算一种特殊的装订印刷形式,不知它出现的具体年代,也讲不清它的消亡时间,而清代内府刻书中这种形式也确实存在。
笔者近期整理内府刻书时发现几部,如:清乾隆十七年武英殿刻本《平定两金川方略二十六卷图说一卷》,嘉庆年间武英殿刊刻的《钦定大清会典》,道光十六年国子监刊刻的《钦定国子监志》,其装帧及版刻形式未见前人提及,也未见有关书目文献记载。
《清史稿》 《满洲秘档》
满汉全席 提出者:努尔哈赤
“满汉全席”起源于清太祖努尔哈赤关于满、汉两族和睦相处的进步政策。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公开反明。由于在萨尔浒一战大获全胜,逐步据有辽沈。据《满洲秘档》,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后,满洲人与关内北迁于此的汉民时有摩擦,以至出现过“今闻满洲以汉人之牛车,执汉人令运粮草,并索取诸物”的事件。对此,努尔哈赤在天命七年(1622年)下了一道旨谕,说这事件“岂令汉人给满洲为仆乎”汉人“因其远处迁来,无住舍食粮耕田”,故令“满汉等合居一处,同住同食同耕……计口合粮而食。所有田地,满、汉人等务宜各自耕种。若满洲人欺索汉人故违此谕,则汉人可扭而告之执法之官;而汉人亦不准因降此谕任意诬诳满洲人,因尔等,同为一帝之民故耳”。
不仅如此,在努尔哈赤的政权中,对满、汉官员(包括蒙古官员)也执行平等的政策,在编制、礼仪,甚至在饮宴和娱乐中,都注意保持均衡。以至“汉之小官及平人前往满洲地方者,得任意径入诸贝勒大臣之家,同席饮宴,尽礼款待”。(《满洲秘档》)
满汉全席 提倡者: 乾隆
乾隆时期,“怀柔郝氏,膏腴万顷,纯庙(乾隆)尝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百余品,王公近侍及舆抬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啸亭杂录》)。可以想见,郝氏能将乾隆请入家中赴宴,是件光宗耀祖的盛事,因此他不惜巨资,意欲乾隆“买账”;郝氏也必然会趋于“满汉一体”的政治社会意识,在饮宴上做到满、汉肴馔并陈,以博乾隆的进食逸兴。我疑这是没有写明的“满汉全席”,是“满汉全席”出现的最初形式。如果这个引证不够确凿,那么还有一例可以佐证。
乾隆在第五次巡游山东时,同皇后到曲阜祭孔,并将女儿下嫁孔府后代,“陪嫁品”中有一套
````````“满汉宴·银质点铜锡仿古象形水火餐具”。这套餐具共计408件,可盛装196道菜,出自广东潮城(今潮州)“颜和顺正老店”的潮阳银匠杨义华之手。也许正因为乾隆赐给孔府这套“满汉全席”餐具表达了他寻求“满汉一体”的“圣意”,人们也就从中领悟到了什么。于是,也就在这个时期,官府和市肆上开始盛行“满汉全席”。``````````
乾隆这个举措,是“满汉全席”形成的引发点,乾隆本人也成为“满汉全席” 的倡导者。
光禄寺的宴制是嬗变满汉全席的基础
清宫光禄寺是专门管理国家筵宴的机构,乃沿袭明宫膳事机构的体制设立,始于顺治元年(1644年)。清定都北京后,面对统治全国的形势,宫中膳事活动骤增。这样,完善、健全宫廷膳事体制便被清统治者们接受。清宫光禄寺的宴制嬗变为后来的“满汉全席”,其原因大体有如下四种:
1光禄寺的宴制分为“满席自一等至六等;汉席自一等至三等;又有上席、中席”(《钦定大清会典》卷七十四)。可以想见,“满席”由满厨主掌,“汉席”由汉厨主掌。“上席、中席”一类,大可值得研究。它既没有标明是“满席”,又没有标明是“汉席”,介于“满席”和“汉席”之间。从用料上看,既有用面定额(做饽饽用),又有“汉席”中的肉类菜肴,既有烧方、羊方这类满式菜肴,又有“汉席”中的蒸食、蔬食;而且,还特别写明有关陈设和席面安排。其实,这是将满、汉食俗和烹饪加以联结和交融的一类筵宴。由于政治原因和清廷统治者的民族心理意识,以及宫规食制的束约,“上席、中席”不便用满、汉联结的名称出现,而笼统地以“上席、中席”谓之。但在实际内容上已经满汉交融。由此窥测,清宫中的“满汉席”已经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隐形地运作着。这是研究“满汉全席”与清宫御膳之间的承袭关系和嬗变特征的一个重要切口。
2清宫光禄寺的宴制,以满族规制为主。出于清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和民族意念,当时朝廷中最重要的筵宴,均为“满席”食制所主宰。另外,清朝统治者在朝政、祭祀、婚丧嫁娶、生活等方面所反映的饮食现象,承袭祖制,已成固有习俗。因此,后来的“满汉全席”,以“满”字当头,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
3光禄寺的“汉席”被规定在传经讲学、文武会试、修书编典等文化活动的应用之内,反映了汉族饮食与汉族的文化一样,被清廷所接受和认定。“汉席”现象的存在,即清宫御膳中的山东饮食风味和康、乾时期引入宫廷的苏扬饮食风味,则是后来“满汉全席”中“汉菜”部分的基础。
4清入关后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其宫廷食制的实际内容已经随着清朝政权的延伸而潜移默化地受到汉族食俗礼仪及烹饪技艺的濡染和渗透,特别是乾隆朝以后,这种迹象更为明显。清宫光禄寺在筵制上划分为“满席”、“汉席”、“上席、中席”的特殊作用,以及清宫御膳在向汉族食俗、烹饪的贴近发展,是导致乾隆时期嬗变、衍生“满汉全席”的蓄积和启领阶段。
清军入关后,广泛吸收汉族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这种变化也体现于宗室成员的起名上。后金及清初,宗室成员的名字多用满语音译,如莽古尔泰、多尔衮、阿济格、多铎、豪格等。后来逐渐汉化,按照辈分取固定用字。乾隆年间,皇六子永画了一幅《岁朝图》,进献孝圣皇太后钮祜禄氏。乾隆帝弘历在该画上题诗,内中有“永绵亦载奉慈娱”诗句。后来,弘历取其中的“永绵亦载”四字为近支宗室的字辈,并将“亦”字改作“奕”。道光五年(1825),道光帝F宁又钦定“溥毓恒启”四字,接续“载”字辈。咸丰六年(1857),咸丰帝奕定“焘增祺”四字,作为“启”字以下的字辈。这样,宗室辈分的取字,前后计有十四字:“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增祺”。
清代宗室不仅确定了辈分用字,并且根据亲疏之别,对第二字的偏旁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自康熙朝始,对宗室成员取名用字的偏旁有较为严格的规定。如康熙帝玄烨诸子之名第二字均用示字旁,如胤、胤等;乾隆帝弘历诸子则用斜玉旁,如永琪、永等。另一方面,远支宗室取名均不得采用与近支宗室相同的偏旁字样,以免混淆亲疏。
不难看出,这时宗室取名已经基本上不再采用满语音译的方式,而是直接用汉语取名,除了姓氏尚保留满族文化特征外,名字已经愈来愈汉化了。然而,随着宗室人口的繁衍,宗室成员起名出现了违规现象,并引起了皇帝的关注和相应处罚。
其一是同名现象。
人口众多,同名现象自然难以避免,但是在宗室群体中,同名就有可能带来尊卑长幼失序的问题,甚至冲犯皇帝的圣讳。康熙三十二年(1693),针对宗室同名现象制订了处理办法。规定自王以下,至闲散宗室,如有同名者,“令卑者、幼者改”,并且更换诰册。(《光绪朝大清会典》)
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帝弘历给刚刚出生的七阿哥起名为永琮。岂料第二天,弘历在西苑瀛台举行宴会时,发现一个出席宴会的宗室成员也叫永琮。甚感扫兴的弘历为此责问宗人府和敬事房,为何没有将有宗室成员起名永琮一事及时上报,并要求将所有永字辈的宗室成员人名进行检查,看有无重名。遵照前述康熙三十二年制定的成例,那个名叫永琮的宗室由于身份卑于七阿哥,故不得不改名,弘历将其改名为永常。余怒未消的弘历还要求宗人府“嗣后外闲起名,不得复用内廷拟定字样”。(《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尽管乾隆帝屡次降旨申明,但是同名现象仍时有出现。甚至出现了低级官员、兵丁与王公大臣同名的现象。嘉庆年间,嘉庆帝琰发现即将升任迪化知州的昌吉知县景安,与时任湖南巡抚景安(钮祜禄氏)同名。琰认为此事“殊属不合”,并无可奈何地说:“从前有与王公大臣同名者,经皇考高宗纯皇帝屡降训谕饬禁。今官员兵丁内,与王公大臣同名者甚多。此皆该管大臣平素并不留心,一任属员兵丁等率意命名所致。”琰下令将景安之名按照满文语义更改,又命令宗人府、吏部、兵部、八旗、内务府三旗“查明宗室觉罗旗员兵丁内,有与王公大臣同名者,俱著更改,毋令与王公大臣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这些禁令并没有彻底根除同名现象。到了咸丰、光绪朝,宗室溥字辈甚至已经有与末代皇帝溥仪同名者。此溥仪系载堪之第七子,其祖父是奕勋。咸丰十一年(1861),载堪卒,溥仪遂承袭奉国将军。光绪九年(1883),溥仪死,其子毓秀承袭奉恩将军。光绪十二年,毓秀死,身后无嗣。(《清史稿》)就在这个名叫溥仪的宗室成员去世的当年,宣统帝溥仪之生父载沣方才出世。载沣之子命名时,内务府没有发现溥仪这个名字已经被人起过。在民国初年,清史馆的前清遗老们也没有注意这个冲犯“今上”圣讳的问题,直接写入《清史稿》中的宗室年表中。
其二是用字偏旁不当。
前面已提及近支宗室人名第二字的偏旁亦有严格规定,但有些宗室成员取名用字并未严格遵循。嘉庆十一年(1806),近支宗室多罗荣郡王绵亿,其长子和次子均属奕字辈,故其名第二字应用糸字旁的字样,但是却分别起名为奕铭和奕。嘉庆帝大为光火,认为绵亿未经奏请,即自行为两个儿子命名,实属非是,而且又不用糸字旁,故将此事交宗人府议处。嘉庆帝还质问绵亿“私用金字偏旁,为伊两子取名,不似近派宗支,自同疏远,是何居心?”并宣布:“伊既以疏远自恃,朕亦不以亲侄待伊。”结果,绵亿被革除领侍卫内大臣之职,退出乾清门。奕铭和奕也分别被改名为奕绘和奕。绵亿面对如此严厉处分,纵有百口,也无法申辩,唯有接受而已。(《光绪朝大清会典》)
有些远支宗室取名用字与近支宗室偏旁相同,造成亲疏难辨。嘉庆十三年,远支宗室成员绵瑚取名用斜玉旁的“瑚”字,而他的哥哥绵开和弟弟绵卞都没有用斜玉旁字。嘉庆帝知悉此事后,认为绵瑚取用玉旁,“大属非是”,并指责所属总管王公、贝勒、族长怠玩疏忽,下令将其改名为绵胡,并谕旨重申:“嗣后各宗室中,遇有命名不合者,随时饬改,以符定制,不得再有疏漏。”(《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其三是未遵照辈分用字原则。
乾隆十一年,弘历在一次宴席中发现一个名叫诸尔杭阿的宗室成员,系庄亲王永之子,论辈分系弘历之孙,却依照满语音译取名。为此弘历谕旨:“昨入燕宗室内,有名诸尔杭阿者,乃朕孙辈,已令改名绵庆。著传谕履亲王、庄亲王等,朕初次见孙,以后永字下辈即用绵字。并将朕此旨载入玉牒。”(《清高宗实录》)
其四是有过度汉化之嫌。
尽管入关已久的宗室成员已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习用汉语,可是清朝皇帝又处处防范过度汉化,以鄙薄的语气称汉文化为“汉人习气”,要求宗室不得沾染。为此,乾隆帝和嘉庆帝等曾屡次在宗室起名问题上重申这一原则。
乾隆三十二年,吏部带领一个叫满吉善的宗室成员入宫接受引见。满吉善系闽浙总督满保之子,而且又属于正黄旗下。结果,乾隆帝大为不悦,认为此人取名满吉善,是以满为姓。为此,他将其名改为吉善,并在谕旨中斥责道:“吉善乃系觉罗,甚属尊贵。吉善竟不以觉罗为尊,以满为姓,照依汉人起名。是何道理?似此者,宗人府王公等,理应留心查禁。今竟不禁止,王公所司何事?恐尚有似此等者,著交宗人府王公等查明俱行更改,将此严禁。嗣后不可如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然而,到了嘉庆朝,嘉庆帝在刑部呈进的题本内看到有一个叫“觉罗太”的人名,质问此名“是何取意,竟染汉人习气矣”。为此,琰下令将觉罗太“交宗人府即令按照满洲语意更改其名外,并著该衙门及八旗满洲蒙古都统,通行查明。如有似此指姓命名者,俱著饬禁,均令按照满洲语意,另行更改,毋得再行指姓命名,致蹈汉人习气”。(《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嘉庆十三年,琰在宗人府呈交的一个题本内,发现奉恩将军英智之次子名叫清永泰。琰认为此名也属违规。为此,他在谕旨中指出:“向来满洲命名,除清语(即满语)不计字数外,若用汉文,止准用二字,不准用三字。今清永泰之名,几与汉人姓名相连者无异,殊乖定制。”为此,他命令清永泰改名为永泰,并将管理宗人府的王公予以罚俸三个月的处分,清永泰本人的族长、学长也受到罚俸六个月的处分。(《清仁宗实录》)
道光三年(1823),道光帝F宁将一名叫永恒泰的宗室佐领改名为永恒,认为永恒泰之名“并非满洲成语,殊属不合”。但他并未处罚其他人员,仅是重申道:“嗣后宗室有似此命名者,著宗人府于呈报时,即行饬改。”(《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既用汉字取名,却又认为宗室取三字名是沾染汉人习气,这种论断显然带有主观随意性,令宗室难以适从,也极大限制了他们取名用字的范围。前所述及的先后两个溥仪重名的现象,正反映了宗室取名用字日益受限的困窘。
作者简介
孙P,1973年生,陕西西安人。历史学博士,商务印书馆编辑。主要从事晚清外交史、中国近代社会史和文献学研究,著有《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
中国古代提到天文学的典籍是哪一本著作
本文2023-10-08 11:15:07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1097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