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格乡愁曲式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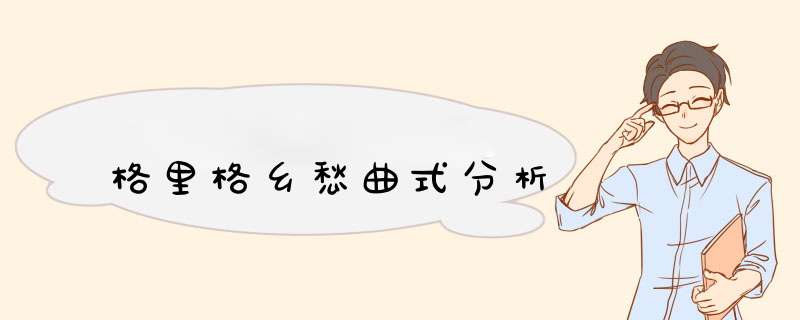
关于格里格乡愁曲式分析:
本篇文章研究分析的《乡愁》是格里格于1891年所创作第57号作品,全集共有6首作品,《乡愁》是最后一首。
一、曲式分析
该乐曲为e小调对比中部的再现性复三部曲式,全曲由80个小节组成。
(一)首部(1—28小节)
整体结构是展开中部的再现性单三部曲式。A乐段(1—8)为4+4方整性结构乐段,是由两个平行双句体构成,且为整个乐曲的主题旋律。B乐段(9—18)是一个在A乐段的基础上展开的非方整性乐段,以主题的三度下行模进发展,并且在低声部结合八度模仿,二者环环相扣。
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挥之不去、连绵不断的思乡愁绪。A乐段(19—28)重复演奏了A乐段的内容,在连接的情绪铺垫下再一次抒发内心的情感,在结束时又添加了一小节的正格补充终止(28小节),使整个首部有明显的终止感。
(二)中部(29—52)以及再现部曲式(53—80)
中部以新的调式新的素材来表达,描绘可爱的故乡。情绪转为轻松愉悦,让笔者看到和感受故乡的另外一面,与首部形成强烈对比。C乐段(29—36)是4+4的方整性乐段,以全新的素材来表达。C乐句(29—32)结束在E大调的属功能上,为开放性终止。
C1乐句(33—36)结束在E大调的主功能上,为收拢性终止。D乐段(37—44)是在C乐段基础上展开的非方整性乐段,由两个两小节的乐句呈模仿递进的方式,使得乐句情绪高涨。C1乐段(45—52)再现C段主旋律。
但在原有的旋律线条中添加了装饰音,使得乐句显得更为俏皮生动。最后,再现部曲式(53—80)是完全重复首部,但情绪表达更加悲伤惆怅,气氛更加忧郁低沉。
三、乐曲的演奏技巧分析
(一)调式
格里格在本首作品中运用了e小调和E大调来突出丰富的音乐色彩,让人们在不同的氛围里感受体会乡愁的滋味。开始运用小调的独特音乐色彩向人们叙说着故事,每一小句的结尾音都有呼吸感,与下一句连接时要有优美的线条感。
到了中部,用e小调的同主音的关系大调E大调,让音乐原本低沉的气氛得到了转变,音乐色彩鲜明突出。乐曲的再现部,调式回到e小调,音乐旋律虽然是首部的完全再现,但此时此刻的情绪要达到情感表述的最高潮,渲染出更加浓郁的思乡愁绪。
(二)和声
和声方面,格里格擅长利用和声的抒情性来烘托气氛。A乐段刚开始(1—8),就分别用主和弦持续音“E”的四组和弦与和弦式的琶音进行。中部29小节以后的三声部,和声柔和,突出右手旋律节奏,左手不太强,从第37小节开始,和声随着旋律的进行渐强推进,直至连接处。
(三)踏板
在首部和尾部都出现在乐句的结尾处,使得情绪表达更加扣人心弦。A1乐段的26到27再到28小节,情绪坚定,踏板与标记处和弦同时踩和放,旋律渐渐地慢下来,直至最后一个和弦、音程,情绪才慢慢平静。
四、乐曲的风格
作者用挪威民间音乐特有的方式——调式交替,来表现柔情和粗狂的对比向人们呈现。这首作品中,作者运用悲痛压抑与轻松欢快对比让人们感受到他对思乡愁绪的表达。在体裁和创作方面,格里格的音乐大都具有挪威浪漫主义情怀和民间音乐的艺术特征。
他的作品吸收了欧洲及德奥浪漫主义和挪威特色乐器的演奏特点、民间舞蹈的节奏、民间音乐的旋律,然后再创新,最后呈现出独具挪威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的作品,并让它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民族音乐财富。
蝉 声 在 耳
蝉是属于夏天的,是夏天特有的一个符号。当你发现自己被蝉声重重包围时,夏天便到了。
每年夏天,蝉音澎湃,一树接一树,一声连一声,从日出到日落,从傍晚到黎明。那时缓时急、忽高忽低、似有似无的蝉声,恬静旷远了一个单调而燥热的季节。
这是夏日特有的风情。
可以说,无蝉不夏。正如有花而无蝶飞蜂绕,清风明月在怀却无琴无酒无茶无诗书相伴一样,总觉少了几分意境。
蝉声四起,在风里流动,于柳岸清绝,在山林热烈,于乡间喧响,像一壶老酒,把千村万落熏得有点微醉。细细聆听,似乎感觉那声声蝉唱在风里轻轻摇动。
于这样的氛围里,可以簟枕邀凉,琴书换日,墙头唤酒,摇扇拈棋,泼墨挥毫,手倦抛书,偷得浮生半日闲。当是时也,那些悠闲的、散淡的、逍遥的,甚或是倦怠的、慵懒的、枕着蝉声入眠的人们,都化作了夏日绝句的一部分。
古人常听蝉。
清代文学家张潮在《幽梦影》中写道:“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际听内乃声,方不虚生此耳。”由此可见,这质朴的带着乡土味的最初的音乐,是一种多么诗意的存在!
然而,这悠扬幽远的蝉声到底是何时出现在文人墨客笔端的呢?
翻开一卷卷古籍,我们很容易找到乡间这最常见的物象,它们常常于闲中、客中、愁中在人们的心头奏响,牵动心灵深处的柔软和悠远。
最早文字记载的蝉鸣,可溯源到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三百》,“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菀彼柳斯,鸣蜩嘒嘒”。《礼记》里也记载了这个有古典诗歌美感的名称,“仲夏之月蝉始鸣,孟秋之月寒蝉鸣”。《楚辞·九辩》有云,“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既交代了时序的更迭,又渗透了作者主观的情绪,令人不免凄凉哽咽。
之后,蝉声如雨,在诗人的耳畔回旋萦绕,经久不散,咏蝉之诗更是层出不穷,佳作频传,诗中之蝉,亦被多情多感的诗人们赋予了深厚的文化意蕴,兴寄遥深。
我想,诗人怕是最能深味蝉声的含义的。
无论是王维、卢仝、虞世南,还是朱熹、柳永、骆宾王,他们对蝉声的理解多饱含了身世之感、君国之忧、人生之智、离别之苦。蝉的声音,便是诗人心底的声音。他们对蝉有着复杂的情结,褒贬不一,爱恨迥然,所咏之蝉,更是各有各的意态,各有各的丰神,写尽了蝉之高洁之清雅之幽寂之萧瑟悲凉……
或许蝉夏生秋亡,和春花、朝露、夕阳一样匆匆去来,因此,这千古如斯的小小尤物,常常使人有一种人生苦短而宇宙永恒的伤逝之感,再加上羁旅异乡、迟暮不遇等因素,则更觉难以为情,闻蝉而悲而愁而寂而肝肠纠结者数不胜数。
蝉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诗人在蝉声里,看到魂牵梦萦的土地,看到故乡最美最朴实的风景。蝉把乡村当成了永远的故乡,人又何尝不曾把蝉当作乡情的眺望?其中,洋溢着最浓重最稠密的乡愁的诗篇,当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早蝉》:“一闻愁意结,再听乡心起。渭上村蝉声,先听浑相似。”
和“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类似,听过蝉鸣的诗人,大多也会感时伤世,产生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的苦闷抑郁悲愤无奈,以及时光短暂而宇宙无穷的遥想,如司空曙的《新蝉》“今朝蝉忽鸣,迁客若为情?便觉一年老,能令万感生”,骆宾王的“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许是蝉餐风饮露、高栖深树的缘故,它历来被认为是高洁的象征,“饮露身何洁,吟风韵更长”,“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音”,“垂 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当然,在有蝉的长长时光里,带着老庄的色彩的蝉鸣,也曾让很多诗人恬静、悠闲、超然物外,宛入太古之境。较为典型的有“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
那,是秋天到了。
水瘦山寒,草木有时,蝉声渐稀渐老渐趋于无声。自此后,我们再也听不到满岸的蝉声,满塘的蝉声,满世界的蝉声了。
秋日听蝉,总带了几分苍凉,一声,足以断了人的肝肠。
秋来吟更苦,半咽半随风。寒蝉就这么悲吟着,声声随风轻送,似乎把一腔寒意,都散布在了这暮色之城里。
岑寂。高柳晚蝉,听西风消息。所有声音的本质,其实都是安静的。白石道人在一片清寂中诉说着时序将变的冷清寂寥。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诗人的心头必是凄然以悲、千头万绪的。
就如同晋代的张翰见秋风起而思吴中鲈鱼之美一样,如果说,落叶是秋天的提醒,那么,蝉声则是生命的提醒。
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告诉我们,四年黑暗中的苦工,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这就是蝉的生活。我们不应当讨厌它那喧嚣的歌声,因为它掘土四年,现在才能够穿起漂亮的衣服,长起可与飞鸟匹敌的翅膀,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什么样的钹声能响亮到足以歌颂它那得来不易的刹那欢愉呢?
庄子曾经感慨“蟪蛄不知春秋”,然而,那餐风饮露、用尽一生光阴歌唱生命的生灵,却向我们庄严宣告,这世界,我来过。它们,把自己的理想活成了自己的模样。
这,是一种境界。
万籁俱寂,唯余蝉声在耳。
我突然对蝉的新生崇敬起来。
蝉鸣“知——了”,那一声又一声的“知了”,唱出一片了然的意境。
蝉已知了,你可知了?
我是你枝头上的一只鸣蝉
蝉在窗外悠长的鸣叫,既远且近。
那是二十年前的蝉声。
对我而言,那缠绵、激越、永无止息的天籁,是我多年前不慎走失的夏天和村庄。
记忆中的村庄恬静安详,很多的往事定格成“如何不向深山里,坐拥闲云过一生”的闲适安然。
蝉在遥远的村庄里欢喜,叫醒酣眠的耳朵,丝毫不管炎炎夏日里人们的烦躁与不耐。它们长时间地一动不动,趴在浓浓的绿荫里怀抱着我的童年,歌唱生命的辉煌。
长风剪不断,还在树枝间。
从树下经过,你看不见它的潜伏,唯有古典的意境在心头铺展蔓延,那流淌的诗意,是陆游的“蝉鸣柳声相续”,又或者是毛文锡的“暮蝉声里落斜阳”。
蝉是中国古典的乡村的产物。
印象里,高栖枝头浩歌天下的小小尤物,涵盖了国人对于自然、宇宙、人性和人生的诸多看法。可以说,它是人们精神世界的物化。
自然是最伟大的一本书,歌德说,在它每一页的字句里,都能读到最深奥的消息。在人们无比深邃的灵魂里,大自然的阵阵蝉声,有着博大而丰富的世界,每一声,都高蹈着人生的气度。
古往今来,有人赞其高洁,有人咏其悠然,有人怜其凄婉,有人想其短暂,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有时,蝉是乡土情结的代言人。
乡愁是中国文化之根,当蝉声渐稀渐凉传达出秋的信息,在冷落清秋时节,就极易引发起游子怀念故土的悠悠情思。
此时,这蝉声如此寂寞凄清,以前在故乡,好像从没有过这样的感受。于是,置身于茫茫人海攘攘红尘,不论漂泊了多久,又走到了何方,那些滔滔无涯之事,都分付给了一声似曾相识来自故乡的蝉鸣。
忽然,所有与故乡有关的风物在异地一一复活。
隔着广漠的时空,开始想念每一个路过的夏天,想念隐身于岁月深处的老屋、石磨、篱笆、炊烟和瓦蓝瓦蓝的偶尔有鸟掠过的天空。
深入蝉声,其实也是深入故乡。
于是,蝉声有了温度,有了长度,有了重量。
但,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把村庄丢了,把蝉声丢了,也把自己也丢了?
脚下的城市,奔忙的城市,虽信美而终非吾土呵。离乡背井寄身闹市的现代人不禁满面含羞,把一颗争逐的心低到尘埃里,“我们到底要怎样的生活,怎样的自己?”
时光远去。
村庄远去。
再也找不到童年的井,童年的桥,童年的土路,童年的蒲公英,童年的和伙伴一起寻找蝉蜕的夏天的黄昏。
俱往矣。
唯一不变的是蝉鸣。
就在村庄之上,就在山林之上,就在曾经涟漪层层水声潺潺不知起于何方又将奔向何处的河流之上。
《礼记》说,水曰清涤。蝉声亦然。蝉者,禅也。听蝉,也是在听自己。
蝉声起伏,总会带给我们至深至大的遥想,纵使我们的世界落木无边、风雪载途,也能荡涤心中积聚的尘埃,忽略人生中的冷漠凄凉,把喜怒哀乐功利贪欲轻轻放下,包容千里风霜,拥抱万里秋色,精神得以皈依,得以回乡。
悠悠蝉鸣,声声入耳。
知否,知否,我遥远的故乡?我是你枝上的一只鸣蝉,每逢夏至秋来,响一片久违的乡音。
乡 关 何 处
多少年了,在城市奔忙之余,常常想起儿时的乡村。
那时的村庄,树多草多水多鸟多,同钢筋水泥的城市相比,多了一份人生的静谧悠闲,仿若一本线装的古典,随随意意的一瞥,便让你入诗境入画境入梦境。
最难忘的,是那条清清浅浅的小河,从远方蜿蜒而来,又蜿蜒而去,把我的村庄分为南北对望、鸡犬相闻的人家。清凌凌的河水淌着云朵,映着尘世,也渲染着一座诗意的世外桃源。
这诗意,在惹雾的小河边,在做梦的蛐蛐上,在风起的山林间,在滴落的晨露里,在向晚的青石旁,在简陋的戏台上,在静默的庭院中,在母亲的炊烟上,在父辈的泥土下,也在和伙伴一起光着脚丫满村庄乱跑或者在夏日的夜晚躺在高高的草垛上看天空数星星的日子里。
在乡村的天空下,水木清华,白云悠悠。不管你行走于阡陌柳岸,还是坐卧在自家的土炕上,总有清风入怀鸟鸣在耳,陶然,怡然,心头一派清空的禅意。
只是回忆依旧,故乡已然换了人间。
村庄陌生了。
曾经长满车前草狗尾草一到雨天就一踩一脚泥的土路消失了,曾经苍苍莽莽每至秋日就芦花飞白的大片大片的池塘不见了,曾经杨柳依依飞鸟绕岸的泥河干涸了,曾经木门竹篱青瓦粉墙的老屋拆除了。
所有的一切,都成了 历史 ,成了曾经。
我的熟悉的整整一个曾经啊。
到如今,只看见越来越多越来越宽的柏油路纵横田野,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华屋广厦崛起家园,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轰鸣盘旋耳际。
站在乡村的背景里,我长久地迷失。
岁月的岸边,芳草萋萋,河水清且涟漪。
我把我的村庄丢了。
我的脚步,再也回不到思无邪的童年,回不到我至亲至爱、温暖而诗意的村庄。
透过灯红酒绿的浮华,望见熟悉而陌生的村庄带着沧桑的表情缄默不语。
时代在进步, 社会 在发展,然而,给予人们心灵的滋养亲情的反哺的乡村却渐行渐远,一点一点,成为古老的符号,成为一个民族鲜活的记忆和想象。
简单朴拙屋舍俨然的村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庄,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村庄,在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的今天,还剩下多少呢?
我们到底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
这个时代的忧伤盘桓心头。
望中的一切,让人有种想要逃离的冲动。
忆起了庄子“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的善意的提醒,忆起了端己“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的凄怆哀伤,想起了库泊的“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的责任和悲悯。
乡村——我们最后一片诗意的栖所、精神的家园,多年以后,会不会不再为人知道,成为古籍史册里永远的寻觅,永远的追怀?
乡村本身就是一首诗。
当生命低处的村庄,背负古老的故事沉甸甸的 历史 ,向城市靠近,被城市异化,模糊了城市与乡村的界限时,来去匆匆的现代人,有没有想到,一个没有了乡村的民族,何其苍凉?
提起西安,人们会想起传承与文明;提起圆明园,人们会想起 历史 与尊严;提起上海,人们会想到繁华与未来;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提起乡村,会想起什么呢?
老屋?石磨?黄牛?麦场?稻田?流萤?鸣蝉?阡陌?
在争逐利益的同时,我们该珍而重之,不管怎样的变革和建设,都懂得保护乡村最初真淳的形态,将一个民族张扬而内敛、繁华或质朴、端庄也深邃的气质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让成为民族 历史 和文化一部分的乡村,沦为人们心头泛黄的记忆。
我们不妨在乡村里寄托梦想,净化灵魂,呈现生命最初的意识,像海德格尔呼吁的那样,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鸟恋山林,鱼思故渊。
用朝圣的虔诚,一个人重温回顾故乡或深刻或温暖的记忆。
夜来幽梦。
站在二十年前的村庄面前,望而却步。
是无处还乡的尴尬。
像一个异乡人,在这里,安顿不了漂泊的灵魂。身前霓虹闪烁,身后市声嘈杂。
我闭上眼睛,说不出一句话。
胡不归?
胡不归?
田园将无,胡不归?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隐约听到崔颢的声音,从唐朝一直吟哦到了如今。
乡关何处?
村庄不说话,乡愁却在我心底潜滋暗长。
我慢慢意识到,我的乡愁应该是对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的眷恋……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鹤发童颜的余光中在接受来自祖国大陆的记者采访时,又一次忘情地吟唱起他作于30年前的《乡愁》。
由于余光中15年前从香港返台后“背弃台北”而“转居高雄”,记者初抵台北欲寻访这位名播两岸的诗人的计划受到困扰。幸好报载他要到台北出席一个文学翻译界的笔会,我们相约于他,没想到诗人竟爽快地答应了。
采访自然是从他的创作谈起,而“乡愁”又是双方共同的话题,余光中告诉记者,中央电视台刚刚与他谈妥,将他的诗作《乡愁》谱曲后作为电视系列片《闽南名流世家》的主题曲,这部电视片讲述的是郑成功后人在海峡两岸生活的情况。
■“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49年离开大陆,3年后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先后在数所大学任教,创作,也曾到美国和香港求学、工作。目前在高雄“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已出版诗集、散文、评论和译著40余种,他自称是“文学创作上的多妻主义者”。文学大师梁实秋评价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从21岁负笈漂泊台岛,到小楼孤灯下怀乡的呢喃,直到往来于两岸间的探亲、观光、交流,萦绕在我心头的仍旧是挥之不去的乡愁。”谈到作品中永恒的怀乡情结和心路历程时他说,“不过我慢慢意识到,我的乡愁现应该是对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的眷恋。”
60年代起余光中创作了不少怀乡诗,其中便有人们争诵一时的“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白发盖着黑土,在最美最母亲的国土。”回忆起70年代初创作《乡愁》时的情景,余光中时而低首沉思,时而抬头远眺,似乎又在感念着当时的忧伤氛围。他说:“随着日子的流失愈多,我的怀乡之情便日重,在离开大陆整整20年的时候,我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一挥而就,仅用了20分钟便写出了《乡愁》。”
余光中说,这首诗是“蛮写实的”:小时候上寄宿学校,要与妈妈通信;婚后赴美读书,坐轮船返台;后来母亲去世,永失母爱。诗的前三句思念的都是女性,到最后一句我想到了大陆这个“大母亲”,于是意境和思路便豁然开朗,就有了“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一句。
余光中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紫金山风光、夫子庙雅韵早已渗入他的血脉;抗战中辗转于重庆读书,嘉陵江水、巴山野风又一次将他浸润。“我庆幸自己在离开大陆时已经21岁。我受过传统《四书》、《五经》的教育,也受到了五四新文学的熏陶,中华文化已植根于心中。”余光中说,“如果乡愁只有纯粹的距离而没有沧桑,这种乡愁是单薄的。”
《乡愁》是台湾同胞、更是全体中国人共有的思乡曲,随后,台湾歌手杨弦将余光中的《乡愁》、《乡愁四韵》、《民歌》等8首诗谱曲传唱,并为大陆同胞所喜爱。余光中说:“给《乡愁四韵》和《乡愁》谱曲的音乐家不下半打,80多岁的王洛宾谱曲后曾自己边舞边唱,十分感人。诗比人先回乡,该是诗人最大的安慰。”
■“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
1992年,余光中43年后再次踏上大陆的土地。谈到这次对北京的访问,余光中说:“我的乡愁从此由浪漫阶段进入现实时期。我大陆之行的心情相当复杂,恍若梦中,我在北京登长城、游故宫,被两岸同胞的亲情所感染,写了不少诗作,尽情抒解怀乡之愁,因为原来并未到过北京,所以首次回大陆,乡愁并没有一种很对应的感觉和体验。”
自此以后,余光中往返大陆七八次,他回到了福建家乡,到了南京、湖南等地,在南京寻访金陵大学故地,在武汉遍闻满山丹桂,探亲访友,与大陆学子对谈,对大陆自然多了一层感知和了解。
他说:“初到大陆,所见所闻,令我兴奋不已。但我也看到洞庭湖变小了,苏州的小桥流水被污染了,这些让我也产生些许失望。但此后去大陆多次,那里的变化之快让我惊异和兴奋。”在四川,作家流沙河赠他一把折扇,问他是否乐不思蜀,他挥毫题字:思蜀而不乐。翰墨间仍飘出了淡淡的乡愁。
他说:“玄武湖,紫金山都变了,但大学原来的校舍我还能认得出来。我接触了许多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水平都不错。尤其是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一心一意搞建设,魄力很大,又很踏实。”
余光中说,在大陆的游历也使他越来越发现,他的乡愁是对中华民族的眷恋与深情。“我后来在台湾写了很多诗,一会儿写李广、王昭君,一会儿写屈原、李白,一会儿写荆轲刺秦、夸父逐日。我突然意识到,这些都是我深厚‘中国情结’的表现。”
他说:“我在大陆大学演讲时朗诵我的诗《民歌》,‘传说北方有的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才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海,风也听见,沙也听见’,在场的学生和我一同应和,慷慨激昂,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感情。”
抗战时期,余光中随母亲逃出南京,日军在后面追赶,他们幸得脱险,后来辗转越南到了重庆。日军大肆轰炸重庆时,上千同胞受难,余光中幸好躲在重庆郊区。谈起这些浩劫,余光中说:“这些都激发起我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那时候,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豪情,只要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万里长城万里长’,都会不禁泪流满面。前几年在东北访问时,青年时的歌谣仍萦绕着我。于是写下了‘关外的长风吹着海外的白发,飘飘,像路边千里的白杨’的诗句。”
余光中承认,他的诗歌在赴美期间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摇滚乐的影响,比较注意节奏,因此也容易被作曲家看中谱曲,但他仍以“蓝墨水的上游是黄河”来表明他的文化传承中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说,尽管他在美国上过学,诗文中也受一些西方东西的影响,但不变的是中国文化的遗韵和对中华民族的怀思。他的作品深受《诗经》的影响,也学习过臧克家、徐志摩、郭沫若、钱钟书的作品。他说:“我以身为中国人自豪,更以能使用中文为幸。”
■“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片厚土”
余光中曾在文章中写道:“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片厚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他说:“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
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
他说,中国文化对所有的“龙族”都有着无法摆脱和割舍的影响。谈到台湾一些人企图割裂两岸的文化联系,他说:“吃饭要用筷子,过端午节,过中秋节,能改得掉吗?大家所信仰的妈祖,不也是从大陆来的?余秋雨等大陆文化学者到台湾演讲引起轰动,不都说明中华文化是一脉相传的?”
余光中的妻子是他的表妹,江苏人,有着女性知识分子的韵味和气息。重庆时期,两人青梅竹马。他们至今都保留着一个特色,那就是在家的时候讲四川话。有次余光中到四川大学演讲,他征求校方,既然到了四川,是否就用四川话演讲,后来校方告诉他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就用普通话吧”,余光中因此没能有机会显示他讲四川话的才能。
从香港返台后,余光中为躲避繁琐的事务和各种交际,一直定居在高雄,在“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尽管年过七旬,但精神矍铄,幽默健谈,不失赤子之心。他每天坚持工作,上课、创作、编书,乐此不疲。他的近作不时被大陆报刊转载,一些大陆出版社要出他的作品集,他便不辞辛苦亲自校对。
“国立中山大学”环境优美,紧邻寿山风景区,南边是世界排名第四的货运港口高雄港,正西是西子湾,他的办公室就在面海的半山腰。余光中面海低语:“在台北时办公室也靠海,不过是靠着台湾东海岸,我看着太平洋有什么意思,看美国有什么意思。这也许是天意,现在我凭窗而立,便可直视海峡西面,尽管身在台湾,我可以眺望对面的香港,可以一生守望着我的大陆。”
本文2023-08-04 13:37:29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1098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