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80年,我国陕西地区发生了一次大的自然灾害,古籍《诗经》上有这样的记录:

地震
公元前780年,西周(都镐,今陕西长安西北)、三川(泾、渭、洛水)流域发生6—7级地震,日食。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奉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川干枯,岐山(今陕西岐山东北)崩。
2002年4月24日媒体报导:我国首次发现西汉时期敦煌地区发生沙尘暴的汉简。我国史书也有沙尘暴气候的记载:《诗经·邶风·终风》有"终风且霾"句,《后汉书·郎岂页传》有"时气错逆,霾雾蔽日"。"霾",《辞海》解释为:"大气混浊态的一种天气现象"。即夹着沙尘飞扬的沙尘暴。古籍中把沙尘暴写成"黄雾"、"飞沙走石"、"黑气"、"黑雾"等认为是一种不祥之兆。《晋书·天文志》说:"凡天地四方昏氵蒙若下尘,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日或一时,雨不沾衣而身有土,名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晋书》记载:从公元249年,即三国魏齐王曹芳嘉平元年;到公元402年即东晋安帝元兴元年,153年中记录了15次严重灾害性沙尘暴,其中有一年两次的。录之如下:�
魏齐王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正月壬辰,西北大风,发屋拆树木,昏尘蔽天。�
孙休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十一月甲午,风四转五复,蒙雾连日。十二月丁卯夜有大风发木扬沙。�
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十二月,黑气四塞。�
西晋愍帝建兴二年(公元315年)正月己已朔黑雾,着人如墨,连夜五日乃止。�
东晋元帝大兴四年(公元321年)八月,雾埃氛蔽日。�
东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十月,京师大雾,黑气蔽天,日月无光。�
东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正月癸已,黄雾四塞。二月又黄雾四塞。�
东晋穆帝永和七年(公元351年)三月,凉州大风拔木,黄雾下尘。�东晋孝武帝宁康三年(公元376年)三月,朔,暴风迅起,飞沙扬砾。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八月乙未,暴风扬沙石。�
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癸未,黄雾四塞。�
东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十月酉申,朔黄雾混浊不雨。�
就以上不完全资料统计:3世纪3次;4世纪9次,其中311-315年2次,321-323年3次,351-383年4次;5世纪1次;总计13个年度15次。非常清楚表明:4世纪属于"沙尘暴百年多发期",一个世纪中有两个多发高峰,第一峰期出现在20-30年代,第二峰期出现在50-80年代。这与文字记载的"诸民远离国境","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完全吻合。
虽然古代中国对于沙尘暴的直接记载并不多见,但我们仍可从古诗文的描绘中发现它的蛛丝马迹:唐代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也许可视为一次真实的沙尘暴记录,原文写道:”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再如陈子昂的“黄沙幕南起,白日隐西隅。”——这些形容黄沙飞扬、疾风肆虐的场景正是沙尘暴的典型特征。
由于蝗灾发生的自然环境条件,古今基本上差不多,所以我国的蝗灾并没有因农业现代化发展而消失,反之,只要是条件合适,蝗灾便会卷土重来。如2002年入夏以来,我国河北、河南、山东、天津、新疆等13个省区市100多个县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蝗虫。截至6月底,农牧区发生蝗虫面积达9000万亩。
蝗灾的历史回顾
先秦古籍如《诗经》等多称蝗为螽(螽是蝗类的总名,还包括螽斯)或蝝,蝝是蝗的若虫(不完全变态的昆虫幼虫称若虫)。战国后多称蝗。蝗和蝝都为害庄稼。古籍上最早记载蝗灾的是《春秋》记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冬,蝝生。"最早记载蝗虫的是《吕氏春秋·孟夏纪第四》:"行春令……则虫蝗为败。"及同书《审时篇》:"……得时之麻……如此者,不蝗。"《礼记·月令》也有"虫蝗为灾"的记载,不俱引。约在宋以后,蝝改称"蝻",合称蝗蝻,沿用至今。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除蝗疏》统计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蝗灾的次数,指出春秋294年中共发生蝝灾111次,按月分布如下:
月份(农历)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发生次数 2 3 19 20 31 20 12 1 0 0 3
以上的数字分布,非常合乎统计学上的常态分布规律。表明蝗虫是在4至9月(农历)间最猖獗,徐光启说:"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也,故为害最广。"
徐光启的这个统计与1920年江苏省及浙江省昆虫局研究全国各地蝗虫的发生季节非常吻合,就飞蝗而言,各地以5~8月(阳历)为蝗患最紧要时期。夏蝗以5月中至7月上旬最盛,秋蝗以8月上中旬为最盛。6、7两月是夏秋蝗灾并发的时期。
笔者对周尧《中国昆虫学史》附录历代蝗虫灾害登记表的重新统计结果,从公元前707年(鲁桓公十三年)至公元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止的2614年中,共发生蝗灾508次(该书印刷有误,统计为2618年,538次)。
《除蝗疏》对于蝗虫的发生与环境气候条件的关系有很科学的见解:闻之老农言,蝗初生如粟米,数日旋大如蝇。能跳跃群行,是名为蝻。又数日,即群飞,是名为蝗。所止之处,喙不停啮……又数日,孕子于地矣。地下之子,十八日复为蝻,蝻复为蝗,如是传生,祸之所以广也……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必也骤涸之处……故涸泽者,蝗之原本也,欲除蝗,图之此其地矣。
唐宋以后,纸张及印刷条件改善,蝗灾的记载便较详细,下面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唐)贞元元年(785年),夏蝗,东自海,西尽河陇,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及畜毛靡有孑遗,饿殍枕道。秋,关辅大蝗,田稼食尽,百姓饥,捕蝗为食。"
"(宋)淳化三年(992年),六月甲申,飞蝗自东北来,蔽天,经西南而去。是夕大雨,蝗尽死。秋七月,许、汝、衮、单、沧、蔡、齐、贝八州蝗。""有蝗起东北,趋至西南,蔽空如云翳日……"
"(元)至正十九年(1353年),五月,山东、河东、河南、关中等处,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尽平。""(蝗)食禾稼草木俱尽。所至蔽日,碍人马不能行。填坑堑皆盈。饥民捕蝗以为食,或曝干而积之……"
"(明)成化二十一年,大旱,飞蝗兼至,人皆相食。流亡者大半,时饥民啸聚山林。太平县蝗虫飞,飞蔽天,禾穗树叶食之殆尽,民悉转壑。是年垣曲民流亡大半,聚啸山林。三月,平阳蝗。四月,河南蝗。七月顺天蝗。"
"(清)咸丰七年(1857年),春,昌平、唐山、望都、乐亭、平乡蝗,平谷蝻生,春无麦。青县蝻子生,抚宁、曲阳、元氏、清苑、无极大旱,蝗……武昌飞蝗蔽天。房县、枝江、松滋旱蝗,宜都有蝗长三寸余。秋,黄安、蕲水、黄冈、随州蝗;应山蝗,落地厚尺许,钟祥飞蝗蔽天,亘数十里……"
蝗灾的地理分布
上引公元前707年(鲁桓公五年)至公元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止的2614年中,共发生蝗灾508次,按其发生次数的地理分布,为:
黄河流域:436次,占85.82%;长江流域:69次,占13.57%;华南西南:3次,占0.58%。这个分布情况与陈正祥研究的"蝗神庙之分布"基本一致。地理学者陈正祥查阅国内外收藏的中国方志3000余种,找出其中记载有蝗神庙地点的,即在地图上标明,最后制成中国"蝗神庙之分布"的历史地理图(蝗神是总称,包括叭蜡、虫王、刘猛将军等)。利用蝗神庙分布绘成的蝗灾分布地图,有一种超过文字记载的优点,因为凡是有蝗神庙的地方,反映当地的蝗灾必有反复发作的历史,故农民不得不立庙祭祀。
陈正祥归纳蝗神庙分布图的特点有四:(1)蝗灾的分布以黄河下游为最多,尤其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2)华中以南,蝗灾渐少,到了东南沿海,几乎没有。(3)蝗神庙分布的南限,大致同春季及年平均80%的相对湿度等值线符合。(4)云南高原中部和太湖流域相似,故蝗灾也较普遍。这图的不足之处是未能反映蝗灾偶然发作的地点,因为蝗灾偶发地区,往往没有建立蝗神庙,便无法在地图上反映出来。
历史上的蝗虫是没有分类的,郭郛等研究现代中国蝗虫的生物学分类,指出有三大类,即东亚飞蝗、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郭郛等也将中国蝗灾的分布绘制成"中国飞蝗三亚种的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蝗虫主要都是东亚飞蝗,亚洲飞蝗主要分布在西北及内蒙古一带,西藏飞蝗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一带。其中东亚飞蝗的分布情况,同陈正祥的"蝗神庙之分布"图非常一致,并且弥补了"蝗神庙之分布"中因不是多发性地区故没有蝗神庙的缺点,以及西北内蒙古和西藏地区因缺乏方志记载故蝗神庙极为稀少的缺点。将两图合起来看,可以对中国蝗灾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分布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概念和理解。
天人感应面临蝗灾的尴尬
子思、孟子等倡言"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天道与人道合一,自然与人为合一。汉代董仲舒更进一步发展为"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万神之君,天子是受天命而有天下。这种君权神授的思想神化了皇权,但另一方面,天人感应也有限制皇权的一面,使得人君不能为所欲为。所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责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度,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在天人感应说的倡导下,产生了"变复"论,所谓变复乃指一切的灾祸都是天意,只有通过祭祀祈祷,才可以转"变"灾异而恢"复"正常。在蝗灾猖獗,眼看禾稼被蝗虫啮食无收,百姓饥饿死亡,人君这时再深自谴责,下诏罪己,又何补于抗灾?所以东汉的王充便坚决反对,在《论衡》中反诘说:天地广大,用一点点祭祀的食品,"天地安能饱?"但天人感应的思想仍深入人心,当政者和老百姓面临蝗灾猖獗时,都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如《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628年)六月,京畿旱蝗时,唐太宗在皇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谷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白居易在其《新乐府》之"捕蝗"中,一方面对蝗灾及捕蝗有客观生动的描述,但最终仍陷于天人感应的困惑中:"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一虫治死百虫来,岂将人力竞天灾。"他还是认为"吾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庆万民赖,是岁虽蝗不为伤。"他相信唐太宗吞蝗后,蝗灾就消灭了。
但是,也有部分官员不相信天人感应,主张蝗来即要捕蝗灭蝗,不能听其猖獗。如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大蝗,官民只知道祭拜,坐视蝗虫食苗,不敢捕杀。玄宗则自责修德不够,致遭天谴。他询问臣下们的意见,宰相姚崇力主利用蝗虫的趋光习性,于"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他派遣御史,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却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拒绝御史执行任务,姚崇大怒,牒报若水,如若听任蝗虫食苗,导致百姓饥饿,要对后果负责。若水这才被动投入捕蝗,"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
天人感应说到宋代,被程朱理学所张扬,仍然很有威力。宋代的朱熹奉旨去浙东一带视察旱灾和蝗灾的情况,随时报奏皇上,其中提到他在会稽县广孝乡亲自主持捕蝗、收买、焚埋蝗虫,大蝗一斗,给钱一百文,小蝗每升给钱五十文。但同时朱熹又举行祈祷,专门写了一本《乞修德政以弭天灾状》,开头报告沿途所见灾情之严重,接着说"臣窃不胜大惧,以为此实安危治乱之机,非寻常小小灾伤之比也。为今之计,独有断自圣心,沛然发号,深以侧身悔过之诚……然后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庶几精神感通,转祸为福……"
在蝗灾猖獗面前,民间对蝗灾的态度也处于非常矛盾尴尬的境地。
周代腊月祭祀称"八蜡"(蜡音zhà),指八种要祭祀的神,即"先啬"(神农)、"司啬"(后稷)、"农"(作物神)、"邮表□(田神)、"猫虎"(益虫神)、"坊"(河堤神)、"水庸"及"昆虫"。先啬和司啬是丰收之神。祭猫可除田鼠,祭虎可除野猪,故猫虎成为祭神。昆虫专指为害庄稼的害虫。"坊"、"水庸"和"邮表□"都是农业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保护神。到后世,八蜡的内容起了变化,先啬和司啬转为神农和后稷以后,从八蜡中分离出去,单独祭祀;猫虎因其捕食对象减少也慢慢淡出了。八蜡神在民间浓缩演变为驱除害虫之神,特别是为害最厉害的蝗虫,被提到了首位,称之为"虫王"。所以八蜡庙或虫王庙,在华北农村实际上都是祭祀蝗神的庙。
刘猛将军庙(简称猛将庙)发生于南宋的太湖地区,当地民间认为刘猛将军的驱蝗威力远超过八蜡庙和虫王庙。清初的袁枚竟然把八蜡神降级为受刘猛将军的支使:"虫鱼皆八蜡神所管,只需向刘猛将军处烧香求祷,便可无恙。"
刘猛将军即南宋抗金名将刘锜(1098~1162年),他和岳飞(1103~1142年)同是南宋抗金名将。因受张俊、秦桧排挤,被剥夺军权,改任地方官,受到人民爱戴。
刘锜曾于宋高宗绍光六年至三十一年间(1136~1161年)先后驻军或转战于镇江、扬州、金陵、平江、巢湖、合肥一带,其战功显赫,深得这一带民间人心。而这一带正是蝗虫的滋生多发区,所以刘猛将军庙独起源于太湖地区,为纪念刘猛将军举行的庙会(猛将会)也特别多。刘锜更被封为灭蝗之神:"宋景定四年封刘錡为扬威侯天曹猛将,有敕书云:‘飞蝗入境,渐食嘉禾,赖尔神灵,剪灭无余。‘"
刘猛将军庙的威名还逐渐传入黄河流域,与北方的八蜡庙或虫王庙并存,河北徐水、武安县还有八蜡庙、虫王庙、刘猛将军三庙并存的现象。《山东·威海卫志》说:"八蜡庙,俗名虫王庙,在东北门外,康熙末年建。后改为刘猛将军庙,刘能驱蝗,有求必应,江、浙多祀之,雍正六年奉文捐建之。"
蝗神庙的历史演变表明,自古以来,人们对蔽天遮日而来的蝗虫,缺乏有效的防治方法,先是祭祀八蜡神,以后发觉不灵验了,直接改祀虫王庙,虫王庙也不见得灵验了,听说江浙一带的刘猛将军"有求必应",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乃又转而建立刘猛将军庙。
八蜡庙和虫王庙的祭祀是贿赂性的,乞求虫王手下留情;刘猛将军庙则是打击性的,不吃软的就请刘将军把你消灭掉。软硬兼施,蝗灾依然如故。三庙林立,是历史上农业生产和农民饱受蝗灾苦难的印证。
历史上治蝗的生态观萌芽
尽管天人感应的思想深入人心,但在治蝗问题上陷于困境时,实际上不论政府官员和老百姓在祭祀虫神的同时,也投入积极的捕蝗灭蝗中去,并且摸索创造出许多灭蝗的经验。
徐光启在《除蝗疏》中归纳历代的除蝗方法,无非是治标和治本两大方面。治标包括北宋淳熙年间敕令,命官民及时上报蝗虫情报,违者受杖责处分;对因穿掘、扑打捕蝗损伤苗稼的,给予免税和赔偿;实行以蝗易粟,鼓励民众捕捉蝗虫;提倡食蝗等。治本方面,在低洼积水和有水草生长的地方,发动农民割草,晒干后既可作燃料,又清除了蝗虫产卵的场所;春夏间发动捕捉蝗卵,捕卵一石,可减少蝗虫百石;干卵一石,等于减蝗千石(笔者按:一斤卵块约有蝗卵4至8万粒,故一石卵绝不止百石蝗)。对捕卵后残存的初生蝻子,预掘长沟,每隔一定距离掘沟一条,发动农民敲锣,驱赶,蝗蝻受惊,跳入沟内,即以泥土填入掩埋。对漏网的成虫飞蝗,用绳兜兜取,布袋盛贮,拿去换粟。最后,在蝗灾过后,还要检查冬月有蝗虫产卵处。再得除子,冬闲除子一石,可敌治虫千石。又鉴于蝗虫不食芋、桑、菱芡、豌豆、绿豆、大麻、芝麻等,可以多种这类作物,有利于减轻蝗灾危害。以上的方法可以说已经相当周详,只因蝗灾之来,非常迅猛猖獗,所以收效也受到限制。
受到明朝徐光启《除蝗疏》和董《救荒活民书》等的影响,进入清朝以后,有关治蝗的专书也多了起来,如湖广布政使俞森的《捕蝗集要》、山东蒲松龄的《捕蝗虫要法》、浙江陈方生的《捕蝗考》、陈仅的《捕虫汇编》、江苏顾彦的《治蝗全法》、陕西芷龄的《除蝻八要》、陈崇砥《治蝗书》等,反映了有知识、有科学头脑的士人,紧跟徐光启、董之后,提倡人力治蝗。当然,明清治蝗书的增多,也不是好事,它反映蝗虫问题到明清时期不见减轻,更见严重。
在祈祷神力驱蝗和主张人力捕蝗的历史过程中,明末浙北嘉兴、湖州地区,农民发明了以蝗虫饲鸭、山区贫民以蝗虫饲猪等措施。对于大量捕集、数以千百石计的蝗虫,如只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一概焚埋,不加利用,也确实是能量(蛋白质)的很大损失。唐太宗带头吞蝗的传说影响很大,据说唐代民间因而形成了食蝗的风俗,甚至于以蝗虫为珍贵的食品,互相馈赠。
据分析,蝗蝻的粗蛋白质含量为71.21%,粗脂肪为9.1%,碳水化合物为5.13%,灰分为5.24%。其食味近似虾干,营养价值和鱼肉类相当。民国时期的北平、天津一带餐馆里,还有以蝗虫为佳肴,供顾客点菜之需。苏北蝗区常年有蝗虫产卵的地方,遇蝗虫大发之年,居民打了蝗虫,晒干后贮藏起来,做干粮或肥料用,荒年时还要预防晒场上的蝗干被人偷去。历史上自南京浦口至徐州一带,处于洪泽湖和微山湖蝗虫滋生地带,蝗灾频繁,形成了以蝗蝻饲鸭的传统,有专业的鸭户领导放鸭,犹如蒙古草原的放牧牛羊一样。据调查,一只大鸭一天中能吃掉蝗蝻两斤,则一千只鸭每天的食蝗量达两千斤之多,当地的蝗虫虽然年年滋生,也就难以成灾了。
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天人感应仍然有其科学的积极的意义。生态学并不认为人可以向自然无限制地索取。人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受自然界生物链规律的约束。蝗虫之所以猖獗,是因制约蝗虫繁殖的客观条件失控,如干旱缺水、天敌减少、植被单一化、越冬残虫量大等,给蝗虫提供了快速繁殖、短期内爆发成灾的可能。气候干旱化是亚洲大陆腹地的大趋势,非人力短期内所能扭转,但其他人为的因素如河滩裸露,湖库脱水,退耕还湖、还草、还滩过程中没有注意综合措施,残留虫量太多等,都是导致蝗虫爆发的条件。蝗虫的天敌包括菌类、螨类、昆虫类、蜘蛛类,两栖动物类、鸟类等,据统计,达68种之多,尤以鸟类的食蝗量为大,其次是捕食蝗虫的昆虫;天然的益鸟因人们捕捉不断减少,只能依靠鸡鸭等家禽实行突击捕蝗。
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蝗虫问题虽然不可能彻底解决,却完全可以科学地给予控制。继承历史经验,在蝗虫多发区和附近地区,有计划地组织一定规模的养鸭养鸡场,扩大推行生物治蝗、食蝗和制作蝗虫饲料,无疑是值得提倡的一项措施。
霍乱病传入中国,使用了传统的霍乱病名。早在《内经》中,就曾多次使用霍乱这一病名。如《灵枢•五乱》篇说:“乱于肠胃,则为霍乱”。《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土不及,民病飨泄霍乱”。《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汉书》说:“闽越夏月暑时,欧(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
《伤寒论》对霍乱的症状和治疗都有比较系统的阐述,如“呕吐而利,此名霍乱”,这些都说明,霍乱在汉代已是众所熟知的病名了。
对霍乱弧菌引起的霍乱,学者们多遵从伍连德在《霍乱概论》中的论述,认为是从清嘉庆二十五年即1820年传入中国的。他是依据宋如林在重刊林森《痧症全书》序中所言:“嘉庆庚辰(1820年)秋,人多吐泻之疾,次年辛巳更甚剧”。又云:“此症始自广东,今岁福建台湾,患者尤甚”。余云岫在《流行霍乱与中国旧医学》一文中考证,中国之有霍乱,约在1817年,由印度经陆地传入,此前虽有记载,皆不能确定为真正霍乱。对此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1817年的传入没造成特大流行,可从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1817年由印度源起造成世界大流行时,霍乱就传入了中国,故首次传入应从1817年算起。日本井村哮全也支持余云岫的观点。对于霍乱,我国似乎还有更早的记载,如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涂绅的《百代医宗》一书中记有“嘉靖甲子(1564年),人多患此疾,自脚心麻至膝上者,不胜其数,死者千万矣”。后世医生据此对霍乱有“麻脚瘟”的病名。医史学家陈邦贤认为,唐代王焘在《外台秘要》记述霍乱的症状有吐利、腹痛、手足冷、烦躁、干呕、转筋等,似已认识此病。
在世界霍乱的七次大流行中,我国每次都是重疫区,并且在两次流行的间期也患者不绝,病毙者甚众。据伍连德《中国霍乱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疗法概况》记载:“自一八二零年英国用兵缅甸,一旦霍乱流行,直由海道经缅甸达广州,波及温州及宁波两处,以宁波为剧。次年,真性霍乱遂流行于中国境内,由宁波向各埠蔓延,直抵北平、直隶、山东等省。一八二六年夏由印度传入中国。又自一八四零年由印度调入英印联军,遂造成第三次之霍乱流行”。陆定圃《冷庐医话•卷三•霍乱转筋》中说:“嘉庆庚辰年(1820年)后,患者不绝”。王清任《医林改错•下卷•瘟毒吐泻转筋说》中也说:“道光元年辛巳(1821年),病吐泻转筋者数省,死亡过多,贫不能葬埋者,国家发币施棺,月余之间,共数十万金”。在清代,以光绪十年(1888年)流行最盛。在民国时代,以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霍乱流行最广,波及城市达306处,患病者达10666人,死亡者达31974人。
霍乱传入我国后,因不知病源,医生则据症状名病和预防。徐子默在《吊脚痧方论》中,称此病为“吊脚痧”,同书又以付题称为“麻脚瘟”,田晋元则在所著《时行霍乱指迷》一书中,称为“时行霍乱”。民国初年,也有据英语者称此病名为“真霍乱”。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在法定文献和教科书中便称此病为霍乱,而不再称“真霍乱”和其他病名了。在王孟英所著《霍乱论》中,提出在春夏之际,在井中投以白矾、雄黄,水缸中浸石葛蒲根及降香为消毒预防之法。
霍乱虽然与《伤寒论》之霍乱病源和轻重不同,但运用《伤寒论》的辨证和方药,如用理中汤、四逆汤等却能收到很好的疗效。徐子默在《吊脚痧方论》中就明确指出以温经通阳之药为治。这一观点,历代以来虽有徐灵胎、王孟英等人反对,谓霍乱属热不可以热药疗治,但从病证有腹痛、米泔样便、手足厥冷等一派寒象来看,用姜附四逆辈方为契合,这也为实践所验证。当年章太炎先生就指出,四逆汤之疗效,和西医的樟脑针、盐水针(补液)效果不相上下,而且原理也相同。在当代,治疗霍乱的几大原则不外乎是输液或口服药物以补充水及电解质,使用抗生素(如磺胺、呋喃唑酮、四环素、强力霉素等)治疗并发症和对症治疗。运用中医药治疗霍乱是值得重视的,早在《内经》的运气学说中,就指出不同类型的气候模式与某些疾病流行相关。1951年,郁维对上海1946~1950年霍乱流行的研究,证实了霍乱流行与大气的绝对湿度有关。
1961年的埃尔托型霍乱,也曾出现于我国广东沿海,后曾波及二十余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造成一定的危害。而1992年于印度及孟加拉等地流行的霍乱,已经证实是埃托型的变型所致,该菌定名为0139。现已波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尼泊尔、我国香港及欧美等地,我国1993年在新疆首先发现0139,5年多时间报告300余例,仅占同期爱尔托病例的05%。目前,在发展中国家霍乱的流行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扰的公共问题。1997年霍乱在扎伊尔的卢旺达难民中大规模爆发,造成7万人感染,1.2万人死亡。这证明,霍乱仍是灾难性的,这也说明第7次流行还没结束。
公元前780年,我国陕西地区发生了一次大的自然灾害,古籍《诗经》上有这样的记录:
本文2023-10-09 07:02:24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112649.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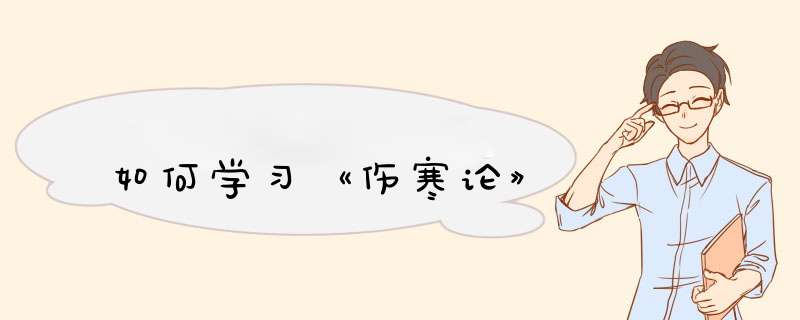



来传递信息.A.声音B.气味C.动作D.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