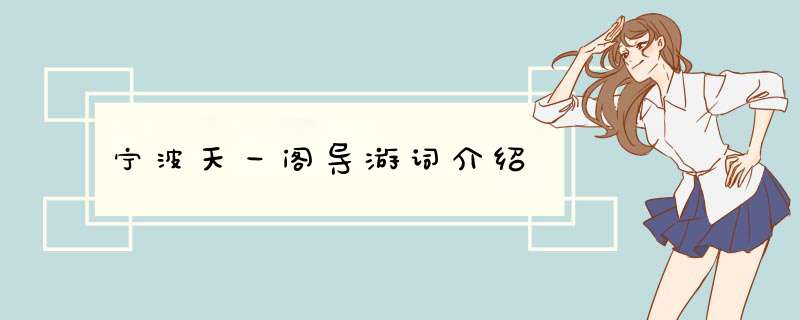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的发现

■李世民的衣冠冢遗址确认、发掘出了长孙皇后墓葬及生前守陵的宫人墓葬
2003年隋唐史学者、昭陵考古队队长张建林掩饰不住他的喜悦,刚刚发掘出了昭陵的寝宫遗址,遗址由一个近似方形的围墙把它围起来,里面有大型的建筑基址。寝宫实际上是唐代进行昭陵祭祀的最主要的场所,里面放置着唐太宗生前所戴的帽子、所穿的衣服和用过的器具。常年供奉的珍馐佳肴、灯烛蜡台等也放在寝宫里。唐朝后世皇帝亲谒昭陵的时候,先要让衣冠出游,就是抬着衣服和帽子,出来普照天光游行一圈又放进去。大批的守陵宫人生前也住在寝宫。宫人就是李世民生前的宫中妃嫔亦无子者,天子薨后被胁迫到昭陵来。宫署所在地、护卫陵园的将士也驻扎寝宫附近。
唐朝的石刻廊房基址里面,还发现了清代祭祀的大殿遗址。此遗址的地下80公分处叠现了唐代柱石。对于这些唐代柱石,若本来就在此,那上面原来是什么样的建筑和用途;若是后世借用唐柱,又是从何迁来,还有待继续考证。
这次勘探对昭陵“以山为陵”的“九嵕山”上的九洞有了更准确的认识,这些洞是墓的可能性得到确证。其中一个规摸较大;另外八个是小洞,规模较小,里面陈设简单,所放的东西也不讲究。过去学者认为这些洞是千年前修筑陵园的匠人生前所住之地,但在皇帝陵山上,为了工匠们居住方便,就近凿洞是破坏风水的,结合出土的物品推测小洞是宫人墓。
大洞更加肯定是墓葬了,墓葬所需要的元素它基本都有,洞口朝南,紧接着是墓道、墓室、墓室里面是棺棚,墓室顶部穹隆顶画着壁画,这些特征都符合墓的要求。长孙皇后临死嘱咐唐太宗,要俭薄:“请因山而葬,不需起坟”(《旧唐书》卷五)。昭陵博物馆副馆长李浪涛说,这次发现的石山上最大凿洞墓葬,应该是长孙皇后的,她于贞观十三年仙逝,后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驾崩时,长孙皇后与太宗皇帝一起重新合葬在了昭陵的地宫。此墓从此就荒了下来,形成一个空洞墓。
另一个重大的新发现就是昭陵东北角的又一丛葬窑,这个窑是用石头堆起来的,共两层,四孔窑洞,里面有铠甲马、陶人等。汉景帝杨陵有丛葬坑,秦始皇陵墓有兵马俑坑,那么以山为陵的昭陵就以“石窑”来置陪葬品。过去于一九六五年做过一些调查,这回彻底把此石窑清理出来了,结构也弄清了。窑最深处八米,做工非常精细,石头打磨得有大头小头,大头七寸,小头五寸;结构极其严密,连缝隙的灰缝都撬不下来,验证了史书上说的“糯米汁共白灰偕浇注”。汉杨陵随葬坑共有81个,昭陵发现类似陪葬窑8座,陵山上其它地方是否有还待继续查探。 ■北司马门为隋唐最大殿堂式门址,铁栅栏隐秘水道现世,三处遗址扩延唐祭坛范围
过去人们对皇陵门的理解就是一个门址,绕着围墙,然后是一段门阙。昭陵考古队队长张建林说,实际上远远不是人们想得那般简单,刚刚全部清理出的唐代昭陵北司马门和北阙的基址,证明它是一个建筑群体,且是祭祀性的,由门阙、列戟廊、廊房、门址、围墙等构成。被专家才恢复原位的唐门墩石遗址,旁边为柱石和门框,两个柱石分隔成了三门道,即北司马门,连着围墙成内八字形。昭陵考古队副队长王小蒙说,因为明清帝王为昭陵建的北门是在唐废墟上筑的。所以的发掘,顺理成章地知晓了明、清两朝的昭陵北门建筑群的总体布局、结构和功,它们先是碑刻、再是金石、最后是陵园内部建筑。
参与发掘的昭陵博物馆副馆长李浪涛则说,从出土遗址的性质还可以判断出,北司马门是殿堂式的门址,是全国隋唐建筑遗址的第二例发现,另一例就是长安城大明宫内城门,其它的唐代门址基本都是过梁式的,拱圈式的门是在宋代以后才出现的。而且,北司马门体量比大明宫内城门大———大明宫的门址是三台阶,昭陵的门是五台阶,所以此陵门对唐代建筑甚至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有了格外的“分量”。
北司马门里的建筑主要是唐朝石刻长廊,过去没有发现过。由于西侧的地势比较高,这处的石刻屋顶建筑基址保存的相对完好一些;东侧由于比较低,除了清代围墙以内的遗址,基本上都破坏掉了。但可以比照西侧,把东侧的还原回来,因为建筑原则是不能改变的。
令考古人员欣喜地还有,北司马门里发掘出了唐时水道,主渠外有副渠,既能排墙顶、门庭雨水,又能泻山洪。这条保存完好的水道里,最称奇的是竟与一暗水道相连,道口用了五块石条上下左右撑起来,暗道中间还用6根铸铁竖成栏杆,既能起支撑作用,又能阻隔柴草漂浮物,还能挡盗贼从水洞潜入陵园;暗道里面还发现了一块山字型的砖,作为一个“山”柱子支撑,与桥梁很相似,减压分水。张建林说,暗水道做得如此讲究,关中的大型唐代建筑里,是首次发现这种铸铁栅栏的出水口;就全国来说,这种暗道只在扬州的唐城里面发现过,其它地方再没见过通例。最不可不佩服的是,暗道里面的铸铁栅栏千年水中流蚀,出土时竟然没有生锈,唐人防锈技术可谓高矣。此暗道的七级台阶,可以把大量的雨水减缓,以免对栅栏和墙基造成冲击,设计相当巧妙。
这次发掘的实物,纠正了一些古代典籍、学者对昭陵认知上的偏差。古籍上记载昭陵“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但北司马门的发掘,改变了此误传,“朱雀门”与“玄武门”之名学者以讹传讹所致,昭陵南门应该叫“南司马门”,陵园门一般是对称而名的。张建林进一步分析,以“方位四神”取陵门名是不符合大唐皇家礼仪的。除了北司马门遗址,考古队另发现了三处唐迹,年代都稍晚一些,是德宗时对昭陵进行了一次大的维修后所留,从所出的烧灰、陶器、陶罐来看,“生活痕迹”明显。这三处出土遗迹,扩延了对昭陵祭坛的划限范围,过去以为的北阙、北司马门和列戟廊就是完整的祭坛,但这些遗迹都在列戟廊之外了,向东、西伸展了。 ■首次发现昭陵六骏的原始鬃丝、六骏原始基座,美国学者专程来看
“自从昭陵六骏1914年离开这个地方以后,这是首次本年度内陆续发现与六骏有关的一些东西”,张建林说,“除了六骏的残块以外,还搞清了昭陵六骏排放的原始位置和原始架构。”昭陵六骏都有基座,每个座都由三层组成。当年唐太宗下葬时为了使六骏显得醒目,座基是非常高的,复原高度距现在地面足1米多。当晓知昭陵六骏的文物出土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部负责人周秀琴万里迢迢来昭陵考察。
今人看到的六骏被盗窃前的基座,其实不是唐朝时六骏的原始基座。清朝时把唐代的六骏从原始位置移动了,同时基座的上层也一块跟随移动,并被重新摆成了一堵紧连的雕壁。而此次发掘的唐代原始基座显示,当时每匹马是分开的,因为原始基座的下层并没有移动,而它们之间是阶梯间隔的。原始基座位置的确定,把一些前代学者论述的昭陵六骏曾经在第四台阶地上摆放过的看法颠覆了,六骏一直就在第五台阶,第四台阶的存痕只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被风雨冲下的滚落残片。
当年,文物盗贩为了方便搬运,把六骏打成了几块,这就是后人以为的“六骏是在那时才被破坏的”。从此次发掘的情况来看,实际上六骏早在唐末五代就有一些残损,但可能残损程度没盗运时高。今年出土的“什伐赤”蹄腕部分,应该在很早的时候就发生了,那些茬口仍棱角犀利。还有前不久出土的一片残块是“青骓”右前腿的膝盖部分,一千多年了,一直埋在地下,所以它表面没有任何的风雨剥蚀,膝窝部分的毛一丝一丝毕现,而如今不论西安碑林的四骏,还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两骏都看不到如此的毛丝,这对于后人感知昭陵六骏的原始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依据与见证。 ■出土十四国蕃郡长像,其写实雕刻对少数民族与唐朝融合历史有重大认知价值
此次发掘的一些石质头像、基座、片块,其中残块共九片,仅高昌王一人就三块,对立于昭陵的“十四国蕃郡长”,有了更加精确的认知和诠释。其中里面有四个突厥部落可汗。史书上记载,李世民熟悉胡人的生活习俗、战术,打突厥人非常得心应手,突厥人遂对李世民非常敬畏,尊称为“天可汗”。丝绸之路的四个王国,从汉到唐一直是中原与外国贸易、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唐初就把这条路彻底打通了。还有一些更远的政权,如南亚的婆罗门,当时李世民借吐蕃与尼泊尔的兵把它的国王俘虏到了长安。再有一个林邑王,越南南部一带的国王。还有新罗(朝鲜半岛)乐浪女郡王,及游牧在青海、甘肃一带的王国。除了东南海外之国,可以说十四个酋长国是唐王朝核心统治区的周遍所有政权的总和,包括有突厥可汗、吐蕃赞府、于阗王、焉耆王、高昌王、薛延陀可汗、吐谷浑可汗、龟兹王、林邑王、新罗乐浪女郡王、婆罗门王等。
李浪涛说,这些重新见阳光的“郡王”的另一重要价值,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讲,它们是“写实性”的。每个王都写清了他的祖述、名字,这样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部落和部落之间的差异,作为单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在石像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四国蕃郡长有戴长帽的、有卷发的、有直发的。本次考古发掘还确定了十四国蕃郡长的分布,自北宋以来,对十四国蕃郡长谁在东边、谁在西边一度混淆,甚至把一个人的名字分成两个人,根据基座与石像的成功对接,已经把西侧的人确定了,西侧是西北少数民族,比如吐蕃赞布、高昌王、焉耆王、于阗王、薛延陀可汗、吐谷浑可汗、龟兹王。而这些归附唐朝中央的国王清晰的“祖述”石刻文,对于研究唐王朝与周遍地方政权的交往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甚至弥补一些史料空白。
清代建祭祀大殿的时候,把唐时的屋子面积缩小了,这样十四国蕃郡长像就晾在外面了,仅把昭陵六骏用廊坊盖了起来。而重新面世的蕃郡长基座显示,十四国蕃郡长与六骏一块本来放在七间房内的。 ■昭陵东、西两门成悬案,昭陵地宫虽五代被劫,但文化珍宝依然会有
《长安志图》记载:“以九嵕山山峰下的寝宫为中心点,四周回绕墙垣,四隅建立楼阁,周围十又二里”。令人遗憾地是,还没有发现昭陵的东门和西门,以及围绕整个陵山的墙垣。如果有东、西两门的话,门的建筑肯定毁掉了,但对门阙来讲,它有两个土堆遗址,比如它封土的砖瓦应该有所保留,但到今天依然没有发现。以昭陵一前一后的两个陵园来类比,献陵的四个门都有,乾陵的四个门也有,单单九嵕山上没发现,给学人留下了巨大疑问。
昭陵其年修筑时,文献描述,在南面山腰凿深75丈为地宫,墓道前后有石门5重;墓室内设东西两厢,列置许多石函,内装随葬品。五代军阀温韬盗掘昭陵也目睹“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这都可想象这个“山下宫殿”内部寝殿层层窍深和宏丽的情景。宋初开宝四年,宋太祖让地方官员对被盗掘过的前朝关中帝王陵的墓统统进行掩埋、修缮。九嵕山是高耸天宇的石质山,一旦洞口被盗开,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掩埋,就是把上面的石头炸掉,用乱石头把墓口封住。经过千年的沉积,整座山到处灌木丛生,野草遍布,根本找不到地宫洞口。但是,时人皆知昭陵在凿玄宫的时候,是在一条险峻栈道上开挖的,所以应该在陡峭的崖壁上。张建林说,盗窃过并不意味着昭陵地宫里面再没有其它东西,像壁画、陶俑,包括一些金银器洒落或者遗失在墓都应是基本的遗存,石棺椁、石棺床、墓志铭、陶俑也是绝对有的,盗墓人对这些不感兴趣。再说,诸多王陵历史上被屡次盗窃,如今不也发现了许多文化珍宝吗。对于是否开挖昭陵地宫,大家一致认为,抢救性的发掘陵园地面濒临消失的文物遗址已经很繁复芜杂了,根本没有精力去勘探皇家地宫;当今的保护技术还没有能力把一些珍贵出土文物进行有效保护,所以也不应该轻易去发掘昭陵地宫。
史前时期的祭祀遗迹,
缘何能实证数千年后的古籍记载?
风格迥异的远古陶器,
诉说着怎样的光阴变迁故事?
城头山的两千年兴衰史,
如何窥见早期中华文明起源?
《中国考古大会》第八期
带您走进城头山遗址,
探秘长江中游史前文化!
洞庭湖畔的澧阳平原,
一片圆形土岗
隆起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人们世世代代在此播种耕作,
而一段数千年前的岁月,
就深藏在这片沃土之中:
1979年7月的一天,
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文化馆的
曹传松下乡工作,
在南岳村旁望见坦荡的平原上,
有一处土岗突兀地隆起。
这一发现让他好几天夜不能寐。
强烈的直觉指引着他回到土岗,
着手开始进行考古调查。
由此,
一段沉睡的 历史 被唤醒了。
自1991年起,
城头山遗址经历 15次 考古发掘,
出土文物 一万六千多件 ,
发掘出 6300多年前的水稻田 、
6100多年前的城墙 ,
以及浓缩了
岁月沉淀的丰富陶器……
就这样,
一座年代远超想象的史前城址
重现于世!
起源于中国的水稻,
是世界上最早
被人类驯化的农作物之一,
今天,
稻米养活了世界上
超过60%的人口。
湖南道县玉蟾岩,
发现了距今约一万多年的炭化稻;
距今8000到9000年间的
彭头山遗址中,
也发现了大量稻谷遗存。
澧县八十垱遗址
出土过近万粒
距今8000多年的炭化水稻,
在城头山遗址的发掘过程中,
再次发现了古水稻的踪迹。
1996年12月,
考古工作者曹传松
在城头山东门城墙探沟底部,
发现一条规则的土埂,
土埂两侧有厚达30厘米的
灰色平整软泥。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
一个月后,
人们又发现了第二条土埂,
同时还有一块
覆盖着陶片的田螺标本,
以及泥土中的许多稻粒。
考古人判定,
这里曾经是一片水稻生长区。
随后,
第三条土埂被清理了出来,
三条土埂合围形成长条形区域。
考古专家对这片区域泥土
进行了光释光测年,
判定它距今6300年左右。
那么这片6300多年前的水稻,
究竟是野生的,
还是人工种植的呢?
在探秘空间中,
“考古推广团”的成员们
解开了水稻的秘密:
他们通过
对水稻基盘衔接面的撕扯痕迹,
判断出这些水稻
属于人工种植而成。
成熟的稻作农业体系,
促进了城头山的建立,
促进了 社会 的发展,
它成为长江中游地区
稻作农业发展影响下的一个缩影。
史前时期稻作农业
对中国文化基因的塑造,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水稻的种植需要精耕细作,
是非常精密的一套程序。
它也因此影响了
长江流域人们的性格,
让他们变得更为细腻。
可以说,
一粒小小的稻谷
催生了一座大大的城,
推动了更灿烂的文明的萌发,
更积淀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
稻作农业在史前时期的发展,
也成为 “以农为本、农耕中国”
文明基因的源头。
新石器时代的澧阳平原上,
先民们选择了
城头山作为定居场所,
开始挖壕筑墙。
沿地势而建的圆形城墙堆筑起来,
合围之内,
远古先民探寻着
与天地和谐共存的法则,
耕种劳作、繁衍生息。
1991年,
城头山遗址拉开了发掘大幕。
最先发掘出来的城墙,
成为当时考古学家研究的重点,
为了判定建造年代,
考古学家对城头山的西南城墙
进行解剖。
历时8年的发掘研究,
最终得出结论:
城墙共分四次修筑。
四期城墙间的土层里埋藏的
陶器、陶片等生活遗迹,
是城头山遗址
留给后世的一份重要密码。
从一期到四期城墙,
稻作农业水平在发展,
先民们的生产力也提高了,
城头山先民们
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
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
在节目中,
我们可以看到
城头山先民的生活场景:
在他们的居住区域,
各类房屋聚集于此,
祭坛区域
正在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
各类精美的陶器
则在制陶作坊区域里诞生。
6000多年前的城头山先民,
就在这座圆形城池里,
繁衍生息。
从栽培水稻到筑城安家,
再到城中悠然有序的生活,
在城头山
我们不仅看到了
进入稻作农业 社会 之后,
人类改造自然,
又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状态;
更看到了
长江中游地区史前人类
文化发展的片段。
城头山真的是
好比一段凝缩住的时光,
我们能从城头山遗址中
看到上一段时光奔涌而来的变化,
也能从城头山之后,
看到后一段奔涌而去的变迁,
身处其中,
经历一场 历史 的穿梭。
这还不够,
让我们跟随
《中国考古大会》的脚步,
继续在这条史前长河游览一番,
去看一看城头山里的时光记录器
——陶器。
陶器,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土与火的交集展现出伟大的创造,
改写了人类的 历史 。
六千多年前的城头山先民,
已经把这项技艺运用得炉火纯青。
城头山目前已发掘的十座陶窑,
其中七座位于城址中部,
有的专门用来烧制红烧土块,
用于建筑材料,
更多的是用来烧制各种器具。
规整的陶窑中遗留着灼烧的痕迹,
似乎还能让人感受到
几千年前制陶的余温。
拌料坑、贮水坑,
清晰地讲述着
城头山人井然有序的制陶工序。
邻近还有许多仅见柱洞,
不见基槽的遗迹,
有可能为简易工棚建筑,
它们与陶窑一起,
构成了完整的制陶区。
实用性和艺术性
同时出现在城头山陶器上,
这些来自远古的陶器,
不仅让我们窥见了
先民的生活样态,
更为研究长江中游地区
史前文化发展的 历史 脉络,
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实证。
节目还为观众们准备了
城头山遗址出土的陶器复制品,
从一件件精美的陶器
与专家讲解中,
仿佛还原了炊烟袅袅,
一家其乐融融的城头山人
炊煮吃饭的场景。
这也恰恰体现了陶器是时光的记录器。
城头山跨越的五个文化期:
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
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
和石家河文化,
我们都能够找到相应年代的陶器。
都说城头山是长江流域的文明之山,
是长江文明的圣地。
城头山遗址的发掘,
让我们再一次确信:
稻作农业的起源,
造就了具有独特特点的
中华农耕文化。
今天我们一起感叹古人的智慧,
感慨今人的传承,
“吾辈生于今日,
幸于纸上之材料外,
更会创新性地守护好,
创造性地发扬好地下之材料”。
澧水下游,
洞庭湖畔,
城头山静卧其间,
先民们曾在此种稻制陶,
挖河筑城,
用智慧和勇气改善生存环境,
见证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
这是几十年考古揭示的一段 历史 ,
是稻作农业文明结出的丰硕果实。
7月17日(今天)17:30
锁定CCTV-4
一起来《中国考古大会》
身临其境地感受
新石器时代
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发展!
良渚文化遗址群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群,距今5300-4000年,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它范围广阔,内涵丰富,分布于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的50余处。其中以反山墓葬群、瑶山祭坛和莫角山土筑金字塔等几处最为重要。遗址群中发现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出土物中以大量精美的玉礼器最具特色。据战国古籍《鹖冠子》记载说“成鸠氏之国……兵强,世不可夺”,实际上就是说良渚文化集团的武力强大,天下无敌。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显示出良渚文化遗址群已成为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浒墅关“赵王坟”发现的金砖,清晰地刻有“乾隆伍拾玖年成造细料贰尺贰寸金砖”边款。
高新区浒墅关镇上塘地区近日发现南宋“赵王坟”遗址,现场挖出部分金砖。经苏报牵线,考古部门前天傍晚已紧急介入。
热心读者、“吴文化学习群”QQ群友钟华6日下午向苏报报料,浒墅关上塘地区在平整地块时,在浒墅关中心小学原址处发现“赵王坟”遗址,里面出土了不少清代金砖,品相较好的已被一些挖掘者取出并随意买卖。钟华还发来了一张由他拍摄的金砖侧面照片,上有“乾隆伍拾玖年成造细料贰尺贰寸金砖”边款。
相城区长期从事金砖制作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高级工艺美术师袁中平看过照片后表示,这些金砖款识很清楚,做工也很好。袁中平说,金砖一般用于宫殿的铺地,但次品也会被挪作他用。“赵王坟”的金砖颜色有点发红,可能火候不到,因此才会被用在坟地上。尽管如此,这些金砖依然颇有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
《浒墅关志》主编殷岩星介绍,根据古籍记载,“赵王坟”是南宋中期定城(今属河南省信阳市)知县赵用及妻子的合葬墓,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相传赵用曾被封为“王”,故墓地被称为“赵王坟”。清代嘉庆年间该墓曾进行过修缮,所以墓地会出现嘉庆皇帝之父乾隆时期的金砖。二十世纪50年代,该墓还存有土墩、假山,占地09亩,后来逐渐失去原貌,以致外界认为已不复存在,没想到这次被重新发现。
接到报料后,苏报立即将情况反映给市考古研究所。前天傍晚,该所已派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踏看,发现少量残损金砖。目前,市考古研究所已要求当地 加强现场看管,并将进一步研究是否对该遗址进行考古挖掘事宜。(施晓平)
本文2023-08-04 16:24:46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122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