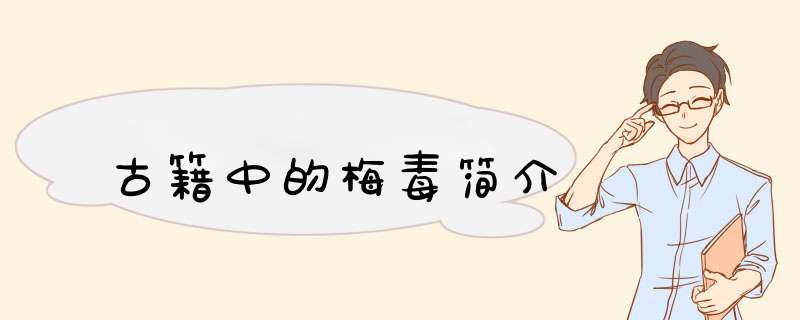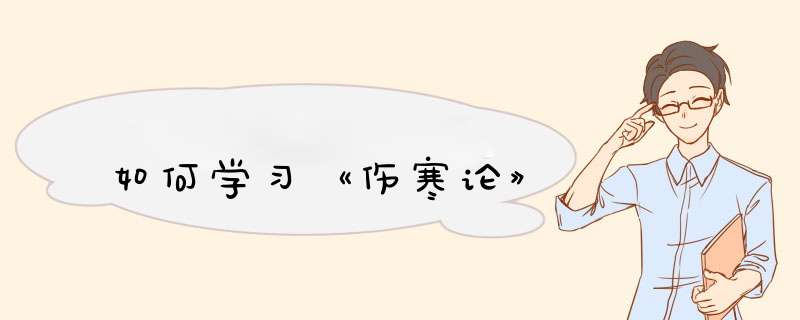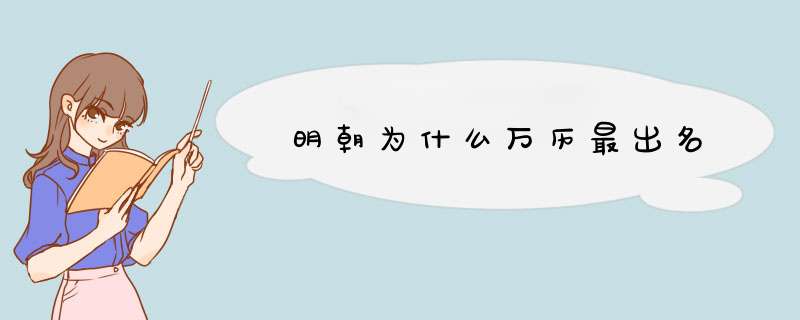在古代一次大型的疾病(如瘟疫)能死多少人
能死多少人.png)
又名又老的中医泰斗邓铁涛先生经常信口开河一些昏话,比如他曾说“中医
不怕流感,早在1700年前的汉代张仲景已留给我们有效的学术与经验,加上明清
医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胸有成竹!”,“中国从未有一次瘟疫流行死亡过百万,
上世纪60年代流感流行就被‘达原饮’一个方子制止了”。我在37度医学网论坛
里曾经对老先生的惊人之语作过一番“考证”和批驳,完全可以为他的“昏话”
作一个注解!
古代瘟疫的说法很多,古籍记载约有数十种,如疫、疫气、疠气、疫疠、温
热、天行、疠、瘥、大头瘟症、疾疫、大瘟、痘疹、痘疫、疙瘩瘟、羊毛瘟、疟
疾、天花、番痧、螺痧、痧症、烂喉痧、喉症、痒子症、瘪落痧、痒疥疾、首疾、
气疾、茄妈瘟、闷头疟、疫瘴、霍乱、转筋霍乱、阴霍乱、鼠疫、鼠瘘等等。无
论何种名目,毫无疑问,古人并不知道瘟疫的真正原因!吴有性虽然天才地感觉
到“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究竟是一种猜测。人类真正认识瘟疫原因的是从病
毒学之父巴斯德开始的(详情略)。
从历史看,中国大疫频发,史不绝书! 现知最早的疫病发生于殷商,甲骨文
有:“贞:疒�不�。”意思是说:当时疫病流行,人们去占卜,希望疫病不要
再流行。从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这 2632年间,共记载有772年次程度不等的
瘟疫,平均不到4年就有一次。从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发生大疫238次,
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大疫流行时,往往“死者不可胜计”,“丁尽户绝”,
“户灭村绝”,是真正的人间惨象!
自西周以来,中国历史上瘟疫大流行的高峰期有以下几段时期:
一是西汉至东汉时期。东汉末年从公元204年至219年,中原地区瘟疫凶猛。
张仲景:“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
伤寒十居其七”(医圣家族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他又哪有什么可以效验千年
的“有效的学术与经验”呢!) 。特别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人尤多。魏
文帝曹丕:“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
。尽管当时没有准确的数字统计,也不难想象这种疫病究竟猖獗到了什么程度!
另一是明末至清初(公元16—17世纪)。从1109年至1234年,“疫死者半”、
“开封大疫,诸门出柩90余万人。”明代万历、崇祯至清康熙年间,即1580至
1663年,疠疫流行,死亡枕籍。最严重的是1641年,南北两直隶,山东、安徽、
浙江、贵州、湖南等地疾疫大作,山东东明县“春二月瘟疫大作,有一家死数口
者,有一家全殁者,白骨山积,遗骸遍野” 。1643年的瘟疫,“有疙瘩瘟、羊
毛瘟等,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月间,死者数百万…至霜雪渐繁,势始渐
杀(古人也观察到瘟疫是被“自然”所控制的,没中医什么事儿)。” 山东
“春夏间瘟疫盛行,甚至户灭村绝。”有历史学家保守估计,明末大瘟疫死亡人
数在千万以上。中医对付这种瘟疫又何尝“胸有成竹”过呢!
近代中国瘟疫大暴发是从光绪十四(1888)年、民国十(1921)年和民国二
十一(1932)年。仅1888年霍乱流行,被清政府统计到的感染的市县达 306处。
1900--1949年,“仅仅死于鼠疫的人数就有102万。病死率89%”1921年,云南瘟
疫流行,病名是“烂喉丹痧(猩红热兼白喉)”。连“云南省长刘祖武全家传染
此症,不治死亡”。
总之,只要不是睁眼说瞎话,我们从历史里从来就看不到中医曾经对瘟疫有
过有效的办法,医圣张仲景也不例外!铁涛老自豪而轻松的狂言不过是昏话而已!
http://xysfreednsus/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7/zhongyi148txt
明末崇祯时期的瘟疫
崇祯朱由检是明朝最后—个皇帝,当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自然灾害不断,农民起义不断。崇祯年间,明朝统治区域内许多地方都流行起了鼠疫,尤其是崇祯末年,各地的瘟疫是一场连一场。 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突然很多地方出现疫情。万历《山西通志》记载这年垣曲、阳城、沁水大疫,“道□相望”。高平、辽州大疫,“死者甚多“。这年山西南部普遍出现旱灾,而疫情主要是在山西东南地区流行。沁州沁源县城中仅数百家,但由于“岁荒,斗米钱半千,夏遭瘟疫,死者不计其数”。 崇祯七年、八年,山西西部靠近黄河的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社会不安定,自然灾害交加,兴县就出现了疫病,“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之为空。” 靠近兴县的临晋这年也有大疫,疫病的高峰在三四两月之间。 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自北到南瘟疫大流行,这年大同瘟疫流行,“右卫牛也疫”。十四年,“瘟疫大作,吊问绝迹,岁大饥”。南部的稷山县也出现大疫“死者相枕藉”。崇祯十六、十七两年是山西流行瘟疫的高峰。浑源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甚有死灭门者”。崇祯十七年大同府“瘟疫又作”,而灵邱县“瘟疫盛作,死者过半”。南部的潞安大疫,“病者生一核,或吐痰血,不敢吊问,有阖家死绝不敢葬者”。 疫情也传到河南地区。河南内黄县《荒年志碑》记述了黄河两岸崇祯十三年“风大作,麦死无遗,有家无人。食糠榆皮,受饥者面黄身肿,生瘟疫,死者过半”。崇祯十四年,中原大地疫病四起。春二月,内黄县一带家家遭瘟,人死七分。当时有地无人,有人无牛,地遂荒芜,偃师县“春大疫,死者枕藉”。阌乡县春天饥荒大疫。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商水县“春大疫,抵秋方止,死者无数。初犹棺敛,继买薄卷,后则阖门皆死,竟无一人能敛者。至六月间,街少人迹,但闻蝇声薨薨而已”(顺治《商水县志》)。这些地区的疫病十分剧烈,挨家挨户传染,一批又—批地死人,连棺材也来不及制作,马路上吓得连行人也没有。 今江苏吴江县曾遭到连续二次的大疫袭击,崇祯辛巳年(1641年)吴江突然大疫流行。这场大疫中死去的人不计其数,死亡率之高令人惊讶。有一大户人家,先是一人染病但几天里全家数十人一一被感染,最后全部不治身死。《吴江志》称:“阖门相枕藉,死无遗类者。”这种高死亡率的疫病当时人十分少见,只觉得“偶触其气”必死无疑。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距上次瘟疫流行仅隔三年,吴江再次瘟疫大流行,得病者最主要的症状是口中不时喷血,喷血后不久就毙命不起。吴江城内死掉的人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甚至一条巷内的居民全部得了这种病而死亡,更不知有多少人全家死绝,一个活的也没留下。这场大疫持续了一个多月,夺走了大量吴江人的性命。 河北京津地区,崇祯十三年后也是大疫流行。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出现。大名府“瘟疫传染,人死八九”。第二年,河北的疫情继续有所发展。大名府上年的瘟疫传染一直延及到了崇祯十四年。当年春天无雨,“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顺德府由于连年荒旱,“瘟疫盛行,死者无数”。广平府、真定府、顺天府均出现大疫,并于这年七月疫病传进了京师。 崇祯十六年,顺天府通州于七月流行疫病,“名曰疙疸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康熙《通州志》)。京师北部的昌平州“十六年大疫,名曰疙疸病,见则死,至有灭门者”。保定府处于京师南约200多里,这年“郡属大疫”,其中雄县的瘟疫最为严重,“人心惊畏,吊问之礼几废’。疫病蔓延进京师是在这年的二月。《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这场瘟疫流行造成了20多万人的死亡。 据吴震方《花村谈往》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至十月,京师内外疫病流行进入高峰。流行的病叫疙瘩病。不论贵贱长幼,得了这种病很快就会死亡,甚至一呼病名,病就来了,不留片刻,人就死去了。患者胸腹稍满,生白毛如羊,日死人数千,很多人死了连病名都还不知道。兵科曹良直正与客人对谈,举茶打恭行礼,人站不起就死去了。兵部朱希莱拜访客人急急赶回来,刚进室内就死去。宜兴吴彦升受命为温州通判,刚想登船去上任,一个仆人就死了,另一仆人去买棺材,很久还未回来,赶去一看,这个仆人已经死在棺材店。有同在一个旅馆住宿的朋友鲍某劝吴某搬迁到另一个旅馆,鲍某先背负行李到新居,吴某稍微落后一会赶来,他看见鲍某已死在新居里。吴某赶忙又搬出去,等到第二天清晨,他也死去。金吾钱晋民陪同客人饮酒,话还未说完就断了气,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及婢女仆辈在短时间内死了15个人。又有两个同伴骑著马赶路,后面的人先说话,前面的人答了话,后面的人再说话,前面的人已经死在马鞍上,手里的马鞭还在高高扬起。沿街小户人家死的人更是无法计算,街道上已经没有人在闲谈、散步了。死的人实在太多,很多人连棺木都设有,因为棺材店来不及赶制。根据官方计数,九扇城门抬出的死者有20余万人。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谈到京师的鼠疫时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所谈和吴震芳的记述完全符合。 与京师很近的天津也受到瘟疫的侵袭,不过已是崇祯十七年了。骆养性谈到:“上天将灾害降临人间,所以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九月,疫病传染到达顶峰。感染疫病者时间长的,一二天中死亡,而时间短的,早晨得病,晚上已经死了。天津城内每天就有好几百人死亡,甚至有的全家不留一个活的。这种病一户挨著一户传染,没有一户能幸免的。只要有一个人得了病,就会传给全家人。这病在天津城内已经传播了有二个月,引起了重大丧亡,至九月达到高潮,城内外都在死人,而城中心死的更加多。现在的天津城中路途上到处都是棺材,耳朵听到的都是哀号之声,人们个个都是悲凉惶恐。”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了太原,遂分兵直趋北京。北京西北的宣府地区在李自成大军经过后疫病重又活跃,“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京师周围的瘟疫直到清初仍未停息。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保安卫、沙城堡大疫后死绝的不下一千家。康熙《怀来县志》载:“生员宗应祚、周证、朱家辅等皆全家疫殁,鸡犬尽死,黄昏鬼行市上,或啸语人家,了然闻见,真奇灾也”。
参考资料: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后世不断的完善和补充,最终形成了一个有理论支撑、有实践指导的系统性中医。
中医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由于近代以来中医从上倒下受到打压,中医的发展历经艰难。作为一个保障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医术也备受质疑,以至于有人怀疑中医在历史上是否有攻克过疾病、战胜过瘟疫?
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这就是因为中医与各种瘟疫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对决,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
说起瘟疫,最让人恐怖的当属于天花病毒,在整个天花的历史上,总共造成了数亿人死亡,而最先发现预防天花的还是来源于中医。中医名医孙思邈用取自天花口疮中的脓液敷着在皮肤上来预防天花。到明代以后,人痘接种法盛行起来。在此基础之上,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了危险性更小的牛痘接种方法。
到目前为止,天花病毒是唯一被消灭的病毒,其中中医的贡献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奠定了天花接种的基本原理。
中国疫病史鉴》记载:从西汉到清末,仅中国就发生过三百二十一次的重大瘟疫。可见人类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和瘟疫不断斗争的历史。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国古代是怎样和瘟疫做斗争的。
在古代,瘟疫发生时,朝廷又是怎样带领民众抗疫的呢?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受政治体制、医疗水平和战乱的影响,朝廷并没有专业的公共医疗监控系统。也就是现在每个国家都有的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往往发生重大瘟疫时朝廷一般会派些医官下去救治,采取迁移人口,隔绝疫区等行政手段。这其实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到了唐朝,政府终于意识到“疫”重在防。设置了医生巡疗体系,也就是专业的医官,叫医博士或者医学博士,领导一些医学生组成医学团队,到全国各地巡视。防治疫病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内容。到宋代的时候,官方在全国各地又设置了官药局,还有安济坊、养济院等医疗慈善机构。并且在唐宋两朝都比较注重对各类疾病预防知识的普及,并张榜公布对各种疾病需要的药物名称、剂量和用法。这些措施有效预防了疫病的发生。
特别在宋朝时,统治者已认识到瘟疫一旦爆发不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甚至动摇国本,危及到王朝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设置了惠及广大百姓的“惠民药房”,并于宋熙宁九年(1076)创办官办药局——买药所。也就是负责制作和出售中成药专业机构。这种药局在全国各地都有设置,每到疫情高发季节或逢旱涝荒灾之年,政府就会派医官送医送药,为百姓诊治。
到元朝和明朝时代惠民药房依然存在的。如《明史职官志》记载“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设医官,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但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明王朝统治的日腐败,惠民药局也渐渐没落。到清朝更没有重新启用这一很好的医疗机构,在清宣统二年(1910)东北鼠疫发生时,政府只是临时设立了医官局,但已没有行政效力可言,这是由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的。
其实中国古代抗疫最核心的力量来自老百姓和中医的力量。中医在传染病的防治中有很大的贡献,如宋朝时中医就研究出以人痘预防天花的方法。明朝医生就发现水的卫生很重要,就提出:山里清泉可直接饮用,但靠近人多居住的地方就需烧开喝。北宋时“医王”庞安时就曾经历过水源的污染导致开的药影响了治病效果的事件。
据说有一年大旱,湖北浠水县瘟疫流行,可庞安时发现开的药在别处可治病,在这里却不行。他通过调查走访发现村民们吃得水太脏了,他和徒弟又为村民找到干净的水源后,再施药救治,果然药到病除。清代名医吴宣嵩所著的《鼠疫治法》提出环境卫生的重要“庭堂房屋,洒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洁,房屋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
古代历代中医都很注重传染病的防治与研究。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疫病的记载,汉代张仲景就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传染病专著《伤寒杂病论》。
三国时方士葛洪写的《肘后方》中,最早记载了一些传染病的症状及诊治方法。如天花、恙虫病等。并立“治漳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劈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㢓散等治疗预防瘟疫的方剂。
民间百姓更是运用自己的智慧总结了一些跟“瘟疫”搏斗的经验。如隔离法、蜃碳法、杼井法、烧艾法。久而久之,这就成了民间的一些习俗,比如每年端午洒扫、熏艾叶、饮用雄黄酒、元旦喝屠苏酒等。这些古人的经验到现在还是有用的。
中国离彻底战胜疫情的一天越来越近 ,这其中中医药以及古人总结的抗疫经验依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虽然瘟疫会一直伴随人类出现,但人类一方面以史为鉴,一方面在医学领域不断突破,相信人类定会战胜一次又一次的瘟疫。
传染病
麻风(leprosy)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病变在皮肤和周围神经。临床表现为麻木性皮肤损害、神经粗大,严重者甚至肢端残废。本病在世界上流行甚广,我国则流行于广东、广西、四川、云南以及青海等省、自治区。建国后由于积极防治,本病已得到有效的控制,发病率显著下降。
病因及传染途径
本病由麻风分支杆菌感染引起,从染色特性而论,麻风菌和结核杆菌一样,是一种抗酸菌。麻风菌的形态和结核菌相似,但较粗短,人工培养迄今尚未成功。本病的传染途径尚未十分明了,其传染源为瘤型和界限类患者,患者的鼻、口分泌液、汗液、泪液、乳汁、精液及阴道分泌物均含麻风菌,通常认为主要传染方式是藉上述分泌液或患者皮肤病变的微小伤口(甚至无破损的病变皮肤)排出的菌感染他人,一般系通过长期的直接接触,但间接接触(通过衣服、用具)可能也起一定作用。麻风杆菌侵入体内后,先潜伏于周围神经的鞘膜细胞或组织内的巨噬细胞内,受染后是否发病以及发展为何种病理类型,取决于机体的免疫力。对麻风杆菌的免疫反应以细胞免疫为主,患者虽亦有特异性抗体的产生,但抗体对抑制和杀灭麻风杆菌似不起重要作用。在细胞免疫力强的状态下,麻风杆菌将被巨噬细胞消灭而不发病,反之,麻风杆菌得以繁殖,引起病变。本病的潜伏期长达2~4年,但也有在感染数月后发病者。
麻风杆菌不能体外培养,使该菌表型鉴定困难。最近,用麻风杆菌特异核酸探针以点印迹杂交可分析活检组织中的麻风杆菌。PCR技术已被迅速应用于麻风病的诊断。
病理变化
由于患者对麻风杆菌感染的细胞免疫力不同,病变组织乃有不同的组织反应。据此而将麻风病变分为下述两型和两类:
1.结核样型麻风(tuberculoid leprosy) 本型最常见,约占麻风患者的70%,因其病变与结核性肉芽肿相似,故称为结核样麻风。本型特点是患者有较强的细胞免疫力,因此病变局限化,病灶内含菌极少甚至难以发现。病变发展缓慢,传染性低。主要侵犯皮肤及神经,绝少侵入内脏。
(1)皮肤:病变多发生于面、四肢、肩、背和臀部皮肤,呈境界清晰、形状不规则的斑疹或中央略下陷、边缘略高起的丘疹。镜下,病灶为类似结核病的肉芽肿,散在于真皮浅层,有时病灶和表皮接触。肉芽肿成分主要为类上皮细胞,偶有Langhans巨细胞,周围有淋巴细胞浸润(图18-17)。病灶中央极少有干酪样坏死,抗酸染色一般不见抗酸菌。因病灶多围绕真皮小神经和皮肤附件,故引起局部感觉减退和闭汗。病变消退时,局部仅残留少许淋巴细胞或纤维化,最后,炎性细胞可完全消失。
图18-17 结核样型麻风
真皮内有主由类上皮细胞构成的结节状病灶,其中可见Langhans细胞,颇似结核结节,但中央无干酪样坏死
(2)周围神经:最常侵犯耳大神经、尺神经、桡神经、腓神经及胫神经,多同时伴有皮肤病变,纯神经麻风而无皮肤病损者较少见。神经变粗,镜下有结核样病灶及淋巴细胞浸润。和皮肤病变不同的是神经的结核样病灶往往有干酪样坏死,坏死可液化形成所谓“神经脓肿”。病变愈复时类上皮细胞消失,病灶纤维化,神经的质地因而变硬。神经的病变除引起浅感觉障碍外,还伴有运动及营养障碍。严重时出现鹰爪手(尺神经病变使掌蚓状肌麻痹,使指关节过度弯曲、掌指关节过度伸直所致)、垂腕、垂足、肌肉萎缩、足底溃疡以至指趾萎缩或吸收、消失。在有效的防治措施下,上述肢体改变已不复见到。
2.瘤型麻风(lepromatous leprosy) 本型约占麻风患者的20%,因皮肤病变常隆起于皮肤表面,故称瘤型。本型的特点是患者对麻风杆菌的细胞免疫缺陷,病灶内有大量的麻风杆菌,传染性强,除侵犯皮肤和神经外,还常侵及鼻粘膜、淋巴结、肝、脾以及睾丸。病变发展较快。
(1)皮肤:初起的病变为红色斑疹,以后发展为高起于皮肤的结节状病灶,结节境界不清楚,可散在或聚集成团块,常溃破形成溃疡。多发生于面部、四肢及背部。面部结节呈对称性,耳垂、鼻、眉弓的皮肤结节使面容改观,形成狮容(facies leontina)。
镜下,病灶为由多量泡沫细胞(foamy cell)组成的肉芽肿,夹杂有少量淋巴细胞。泡沫细胞来源于巨噬细胞,在吞噬麻风杆菌后,麻风杆菌的脂质聚集于巨噬细胞浆内,乃使后者呈泡沫状。抗酸染色可见泡沫细胞内含多量麻风杆菌,甚至聚集成堆,形成所谓麻风球(globus leprosus)。病灶围绕小血管和附件,以后随病变发展而融合成片,但表皮与浸润灶之间有一层无细胞浸润的区域(图18-18),这是结核样型麻风所没有的。由于患者对麻风杆菌的细胞免疫缺陷,病灶内不出现类上皮细胞,淋巴细胞也很少。经治疗病变消退时,麻风杆菌数量减少,形态也由杆状变为颗粒状,泡沫细胞减少或融合成空泡,纤维组织增生。最后病灶消退仅留瘢痕。
图18-18 瘤型麻风
表皮萎缩变薄,真皮内有泡沫细胞的弥漫浸润,后者与表皮层间有一薄层无细胞浸润区相隔
(2)周围神经:受累神经也变粗,镜下,神经纤维间的神经束衣内有泡沫细胞和淋巴细胞浸润,抗酸染色可在泡沫细胞和Schwann细胞内查得多量麻风杆菌。晚期,神经纤维消失而被纤维瘢痕所代替。神经病变的临床表现和结核样型相似。
(3)粘膜:鼻、口腔,甚至喉和阴道粘膜均可受累,尤以鼻粘膜最常发生病变。
(4)脏器:肝、脾、淋巴结和睾丸等脏器常被瘤型麻风波及,可伴有肝、脾和淋巴结的肿大。镜下皆见泡沫细胞浸润。睾丸的曲细精管如有泡沫细胞浸润,可使精液含有麻风菌而通过性交传染他人。
3.界限类麻风(borderline leprosy) 本型患者免疫反应介于瘤型和结核样型之间,病灶中同时有瘤型和结核样型病变,由于不同患者的免疫反应强弱不同,有时病变更偏向结核型或更偏向瘤型。在瘤型病变内有泡沫细胞和麻风菌。
4.未定类麻风 本类是麻风病的早期改变,病变非特异性,只在皮肤血管周围或小神经周围有灶性淋巴细胞浸润。抗酸染色不易找到麻风菌。多数病例日后转变为结核样型。少数转变为瘤型。
麻风的早期诊断和分型有赖于活体组织检查。及时的有效治疗可治愈。
瘟疫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温疫在我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瘟疫成人类头号杀手列入八国首脑议题
近期,八国集团***(G8)将在日本冲绳举行年度会议。鉴于包括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等在内的传染病已成为人类头号杀手,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数计,如何遏止全球瘟疫的蔓延将首次正式列入此次会议的议题。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言人格里高利-哈特尔表示,“此举标志着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三种传染病很有可能彻底摧毁人类经济和社会结构。相反,如果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能共同为此做出贡献,事情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共有35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70%的人生活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该地区迄令为止已有1100万人死于艾滋病。
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患者最后都死于肺结核,后者每年夺去200万人的生命,同时又有800万人感染,几乎全部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疟疾只需借助蚊子叮咬就可以传染,在非洲,它每年要夺取100万人的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发展中国家,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疫这三种传染病使各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过去35年中,仅疟疫一种传染病就使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了三分之一。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一次重大艾滋病会议上曾表示,他将在八国集团***会议上敦促其他国家的***支持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水平。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八国集团所做的允诺往往最终不能兑现。例如,去年,八国集团曾宣布将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削减1000亿美元的债务,但迄令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采取具体行动。
有鉴于此,正在积极呼吁向贫穷国家提供廉价药品的世界慈善医疗卫生阵线(MSF)警告说,八国集团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所许下的诺言。
MSF女发言人萨曼莎-波尔顿说,“八国集团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生产一些普通药品,如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酶病毒药品,以使这些国家摆脱对国外大医药公司的依赖。”
此外,鼓励、支持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要,研制新药品不应该象商品一样为某个跨国大公司所垄断。肺结核的治疗就是一个突出例子。目前仅有的一种疫苗还是在1923年发现的,此后,几乎没有人再去研究新的更为有效的药品。而这种名为TB的疫苗经过30多年的运用之后,不仅价钱昂贵,而且药力也在逐渐下降。
波尔顿说,“肺结核是穷人的疾病。如果感染了肺结核,你必需呆在医院里几个月,无法工作,而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根本负担不起的。”
霍乱病传入中国,使用了传统的霍乱病名。早在《内经》中,就曾多次使用霍乱这一病名。如《灵枢•五乱》篇说:“乱于肠胃,则为霍乱”。《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土不及,民病飨泄霍乱”。《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汉书》说:“闽越夏月暑时,欧(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
《伤寒论》对霍乱的症状和治疗都有比较系统的阐述,如“呕吐而利,此名霍乱”,这些都说明,霍乱在汉代已是众所熟知的病名了。
对霍乱弧菌引起的霍乱,学者们多遵从伍连德在《霍乱概论》中的论述,认为是从清嘉庆二十五年即1820年传入中国的。他是依据宋如林在重刊林森《痧症全书》序中所言:“嘉庆庚辰(1820年)秋,人多吐泻之疾,次年辛巳更甚剧”。又云:“此症始自广东,今岁福建台湾,患者尤甚”。余云岫在《流行霍乱与中国旧医学》一文中考证,中国之有霍乱,约在1817年,由印度经陆地传入,此前虽有记载,皆不能确定为真正霍乱。对此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1817年的传入没造成特大流行,可从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1817年由印度源起造成世界大流行时,霍乱就传入了中国,故首次传入应从1817年算起。日本井村哮全也支持余云岫的观点。对于霍乱,我国似乎还有更早的记载,如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涂绅的《百代医宗》一书中记有“嘉靖甲子(1564年),人多患此疾,自脚心麻至膝上者,不胜其数,死者千万矣”。后世医生据此对霍乱有“麻脚瘟”的病名。医史学家陈邦贤认为,唐代王焘在《外台秘要》记述霍乱的症状有吐利、腹痛、手足冷、烦躁、干呕、转筋等,似已认识此病。
在世界霍乱的七次大流行中,我国每次都是重疫区,并且在两次流行的间期也患者不绝,病毙者甚众。据伍连德《中国霍乱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疗法概况》记载:“自一八二零年英国用兵缅甸,一旦霍乱流行,直由海道经缅甸达广州,波及温州及宁波两处,以宁波为剧。次年,真性霍乱遂流行于中国境内,由宁波向各埠蔓延,直抵北平、直隶、山东等省。一八二六年夏由印度传入中国。又自一八四零年由印度调入英印联军,遂造成第三次之霍乱流行”。陆定圃《冷庐医话•卷三•霍乱转筋》中说:“嘉庆庚辰年(1820年)后,患者不绝”。王清任《医林改错•下卷•瘟毒吐泻转筋说》中也说:“道光元年辛巳(1821年),病吐泻转筋者数省,死亡过多,贫不能葬埋者,国家发币施棺,月余之间,共数十万金”。在清代,以光绪十年(1888年)流行最盛。在民国时代,以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霍乱流行最广,波及城市达306处,患病者达10666人,死亡者达31974人。
霍乱传入我国后,因不知病源,医生则据症状名病和预防。徐子默在《吊脚痧方论》中,称此病为“吊脚痧”,同书又以付题称为“麻脚瘟”,田晋元则在所著《时行霍乱指迷》一书中,称为“时行霍乱”。民国初年,也有据英语者称此病名为“真霍乱”。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在法定文献和教科书中便称此病为霍乱,而不再称“真霍乱”和其他病名了。在王孟英所著《霍乱论》中,提出在春夏之际,在井中投以白矾、雄黄,水缸中浸石葛蒲根及降香为消毒预防之法。
霍乱虽然与《伤寒论》之霍乱病源和轻重不同,但运用《伤寒论》的辨证和方药,如用理中汤、四逆汤等却能收到很好的疗效。徐子默在《吊脚痧方论》中就明确指出以温经通阳之药为治。这一观点,历代以来虽有徐灵胎、王孟英等人反对,谓霍乱属热不可以热药疗治,但从病证有腹痛、米泔样便、手足厥冷等一派寒象来看,用姜附四逆辈方为契合,这也为实践所验证。当年章太炎先生就指出,四逆汤之疗效,和西医的樟脑针、盐水针(补液)效果不相上下,而且原理也相同。在当代,治疗霍乱的几大原则不外乎是输液或口服药物以补充水及电解质,使用抗生素(如磺胺、呋喃唑酮、四环素、强力霉素等)治疗并发症和对症治疗。运用中医药治疗霍乱是值得重视的,早在《内经》的运气学说中,就指出不同类型的气候模式与某些疾病流行相关。1951年,郁维对上海1946~1950年霍乱流行的研究,证实了霍乱流行与大气的绝对湿度有关。
1961年的埃尔托型霍乱,也曾出现于我国广东沿海,后曾波及二十余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造成一定的危害。而1992年于印度及孟加拉等地流行的霍乱,已经证实是埃托型的变型所致,该菌定名为0139。现已波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尼泊尔、我国香港及欧美等地,我国1993年在新疆首先发现0139,5年多时间报告300余例,仅占同期爱尔托病例的05%。目前,在发展中国家霍乱的流行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扰的公共问题。1997年霍乱在扎伊尔的卢旺达难民中大规模爆发,造成7万人感染,1.2万人死亡。这证明,霍乱仍是灾难性的,这也说明第7次流行还没结束。
白血病(leukemia)是指发生于造血器官,以血液和骨髓中的白细胞及其前体细胞的增殖和发育异常的一种进行性恶性疾病。
其特征为一种或几种血细胞成分的自发性、进行性异常增殖,具有质和量改变的异常白细胞(白血病细胞)在骨髓和其他器官的广泛浸润,导致正常血细胞进行性减少,临床以贫血、出血、发热、白血病细胞浸润为主要表现。国外自1845年起开始认识本病,至今虽已有一个半世纪,但病因尚未完全阐明,可能与遗传、病毒感染及某些理化因素(如电离辐射、苯、氯霉素、某些农药中毒)等有关。国内外尚无特异的药物能彻底治愈。西医采用联合化疗方法诱导缓解,但有明显的毒副作用。有资料表明,我国白血病死亡率3~4/10万,预后较差。
中医无白血病这一病名,但类似症候在历代的一些医书中有所记载。如《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中描述的“五劳虚极羸瘦”,《圣济总录虚劳门》之“急劳”等。而随着病情的发展,可逐渐形成“症瘕”。因而,白血病可归属于中医学中“虚劳”、“急劳”、“症瘕”、“积聚”、“痰核”等范畴中。
现代约自1955年起就开始应用中医药治疗急性白血病。此后,直至60年代,是我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方法研究白血病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临床资料及理论探讨文章不多,仅23篇,且多数属个案治疗经验。多数的临床经验总结主要是在70~80年代累起来的。70年代中,从中药中提取出的靛玉红、叁尖杉脂堿等,经临床验证,对白血病疗效良好,是我国发现的治白血病良药,提示开发应用中医药对玫克白血病具有广阔的前景。80年代报道病例数不断增多,至1990年为止,国内期刊共发表了有关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白血病研究的文章近200篇(包括5例以下的个案50多篇)。据粗略统计,报道的总病例数有3000例左有,使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对白血病的病因调查研究和中医学探讨,从细胞动力学、免疫学指标、动物实验对照治疗和辨证分型与血象、骨髓及血、尿环核苷酸的关系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以探讨中医中药的治疗机理。还有人系统地研究了150例急性白血病患者的脉象变化特点,认为脉象的变化与疾病性质、感邪轻重和正气盛衰有一定的规律,进一步完善了中医诊治白血病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从临床应用来看,用中药治疗白血病有两方面的倾向:是根据已知中药对白血病具有明确的疗效,且本身毒副作用较小的特点,以中药为主进行治疗。二是利用中药具有调整机体偏胜、降低化疗药物毒性的作用,以中药为辅,配合西药进行治疗。据观察,中西药合用,疗效一般优于单用中药或西药,故临床上常以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为主。此外,也有一些用气功、针灸、中成药治疗本病的零星报道。
用中医药治疗白血病虽已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但如何使治疗方案、疗效标准趋于统一、稳定,减少组方用药的随意性,提高中医药的疗效,除必要的文献研究总结外,还需要临床进一步作药物筛选,有效成分分析及剂型改革等等。
详见百科词条:白血病 [ 最后修订于2016/7/20 10:01:29 共10360字 ] 以下结果自动匹配而成,不排除出现与主题不相关的内容,请自行区分。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这只是其中一方面而已,按照中医五运六气的理论,在五运六气特殊之年份,或因某运不及刚好与司天之气想矛盾时,会爆发瘟疫。如2003年为火运不及,司天之气为太阴湿土,所以有‘九宫灾’,九即对应于人体的肺。而2009年为土运不及,司天之气也为太阴湿土,故而有‘五宫灾’,其对应于人体的脾胃。所以2009年会爆发类似霍乱型的传染病,这个需要每一个人都要注意的事情。
温疫在我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在古代一次大型的疾病(如瘟疫)能死多少人
本文2023-10-12 19:13:56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1250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