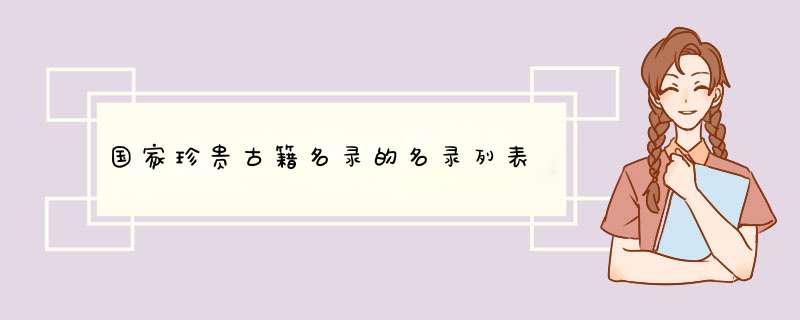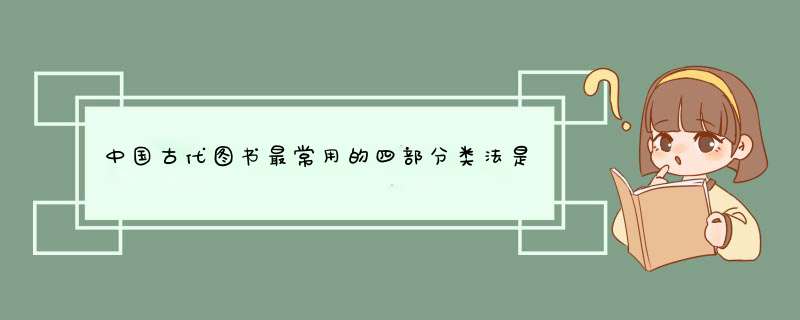日本是如何向中国学习的?

汉代以前,日本向中国学习主要采取“请进来”的方式,通过从赴日中国人那里得到先进的技术文明。汉代以后,日本开始派人到中国主动学习先进文化。中国后汉时期,日本进入奴隶社会,并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邪马台国(“邪马台”为日语“大和”的音译)。根据《魏志·倭人传》记载,邪马台国“本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我国打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后汉末年,中国在魏蜀吴三国鼎立之时,卑弥呼多次派使节前往魏国风险“生口”(奴隶)、倭锦等供品。对此,魏明帝下诏书予以嘉勉称“汝所在逾远,乃前世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还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予金印紫绶。以卑弥呼为起点,中日两国从此开始出现官方往来。到了唐朝日本学习中国的热潮逐渐高涨,当时的中国拥有辽阔的疆土,国力鼎盛,在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古代国际关系的中心,呈现出万邦来朝的局面。出于对中国大唐先进文化的仰慕和渴求,为了求的推动本民族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治国经验,日本曾在唐朝时期一次次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及僧人被通称为遣唐使。其实,早在隋朝时日本就开始派遣遣隋使,但是次数和人员不多。到了唐朝,日本来华使节和留学生急剧增加,其数量和频繁程度可谓空前绝后,达到历史顶峰。究其原因不仅是唐超开过之后国力空前鼎盛,威名远播,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历史发展恰处于奴隶社会区趋于解体的社会变革时期,当权者急需学习引入中国当时还很先进的封建社会体制,以加速本国的建设,建立和强化中央集权。公元623年即唐超建立后不久,访华归来的日本药师惠日等上奏天皇说:“大唐国者,法事备定,珍国也,长须达”。惠日的上奏促使日本天皇下定决心派出遣唐使,并把派遣唐使一事视为事关国家兴衰的战略举措予以高度重视。派遣的使团成员一般都是上层贵族和有学问造诣的人,使团经费以及乘坐的船只都由朝廷拨付经费、专门督造。经过几年精心准备,公元630年日本第一个遣唐使团出访中国。此后绵绵不绝先后达18次之多。到唐朝后期,日本已尽得唐文化的精髓,逐渐失去了越海求学的热情,同时出示中国所需要的巨额费用也使日本朝廷财政吃紧,这样遣唐使的派出便无疾而终。遣唐使的经历如一首万行史诗,反映了大和民族强烈的求知欲和不畏艰险的冒险精神。中日两国素有一衣带水之说,以现代眼光来看不过四、五百海里的距离,一两天的路程,算不得遥远,等谈不上艰险。但是,当时的日本虽为海洋国家,造船航海技术却非常简陋。据史料记载,日本的使唐船舶不过是把大树锯成方木之后,用铁片连在一起,木缝之间塞上一种细草。整个船舶既无铁钉固定,更无桶油等物密封,而且船底也不像是现代海船那样成V字形。这种船舶防漏性能很差,不能劈波斩浪,一遇大风大浪很容易解体或倾覆。不仅如此,由于不了解海洋潮流和信风的规律还常常遭遇顶峰逆流,导致迷航、翻船,而且长期在海上漂泊,还要忍受严酷的生存条件,许多人由于饮食失调、酷热冷雨而换上疾病不治身亡。所以,每一次处世唐朝都是生死难料,一入大海,就像走向战场,要于惊涛骇浪搏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18次使者中,有6次遣唐使全军覆没葬身于大海,有2次遭遇船难,只有部分人侥幸回国。航程之艰险,可举日本古籍《续日本纪》关于第10次遣唐使遇难经过为证:公元777年,日本第10次遣唐使团在完成出使任务后,从中国长江口入海踏上回国的旅程,搭乘使船的还有唐超派出的使节。惹人注目的是船上还有一位名叫喜娘的少女——客死中国的第9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和唐女所生。在船航行到东海将近日本时,突然遇到疾风大浪,使团的三艘船舶沉没两艘。包括中国使节在内的20多人葬身鱼腹,喜娘及其余人员只得将船上物资全部抛入海中,在海上漂流6天6夜,粒米未进,侥幸回到日本。作为中日友好的结晶喜娘九死一生方回到亡父的故土,收到包括日本天皇在内的隆重欢迎,写就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但遣唐使旅途之艰辛由此可见一斑。绝大多数遣唐使都有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往往能前赴后继不绝于途。因此,当时日本人往往把遣唐使出行视为英雄所为、悲壮之旅。每当任命遣唐使时,天皇都要率文武大臣举行召见、赐节刀等仪式,然后赐宴赋诗践行。例如日本孝谦女天皇时期给遣唐使践行时,上至女皇下至大臣都赋诗话别,其中一首写到“此行唐国去,事毕自归来。威武英雄业,平安奉酒杯”,遣唐事业之伟溢于言表。这些遣唐使回国之后,带回大量唐朝的文化典籍、科学技术,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遣唐使还得到日本朝廷的重用,进入权利中枢,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封建改革。其中遣唐使吉备真备作为遣唐使中的翘楚,回国后不久被孝谦女皇所赏识,受命教育皇族《礼记》、《汉书》,成为女皇的宠臣,对儒教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不避艰险到中国的日本使者和留学生,唐帝国基本上持欢迎态度,对日本使节和留学生都赏赐甚厚。个别日本人来华后还长期旅居,甚至归化了中国。比如名载史册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叫晁衡)学成后就不愿回国,留在大唐。因才华卓著,身为唐玄宗所器重,得以随侍唐太子左右,最后竟官至二品。由于唐帝国对待异族能想太宗所言“爱之如一”,由于日本遣唐使的艰苦努力,使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一度达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彼以好来,废关驰禁”的境界。但是,客观地说,日本派遣遣唐使并非完全是为了学习,还抱有重要的外交目的,想通过使唐,为处于中国的良好关系,提高日本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的国际地位。因此,在出使过程中日本对其外交地位非常重视。公元753年唐玄宗在大明宫接见各个藩国使臣时,司礼官在安排座次时一度把新罗使节排在日本之上。结果,日本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吕提出严重抗议,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日本国已久。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直到司礼官接受日本的要求与新罗对调座次之后,方才罢休。不仅如此,日本还企图通过出使唐帝国,采用外交手段,扩大其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和影响。比如日本在派遣第四次遣唐使时,正积极支持朝鲜半岛的百济和高句丽侵略与唐结好的新罗,并企图通过使唐离间唐帝国与新罗的关系,实现其控制朝鲜半岛的企图,不料被唐朝政府看清了底细。这次遣唐使团不仅例外地没得到款待,反而收到警告:“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结果被羁留在长安两年。知道唐超出兵消灭百济,控制了朝鲜半岛局势以后,才被释放回国。中国在唐朝之后,国家出现“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先朝建立的册封体制逐渐趋于松散,日本在对华交往方面态度比较消极,很少再向中国派出官方使节。公元960年大宋王朝建立,中国逐渐实现统一稳定,开始积极整饬修复与周边小国的册封体制。1072年宋神宗接见日本民间访华僧人赖缘,并托其向日本天皇捎去书信表达欲与日本通好之意。对于宋神宗的亲笔书信,日本朝野颇为震动,争论犹豫一番之后才回应中国方面的善意,重开两国的正式交往。但是,这种交往的规模已不能和盛唐时期相提并论,不仅人数少(整个宋朝期间只有20多人),而且来华的都是僧人,所以才有“入宋僧”直说。和唐朝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主要是中国采取主动。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指南针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出航日本的冒险性,缩短了航行时间(仅需一个星期就可到达日本)。因此,虽然两国官方往来较少,但中国民间商人为利所驱,不断漂洋过海来往中日之间开展贸易。宋朝达官贵人在使用欣赏日货之余,对日本的风土人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宋代诗人梅尧臣、欧阳修等都有关于日本的诗词传世。比如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曾咏到:“百工五种与之居住,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不仅夸奖了日本的产品精美,而且赞叹其人民文化水平高,还保存了不少在中国已失传的古籍。公元983年,宋太宗赵光义在召见日本入宋僧时,听说日本天皇乃“万世一系”,便大为赞叹,觉得日本真好不像中国隔不了几代就不知皇权又落谁家。从这一时期以遣宋使为渠道的中日官方交往可以看出,两国关系已发生微妙变化,作为文明宗师的中国以基本完成“传道、授业”的任务;日本对华夏虽然仍抱有敬慕之心,但学习热情大减。在民间交往中,对于来日经商的中国商人,日本官方起初还给予接待,到后来就不再过问;更有甚者这些商人有时还要受到日方的欺诈,以至于有人因日本政府长期拖欠货款竟饿死在异国。纵观中日之间的古代交流,具有明显的师徒关系特征。日本学习中国、了解中国甚多,而中国却一直扮演老师的角色,很少向日本学习什么,对这个东瀛邻国的了解长期限于“海上三仙山”。甚至到了清代中期,中国有的学者竟然还以为日本只是位于台湾以南附近的几个岛屿,其认识之荒谬令人慨叹。因此,在漫长的中日古代交流史中,日本文化反哺中华的例子是在少得可怜。为弥补某种缺憾,作者特举出折扇的来历以慰读者。折扇直到今天还是中国人盛夏纳凉的工具,其优点不仅在于可以开合、方便携带,扇面上还可以随人所好饰以字画,使人在纳凉的同时添以儒雅之风。因此,在古代只有文人、士绅有闲阶层才使用折扇以与市井相区别。我国古代很多文人画家都曾吸收日本的画扇技巧,在扇面作画方面下过工夫,使得题扇成为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详察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人使用折扇确实宋代以后的事情。此前,中国只有蒲扇、羽扇、团扇,这些扇子都不能开合。到了宋朝,日本入宋僧出使中国时层作为礼物送给宋太宗,时称蝙蝠扇又叫聚头扇、倭扇。但是,折扇并没有在中国很快传开,偶尔有人在手还会因使用倭人之物遭到耻笑。到了明代,中日官方交流渠道开通后,日本使节出使中国时再度以供品向明朝仿制。这样上行下效,折扇终于在中国流行起来。明朝一位大臣还曾赋诗夸奖折扇的好处,称赞其“随时舒卷足称意,一寸机关哪可量”,“香山写入画图中,金鳌腾空怒涛卷”,“无穷变化不可量,俯仰神仙知是谁”。从现代眼光来看,诗人的用辞虽然似乎有些夸张,但是我们从中不难体会,当时世人初次接触这一新事物时的兴奋心情——其高兴劲儿足可以和80年代中国人刚刚买了一台日本空调时的心情相比。折扇的精巧虽然一度引起文人骚客的吟咏,但在中国士人看来毕竟属于*巧之列。所以,直到清末甲午战争以前,许多中国人仍以“老师”的眼光小视这个“东瀛小国”,认为甲午之战不过是“狮搏兔”。在甲午之败尝到切肤之痛之后,中国的士大夫们才对这个“教”了近两千年的“学生”刮目相看,把日本视为学习西方文化的窗口,不少人放下架子纷纷到日本留学、考察,中日之间的“师徒”关系由此逆转。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人对中国由尊敬一变为蔑视,曾经被日本奉为“国学”的儒学几乎销声匿迹,对中国的称呼由“唐”、“中华”一变而为极富侮辱性的“支那”。而那些为寻求国家自强之道,赴日求学的中国学子们,在日本总是备受歧视。总之,面对东渡求学的中华学子,日本人心胸狭窄的民族性格被发挥到了极至,和两千年来中国接纳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入宋僧时的那种宽容和热情形成鲜明对比。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等,无论提到哪一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古籍都是让人羡慕无比的瑰宝。
当阿里达摩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四川大学的文史专家们的牵线搭桥下。终于在汉典重光平台上回归了首批数字化的古籍,包含40余种宋元刻本、写本,共有20万页。让我们不禁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国古籍流失最严重是主要原因是战乱。当时许多所谓的外国科考队趁着混乱的局势,肆无忌惮的盗挖、偷运、走私、贸易。导致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众多古籍珍本纷纷流落海外。更有甚者连流落何方都无从得知。让国人为此感到心痛不已。
而在全球许多博物馆内都可以看见这些中国古籍的身影。让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经发出无奈的感慨:“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国家政府对这些流失海外的古籍也极其高度重视,但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我国想要全部追回这些古籍原件的难度非常大。有很多时候也是凭着爱国人士的一腔热忱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让古籍回家。
这些古籍都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载体。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了更详尽清楚的路径。为了避免这些古籍再次流失遭受毁坏。我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运用传统的修补技艺来修补受损的古籍外。还通过数字化这种科学技术让这些珍贵的古籍得到长久的保存。每一本能传承至今的古籍都是无数前人耗费心血或牺牲生命保留下来的,而我们必须更好的将这些传承给后世子孙们。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夕,全中国有4747所图书馆,但是到了1943年,中国图书馆的数量下降到940所,五分之四的图书馆不是被毁坏,就是被抢空。在日本入侵期间,中国损失了图书馆藏书量的40%。
1905年,中国才开始建立现代图书馆体系。到1930年之前,中国所有的主要省市都建立了公共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中的大部分遭到日军洗劫。
根据日本和中国的文件记载,在南京 大屠 杀期间,日本军队对南京各类图书馆进行了系统地劫掠,掠夺图书总数达897,178册。
主要参与编著、整理,已经出版的图书;(乾隆)《嘉应州志》、(康熙)《程乡县志》、《二十七松堂集·廖燕作品补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等。主要学术论文:《新版(广东新语)辨误九则》(文献》1991年第2期)、《从(诗外)看晚年翁山》(《岭南文史》1991年第2期)、《广东书坊录》、(《广东出版史料》第三辑,1992年6月)、《和刻本(二十七松堂集)初考》(池田温译, 汲古》,日本第25号, 1996年6月)、《和刻本(二十七松堂集)初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台湾)第4卷第4期,1996年12月)、《近代广东图书出版概述》(《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该文获广州市第六次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清初两藩攻占广州史实探微》(岭南文史》,1996年3月)、《古籍保护方法的继承与实践》(《图书馆论坛》,1996年5月)、《从丝绸到纸张--略述西汉丝绸印刷术发明的影响》(《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
本文2023-08-04 17:21:0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126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