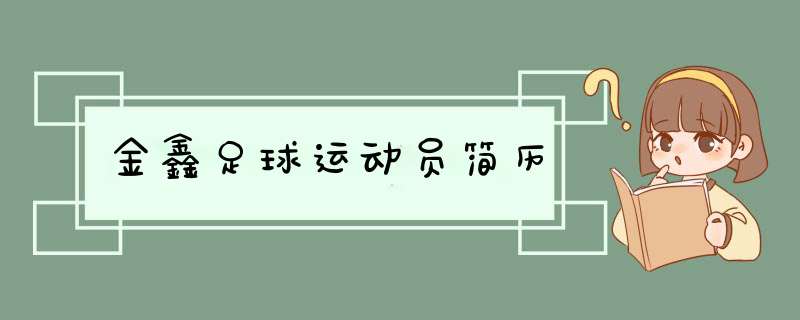中国古代 十二个藏书阁都是

1、北京文渊阁
文渊阁,位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东华门内文华殿后,是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座皇家藏书楼。它是中国古代汉族宫殿建筑之精华,坐北面南,阁制仿自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下诏征书,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九年,下诏兴建藏书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文华殿后之皇宫藏书楼建成,乾隆皇帝赐名文渊阁,用于专贮第一部精抄本《四库全书》。
在中国古代,黑色在五行中代表水,文渊阁琉璃瓦采用黑色寄予着藏书防火之意。灰色的外墙,绿色的廊柱与雕花窗栏肃穆雅致,屋顶彩画绘着河马负书和翰墨卷帙,呈现一股淡然悠长的意境。
文渊阁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后,皇帝每年在此举行经筵活动。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全书》告成之时,乾隆帝在文渊阁设宴赏赐编纂《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和参加人员,盛况空前。
《四库全书》编成后,最初用了六年的时间抄录正本四部,除一部藏文渊阁外,另三部分别藏于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四阁又称「北四阁」。后又抄三部藏于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称「南三阁」。 七部之中或已亡失,或为各图书馆收藏。文渊阁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2、辽宁沈阳故宫文溯阁
文溯阁位于沈阳故宫,建筑格局与文渊阁一样脱胎于天一阁,修建于1781年。
文溯阁有“溯涧求本”之意。乾隆在《文溯阁记》中说:“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意”。
袁世凯北京称帝后,文溯阁内的《四库全书》运抵北京,成为窃国大盗袁世凯的礼物,文化典籍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1922年,冷落故宫多日的《四库全书》被清室盯上,欲卖给日本人,在这危急时刻,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挺身而出,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民族文化良知与爱国心振臂高呼,挽救了国宝的命运。1931年,在张学良等人的呼告下,《四库全书》回到了它的“家中”文溯阁。“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文溯阁落入日本人手中。新中国成立后,文溯阁《四库全书》真正回到人民手中。1966年10月,中苏关系紧张,出于战备考虑,此书从沈阳故宫文溯阁运抵甘肃。现存于甘肃省图书馆。
3、北京圆明园文源阁
1861年11月25日,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奋笔疾书,愤怒地写道:“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在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他们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胜利者均分。”
这位老人就是雨果,他矛头所指向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犯下的滔天罪恶——火烧圆明园。染红夜空的大火不仅仅是民族之痛,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就在这场浩劫中,一座藏书楼也在烈焰冲天中化为断砖残瓦。
圆明园内的这座藏书楼名为文源阁,始建于1774年秋,次年春天完工,乾隆皇帝将《四库全书》第三抄写本藏于此。
据历史记载,文源阁内藏书《四库全书》页首印有“文源阁宝”“古稀天子”之印;页末则印“圆明园宝”和“信天主人”。喜欢浮华与奢侈的乾隆自文源阁修好后,多次来圆明园享受生活与读书之乐。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面对“恍如月宫”的万园之园,他们像一群狰狞残暴的野兽,在园内大肆掠夺,四处焚烧,黑色的烟雾遮蔽了北京城的夜空,文源阁与它所珍藏的《四库全书》不能幸免于难,最终化为灰烬。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
如今,那场弥漫凄怆的大火早已经散尽,文源阁只留下一片地基,在郁郁丛草中向每一个经过它身边的人讲述着昨天的故事。
4、河北承德文津阁
文津阁位于热河行宫(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平原区的西部,建于乾隆三十九
年(1774年),是仿浙江宁波天一阁建造的。它不仅是清代的重要藏书之所,也是一处很有特色的小园林。这里曾藏《四库全书》,以及经、史、子、集分类,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万册,是一份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弘历(乾隆皇帝)在《文津阁记》中写道:“欲从支脉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此句即含有“文津”之意。
文津阁是一个二层楼阁,实际上是三层楼阁,中间有一暗层。暗层全用楠木造壁,能防虫蛀,是藏书之处。此阁在设计上按《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将一层的六楹隔为六个单间,而将顶层的六楹相通为一大间,用“地六”、“天一”来克火。文津阁有围墙环绕,坐北朝南,三面临水,从南往北为门殿、假山、水池、文津阁、碑亭。阁的东北部有水门与山庄水系相通,阁前池水清澈,人在阁前特定位置向池中望去,只见池中有一弯新月,随波晃动,而天空却是艳阳高照。 原来这是造园家在池南的假山上,开出一个半圆形如上弦月的缝隙,利用光线,在水中形成下弦月的倒影,构成“日月同辉”的奇特景观。
文津阁内原藏《古今图书集成》万卷、《御制诗》四集,1785年《四库全书》也曾收藏于此。1915年,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由国民政府内务部运归北京,藏于古物保存所,后拨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保存,遂至于今天,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古今图书集成》早年已被军阀盗卖净尽。
5、江苏镇江文宗阁
文宗阁位于江苏镇江金山寺,1779年修建。阁楼仿“天一阁”,与两侧廊楼和阁前的门楼围成四合院落。藏书楼面临长江,雪涛翻卷,空阔无垠,楼后山崖奇崛,气势威严。乾隆皇帝来到文宗阁,诗情蓬勃,写道:“百川于此朝宗海,此地诚应庋此文。”
然而,陶醉于康乾盛世景象的乾隆不会想到,他之后的清王朝逐渐走向没落。1842年,英军炮轰镇江,文宗阁藏书受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53年3月31日,太平天国将领罗大纲猛攻镇江,战火硝烟将文宗阁和《四库全书》抄本烧为灰烬。
时隔160多年后,文宗阁于2011年复建完成,昔日风采重现盛世。
6、江苏扬州文汇阁
文汇阁1780年在古城扬州行宫御花园内建成,乾隆题写“文汇阁”匾和“东壁流辉”匾,入藏《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
文汇阁与其他藏书阁一样外观看似两层,实则利用两层之间的上下楼板部分暗中设计了一个夹层,从而使内部分为三层。人们不能不赞叹清代建筑设计艺术的高超。一层楼内左右侧安置经部,中层为史部,最上层左置子部,右置集部,秩序井然,利于士子阅读。
1790年,乾隆圣旨中说:“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在文汇阁存世的70余年里,一位位士子出出进进文汇阁,汲取精华,传承文化。从进步意义上说,文汇阁内的各种书籍就像一粒粒种子,在江南的文化大地开花结果。
1854年,文汇阁与所藏书籍毁于太平军的冲天大火中。
7、浙江杭州文澜阁
文澜阁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浙江省博物馆内。初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七座皇家藏书阁当中修建得最晚的是文澜阁,1782年在杭州西湖孤山圣因寺修建,次年完成。它为重檐歇山顶建筑,布局带有明显的江南园林之巧妙与精思。阁前假山堆叠,小桥流水,一神女峰假山石玉立一汪澄清池中。池边建有碑亭,乾隆的题诗刻于石碑正面,碑后刻有《四库全书》上谕。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文澜阁与军营无异,这些士兵没有心思保护这座建筑和所藏之书,大量图书散佚。面对国宝的危殆局面,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挺身而出,在断砖残瓦间,在街巷人家中不惜重金寻觅国宝。对一些损毁的藏书倾力补抄。集多年之力,补到了34796种图书。后浙江图书馆馆长钱恂、继任张宗祥又历时7年补抄,史称“乙卯补抄”和“癸亥补抄”。两次补抄完整后的《四库全书》集中了全国藏书楼的精华所在,是所存于世版本当中最好的一部。现江南三阁惟文澜阁及所藏《四库全书》存世,成为“东南瑰宝”。
8、 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
天一阁之名,取义于汉郑玄《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之说,因为火是藏书楼最大的祸患,而“天一生水”,可以以水克火,故取名“天一阁”。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其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建于明朝中期,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
仅天一阁,就凭借其所藏的30万古籍,卷走了中国现存藏书楼的所有荣光。天一阁在历史上至少有两件事是震古烁今的,一是清乾隆时编篡《四库全书》,天一阁进呈了古籍600余册,其中96种被收录至《四库全书》中,并有300多种列入存目。二是天一阁的藏书之所和建筑构式备受乾隆推崇,命人测绘天一阁房屋、书橱的款式,以此为蓝本,在北京、沈阳、承德、扬州、镇江、杭州兴建了文源阁,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汇阁,文澜阁,文宗阁等七座皇家藏书楼以收藏《四库全书》。天一阁从此名扬天下。
山东聊城杨以增氏海源阁、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浙江吴兴陆氏皕宋楼,合称中国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
9、海源阁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聊城古城中心,由清代江南河道总督、邑人杨以增创建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总计藏书四千余种,二十二万余卷,金石书画不胜枚举,收藏之富“为海内之甲观”。海渊阁于本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屡遭兵燹匪劫,珍藏流散,楼舍损毁,只有一小部分辗转收入北京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1992年10月,聊城市筹集资金200万元,在原址按原来的结构样式重建,并开始对游人正式开放。
10、 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
铁琴铜剑楼是清代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建于清乾隆年间,建筑面积285平方米。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原名“恬裕斋”,创始人瞿绍基,瞿氏五代藏书楼主都淡泊名利,以藏书、读书为乐,绵延二百多年,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十字:“读书、藏书、刻书、护书、献书”,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藏书除部分遭劫外,绝大部分于建国初由瞿氏后人捐赠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常熟图书馆等。
11、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
清代浙江丁国典慕其远祖宋代丁顗藏书八千卷而名其所建藏书楼为“八千卷楼”。清咸丰十一年(1861)毁于兵燹。丁国典之孙丁丙沿用楼名重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
八千卷楼包括嘉惠堂八千卷楼、后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嘉惠堂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所收及附入存目之书,后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小八千卷楼收藏宋元刊本、明刊精本、旧钞本、校本、稿本等善本书籍。八千卷楼所藏宋元刊本不多,但富有特色:①收藏四库馆修书底本。这些底本上往往钤有翰林院印,有的经过点校钩改,可使后人考见当时修书的规制。②收藏浙江地方文献。③收藏名人稿本、名人校本及钞本。八千卷楼藏书不仅数量多,且版本类型多样。除藏书外,丁丙一生曾刻书200余种,辑书20余种,著书10余种。其所辑主要有《武林掌故丛编》、《武林往哲遗著》(前后编)、《西泠王布衣遗著》、《当归草堂医学丛书》、《当归草堂丛书》等。所著之书主要有《善本书室藏书志》、《礼经集解》、《九思居经说》(稿佚)、《说文篆韵谱集注》(稿佚)、《三塘渔唱》等。咸丰、光绪年间,丁丙曾与其兄丁申共同在战乱中收集散失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并加以钞补,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复其本原。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奏请清政府创设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时为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售与日本的第二年,为防止古籍再次外流,端方将八千卷楼藏书收购入藏江南图书馆。八千卷楼藏书目录,主要有丁丙撰《善本书室藏书志》、丁仁编《八千卷楼书目》。
12、浙江吴兴陆氏皕宋楼
中国清末陆心源藏书楼之一。以皕(音bì)宋为楼名,意谓内藏宋刻本有 200种之多。但实际不及此数。陆氏藏书多得自上海郁松年宜稼堂,其中大部分为汪士钟艺芸书舍所收乾嘉时苏州黄丕烈士礼居、周锡瓒水月亭、袁廷梼五砚楼、顾之逵小读书堆等四大家之旧藏,极为珍贵。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皕宋楼和守先阁藏书15万卷,由陆心源之子陆树藩以10万元全部售与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
13、江苏苏州顾氏“过云楼”
过云楼是江南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世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 过云楼以收藏名贵书画著称,享有“江南第一家”之美誉。值得一提的是,过云楼里面还有一个密室,顾家的书是放在密室里面,秘不示人。顾氏保存的善本极为完好,整洁如新,宋本纸张洁白,字大悦目,是艺术珍品。其中,《锦绣万花谷》于南宋淳熙十五年刊刻发行,是目前已知海内外最大部头的宋版书。这部“宋代的百科全书”,将现存百科全书的年代拉到历史上限。
1951年和1959年,过云楼顾氏后人,先后两次将所藏的三百多件书画精品,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过云楼历经150余年,集藏的书画珍品,有了它们最终的归宿。然而过云楼几代人密藏、从不轻易示人的善本古籍,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有大约四分之三转归南京图书馆收藏,尚有剩余的170多种图书留存民间,这些图书被嘉德公司征集拍卖。
分类: 地区 >> 浙江 >> 甯波市
解析:
天一阁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之一。古籍浩瀚,历史悠久,距今已有430多年的历史,素负“南国书城”之盛誉,巍然屹立在宁波城月湖之滨,成为亚洲现存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个家族图书馆之一。它是宁波人最引以自豪的一个文明星座。文人墨客到了宁波,没有不到天一阁一饱眼福的。这古朴的建筑,幽雅的园林,恬静的环境,确实令人神往。然而过去的天一阁只是一个普通的私家藏书楼,历经几代沧桑;如今的天一阁则是宁波的一颗“明珠”,它集藏书、文物、旅游于一体。1982年2月23日,天一阁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雄踞大门两侧是一对清代石狮。这些木结构的大门,是清道光年间造的。“南国书城”这四个字由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所书,而“古阁藏英”则是由大书法家沙孟海亲题。现在所看到的大门两旁对联是钟鼎文,读作“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对联说明了天一阁藏书楼历史悠久和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登上天一阁藏书楼以后的感叹心情。黄宗羲号南雷,他曾赏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进入天一阁,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照壁上气势宏大的“溪山逸马图”,当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曾在这里拍照留念。这幅八骏图是“堆塑”,它的作者是已故民间老艺人胡善成。天一阁的堆塑,绝大部分是他的作品。参观完这块照壁后,从右边的直门“春随人意”中进去(左面是1980年新建的书库和阅览室)。可以看见天一阁的又一块照壁,大家知道它叫什么吗?它统称为“麒麟”。但细分下来,这是一个龙角、牛嘴的“豺”,是正义的象征。
天一阁藏书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幢藏书楼就是几经修缮后保存下来的天一阁遗址,它是晚清时期的建筑遗物。天一阁的主人名叫范钦,字尧卿,号东明。明嘉靖十一年(范钦27岁时)进士,做过湖广隋州知府、江西袁州知府、广西参政、福建按察使、云南右布正使以及陕西、河南等省的地方官。后来又巡抚南赣汀漳诸郡,宦迹遍布半个中国,直至官升兵部侍郎。范钦生性耿直,不畏权贵,曾顶撞过权倾朝野的武定侯郭勋,因此蒙受冤狱。后在袁州知府任内,因秉公执法又得罪了权臣严世藩,为了避祸,辞官还乡。回到宁波后,就建造了藏书楼。范钦爱书成癖,在做地方官时,每到一处总是留心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对无法买到的书就雇人抄录。经史百家之书,他兼收兼蓄,不厚古薄今,比较重视当代著作和文献的收藏。在他的藏书中,明代地方志、政书实录、明人诗文集及历代科试士录,占了很大的比重。此外,还汇集了许多有价值的碑贴,其中著名的是北宋拓本。
范钦的藏书楼原名叫“东明草堂”,楼前开凿一池与月湖沟通,蓄水备用。当时宁波有许多藏书楼,但先后遭受兵火破坏,范钦想,兵灾无法避免,火灾可以防止。为了防止火灾,范钦费尽苦心,查阅了许多书本,最后在《易经》中看到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这句话而受到启发,便取其以水制火之意,将藏书楼改名“天一阁”。藏书楼上为一大通间,楼下六间,象征:“天一地六”。范钦不但将藏书楼改了名,还规定抽烟喝酒后切忌登楼,不准擅领亲朋好友开门入阁及留宿阁内,更不准擅自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凡违者处以不能参加祭祀祖宗的大典的惩罚。天一阁的主人连取名时都考虑到了防火的重要,可见其用心良苦。
范钦一直活到80岁。临终时把大儿子大冲和二媳妇(次子大潜已故)叫到榻前,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是白银万两,二是全部藏书。大冲体察老父心情,决定“代不分手,书不出阁”。范钦的后代对天一阁藏书的保护制订了许多严格的禁约。据记载嘉庆年间,宁波知府邱铁卿的内侄女钱绣云是一个酷爱读书的聪明才女,为求得登阁读书的机会,托邱太守为媒与范氏后裔范邦柱秀才结为夫妻,婚后的绣云满怀希望,以为这下可以如愿以偿了,但万万没想到,已成了范家媳妇的她还是不能登楼看书,因为族规不准妇女登阁,竟使之郁郁含恨而终,遗命夫君将她葬于阁边,愿以芳魂与书作伴,了却她另一种“青灯黄卷”的夙愿……这一悲剧足以说明禁约的严格。
原来藏书楼四周都是花园,以防附近一旦发生火灾不会遭受其害。到了清初时,范钦的曾孙范文光请来名匠垒起玲珑假山“九狮一象”、“福禄寿”等。由名匠大师堆砌造就的玲珑剔透、形象逼真的假山中有许多动物,大家不妨数一数共有几只?
主人为了保护藏书楼而制定了极为森严的规定,同时作为一份私人财富,藏书楼也是外人不可染指的。然而世代规约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第一个破例登上天一阁藏书楼的外姓族人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清代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黄宗羲由于他的道德、文章、学识、气节在当时普遍受到人们的敬佩。在范氏族中曾做过嘉兴府学训导的范友仲帮助下,很快取得了范氏各房的同意,登上了天一阁。原来范钦后代为防止藏书失散,还议定藏书由子孙共同管理,阁门和书橱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任何人不得擅开。黄宗羲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
风雨天一阁
余秋雨
一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
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
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
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
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
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
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
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
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
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
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
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
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
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蹚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
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
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
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
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
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
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
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
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来
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二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
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
的象形文字,创造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
地催发出一个书籍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
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
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
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
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
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
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
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
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
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
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
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
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
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
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
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
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
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
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
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
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
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
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
唯此岿然独存。”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
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
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个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
个小小的栖脚处。
三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
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
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
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
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
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正书、实录以及历科
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
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
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
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
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
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
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
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
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
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
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
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
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
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
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
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
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
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
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
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
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
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
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
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
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
籍转售给范钦。
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
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
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
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
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
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
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
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
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
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
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
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
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
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
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
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四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
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
于范钦死后。
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
年的苦役。
活到八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儿媳妇(二儿子已
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
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们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
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
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
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
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
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
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
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
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
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诮或鄙薄要继承
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
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
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
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
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
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
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
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
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
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
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
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
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
却不知是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
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
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
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
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
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
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
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
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
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
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
媒嫁给了范家。
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
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
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
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
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
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
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
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
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
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
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
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
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
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族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
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
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
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
后来宦官集团受审,十九岁的黄宗羲在廷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
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
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
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
想学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
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
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牛。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
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
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
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
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
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
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
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
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
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
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
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办法中的办法。但是,
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
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
贵古籍六万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万七十余种列入
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
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
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
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
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的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
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
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五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
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
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某位学者上楼的
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
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
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
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
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
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
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
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
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
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
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
里。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
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
也终于失效。
六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
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怒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
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
事。幸好,本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
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
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
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
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
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
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孑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
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
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阁中一位年老的
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
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杳无可寻。
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
裴明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溥、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
内中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
史实。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我们的文学艺
术家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中国古代 十二个藏书阁都是
本文2023-10-17 03:35:57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1395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