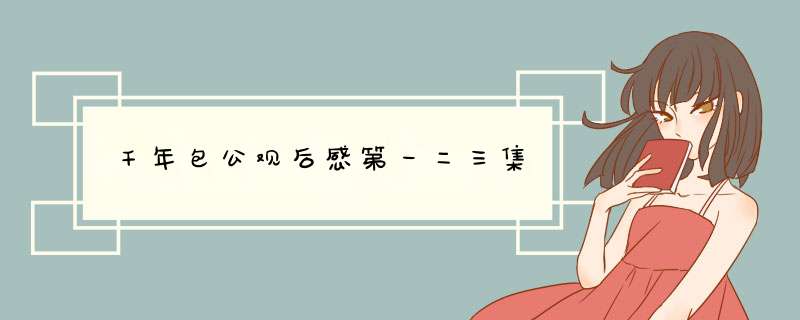台湾、新疆、西藏在西汉东汉三国隋朝唐朝元朝明朝清朝时的名称

台湾 在汉朝时期当时的朝廷文字记载把台湾分为三部分,“东鯷”即为北台湾,“夷州”为中台湾,“澶州”为南台湾。到了三国时期台湾被叫做夷洲。到了隋唐开始台湾就被叫做琉球了。一直到了清朝康熙大帝设立台湾府,才有了台湾这个名称。新疆 最早在西汉开始就一直被纳入中国政权的版图,当时被统称为西域。在元朝蒙古人设立了阿里麻里行省,当时就把新疆一带叫做阿里麻里。在清朝在乾隆24年合并天山北麓及天山南麓,改称伊犁。后来改称新疆以为新的土地之意。西藏 在汉朝没有没有指定的明朝,当时那一代都属于羌人各部的居住地。各种名字都有。唐宋为吐蕃;元属宣政院;明称乌思藏,清初称卫藏,卫即前藏,藏即后藏;后正式定名为西藏。、
新疆地区出土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家文化典籍,说明了儒家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也反映了新疆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互动。
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文化交汇之地,同时也是儒家文化传播的重要区域之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互动更加频繁,这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
首先,新疆地区的政治环境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在汉朝时期,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此后,历代中原王朝在新疆地区设立行政机构,实行管辖和治理。这些政治举措促进了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联系,为两地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奠定了基础。
其次,新疆地区的经济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这对于新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中原地区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也通过移民、商贸等方式传入新疆地区,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此外,新疆地区的文化也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包括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等。这些文化元素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对于当地的文化和宗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新疆地区出土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家文化典籍,说明了儒家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也反映了新疆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互动。这些文化遗产对于研究中华文化和历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焉耆地名写法刘正琰诸先生编著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中,把散见于卷帙浩 焉耆回族自治县
繁典籍之中的"焉支"一语 的汉语音译10种写法收录如下:焉支、 燕支、烟支、胭脂、胭支、燕脂、烟肢、燃支、焉耆、焉提。焉耆的名称在中国古籍上,汉唐时基本上有三种写法:《两汉书》、《晋书》、《魏书》、《周书》、《隋书》、《新唐书》、《旧唐书》、《高 僧传》、《续高僧传》、《悟空行记》都写作焉耆,《佛国记》和《水经注》及《释氏西域记》写作乌彝, 《大唐西域记》叫阿焉尼。后来的各派学者议论 纷杂,相持不下。据日本松田寿南先生说,阿耆尼是古代焉耆僧侣所使用的雅称,把焉耆一词梵语化了。梵语阿耆尼即火神之意。中国一些学者提出乌彝、阿耆尼,都是"焉耆"的同音异译。
“昌吉”地名的称呼始于元代。据《新疆图志》载:“侍行纪云:《元地志附录》有仰吉八里……按:仰吉与昌吉音近……蒙语……” 以此可知,“昌吉”是由蒙古语“仰吉”转化而来的。另外,自元代以来,除“仰吉八里”的地名称呼外,史籍中还有 “昌八刺”(音读喇)、“彰八里”、“掺八里”、“昌八里”等地名称呼。据我国学者考证,这些称呼其实都是一音多转,或曰一音多译,它们其实都指的是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就在现昌吉市境内。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昌吉”是由“仰吉”转化而来的。 关于此,从清代另一位官员萧雄的诗句中亦可得到印证。萧雄在清光绪年间写的《昌吉》诗中有“沿革想从昌八喇”句,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关于“仰吉八里”的含义,据有关史载及专家考证,“仰吉”蒙语意为“场圃”,亦即游牧和种植的园地;而“八里”蒙语意为“城”。这样将两者的意思合起来,“仰吉八里”的意思便是“游牧与种植的园地之城”。根据昌吉这一带建县前曾长期为准噶尔蒙古人的游牧地,而昌吉县城东南面又有古城,所以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是可信 的。 由上可知,古代的昌吉是"游牧与种植的园地"。
哈密最早的名称为:西漠(西膜)、古戎地。《穆天子传》载:“己巳,至于文山,西漠(西膜)之所谓口,觞天子于文山,西漠之人乃献食马三百,牛羊二千…”意思为流沙之西,《穆天子传》成书于战国时代,由此可见,哈密被称为“西漠”(西膜)是战国之前,如果从周穆王算起的话,时间距今为3000年左右。但是,在查看资料时,《伊犁历史与文化》一书对“西漠”(西膜)就不仅仅是哈密的地名那么简单了,很可能是哈密当时就是以塞人为主要居民的地区了,因而就以自己的人种命名了当时的哈密绿洲。他们和黄种人也就是羌人共同生活在这一片绿洲大地上,造就了哈密三千年前的绚烂多彩而又神秘的游牧文化。这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哈密和伊犁都曾是塞人的根据地,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个名称就是“昆莫”。唐朝《元和郡县图志》说:“禹贡九州之外,古戎地。古称昆莫,周穆王伐西戎,昆吾献赤刀,后转为伊吾,周衰戎狄杂居泾渭之北,伊吾之地又为匈奴所得。”现在,哈密地区还有伊吾县,保留着名称的传承。春秋战国时代以前,从河西走廊到哈密、罗布泊都是游牧民族,包括外来的欧罗巴人种的塞人、大月氏、乌孙。其中,塞人、大月氏、乌孙人都是哈萨克的主体族源。他们都曾游牧在敦煌到哈密之间。有些学者如著名西域史专家苏北海等认为哈密原来的名称应为昆莫,他在他的那本著名的《西域历史地理》中写道:哈密的名字源于乌孙人的首领“昆莫“,伊吾之音是由昆莫转变而来,从而可知昆吾、伊吾、伊吾卢,以及后来释城的哈密、哈密力、哈迷里都是昆莫的一音之转。汉人在古代译兄弟民族名称时,把库木尔译成昆莫,而少数民族则直称库木尔。昆在突厥语中是太阳的意思,莫是统治者的意思,因此,哈密二字是就像太阳一样的统治者的意思。对这个说法,有学者不同意,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认为:哈密古为昆莫之地,古籍记载不甚详备。但是,乌孙人和塞人血缘关系浓厚,从某种意义上讲,乌孙人是塞人的后裔。乌孙作为历史上被称为:“游牧于敦煌、祁连山以东”,是不会有问题的。这里的祁连山,大多数专家学者已承认应该是位于哈密境内的东天山。乌孙人与大月氏人、羌人杂居于敦煌至哈密绿洲也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种是著名维吾尔学者阿不都西库穆罕木德伊明提出的,他认为,哈密二字的意思要从哈密在新疆的位置入手考虑,他经过大量考证,得出的结论是,哈密本意就是新疆东大门之意。
第四种著名西域研究学家、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的意见。他是中国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弟子,中国屈指也数能读懂吐火罗文的人,通过对吐火罗文的研究,他提出一个崭新的提法。他认为;哈密古代被称为“伊吾卢”,为夷狄生长之地,有蒙古人种,也有欧洲原始人种,还有高加索白种人种,文化层次丰富,具有多元性。而“伊吾卢”是大月氏也就是吐火罗人对哈密称呼,意思是“龙马”。联想到大月氏人对马的崇拜,此说不无道理(后文将谈到这一问题)。哈密作为多种人种杂居之地,对“伊吾卢”的称呼也带有其他味道,伊吾后面加了个卢,应该是哈密当地土著夷狄人的习惯,到东汉后,随着东汉政府的管理最终定名为伊吾。库车在历史上曾经定名为“伊罗卢”,和哈密的原称“伊吾卢”非常相似,也是吐火罗语,大月氏人的统治地域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第五种是蒙古族语“窄沟”的意思。主要是对拉甫却克的形象概括。拉甫却克东西各一座城,中间隔着一条窄沟,故而谓之。
第六种是哈木尔,为突厥语,蒙古语叫“哈密里”,因为有沙山哈木尔,所以地以山名。这一说与后面的第十种基本一致。
第七种是到五代时,又称为“葫芦碛”。来由是伊州两边都是沙漠,哈密绿洲就在沙漠中间,一面是著名的罗布泊沙漠,一边是八百里的流沙莫贺延碛,形象好似葫芦,因以名之。
第八种是《西域图志》记载乾隆的说法。《西域图志》说:“阳关西一千六百里至鄯善,又西七百二十里至且末,又西两千里至精绝,又西四百六十里至扞冞,又西三百九十里至于阗。”由此可知,扞冞在精绝和于阗之间,距阳关3780里。这一说似乎有此牵强,哈密至阳关哪有1300多公里?《西域图志》解释:伊吾与哈密音不相类,意扞冞人尝居此。因转扞冞为哈密。
第九种“了望墩台”说,成书于乾隆年间的《钦定河源记略》中写到:回语哈密即哈勒弥勒之转音。哈勒,了望之谓;密勒,台墩也。地有墩台可以了望,故以名其城焉。同一暑期的《钦定西域同文志》也说:“回语,哈勒弥勒之转音。哈勒,了望之谓;密勒,墩台也。地有了台,故名。”
第十种“俱密说”。但是此说者是清朝末年的学者陶葆廉,他在《辛卯侍行记》一书中写到:“缠回之称哈密皆日哈木尔(或库木尔),稽古者以哈密为汉伊吾,而不知哈密直名亦古。《元和志》伊州纳职县北有俱密山,是哈密因山得名,唐初已然。今三堡西北之哈木尔达坂即古俱密山。西戎语哈、俱、库、克等均可通用。”俱密山就是指位于哈密境内的东天山。
台湾、新疆、西藏在西汉东汉三国隋朝唐朝元朝明朝清朝时的名称
本文2023-10-19 23:28:46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1494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