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生态思想?

生态思想即是指自己所布局的要讲究生态平衡,齐头并进。 不能为了这,而牺牲那,好比为了发展污染了环境,到头来还得在倒贴钱去治理环境,生态即自然。 在商业上的布局,讲究生态系统性的建设,是富有远见的观念。
扩展资料:
生态思想的几个观念:
1、整体的观念
是说生物与其环境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生物均不能脱离环境而单独存在;
2、循环的观念
是指作为生产者的植物、消费者的动物、分解者的微生物,它们互相耦合,形成由生产、消费和分解三个环节构成的无废弃物的物质循环;
3、平衡的观念
认为生物之间的食物链关系、金字塔结构和循环体系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之中;
多样性的观念,即“多样性导致稳定性”的生态原理,它强调保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认为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直接威胁着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是以时代精神的主旋律为根据的,离开时代精神,也就无所谓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伴随着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形成的,但这并不能据此论定我们的祖先没有生态伦理意识。先秦儒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十分注意总结自然界的规律,在保护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1、先秦儒家的生态自觉意识
先秦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来源之一,一个基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生态伦理学是建立在自觉地对生态学的科学认知的基础上。
先秦儒家认识到单个生物物种的存在是不可能的,生物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要以种群的方式进行,他们对自然界生命系统的组织层次的认识,是用“类”、“群”、“畴”等概念来表达的。
长沮、莱溺,辐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授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忧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鸟兽不可与同群”说的是鸟兽分属于不同的群。他还从生态学上提出了“类”的概念。孔子曾说:“丘闻之也,剖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荀子也说:“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草木畴生,禽兽群也,物各从其类也”。荀子已经把植物草木和动物禽兽区分为生物系统中的两种不同的类,并且认识到草木以“丛”的形式生长,禽兽以“群”类的方式存活,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先秦儒家对生物及其环境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这些都指出生物的生存离不开一定的环境,环境决定生物的存在。先秦儒家在关注环境的同时还注意到了生物之间存在着的食物链的关系。“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即草木为动物提供了食物,而当动物的数量减少时,植物就会茂密地生长。
在农业社会条件下,先秦儒家对时间结构中的季节规律尤为重视,他们用“时”来反映和概括生态学的季节规律,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认识。“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滋基,不如待时”。这就是说,作为条件和环境的生态学季节规律的“时”是不可超越的。因此,先秦儒家以“时”为媒介将人和自然联络起来,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要求人们根据季节的变化来合理地安排获取自然资源的活动。“挎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
2、“天人相分”—改造自然的依据
人类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去参与自然的创造和化育过程,使得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荀子称这种能动性和创造性为“制天命而用之”。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在荀子看来,与其高喊“惟天为大”而仰慕它,不如把天看作自然的物质而控制它;与其“顺天”、“从天”而歌颂它,不如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与其仰望天时而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因时制宜地利用天时;与其消极地听任物类的自然增多,不如积极地施展人的才能而促进物类的化育繁殖。因此,他认为只要发挥“人治”的作用,善于经营管理,就能提高生产,增加收获。
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荆车;雹笼鱼鳖鳅鳗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亮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
先秦儒家认为,作为自然之天,它的存在变化具有自身的某种特定的规律性,“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所谓“故”,即是指自然界的规律。因为自然界有“故”,所似人可以通过对自然界所获得的某种规律性进行类推,由近及远,由古及今,得到更多的更广泛的认识。但在他们看来,自然的规律是客观的,并不取决于人的意志,“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柴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对自然界的这种客观规律,人们只有遵循它才能取得好的结果,“应之以治则吉”,如果违背它,就要遭殃,“应之以乱则凶”。
3、“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矛盾统一
“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生态伦理学价值就在于它们不仅为儒家的生态伦理学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且为现代生态伦理学提供了一种哲学构架—人与自然和谐、协调、一致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这正是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所缺乏的东西。“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不仅是克服人类中心论顽症的一剂猛药,而且是从生态中心论过渡到生态协调论的一副良性的催化剂,是从现代工业文明过渡到后现代的“桥梁”。事实上,只有将“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互补起来,才能为生态伦理学提供科学的哲学基础。
“天人合一”要求在处理人类和生态环境关系上追求和谐、圆润、统一的境界。人不仅与自然平等,而且与自然浑然一体。世界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是不可言说的,不可思议的,其中根本就没有差别。人与世界万物,只是在一定认识层次上差别,而在更高层次上彼此相融,无法分别,即哲学所谓“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认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仁”作为人的道德本性,要求视人如己,视物如我,以合内外,以天下的“廓然大公”为至境和理想。一个人作彼此、内外之分,把物我、天人隔绝开来,对他人的痛痒漠不关心,这就是“不仁”,即道德本性的丧失,其根源在于有“私”。一个人的行为受道德理性的支配而出于公,就能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凡利于天下事,则为之;凡害于天下事,则弃之。这一观念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则必然要求人以整体生存为目的,而不仅仅只顾及个体的、区域性的、眼前的利益。
然而,现在有一种倾向,把“天人合一”抬得高而又高,把“天人相分”贬得低而又低,似乎“天人合一”是拯救人类命运的不二法门,而“天人相分”则是造成生态环境危机的罪魁祸首。应该看到,征服自然与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不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从根本上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改造自然而禽兽不能。墨子说人是“赖其力而生”,荀子说人能“制天命而用之”,可使“牛马为用”,所以才最为天下贵,“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改造自然也就是对自然的征服,也可以说征服自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没有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就没有人类的文明。事实上,人与自然本来既有合的一面又有分的一面,没有“天人相分”的“天人合一”是不健全的,“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是互补的矛盾统一体。
4、“天人合一”—维护生态的依据
先秦儒家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了天人和谐、均衡、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并提出了“仁民而爱物”的观点。“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概念,是人类道德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原则,它虽然始于爱亲,但并不终于亲,甚至于要超出亲情的范围来“泛爱众”,并最终将爱心推及最广大的万物。“仁民而爱物”的思想是将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推广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仁爱的精神和情感贯注于自然万物。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在这里阐述了仁的层次性,即对于“亲”、“民”、“物”三种不同层次的物件,应该采取相应的程度不同的态度—“亲”、“仁”、“爱”,也就是说,对亲人要“亲”,对民众要“仁”,对万物要“爱”。这三步自成系统,是先秦儒家仁爱思想的逻辑展开。而这正是人类道德情感投射于外物的表现,在他们看来,动物存在着与人相似的道德情感,所有动物对自己的种群都具有一种天生的情感,当自己的同伴受到伤害时,它们都会流露出一种同情心,而当自己的同伴死亡时,它们都会发出撕人心肺的哀鸣:
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反沿。过故乡,则必排徊焉,鸣号焉,娜蜀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扰有惆憔之顷焉,然后能去之。
动物尚且对同类的不幸遭遇具有悲哀和同情之心,人类则更应该自觉地禁止这种伤害动物的行为,保证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孟子甚至认为人固有一种爱护生命的侧隐之心: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休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这种被称为“侧隐之心”的同情心,不是后天的思虑所得,乃是先天的本能,是人天生的对生命的同情之能力,人与人正是凭此得以感通。
“仁民而爱物”的实际内容就是将自然保护作为落脚点。先秦儒家在人类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认识到自然是人类的生存的根本。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虎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
在这里,荀子和孟子充分肯定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的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基于天之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从持续发展、永续利用原则出发,先秦儒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针对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保护措施: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雹尾鱼鳖鳅鳝孕别之时,周苦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尤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苦不入垮池,鱼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这里先秦儒家明确提出了重视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根本目的是为了“利国富民”,甚至把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同国家政治联络起来,认为这是王道政治的起点,是同“养生丧死”息息相关的大事。而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季节规律,即按照四季来安排“时禁”和“时弛”是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手段,并且认识到保护自然资源就是要注重资源的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即“不夭其生,不绝其长。”
中国,是一个拥有灿烂文化和丰富资源的古老国度,在发展的过程中,总结出了自己一套关于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环保理论和实践,并且深刻影响着今天的环保工作。
一,古代人的朴素环保思想
1,源于自然崇拜的生态观念
在远古时期,由于人类生产力量的限制,很多的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大自然。这个时候,讲究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自然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而人类对于大自然的依赖程度很高。
在当时,人类对于自然的理解是“神秘的力量”,将自然视为神明,进而产生了对于大自然的崇拜和敬重。
同时,由于当时人类科学技术和理论知识的欠缺,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解释一些问题,将自然中的“打雷”“闪电”看作是一种神明对于人类的惩罚,从而对自然产生了一系列的畏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自然禁忌。这种自然禁忌就变成了大家都要去遵守的条款和条约,用来约束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行为。
这个时期,神话传说成为了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实践中的理想追求,也反映了古人对于自然和人类和谐关系的理解。
在“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人心中,不仅有改造自然的朴素愿望,还有古人在长期劳动和生产中体会到的人与自然的相对独立性。自然不依赖于人类而独立存在,而人类则不能脱离自然而独立生存,讲究的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2,“天人合一”的思想
在古代环保工作中,“天人合一”是最重要的环保观念,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天人合一”讲究的是尊重自然,善待万物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念。主要包含着两个层次:
第一,在《易经》中,有这样的思想:“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人类从宇宙中演变而来,需要依赖于自然环境而生存发展;
第二,儒家讲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人类要生存,就需要将自然放在和人类同等重要的地位,将它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讲究社会活动中需要善待自然,对万事万物需要用仁德之心对待。
“天人合一”是中国最基本的传统思想,也反映了古代传统思想最深层次的观念,是古人朴素的生态理论和环保观念,为中国的环保工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跨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3,道法自然
在《道德经》中,有这样的哲学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意思是 "道"所反映出来的规律是 "自然而然" 的。老子用了一气贯通的方法,将天、地、人乃至整个宇宙的生命规律精辟涵括、阐述了出来,告诉我们需要尊重自然法则,不得违背自然规律。
在道家的思想中,“天道”和“人道”是一个整体,而“道”是天地之根本,万物之源泉,自然万物从本源上就有着统一性,人类也要以“道”作为出发点去对待世间万物。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道,天,地,人是一个完整的生态链,打破其中任意一环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自然界的和谐运转,而作为其中一环的“人”,也需要遵守生态中的生存思想,以遵循自然为前提,不得逾越,打破自然和谐。
二,中国古代的环保举措
1,环保部门和机构设置
在古代,不仅有着深刻而成熟的环保思想,也有付诸实施的环保工作和官职。在很多朝代中,都有虞,衡的官职。
中国最早的环保机构则是大舜设置的“虞”,在《尚书·舜典》中有这样的记载: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 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 ”
益就是中国最早的环保官员,后来还设置了大司徒和虞部下大夫;
到了秦朝,环保部门为少府,少府下还设置有林官,湖官,破官和苑官,而大汉朝也承袭了秦朝的旧制,环保机构改成了水衡都尉,而东汉的司空一职也是针对环保部门的官员,司空“掌水土事”。三者各司其职,地位相等,无轻重之分。
到了唐宋以后,虞,衡的官职权力有所扩大,在《旧唐书·职官》中这样记载:
“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戈猎采捕。”
中国环保机构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机构和职责不断清晰的变化过程,虽然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不失为古人对环保事业的探索发展的贡献。
2,环保法律
古人们不仅设置环保相关的职位,还有相关的立法来保障环保事业配套的实践。
在夏禹时期,曾经有禁令,据《逸周书·大聚解》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以成鱼鳖之长”。
用具体的政策来落实环保工作的实施,约束人们对自然行为的破坏;
殷商时期,有了“弃灰之法”,西周时期曾颁布《崇伐令》:
“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表现了统治者对于环保事业的重视和对自然地尊崇。
在周朝统治期间,以“以德配天”的主要思想下,“礼”在约束人们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后来的朝代中,不仅是秦朝的《田律》,还是唐朝的《唐律》,关于环保的问题都有相关的规定,且逐渐趋于完整。包括在明清等很多朝代,立法也都是沿袭了前朝的相关环保法律,对于当时的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国家安定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于我们今天应对和解决环保问题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人们就已经具有环保思想,他们很早就认识到,要想利用自然资源,尤其是生物资源,必须要注意保护,合理开发,反对过度利用,特别是破坏性的开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典籍论述了关于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保思想。这种环保思想最初是不自觉的,甚至带有迷信色彩。《诗经》中有“是飨是宜,降福既多”的说法,同时又有:山川乃资源的产处,要与百神一同祭祀。《礼记·月令》中也包含了气候、生态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文中说:孟春,草木萌动时,“牺牲毋用牝(母兽),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管仲指出,“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国语》中有九州山川河湖,生产物质资源,所以要保护和祭祀。《易》以生生不息为准则,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因此,“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就是说,人类要顺从自然,适应自然,达到天地之间的和谐。
一、古代的环保立法
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就已经有了保护自然资源的法规,叫“禹之禁”。“禹之禁,春三日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日,川泽不施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环保的法规了。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刑弃灰于街营”的法律。古代还设立了一些环境管理的官员,如“林”,“虞”,“牧”等官,他们分别管理山林,川泽和畜牧。《韩非子》记载,商代已有不得随意倾倒垃圾的法律,“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可见处罚之重。秦国商鞅变法,他制定的秦律中有“弃灰于道者被刑”的条文,这是商朝法律的延伸。
在周朝,周人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有初步认识。传说,周文王曾告诫儿子周武王对大自然不要进行过度开发,要按自然规律合理使用。他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周文王时期颁布的《伐崇令》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毋坏屋,毋坏井,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个保护生态环境的法令,规定得极为严厉。
秦汉时期(约公元前220年—公元220年)保护生物资源的理论达到了高水平。西汉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中对古代生物资源保护政策做了最完善的论述。他指出:禁止砍伐生长的树木,不能捣毁鸟巢、不捕杀怀孕孵卵的动物,特别要保护好幼小的麋和鹿等。秦朝的《田律》、《厩苑律》、《仓律》、《工律》、《金布律》中都有一系列的关于按照季节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森林、土地、水流、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规定。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发掘出土的大量秦代竹简中的一些竹简上刻着内容具体的《田律》,其中已用法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这里既规范了一般的保护范围——森林、水植被、其他植物及动物(包括野生物);又照顾到特殊的例外——人死入葬,伐木成棺,不受时间限制。在秦代的立法中就能有这样的环境保护法规,其意义颇值得后人借鉴。规定:从春季二月开始,不准进山砍伐林木;不准堵塞林间水道;不到夏季不准入山采樵,烧草木灰;不准捕捉幼兽幼鸟或掏鸟卵;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诱捕鸟兽的网罗和陷阱。以上禁令,到七月得以解除。这份《田律》禁令,不但保护植物林木、鸟兽鱼鳖,而且还保护水道不得堵塞。这一珍贵文献,可算得上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环境保护法了。
西汉的《四时月令五十条》颁布于公元五年汉平帝时期,这是一份以诏书形式向全国颁布的法律。这部法律规定,每年一月禁止伐木(无论树木大小,都不得砍伐)。二月不能破坏川泽。三月则修缮堤防沟渠。四月不得砍伐树林。五月不能烧草木灰。六月官员派人到山上巡视。从这部法令中可以看出,物要因时禁发,在非开发的季节,不得进山砍伐小树取材,不得捞水草烧灰,不得带捕捉鸟兽的器具出门,不得携网捕鱼等。汉宣帝为保护益鸟,下诏曰:“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
唐代把山林川泽、苑囿、打猎、城市绿化、郊祠神坛、五岳名山纳入政府管理的职责范围。还把京兆、河南两都四郊三百里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管理范围超过了先秦时期。中国最为完备的封建法典《唐律》专设“杂律”一章。“杂律”对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保护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例如,“诸弃毁官和器物及毁伐树木、稼穑者,准盗论。”明朝和清朝基本上延续了《唐律》的环保规定,但是,明朝到仁宗时,朝廷开始放弃管制措施。当时在社会中规定:“山场、园林、湖泊、坑冶、果树、蜜蜂官设守禁者,悉予民”。由于驰禁湖泊,使许多湖泊被盗为田,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人为的自然灾害。明万历年间,官府张榜全国,严禁民间擅捕青蛙,违者“问罪枷号”。《唐律》规定:“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虽种植无所妨废者,不坐。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者与同罪”。
宋代注重了对生物资源的立法保护。从宋代起,人们对围湖造田导致蓄泄两误,滥砍乱伐导致水土流失的问题已经有所觉察,说明当时的有识之士对环境问题的敏感。
明代对山林川泽的保护承袭了前代的规定,并且管制范围相当广泛。到仁宗(公元1425—1426年)时,政府开始放弃管制措施。“山场、园林、湖泊、坑冶、果树、蜜蜂官设守禁者,悉予民。”由于驰禁湖泊,使许多湖泊被盗为田,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人为的自然灾害。这是保护方面的倒退,对环境损害很大。
清朝时由于人口剧增,进而开放了东北、西北及江南的无度开垦,许多草原和山地被开垦为农田,造成了草原退化,沙漠扩展,林木破坏和水土流失。当时的有识之士针对这种无度开垦曾提出警告,但未引起清王朝的重视。清朝的生态环境也在“禁”与“驰禁”中受到掠夺。
二、古代的环保文献
儒家的“制天”与“可持续”思想。儒家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自己,爱惜其他事物的生命,也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先秦时期管子、荀子、孟子的思想中,也闪耀着环境保护的光芒,如管仲认为,“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他提醒人们保护山湖草木,注意防火,按时封禁和开放,反对过度采伐。荀子根据生物资源消长规律,提出了一套保护生物资源的理论和措施。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周礼·春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郑玄注:“物为之厉,毎物有蕃界也。为之守禁,为守者设禁令也。”“厉”与“列”字同音通假,这里是遮列的意思。对山林中的各种资源(“物”)设立“蕃(藩)界”而“遮列”之,实际上就是建立某种资源保护区。当时的各种“时禁”,主要是在这些“保护区”内实施的。所以《周礼·春官·山虞》又说:“春秋之斩木不入禁。”郑注:“非冬夏之时,不得入所禁之中斩木也。斩四野之木可。”所谓“禁”就是上文的“厉”,即山林遮列之处——“保护区”。非禁区春秋可以斩木,但也不是亳无限制。制定了防火法令。《周礼》中还有一个专门“掌行火之政令”的“司”。《周礼·夏官·司爟》:“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时则施火令。凡祭祀,则祭爟。凡国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周礼·秋官·司烜氏》:“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烛,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军旅,修火禁。邦若屋诛,则为明□焉。”
《礼记·曲礼》中说:“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
《周易》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没有节制,自然环境就会日益恶化,人类最终将走向毁灭。《周易》中写到“井甃无咎,……井冽,寒泉食”,就是说井被污染了,不要消极地舍弃不用了,而应该进行修理整治,使之变成“井冽,寒泉”。
《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孔子曾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经》)从这些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非常反对对山林的过度采伐和对鱼虾的滥捕滥杀,这体现了古人伟大而朴素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也反映了我国人民质朴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他认为,人与自然应建立一种爱的关系。人对自然不能只讲索取与征服,必须把自然看作人类的朋友,像爱护朋友一样爱护自然。孔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后汉书·章帝纪》注引《礼记》)我们知道,孝是为人之本,这就意味着他把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惜上升到道德要求的高度。
孔子也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就是说只用钓钩钓鱼不用大网捕鱼,从数量上进行捕捉的限制,达到保护生物的目的。这些思想归结起来,就是要告戒我们要节制,人口要节制,对自然资源的索取要节制,一切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事情都要有所节制,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孟子强调了保护生物资源的重要性。《孟子·梁惠王上》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树木不可胜用也。”
荀子说:“列星旋转,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荀子·天论》,以下凡引该书,只注篇名。)就是说,诸如日月星辰、阴阳四时、风雨霜露、山川草木等林林总总的自然物象及其生化运动的规律或秩序,都是构成“天”的物质要素;所谓“天”不过是客观存在着的自然界本身而已。正是基于对“天”的这种自然而客观的存在实质的界定,荀子做出了“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天论》)的哲学判断。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解蔽》),强调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荀子的思想中还体现了朴素的“可持续”思想,表现在他想到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具体办法,他指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王制》) 《荀子·王制》中载:“五谷不时,果实不熟,不粥(鬻)于市;木不中伐,不粥(鬻)于市;禽兽鱼不中杀,不粥(鬻)于市”。从这两条我国古代早期的环境法律规定不难看出,当时的立法对自然资源主要是生活资源的保护。荀子还曾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鱼鳖鳅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污地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与当今所谓“可持续发展”也不无可比之处吧。《荀子·王制》把保护自然作为圣王之制,书中说:“圣王之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绝其长,鼋鼍鱼鳖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气也。”荀子谈到了生物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树成荫而众鸟息焉,硫酸而螨聚焉。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
《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孔子)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为,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先秦时就规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以成鱼鳖之长”。
《吕氏春秋》一书中。其中颇有“顺时立政”的意味。书中写道:
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
仲春之月: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
季春之月:田猎罼弋,罝罘罗网,喂兽之药,无出九门。
孟夏之月:无伐大树,…… 驱兽无害五谷,无大田猎。
仲夏之月:令民无刈蓝以染,无烧炭。
季夏之月:令渔师伐蛟取鳖,升龟取鼋。…… 树木方盛,…… 无或斩伐。
孟秋之月:鹰乃祭鸟,始用行戮。
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
仲冬之月: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 日至短,则伐林木,取竹箭。
《管子》一书发挥了《易》天地人和的思想。书中说道“凡人之生也,天地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吕氏春秋》也有关于生态保护的思想。
道家的“顺天”和“天人合一”思想,道家以老庄为代表,是中国古代哲学流派之一。道家思想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天人关系,提出“天”与“人”合而为一,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这对中国古代保护环境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庄子曾提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庄子·大宗师》)和“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庄子·秋水》)的顺天思想,对自然听之任之的思想固然不可取,但他道出了自然界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易经》进一步发展了庄子的学说,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点,书中提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先天”是指在自然变化未发生前加以引导,“后天”是指遵循天的变化,尊重自然规律、用哲学原理来解释,就是告诉人们既要顺应自然,尊重客观规律,又要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
《淮南子》主张要想获得更多更好的自然资源,人类就要优化环境,“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之,水积则鱼聚,木茂则鸟集。”古人也非常强调一种环境整治观,即污染了的环境通过整治也可以变成好环境。汉淮南王刘安发展先秦的环保思想,提出了协调发展农林牧渔大农业的可贵思想。他总结前人的经验说,打猎的不能把野兽全部打尽,不要猎取幼小动物,不要把水排干而捕鱼,更不能烧林而捕猎。
本文2023-08-05 00:11:1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15611.html



.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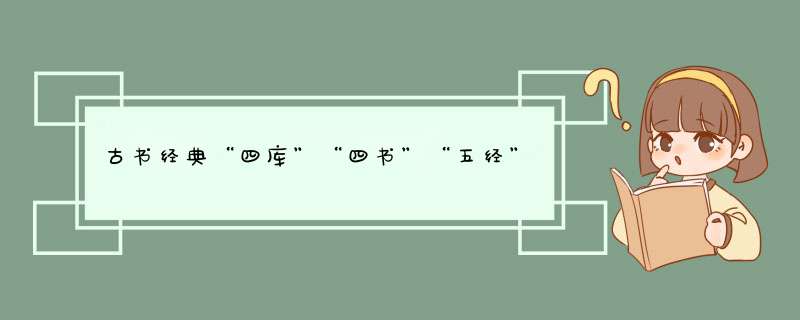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