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的古籍是怎么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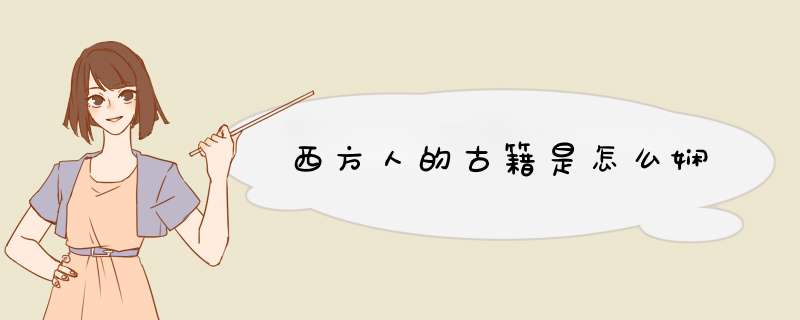
先说说你说的第一句话:看史记,感觉古代文人尽玩“文字游戏”,对自己思维能力提升没有帮助。
这个“文字游戏”,我想应该是指善用典故或春秋笔法。
《史记》其何以见长?述通古今,不虚美不隐恶,辞练文采。这些尽是道德文学修养,岂能比于侦探逻辑小说?想通过读《史记》来提升自己思维能力?可见你读书不得其道了。若论春秋笔法,我觉得实是史书必须。中国古时是极讲求道德伦理,有一定地位的人死了会定諡号,通常都是为了概括其为人,暗含褒贬,目的就是为了扬善贬恶,风行教化。
史书的目的,当然不只是为了记述事实。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见其目的也是为了评判是非,扬善贬恶。史官自已在叙述事实时,要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又不能因个人观点或情感歪曲历史,就不得不用词隐讳,暗含褒贬,才会有“郑伯克段于鄢”这样言简意赅评判得当的历史记述,所谓阐幽发微。后代史家常运用此种笔法,并不是后人的过度解读。
(其实,我窃以为也可能有不得以而为之。众所周知,史笔如铁。然而这样一件极需要执论公允的事情又常会因为犯讳而面临杀身之祸,往往只能是本朝修前朝史,所以才会产生类似于躲避言论审查的用词讲究。)
很多人不区分“读书”一词的内涵,只是简单地以为是获取知识,而不知有修身筑基之说。
如果读书只是从功利效率出发,直接使用Google搜索就行了,有目的性的获取知识,这好像才是最值的方法。
“中国古籍还值的阅读吗”这种问题形式早已在其它地方讨论过好多次,比如有人会问“拉丁文古籍还值得阅读吗?”、“《修昔底德历史》还值得阅读吗?”、“《荷马史诗》还值得阅读吗?”。如果撇去文学修养的需求,还可以换成这样:“《几何原本》还值得阅读吗?”、“《九章算术》还值得阅读吗”、“亚里士多德还值得阅读吗?”,如果历史再跳到五百年后的未来,估计还会有人问:“《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还值得阅读吗?”、“《晶格动力学理论》还值得阅读吗?”
这类问题归根到底其实是这样的一种问题:我们在学习知识时,是否还值得去了解它产生的历史。
对于科学更是如此,数学教科书更是深有此弊病,直接告诉你公式结果,而对于其产生的历史过程我们则知之甚少,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学生没有必要再去了解过去的大师走过的弯路了。
显然,我是属于支持学术与学术史一齐学习了解的。我的论点并不新奇,早已有人论述过。前时读《高观点下的初等数学》与《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时,其中的教育观点更引为知音。
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要问“中国古籍还值的阅读吗”,那就从另一些近代批判书籍中寻找答案吧,以上可供参考。
引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爱心斗士」中一段文字: 让我们首先考察历史,因为在几个方面,历史是教育的核心。这一点无需我来争辩,正如西塞罗所云:“如果你对你出生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这就意味着,你永远只是幼稚的孩童。”只提一点就足以说明历史的重要性:历史是我们“提高觉悟”的最强大的思想手段。不过,关于历史和历史教学还是有一点要强调,因为它们在学校里常常被忽略。历史并非众多必须传授的课程之一;每一门课都有历史,生物学、物理学、数学、文学、音乐、艺术都有自己的历史。我在这里建议,每一位老师都必须是历史老师。比如,只传授今天所知的生物学而不教过去所知的生物学,那就是把知识贬低为纯粹的消费品,那就使学生无缘了解我们知识的重要性,使他们无从知道我们的知识是如何得到的。倘若教学生原子而不提德谟克里特,教电学而不提法拉第,教政治而不提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利,教音乐而不提海顿,那就是不让学生参与 “伟大的会话”。再者,那就是斩断了他们知识的根基。目前,其他的社会对知识的本源都不太感兴趣。了解你的根基不仅仅是了解自己的祖父从何而来,不仅仅是了解他吃过什么苦。你还要知道你的思想从何而来,你为何相信这些理念;你还要了解你的道德感和审美体验从何而来;你还要了解你的世界从何而来,而不仅仅是知道你的家庭从何而来。为了完整展示上文开始的西塞罗的思想,我们再引他的一句话:“除非人的生命融入了祖先的生命,除非人的生命置入历史语境中,否则人生又有何价值呢?”当然,西塞罗所谓的“祖先”并不是指母亲的姑母或姨母。
据此我建议,每一门课程都要当做历史教。这样,学生在初小时就知道,知识不是固化的物体,而是人类发展的某一阶段,有过去也有未来;可惜现在的学生不了解这一点。让我们回头说一说创世论的问题,我们想要说明,四千年前产生的思想不仅在时间上传到今天,而且在意义上发生了变化,这些思想从科学变成宗教暗喻,又从宗教暗喻变成科学。古希伯来人在沙漠帐篷里神奇的思辨,和现代麻省理工学院教室里神奇的思辨,两者之间一以贯之的联系是多么亲切、多么深刻啊!我想要说的是,学科的历史使我们学会其中的联系;历史教育我们:世界并不是每天都被重新创造的,每个人都站在他人的肩头上。题外,引用《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一文中的一段话以概述史学对于人文的重要:
一般说来,一个有着道德感的人,自是一个有着内心敬畏感的人。反之,一个内心无所畏惧的人,一个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无信仰者,自是一个缺乏道德感的人。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前者的宗教意识与后者的历史意识,虽对象不同,但功能相近。
有一些中国学者(多为中青年学者)在比较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时,既发出叹息:中国人缺乏宗教感;又发出呼吁:中国人应亲近宗教,应陶冶出宗教感来。
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有些偏颇:
只看到中国人缺乏诚挚的宗教感,未看到中国人富有醇厚的历史感,即能在某些方面替代宗教感的历史感;
只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巨大差异,未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着一些共性,即都有着内心敬畏感。
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简单的事实,就是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并已延续数千年了,不可能不在中国人的心底酿出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只是这种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在今天变得有些淡薄了。
(我们民族通过著史来维系社会公正这一途径,在不同社会层面有不同表现形式,在主流社会有正史,在民间社会有家谱、墓志、说唱……--从略)
根据上述看法,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其他许多看法,至少还可以引申出下面一些看法。
其一,传统中国史学兼容并包事实判断系统和价值判断系统--传统中国最为丰富的事实判断系统和传统中国最为基本的价值判断系统,因而拥有我们民族最为深厚的精神资源。
正因如此,我们民族拥有一句其他民族不大可能拥有的名言:"史不亡国亦不亡",即史为国本,史为民族精神之根本。
最早的西医文献,一般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Matthieu,1552~1610)开始。而成册最早译著西医著作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德国传教士邓玉函(J,Terrenz,1576~1630),1621年来华译《人身说概》。估测该书成于1621~1630年。《人身说概》可以作为研究的起点,但实际所起的作用及影响并不大。
西医译著在我国产生较大影响的,首推英国皮尔逊著的《种痘奇法》,该书著于1805年,1815年由斯当顿(Staunton)译成中文,皮尔逊的学生丘浩川于1817编译成《引痘略》,风行一时。因此,也有人认为皮尔逊的《引痘略》应该是西医文献在中国流传的起点。而西方医学较系统地传入中国应自合信的中文著作出现开始。
合信(1816——1873 Benjamin Hobson)英国人,医学硕士、皇家外科学会会员,1816年生于诺桑普敦的韦尔弗德,毕业于伦敦大学医学院,1839年受伦敦会派遣来中国。他是以传教医师身份来华,抱有善意,致力于治疗和著述的少数的几个人之一。
合信翻译成中文的医学著作有:
《全体新论》(An Outline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咸丰元年(1851年)
《西医略论》(First Lines of the Practice of Surgery in the West)咸丰七年(1857年)
《内科新说》(Practice of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同上
《博物新编》(Medical Vocabulary) (约1859年)
《妇婴新说》(Treatise on Midwifery and Disease of Children)咸丰八年(1858年)
继合信之后,我国最早的有系统的西医药书籍的翻译当推广方言馆,同治九年(1870年)开始招生,后改名兵工中学堂,下设翻译馆。译著西医书最多的一个是傅兰雅(多与赵元益合作),傅兰雅翻译的西医书籍主要有:《儒门医学》(1876年,4卷,赵元益笔述);《西药大成》(1879年,10卷,赵元益笔述);《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1879年,1卷);《英国洗冤录》(1888年,2卷);《孩童卫生论》(1893年,1卷);《初学卫生论》(1卷)等。另一人为嘉约翰。他两人的译著约占这时西医书的一半,傅兰雅重卫生学,嘉约翰则专重临床外科。
西方人的古籍是怎么娴
本文2023-10-25 07:47:07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167584.html
- 181761-東萊先生分門詩律武庫五_題呂祖謙輯 .pdf
- 181760-東萊先生分門詩律武庫四_題呂祖謙輯 .pdf
- 181759-東萊先生分門詩律武庫三_題呂祖謙輯 .pdf
- 181758-東萊先生分門詩律武庫二_題呂祖謙輯 .pdf
- 181757-東萊先生分門詩律武庫一_題呂祖謙輯 .pdf
- 181756-太學新增合璧聯珠聲律萬卷菁華五十一_李昭═輯 .pdf
- 181755-太學新增合璧聯珠聲律萬卷菁華五十_李昭═輯 .pdf
- 181754-太學新增合璧聯珠聲律萬卷菁華四十九_李昭═輯 .pdf
- 181763-回溪先生史韻一_錢諷輯 .pdf
- 181753-太學新增合璧聯珠聲律萬卷菁華四十八_李昭═輯 .pdf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