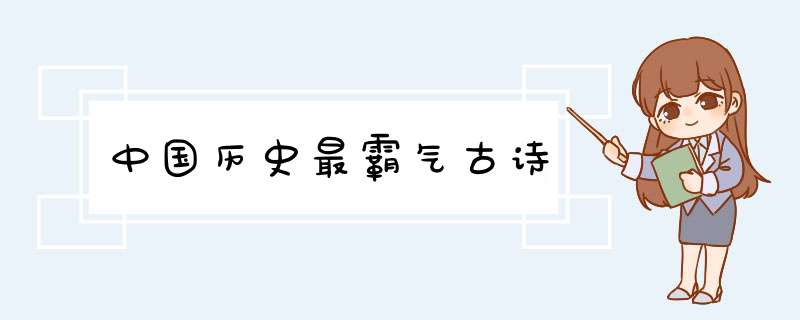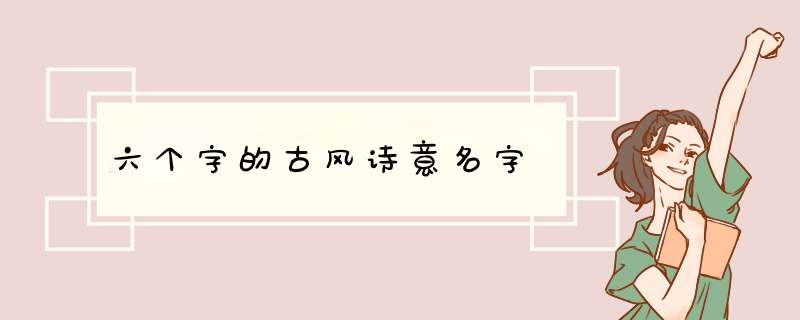中国古代文学与历史

先秦
古谣谚
秦代以前,远及上古时代的歌谣、谚语。先秦诗歌除《诗经》、《楚辞》及“逸诗”外,还有些歌谣谚语,它们也反映了古代诗歌的发展过程。
远在文字出现之先,歌谣就已在人民口头流传。由于当时无法记载下来,今天只能从古代文献中去发掘一些后人追记的材料。如《弹歌》,是一首古朴的原始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它以两个字为一拍,构成四个短句,记录了制造弹弓,弹出土丸,追赶飞禽走兽的狩猎生活片断。相传为上古伊耆氏时代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性》)这本是蜡祭祝辞,辞句带点命令口气,实际上是求八蜡之神消除自然灾害,使人们生活得以安定。歌辞句式整齐,文字技巧已相当熟练,不可能出于传说中的伊耆氏时代,后代追记时大概已加润色。《尚书·汤誓》则记载了传说是夏代末年的歌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表现了人们对暴君的仇恨,具有强烈的反抗情绪。《孟子·梁惠王》也有同样的记载,说是诅咒夏桀的民谣,应当是比较可信的。
传说为上古时代的歌谣,散见于文献中的,还有《击壤歌》、《卿云歌》、《夏人歌》、《麦秀歌》等。所载之书,虽然比较晚出,但韵语赖口头流传,记载之前当已有较长的流传时间,记载时可能作些修饰,又难免受当时文体的影响,但不能断定它们就是伪作。如《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见《帝王世纪》)据记载,这是帝尧时代一个80岁老人所唱的歌。从社会发展史看,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相当低下,不可能有独立“凿井”“耕田”这样的经济生活,那个时代的人,也不大会有“帝力何有于我”的思想。这些牴牾之迹,或出于后人的改笔,但从基本内容看,应该还是产生较早的。再如《卿云歌》:“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见《尚书大传》卷一)这首短诗,有内容,有辞采,句式整齐,技巧娴熟,虞舜时代的口头创作很难达到这样高的造诣,显然经过后人润色,但它的内容,表达了歌颂日月、崇拜自然的朴素感情,保存了古代思想习俗的影子。
古籍中记载的时代稍后一些的歌谣,如《采薇歌》,据《史记·伯夷列传》,它产生于以四言诗为主体的《诗经》时代,象这种艺术上比较成熟的自由体歌辞,即使可能产生,也未必能完全保持原貌。《楚狂接舆歌》(《论语·微子》)、《孺子歌》(《孟子·离娄上》),则已透露出向《楚辞》体过渡的端倪。
与《楚辞》更接近的,是战国时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君兮君不知”,据《说苑》记载,这首歌是从少数民族语言翻译过来的,乘船的是王子鄂君子皙,越人歌手对鄂君拥楫而歌,歌调婉转,感情深挚。“山有木兮木有枝”是一句隐语,“枝”是“知”的叶音,有点象南朝民歌,沈德潜评此诗说:“与‘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夫人》)同一婉至。”(《古诗源》)
古代往往谣、谚并称,其实谣和谚意思相近而又有别。谣指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谚指谚语,它用简单通俗的固定语句,说明一定的道理。
殷商以前的谚语,今已罕见。记载谚语较多的古书莫过于《左传》,如:“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闵公元年》);“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僖公五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僖公五年》);“非宅是卜,唯邻是卜”(《昭公三年》)。这些谚语产生的上限,已经很难考定,而它所反映的内容和表现的形式,都已相当成熟。前两例亦谣亦谚,后两例已近格言,都不可能是上古初民的创作。
《论语》、《孟子》、《荀子》、《国语》、《战国策》、《礼记》等书中记载的古谚语还有很多,产生和写定的时间更晚,大体上都是句式整齐的格言式的语句,是人们劳动和生活经验的总结。
逸诗
先秦古籍中常常引用“诗”句,其中有一些是今本《诗经》305篇以外的,前人称它们为“逸诗”。
今传的《诗经》并非足本,如《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等6篇,篇名都见于《仪礼·乡饮酒礼》和《仪礼·燕礼》,而其辞不存。《毛传》以为“有其义而亡其辞”,朱熹《诗集传》认为这6篇皆“有声而无辞”。多数学者则同意《毛传》之说,以为本来有辞而亡逸了。还有《商颂》,据《国语·鲁语》说,原来有12篇,今《诗经》所收只有5篇,其他7篇何时散逸不能定。此外,今传本《诗经》中还有阙句的情况,如《小雅·沔水》共3章,前2章每章皆8句,而第3章仅有6句,朱熹疑脱首2句;《周颂·维清》仅有4句,朱熹疑有脱文;《鲁颂·(外门内必)宫》共9章,前5章中,第一、第二、三、五章每章皆17句,独第四章为16句,朱熹以为脱1句。姚际恒《诗经通论》反对朱熹之说,以为此诗无阙句,但理由不足。
先秦古籍所引的“诗”句,如《荀子·王霸》所引“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臣道》所引“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以及《解蔽》、《正名》和《法行》等篇中都有些“诗”句,但不见于今本《诗经》。又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以及《左传·成公九年》、《襄公五年》、《襄公八年》、《襄公三十年》、《昭公四年》、《昭公十二年》、《昭公二十六年》中所引的一些诗,也都如此。但这些诗是否都是原属《诗经》所收而后散逸的诗,尚难断定。其他古籍如《国语》、《论语》等书中还有一些。这些“逸诗”总数并不很多。
清代郝懿行《郝氏遗书》中有《诗经拾遗》1卷,辑录较为完备。
骚体
骚体是韵文体裁的一种,得名于屈原的作品《离骚》。由于后人常以“骚”来概括《楚辞》,所以“骚体”亦可称为“楚辞体”。由于汉代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大人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等作品与《离骚》体裁相类,所以后者亦被称之为“骚体赋”。这样,“骚体”又包括了与《离骚》形式相近的一些赋。
骚体是屈原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所创造的一种抒情韵文,以《离骚》为代表,一般篇幅较长,句式灵活参差,多六、七言,以“兮”字作语助词。另外,过去有人总结过,“骚”调以虚字为句腰,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平仄相异为谐调,平仄相同为拗调;《九歌》以“兮”字为句腰,句调谐拗亦同。骚体可以称诗,亦可以指赋。汉以后署名蔡琰的骚体《悲愤诗》后半部分,韩愈的《复志赋》,柳宗元的《惩咎赋》、《闵生赋》等均可归入骚体类。
骚体主要作家:屈原、宋玉、蔡琰。
回到菜单
--------------------------------------------------------------------------------
秦汉
两汉乐府
乐府原是汉代掌管音乐的官署,由于专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入乐的民歌俗曲和歌辞。在六朝,更明确地把“乐府”和“古诗”相对并举,以区别入乐的歌辞和讽诵吟咏的徒诗这两类诗歌体裁。宋、元以后,“乐府”又被借作词、曲的一种雅称。
东汉民间歌谣异常活跃,多与汉光武帝采取听风察政的用人政策以及迷信谶纬术数有密切关系。光武帝“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促使“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建武、永平之间,吏事深刻,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后汉书·循吏传序》)。“谣言”即“谓听百姓风谣善恶”(《后汉书·刘陶传》注)。和帝曾“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后汉书·李郃传》),灵帝也曾“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后汉书·刘陶传》)。以至于州官上任,也“羸服间行”,“观历县邑,采问风谣”(《后汉书·羊续传》)。这种用人政策措施,显然助长地方吏民士流利用歌谣制造舆论,成为结党斗争的政治手段。与此同时,推行谶纬术数的儒生方士往往编造、利用民间歌谣以神其说。因此,有关史传志书所载歌谣多为政治性和风俗性的徒歌谣辞,其中相当一部分实出文人之手,其采集与音乐官署无涉。
今存两汉乐府歌辞中最有价值的作品是50余首民歌、部分谣谚和少量有主名或无名氏文人诗歌,其中民歌歌辞的写作时期,多数难以确定,前人或据乐曲本事与古辞旨意的相合与否,或泛引史事以推测讽谏意向,都可作参考,但不足以断定写作时期。大体说,《汉铙歌十八曲》由于当时“但取铙歌为军乐之声”(朱乾《乐府正义》),曲、辞早已分别存用,而歌辞久未整理,声、辞混杂,不易通晓,其中有原始古辞或后补之辞,则其写作当在西汉初期或更早时期。《相和歌》本是汉旧曲,“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宋书·乐志》)。《乐府诗集》卷二十六“《晋书·乐志》载:‘凡乐章古辞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采莲》、《乌生八九子》、《白头吟》之属’,其后渐被于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其中有一些当是西汉作品,但也有东汉作品,如《雁门太守行》歌咏东汉洛阳令王涣事,并非曲题古辞。《杂曲》本是乐府未收歌曲,其歌辞亦多东汉作品。至于谣谚及文人制作,则或有记载,或可考略,也以东汉作品为多。所以,今存两汉乐府,大致东汉作品多于西汉。
乐府官同黄门,事近倡优,在人品分清浊、诗乐辩雅俗的传统观念中是受轻视的。汉元帝好音乐,欣赏定陶王懂音乐,大臣史丹批评说:“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则是陈惠、李微(皆黄门鼓吹)高于匡衡,可相国也。”(《汉书·史丹传》)皇帝不免顾忌,文人势必更受拘束。而乐府歌曲为俗曲,五、七、杂言歌辞是“俳谐倡优所用”的俗体(挚虞《文章流别论》),所以西汉著名作者“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钟嵘《诗品序》)。东汉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为数甚少。大约在顺帝、桓帝时期,民间涌现出一批无名氏文人写作的五言诗,即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五言“古诗”,其中有的就是乐府歌辞,到魏晋仍被弦歌。此外,两汉黄门乐人也写作歌辞,如李延年就有《北方有佳人》歌一首,东汉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更是乐府歌辞的名篇。总起来看,两汉乐府歌辞的成就,主要以民间创作为代表。
今存两汉乐府歌辞谣谚作品,有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元代左克明《古乐府》,明代冯惟讷《古诗纪》,梅鼎祚《古乐苑》等总集。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将前人所辑全部搜列。
回到菜单
--------------------------------------------------------------------------------
魏晋
建安七子
建安年间(公元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瑀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瑒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瑀《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瑒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在诗歌方面,“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在辞赋方面,“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第二,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第三,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在散文方面,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干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正始体
正始为三国曹魏第三代皇帝曹芳年号,自公元240年至249年。不过习惯上所说的“正始体”,是指包括正始在内的整个曹魏后期(240~265)的文学风貌。
从文学史阶段来说,正始上承建安,下接太康,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转折时期。然而正始文学,并非浑然一体,大略又可析为两个流派。一派以何晏、王弼为代表,史称“王何”。这派作者都宗尚老庄,校练名理,喜好玄谈。他们大多出身贵族,身居高位。他们的诗歌,大多以抒发道家志趣为主旨,娱心老庄、游志玄虚,所以刘勰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另一派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包括“竹林七贤”中的一些人。他们也都宗尚老庄,喜好清言,但对现实矛盾也比较关心。他们的诗歌以抒发自己的现实生活感受为主,有比较深厚的内容,加上艺术技巧比较圆熟,成就大大超过前一派,阮籍的《咏怀诗》是最优秀的代表。刘勰说:“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同前)正是指出了他们创作的基本特色。不过,由于这一派作家大多处在执掌大权的司马氏集团的政治高压之下,处境微妙而危殆,所以他们作品的锋芒和现实性,也在不同程度上受着限制。总的来说,嵇、阮一派继承着建安文学的遗风,表现了时代现实的特色,而王、何一派则与建安文学传统已经脱节,开了两晋玄虚之风的先河。这两派的综合,就构成“正始体”的基本面貌。
太康体
这是西晋时期一种诗风,或一种诗体。“太康”(公元280~289)为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太康体”之名,始见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严说本于梁钟嵘《诗品》“太康中,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钟嵘此论,是概述西晋初年和中期一个阶段的诗风。而严羽则明确指太康时期以左思、潘岳等为代表的诗体,即其所谓“分明别是一副语言”。
太康前后是西晋文坛上比较繁荣的时期,众多的作家都有不少传世之作。太康诗歌一般以陆机、潘岳为代表。他们的诗歌比较注重艺术形式的追求,讲究辞藻华美和对偶工整,“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诗歌的技巧虽更臻精美,但有时过分追求形式,往往失于雕琢,流于拙滞,笔力平弱。总之“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文心雕龙·明诗》),是这一时期诗人的总风格。不过每个作家仍有独特之处,“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文学》)。其他如张协以造语新颖,“巧构形似之言”著称。左思则在太康诗风中独树一帜。其诗内容充实、语言质朴,气势雄浑,“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简贵”(《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不失汉魏遗风。
玄言诗
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自魏晋以后,社会动荡不安,士大夫托意玄虚以求全身远祸。到了西晋后期,这种风气,逐步影响到诗歌创作。尤其是东晋时代,更因佛教的盛行,使玄学与佛教逐步结合,许多诗人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玄理的领悟。《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老子)之旨归,赋乃漆园(庄子)之义疏。”《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还指出“过江(指东晋)佛理尤盛”。这个诗派的出现,虽反映了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但其实质则与王弼、何晏、阮籍、嵇康等早期玄学家不尽相同。西晋后期,玄学已成为门阀士族的思想理论,这种理论又经东晋支遁诸人之手,与佛教思想结合起来,反映当时士大夫逃避现实的精神状态。孙绰、许询是玄言诗人的代表。由于玄言诗大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缺乏艺术形象及真挚感情,文学价值不高,所以作品绝大多数失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有孙绰诗12首、许询诗3首。此外,谢安、王羲之等所作的《兰亭诗》,也是典型的玄言诗。不过由于魏晋玄学提倡“得意忘象”,所以自然景物也往往作为领略玄趣的:“言象”出现在玄言诗人的笔下。如孙绰《秋日》诗就写得较有文采。许询也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的写景佳句。《兰亭诗》中也有较为生动的景物描写。谢灵运那种夹带玄言的山水诗,和陶渊明一些诗所创造的恬淡意境,似也多少受到玄言诗的影响。
代表作家:孙绰、许询、谢安、王羲之。
竹林七贤
三国魏末七位名士的合称,他们是谯国嵇康、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沛国刘伶、陈留阮咸、琅邪王戎。由于他们互有交往,而且曾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七人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服膺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七人在文学创作上成就不一。阮籍的五言诗,嵇康的散文,在文学史上都占重要地位。向秀的赋,今存唯《思旧赋》一篇,篇帙短小,感情深挚,亦称名作。刘伶有散文《酒德颂》,风格与阮籍《大人先生传》颇相接近。他的五言诗也有一定水平,但今存作品很少。阮咸精通音律,然而在文学方面没有留下作品。山涛、王戎虽擅清言,但似乎不长于文笔。《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今所见佚文,全部是奏启文字,文学价值不大。王戎的著作则很少。
回到菜单
--------------------------------------------------------------------------------
南北朝
杂体诗
通指古典诗歌正式体类以外的各种各样的诗体。这些诗多把字形、句法、声律和押韵加以特殊变化,成为独出心裁的奇异之作,一般带有文字游戏性质。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说:“按诗有杂体:一曰拗体,二曰蜂腰体,三曰断弦体,四曰隔句体,五曰偷春体,六曰首尾吟体,七曰盘中体,八曰回文体,九曰仄句体,十曰叠字体,十一曰句用字体,十二曰藁砧体,十三曰两头纤纤体,十四曰三妇艳体,十五曰五杂俎体,十六曰五仄体,十七曰四声体,十八曰双声叠韵体,十九曰问答体,皆诗之变体也。”实际上可以归为杂体诗类的远不止上述这些。诸如藏头诗,神智体,辘轳体等等。杂体诗多为汉魏六朝时文人所创制,虽表现出一定的巧思和驾驭文字的能力,但“终非诗体之正”(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一般不能列为正规的文学作品。
乐府诗
原为音乐官署,始置于西汉。掌管朝会庙堂所用的音乐,制定乐谱,训练乐工,采集民间诗歌和乐曲。后来,把乐府官署所采集、创作的歌辞,统称为“乐府诗”,或简称为“乐府”。后世也称魏晋至唐代可以入乐的诗歌和后人仿效乐府古题的作品为“乐府”。宋、元、明的词、散曲和剧曲,因配合音乐,有时也称为“乐府”。
宫体诗
南朝梁后期和陈代所流行的一种诗歌流派。“宫体”之名,始见于《梁书·简文帝纪》对萧纲的评语:“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但这种风格的诗歌,自梁武帝及吴均、何逊、刘孝绰已开其端。宫体诗的主要作者就是萧纲、萧绎以及聚集于他们周围的一些文人如徐干、庾肩吾、徐陵等,陈后主陈叔宝及其侍从文人也可归入此类。历来对宫体诗的批评,多以为其中有不少以写妇女生活及体态为内容,其实宫体诗内容并非限于妇女生活,也有一些抒情咏物之作,即使写妇女生活的作品,格调低下的也只占少数。总的来说,宫体诗的情调流于轻艳,诗风比较柔靡缓弱。至于被称为宫体诗人的萧纲、萧绎等人,也写过不少清丽可读之作,至于庾肩吾、徐陵等,更有一些比较优秀的诗篇。
从诗歌发展史上看,宫体诗起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隋及唐初诗风流于靡弱,多少是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在形式上比永明体更趋格律化。《梁书·徐摛传》称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这种“新变”正是宫体诗的形式特点。据有的学者统计,宫体诗中符合律诗格律的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基本符合的数量尤多。这说明“宫体诗”对后来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于它用典多、辞藻秾丽的特点,对后世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唐代的李贺和李商隐的诗,显然曾吸取过“宫体诗”的某些手法。
代表作家:萧纲、萧绎、徐干、庾肩吾、徐陵。
徐庾体
指南北朝时期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的诗文风格。徐摛和庾肩吾都是南朝梁后期诗人,为简文帝萧纲所器重,并以写艳体诗闻名。徐陵和庾信早年仕梁,诗风亦继承父辈,比较靡丽,而且多用典。徐陵后来仕陈,继续写作艳体诗。庾信则因出使被留在北周,后期诗风有所变化,显得苍凉刚健,非徐陵所及;但重辞藻、用典多的特点,仍与徐有相似之处。唐代元稹为杜甫作墓志铭,曾概括“徐庾”的特色为“流丽”,这是就诗来说的。就骈文而论,则专指徐陵和庾信两人。他们比前辈沈约、任昉等,更讲究用典,写得更丽逸,但由于过份拘泥于典故,有时个别文句欠通顺,影响了文章的流畅。
清代蒋士铨说:“唐四六毕竟滞而不逸,丽而不遒。徐孝穆(徐陵)逸而不遒。庾子山(庾信)遒逸兼之,所以独有千古。”(《评选四六法海·总论》)这段话虽有推崇过当处,但指出了徐、庾的共同点,并且指出庾信骈文胜于徐陵,则不失为公允之论。
联句
古代作诗的方式之一,即由两人或多人共作一诗,联结成篇。旧传最早的联句始于汉武帝时《柏梁台诗》,全诗七言,26句,分别由26人出句,一句一意,相联而成,每句用韵,后人又称其为“柏梁体”。但据后人考订,此诗系伪托之作,并不可靠。晋
文艺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研究文学的起源,不仅能从发生学角度来解释文学产生之谜,而且能由此阐明文学与社会生活、与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正确地认识文学的本质。
中外关于文学起源的理论 自古以来,许多文艺理论家对文学起源的问题发表过见解,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有以下几种:
①模仿说。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首先提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的模仿。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认为诗歌起源于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模仿,而模仿的本能植根于人的天性之中。古罗马的卢克莱修、贺拉斯,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似。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马佐尼,既把诗看成是模仿的艺术,又把诗看作是游戏,实际上把文学的起源归之于模仿的游戏。稍后英国的锡德尼,通过对印第安人原始文学的论述,指出文学产生于含蕴着教育和愉悦意味的模仿。这些说法,承认文学的源泉是自然界和社会生活,闪烁着唯物主义思想光采。但他们把模仿解释为人的某种天性,忽视了社会实践在形成人的心理能力上的巨大作用。
②神示说。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就把诗歌的产生解释为神的灵感在诗人身上的凭附。欧洲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则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的心灵,而心灵是上帝的形象和创造物。这种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很流行。如薄迦丘认为,诗是一种实践的艺术,发源于上帝的胸怀。甚至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培根,也流露出诗歌产生于上帝启示的观点。“神示说”随着近代文明的演进,逐渐失去了说服力。还在18世纪,便有一批哲学家(如赫尔德尔等人),驳斥了它的荒谬。
③游戏说。16世纪的马佐尼,在倡导模仿说的同时,披露了“文艺是游戏”的观点。德国哲学家康德,进一步把诗歌看成是“想象力的自由游戏”。到了席勒,正式形成了艺术起源的“游戏说”。席勒认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束缚,渴望运用过剩的精力去达到自由,这就是游戏;而艺术活动,即在游戏中导源。19世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对席勒的观点作了补充,指出艺术和游戏的本质是人们发泄过剩精力的自由模仿活动。著有《人类的游戏》等书的格鲁斯,则批判地接受席勒的“游戏说”,认为游戏不是因为精力过剩,而是对实用活动的准备和练习。“游戏说”曾经受到居约、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批评。当心理学家冯德提出“游戏是劳动的产儿”观点后,普列汉诺夫又在这个观点上部分肯定了“游戏说”。
④心灵表现说。把艺术看成是人类心灵(包括思想、情感等等)的一种表现,早在古希腊哲学中就露出端倪。19世纪,它广泛地为浪漫主义艺术家、理论家所提倡。雪莱在其《诗辩》中说,诗歌是“野蛮人表达周围事物所感发他的感情”,是一种“想象的表现”。柯勒律治也认为,诗歌发源于并不反映现实而又能自身完美的想象 力。这种“想象表现说”,还得到布拉德雷、王尔德等人的支持。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则认为艺术是人类表达感情的工具,起源于人们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这种“情感表现说”,拥有更多的支持者。著有《艺术的起源》一书的希尔恩,把艺术说成是“交流思想的重要手段”。近代美学家理德、艾伯克朗龙比、理查德等人,都赞同这种“思想表达说”。意大利唯心主义美学家克罗齐,反对艺术表现任何理性思想,宣传“直觉即表现”、“直觉即艺术”,实际上把艺术的起源归为低级的、只能反映个别意象的直觉。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风靡一时。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用精神分析主义观点解释艺术的起源,认为人的心理有意识与潜意识两个对立部分,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性本能是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性本能总受到现实的压抑,当人们把它转移到所希望的幻想生活创造中去时,就产生了艺术,所以艺术实质上是以性本能为核心的无意识表现。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与弗洛伊德近似。他们都拥有大批信徒,迄今还在西方盛行。以上各种观点,都从一个侧面抓住了艺术表现人的心理的特征;但他们总把人的心理看成是与现实生活脱节的先验的东西,并未能真正解决艺术起源问题,只是把这个问题抽象化、神秘化了。
⑤巫术说。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最初谈到了原始诗歌与原始宗教的密切关系;但他还没有明确地指出诗歌起源于巫术。19世纪以来,以泰勒、弗雷泽、哈特兰特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对现存原始部族的巫术进行了深入研究,为艺术起源的“巫术说”提供了丰富材料。法国考古学家雷纳克,就在这些资料基础上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始人交感巫术的论点,认为原始艺术实际上是巫术的一种,目的是祈求狩猎的成功。这一论点在20世纪以来颇为流行,当代许多美学家(吉德逊等人)都加以赞同。但马林诺夫斯基等民族学家则提供了某些原始部族只有艺术并无巫术的资料,使得“巫术说”难以自圆其说。
⑥劳动说。明确地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实际上始于19世纪晚期的一批民族学家、艺术史家。德国的毕歇尔在《劳动与节奏》中指出,劳动、音乐和诗歌最初是三位一体地联系着的,它们的基础是劳动。梅森认为最原始的诗歌是劳动诗歌,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劳动的效果。德索在《美学与艺术理论》中也谈到了诗歌与劳动的关系,但他认为劳动诗歌的目的不是为了加强劳动,而是为了使劳动变得更轻松。普列汉诺夫在其名著《没有地址的信》中,论述了许多“劳动先于艺术”的实例,他的主要观点是:“艺术发展是和生产力发展有着因果联系的,虽然并非总是直接的联系。”若干年来,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在苏联和中国的文艺理论界盛行;但有时简单地寻求劳动与艺术的“直接的联系”,不能完满地解释一切原始艺术的起源。对艺术起源的“劳动说”,应防止其简单化和绝对化。
除了上述各种观点之外,19世纪以来,还有其他一些关于艺术起源的学说。如:法国艺术史家丹纳认为文学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要素,他和德国人类学家拉策尔等人被称为“社会学派”;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艺术(特别是音乐)起源于从鸟类动物就有的性的吸引,这种艺术起源上的“性爱说”,如今已被大多数美学家摈弃;当代美国史前考古学家马沙克认为最早的艺术乃是原始人记录季节变换的符号体系,等等。
在中国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艺术起源或原始艺术的记述。中国古籍一致认为文学艺术的起源很早。汉代郑玄在《诗谱·序》中说:“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把“诗之兴”定于传说中的虞舜时代。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认为诗歌“必不初起舜时也”,“讴歌自当久远”。南北朝时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然则歌咏所生,宜自生民始也。”和他同时的刘勰也持有同样看法。可见,1500年前的中国古代学者,已经得出文学艺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结论。同时,中国古籍也记述了几种艺术起源的观点。《吕氏春秋·古乐》谈到原始的乐歌是“效八风之音”、“听凤凰之鸣”而产生的;《路史·后记十》写道:帝尧“命质放山川溪谷之音,以歌八风。”晋代阮籍在《乐论》中也指出原始乐歌具有“体万物之生”的特征。这实际上是一种艺术
起源于模仿的观点。《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这些观点与西方的“表现说”相似。在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诗言志”的观点占有统治的地位。《吕氏春秋·古乐》记述了传说产生于上古时代的“葛天氏之乐”的篇名,其中的《奋五谷》大约歌唱农业生产,《总禽兽之极》大约歌唱狩猎生活。《吕氏春秋·*辞》与《淮南子·道应训》记述了“前呼邪许,后亦应之”的“举重劝力之歌”。在《史记》索隐引《三皇本纪》和《古今图书集成》引《辨乐论》中,还记述了伏羲时代的“网罟之歌”。大概是基于这种情况,《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释里提出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观点,蕴含着劳动生产诗歌的思想。《周易》说:“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周礼》说:“大合乐以致鬼神示。”《汉书》说:“乐者歌九德,诵六诗,是以荐之郊庙,则鬼神享之。”《路史·后纪八》说:“……为圭水之曲,以召而生物。”这些记述,揭示了诗歌乐舞与祭祀巫术的密切联系。可见在中国古籍中,关于艺术的起源也进行了多方面探讨。以上列举的各项见解,均属猜测性的假说,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都未能全面占有资料,各自只抓住了问题的一个侧面。今天,在研究文学艺术起源时所应依据的资料有以下几种:①史前考古学资料;②现存原始部族的民族学资料;③古籍中关于文学艺术起源的记述;④可供参考的儿童艺术心理学资料。对比起来看,史前考古学资料最为可靠。但基本上凭借口头流传的原始文学,同音乐、舞蹈等时间艺术一样,极难在史前考古学资料中留下痕迹。因此,在20世纪初还保留原始特征的澳洲土人、南非布须曼人、爱斯基摩人(他们大体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的渔猎民族)、太平洋各岛屿的美拉尼西亚人和波里尼西亚人、美洲印第安人(他们大体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农牧民族),以及中国的鄂伦春、鄂温克、佤、纳西、独龙、怒、布朗等少数民族,就成为研究的重要依据。此外,各民族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古歌、史诗,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根据大量的现存原始部族的民俗资料,可知在一般情况下,原始诗歌与音乐、舞蹈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的产生,不会比原始造型艺术产生的年代晚很多。据放射性同位素碳的测定,绘有巫术仪式图像的马格德林期洞画,约出现于公元前18000年至11000年之间。这个年代,可确定为原始诗歌起源的下限。实际上,原始诗歌起源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些。
文学起源研究的新趋向 尽管原始诗歌与音乐、舞蹈关系密切,但并不能像冯德那样把原始诗歌看成是舞蹈的衍生物。原始诗歌自有独特的、多元的起源途径。最初,原始人进行体力劳动,会在劳动呼声中嵌进一些没有意义的单词,如“邪许”之类,目的是减轻劳动的紧张,获得因声音的重复而产生的愉快。在有些情况上,它相反地又能协调大家的劳动动作,成为组织集体劳动的信号。更进一步,人们不满足于声音的简单重复,就会进入到韵律阶段。韵律和节奏一样,都能给劳动者以听觉的快感。开始时因为缺少足够的词汇,常常运用没有意义的衬词来押韵。鄂伦春族一首原始狩猎歌曲:“阿索亚,阿索亚,黑色的毕拉尔河呀!阿索亚,阿索亚,沿着河道游猎呀!……”这里的“阿索亚”,就是用来押韵的衬词。尔后衬词取消了,人们把叶韵的生活词汇组合在一起,像《吴越春秋》记载的传说是黄帝时代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那就是一首完整的诗歌了。由此可见,原始人的劳动呼声和劳动号子,乃是产生原始诗歌的胚基。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即人们在劳动胜利后用诗歌来表达狂欢的心情。例如南美波托库多人的一首歌:“今天打猎打的好,一只野兽被杀掉;现在有了食物了,吃的美来喝的饱。”再如鄂温克族的《欢喜歌》:“蹦蹦跳跳的狐狸,欢喜嫩绿的草地;各处来的客人们,一起玩乐最欢喜。奔跑嬉闹的狐狸,喜欢山高林子密;各处来的客人们,一起唱歌最欢喜。”可见单纯地表现情感,也能产生原始诗歌。但这种情感并非先验的“人之天性”,而是与原始部族人的劳动或生活紧密相连的。原始公社后期,部族间的战争愈益频繁,一些诗歌是用来激昂士气的,如澳洲土人的一首战歌:“刺他的额,刺他的胸;刺他的肝,刺他的心;刺他的腰,刺他的肩;刺他的腹,刺他的肋!”在鼓舞战斗激情同时,带有演习操练的意味。流传在贵州剑河地区的苗族古歌唱道:“用石头当锄头,折树枝当钉耙,划竹蔑当撮箕,到山上去开田。”诗歌伴随舞蹈,也有操练生产动作的意味。因此,最初产生的原始诗歌,大都与实用性目的有关。那些在巫术中咏唱的诗歌,表面上看来是荒诞迷信的,究其实质,仍然是为了征服异化的自然,谋取生活的资料。而且巫术中的许多细节,正是变相的劳动动作。所以,战争诗歌、模仿性的操练诗歌、巫术诗歌,全没有同劳动生活绝缘,鉴于这些理由,也鉴于劳动的诗歌起源最早,可以把劳动看成是文学起源的初始的、核心的原因。
然而,其他一些原始文学样式的起源,不能都简单地归之于劳动。原始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日益丰富发展。比劳动诗歌较为晚起的性爱诗歌,应认为是从原始部族人的炽烈情欲发端的。在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鄂伦春人中搜集到的吟咏自然美、吟咏爱情的诗歌,出现得更晚,它们达到了真正的艺术审美品格,是由复杂的原因形成的。神话、传说、史诗、动植物故事、谚语、童话等文学样式,大约在原始公社后期产生。它们产生的原 因也是多方面的,或者是想对自然现象进行解释,或者是记录部族的斗争史,或者是向后代传播知识经验,或者是用英雄祖先的精神激励部族成员,甚至把它们充作少男少女举行“成丁式”的考试科目。有些诗歌、神话与史诗,被列为氏族的经典,只能由氏族酋长和巫师来掌握。但也有不少诗歌、神话、故事、谚语,成为全部族共有的精神财富,通过口头方式流传。因此,就总体来说,原始文学起源的契机是复杂的。近代几名专门研究艺术起源的学者,如分别著有《艺术的起源》专著的格罗塞、希尔恩,著有《艺术的演进》的哈顿及普列汉诺夫、柯斯文、德索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流露出多元论倾向。今天,把文学的起源归之为以劳动为核心的多种社会实践,形成最新的理论研究趋向。
中国古代文学与历史
本文2023-10-28 08:55:46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1776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