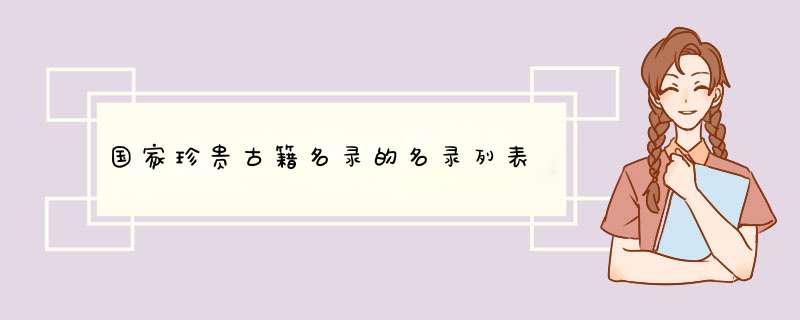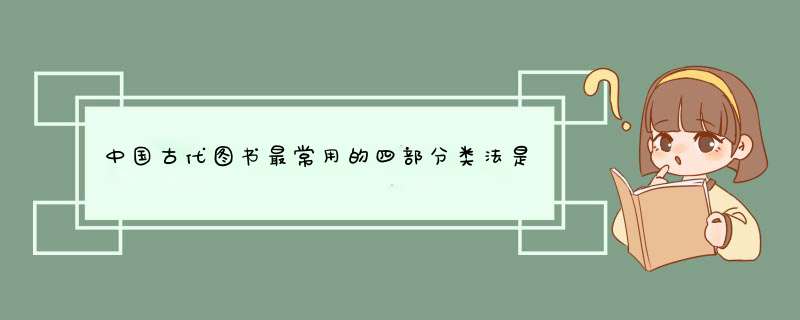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标示错误

将其他单位藏书误标为河南省图书馆藏书
(1)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书目中,书名编号9508的《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宋章如愚辑,元延祐七年圆沙书院刻明修本),其收藏单位的代号有:0101,0201,2201(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检索表》,以下此类情况不再进行说明)。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2201指代的是河南省图书馆(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中“0101”原指“北京图书馆”,以下行文统称为“国家图书馆”)。经查河南省馆藏书和目录,却并无此书。查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正式出版前的《征求意见稿》对藏书单位的标示,该书为代号2261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又请河南省社科院图书馆确认,此书的确是其所藏。可以确切地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2261误为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9508 0101,0201,2261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编号8868的[万历]《山西通志三十卷》(明李维桢纂修,明万历刻本),标示有四家单位收藏,其中河南省只有一家,即河南省图书馆。经过一番查找求证,确认河南省馆没有收藏此书。查《征求意见稿》,又查当年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河南省内各单位著录各自所藏古籍善本、而后汇总到河南省馆的善本目录卡片(注:由于时间、地点、人事变化等的缘故,笔者没能见到这部分善本目录卡片的全部。以下行文中称其为“善本目录卡片”),均显示该书为河南省南阳市图书馆收藏,又与南阳市馆核对无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错将南阳市图书馆的代号2210印成了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8868 0101X,0201X,0581,2210X
(3)《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代号9165的[顺治]《西华县志八卷》(清左国桢、王鼎镇等纂修,清顺治刻本),标示只有河南省图书馆一家收藏,为孤本。经过对河南省馆藏书的追究,又查《征求意见稿》和善本目录卡片,该书的收藏单位实为南阳市图书馆,经过联系,南阳市馆也对此书予以了确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错误与上述[万历]《山西通志》的错误相同。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9165 2210
(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书目中,书名编号2734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宋范纯仁撰,元刻明修本),标示国内有三家图书馆收藏,河南省图书馆为一家,另两家分别为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征求意见稿》的标示同上(注:《征求意见稿》集部宋别集类中,该书名编号为551)。但遍查河南省图书馆现有的古籍目录,却未见有对此书的著录。查善本目录卡片,关于元刻本的范纯仁文集,只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一张“二范集四十四卷”的目录卡片(归入集部宋别集类)中,显示有“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位于其父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之后,版本著录为“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中,先后著录有范氏父子的集子。书名编号2355的为“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宋范仲淹撰)遗文一卷(宋范纯仁、范纯粹撰)年谱一卷(宋楼钥撰)年谱补遗一卷祭文一卷诸贤赞颂论疏一卷论颂一卷诗颂一卷朝廷优崇一卷言行拾遗事录四卷鄱阳遗事录一卷遗迹一卷褒贤祠记二卷义庄规矩一卷”(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一书,在其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可以找到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且标示其所藏书残缺;《征求意见稿》著录相同,只是未标示残缺且书名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略有差异(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192)。而在所有的元刻本(包括元刻明修本)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书名编号从2732至2735)的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却都没有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只有在书名编号2734《范忠宣公文集》(元刻明修本)的藏书单位代号中,有河南省图书馆的代号2201。又查《征求意见稿》(该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551),藏书单位的标示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相同。综上所述,可以推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编纂过程中,将原本是郑州大学图书馆藏书《范忠宣公文集》误标成河南省图书馆的藏书了。如果笔者的这种推论不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于郑州大学图书馆所藏范氏父子的这两种书籍的残缺情况、版本等方面的认定与著录,与郑州大学图书馆原来的判断和著录也是有所不同的。河南省图书馆现存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二范集四十四卷”的另一张目录卡片,它与前面所提到的那张卡片著录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在卡片背面多出了对于书籍行款、版式、序文、牌记、印鉴等方面的描述文字,文字的旁边还有铅笔批字:“据纸张墨色看,系元刻明印本。”这一点似乎也能从另一方面佐证笔者的上述判断。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2734 0101,0201,2241
在元代是最先对善本的开发与推广,“善本”原指那些版刻古籍中的校刊好、装帧好,时代久、流传少,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书籍。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对善本的概念不断完善,最后形成了现在通用的“三性”、“九条”说。善本的“三性”指书籍应具备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善本的“九条”主要包括: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明代刻、抄写的图书;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等。善本的时代下限,现在一般确定在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孤本”指的是仅存一本的图书,也包括仅存一份的某书的某种碑刻的旧拓本和未刊刻的手稿等。现存世界最早的印刷品——唐代印刷的《金刚经》,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明末清初小说《后水浒传》,都是孤本,因而身价极高。由于孤本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为人所重。正因为此,有的人不惜假造“孤本”以欺世盗利。《世载堂杂忆》中载:杨守敬住武昌时,藏有宋刻大观年间《本草》一部,因此书为孤本,价值昂贵,引得时人觊觎。邻人柯逢时以高价代售为名,将此书借看一昼夜。书借到手后,柯逢时全家上阵,一夜之间把书全抄了下来,次日还书时,柯说“这书并不珍贵,市场上已有刻本可见。”几个月后,书肆上果然有《本草》出售,杨守敬方悟被骗,于是“恨之刺骨,至移家避道,终身不相见”。“珍本”指的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的书籍或文学资料。如罕见的革命文献、极有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等。珍本贵在“难得”,所以国内所存较早较稀有的原拓版本,就是稀世珍本。孤本属于珍本的范畴。祝您生活愉快,谢谢提问😊
一个文化大省,要有标志性人物,山东省因为有孔子、孟子、管子、墨子、孙武、孙膑这样一些誉满中外的文化名人,因而被公认为文化大省。但是,一个文化大省还必须有标志性的文献。以省级地方文献丛编为例,清代道光至同治年间广东的伍元薇、伍崇曜编刻《岭南遗书》、光绪年间定州王灏编刻《畿辅丛书》、民国年间山西省文献委员会排印《山右丛书初编》、金毓黻编印《辽海丛书》、张鹏一编印《关陇丛书》、安徽丛书编审委员会影印《安徽丛书》、卢靖编刻《湖北先正遗书》、孙文昱编印《湖南丛书》、胡思敬编刻《豫章丛书》、广东丛书编印委员会编印《广东丛书》、琼州海南书局排印《海南丛书》、贵阳任何澄等编印《黔南丛书》、云南丛书处赵藩等编刻《云南丛书》等等,都是一省文化之标志。下至地区一级文献丛书,也不乏闻名于世的,其典型事例为民国年间上海暨南大学校长张寿镛个人出资编刻的宁波地方文献丛书《四明丛书》,久已被学术界视为善本。其馀如丁丙编刻《武林先哲遗书》、盛宣怀编刻《常州先哲遗书》等都享有盛名。可是,山东作为一个文化大省从没有像其他几个省份那样,编印出足以标志山东文化的“山东丛书”,这是一个重大遗憾,也是我们当代山东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根据山东大学教授王绍曾先生主编的《山东文献书目》、沙嘉孙先生编著的《山东文献书目续编》,从先秦到近代,山东历史上产生的著述在一万种以上,数量庞大,在此基础上选编一部超过其他各省的山东地方文献丛书,是具备优越条件的。作为山东省第一学府素以文史研究闻名于世的山东大学,理应承担起这一重任。二○○五年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王学典院长、杜泽逊教授提出编纂《山东文献集成》的计划,经山东大学领导上报山东省人民政府,由韩寓群省长特批立项,成为山东省政府重大文化工程。二○○五年底开始筹备,二○○六年初正式启动。《山东文献集成》由韩寓群省长任主编,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朱正昌、校长展涛等任副主编。编纂处设在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王学典任编纂处主任,杜泽逊任副主任。全书初步计划搜集山东先贤著述一千种,主要收入流传未广而又价值较高的稿本、钞本、刻本等,影印出版。外省人士所撰关於山东的重要书籍,亦酌予收入。共分四辑,精装十六开本二百册。
现在出版的是第一辑五十册,收书一百七十九种,以名家未刊稿本、钞本为主。其中经学著作有清卢见曾《读易便解》(清钞本)、清牟庭《周易注》(钞本)、清张尔岐《书经直解》(清钞本)、清牛运震《尚书评注》(清钞本)、清宋书升《尚书考》(稿本)、清王守训《诗毛传补证》(稿本)、《春秋地理补考》(稿本)。语言文字学著作有清王维言《方言释义》(稿本)、清时庸劢《单县时氏音学遗著》三十八种六十二卷(稿本)。金石学著作有清刘喜海《古泉苑》一百卷(清稿本)、清翁树培撰、刘喜海补注《古泉汇考》(稿本)、清许瀚《许印林先生吉金考释》(钞本)、《攀古小庐古器物铭》(钞本)、《攀古小庐甎瓦文字》(王献唐钞本)、《攀古小庐古器物铭释文初草》(稿本)、《攈古录金文考释》(王献唐钞本)等。史部著作有清李文藻《恩平程记》(稿本)、《长途备忘录》(稿本)、清杨以增撰、杨绍和辑《杨端勤公奏疏》(清稿本)等。集部有清高凤翰《南阜山人诗集类稿》、《斅文存稿》(清刘喜海藏精钞本)、清孔广栻辑《海岱人文》三十三种(稿本)、清蒲松龄《聊斋文集》(稿本十二册)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些珍贵的稿本、钞本,大都未曾刊印过,学术界难得一见。
济阳张尔岐是清初著名经学家。顾炎武曾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亭林文集广师》)对张尔岐评价很高。但张氏教授乡里,生前著述多未刊行,今影印其《书经直解》清钞本,对《书经》之诠释,深入浅出,细致入微,显示出张氏深厚的经学功力。诸城刘喜海为金石学大家,久负盛名,其《古泉苑》一百卷,系清稿本。又大兴翁树培《古泉汇考》,从未刊行,刘喜海在书眉作了详细批注考释,是计划刊印而未成的原稿本,书中还保存了著名金石学家利津李佐贤、福山王懿荣的手批,更加珍贵。王献唐先生曾说:“大兴翁氏《古泉汇考》与刘氏《古泉苑》、李氏《古泉汇》并为泉学钜制,李书已刻行,此与《泉苑》迄未付梓,学者以不见为憾。”(《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续编古泉汇考跋》)刘氏《古泉苑》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翁著刘批的《古泉汇考》原件保存于山东省图书馆,今将二书一并影印,可谓中国古钱币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于不为人知的音韵学大家时庸劢,生活于同治至光绪前期,曾是著名金石学家吴式芬的门人,用一生心血著成音韵学专著三十八种,对清代音韵学家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等人的成就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提出独到的古音体系。对诸家文字的归部,进行了细致讨论,涉及古文字学、训诂学等领域,多有创获。王献唐先生认为:“他的功力和新颖见解,在清代二百六十年内,具有山东全省的代表性,同时也有全国的代表性。”但时氏音学遗著沉埋一百多年,几乎不为人知,此次全部影印问世,将为研究中国音韵学提供一大批崭新的文献资料,也为我们全面认识有清一代的音韵学成就提供更为广泛的可靠依据。日照许瀚为清中叶著名金石学家、文字学家和校勘学家,龚自珍《己亥杂诗》称赞他“北方学者君第一”,有“北方顾千里”之誉。但一生潦倒,著述多未刊行。王献唐先生作为日照後学,曾努力搜访借钞,在一九三一年前後集为《许印林遗书》,计二十一种,一大函。在七十馀年後,我们予以影印问世,实现了老一代文献学家的宿愿。
历城马国翰终生从事辑佚之学,成《玉函山房辑佚书》六百零三种七百二十九卷。著名文献学家王重民先生说:“清代辑佚,我推先生为第一家。”(《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绝非过誉。这部辑佚大书在道光间由马国翰陆续刊版,直至他咸丰七年去世,尚未最终完成。同治十年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期间,从马国翰女婿章丘李氏家借得书版,由泺源书院山长匡源等修补整理刷印,即济南皇华馆书局印本,这部书才流传稍广。近年来有出版社影印《玉函山房辑佚书》,根据的是南方重刻本,效果不佳,往往有漫漶不清之处。此次重印有三个优点:一是采用马国翰的初刻本,当然优于南方重刻本。二是印本清朗。我们用山东省图书馆藏济南皇华馆白纸印本重新扫描,缩为上下栏十六开本,清晰度大大胜于以往影印本。三是附有光绪十五年章丘李氏所刻《玉函山房辑佚书续补》十一种十四卷、《目耕帖续补》二卷,以及光绪间蒋式瑆撰辑《玉函山房手稿存目》一卷、《玉函山房辑佚书书後》三篇。这都是南方重刻本所没有的,却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次影印本可说是清代第一辑佚大书《玉函山房辑佚书》迄今最完整的本子。
《山东通志》二百十一卷,创修於光绪十六年,经山东巡抚张曜、杨士骧等前後苦心经营,耗费著名学者孙葆田半生心血,集数十位晚清学者的智慧,历时二十年始告修成,而完成时间恰为宣统三年。在各省通志中,这样完整系统地记载上古至清末一省地理、历史的,实在不多见。同为文化大省的江苏、浙江,也都没能在清末民初这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修成他们的通志,因此宣统《山东通志》弥足珍贵。商务印书馆曾在民国间缩小拼版影印为三十二开本,上海在近年又翻印商务本,版小字密,小注几不可识。鉴于该书有重大学术价值,我们改用山东通志刊印局初印本重新扫描影印,完全解决了清晰度问题,为读者提供了更好的读本。
对山东文献的系统搜集整理工作,前人早已开始。以诗歌而论,乾隆间卢见曾辑刻《国朝山左诗钞》六十卷,收入清初山东诗人六百二十馀家的诗作,同时宋弼辑《山左明诗钞》三十五卷,乾隆三十六年李文藻刻印,收明代山东诗人四百三十一家的诗作。嘉庆间张鹏展辑刻《国朝山左诗续钞》三十二卷《补钞》四卷,上继卢氏,收山东诗人七百四十七家的诗作。道光间余正酉又辑刻《国朝山左诗汇钞後集》三十九卷,收入山东诗人三百八十九家的诗作。合计以上四种,共得近五百年间山东诗人二千一百八十七家,每人都系有小传。其中绝大部分人物没有别集传世,其姓名亦不见经传,因此这四种前後蝉联的地方诗歌总集,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对研究山东古代文学史、古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史,都堪称资料渊薮。此次将四种总集配齐影印,有着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
在调查搜集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著述,尽管曾经印行,但流传仍十分稀少。例如莱阳姜埰、姜垓兄弟,在明末清初都有重要影响。姜埰《敬亭集》有光绪十五年山东官书局刻本,尚不难得。其弟姜垓在崇祯间曾建言除掉题名碑上奸臣阮大铖的名字,南明弘光间阮大铖得势,欲杀姜垓,垓乃变易姓名,逃到宁波,明亡後隐居苏州。姜垓的集子《流览堂残稿》六卷,经其後人四处搜集,于宣统二年由莱阳通兴石印馆石印。这个普普通通的石印本,十分罕见,网罗晚明文献最完备的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大型书目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专门书目《山东文献书目》等,均未记载这个本子。《清人别集总目》虽然著录了该书,但唯一的收藏者是山东省图书馆。我们这次就是用山东省图书馆藏宣统二年莱阳石印本影印的,这不仅有利于该集的利用,同时也有利于该集的保存。值得指出的是,该书有王懿荣在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作的序言,三个月後八国联军进北京,王氏就以身殉国了。这篇序言《王懿荣集》没有收录,其子王崇焕作的《王文敏公年谱》也只字未提。该序对研究王懿荣显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我们的编纂工作包括调查搜集、版本鉴别与遴选、书名卷数之核定、作者及其籍贯之确认等等。对于前人的错误,我们尽可能作了订正。例如山东省博物馆藏《海岱人文》稿本,收入曲阜颜氏的诗文集三十三种,大部分传世稀少。该书的编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定为清代王懿荣。但我们从这部书上未曾发现王懿荣任何痕迹,既无序跋批校,亦无印鉴。同时我们发现,大部分集子有微波榭主人亲笔补写的详细目录,并留下了题记。如:《水明楼诗》补目末:“乾隆乙卯(六十年)正月廿四丁未微波榭钞,是日天阴有风。”《江干幼客诗集》目下:“乾隆癸丑(五十八年)冬十月十四日甲戌颜运生崇规学博所贻,一斋记。”同上补目下:“嘉庆三年戊午冬十二月廿四日癸丑午刻微波榭晴牕录。”考“微波榭”是曲阜孔继涵堂号,但孔继涵已于乾隆四十九年去世,这些题记显然是孔继涵之子所作。又考“一斋”为孔继涵长子孔广栻的号,题记中最晚的一条是嘉庆三年十二月廿四日,而孔广栻嘉庆四年去世。从《祇芳园诗》补目下的题记,我们可以了解到嘉庆三年冬孔广栻已有病在身。该题记云:“嘉庆三年戊午腊月廿二辛亥录。是日招诸弟与颜思诚饮,予以疾不陪。”孔广栻在去世前犹抱病为这批文献钞补目录,作必要的编纂工作,他的精神对我们也具有很大的感染。顺着这一思路,我们查阅了王献唐先生题跋,发现两条有关的记载:一是《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续编十子诗略跋》:“此《十子诗略》之一,护叶後面十子名次及《乐圃集目》、集中批点,皆曲阜孔伯诚广栻先生手笔。……身後遗藏,十年前多为北平翰文斋购去。先後凡见四十馀种,其《微波榭遗书》、《通德遗书所见录》、孔氏说经稿底本,由余作介,仍归衍圣公家,馀则多为山东图书馆购藏。内以曲阜孔、颜各家诗文集钞本为多,类经伯诚先生订定编录,朱墨烂然,似当时欲编集付梓者。”二是《双行精舍书跋辑存藤梧馆金石题咏集录跋》:“右书为曲阜孔伯诚先生集录。……藤梧馆为先生书室,所著诗文均以是名署之,前见《海岱人文》先生集钞各书,板心多有藤梧馆三字。”从这两条跋文,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这部《海岱人文》是孔广栻所辑。过去定为王懿荣辑,是错误的。那么,这一错误是为何发生的呢?考《王文敏公年谱》,光绪十七年云:“公自本年始搜集《海岱人文》,九月,撰《海岱人文序》。”天津图书馆藏有王懿荣《海岱人文册目》稿本二册,经向该馆专家请教,系王懿荣所藏山东人书札、诗牋、闲帖等文献的目录。王懿荣收藏的山东人书札等文献,装裱成册子,题名《海岱人文》,所以这两本目录题作《海岱人文册目》。《册目》前有王懿荣自序,亦未提及孔广栻的《海岱人文》。可见王氏所辑《海岱人文》与孔广栻辑《海岱人文》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只是书名相同而已。前人误定孔广栻所辑《海岱人文》为王懿荣辑,当是循名失实所致。至于孔、王两书有无先後配合的关系,孔广栻辑《海岱人文》内容是否止於此,尚待进一步探讨。
在编纂《山东文献集成》过程中,我们时时感受到前人在搜集保护乡邦文献方面的苦心孤诣和卓越贡献。乾隆间德州学者宋弼,在与卢见曾合辑《国朝山左诗钞》後,又辑《山左明诗钞》,当时益都学者李文藻也参与了搜集工作。宋弼把《山左明诗钞》稿本交给卢见曾,希望卢氏刊刻行世。乾隆三十三年秋卢见曾获罪,被抄家,数十万卷藏书都堆在德州官府内。时宋弼官甘肃按察使,入觐途中死在洛阳。李文藻深恐此书就此湮没,第二年正月赶到德州,托人购买此书,花了三天时间,才从书堆中清理出该书的稿本三十五卷。可是未找到诗人小传。数日後,宋弼的灵柩从洛阳迎到德州。李文藻吊唁後,打开宋弼的行李箱,小传一册正在其中。延津剑合,盖出天意。这年秋李文藻得了广东恩平知县,就携带这部稿子南下广东。次年夏到任,入冬即着手校刻,使这部包括四百三十一人诗作的山东文献得以问世。
至于王献唐先生,几乎用一生心血搜集、保护、研究山东文献,他在古代史、金石文字、版本目录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愧一代宗师。抗日战争爆发,王献唐与屈万里、李义贵携带山东图书馆善本、文物,历尽千辛万苦,向後方迁徙,因资金匮乏,甚至讨饭,而所有图书文物丝毫无损。途经万里,时逾十载,一九五○年冬这批珍贵文献终于从四川运回山东,後来入藏山东省博物馆。其中山东先贤遗著稿本、钞本,未经刊行的,数量可观。我们这次影印的不少文献,就是王献唐先生带到四川又运回山东的,许多书上都留下了献唐先生的题跋,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山东文献的重要向导。在国破家亡,战火联绵的年代,王献唐先生辑印《山左先喆遗书》的计划难以实现。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受到高度重视的今天,我们有条件把这些珍贵文献影印出版。可是,如果没有前辈们的薪火传灯,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也无法创造出这些文献。前人对于我们是这样,我们对于後人也应该是这样。保护和传承文献,实质上就是保护和传承古老的中华文明,这才是我们编纂出版《山东文献集成》的初衷。
《山东文献集成》的编纂出版工作,得到山东省政府的关怀和支持,还得到山东大学、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师范大学、济南市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负责编纂工作,山东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工作,江苏金坛古籍印刷厂负责印刷工作,有关人员都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山东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
二○○六年十二月十日
本文2023-08-05 04:52:14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179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