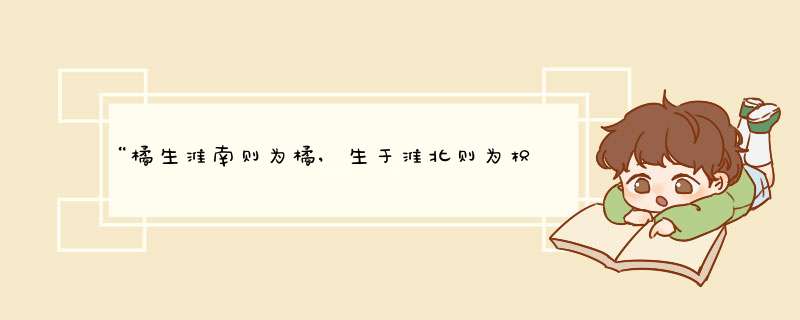在《楚辞》中屈原的主要作品都有哪些?

“楚辞”是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它受《诗经》的某些影响,同它有直接血缘关系的,是南方土生土长的歌谣。以前楚地歌谣仅一鳞半爪地存于历史记载中,直到战国中期,屈原等人的一系列作品出现在楚国文坛之后,“楚辞”才成为一种文学样式。汉代起,“楚辞”成为屈原等人作品的总集名。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其他人的作品未能流传下来。屈原的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
《楚辞》书影
有一些学者认为历史上没有屈原这个人。因为在先秦的古籍中找不到屈原。现在我们看到的作品,最早提到屈原的是西汉时贾谊的《吊屈原赋》,然后就是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是有屈原这个人的,不然像《离骚》这样伟大的作品是怎么产生的。可能是由于屈原生活在楚国,跟其他诸子生活的地方不一样,又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所以在先秦的古籍中找不到屈原。
在汉代以原道宗经为纲领的区别批评中对屈原持负面态度的批评家是谁
一、屈原是否真有其人的学术争议
《短史记》以前的文章,曾就“屈原是否真实存在”这个问题的学术争议,做过介绍。质疑者的主要论据,扼要来说包括如下三点:
(1)现存先秦诸子百家著作及《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典籍中,完全找不到“屈原”这个名字。今天所见有关屈原的史料,几乎全部出自《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而司马迁似乎也并未掌握多少有关屈原的确凿史料。比如,作为一篇传记,按常理有必要介绍一下传主的籍贯与家世,司马迁却只能以一句笼统的“楚之同姓”权做交待,可见他对屈原的家世几乎没有了解。汉文帝时代的贾谊写过《吊屈原赋》,经历了文帝、景帝和武帝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写过《离骚传》(已失传),这些司马迁参考过的材料,同样不能就屈原的籍贯与家世提供确切的说法。
(2)今天所见《屈贾列传》已非司马迁的原始版本。列传中记载了贾谊之孙贾嘉“至孝昭时,列为九卿”。司马迁没有活到贾嘉官至九卿的年份,也无法未卜先知汉昭帝的谥号是“孝昭”。显然,在司马迁之后,有人对《屈贾列传》进行了补写或增删。
(3)《列传》中有些情节似存矛盾。比如先说楚怀王“怒而疏屈平”,继而又说“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齐国是大国,对齐关系是楚国需要重点经营的政治事务。这种事,似不宜交给一个已被疏远的边缘人去负责。齐国不会开心与一个楚国政坛的边缘人接洽,会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楚王也不会放心让一个失宠之人居于外交要津,天知道他会不会乘机挟怨报复,至少也会担心他会不会尽职尽责。在并无其他史料可以佐证存在“屈原使齐”之事的情况下,传记中这种似存矛盾的记载,就显出了它的可疑。
图:《三才图会》里的屈原像
晚清学者廖平,是近代最早对“屈原的真实存在”提出质疑的学者。按他的考证,《离骚》是方士们为秦始皇所写的“仙真人诗”,目的是满足始皇长寿、成仙的想象。廖平之后,胡适从思想史方面入手,指出屈原即使真有其人,也不会生在秦汉以前,理由是屈原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会发生的”,战国时代不会存在屈原那种“奇怪的君臣观念”,是“汉朝的老学究”们塑造了屈原这样“一个理想的忠臣”。
徐复观的研究则认为,司马迁为屈原做传,所依据的核心材料之一,是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而《离骚传》又是刘安写给汉武帝看的。刘安写《离骚传》的目的,“是借屈原之冤,以明自己之志”,具体来说就是婉转地向汉武帝传达信息,说自己忠心耿耿犹如屈原,绝无谋反之意,以求改善被朝廷疑忌、监视、打压的艰难处境。若朝廷不能体察这种忠诚,那自己就只好学屈原去自沉了。正所谓“不仅是表白屈原,亦实际上是表明他自己”。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有学者推测认为《离骚》的原作者其实就是淮南王刘安。也有人推测认为,屈原其实是贾谊伪造的历史人物——贾谊忠于汉文帝,为其擘画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弱诸侯王的妙策(也就是后来汉武帝搞的“推恩令”),结果却因为与文帝的宠臣邓通不和,“数廷讥之”,多次在公开场合讽刺邓通,招致文帝的不满,“由是疏远,迁为长沙太傅”,被从长安中央下放至偏远的长沙国去做太傅。贾谊的这些人生经历,与屈原故事中的情节——忠于楚怀王、有政治能力(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被怀王寄予重任、遭怀王身边宠臣进谗言而被疏远、下放至偏远地区为官——可以说是高度吻合。
附带一提:写过《吊屈原赋》的贾谊,后来又做了梁王的太傅。梁王坠马而死后,贾谊自责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哭泣岁余,亦死”。这位从马上掉下来摔死的梁王,谥号正是“梁怀王”。长沙王+梁怀王,似可与屈原故事里的“楚怀王”构成呼应;贾谊的哭泣而死,亦可与屈原故事里的怀石沉江构成呼应。考虑到上述种种,司马迁将屈原与贾谊并入同一列传当中,这种处理显然有着一种意味深长的用心。
总而言之,“屈原”究竟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目前仍是一桩未解的学术疑案。疑案的源头,在于先秦典籍中找不到屈原的相关记载,以及《史记》中的屈原传记存在许多可疑之处。也就是说,自一开始,关于屈原的事迹,就缺乏一个拥有可信度的传世文本。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2017年投入使用的最新版初中历史教课书七年级(上册)已不再收录屈原的相关内容——使用至2015年的旧人教版教材第八了《中华文化的勃兴(一)》中,曾用了较大的篇幅来介绍屈原(如下图)。与之一同从教材中消失的历史人物,还有真实性同样存疑的扁鹊。当然,最新版的初中语文教材中,仍保留着与屈原相关的内容。
图:旧教材关于屈原的描述
二、古人对屈原的所谓“批评”
与近现代学者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屈原这个人”不同,古人围绕屈原的主要争议,是这个人的作为究竟值不值得效仿。
贾谊要借屈原自伤身世,刘安要借屈原向汉武帝表忠心,自然都对屈原持肯定立场,刘安甚至说他“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有借屈原讽刺汉武帝的用意,所以行文中也始终对屈原怀抱着同情、赞赏与惋惜。
西汉末年的大文豪扬雄,首开批评屈原的先河。他虽然喜欢《离骚》,也赞赏屈原的人格,却不能同意他的自杀。他写了一篇《反离骚》批评屈原,说他非要在楚国这一棵树上吊死,实在是不值得。楚国既然不肯重用你,不肯听你的逆耳忠言,你就该学学孔夫子,像他那样离开乌七八糟的鲁国,去更广阔的天地里发展,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嘛,何必固执地呆在楚国呢?何必将自己的性命交给湘水的浪涛呢?
扬雄的这种意见,与西汉中晚期知识界反对忠于一家一姓的思想潮流,有直接关系。汉宣帝时代,名儒盖宽饶曾站出来给皇帝上书,公然指责“圣道陵迟”,警告汉宣帝要行仁政,否则“天命”是要转到别家去的。汉成帝时,又有名儒谷永站出来,公开对皇帝说天意从来不会只眷顾一家一姓,警告汉成帝要早点改弦更张,放弃恶政。王莽后来毫无舆论阻力、以禅让的形式取代西汉建立新朝,正是这种思想潮流发展到极致的结果。扬雄本人也实践了他对屈原的批评——他欢迎新莽,对刘汉王朝没有“忠君”层面的留恋。
进入东汉后,又有《汉书》的作者班固站出来,写了一篇《离骚序》,公开批评屈原。班固说,刘安对屈原的赞美,讲什么屈原可以与日月争光,可谓“似过其真”,实在是名不副实。那屈原,实际上是这样一个人: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清絜狂狷景行之士。”
意思是:那屈原为了显露自己的才华、炫耀自己的名声,常年与那些危害国家的小人相争,打口水官司,自然是要遭遇谗言的。他还经常责备楚怀王,成天怨恨怀王身边的佞臣,最后闹了一个沉江自杀的结局,实在算不上是一个清洁之人、狂狷之人、景行之人(清洁指的是品行好;狂指做事激进,狷指做事保守;景行,光明正大之意)。
图:《晩笑堂竹荘画传》班固像
班固如此批评屈原,实出于一种“时代需要”。他早年与东平王刘苍(曾以骠骑将军身份在朝辅政)交往,论及屈原时,说的是“屈子之篇,万世归善”,且希望刘苍能够折节下问,多听谏言,让天底下再无“汨罗之恨”。那时候,班固年约二十,正畅想着能被人赏识,进而在政坛上有一番作为。写文章批评屈原时,班固已入中年,已是皇帝的亲近之人,史称他入宫给皇帝读书,常常“连日续夜”;皇帝有巡狩之事,让班固“献上赋颂”已是常规操作;朝中有大事要讨论,也常被皇帝指定站出来与公卿们辩论。
更要紧的是,汉明帝、汉章帝父子,一点都不喜欢屈原、贾谊与司马迁这类人。汉明帝曾亲口对班固说,他很不满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却因为受刑的缘故,在《史记》里说汉武帝的坏话;也很不满司马迁在《史记》里借贾谊之口将秦王朝的灭亡归因为“仁义不施”,而非君权神授合该轮到刘家人做皇帝。总之,司马迁这类人“非谊士也”,不是好人。汉明帝心目中理想的忠臣,是司马相如。他对班固说,这个人虽然也不太得志,但从不对皇帝发怨言,临终的时候还在文章里“颂述功德,言封禅事”,还在歌颂汉武帝的丰功伟绩,实在是“忠臣效也”——是忠臣的典范,“贤迁远矣”——比司马迁那家伙强多了。
明、章两帝的时代,是一个“法宪颇峻”、人人战战兢兢的时代。北海敬王刘睦,本是个性情谦恭、爱好学问、喜欢与知识分子交朋友的人。因为害怕“敬贤乐士”的名声被皇帝知道,他只好将大门关起来谢绝宾客,将精力全部投入到狗马音乐之中。深知皇帝厌恶读书人博取名声的班固,也非常自觉地选择将“不以才高人”(不在人前人后突出自己的才能)作为自己的处世之道。他批评屈原不该露才扬己,不该责备楚怀王,是因为皇帝不喜欢屈原露才扬己,不喜欢屈原责备楚怀王。
在《楚辞》中屈原的主要作品都有哪些?
本文2023-10-29 13:30:19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1806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