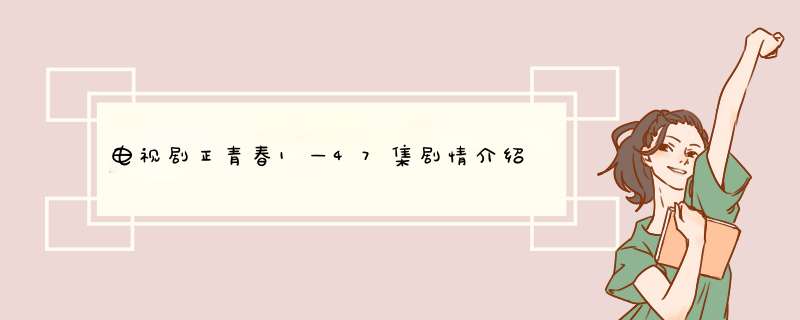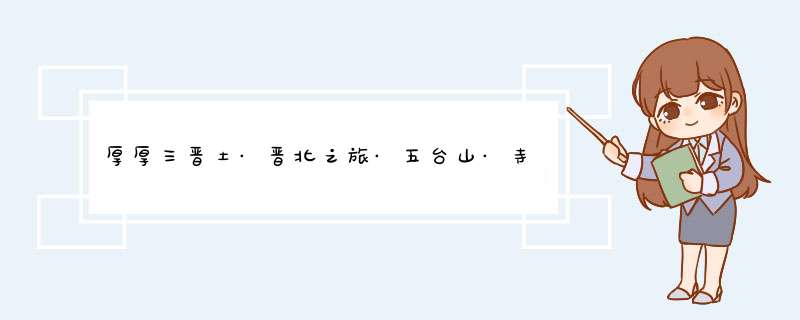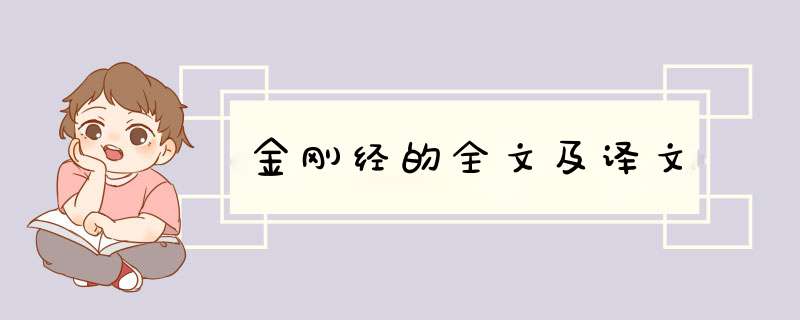花间词派代表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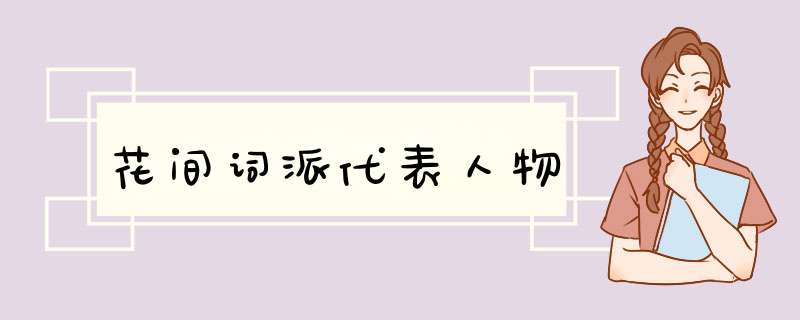
花间词派代表人物
温庭筠、和凝、韦庄、毛文锡、牛希济、顾敻、鹿虔扆、阎选、尹鹗、李珣等。花间词派产生于晚唐五代时期的前蜀,是中国古代诗词学流派之一,其名得自于后蜀赵崇祚所编词集《花间集》。其作者大多是蜀人,词风近似,词作内容多为歌咏旅愁闺怨、合欢离恨,局限于男女燕婉之私,因此被称为“花间词派”。
花间词派的人物简介
温庭筠
温庭筠,原名岐,字飞卿,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唐代诗人、词人。温庭筠精通音律,诗词兼工。诗与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其诗辞藻华丽,秾艳精致,内容多写闺情。
其词更是刻意求精,注重文采和声情,成就在晚唐诸人之上,为“花间派”首要词人,被尊为“花间派”之鼻祖,对词的发展影响很大。在词史上,与韦庄齐名,并称“温韦”。文笔与李商隐、段成式齐名,三人都排行十六,故合称“三十六体”。
和凝
和凝(898年—955年),字成绩,郓州须昌(今山东省东平县)人。五代十国时期宰相、文学家、法医学家。和凝于后梁贞明三年(917年)登进士第,进入宣义军节度使贺瑰幕府,后又在郓、邓、洋三州幕府任从事。
后唐明宗天成年间调入中央任职,此后历仕后唐、后晋、辽、后汉、后周等朝,在后晋时担任过六年宰相(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受封鲁国公,最终官至太子太傅,于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追赠侍中。
韦庄
韦庄(约公元836年-公元910年),字端己。京兆郡杜陵县(今陕西西安)人,晚唐诗人、词人,五代时前蜀宰相。文昌右相韦待价七世孙、苏州刺史韦应物四世孙。韦庄工诗,其律诗圆稳整赡、音调浏亮,绝句情致深婉、包蕴丰厚;其词善用白描手法,词风清丽。与温庭筠同为“花间派”代表作家,并称“温韦”。
毛文锡
毛文锡,字平珪,高阳(今属河北)人,一作南阳(今属河南)人,五代前蜀后蜀时期大臣、词人。十四岁进士及第。事前蜀高祖王建,官翰林学士承旨。前蜀永平四年(915年),迁礼部尚书,判枢密院事。期间成功劝阻王建乘长江涨水,决堰水灌高季昌盘踞之地江陵的想法。前蜀通正元年(916年),进文思殿大学士,拜司徒,仍判枢密院。
前蜀天汉年间(917年),因与宰相张格、宦官唐文扆争权,贬茂州(今四川松潘)司马,子员外郎毛询流放维州(今四川理县)。前蜀亡,归后唐。不久,又事后蜀。与欧阳炯等五人以小词为后蜀君主所赞赏。
牛希济
牛希济,陇西(今甘肃)人。词人牛峤之侄。早年即有文名,遇丧乱,流寓于蜀,依峤而居。后为前蜀主王建所赏识,任起居郎。前蜀后主王衍时,累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随前蜀主降于后唐,明宗时拜雍州节度副使。
顾敻
顾敻(xiong),五代词人。生卒年、籍贯及字号均不详。前蜀王建通正(916)时,以小臣给事内廷,见秃鹫翔摩诃池上,作诗刺之,几遭不测之祸。后擢茂州刺史。入后蜀,累官至太尉。顾夐能诗善词。《花间集》收其词55首,全部写男女艳情。
鹿虔扆
鹿虔扆(yǐ)五代词人,生卒年、籍贯、字号均不详。早年读书古诗,看到画壁有周公辅成王图,即以此立志。后蜀进士。累官学士,广政间(约938~950)曾任永泰军节度使、进检校太尉、加太保,人称鹿太保。与欧阳炯、韩琮、阎选、毛文锡等俱以工小词供奉后主孟昶,忌者号之为“五鬼”。
阎选
阎选,生卒和字里不详,五代时期后蜀的布衣,工小词。与欧阳烔、鹿虔扆、毛文锡、韩琮被时人称为“五鬼”,世传有八首小词被唐人赵崇祚收入《花间集》。
尹鹗
尹鹗(约公元896年前后在世)字不详,成都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昭宗乾宁中前后在世。事前蜀后主王衍,为翰林校书。累官至参卿。花间集称尹参卿,性滑稽,工诗词,与李珣友善,作风与柳永相近,今存十七首。词存《花间集》、《尊前集》中。今有王国维辑《尹参卿词》一卷。
李珣
李珣(855-930),晚唐词人。字德润,其祖先为波斯人。居家梓州(四川省三台)。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昭宗乾宁中前后在世。
花间词派人物的个人作品
温庭筠
五言古诗:烧歌、边笳曲、嘲春风、湘宫人歌、侠客行、故城曲、西洲曲、黄昙子歌。
七言古诗:莲浦谣、堂堂曲、塞寒行、汉皇迎春词、舞衣曲、拂舞词、懊恼曲、春江花月夜词等。
杂言古诗:罩鱼歌、春野行、苏小小歌、会昌丙寅丰岁歌。
五言绝句:碧磵驿晓思、地肺山春日、题贺知章故居叠韵作、光风亭夜宴妓有醉殴者。
七言绝句:莲花、蔡中郎坟、咸阳值雨、夏中病痁作、赠少年、夜看牡丹、杨柳八首、题李相公敕赐锦屏风等。
五言律诗:芙蓉、商山早行、敕勒歌塞北、题造微禅师院、咏晓、西游书怀、初秋寄友人、送渤海王子归本国等。
六言律诗:送李亿东归。
七言律诗:南湖、苏武庙、寒食日作、题李卫公诗二首、题柳、开圣寺、和友人悼亡、自有扈至京师已后朱樱之期等。
和凝
诗:《宫词百首》、《题鹰猎兔画》、《醴泉院》、《兴势观》、《洋川》等。
词:《渔父》、《解红》、《柳枝》三首、《天仙子》二首、《江城子》五首、《何满子》二首、《望梅花》、《薄命女》、《春光好》二首、《抛球乐》等。
文:《请置医学奏》、《请减明法科选限奏》、《补奏斋郎奏》、《请放榜后贡举官晚出奏》、《立四庙议》、《大晋故天下兵马都元帅守尚书令吴越国王谥文穆钱公神道碑并序》。
韦庄
诗:《金陵图》、《忆昔》、《送日本国僧敬龙归》、《章台夜思》、《台城》、《登汉高庙闲眺》、《题裴端公郊居》、《杂体联锦》、《赠渔翁》、《春愁》、《寄湖州舍弟》、《和郑拾遗秋日感事一百韵》、《李氏小池亭十二韵》等。
词:《菩萨蛮五首》(《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菩萨蛮·洛阳城里春光好》、《菩萨蛮·红楼别夜堪惆怅》、《菩萨蛮·如今却忆江南乐》、《菩萨蛮·劝君今夜须沉醉》)《江城子·恩重娇多情易伤》、《诉衷情·烛烬香残帘半卷》等。
牛希济
《临江仙》、《酒泉子》、《中兴乐》、《谒金门》、《生查子》。
顾敻
《虞美人》、《河传》、《诉衷情》、《醉公子贰首》、《荷叶杯》、《献衷心》。
鹿虔扆
《女冠子》、《虞美人》、《思越人》、《临江仙》。
阎选
《虞美人》、《临江仙》、《浣溪沙》、《八拍蛮》、《河传》、《谒金门》、《定风波》。
尹鹗
《菩萨蛮》、《秋夜月》、《何满子》、《满宫花》、《江城子》、《醉公子》、《女冠子》、《杏园芳》、《清平乐》。
李珣
李珣词现存54首,《花间集》录37首,《尊前集》录18首,其中1首《西溪子》重复。其词调可分为《渔父》、《南乡子》、《西溪子》、《女冠子》、《中兴乐》、《酒泉子》、《浣溪沙》、《巫山一段云》、《菩萨蛮》、《渔歌子》、《望远行》、《河传》、《虞美人》、《临江仙》、《定风波》等,计15种。值得注意的是,南宋王灼《碧鸡漫志》还记载了李珣以5种词调创作的另外5首词作。
花间词的艺术特点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李泽厚先生指出:“盛唐以其对事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势:中唐是退缩和萧瑟。晚唐则以其对日常生活的兴致,而向词过渡。这并非神秘的气运,而正是社会时代的变异发展所使然。”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动摇了唐王朝的执政根基,继之而出现的政治腐朽、社会颓败,使文人志士的精神追求发生根本性变化。面对着衰乱的时世,人们在忧患中失望。在无奈中麻木,在躁动中挣扎。文学的字里行间体现出社会需要的熨贴与慰藉,从而使浮躁、空虚的形态得到些滋润和平衡。于是,生活类、消遣类、调侃类作品应运而生。另外,生产力的局部发展和阶段性发展,使得富有阶层追求世俗享乐的意识迅速膨胀,呈现出回光反照似的歌舞升平,并且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花间词的诞生便是这种社会形态的反映。
花间词的编者是古代后蜀的赵崇祚,共收集18个词人的500首词。18人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等三人之外,都是五代西蜀的文人。分析这种现象可以看出,巴蜀人文环境对花间词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天府之国”衣食无忧,生活富足,为”安逸”文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加之因战乱而导致西进的文人雅士及时行乐的心理,助长了欢愉情绪和纵情声色,表露出文人士大夫的末世情结。应该说,西进的这种排遣心理与西蜀君臣的,虽封闭而惶恐的心理是不谋而合的。于是形成了特殊地域、特殊人群审美感受的特殊性,并且引发了天马行空的奇情异想。其实,特殊来特殊去,最深层的特殊是人们对儒家学说的深刻反思,而且反思成果又及时地与那些浪漫个性结合,并聚焦、凸现于花间词这一富有灵性的艺术活体中。
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文学创作方式提出了适应性要求。爱情作为一个永恒的话题,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都不断地述说着。近体诗发展到晚唐李商隐时,在摹写真挚的闺情,捕捉细腻的心绪等方面代表了唐代爱情诗歌的最高成就。但是与人们感情的丰富性及复杂程度相比,几乎显得捉襟见肘。它四平八稳、整齐划一的体制形态,难以扣合波澜起伏的内心情感:“发乎情,止乎礼”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规范,也束缚着绮情艳思的自然流露。因而必定要寻找一种能够补充诗教不足,更加自由地传达心曲的文学载体。对此,首先还是像温庭筠这样的一些诗人反映最敏感,他们采用了长短句这种富有新鲜活力的文体形式,打破近体诗整齐、单一的格局,使作品具备灵巧多变、音律和谐的特质,契合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
花间词是时代的产物,因此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第一,作者单一,主要来自于诗人和文人,都是男性。《花间集》18名作者基本上都是文人和诗人,500首歌辞中没有一个女性的作品,这与敦煌曲形成鲜明对照。敦煌曲的内容十分广泛,生活当中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填写一首词,大夫看病,为了便于记诵,比如当时针对伤寒病的症状写成了多首《定风波》。由此可知,敦煌曲的作者大都是市井之间的,将军、战士、郎中、乐工、算卦的,还有宫廷的歌女和社会上的歌妓等等。《花间集》的内容典雅、美丽,一般都是在春怨秋恨中反映悠闲的生活情调,文人悠哉游哉的作词,歌妓轻松自在的咏唱,词人的创作成果一般是都切换成娱乐的工具。当时词的功能就是用来咏唱,在咏唱中、在舞蹈中、在饮酒中欣赏。
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处境所致,《花间集》的内容有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因此从宋代陆游开始,就认为《花间集》的作者太无聊。陆游曾经说过,天下岌岌可危,生民救死不暇,老百姓在生死线上挣扎,很痛苦,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总体而言,花间词的内容比较艳丽,缺乏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感情,几乎完全是一种享乐的生活。所以陆游说他放纵、放浪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唐宋词的发展,《花间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第二,花间词对词的形式进行了比较严整的规范。规范是相对早期的敦煌曲子词而言的。在敦煌曲子词中,不仅有衬字、字数不定、平仄不和、叶韵不定,而且在同属一调中句法也有较大出入。花间词对此进行了规范,规范的意义在于它一直影响着后来词曲的发展。在创作形式方面,花间词基本格调是代言体。温庭筠和韦庄是花间词的两个代表性人物,除韦庄少量作品直抒胸臆外,他们基本都是代言体风格,其他作者也都不同程度地效仿着这种创作方式。审视《花间集》这个群体的创作方式,他们一般都以怨妇思妇为抒情主人公,把内容统一在男女悲欢离合上。敦煌曲子词则与此不同,方式粗糙随便,内容无所不包,什么边客游子的呻吟,忠臣义士的壮语,隐者的怡情悦志,学子的热望失望,佛家的赞颂,医者的歌诀等等无不入词。
第三,花间词艳丽、婉约,带有非常强烈的女性化特点。这种风格,和文学创作一样,鲜活亲切,栩栩如生,如临其境。这种风格对后来词曲写作有非常大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范式。大家在写词的时候,自然不自然地就会把它当作一种标准,要写成像花间词那样才是词,形成了一种词文化的观念。这个观念一直到苏东坡之前,可以说没有改变过。作品注重描写人的思想,刻画人物的性格,抒发人的感情,尤其善于捕捉人的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花间词由于多采用于代言体,因此暗示的手法表现得十分突出,这也是花间词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理解花间词的特点,离不开加深对温庭筠风格的认识。认识温庭筠风格,也是对花间词特点的再理解。温庭筠堪称花间词鼻祖,其风格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作品题材的女性化。我们在分析花间词的特点时,曾把代言体作为花间词的一个重要特点看待,其实这个代言体在词中的知识产权,可以说是属于温庭筠的,并且在文学史上发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所谓代言体,就是男性作者站在女性的立场,运用女性心理,抒发女性的情感。反过来说,也是用女性情感掩盖遮蔽男性作者的内心世界。作品题材女性化的萌芽在《诗经》、汉赋、唐诗中已有端倪,但真正称得上女性化的,当属《花间集》,尤其《花间集》的骨干作者或称祖师爷的温庭筠。题材女性化曾受到很多后人的批评,尤其清代人,批评代言体是男子而做闺音。因为温庭筠的词写得都是一些女性的生活、容貌,而且比较香艳,比较艳丽,比较女性化,浓妆艳抹,构成了比较典型的女性化风格。然而,批评题材女性化的年代并不代表那个年代不存在作品女性化风格,《红楼梦》中的诗词,几乎无不涉及女性的生活、容貌,无不香艳艳丽就是一个证明。
二是把相思和离愁的季节锁定在春季。春天万物生发,人的情绪容易波动起伏,青春消逝的体会刻骨铭心。此时此刻的闺中思妇,孤独一人,伤春、怀春、悲春、怨春的感受异常强烈,因此而感叹时光,思念亲人、爱人、情人和友人。温庭筠往往善于编织以季节为经,以情绪为纬的词的场景,他编织的那个场景,基本上是设在春天,这是温庭筠词的很有意趣的现象。在春天这种场景中,温庭筠词的切入点一般放在黄昏、黎明或夜晚。夜晚人梦,黎明出梦,梦中难以割舍却又千万 遍重复的就是那个情字。那么季节和具体时间的设定,都是比较贴合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具体感受的。思念的人,对季节感受鲜明、强烈,对季节的变迁喜形于色、敏感甚至胆怯。温庭筠的词对春的选择与青睐是文人的浪漫之举。
三是以阐述梦境为典范性的情景。温庭筠的词,梦境奇妙,内容丰富,以梦说情、说恨、说怨,说酸甜苦辣,说悲欢离合。相思、离别从梦中来,到梦中去,言梦境以明真意,昼话夜说,真话梦语,梦境成了温庭筠的灵魂演讲大平台。梦境使词的意境朦胧迷离,也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广阔而自由的空间。同时,梦境风格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词人。比如北宋著名词人晏几道,他的词很多情景都是发生在梦里,或涉及到梦这样一个意象,明显地受到温庭筠风格的影响。
四是以一个片断的感受构成作品的抒情方法。温庭筠的词抒情方法很多,但最突出的是片断似的抒情方法,即一个片断与另一个片断似乎没有关系,每一个片断之间的关联,依靠读者的联想、推理和想象。读者在解读中,要以创新思维为纽带把片断之间连接起来,读者成了两个片断之间的补充。比如他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这是一个特写,也是一个片断。接下来“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又是一个片断。更为有趣的是,刚说完“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不想化妆,马上又说“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已经打扮得非常漂亮了。从不想化妆到精心化妆,从懒得化妆到化妆得十分得意,为什么她又是如何进行化妆的这些中间环节,温庭筠放权于读者,让你去想象、联想、推理、补充,然后把它连接起来。
下面,通过欣赏温庭筠的两首《菩萨蛮》,来更加具体真切地解读温庭筠词的风格和花间词的特点。一首《菩萨蛮》是《花间集》的第一首词:“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综合历代鉴赏资料,“小山重叠金明灭”的“小山”大概有四种指向。一、有人认为是古代的枕头,枕头上绣的图画反映的一种意象。二、有人认为是房间内的屏风,屏风上的装饰重重叠叠、明灭变幻。三、有人认为是形容女性头发的样式,发髻上面的装饰,闪闪烁烁明灭不定的感觉。四、沈从文专门研究古代女性装饰发带和衣服后提出,古代妇女发髻很高,发髻上面要插各式各样的珠子,珠子上面有的用金银装配,有的用螺纹装饰,珠子的反光,闪闪烁烁而重重叠叠。四种说法实际上是四种理解,心情不一样,理解的结果自然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很重要。“鬓云欲度香腮雪”,描述从头部到脸上,定格在两腮。脸是白的,头发是黑的,黑白形成对比,描写地细腻多情。下面写心情,“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心烦意乱,不愿意打扮,不愿意梳妆,暗示对宫廷生活的厌烦,被困在闺房当中,情绪当然不好,懒洋洋的没有一点心情。为什么不愿意打扮,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诗经》里说“自昔徂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丈夫到边关打仗去了,自己一个人呆在闺房里,头发乱蓬蓬,乱糟糟的,没有心思去梳理,为什么呢难道是没有妆品吗不是!是因为打扮了没有人看。有温庭筠的“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也是这样的心态。词写到这儿,已经很有意境了,但是词人却在这个节骨眼上设置了拐点。以上他为女主人公不愿意打扮,找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后写道:“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她不仅愿意打扮,而且打扮得极为漂亮、极为得意。“照花前后镜”是精益求精,也是自我陶醉:“花面交相映”是自我欣赏。从不愿意打扮,到仔仔细细地打扮,又是一个暗示。大概暗示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表述她过去时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表述现在时的状态,说明她丈夫现在要回来了,无论过去时还是现在时,心情都一样,思夫心切!怎么破解这个暗示呢“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女主人公换上了具有特定意义的新衣服,所谓特定是指“双双金鹧鸪”的那件衣服,暗示此一件衣服只有丈夫在家时才穿在身上的。因此,“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便是“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注解了。那么,从不愿意打扮,到仔仔细细地打扮,深层次原因也就一清二楚了。
这首《菩萨蛮》不仅是温词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且如果议及花间词的典型风格,人们也一定会以这篇为例。这首词的形象的描写,是艳丽的,给人留下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官印象,花间词特别擅长表现这样的情景。他的另一首《菩萨蛮》和上面讲的一首很相似:“水晶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所不同的是,一个在闺房内照镜、梳洗、画眉,而另一个从闺房之内到闺房之外一“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有江有河,景象辽阔,给人以无限的想象。“水晶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首先详细地刻画闺房当中的摆设,水晶帘,玻璃枕。晶莹剔透,富贵艳丽。还有绣着鸳鸯锦的被褥,为进人梦境埋下伏笔。这个鸳鸯锦的概念是很隐晦的,不明说对丈夫的思念,让读者去联想。
“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人胜,指正月初七,这天被称为人日。过去对人日很重视,像过节一样要安排很多纪念活动,比如吃七菜粥,剪纸做成图案,装饰在头上等等。“人胜参差剪”,写的就是人日的一种活动。按照古代的风俗,在人日那天,流浪的人要回家团聚,在家里面的人要盼望在外面的人这一天能够回来。女主人公的心思更是盼望与丈夫团聚,这里又有暗示,“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头的两边戴上了美丽的花朵,头上插了很多玉钗,打扮这么漂亮为什么一定是希望夫妻团圆。围绕着盼夫心情,词人对玉钗进行了慢镜头似的描写。古代玉钗的装饰是一种线状的东西,所以风吹的时候,就会颤动摇摆,表现出各种各样的造型,看看慢镜头:“玉钗头上风”。 这首词的风格也是片断型的,“水晶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这是一个画面:然后中间没有什么过渡,直接就跳到了“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又是一个片断:“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又从梦境回到了人的活动,再是一个片断:“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又成了两个非常强烈的特写镜头,聚焦在两个具体的镜头上面,而且用具体的意象来暗示急切的心情。读这类词的时候,读者必须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否则会觉得东一句西一句,不知道说的什么。这就是文人词的一个特点。
责任编辑 晓 晨
两宋词坛雅俗之辨
原文出处中国韵文学刊
原刊地名湘潭
原刊期号199601
原刊页号59-67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703
作 者聂安福
责任编辑刘庆云
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领域中,雅俗这对重要范畴源自先秦儒家乐论。《论语》中有雅乐、郑声之分,《孟子•梁惠王下》有“先王之乐”与“世俗之乐”、“今乐”与“古乐”之说。雅乐、俗乐的划分标准在于乐教,体现出儒家的文艺教化思想。孔子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荀子•乐论》则对先王制《雅》、《颂》的意图有所说明:“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是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故君子耳不听*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此三者,君子慎之。”这也就是对《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乐德”(“中和•只庸•孝友”)的发明。历代乐坛上的雅、俗之论多承袭这一传统观念。
汉魏之后,雅俗观念渐入品人谈艺之中。王充《论衡•四讳》:“夫田婴,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刘勰《文心雕龙》:“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通变》)“习有雅郑……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体性》)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谓文“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
可见,宋代之前,雅俗观念已流行于音乐、文学领域。正如刘熙载所说:“乐中正为雅,多哇为郑。词,乐章也,雅郑不分,更何论焉。”(《艺概》卷四)雅俗之辨也自然成为两宋词坛的重要议题。
一 “宋人所称雅词”
晚清沈曾植《全拙庵温故录》说:
宋人所称雅词,亦有二义。此《典雅词》[1],意取大雅。若张叔夏所谓“雅词协音,一字不放过”者,则以协大晟乐律为雅也。曾端伯盖兼二义。又按《碧鸡漫志》:“万俟雅言自定其集,分两体,曰雅词,曰侧艳。”又云:“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离骚》遗意。如贺之《六州歌头》、《望乡人》、《吴音子》,周《大酺》、《兰陵王》、《六丑》诸曲最奇(崛)。或谓‘深劲乏韵’,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2]
沈氏所提及的《典雅词》、曾慥(端伯)《乐府雅词》以及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等都是考察宋人雅词观念的重要依据。然而沈氏据以解释“宋人所称雅词”时却有疏漏之处。曾慥《乐府雅词引》云:
涉谐谑则去之,名曰《乐府雅词》。九重传出,以冠于篇首;诸公转踏次之。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幼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
未曾言及协律,更未限定协大晟乐律。清初朱彝尊《乐府雅词跋》说:“卷首冠以《调笑》绝句,云是‘九重传出’,此大晟乐之遗音矣。”沈氏盖误读朱跋而谓曾慥题名“雅词”兼“意取大雅”及“以协大晟乐律为雅”二义。考《宋史》卷一二九《乐志四》,大晟乐律成于崇宁四年(1105),政和二年(1113)播之教坊,施之宴乐。《乐府雅词》中所录欧阳修、晁补之等人词作就不可能协大晟乐律。
再说张炎的雅词观。沈氏所引“雅词协音,一字不放过”见于《词源》卷下“音谱”:
词以协音为先。音者何?谱是也。……先人晓畅音律,……每一作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曾赋《瑞鹤仙》一词云……此词按之歌谱,声字皆协,惟“扑”字稍不协,改为“守”字乃协。始知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信乎协音之不易也。
张炎强调协音,这当归属他词学观念中的传统意识。然而词乐分离的客观趋势却使他切实感到“协音之不易”,“旧有刊本六十家词,可歌可诵者,指不多屈”(《词源•序》)便是实证。因此具体谈到创作时,张炎并非“以协音为先”:
词之作必须合律。然律非易学,得之指授方可。若词人方始作词,必欲合律,恐无是理。正如方得离俗为僧,便要坐禅守律,未曾见道而病已至,岂能进于道哉。音律所当参究,词章先宜精思。俟语句妥溜,然后正之音谱,二者得兼,则可造极玄之域。
《词源》卷下“杂论”
这无疑是对不协音律之作的某种程度的肯定。与此相应,在评断词作雅俗时,张炎并非拘于协音与否。如被他誉为“景中带情,而存骚雅”的陆淞《瑞鹤仙》(脸霞红印枕)[3],词中对应于前引张枢“按之歌谱”而改定的“粉蝶儿、守定花心不去”一句作“待归来、先指花梢教看”。“先指”二字与张词字声迥异。则陆淞之作必不协音,而张炎评为“骚雅”,则其雅词观主要就词章而论。这在《词源》中颇多例证:
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而于音谱且间有未谐,可见其难矣。
《词源•序》
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
《词源》卷下“杂论”
故其燕酣之乐,别离之愁,回文题叶之思,岘首西洲之泪,一寓于词,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
《词源》卷下“赋情”
所谓“善于融化诗句”、“志之所之”、“屏去浮艳,乐而不*”云云,均从词章方面论述雅词。又如谓寿词“倘尽言富贵,则尘俗”(《词源》卷下“杂论”)、“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同上)、“若使尽用虚字,句语又俗,虽不质实,恐不无掩卷之诮”(《词源》卷下“虚字”)以及上引“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等等,则从词章方面指斥俗词。也许可以说,词章之雅俗同协律与否并无多少联系,论评词作者自可分别待之。张炎谓“昔人咏节序,不惟不多,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词源》卷下“节序”),沈义父谓“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乐府指迷》),雅俗之评显属词章方面。
辨清了张炎雅词观的立论视角,便须进一步探明其具体义蕴。其实,上引“志之所之”、“屏去浮艳,乐而不*”、“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等已显示出张炎雅正词学观念中的诗教因素。张炎《词源•序》云:“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并谓其《词源》旨在重振古音雅词。复古尚雅的词学观是不可能摆脱诗教的,南宋复雅词风盛行下的有关词评充分证明了这一必然趋向。如许顗称张先词句“眼力不知人,远上溪桥去”远绍《诗•邶风•燕燕》,评晁补之《满江红》(华鬓春风)“善怨似《离骚》”[5],鲖阳居士谓苏轼《卜算子》“与《考盘》诗极相似”[6],曾丰谓黄公度词“清而不激,和而不流,要其情性则适,揆之礼义则安”[7],张镃评史达祖词“无 荡污*之失”、“跻攀风雅,一归于正”(《梅溪词序》),林景熙评胡汲古词“清而腴,丽而则,逸而敛,婉而庄……所谓乐而不*,哀而不伤,亦出于诗人礼义之正”(《胡汲古乐府序》),林正大自称其词“婉而成章,乐而不*”(《风雅遗音序》)等等。
“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等传统儒家诗学中的道德功用论在南宋词坛的盛行与理学所张扬的道德教化文学观念有关。前面提及的曾丰《知稼翁词序》就从作者道德修养角度评词,对黄庭坚评苏轼《卜算子》不以为然:“余恐不食烟火之人口所出,仅尘外语,于礼义遑计欤!”并谓黄公度“非能为词也,道德之美,腴于根而盎于华,不能不为词也”,显属“有德者必有言”之论《(论语•宪问》)。与曾丰同时的詹效之在《燕喜词跋》中称曹冠词作“得于六义之遗意,纯乎雅正者也。……和而不流,足以感发人之善心,将有采诗者播而飏之,以补乐府之阙,其有助于教化,岂浅浅哉!”“感发人之善心”与理学家所谓“兴起人善意”[8]同一旨趣。
词人的“道德之美”,创作上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以及教化功用上的“感发人之善心”,归结到词作艺术特征上就是“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逸而敛”、“婉而庄”、“丽而则”等所构成的风格系列。张炎所总结的南宋雅正词学观念的风格内涵也就在此,是为两宋词坛雅俗之辨的终结所在。回溯两宋词学发展历史,雅俗之辨体现在两种主要趋势之中:言情之婉雅和言志之骚雅。
二 言情之婉雅
词在唐五代生成期就已形成以抒写男女情事为主的传统,但在格调上大体可分为雅俗两类。欧阳炯的《花间集叙》就有“诗客曲子词”与“莲舟之引”之分,而中唐“诗客曲子词”作者的自序也透露了“曲子词”发展的雅、俗两种趋向,如刘禹锡《竹枝词序》自述在建平聆“里中儿联歌《竹枝》”,病其词多鄙陋,故承屈原作《九歌》之意而“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陆游称“花间鼻祖”温庭筠“南歌子八阕,语意工妙,殆可追配刘梦得《竹枝》,信一时杰作也”。[9]《花间集》中五百首“诗客曲子词”并非绝无鄙俗之作,但整体格调堪为唐五代雅词之代表。在两宋词坛尚雅贬俗风气中,《花间集》(准确地说是“花间”词风),颇得好评。梳理有关评论可以见出宋人对于词之言情(抒写男女情思)的规范。
(一)宋人所谓“花间”词风
在北宋,与柳永俗词相对的晏(殊、几道)、欧词风被公认为南唐嗣响。刘攽《中山诗话》称“晏元献尤喜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南宋罗愿《新按志》卷十载冯氏子孙璪以《阳春录》“示晏元献公,公以为真赏”,又引元丰间崔公度跋《阳春录》:“近时所镂欧阳永叔词亦有之(指冯延巳词),皆失其本也。”而晏几道则明确自称“续南部诸贤绪余”(《小山词自序》)。“花间”、南唐在词风上并无多大区别,罗大经就称誉欧阳修“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10],陈振孙评晏几道词“独可追步《花间》,高处或过之”[11]。在宋人眼中,“花间”、南唐词风实质上被视为言情而不入浇风之典范:
南唐相国冯公延巳……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观其思深辞丽,韵律调新,真清奇飘逸之才也。[12]
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阕。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13]
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14]
吾友黄载万歌词,号《乐府广变风》,学富才赡,意深思远,直与唐名辈相角逐,又辅以高明之韵,未易求也。[15]
右《花间集》十卷,皆唐末才士长短句,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16]
《花间集》十卷,……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也。[17]
词之难于令曲,……当以唐《花间集》中韦庄、温飞卿为则。[18]“思深辞丽”、“情真调逸”、“意深思远”云云,固然是对唐五代词风的评鉴,但严格说来,只能是宋人眼中的“花间”词风,寓有宋代雅词观念,都可归入“温柔敦厚”、“乐而不*”、“和而不流”等雅正词学观念下的风格系列之中。
然而落实到唐五代词作实况,文人词受绝句诗之0响而呈现出语简意深、情真调逸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存有民间曲子词的艳俗成分,酒筵歌席间浅斟低唱以娱宾遣兴的曲子词自然难免绮靡乏韵之作。针对后者,宋人对唐五代词又有所贬斥,或谓唐五代词“乏高韵”[19],或谓“唐人《花间集》,不过香奁组织之辞”[20],或谓“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艳猥亵不可闻之语”[21]等。至于苏轼《跋李主词》指斥李后主“苍皇辞庙日”不“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却“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李清照《词论》谓唐开元、天宝之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五代干戈,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陆游《〈花间集〉跋》谓唐末五代“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则都从世风教化角度发论,即晁补之《跋〈花间集〉》中所叹:“嗟夫!虽文之靡无补于世,亦可谓工矣!”
从儒家教化着眼对唐五代艳俗词风进行矫正,也可透过两宋雅士为欧阳修的艳词辨诬这一现象看出来。文莹《湘山野录》卷上、钱愐《钱氏私志》(宛委山堂《说郛》本),蔡绦《西清诗话》(《四库提要》卷198引,今本无)、曾慥《乐府雅词序》、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四库提要》卷198引,今本无)、罗泌《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跋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等都否定欧阳修有艳俗之词,或谓“憸人构*艳数曲射之,以成其毁”(文莹语),或谓落第举人刘煇所作(钱愐、蔡绦)、朱熹、罗泌等人主此说)。其实欧阳修承袭唐五代词风,难免有轻艳之作。考欧阳修早年任西京留守推官时诗酒放达[22],词作如《玉楼春》“春山敛黛低歌扇”、“尊前拟把归期说”、“洛阳正值芳菲节”,《夜行船》“忆昔西都欢纵”等都是这段生活的写照。某些艳词很可能作于此时,其明道二年(1033)所作《拟玉台体》七首似可参证。陈廷焯《词坛丛话》谓欧阳修艳词为“年少时笔墨”,不为无见。至于刘煇造谤之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已有辩正:
世传煇既黜于欧阳公,怨愤造谤,为猥亵之词。今观杨杰志煇墓,称其祖母死,虽有诸叔,援古谊以适(嫡)孙解官承重服,又尝买田数百亩,以聚其族而饷给之。盖笃厚之士也。肯以一试之淹,而为此憸薄之事哉?
然而陈氏为刘煇辩证即以刘氏人品“笃厚”为据。这与前述诸家(包括陈振孙本人)为欧阳修艳词辩伪是同一出发点,都间接反映出宋人对唐五代词风中艳俗成分的摈弃态度。
综上所述,宋人所称誉的“花间”词风是对唐五代文人词传统进行去俗存雅之后的词体模式,体现着宋代词学观念的尚雅倾向。就唐五代词而言,《花间集》所代表的文人词之外,尚存在民间浅俗轻艳词风。宋初与晏、欧同时的柳永纵游娼馆酒楼间,“作新乐府,骫骳从俗”[23],主要承继了唐五代民间曲子词风气。因此,对柳永俗词的评论便成了宋代词坛雅俗之辨的重要内容。
(二)对柳永俗词的反拨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39引《艺苑雌黄》:
柳三变,字景庄,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日与獧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呜呼!小有才而无德以将之,亦士君子所宜戒也。柳之乐章,人多称之。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媟之语,若以欧阳永叔、晏叔原、苏子瞻、黄鲁直、张子野、秦少游辈较之,万万相辽。彼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
宋人对柳词的贬斥与其“薄于操行”不无关系。近人汪东就曾说:“当时名卿大夫颇有屏抑其词,不屑称道者,此本由薄其人故。”(《唐宋词选评语》,《词学》第二辑)就柳词而言,其羁旅穷愁之作中不无身世之概,如郑文焯就盛赞柳词写景高健,“而景中人自有无限凄异之致,令人歌笑出地。”(《大鹤山人词话》附录,《词话丛编》本)宋人主要针对柳永俗词发论:一则斥其“词语尘下”(李清照语);二则斥其格调软媚而无高致,苏轼所谓“柳七郎风味”,晁补之所谓“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能改斋漫录》卷16)、王灼所谓沈公述等六人“源流从柳氏来,病于无韵”(《碧鸡漫志》卷2)、陈振孙所谓“柳词格固不高”)《直斋书录解题》卷21)等都是此意。自然,对柳永俗词的摈斥也就是倡导词体雅化。上述《艺苑雌黄》所举出的与柳永“万万相辽”的欧、苏等人,徐度《却扫编》卷下即评为“体制高雅”:柳永“其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
“文格一变”、“体制高雅”只有归结到雅化(士大夫化)这一词体创作观念上才能统冠“欧、苏诸公”。从词作风格上说,欧阳修仍属《花间》、南唐一系,以深婉闲雅为本色。与柳永鄙语俗词相对而言,欧、苏诸公词作都可谓“体制高雅”,但具体到欧、苏诸公间的词风差别,对“高雅”一词又当有所辨析。联系欧、苏等人词风及时人有关论评,“高雅”大体可析为两类风格:一类可称为婉雅,欧阳修、晏几道、秦观等人属此;一类可称为清雅,苏轼可为代表。上面所引诸家斥柳词气格雌下的种种议论中,晁补之所谓“子野韵高”、王灼谓源出柳词者“病于无韵”而评苏词“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即言清雅;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中谓柳词“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则指婉雅。这种分歧存在于反对柳永俗词这一共识之下,又体现着对《花间集》所代表的唐五代传统词风的不同态度。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二有一段评及苏词:
晁无咎云:“眉山公之词短于情,盖不更此境耳。”陈后山曰:“宋玉不识巫山神女,而能赋之,岂待更而后知?”是直以公为不及于情也。呜呼!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当如是,其溢为小词而及于脂粉之间,所谓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辈,岂公之雅趣哉?
文中所引晁、陈之语见陈氏《书旧词后》(《后山集》卷19)。在对待柳永“纤艳*媟”词作的态度上,晁、陈与王若虚是一致的,晁推赏柳词《八声甘州》中“渐霜风凄紧”诸句“此真唐人语,不减高处矣”(《能改斋漫录》卷16),正是对柳词的去俗尚雅之举。然而在词学观念上,晁、陈二人倾向于传统词风,而王若虚则禀承苏轼,主张“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滹南诗话》卷2)。因而对词之言情各有所见:晁、陈以言儿女柔情为词之本色,王若虚则以士大夫高情雅趣为词情之正。陈师道自称其词“不减秦七、黄九”(《书旧词后》),晁补之谓“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能改斋漫录》卷2)。从传统词情角度看,苏词与秦词格调迥异:苏轼突破传统词情局限,将士大夫高情雅志揽入词境,因而有“以诗为词”之称;秦观则基本维护词情传统,与柳永的区别主要在字面之雅俗及情韵之厚薄方面,因而与苏轼形成继承传统词风和变革传统词风两种趋势。这也就是苏轼以其词作“无柳七郎风味”而自豪(《与鲜于子骏》),指责秦观学柳词的根源所在。
陈洵《海绡说词》有云:“东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尽管秦观词风对柳词也是一种雅化,但在苏轼看来,二者同样气格雌下,“故常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避暑录话》卷上)从苏轼《与鲜于子骏》中可见出他以所作小词应复鲜于侁索诗之求,而他称鲜于侁诗“萧然有远古风味”,与其评陈慥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与陈季常》)、评蔡景繁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同一旨趣,显示出诗词并论、不当分异的观念。“长短句诗”一语又被移评苏轼本人词作,如李清照所谓“句读不葺之诗”(《词论》)、王灼所引时人评苏词为“长短句中诗”、“移诗律作长短句”(《碧鸡漫志》卷2)。按此“长短句诗”就词作格调、境界而言,与宋末沈义父从协音角度谓“不协则成长短句之诗”者不同。
苏轼从观念到创作上揽诗入词,对柳永俗词、对传统艳词无疑是一种雅化,同时又与秦观对柳词的雅化有着根本区别。秦观词风实可归属宋人所谓“花间”词风一系;而苏轼所倡导的诗化词风则是对“花间”词风的革新。胡寅《酒边词序》将《花间》与柳词一并视为苏轼改革的对象是极具见地的。如果以“言情”指称前者,则后者可冠以“言志”一名。
三 言志之骚雅
在与音乐合体这一特征上,词与“诗三百”、古乐府是一致的。北宋中叶儒学复兴思潮通过当时的儒臣词家影响到词坛,“诗言志”这一传统儒家诗论便成为词体雅化的理论依据。
胡适《词选•自序》中提出“诗人的词”,说:“这种‘诗人的词’,起于荆公、东坡,至稼轩而大成。”“诗人的词”也就是“诗言志”观念渗入词坛的创作体现。王安石、苏轼为变革传统言情词风的先驱,在词学观念上都具有复兴儒家传统诗学的意识。《侯鲭录》卷七载王安石语:“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这尽管是从词乐结合方式上以古之先词后乐责难今之先乐后词,却显示出以词为主的创作新观念,与苏轼“非醉心于音律”(《碧鸡漫志》卷2)、张耒评贺铸“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贺方回乐府序》)正可呼应。至于苏轼及其门人黄庭坚、张耒等将词拟诸《诗》《骚》、古乐府则进一步显示出词学观念中的“言志”意识。
承上述诸家之后,明确而较系统地以儒家传统诗、乐观念论词的是王灼。其《碧鸡漫志》从溯源角度以伪《古文尚书•舜典》、《毛诗序》及《礼记•乐记》中有关诗、乐理论为依据,提出“有心则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歌”。在王灼看来,“诗三百”与“古歌”、“古诗”与“古乐府”乃至今诗与“今曲子”在“言志”这一本质上是相同的,认为“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因此他赞同苏轼以诗伟词,在评词中也常以“如其诗”为妙、为佳,评陈无己、陈去非、徐师川、苏养直、吕居仁等人词作。
先秦儒家所谓“诗言志”与政治教化密切相关,如《论语》中所言之“志”皆为有关修身治国的怀抱。就《诗经》而言,说到作诗意图者共十二处,都不出讽谏美颂,但称“诗”者仅三处,余者或称“诵”,或称“歌”。这说明“诗言志”的政教功能是通过合乐应歌实现的。王灼对此有明确的认识:
古者采诗,命太师为乐章,祭祀、宴射、乡饮皆用之,故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至于“动天地,感鬼神,移风俗”,何也?正谓播诸乐歌,有此效耳。(卷一)
王灼承继王安石、苏轼等人“言志”词学观念,提出“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同时又从“美教化,移风俗”方面对所发之志进行规范。据此,王灼较全面地考察了北宋词学创作,分别出苏轼、周邦彦、贺铸等人所代表的雅词派和柳永、曹组等人所代表的俗词派。这标志着“言志”观念进入词坛之后雅俗之辨的展开。综合考察“言志”词学观念所导致的词坛雅俗之辨,可从词情,词法两方面来进行。
(一)词情之雅俗
传统词情主要指男女情事。北宋范仲淹、王安石,尤其是苏轼出现于词坛之后,词情有了很大拓展,如元好问所说:“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词成为一种新型抒情诗体,可以言男女之情,也可以发身世之感,还可以写诙谐之趣。以“诗言志”这一传统诗教而论,纯粹的男女私情及诙谐之趣均为卑俗情趣,有害于风教。王灼对苏轼、周邦彦、贺铸等人的赞赏以及对柳永、曹组等人的斥责就显示出词作情趣的雅俗之分。苏轼以士大夫之高情雅志运诸笔端,词情之雅自不必论;曹组所代表的滑稽戏谑词风,趣味之俗也显而易见。需要辨析的是柳永、周邦彦、贺铸等人的词情之雅俗。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
前辈云:“《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间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贺《六州歌头》、《望湘人》、《吴音子》诸曲,周《大酺》、《兰陵王》诸曲最奇崛。或谓深劲乏韵,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王灼举出周、贺二人词例誉为得《离骚》之意,而斥柳永词作为“野狐涎”,前者为雅,后者为俗。其实,王灼以人论词,不免偏颇。《离骚》所代表的屈、宋辞赋以抒发士大夫穷通出处之感为主,即“贤人失志之赋”(《汉书•艺文志序》),是对“诗言志”原有讽谏颂美内涵的发展和引申。其艺术表现上借香草美人寓托身世感慨之法,为词坛“言志”新风与“言情”传统的结合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王灼本人及其提及的“前辈”都对此有所感悟,但王灼否定柳永《戚氏》一词得《离骚》之意,则属拘于成见。柳永此作与王灼所称誉的贺铸、周邦彦数词都抒发了作者的身世之感,都可说远绍《离骚》之意。就周邦彦词作而言,抒发男女私情率真如柳永者未尝没有,张炎《词源》卷下“杂论”有云:
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如“为伊泪落”,如“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时相见何妨”,……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
沈义父《乐府指迷》也指出周邦彦这类词“不可学”。王灼、张炎、沈义父为两宋雅正词学观的代表,张、沈二人对周邦彦软媚词作的指斥不妨看作对王灼评周词的补充。综合观之,王灼、张炎等人对周、柳词的雅俗之辨体现在词情上即以士大夫有关穷通出处的身世之感为雅,以单纯的男女情爱为俗。而于词学“用功四十年”的张炎对词的言情传统及其相应的艺术特质深有体味,能从词体艺术本色角度调和言志与言情的关系而归于雅正,使言志不入粗豪,言情而不入浇漓。这便属于词法问题。
(二)词法之雅俗
北宋词坛曾有柳永(《戚氏》)、晏几道、晁补之(《满江红》“华鬓春风”)、贺铸、周邦彦五人词作被同时或稍后的评论者拟比屈、宋辞赋。这固然着眼于其作品中的身世感慨,同时也包括词法上的比兴寄托特色。王灼称贺铸、周邦彦“卓然自立,
“花间词派”鼻祖温庭筠
沮庭筠(约812-870年),本名歧,字飞卿,唐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世居太原,是晚唐著名的诗人、词家。也是当时作词最多,对后世长短句的发展影响极大的词人之一。
庭筠出身于没落的官僚贵族家庭,虽为唐初名声显赫的太原温氏后裔,但是,到他父亲这一代时,早是家道中落,衰微而已。他少年时代,即以善思敏悟。才华横溢而称著乡里。逮至长成,更是博闻强记,通晓音律,善为管弦,而且,尤以诗词文赋见长。世传,庭筠每入试,押官韵作赋,从不起草, “但笼袖凭几,每赋一咏,一吟而已”,故得“温八吟”之号。曾经“八叉手而成八韵”,又别称“温八叉”。大约是因为其长相较为丑陋的缘故吧,所以时人亦有称他“温钟馗”的。
温庭筠虽然甚有才思,弱龄有志.然而,仕途却闭不得意。从28岁到35岁的八年之中,他屡屡应试,屡屡不第,尤其是最末一次应试,竟因恃才傲物,讥讽权贵,触犯上司,被诬为“有才无行”,再次名落孙山,以至于一生都未能得中进士。
大约是唐直宗大中三年(849年)的前后,温庭筠以善于诗词,被当朝宰相令狐绹选用为考功郎中,进入相国的书馆工作。有一次,令孤绹看到他填的一首《菩萨蛮》词很好,就假冒自己的名字把它进献给唐直宗,并再三嘱咐庭筠为其保密。但是,温庭筠非常鄙夷令孤绹的这种行为,很快便把此事宜捅出去,弄得堂堂相国尴尬异常,大失体面。又一次,宣宗赋诗,上句用了“金步摇”,但对句一时怎么也想不出来,遂令庭筠来对。庭筠立即以“玉条脱”应对,宣宗听罢非常满意。当时在旁的令狐相国不知温庭筠所对词语的出处,庭筠便告诉他典出《南华经》,井很不客气地指出:“《南华经》是一部极普通的书,并非什么生僻著作,相国在公事之余,应读一点古籍才是。”他的这一番语带教训的批评,使令狐绹出乖露丑,遂把他忌恨在心。在一次科举考试中,庭筠替应试者提笔代劳,事发后,令狐绹便以他搅扰科场罪名,贬为隋县尉。此后,庭筠依附徐商,被任为巡官。在这段时间,他常与段成式、余知古、徐商等,往来唱和,吟诗作赋,度过他一生最愉快的几年。咸通七年(865年),徐商攉升宰相,任庭筠为园子助教。然而,好景不长。是年秋试中他竭力赞赏推荐邵谒的文章,而邵谒之文以激切的育词揭斥了时政,温庭筠也因此被罢官。从此,他落魄江湖,四处飘流,几年后,在贫病交加中,客死他乡。
在晚唐的诗人中,温庭筠声名鹊起,与李商隐齐名,史称“温李”;在晚唐的词家中,温庭筠填词最多,和著名的韦庄齐名。但是,他的诗作,无论思想境界,表述内容,还是艺术成就,都远不能和李商隐相提并论。至于他的词,尽管存在着题材狭窄,用词轻艳的不足,但在构思的精巧,语言的含蓄,声津的和谐等方面,都有自己艺术风格上的特点,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在词在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有着突出的贡献。半个世纪之后出现的花间词派,就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
对于温庭筠的品行,历来毁誉参半。不过从他那些充满脂粉香泽,浓艳重抹,刻意描述女子体态、容貌的词作来看,他的生活确是比较轻浮,比较放荡。这必然会影响他向更高的艺术境界升华,同时,也给后世的词人带来了不甚良好的影响。
婉约派
宋词风格流派之一。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两派的,一般认为是明人张□(字世文,著有《诗馀图谱》、《南湖诗集》。清人王士禛《花草蒙拾》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王又华《古今词论》所引张说,大意略同。稍晚于张□的徐师曾(字伯鲁,明嘉靖时人),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指出:“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徐师曾的说法与张□相近。婉约与豪放并不足以概括风格流派繁富多样的宋词,但可以说明宋词风调具有或偏于“阴柔”之美、或偏于“阳刚”之美的两种基本倾向,有助于理解宋词的艺术风格。
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 《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因此,前人多用“婉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软媚”(《词源》)、“绸缪宛转”(《酒边词序》)、“曲折委婉”(《乐府馀论》)等语,来形容他们作品的风调。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
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
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花间词派”是中国古代诗词学流派之一。
花间词诞生于晚唐五代,花间词派作为最早的流派之一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着巨大的影响。晚唐五代时,中国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词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相继出现了西蜀和南唐两个词坛中心。
五代赵崇祚撰《花间词》,收集了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韦庄、和凝、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顾夐、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等人的500首词作。其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之外,都是集中在西蜀的文人,称为“花间派”。
“花间词派”代表人物
1、温庭筠
温庭筠本名歧,字飞卿,唐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世居太原,是晚唐著名的诗人、词家。也是当时作词最多,对后世长短句的发展影响极大的词人之一。
2、韦庄
韦庄字端己。京兆郡杜陵县(今陕西西安)人,晚唐诗人、词人,五代时前蜀宰相。文昌右相韦待价七世孙、苏州刺史韦应物四世孙。韦庄工诗,其律诗圆稳整赡、音调浏亮,绝句情致深婉、包蕴丰厚;其词善用白描手法,词风清丽。与温庭筠同为“花间派”代表作家,并称“温韦”。
3、顾敻
顾敻五代词人。生卒年、籍贯及字号均不详。前蜀王建通正时,以小臣给事内廷,见秃鹫翔摩诃池上,作诗刺之,几遭不测之祸。后擢茂州刺史。入后蜀,累官至太尉。顾夐能诗善词。《花间集》收其词55首,全部写男女艳情。
1 花间词是什么意思
花间词是花间词派的作品,花间词派”是因西蜀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而得名。《花间集》辑录了温庭筠和西蜀作家韦庄等人的词作。后人遂称他们为花间词派。西蜀的“花间词派”词人奉温庭筠为“鼻祖”,极力推崇、仿效。“花间词派”主要作家有韦庄、牛希济、李珣、欧阳炯等。其词的内容主要写男女离别相思之情,歌舞宴乐之事。其风格浓艳香软,辞藻华丽,但也有一些作家的作品写得比较清丽自然,境界高远。
温庭筠的词。
更漏子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梦江南
千万恨,恨极在天涯。
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
望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
韦庄的词。
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菩萨蛮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
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
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
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2 花间词里的句子此词将人生失意的无限怅恨寄寓在对暮春残景的描绘中,是即景抒情的典范之作。起句“ 林花谢了春红 ”,即托出作者的伤春惜花之情;而续以“太匆匆”,则使这种伤春惜花之情得以强化。狼藉残红,春去匆匆;而作者的生命之春也早已匆匆而去,只留下伤残的春心和破碎的春梦。因此,“太匆匆”的感慨,固然是为林花凋谢之速而发,但其中不也糅合了人生苦短、来日无多的喟叹,包蕴了作者对生命流程的理性思考?“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一句点出林花匆匆谢去的原因是风雨侵龚,而作者生命之春的早逝不也是因为过多地栉风沐雨?所以,此句同样既是叹花,亦是自叹。“无奈”云云,充满不甘听凭外力摧残而又自恨无力改变生态环境的感怆。换头“胭脂泪”三句,转以拟人化的笔墨,表现作者与林花之间的依依惜别之情。这里,一边是生逢末世,运交华盖的失意人,一边是盛时不再、红消香断的解语花,二者恍然相对
花间词派代表人物
本文2023-10-30 13:17:01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183901.html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