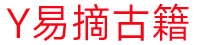柏拉图对人性善恶的看法

柏拉图在其对话录《理想国》的第七卷中,提出了一个“洞穴”的隐喻。关于这个隐喻,小编有如下思考:
对“洞穴理论”的理解:
这个隐喻的本体简单概括成如下图示:
影像——洞外的人与手偶——火光囚徒
可见,囚徒处在整个过程的最末端和最底部,他们只是任人愚弄的对象。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他们是有思考的能力的,但悲哀的是他们所能够认知的并不是真正的最高的存在,而是经过加工演变形成的影像,于是他们便把这影像当成了真实。在洞穴中,被绑缚的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洞外的人的行为,更不可能认识作为一切的起点与终极的火光。他们能够感知到的关于火光的有且只有洞壁上的影像。
柏拉图的这个隐喻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一个脱离桎梏的人历经艰难见到了火光,而此时的他已经与原来的群体——洞穴中的囚徒——格格不入了,在旧友中,他已经是一个不能被接纳甚至要被杀掉的另类。
柏拉图在解释这一隐喻时说:“……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个比喻整个儿地应用到前面讲过的事情上去哲学论文,把地穴囚室比喻可见世界,把火光比喻太阳的能力。如果你把从地穴到上面世界并在上面看见东西的上升过程和灵魂上升到可知世界的上升过程联想起来,你就领会对了我的这一解释了,既然你急于要听我的解释。至于这一解释本身是不是对,这只有神知道的。
但是无论如何,在可知世界中最后看见的,而且是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最后看见的东西乃是善的理念。我们一旦看见了它,就必定能得出下述结论:它的确就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看见了善的理念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柏拉图把“善的理念”作为一种本源,就像火光(用来喻太阳)对于囚徒一样,它是人赖以走进理想国的终极理念。对于“善的理念”,柏拉图解释为:“它的确就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看见了善的理念的。”
要摆脱现实的可知世界的愚弄,成为一个“理性”的人,就必须摆脱桎梏,向“善的理念”靠近,这是我们从柏拉图的“洞穴”的隐喻中得到的结论。
关于“洞穴理论”的一点思考:
在这里,小编想把这个隐喻做如此理解:
所谓“善的理念”是柏拉图赋予“火光”这一符号的所指。而真正决定着人的理性和人对“可知世界”的认识的,应该是人性本身。其实套用“洞穴理论”的形式我们可以生动地解释这一观点。“火光”即为人性,摆弄手偶的人便是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左右着“可知世界”的表现形式,洞壁上的影像则是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各种现实存在,洞穴中的囚徒无疑是被现实愚化并玩弄着的人们。
被柏拉图比喻成“善的理念”的火光,在小编的理解中被比喻成了人的本性,即人性。人性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的源泉。而人性的核心是欲望。
人性有善有恶,善恶在所养焉的意思:
人的本性中有善有恶两个方面, 取人之善性, 培养引导, 善就滋长; 取人的恶性, 培养引导, 恶就滋长。这样看来, 情性各有阴阳正反两个方面, 善恶在于从哪个方面培养了。
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善象”和“恶象”,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人性、道德与善恶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各种哲学思想与伦理体系中,思想家们往往是从人性及其善恶开始而建构其理论体系的。
人性善恶的动态轨迹分析从宏观上分析,人性在其善恶发展上是动态的。人性的善恶,是从自然属性开始的。人出生时,自然属性多些;随着自身的发展,社会属性越来越明显。
每个人生下来内心都会有君子和小人的成分。
比如三岁小儿,坐在超市的小推车里,走到散装的零食货架旁边,都要拿起超市的东西往嘴里塞,这时就需要大人的教育引导,告诉他,超市里的东西如果没有付费的话,是不能据为己有的。孩子会在大人的教育下逐渐去掉小人的角色,变成有规则意识和自我约束感的君子,所以一个人成长就是内心的君子不断打败小人的过程。
人性善恶问题为中国传统哲学之重大命题,千载聚讼纷纷。《三字经》开头四句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其中前两句语出《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什么是“初”?就是“始”的意思。制做衣服一定要先将布料裁剪成若干片一定形状的料块,然后把这若干片缝合纫缀起来,才能形成衣裳。俗称制衣匠为“裁缝”,就是就这两个制衣的基本工序而言的。裁剪必用刀,故“初”字从“衣”从“刀”以示其始。所以“人之初”是指人刚生下来的时候。什么是“性”?就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性”的本义就是如此。古籍中“性”有时作“生”即为明证。“性相近,习相远”出自《论语·阳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习”是后天环境的影响。任何人,不管他父母是什么民族、种族,也无论他的父母是贫贱还是富贵,是好人还是坏人,其与生俱来的“性”都像是素练白绢,没有颜色,没有善恶的痕迹。——这就是 “性相近”的意思;而人既生之后,环境影响各异,性随之而变,如素绢白练沾染了各种颜料,逐渐变得差异越来越大,有了善恶的区别。——这就是 “习相远”的意思。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可以看出,其实孔子是把性和习明确分开的:先天为性,后天为习。而历来论性,不辨性习,至于混习为性,——性善、性恶的争辩皆由此而生。
人与生俱来的东西有两个方面,一是形体容貌即所谓肉体,二是情志欲望即所谓精神。性从“心”,故特指精神而言。后世谈论争辩人性,也都是特指精神而言。而精神包含广泛:一是知识智能,二是情绪,三是意志,四也品质志趣,五是脾气性格。知识智能,是就真伪是非而言的;情绪,是就喜怒哀乐而言的;意志,是就抵御外界摧折诱惑所体现出来的差异而言的;品德志趣,是就人面对外界摧折诱惑时的取舍态度以及社会对人的言行的道德评价而言的;脾气性格,是就刚躁柔静而言的。显然,知识智慧、情绪、意志、脾气性格都无法说它们是善是恶。因此,人性之“性”,并非指全部精神,而是特指人的品德志趣而已。
先哲论“性”,有五种观点:孟子性善说、荀子性恶说、董子(仲舒)性三品说、扬子(雄)善恶混杂说、告子性无善恶说。大致以本以三品说为主流,自有宋理学兴起,性善说遂为主流。
孟子主张性善,认为人人皆可以成尧舜。所以特别重视修身育德,以仁义自持。孟子的性善说的缺陷在于,无法回答这样的诘问:人性既然是善的,那么人性中的恶从何而来?如果说是由于沾染了社会环境中的恶而来的,那么社会环境中的恶又从何而来?社会不是许许多多个人组成的吗?既然 “人人皆可以成尧舜”,那就是说,每个人的人性都是善的,社会里怎么会产生恶呢?而且,如果人性本善,那么向善容易变恶就不易了,为何实际情况却是,人容易向恶而不易向善呢?
荀子以为人性本恶,所以特别强调用礼和制度来约束规范人的行为。到了其弟子李斯,一变而重法,就流入法家了。性恶说也存在着与性善说类似的问题:人性本恶,谁肯向善?谁又知善?善从何而来?
扬雄认为: “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身》)。扬雄的“善恶混杂说”可以回答善恶从何而来的问题,比“性善说”和“性恶说”要经得起推敲一些。然而,这种观点仍然无法回答进一步的诘问:初生的婴儿,其啼哭、吃奶、便溺等外在可见的表现是善还是恶?如果说这些无所谓善恶,但婴儿的心中的确有善恶,那么婴儿未表现出来的善恶念头,我们又如何知道?
董仲舒认为“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以米为饭,以性为善,此皆圣人继天而进也,非情性质朴之能至也,故不可为性。”他把人分为三种:圣人、斗筲之民和中民。认为“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由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人之性。……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他给“性”的定义是“无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
其实三品说并非董仲舒自创,而是承袭了此前历史上曾经流行的观点。如《老子》把人分为上士、中士、下士三等,《庄子》则有至人、神人、圣人的分法。在《论语》中孔子曾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篇》),又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因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汉书·古今人表第八》对孔子的话有段解释:“传曰:譬如尧、舜,禹、稷、卨与之为善则行,鲧、讙兜欲与为恶则诛。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桀、纣,龙逢、比干欲与之为善则诛,于莘、崇侯与之为恶则行。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齐桓公,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
董仲舒首先把人分为三品,然后再论其中绝大多数人的人性问题,这个思路比把每个人的人性一概而论要好。三品说是把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的“圣人(或上智)”“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下品的“斗筲之民(或下愚)”“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后天环境对他们没什么影响,所以不论。董仲舒甚至把人性进一步局限到“中人”的“人性”,这是他的不足。
在区分了三品之后,董仲舒开始论“中人”的人性。不过他似乎在这里不自觉地跑题了:把人性的善恶问题转换为“性”与“善”的关系问题了。的确,人性与善恶不是一回事,但是也没有人认为“性”就是“善”或“恶”啊。
细品董仲舒关于“善如米,性如禾”的论述,其实跟性善说或善恶混说是一致的。米虽然不是禾,但米是对禾加工,去除茎叶糠壳后得到的。那就是说,善本来就存在于人性中,并不是从外界加入的。一般的禾都有谷实,都可以通过加工得到米;一般的人的本性中都存在善,都可以通过教化得到善。这不是 “中人皆可以为尧舜”嘛!董仲舒没有说禾的茎叶糠壳就是恶,但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如果把禾的茎叶糠壳比做是恶,那么米的加工过程就是一个去恶存善的过程。这又和杨雄的“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的说法一致了。
告子关于人性的观点记载在《孟子》一书中。告子认为人性本无善恶之分,一个人是善是恶,全在于后天的影响塑造。既然前面四种人性论都不能经得起诘问,那么告子的观点就很可能是正确的。而且这种观点无疑极容易被现代人所认同。我也认同这种说法。不过,告子的人性无善恶的观点,似乎也是针对一切人而言的。这就不符合实际的社会现象了。同样生活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受到的教育也影响都是善的,有些人表现出的是善,但有些人却作恶为非;同样生活在一个坏的社会环境里,受到的教化影响都是坏的,但有些人却能“出污泥而不染”。这种现象表明,告子的性无善恶说虽然比其它四说经得起推敲,但如果不加区分地把任何人的人性都看做一样,也是有缺陷的。
古人虽然对人性善恶持论不一,但在重视后天教化这一点上还是一致的。不管人性如何,要想让人良善,就必须用良善的东西去教化影响。而教化必须从人幼小的时候抓起。
我认为,要解决人性善恶问题,必须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区分性和习,二是弄清什么叫善恶,三是不搞一刀切,要看到个人在人性上的差别。
“性”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是先天性的;“习”是在先天的“性”的基础上受后天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先天的东西无所谓善恶,不能用后天形成的善恶来评价先天的人性。通常所说的人性其实是“习”。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善恶其实是个伪命题。准确的命题应当是:“人习善恶”。
所谓善恶,是一种的道德评价。道德是人类社会交互作用中形成的关于人的行为规则和行为评价标准。何谓善?何谓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体系下道德标准。对于一个具体的问题,不同文化体系里,善恶评价不一样,甚至相反。譬如被好多假洋鬼子奉为民主楷模的西方国家,其实在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评价体系里不过是魔鬼而已。强盗似的哥伦布、麦哲伦之流,被西方人和被西方文化奴化了的中国人奉为英雄,而下西洋的郑和完全有能力做强盗却没有抢掠和殖民,至今还被号称精英的中国人所讥笑和诟病。英法等西方国家大肆贩卖黑奴的罪行,向其它国家武力倾销鸦片、杀戮掠夺和殖民的罪行,至今未见西方人反省认罪,而假洋鬼子们却甚而歌颂其功德!当年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流氓、强盗、冒险家等侵入美洲大陆,喊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印第安人等土著居民进行欺骗、掠夺,甚至进行种族灭绝式的排斥、屠杀,最后鸠占鹊巢,建立了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何曾见过把这些口号喊得更响的现代西方人(包括美国人)忏悔过?!何曾见过假洋鬼子们谴责过?!美国白人们倒是年年过所谓的“感恩节”,可他们感谢的不是原来曾帮助接纳他们的印第安人,而是他们所谓的“上帝”!为什么?因为在西方文化体系下的道德标准跟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下的道德标准不一样。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如匈奴,以抢掠他人财物为荣,其道德评价标准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下的道德标准相反。可见,我认为是善的,也许别人认为是恶的。我认为是恶的,别人却不认为是恶的。
其实,善恶评价标准取决于对于人的欲求的态度:适度抑制欲求,不使之泛滥就是善;放纵欲求,不择手段地去加以满足就是恶。“人之初”的欲求不过是求生本能而已,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超过“度”,所以无所谓善恶。
对于人性善恶之说,我认为,首先应当看到个人人性上的差异性。人性从内容上来看,都如白练素绢,空无印迹,无善也无恶。善恶皆在后天的濡染。但从受到濡染的倾向性或可能性上来说,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容易沾染恶的颜色。有些人则容易沾染善的颜色。这种对于善恶影响的接受度其实因人而异,很难截然分为三种或几种。但大体分为三品还是可以的。对于极个别的人来说,他们的质性决定了无法沾染恶的颜色而极易沾染善的颜色,这就是“圣人或上智”了。同样,对于极少数人而言,他们的质性决定了无法被善所濡染而极易被恶所濡染,这就是“恶人或下愚”了。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绝对正确。对于绝大多大多数人(中人)而言,他们对善恶的沾染都有一定的接受度,所以他们的善恶基本取决于后天的影响。当然,“中人” 对善恶沾染接受度是有差别的。这样就可以解释告子的人性无善恶论所难以回答的问题了。
人都有欲求,而且人类的欲求就其本性来说是得寸进尺且没有上限的。人人都希望自己的欲求能完全得到满足,有放纵欲求而向恶的倾向。向善发展,意味着必须适度抑制自己的欲求,这当然比较难;而向恶发展则很容易,只要你放纵自己的欲求就可以了。打个比方,人类生活像一条河流,善在上游,恶在下流。求善如逆水行舟,必须努力向上划动出船桨,稍有懈怠就会被水带动向下流跑。如果放弃向上划动,放舟中流,就会很容易很迅速地堕落下去。
最后,把我的基本看法简单归结为这样几点:
一、人性本无善恶而习有善恶;
二、极少数人本性或善或恶,后天对其几乎没有影响;
三、对于绝大多说人来说,其习的善恶取决于后天生活环境的影响,且有易于流于恶的倾向。
康德哲学思想深邃,博大精深,这是不言而喻的。人们每每谈起康德,总会不约而同的想到他的“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以及他著名的“三大批判”,但对于他在宗教哲学方面的研究,则常常被人们被人们忽略。而事实上,《纯粹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的问世,早就弥补了康德在宗教哲学方面的欠缺。通过这本书,康德系统的阐释了自己对于宗教的见解。而在康德的宗教哲学体系里,最重要的莫过于他对于人性善恶的探究。而这,也是康德宗教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一、康德对传统人性论中的善恶观的否定
从康德的角度来说,宗教存在的意义在于解决“我可以希望什么”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作为希望的主体的人的本性,继而对人的本性做出善与恶的评价。那么,人的本性,也就是人性,究竟是什么呢?按照通常的理解,“人的本性是指人身上与生俱来的、天赋的属性,而这种天赋的属性又往往是指人作为自然存在者所具有的自然本性。人们往往把人的各种自然本能、冲动和欲求,当作人的本性。”当然,康德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其次,传统的讨论里,关于人性善恶的说法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相信人的本性生来是善的,只是在后来受到某些恶的因素的影响而走向了堕落。但同时他们也相信只要我们愿意,与生俱来的这种向善的道德禀赋会帮助我们恢复善性;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世界是从恶向善不停顿的向前进步,因为在人的本性中可以发现这种进步的禀赋,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不太能迎合大众的想法。但这两种观点都在康德这里被推翻。康德认为:“如果我们说,人天生是善的,或者说人天生是恶的,这无非是意味着:人,而且是一般地作为人,包含着采纳善的准则或者采纳恶的(违背法则的)准则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无法探究的)原初根据。”而这个原初根据确实无法探究的。因为采纳是自由的,而我们在善与恶准则中进行选择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疑问,即“我为什么选择了善而非恶”或“我为什么采纳了恶的准则而非善”,如此一来,我们就还要为这个原初根据在寻找根据,继而难免陷入类似于还原论的怪圈中。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前两种观点在经验上的检验都存在困难。故而有人试图在人性的善恶性归属中找到一种调和,即认为人性可能没有绝对的善恶,就人的种族而言,人可能既非善也非恶,或者既是善的也是恶的,还可能是部分为善部分为恶。这种论断虽然改善了前两种观点过于绝对化和片面化的缺陷,但康德认为,“假如法则并没有在一个与它相关的行动中规定某人的任性,那么,就必然会有一个与它相反的动机对此人的任性发生影响;而且,由于这种情况在上述前提下只有通过此人把这一动机(因而也连同对道德法则的背离)纳入自己的准则才会发生,所以,此人的意念就道德法则而言绝不是中性的(绝不会不是二者中的任何一个,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同理,康德也否定了“既是善的也是恶的”和“部分是善的部分是恶的”的假设。
康德宗教哲学中的善恶观
康德认为,人与人性善恶的探究往往有两种路径,即从时间上探究善恶的起源和从逻辑上探究善恶的起源。前者属于传统人性论的探讨思路,康德认为这一方式存在一定的问题,故而他极力推崇从逻辑上寻找人性善恶的根源。其次,康德在探讨人性问题时,非常强调族类的观点,而非个人的特性。
康德对于人性中“向善的原初禀赋”的解读
在对善的讨论中,康德首先把这种原初禀赋与其目的相联系,作为人的规定性的三个要素,即“作为有生命的存在者,人具有动物性的禀赋;作为一种有生命同时又有理性的存在者,人具有人性的禀赋;作为有理性同时又能够负责任的存在者,人具有人格性的禀赋。”三种禀赋层层递进,从不以理性为根源进阶到以隶属于其他动机的理性为根源,最后发展为以无条件的立法的理性为根源,完成了人之为人的人格性的建构。需要注意的是,第一种禀赋可以嫁接本性粗野的恶习,如贪婪等;第二种禀赋可以嫁接文化的恶习,例如嫉妒、忘恩负义等;只有第三种人格禀赋,属于一种易于接受对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的纯然敬重的素质,也就是道德情感,在它之上是不能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
康德认为,人身上的这些禀赋本身不仅仅是善的,同时还是向善的禀赋,它们不仅不会与道德法则之间产生冲突,还能够促进人们遵从道德法则。
康德对于人性中“趋恶的倾向”的解读
康德所说的倾向,是指一种偏好的可能性的主观根据,与“一般人性完全是偶然的”相对立。与禀赋不同,倾向虽然也有可能是与生俱有的,却不可以被想象为与生俱有的。但另一方面,善的倾向可以被设想为是赢得的,本真恶或者道德上恶的倾向则是由人自己招致的。
同向善的原初禀赋一样,康德也把“趋恶的倾向”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人心在遵循已被接受的准则方面的软弱无力,或者说人的本性的脆弱;第二,把非道德的动机与道德的动机混为一谈的倾向(即使这可能是以善的意图并在善的准则之下发生的),既不纯正;第三,接受恶的准则的倾向,即人的本性或人心的恶劣。5康德认为,前两个层次里,人性表现出一种不作为或不纯粹,即使为恶,属于人心所犯的一种“无意之罪”,但是“人心的恶劣”则属于“有意之罪”。它将人心中道德的动机置于非道德的动机之后,造成了道德次序的颠倒,使得人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被败坏了。从康德的主张来说,这种恶是真正的恶。康德强调,即使是行动上表现的最好的人那里,也同样存在趋恶的倾向。
因此,综合看来,康德对于人性善恶问题的观点是:人天生是恶的,因为人的本性中具有与生俱来的恶的倾向。但是,又由于人天生具有“向善的原初禀赋”,因此,从应然层面来说,人本性应该为善。虽然有人斥责康德的这一论断,认为这样的想法太过理想主义而与现实脱节,但事实上,这种指责是错误的。康德并没有忘记在应然与事实两者之间寻找连结的纽带。他主张,直面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人心的败坏,重建人们本性里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
康德关于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主张
首先,康德指出,从逻辑上对人性的善恶进行探究虽然更根本,但是在现实中也存在一定的困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为人性的善恶属性寻找时间上的起源也是有可取之处的。继而,康德援引《圣经》中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因为受到蛇的引诱而偷食禁果,使得后世人类整个族群都因此而具有原罪的故事,康德认为人虽然因为外界的一些原因而陷入恶,但只要不是从根本上(即人的向善的原初禀赋)败坏了,就还是可以恢复善性的。换言之,只要人保有善良意志,就可以回到人曾经背离的那个代表了人的最高道德准则的善。
其次,康德强调原初的善就是要纯然出自义务地遵循个人在义务方面准则的圣洁性。而所谓的重建也正是要建立道德法则作为我们所有准则的最高根据的纯粹性。因此,人们如果想要回到原初的善,一方面必须坚定的遵循自己的义务,培养自己的德性,纯化个人行为的动机,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做一个善良的人;另一方面,人们要学会经常鼓励自己,增强自己对道德使命的崇高感,以唤醒个人的道德意念。这一行动可以压制把我们任性的准则中的动机颠倒过来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倾向,有利于在作为所有可被采纳的准则的最高条件的对法则的对法则的无条件敬重中,重建各种动机中的原初的道德秩序,继而以此为基础,重建人类心中向善禀赋的那样一种纯粹性。
再者,人类还可以借助宗教的力量,但是前提是,这种宗教必须是道德的宗教,而人们对它的求助也绝不能是单纯的祈祷,而是要在信仰宗教的基础之上,尽力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努力成为一个更加善良的人。
以上,是康德在《纯粹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对于人性善恶方面的解读。其实,总结来说,康德肯定人的趋恶的倾向,但同时也肯定人性本应该为善的理想状态。在人的善恶判定上,他是一个坚定的动机论者,提倡要肯定人们心灵上的善,而非从行为结果来判定善恶。对于人性的探讨构成了康德宗教哲学的基础。尽管后来的学者康德在宗教和人性方面的解读存在质疑,但就总体而言,康德的在宗教哲学方面的研究仍然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的,需要我们在以后的时间里更加深入的去学习和思考。
人性的善恶之辩在历史的长河中代表了地缘政治和皇家政权,善事育化万民福祉后世流传千古,恶是一种恶势力也是暴戾的象征祸及生灵涂炭遗臭万年,最典型的例子尧舜禹禅位,舜育化万民是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商纣*乱无度暴戾重重祸国殃民而江山毁于一旦,在人们心中对于一个人的看法最突出的就是善与恶的突出表现这是人的思想价值观所决定的。
柏拉图对人性善恶的看法
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