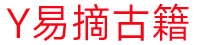性文化说

12月29日,阴。
阅读书目:《中国古代房内考》。
作者:高罗佩,是一位来自荷兰的外交官,他熟读各类中国典籍,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很深入的了解。在收集古代春宫图的过程中,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文化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对此进行深入研究。高罗佩在书中表示,当中文的著作对性避而不谈的时候,西方却对这个文化内容十分感兴趣,但是当时西方的很多书籍,对中国的性文化都有着很大的误解,所以他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西方人修正他们的认知。
金句:
1大众对于性的态度十分矛盾:人们一方面出于本能而对它感到好奇,另一方面,却又因为社会环境和道德标准而对它十分抵触。
2 清政府为了完成思想统治,禁封了所有与性相关的书籍资料,这种精神上的“阉割”,使得人们开始一边对性讳莫如深、惺惺作态,一边却又要竭力压抑内心的欲望。
3 也就是说,那时涉足青楼的男人们,其实是渴望与女性建立一种平等、自由的情感关系,他们的最终目的其实并不是与艺妓同床共枕,而是去享受一个优雅又自由的追求过程。
4 我们可以把明朝末年大量出现的色情小说,看作是中国人在性文化中最后的狂欢,随着明朝土崩瓦解,中国人的思想也受到了最严格的控制。
5 这段时间的思想控制,对中国的性文化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创伤。这个创伤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性观念,一直到现在,它也无法被时间完全抚平。
记录与感悟:清代以前,人们对性一直保持开放的态度,当时一些与性相关的文学作品可以自由流通。在这本《中国古代房内考》中,“性”不只具有生理上和生物学上的含义,还包括了男女之间的爱情、婚姻、社会关系和相处方式。作者高罗佩认为,只有当我们把“性”放在一个时代背景下,将它和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时,我们才可以全面充分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性文化。
一、女性在古代性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地
通过对殷王朝的文物考证,我们可以推测出,殷王朝曾是一个以女性为主导的母权制社会。在那一时期的古老神话中,妇女总是掌握着特殊的神力,她们常常是一些闺中秘术和神秘玄学的掌守人。同时,殷朝人认为女性是万物之母。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最古老的中国社会,女性的地位是很高的。
古代中国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正、负二重作用力掌控的,著名的古籍《易经》将这两种正、负作用力分别称为阴和阳。《易经》认为,男女之间的性行为是一切生命的起源,所以在《易经》当中,“一阴”一般用来指“一女”,而“一阳”则用来指“一男”。在“阴阳”这个词中,女性被排在了男性的前面,这也说明了,在古人的宗教信仰中,女性被排在了很重要的位置,她们在性方面的地位是要高于男性的。
道家学说提倡天人合一,无为胜有为。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一些人甚至摒弃了凡人的生活,希望通过冥想来与自然沟通。这一类人十分崇拜女性,他们认为女性更接近自然的原始力量。而崇尚道家思想的另一些人,希望通过修行,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这一类人也崇拜妇女,他们认为女性的身体中有着修炼仙丹不可缺少的元素。这两类人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对女性的崇拜却都是相同的。
道家学说是带有浓厚的母权制色彩的学说,而儒家学说则恰恰相反。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建立在父权制社会中的实用哲学,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女性的地位非常低下,男性是一家之长,而妇女的首要职责是服侍丈夫,把家务料理好,养育健康的男孩。儒家学说认为,女性应该首先发挥她们的生物功能,其次才能考虑感情生活和精神需求。
二、妓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处境以及这个职业的社会意义
妓女这个职业是从东周开始的。这一时期的王公贵族,除了拥有妻室之外,还豢养了其他的女性,这些女性被称作“女乐”。女乐会进行歌舞表演,并且与她们的主人以及宾客进行混乱的性行为。这些女乐就是官妓的前身。
汉代的宫廷中仍有成群的伎乐,不但如此,汉武帝还在军队当中设置了女营,让女子跟着士兵一起从征,这些女性被叫作“营妓”。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也开始出现妓院,这些私营的商业性妓院被叫作“倡楼”,也就是后来的“青楼”。
唐代的科举制度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这些考生一旦中试,就必须在皇宫东南边的妓院区设宴请客。这片妓院区中妓女们有等级之分,也要进行严格地职业技能训练。为了迎合年轻文人的喜好,这些艺妓们必须多才多艺,她们当中许多人都很擅长作诗。
唐代的科举制度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这些考生一旦中试,就必须在皇宫东南边的妓院区设宴请客。这片妓院区中妓女们有等级之分,也要进行严格地职业技能训练。为了迎合年轻文人的喜好,这些艺妓们必须多才多艺,她们当中许多人都很擅长作诗。唐代以后,妓女这个职业依然有所发展,并在明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虽然当时的首都迁往了北京,但是很多人还是愿意留在江南。当时南京最有名的妓院区叫做秦淮,很多学者、艺术家都会前来光顾。所以在秦淮,艺妓的艺术水准有了很大地提高,她们甚至发展了很多新的唱腔和演奏手法,这些技艺甚至到现在都十分流行。
妓女这个职业可以经久不衰是社会原因造成的,艺妓逐渐成为了人们社会交际中不可缺少的角色。人们在宴请宾客时,都需要有人表演歌舞,活跃气氛,而这种场合,又不允许妻妾参加,所以,只有艺妓可以来充当这样的角色。另一方面,那时很多人与艺妓交往,其实恰恰是为了逃避性生活,摆脱家庭中出于义务而不得不履行的性关系。也就是说,那时涉足青楼的男人们,其实是渴望与女性建立一种平等、自由的情感关系。
三、性文化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表现
古代中国人并不避讳讨论性,所以涉及到中国古代性文化的书籍有很多。在这么多古籍中,有一种类别的书,对古代社会的两性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一类书就是房中书。古代房中书对人们两性活动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十分详细的指导。同时,古代房中书还告诉人们,性行为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古代的性文化才呈现出一种健康的状态。
在周代的《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于求婚、爱情以及婚姻的描写。在同一时期的文学经典《左传》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古代婚嫁的小故事。到了汉朝,统治者决定推崇儒家思想,学者们将儒家的制度记录在《礼记》这本书当中,书中强调了儒家的家庭观念,并提出了两性隔离的原则。
唐朝是一个开放而包容的朝代,在这个历史时期,各类文学题材中都可以自由地讨论与性有关的内容。唐朝的一些作家喜欢在诗中加入一些有趣的性描写来逗乐,这种题材的文学作品为后来中国的色情文学开创了先河。
中国古代女性的缠足文化,是从宋代开始的。从那时起,女人的小脚成为了性魅力的象征。在此之后,几乎所有的两性文学,都以男子触碰女伴的脚来作为开端。在元代,消遣性的文学逐渐繁荣了起来,戏曲成为了文人最热衷的活动。有才华的文人们将爱中国古代女性的缠足文化,是从宋代开始的。从那时起,女人的小脚成为了性魅力的象征。在此之后,几乎所有的两性文学,都以男子触碰女伴的脚来作为开端。在元代,消遣性的文学逐渐繁荣了起来,戏曲成为了文人最热衷的活动。有才华的文人们将爱情故事改编成剧本,这其中,也参杂着一些华丽的关于性的描写。当时有两部最为著名的戏剧作品,那就是《西厢记》和《琵琶记》。
到了明朝,政治家们的思想控制更为严重,特别是明朝末年,压抑的文学氛围令很多人压抑不堪。来自明代末年最后的反抗,是一本叫做《金瓶梅》的色情小说。现代学者们一致认为,《金瓶梅》这部小说,不但具有很高文学价值,也有一定的社会学意义。
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很少被谈及的,因此古代的性文化是具有其独特的个性的,作者认为清代以前,人们对性一直保持开放的态度,当时一些与性相关的文学作品可以自由流通。个人认为并无确切史料予以支持,但在专制社会体制下,性总比政治话题更安全,虽不为儒家文化所喜,却无丧命之忧。作者并非国人,以其不同的视角观察探究,虽不全面,却实属难得。
张爱玲谈两性关系的一首诗句如下:
《爱》原文:
这是真的。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
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爱》赏析:
爱”这一永恒的主题,张爱玲仅以三百四十余字的袖珍篇幅,看似轻松地淡淡道来。语言洗尽铅华,单纯干净,全然没有她惯有的华丽绚烂。然而,一种不动声色的人生苦难和沧桑已被她轻轻地触及;而一份爱的无奈和哀痛也被她暗暗地激起,让人想想就忍不住要心酸落泪。
张爱玲小说的成就:
拓展了女性文学的新天地:
张爱玲的小说具有更为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远离主流话语,把眼光投向了“婚姻、爱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女性气息的世界”。其小说集《传奇》刻画了一大群真实地生存于男权文化之下的女性群像。
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
她摆脱主流文学的影响,用自己的传奇故事营造出一个政治之外的生活天地,把关怀的焦点放在普通人身上。于是,张爱玲非常重视继承写实小说的传统,摒弃了写实小说中常见的因果报应和教化宣传对小说形式的禁锢,以平淡、自然、真实的笔触摹画生活。
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
张爱玲是人物刻画的巧匠,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变态人物形象和各色人物,尤其是对两性心理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由此反映出人物心理的进展,体现了作者对人物丰富复杂内心的深切理解,揭示出某种社会根源。
明代小说的人物形象
从深层意义上说,文学史实际上是人的灵魂的历史。在此一角度上观察明代后期的通俗小说,我们似可清晰地把握到其中市民意识的崛起与人物形象的蜕变,这一从内在到外表的不断深化的流动轨迹。
这里所谓的市民意识是指市民的道德归依,人格理想,以及他的人生观,价值判断和审美理想;而人物形象蜕变,则是说传统通俗小说中一贯的理想性格和模式化的人物形象,至此有了突出的改变。
就社会历史发展的方面言,明代后期通俗小说中市民意识的崛起与人物形象的蜕变,是为其时都市商业经济繁荣所决定的。古代中国,从唐朝开始,城市经济就相当发达,到了宋代,一些大的城市已经相当繁荣。从柳永的一首《望海潮》之描绘里颇可见其时城市面貌之一斑:“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到了明朝,尤其是明代后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均发生了结构上的革命。于是以新兴商人为主体的城市市民作为一个较为庞大、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便出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行为特点和人生思想、价值判断以及感彩已然明确地标识出他们的独立和与既往其它社会阶层的不同。在此种时代的和社会的特定情况影响下,作为人的生活和情绪之的艺术载体——小说,便很自然地展现了这种思想意识领域的巨变,而其展现又恰好是通过其时的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人物形象来实现的。于是有明代后期通俗小说中市民意识的崛起和人物形象的蜕变。就小说发展史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拓展和更新。
中国古代小说在唐朝之前虽然在人物形象方面有一定的变化,但它基本上是在封建农业生产方式及其所决定的精神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实现和产生的,当然其中也有文学本身方面暨小说观念和美学思潮的演进,但后一因素的作用并不显著,到了宋明之际,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市民阶层崛起,这些社会因素却比较深刻和直接地作用于小说的创作。从而引起了小说的大变化,这些变化有的是创作主体的变化。即小说家由唐以前的文人才士群体,变为以俚儒野老为主体,而在通俗小说之创作方面更是如此。这一点,明人胡应麟曾有论及。他说:“小说,唐人以前,记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艳彩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少室山房笔丛》)冯梦龙也言:“食桃者不费杏,稀谷毳锦,唯时所适。……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斗,再欲捐金;怯者勇,*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涌《考经》《论语》,其惑人未必如是之捷目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古今小说叙》;有的是作家审美取向上的变化。如凌蒙初就说:“多采闾巷新事……语多俚近,意存劝讽”,进而指出“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鹬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初刻拍案惊奇序》)笑花主人也说,以“三言”为代表的拟话本小说“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极悲欢离合之致”,“故夫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古今奇观》序)。有的则是从创作题材上的变化。“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小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家也。“(清·罗浮居士语)
从上面的一些阐述可见,明代前后,通俗小说中从各个方面均开始向市民社会进入。
随着这些审美趣味上的、语言形式上的、作家取材上的变化,“通俗“这个直接指向市民阶层的小说理论主张也在明代后期被响亮地提出。通俗小说本是从民间艺人的说话发展而来,明代后期的拟话本则很好地继承起“说话”的传统。除将审美聚焦于市民阶层外,在语言和形式上又强调作品本身的通俗性。所谓“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
明代后期通俗小说的这些变化,反映在人物形上便造成了通俗小说中的市民意识的凸现和人物形象的蜕变。
二
明代后期言情小说所凸现出的市民意识,其内容较为复杂,它首先,也是主要地表现在其时通俗小说中的婚爱观念上。
爱情历来是人的心理世界中最富于情感力量,最能体现道德伦理规范与人性人情内在冲突的领域之一,这一点在妇女那里有更突出的体现。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施加于女性的钳制特别严酷。妇女不仅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而且在爱情婚姻上相对于男子总是处于依附的地位。就人生的价值取向而言,男子所追求的,有富贵仕途、建功立业;而妇女则几乎被剥夺了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方面的愿望和追求。她们的人生价值的寄托和实现,大多是靠婚姻及家庭,具体地说就是家长和丈夫的态度,这种极为偶然的机遇上。因之,作为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就是女性在心灵上形成对爱情的专注、执着而又惘然无助的悲剧感。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积淀,在封建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凝固、加强,从而演出了许多善良的心灵、美的精神被毁灭的悲剧。
这种情况的转变,期待着新的社会变动的契机。在爱情和婚姻领域中,解放的标志便是妇女从“物”的依附上升到人的独立,把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非人关系转变为情人人格相互对等和尊重的“人的关系”。这种解放,当然不是某些人的善良愿望所促成的;它首先是社会结构变迁,思想观念更新的结果。用这样的观点去考察话本、拟话本小说的人物,可以明晰地感受到市民阶层的意识中已经开始显现出解放的讯息,从而冲击着两性关系的封建扭曲。对
《卖油郎独占花魁》、《玉堂春落难逢夫》的描写是对这种市民意识出现的很好说明。作为一夫一妻制补充的卖*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不断。它以妇女的人格失落为沉重代价,赋予统治阶级于合法的婚姻之外随时发泄*欲的特权。《全唐诗》所录的妓女徐月荣《叙怀》云:“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虽然日逐人生寄,长羡荆钗与布裙。”很可说明这种制度给妇女的迫害;明王世贞《艺苑厄言》也记载了一首妇女诗,云:“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从遭污贞,抛掷到如今。”唐传奇《霍小玉传》等,更深入地揭示了妇女此一方面的心灵伤痕,以及他们为争取人的尊严所作的艰难斗争。艺术家的良心总是倾向于人间的不平与弱者的不幸。但封建压迫和礼教束缚却铸定了这种斗争的悲剧性。直到都市市民闯进了文学殿堂,才在这黑暗的地狱里闪起新的亮色。点燃解放的思想火花。这正如一个哲人所言:“封建的中世纪内部孕育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
上述两篇小说中的“独占”、“落难”,既是概括性的点题之笔,又提示了各篇情节开展和艺术结构所确定审美内涵。
《卖油郎独占花魁》设置了一组矛盾,三种力量。矛盾的两端,一端是沿街叫卖的小贩,另一端是临安城享有“天大的名声”的“花魁娘子”。前者本与豪门权贵所溷迹其中的风月场无缘,后者虽误落风尘,心怀从良,但也从未想到会与一个卖油郎结合。介入这组矛盾的第三种力量是“慕其容貌,都备着厚礼求见”的权门子弟。“独占”,以鲜明的竞争色彩,突现这场妓院情感角逐的最终胜利者竟是卖油郎秦重。无论是地位,还是财富,按封建社会品评人物的标准,秦重都明显处于劣势。那么,他究竟凭借什么力量来走完这方面的遥远距离,使得这悬殊的天平倾向于自己一方的呢?小说把握了历史和生活的逻辑,在日常生活的真实描写中,以形象的说服力,逐步地导向了这个喜剧的结局。
秦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与花魁相逢,为她的“容颜娇丽,体态轻盈”所倾倒。尽管封建礼教把合乎人的自然天性的心理压抑在地位卑微者深层的潜意识里,但一旦出现了异性的吸引,它仍然要顽强地表现出来。而且它的力度可以强烈到驱使人从非现实的条件中去竭力创造实现与倾心爱慕的对象亲近的机缘。为此秦重惨淡经营,苦行僧地趱积,一年有余,才凑足这可以与花魁娘子相见的见面钱――十几两银子。自尊心又使他做了另外一些弹精竭虑的准备,比如换上体面的衣服等。这些准备显示出卖油郎简直是怀着朝圣者的虔诚心理去仰慕、高攀花魁的青睐的。宿院之夜,花魁故意“一连吃上十来杯”,以十分轻慢的态度冷落他,而秦重却依然怀着爱美重美的纯净心地去对待这一切她,显然这已超出了一般意义的“怜香惜玉”和封建式的“坐怀不乱”。小说作者通过秦重彻夜不眠体贴入微地照顾了花魁的“病酒”这个独特的情节,从而将市民阶层的爱情意识作了生动的表现。特别是对卑贱者的精神情操高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表达了市民婚爱方面的审美意识。
花魁形象的塑造,亦包含着比较复杂的生活意识和新的审美观念。作家先把她放在居高临下的态势里对待秦重。这种态势是由于她“来往的都是大头儿”的环境决定的,但在灯红酒绿,低醉金迷的生活中,她并没有沉论。她后“哭了一日,茶饭不沾”,这既有贞操观念的影响,更有尊严和爱情受到了亵读的痛彻。侮辱彻底毁灭了她本来就感到屈辱和难堪的人生。只是在刘四妈开导她委曲求全,徐图从良之计,她才勉强随波逐流苟活下来。花魁的性格:一方面保持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心灵洁净;另方面也表现出了她久入鲍鱼之肆而不觉其臭的环境污染。后一点使她“从良”的视野局限于刘四妈为她圈定的范围里。只有当吴八公子施于她强暴与蹂躏时,她才真正彻悟,意识到风尘女子即使如自己是“才貌两全”,名噪京都的名妓,也只是贵客逢场作戏的玩偶。因此,她终于决心与秦重“布衣蔬食,举案齐眉”。在封建文化与市民文化的比较鉴别中,她看到了情感的真、道德的善,人性的美,存在于她所出生却陌生的市民的世界。作者将秦重境界以及它对花魁的感动和花魁的觉悟,作为市民精神美好的一面,作为净化与拯救挣扎于沉沦之中的灵魂的圣水,使得这篇作品在伦理与审美方面,突破了封建中世纪的禁锢,萌发了历史进步意义的审美的嫩芽。
《玉堂春落难逢夫》则从另一角度,即男子对于爱情的看重和珍惜,助长了这一嫩芽。
三
市民阶层的人生价值观和道德审美判断。是明代后期通俗小说所表现的市民意识之又一方面。这首先在《施润泽滩阙遇友》所塑造的手工业者施复的过程中,有突出的表现。该篇是中国古典小说于长期徘徊于封建社会的灰暗程途中闪现出新的曙色。千百年“重本抑末”的传统思想,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悄悄地改变着它的走向。另一方面,历史的惯性力量,仍然把人们的情绪凝结于安土重迁的心理建构之中。这正如《杨八老越国逢奇》所写到的那样:“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男儿远游虽得意,不如骨肉长相聚”这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变动的不适应。然而,文明的演进,又引导一些人把眼光投向新的天地。施复便是其中的一个,此外《初刻拍案惊奇》中《乌将定一饭必酬》的头回所写的苏州王生也大率如此。王生出生于经商世家,几次出外贩货均遭抢劫,他心灰意冷,无意再远出了,而他的婶母却一再劝他“不可因此两番,堕了家传世业”。这种“重商”风气的兴起,与人生价值取向的转变逐渐汇合。就使得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念发生了动摇,所以虽然“唯有读书高”还被奉为正统地圭臬,但同时也有一些人认为“经商亦产善业,不是贱流。”而且徽州风俗,甚至“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
作家正是从这历史的变革中,实现了审美意识和人生价值观的更新。在这种新的思想意识光照下,人物的行为、心理、道德,以及围绕着他们的生活环境,都融进了新质。施复的家乡盛译镇,商业熙攘繁荣,与此相谐,小说主人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反映着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变迁。施复偶拾几两银子,他欣喜异常,且围绕着财富追求对这几两银子作商业上的精打细算。它触及了商品和货币对个体劳动者的心理冲击所激发的扩大生产。发展家业的强烈驱动力。然而施复毕竟不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在长期劳动生涯实践中所形成的道德准则,不允许他损害如同他一样处境的辛苦善良的人们。这一方面显示了施复对富人的冷漠甚至敌视,另一方面他深挚的同情又倾向于“苦持过日”的同一阶层的兄弟。在他的想象里,出现了他们一目断绝了这“养命之根”可能酿成的种种惨象,这种沉重的内疚和自我遣责的折磨,他是不堪承受的。他宁愿舍弃进一步“营运发迹”的机遇,以求得良心的平静。基于人类同情心,特别是对下层不幸人们的关注,使施复的精神臻于道德的善和人性的美的境界。这种善和美,并不带有惊心动魄的英雄壮举,而是展示一个平凡而真实的人生情景,发掘一个市民的质朴的心理感受,是市民阶层理想道德的标本。作品还通过比较鉴别式的议论:“衣冠君子中,多有见利忘义的,不竟愚夫愚妇到有这等见识。”表现出市民道德的归依和小说文学中崭露头角的市民阶层审美意蕴的光彩
四
与上一点的表现有所关联的是,平中求奇之审美趣味作为民意识的又一表现,在当时也有突出的表露。时至明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和思潮的变化,作为小说创作作者的小说家和接受小说的市民群众,都对平凡日常生活中的奇特表现出浓郁的兴趣,平中之奇作为一种欣赏趣味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倾向。如睡乡居士就说:
今小说之行世者无滤百种,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舍目前可纪之事,而驰 于不论不议不乡,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魅者,曰:“吾以骇听而止耳。”夫刘越石清吹笳,尚能使群胡流涕,解围而去。今举物态人情,恣其点染,而不能使人欲歌欲泣于其间。此非奇与非奇,因不待智者而后知之也(《二刻拍案惊奇序》)
这种平中求奇的审美趣味,不惟使一些作家自觉地在小说创作中落实,如凌氵蒙初就在此一审美趣味之作用下,“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凡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拍案惊奇序》)同时还作为一种鉴赏标准为部分小说批评家所提倡。姑苏笑花主人在其《今古奇观序》中即说:
吾安知闾阎之务不通于廊庙,稗秕之语不符于正史?若作吞刀吐火、冬雷夏冰例观,是引人云雾,全无是处,吾以望之善读小说者。
小说家的这一审美趣味在其时夫妻离合小说中亦有所体现,如《石点头》卷十入话所云:
还有一说,或者(夫妻)分离之后,思断义绝,再无完聚日子,倒也是个平常之事,不足为奇。惟有姻缘未断,后来还依旧成双的,可不是个新闻?
凌氵蒙初在改编《芙蓉屏记》时更说:
这美中不足处,那王夫人虽是所遭不幸,却与人为妾,已失了身,又不曾查得奸人跟脚出,报得冤仇,又重会了夫妻,这个话本好听。(《拍案惊奇》卷二十七入话)
这个颇有在平中求奇上竞长争高的意味了。
五
如上所述,明代后期市民阶层的独立,及其意识的崛起,有些是通过通俗小说来表现的,而该类小说在表现这一内容时,又主要是通过其中的人物形象来完成。因此,与前一时期相比,明代后期通俗小说一个极显著的不同,便是其中人物形象的蜕变,即是由此前的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江湖好汉,为主体,嬗变为以平民百姓中的工商士农和旷男怨女,烈妇节夫为主体。
性文化说
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