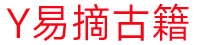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

B 天人合一排除
其实说句实话,古人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生态平衡问题,这有点牵强附会,天人合一其实是道家修仙的思想,但是好歹讲究个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能沾点边,以中国人自吹自擂的心理可以牵强附会。
至于a自然崇拜那是比较原始的崇拜,其所涉足的是宗教信仰或封建迷信,与生态平衡挨不上c中庸学说,是搞政治搞人生更不沾边,d众生平等是佛家思想,似乎很贴近生态平衡,但是很多佛家信徒,不顾生态平衡,胡乱放生,的事实说明,其众生平等是没有从生态平衡的角度出发的,是一种纯粹的慈悲老好人角度出发的。
论文摘要:本文从“行为规范”、“精神实质”和“生态智慧”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加以分析和阐述,指出在“行为规范”方面,儒家所主张的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精神实质”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道德理性,而对环境保护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的生态智慧,则是儒家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儒家 生态伦理 思想 0引言 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援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援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援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宗教信仰,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生态智慧”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做的充分认识和睿智选择。 1顺应自然、禁弛有秩的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体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日:“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日:“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日寸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络起来的趋向,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中的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刨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与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 对这些“时禁”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如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极性的限制。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式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自身就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第三,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地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可以设想,在儒家那里,在行为规范的方向上,除了人类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这样一个推爱的圆圈,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由动物、植物到自然山川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关怀圆圈,前一个圆圈又优先于后一个圆圈。 2“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精神实质 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就表明了人融自然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而从人性,从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人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人”,在此人是主动的,但却不是僭越的。一般在这样的场合,亦不专提“天”,而是说“天地”。单提“天”时有最高主宰,规律或命运的意思,而说“天地”则一般是指包容万物的大自然。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宋儒进而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 鉴于当代生态哲学中的争论,我们如果问: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从前面的叙述看,儒家行为规范方面是紧密联络人事或主要考虑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劝诫的意味:而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独立的宇宙哲学,它是与一种人生哲学联络在一起的,并以后者为重心的道德理性。 3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 人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是集中表现在人的发展上,如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提高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等等。但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说明了天地人之间法则的相通,而这种法则并非以人为依归,而是以天地、自然为依归。儒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在本源上是相同的,自然与人类也是平等的关系,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儒家主张,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的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自然地得到发展,而不横加干涉;人类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存,就应与天地万物保持和谐。这样,才不会扼杀宇宙的生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对自然界过分掠夺,势必危害人类自身。儒家文化还把万物是否“皆得生息”。也就是环境是否处于自然状态看作是否富足的标志,“天以万物悉生出为富足”,非常强调保护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应该说,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进行过分掠夺而没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造成的,它正在破坏着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平衡发展的辩证关系。要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矛盾状态,维护生态平衡,解决人类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我们当然要依靠今天的高科技手段,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利用价值。
中国,是一个拥有灿烂文化和丰富资源的古老国度,在发展的过程中,总结出了自己一套关于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环保理论和实践,并且深刻影响着今天的环保工作。
一,古代人的朴素环保思想
1,源于自然崇拜的生态观念
在远古时期,由于人类生产力量的限制,很多的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大自然。这个时候,讲究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自然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而人类对于大自然的依赖程度很高。
在当时,人类对于自然的理解是“神秘的力量”,将自然视为神明,进而产生了对于大自然的崇拜和敬重。
同时,由于当时人类科学技术和理论知识的欠缺,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解释一些问题,将自然中的“打雷”“闪电”看作是一种神明对于人类的惩罚,从而对自然产生了一系列的畏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自然禁忌。这种自然禁忌就变成了大家都要去遵守的条款和条约,用来约束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行为。
这个时期,神话传说成为了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实践中的理想追求,也反映了古人对于自然和人类和谐关系的理解。
在“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人心中,不仅有改造自然的朴素愿望,还有古人在长期劳动和生产中体会到的人与自然的相对独立性。自然不依赖于人类而独立存在,而人类则不能脱离自然而独立生存,讲究的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2,“天人合一”的思想
在古代环保工作中,“天人合一”是最重要的环保观念,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天人合一”讲究的是尊重自然,善待万物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念。主要包含着两个层次:
第一,在《易经》中,有这样的思想:“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人类从宇宙中演变而来,需要依赖于自然环境而生存发展;
第二,儒家讲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人类要生存,就需要将自然放在和人类同等重要的地位,将它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讲究社会活动中需要善待自然,对万事万物需要用仁德之心对待。
“天人合一”是中国最基本的传统思想,也反映了古代传统思想最深层次的观念,是古人朴素的生态理论和环保观念,为中国的环保工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跨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3,道法自然
在《道德经》中,有这样的哲学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意思是 "道"所反映出来的规律是 "自然而然" 的。老子用了一气贯通的方法,将天、地、人乃至整个宇宙的生命规律精辟涵括、阐述了出来,告诉我们需要尊重自然法则,不得违背自然规律。
在道家的思想中,“天道”和“人道”是一个整体,而“道”是天地之根本,万物之源泉,自然万物从本源上就有着统一性,人类也要以“道”作为出发点去对待世间万物。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道,天,地,人是一个完整的生态链,打破其中任意一环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自然界的和谐运转,而作为其中一环的“人”,也需要遵守生态中的生存思想,以遵循自然为前提,不得逾越,打破自然和谐。
二,中国古代的环保举措
1,环保部门和机构设置
在古代,不仅有着深刻而成熟的环保思想,也有付诸实施的环保工作和官职。在很多朝代中,都有虞,衡的官职。
中国最早的环保机构则是大舜设置的“虞”,在《尚书·舜典》中有这样的记载: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 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 ”
益就是中国最早的环保官员,后来还设置了大司徒和虞部下大夫;
到了秦朝,环保部门为少府,少府下还设置有林官,湖官,破官和苑官,而大汉朝也承袭了秦朝的旧制,环保机构改成了水衡都尉,而东汉的司空一职也是针对环保部门的官员,司空“掌水土事”。三者各司其职,地位相等,无轻重之分。
到了唐宋以后,虞,衡的官职权力有所扩大,在《旧唐书·职官》中这样记载:
“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戈猎采捕。”
中国环保机构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机构和职责不断清晰的变化过程,虽然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不失为古人对环保事业的探索发展的贡献。
2,环保法律
古人们不仅设置环保相关的职位,还有相关的立法来保障环保事业配套的实践。
在夏禹时期,曾经有禁令,据《逸周书·大聚解》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以成鱼鳖之长”。
用具体的政策来落实环保工作的实施,约束人们对自然行为的破坏;
殷商时期,有了“弃灰之法”,西周时期曾颁布《崇伐令》:
“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表现了统治者对于环保事业的重视和对自然地尊崇。
在周朝统治期间,以“以德配天”的主要思想下,“礼”在约束人们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后来的朝代中,不仅是秦朝的《田律》,还是唐朝的《唐律》,关于环保的问题都有相关的规定,且逐渐趋于完整。包括在明清等很多朝代,立法也都是沿袭了前朝的相关环保法律,对于当时的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国家安定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于我们今天应对和解决环保问题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生态思想即是指自己所布局的要讲究生态平衡,齐头并进。 不能为了这,而牺牲那,好比为了发展污染了环境,到头来还得在倒贴钱去治理环境,生态即自然。 在商业上的布局,讲究生态系统性的建设,是富有远见的观念。
扩展资料:
生态思想的几个观念:
1、整体的观念
是说生物与其环境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生物均不能脱离环境而单独存在;
2、循环的观念
是指作为生产者的植物、消费者的动物、分解者的微生物,它们互相耦合,形成由生产、消费和分解三个环节构成的无废弃物的物质循环;
3、平衡的观念
认为生物之间的食物链关系、金字塔结构和循环体系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之中;
多样性的观念,即“多样性导致稳定性”的生态原理,它强调保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认为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直接威胁着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传统生态思想的核心价值观是天人合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人与自然关系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命题。如何把握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和思维模式,是认识和理解传统生态思想的关键。正是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辨和追问中,奠定了传统生态思想发展的基础和脉络。
扩展资料:
传统生态思想的核心价值观是“天人合一”的原因:
1、天人合一是传统生态思想的核心价值观。
天人合一强调物我一体,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追求天地人的整体和谐。这里的“天”是自然之天,包含“天道”、“天意”、“天命”、“最高主宰”、“客观规律”等含义。
2、追求主客观世界的和谐与平衡是传统生态思想的伦理体现。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平衡,通过人与物之间的和谐从而促进和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体现。它要求人们关爱自然,关心人之外的事物,不断赋予客观世界的主体性特征。
3、遵从自然规律、强调强本节用是传统生态思想的重要内容。
中国长期以来都是农业社会,以农耕方式为主、以农为本,农业生产成为国家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而农业主要“靠天吃饭”,农业生产受到天气、土地、环境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必须要遵从自然规律,与自然节拍相符合。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是以时代精神的主旋律为根据的,离开时代精神,也就无所谓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伴随着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形成的,但这并不能据此论定我们的祖先没有生态伦理意识。先秦儒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十分注意总结自然界的规律,在保护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1、先秦儒家的生态自觉意识
先秦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来源之一,一个基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生态伦理学是建立在自觉地对生态学的科学认知的基础上。
先秦儒家认识到单个生物物种的存在是不可能的,生物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要以种群的方式进行,他们对自然界生命系统的组织层次的认识,是用“类”、“群”、“畴”等概念来表达的。
长沮、莱溺,辐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授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忧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鸟兽不可与同群”说的是鸟兽分属于不同的群。他还从生态学上提出了“类”的概念。孔子曾说:“丘闻之也,剖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荀子也说:“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草木畴生,禽兽群也,物各从其类也”。荀子已经把植物草木和动物禽兽区分为生物系统中的两种不同的类,并且认识到草木以“丛”的形式生长,禽兽以“群”类的方式存活,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先秦儒家对生物及其环境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这些都指出生物的生存离不开一定的环境,环境决定生物的存在。先秦儒家在关注环境的同时还注意到了生物之间存在着的食物链的关系。“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即草木为动物提供了食物,而当动物的数量减少时,植物就会茂密地生长。
在农业社会条件下,先秦儒家对时间结构中的季节规律尤为重视,他们用“时”来反映和概括生态学的季节规律,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认识。“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滋基,不如待时”。这就是说,作为条件和环境的生态学季节规律的“时”是不可超越的。因此,先秦儒家以“时”为媒介将人和自然联络起来,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要求人们根据季节的变化来合理地安排获取自然资源的活动。“挎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
2、“天人相分”—改造自然的依据
人类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去参与自然的创造和化育过程,使得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荀子称这种能动性和创造性为“制天命而用之”。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在荀子看来,与其高喊“惟天为大”而仰慕它,不如把天看作自然的物质而控制它;与其“顺天”、“从天”而歌颂它,不如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与其仰望天时而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因时制宜地利用天时;与其消极地听任物类的自然增多,不如积极地施展人的才能而促进物类的化育繁殖。因此,他认为只要发挥“人治”的作用,善于经营管理,就能提高生产,增加收获。
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荆车;雹笼鱼鳖鳅鳗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亮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
先秦儒家认为,作为自然之天,它的存在变化具有自身的某种特定的规律性,“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所谓“故”,即是指自然界的规律。因为自然界有“故”,所似人可以通过对自然界所获得的某种规律性进行类推,由近及远,由古及今,得到更多的更广泛的认识。但在他们看来,自然的规律是客观的,并不取决于人的意志,“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柴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对自然界的这种客观规律,人们只有遵循它才能取得好的结果,“应之以治则吉”,如果违背它,就要遭殃,“应之以乱则凶”。
3、“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矛盾统一
“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生态伦理学价值就在于它们不仅为儒家的生态伦理学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且为现代生态伦理学提供了一种哲学构架—人与自然和谐、协调、一致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这正是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所缺乏的东西。“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不仅是克服人类中心论顽症的一剂猛药,而且是从生态中心论过渡到生态协调论的一副良性的催化剂,是从现代工业文明过渡到后现代的“桥梁”。事实上,只有将“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互补起来,才能为生态伦理学提供科学的哲学基础。
“天人合一”要求在处理人类和生态环境关系上追求和谐、圆润、统一的境界。人不仅与自然平等,而且与自然浑然一体。世界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是不可言说的,不可思议的,其中根本就没有差别。人与世界万物,只是在一定认识层次上差别,而在更高层次上彼此相融,无法分别,即哲学所谓“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认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仁”作为人的道德本性,要求视人如己,视物如我,以合内外,以天下的“廓然大公”为至境和理想。一个人作彼此、内外之分,把物我、天人隔绝开来,对他人的痛痒漠不关心,这就是“不仁”,即道德本性的丧失,其根源在于有“私”。一个人的行为受道德理性的支配而出于公,就能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凡利于天下事,则为之;凡害于天下事,则弃之。这一观念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则必然要求人以整体生存为目的,而不仅仅只顾及个体的、区域性的、眼前的利益。
然而,现在有一种倾向,把“天人合一”抬得高而又高,把“天人相分”贬得低而又低,似乎“天人合一”是拯救人类命运的不二法门,而“天人相分”则是造成生态环境危机的罪魁祸首。应该看到,征服自然与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不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从根本上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改造自然而禽兽不能。墨子说人是“赖其力而生”,荀子说人能“制天命而用之”,可使“牛马为用”,所以才最为天下贵,“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改造自然也就是对自然的征服,也可以说征服自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没有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就没有人类的文明。事实上,人与自然本来既有合的一面又有分的一面,没有“天人相分”的“天人合一”是不健全的,“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是互补的矛盾统一体。
4、“天人合一”—维护生态的依据
先秦儒家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了天人和谐、均衡、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并提出了“仁民而爱物”的观点。“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概念,是人类道德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原则,它虽然始于爱亲,但并不终于亲,甚至于要超出亲情的范围来“泛爱众”,并最终将爱心推及最广大的万物。“仁民而爱物”的思想是将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推广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仁爱的精神和情感贯注于自然万物。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在这里阐述了仁的层次性,即对于“亲”、“民”、“物”三种不同层次的物件,应该采取相应的程度不同的态度—“亲”、“仁”、“爱”,也就是说,对亲人要“亲”,对民众要“仁”,对万物要“爱”。这三步自成系统,是先秦儒家仁爱思想的逻辑展开。而这正是人类道德情感投射于外物的表现,在他们看来,动物存在着与人相似的道德情感,所有动物对自己的种群都具有一种天生的情感,当自己的同伴受到伤害时,它们都会流露出一种同情心,而当自己的同伴死亡时,它们都会发出撕人心肺的哀鸣:
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反沿。过故乡,则必排徊焉,鸣号焉,娜蜀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扰有惆憔之顷焉,然后能去之。
动物尚且对同类的不幸遭遇具有悲哀和同情之心,人类则更应该自觉地禁止这种伤害动物的行为,保证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孟子甚至认为人固有一种爱护生命的侧隐之心: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休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这种被称为“侧隐之心”的同情心,不是后天的思虑所得,乃是先天的本能,是人天生的对生命的同情之能力,人与人正是凭此得以感通。
“仁民而爱物”的实际内容就是将自然保护作为落脚点。先秦儒家在人类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认识到自然是人类的生存的根本。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虎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
在这里,荀子和孟子充分肯定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的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基于天之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从持续发展、永续利用原则出发,先秦儒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针对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保护措施: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雹尾鱼鳖鳅鳝孕别之时,周苦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尤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苦不入垮池,鱼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这里先秦儒家明确提出了重视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根本目的是为了“利国富民”,甚至把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同国家政治联络起来,认为这是王道政治的起点,是同“养生丧死”息息相关的大事。而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季节规律,即按照四季来安排“时禁”和“时弛”是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手段,并且认识到保护自然资源就是要注重资源的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即“不夭其生,不绝其长。”
试析道教劝善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道教劝善书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教化书,其中所述的伦理道德规范不仅用以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进一步推广到调节人与动植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主张自然界生命的平等性,倡导“贵生”的生命情怀,提出“是道则进,非道则退”的生态伦理行为准则,从而形成了具有神学特征的以生命为中心的生态伦理观。
关键词: 道教;劝善书;生态伦理
Abstract: Instructions on morality in Taoism has served as a guidebook on moral integrity The moral disciplines discussed in the book can not only be used to regulat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ace and between human race and the world, but also can be extend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ace and plants, animals, human being and nature The instructions stress the equality of all the living beings, promote the value of life, and put forward the law of ecological ethics that the world progresses if everything accords with the way of the world, and go backward if not These help to form the life-oriented ecological ethics with theological flavor
Key words: Taoism; instructions on morality; ecological ethics
现存于《道藏》、《藏外道书》中的道教劝善书主要有《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十戒功过格》、《警世功过格》、《石音夫功过格》等。有学者将道教劝善书界定为“一种宗教的伦理教化书”,认为它是假托神仙的名义制作或道教徒以个人名义撰著的、从道教神学的角度运用道教教义劝人去恶从善以成仙了道和积善获福的通俗道德教化书。[ ]关于道教劝善书,已有一些学者从伦理学的角度作过专门的研究。本文侧重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并且认为,道教劝善书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教化书,其中所述的伦理道德规范不仅用以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进一步推广到调节人与动植物、人与自然的关系,蕴含着具有神学特征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从道德教化到生态伦理
道教劝善书的根本宗旨在于劝人行善积德、去恶从善,即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道教劝善书中所说的“善”和“恶”,不是理论上的抽象界定,而是较多地表现为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和守则。《太上感应篇》[ ]是北宋末年出现的最早的道教劝善书,其中所列举的善行有:“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已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等二十多条,恶行有:“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诳诸无识;谤诸同学;虚诬诈伪;攻讦宗亲”等一百多条。此后的道教劝善书大致仿效这一模式。
然而,道教劝善书在罗列其所认定的善行和恶行时,也把保护动植物看作是善行,把伤害动植物看作是恶行。比如《太上感应篇》中就明确提到“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对于该篇列举的善行中所谓“慈心于物”,《太上感应篇图说》注:“隐恻矜恤于物,谓之仁。如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启蛰不杀、方长不折之类。”[ ]可见,“慈心于物”的“物”主要是指动植物,“慈心于物”就是要施仁于动植物,就是要保护、关爱动植物。《太上感应篇》所列举的恶行中则明确提到“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用药杀树”,“春月燎猎”,“无故杀龟打蛇”,认为伤害动植物也属于恶行之列。约成书于元代的道教劝善书《文昌帝君阴骘文》[ ]教人要“救蚁”,“济涸辙之鱼”,“救密罗之雀”,“或买物而放生,或持斋而戒杀,举步常看虫蚁,禁火莫烧山林……勿登山而网禽鸟,勿临水而毒鱼虾”,等等。还有明代的道教劝善书《关圣帝君觉世真经》[ ]也教人要“戒杀放生”,“利物救民”,反对“宰杀牛犬”。显然都是把保护动植物看作善举,把伤害动植物视为恶行。
功过格是道士自记善恶功过的一种簿册,属于道教劝善书之一类,其中也列举了保护和伤害动植物的善恶功过。南宋时期出现的《太微仙君功过格》[ ]是现存最早的功过格,有“功格三十六条”,“过律三十九条”。在“功格三十六条”之下有“救济门十二条”,包括救助野兽、牲畜以及“虫蚁飞蛾湿生之类”,在“过律三十九条”有“不仁门十五条”,包括“害一切众生禽畜性命”以及杀“飞禽走兽之类”、“虫蚁飞蛾湿生之属”、“恶兽毒虫”。后来的《十戒功过格》[ ]有“一戒杀”、“二戒盗”、“三戒*”、“四戒恶口”、“五戒两舌”、“六戒绮语”、“七戒妄语”、“八戒贪”、“九戒嗔”、“十戒痴”。其中的“戒杀”包括戒杀“微命”、“小命”、“大命”和“人命”;“微命”,如蚊蝇蚤虱、蟋蟀蝴蝶之类,“小命”,如蛇虺獾雉鸡鹅、八哥画眉鹌鹑之类,“大命”,如虎狼獐鹿猢狲、牛马猪羊之类。显然,这些功过格都包含了保护动物的要求。
一般说来,伦理道德规范是用以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然而,道教劝善书所述的伦理道德规范除了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外,还进一步推广到调节人与动植物的关系,广义地说,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也包含了生态伦理的内容。
当然,在道教劝善书所涉及的道德规范中,“忠”、“孝”是最为根本的,卿希泰先生说:“忠孝之道是各色劝善书不惜笔墨提倡的,各种道德义务和善行中忠孝居首位。”[ ]而且,在道教劝善书中,涉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规范和守则,无论从其数量上还是在其重要程度上,都在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规范之上。但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规范和守则毕竟包含于道教劝善书之中,是道教劝善书进行教化的内容之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一些功过格中,“功”和“过”的大小被量化。以《十戒功过格》为例,无故杀有功于世之畜(如牛马驼象之类),一命为五十过,救一有功于世之物,为五十功;与此相比较,因医术不精误用药物而致伤人命,一命为五十过,力救一被焚被溺者为五十功;谋人产业夺人生理者,一事为五十过,设法广募泽可远布者,一事为五十功。再比如《警世功过格》,救一有力于人之物命(牛马犬类),五功至五十功,而免一贫人债,十功至五十功;毒药杀鱼三十过,谎骗财物三十过。通过这些定量化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功过格中,保护或伤害动物的“功”或“过”还是比较大的,因而有关保护动植物的教化也是较为重要的。
在中国古代,把保护动植物当作善行,把伤害动植物看作是恶行,可以追溯到 春秋战国 时期。《论语•述而》讲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礼记•祭义》记:“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孔子曰:“开蛰不杀则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孟子则要求“仁民而爱物”[ ],汉代的董仲舒也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 ]后来的张载则进一步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在道教史上,早在《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道教的主要经典《太平经》就说:“夫天道恶杀而好生,蠕动之属皆有知,无轻杀伤用之也。”[ ]魏晋时期的葛洪说:“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而不可“弹射飞鸟,刳胎破卵,春夏燎猎”,等等。[ ]五代时的谭峭说:“夫禽兽之于人也何异?有巢穴之居,有夫妇之配,有父子之性,有生死之情。鸟反哺,仁也;隼悯胎,义也;蜂有君,礼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孰究其道?万物之中五常百行无所不有也,而教之为纲罟,使之务畋渔。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夺其亲爱,非义也;以斯为享,非礼也;教民残暴,非智也;使万物怀疑,非信也。”[ ]
显然,在道教劝善书出现之前,已有不少思想家,包括道教学者,已经从一般的伦理道德中引申出生态伦理,将保护动植物当作重要的道德规范。应当说,道教劝善书的生态伦理思想正是对于前人,主要是道教学者的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二。以生命为中心的生态伦理观
道教劝善书的生态伦理思想虽然是从一般的伦理道德中引申出来的,但同时也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形成了基本的生态伦理观。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道教劝善书的生态伦理观的基础是自然界生命的平等性。
对于《太上感应篇》所谓“慈心于物”,有郑清之赞曰:“万物同体,均受于天。……肖翘蠕动,皆在所怜。视物犹己,仁术乃全。”认为自然物与人是平等的。李昌龄在为《太上感应篇》“射飞”作注时说:“太上曰:混沌既分,天地乃位;清气为天,浊气为地;阳精为日,阴精为月,日月之精为星辰;和气为人,傍气为兽,薄气为禽,繁气为虫。种类相因,会合生育,随其业报,各有因缘。然则,人之与飞有以异乎?肇论所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非诳语也。”认为人与自然物都是天地所产生的,为同根所生。
在道教劝善书看来,自然界生命的平等性不仅在于人与自然物的同根而生,而且,自然物与人一样都具有灵性。李昌龄注释《太上感应篇》“用药杀树”时说:“树木中亦有圣人托生其中,如《水经》所载伊尹生于空桑是也;又有修行错路精神飞入其中,如《业报经》所谓韩元寿化为木精是也;又有中含灵性无异于人,如钱师愈所斫松根是也;又有窃树起祸而先为树神所知,如钱仁伉所窃牡丹是也。”
此外,道教劝善书还认为,自然物与人一样还有知。《十戒功过格》“戒杀”中把动物分为“微命”、“小命”、“大命”,其中“微命”即所谓“一切生物之最蠢者”,“小命”即所谓“微有知者”,“大命”即所谓“大有知者”。认为自然界的动物都有知,只是有大小的区别。
第二,道教劝善书要求保护动植物包含了“贵生”的生命情怀。
道教重视人的生命,《太平经》卷一百十四《不用书言命不全诀》说:“要当重生,生为第一”,《度人经》讲“仙道贵生,无量度人”,司马承祯的《坐忘论》讲“人之所贵者,生”。同时,在道教看来,自然界的一切生命是平等的,所以,道教对于人的生命的重视,又进一步扩展到对自然界一切生命的重视,这样也就把对于人的生命的情感投射到自然界的一切生物,形成了普遍的“贵生”的生命情怀。
李昌龄在注《太上感应篇》“慈心于物”时说:“慈为万善之本。”认为对于一切生命的慈爱是善的根本。所以对待动植物,要戒杀,要放生,要救助,甚至不要惊扰他们。李昌龄注《太上感应篇》“惊栖”时说:“太上戒人无得惊栖,与孔子弋不射宿之说意皆一也。大抵鸟之已栖亦犹人之已寝,忽然有惊,岂不举家惊扰?”该注释还以李奚子、陈安世二人为例:“李奚子本一山妪,每遇大雪,鸟无安枝,徃徃飞集其家,遂留不去,妪济以谷,且不敢惊”;“陈安世本权叔本家一佣力人,平生不践生虫,不杀物命,每出入见飞禽当道,必下道引避,不欲惊之”。
同时,道教劝善书对于动物的描述往往还赋予了人的情感。《太上感应篇集注》在注释“射飞逐走”时举二例:其一,“镇江钱叅将部下卒获一雁笼之舟尾,空中有一雁随舟悲号;将登岸,笼中雁伸颈向外大呼,空中雁忽下,二雁以颈相交而死”;其二,“河南潘柽好猎,入山见一老猴,发弩射之。初发为猴所接,再发中臂。度不能支,遂抱其子乳之,复摘木叶数片,盛余乳在傍,大号而死”。然后接着说:“由此二事观之,一切禽兽皆有人性,皆有眷属。或飞或走,射而逐之,如人离家出游,路被杀害,妻子盼望,其惨何如。”[ ]最后,还引一诗云:“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这一诗句是各种道教劝善书所经常引述的;它用极富感染力的手法赋予动物以人所具有的各种情感,并表现出对受伤害动物的极大同情。
应当说,道教劝善书提出要保护动植物,是带着深厚感情的,带有一种对于生命的普遍的慈悲和怜悯之心,要求以“贵生”的情怀去善待一切生命。
第三,道教劝善书所追求的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
道教劝善书讲保护动植物,不是一味地盲目的保护,而是要依照自然规律,这就是“道”。人要以动植物作为生活资料的来源,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但是必须按照自然之道行事,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这就是《太上感应篇》所谓的“是道则进,非道则退”的生态伦理的基本行为准则。《石音夫功过格》中有道长与乞儿的对话很能说明这一点:乞儿曰:“……无论不杀生,方为万物之生,即如鸡鸭不杀,喂他何益?牛马不杀,胶皮何取?猪羊不杀,祭祀何有?若论不杀生,竹木不宜砍,柴薪何来?草木不宜伐,人宅无取。这真难也。”道长曰:“极容易的。(历史论文 )鸡鸭不损其卵,不伤其小,又不妄费。当用之时,取其大者杀之,何得为杀?马有扶朝之功,牛有养人之德,临老自死,何必在杀?何至无取竹木?草苗方长不折,相时方伐,何得无用?”乞儿曰:“据道长说,这等看起来,凡物当生旺之时杀之,方才为杀;至休囚衰弱之时杀之,不足为杀。可见生旺时,乃天地发生万物之情,不可违悖天意。至垂天地收藏之时而取之,则用无穷也。”乞儿至是觉有会心,喟然曰:“天地有好生之德,万物有贪生之心。凡事顺乎天理人心而为之,勿逆天理人心而行之,未有不心平意合者也。”[ ]
道教劝善书讲戒杀,但不是绝对的不杀,而是指“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启蛰不杀、方长不折”。也就是说,要按照自然之道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之物。《太上感应篇集注》在注释“春月燎猎”时说:“春为万物发生之候,纵猎不已,已伤生生之仁。乃复以纵之火,则草木由之而枯焦,百蛰因之而煨烬。是天方生之我辄戕之,罪斯大矣!”[ ]认为“春月燎猎”之罪过在于违背了天道。
再比如,《十戒功过格》讲戒杀,但是又认为,虎狼之类,如果“已伤人者其罪宜死”,那么“杀之反为功”。也就是说,人出于天道而开杀戒,还是允许的。与此相反,“牢养调弄曰戏杀”。戏杀“微命”,“如斗蟋蟀、拍蝴蝶之类,一命为一过,虽不伤命,而调弄不放,亦为一过”;戏杀“小命”,“如养八哥画眉、斗鹌鹑之类,一次为二过,虽不伤命,而调弄不放,亦为一过”;戏杀“大命”,“如弄猢狲之类,一命为二十过,虽不伤命,而或开囿辟园系猿养鹿者,一事亦为十过”。也就是说,人如果只是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圈养野生动物,实际上也是对动物的伤害,也为有过。
道教劝善书所反映的生态伦理思想与现代西方生态伦理学奠基人阿尔贝特•施韦兹(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亦译作阿尔贝特•史怀泽)提出的“敬畏生命”[ ]的生命中心主义非常相似。施韦兹强调把爱的原则扩展到一切动物,否认各种生命形式具有高级和低级、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区分,并明确指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 ]有趣的是,在他所著的《敬畏生命》一书中对于《太上感应篇》有一段论述:“《太上感应篇》(赏罚之书),中国宋代(公元960——1227)的一部212条伦理格言集,其中同情动物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些格言本身也许是非常古老的。这部至今仍然很受民众推崇的格言集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天’(上帝)赋予一切动物以生命,为了与‘天’和谐一致,我们必须善待一切动物。《太上感应篇》将喜欢狩猎谴责为下贱行为。它还认为植物也有生命,并要求人们在非必要时不要伤害它们。这部格言集的一个版本还用一些故事来逐条解释同情动物的格言。”[ ]可见,施韦兹对于《太上感应篇》的生态伦理思想是认同的。
三。神学化的生态伦理
道教劝善书的神学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已有学者将其概括为:(1)“道教善书一般都假托道教神仙的名义来制作”;(2)“道教善书宣传有神明监督人的善恶”;(3)“道教善书强调神明对人施行赏罚”;[ ]《太上感应篇》一开始便是:“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月晦之日,灶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根据《太上感应篇》的这一段论述,并结合其它道教劝善书的内容,道教劝善书的上述神学特征是不难概括出来的。
既然道教劝善书具有明显的神学特征,那么道教劝善书中所包含的有关保护动植物的教义当然也具有神学的特征。在道教劝善书中,保护动植物的教义同样属于道教神仙所降授,人保护或伤害动植物的行为同样受到神明的监督和赏罚。
值得注意的是,道教劝善书通过赋予其神学特征而使之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具体表现为较多地讲因果报应,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太上感应篇》说:“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太微仙君功过格》开宗明义便是:“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科曰:积善则降之以祥,造恶则责之以祸。”同时,道教劝善书还通过大量的因果报应的事例以达到去恶从善的教化效果。《文昌帝君阴骘文》有“救蚁,中状元之选”一条,有注:“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学,有僧相之曰:小宋当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后复遇之,僧惊谓郊曰:公丰神顿异,似曾活数百万命者。郊笑曰:贫儒何力及此。僧曰:肖翘之物皆命也。郊曰:旬日前,堂下有蚁穴为暴雨所浸,吾编竹桥渡之,岂此乎?僧曰:是也。小宋固当首捷,公终不出其下。及唱第,祁第一。章献太后谓弟不可先兄,改郊第一,祁第十。”[ ]李昌龄在注《太上感应篇》“填穴”时也引述了此例。这就是善有善报。《太上感应篇集注》在注释“填穴覆巢”时举二例:其一,“朱某平生恶蜂巢,每见蜂从窍入,虽高处必设梯塞之。在人家亦然。后生二子,榖道皆塞。人教以秤尾烧红钻之,竟死”;其二,“苏州薛氏小儿,屡升木杪覆巢取雏。一日上树,不期先有大蛇啖雏巢中,儿惊视张口,蛇竟入口,儿遂死”;[ ]这就是恶有恶报。在道教劝善书中,诸如此类的例证不胜枚举。《阴骘文图证》在证“买物而放生”时有附证:“吕祖曰:汝欲延生听我语,凡事惺惺须恕己;汝欲延生须放生,此是循环真道理;他若死时你救他,你若死时天救你;延生生子别无方,戒杀放生而已矣。”[ ]用因果报应论证戒杀放生对于延生之重要。
虽然道教劝善书带有明显的神学特征,但这一特征恰恰是其得以落实并能够获得教化效果的重要保证。同样,道教劝善书中所包含的具有神学特征的有关保护动植物的教义,虽然由于缺乏科学的解释而没有能够真正说明保护动植物的意义,但是,这些教义在当时尤其是在道教以及相关的领域中得到传播,的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这些纯粹出于宗教目的的教义,虽然在当时科学水平条件下,缺乏科学的基础,但就其要求保护动植物而言,与当今生态伦理学的某些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并得到一些现代生态伦理学家的认同,这也许正是道教劝善书中有关生态思想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注释:
[1][21] 陈霞。道教劝善书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1999911——17
[2] 太上感应篇[M] 道藏(第27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1——142
[3] 太上感应篇图说[M]藏外道书(第1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101——102
[4] [22] 文昌帝君阴骘文注[M]藏外道书(第1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402——428407
[5] 玉历至宝钞[M]藏外道书(第1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772——773
[6] 太微仙君功过格[M]道藏(第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449——453
[7] 十戒功过格[M]藏外道书(1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43——71
[8] 卿希泰。道教文化新探[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36
[9] 孟子•尽心上[M]
[10] 春秋繁露•仁义法[M]
[11] 正蒙•乾称篇。
[12] 王明。太平经合校(卷五十)生物方诀[M]北京:中华书局,1960174
[13] 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M]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126
[14] 谭峭。化书(卷四)仁化[M]道藏(第2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598
[15][17] [23] 太上感应篇集注[M]藏外道书。(第1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137153137
[16] 石音夫功过格[M]藏外道书(第1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88
[18] 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19][20] 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972——73
[24] 阴骘文图证[M]藏外道书(第1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623
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