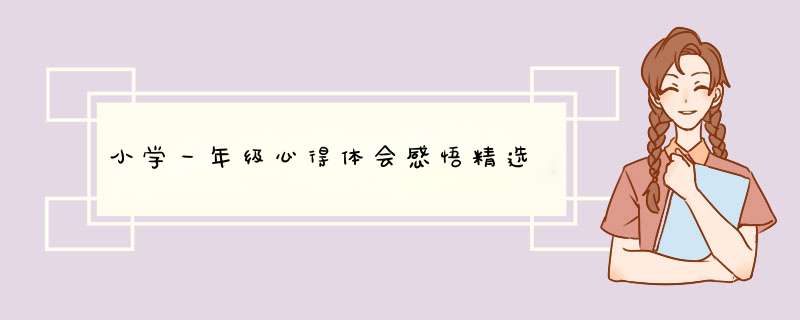列传·第二十章原文_翻译及赏析

列传·第二十章
房玄龄等
曹志,字允恭,谯国谯人,魏陈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学,以才行称,夷简有 大度,兼善骑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为嗣。后改封济北王。武帝为抚军 将军,迎陈留王于邺,志夜谒见,帝与语,自暮达旦,甚奇之。及帝受禅,降为鄄 城县公。诏曰:“昔在前世,虽历运迭兴,至于先代苗裔,传祚不替,或列籓九服, 式序王官。选众命贤,惟德是与,盖至公之道也。魏氏诸王公养德藏器,壅滞旷久, 前虽有诏,当须简授,而自顷众职少缺,未得式叙。前济北王曹志履德清纯,才高 行洁,好古博物,为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为乐平太守。”志在郡上书,以为 宜尊儒重道,请为博士置吏卒。迁章武、赵郡太守。虽累郡职,不以政事为意,昼 则游猎,夜诵《诗》《书》,以声色自娱,当时见者未能审其量也。
咸宁初,诏曰:“鄄城公曹志,笃行履素,达学通识,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 教。其以志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 作邪?”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此。”帝 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 于后,是以假托。”帝曰:“古来亦多有是。”顾谓公卿曰:“父子证明,足以为 审。自今已后,可无复疑。”
后迁祭酒。齐王攸将之国,下太常议崇锡文物。时博士秦秀等以为齐王宜内匡 朝政,不可之籓。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于魏,因怆然叹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 之亲,不得树本助化,而远出海隅?晋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议曰:“伏闻大 司马齐王当出籓东夏,备物尽礼,同之二伯。今陛下为圣君,稷、契为贤臣,内有 鲁、卫之亲,外有齐、晋之辅,坐而守安,此万世之基也。古之夹辅王室,同姓则 周公其人也,异姓则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内,五世反葬。后虽有五霸代兴,桓、文 谲主,下有请隧之僭,上有九锡之礼,终于谲而不正,验于尾大不掉,岂与召公之 歌《棠棣》,周诗之咏《鸱鸮》同日论哉!今圣朝创业之始,始之不谅,后事难工。 干植不强,枝叶不茂;骨骾不存,皮肤不充。自羲皇以来,岂是一姓之独有!欲结 其心者,当有磐石之固。夫欲享万世之利者,当与天下议之。故天之聪明,自我人 之聪明。秦、魏欲独擅其威,而财得没其身;周、汉能分其利,而亲疏为之用。此 自圣主之深虑,日月之所照。事虽浅,当深谋之;言虽轻,当重思之。志备位儒官, 若言不及礼,是志寇窃。知忠不言,议所不敢。志以为当如博士等议。”议成当上, 见其从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议甚切,百年之后必书晋史,目下将见责邪。”帝 览议,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以议者不指答所问,横造异论, 策免太常郑默。于是有司奏收志等结罪,诏惟免志官,以公还第,其余皆付廷尉。
顷之,志复为散骑常侍。遭母忧,居丧过礼,因此笃病,喜怒失常。九年卒, 太常奏以恶谥。崔褒叹曰:“魏颗不从乱,以病为乱故也。今谥曹志而谥其病,岂 谓其病不为乱乎!”于是谥为定。
庾峻,字山甫,颍川鄢陵人也。祖乘,才学洽闻,汉司徒辟,有道征,皆不就。 伯父嶷,中正简素,仕魏为太仆。父道,廉退贞固,养志不仕。牛马有踶齧者,恐 伤人,不货于市。及诸子贵,赐拜太中大夫。峻少好学,有才思。尝游京师,闻魏 散骑常侍苏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尝就乘学,见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 性退让,慈和泛爱,清静寡欲,不营当世,惟修德行而已。鄢陵旧五六万户,闻今 裁有数百。君二父孩抱经乱,独至今日,尊伯为当世令器,君兄弟复俊茂,此尊祖 积德之所由也。”
历郡功曹,举计掾,州辟从事。太常郑袤见峻,大奇之,举为博士。时重《庄》 《老》而轻经史,骏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属高贵乡公幸太学,问《尚书》义 于峻,峻援引师说,发明经旨,申畅疑滞,对答详悉。迁秘书丞。长安有大狱,久 不决,拜峻侍御史,往断之,朝野称允。武帝践阼,赐爵关中侯,迁司空长史,转 秘书监、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谏议大夫。常侍帝讲《诗》,中庶子何劭论《风》 《雅》正变之义,峻起难往反,四坐莫能屈之。
是时风俗趣竞,礼让陵迟。峻上疏曰:
臣闻黎庶之性,人众而贤寡;设官分职,则官寡而贤众。为贤众而多官,则妨 化;以无官而弃贤,则废道。是故圣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处,故有朝廷 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犹人之有股肱心膂,共为一体也。山 林之士,被褐怀玉,太上栖于丘园,高节出于众庶。其次轻爵服,远耻辱以全志。 最下就列位,惟无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贪污,退让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 士闻其风而悦之,将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宠之臣所以为美也,先 王嘉之。节虽离世,而德合于主;行虽诡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 次有几杖之礼,以厚德载物,出处有地。既廊庙多贤才,而野人亦不失为君子,此 先王之弘也。
秦塞斯路,利出一官。虽有处士之名,而无爵列于朝者,商君谓之六蝎,韩非 谓之五蠹。时不知德,惟爵是闻。故闾阎以公乘侮其乡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 汉祖反之,大畅斯否。任萧、曹以天下,重四皓于南山。以张良之勋,而班在叔孙 之后;盖公之贱,而曹相咨之以政。帝王贵德于上,俗亦反本于下。故田叔等十人, 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而未尝干禄于时。以释之之贵,结王生之袜于朝,而其名愈 重。自非主臣尚德兼爱,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
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务救世之政,文士竞智而务入,武夫恃力而争先。官高矣, 而意未满;功报矣,其求不已。又国无随才任官之制,俗无难进易退之耻。位一高, 虽无功而不见下,已负败而后见用。故因前而升,则处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无 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竞而后让,举世之士,有进而无退。大人溺于动俗,执政挠 于群言,衡石为之失平,清浊安可复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为弊, 是故功成必改其物,业定必易其教。虽以爵禄使下,臣无贪陵之行;虽以甲兵定功, 主无穷武之悔也。
臣愚以为古者大夫七十悬车,今自非元功国老,三司上才,可听七十致仕,则 士无怀禄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听终养,则孝莫大于事亲矣。吏历试无绩,依古 终身不仕,则官无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还涖小,则使人以器矣。人主进人 以礼,退人以礼,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阳,临九折而去官,洁如贡禹, 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孙,知足如疏广,虽去列位而居东野,与人父言,依于 慈,与人子言,依于孝。此其出言合于国检,危行彰于本朝。去势如脱屣,路人为 之陨涕;辞宠如金石,庸夫为之兴行。是故先王许之,而圣人贵之。
夫人之性陵上,犹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决,升而不已必困。始于匹夫行义 不敦,终于皇舆为之败绩,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进趣,上宜以退让去其甚者。 退让不可以刑罚使,莫若听朝士时时从志,山林往往间出。无使入者不能复出,往 者不能复反。然后出处交泰,提衡而立,时靡有争,天下可得而化矣。
又疾世浮华,不修名实,著论以非之,文繁不载。九年卒,诏赐朝服一具、衣 一袭、钱三十万。临终,敕子珉朝卒夕殡,幅巾布衣,葬勿择日。珉奉遵遗命,敛 以时服。二子:珉、敳。
珉字子琚。性淳和好学,行己忠恕。少历散骑常侍、本国中正、侍中,封长岑 男。怀帝之没刘元海也,珉从在平阳。元海大会,因使帝行酒,珉不胜悲愤,再拜 上酒,因大号哭,贼恶之。会有告珉及王亻隽等谋应刘琨者,元海因图弑逆,珉等 并遇害。初,洛阳之未陷也,珉为侍中,直于省内,谓同僚许遐曰:“世路如此, 祸难将及,吾当死乎此屋耳!”及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谥曰贞。
敳字子嵩。长不满七尺,而腰带十围,雅有远韵。为陈留相,未尝以事婴心, 从容酣畅,寄通而已。处众人中,居然独立。尝读《老》《庄》,曰:“正与人意 暗同。”太尉王衍雅重之。
敳见王室多难,终知婴祸,乃著《意赋》以豁情,犹贾谊之《服鸟》也。其词 曰:“至理归于浑一兮,荣辱固亦同贯。存亡既已均齐兮,正尽死复何叹。物咸定 于无初兮,俟时至而后验。若四节之素代兮,岂当今之得远?且安有寿之与夭兮, 或者情横多恋。宗统竟初不别兮,大德亡其情愿。蠢动皆神之为兮,痴圣惟质所建。 真人都遣秽累兮,性茫荡而无岸。纵驱于辽廓之庭兮,委体乎寂寥之馆。天地短于 朝生兮,亿代促于始旦。顾瞻宇宙微细兮,眇若豪锋之半。飘摇玄旷之域兮,深漠 畅而靡玩。兀与自然并体兮,融液忽而四散。”从子亮见赋,问曰:“若有意也, 非赋所尽;若无意也,复何所赋?”答曰:“在有无之间耳!”
迁吏部郎。是时天下多故,机变屡起,敳常静默无为。参东海王越太傅军事, 转军咨祭酒。时越府多隽异,敳在其中,常自袖手。豫州牧长史河南郭象善《老》 《庄》,时人以为王弼之亚。敳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瘐子嵩”。象后为 太傅主簿,任事专势。敳谓象曰:“卿自是当世大才,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
敳有重名,为搢绅所推,而聚敛积实,谈者讥之。都官从事温峤奏之,岂攵更 器峤,目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礧砢多节,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时刘舆见任于越, 人士多为所构,惟敳纵心事外,无迹可间。后以其性俭家富,说越令就换钱千万, 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于众坐中问于敳,而敳乃穨然已醉,帻堕机上,以头就穿 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万,随公所取矣。”舆于是乃服。越甚悦,因曰: “不可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王衍不与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为 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 石勒之乱,与衍俱被害,时年五十。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 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 掾,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 由是素论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论十二篇。
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 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 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 《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巳。其后秀义别本出, 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庾纯,字谋甫,博学有才义,为世儒宗。郡补主簿,仍参征南府,累迁黄门侍 郎,封关内侯,历中书令、河南尹。初,纯以贾充奸佞,与任恺共举充西镇关中, 充由是不平。充尝宴朝士,而纯后至,充谓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后?” 纯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来后。”世言纯之先尝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 者,充、纯以此相讥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纯行酒,充不时饮。纯曰: “长者为寿,何敢尔乎!”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纯因发怒曰: “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 下为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众坐因罢。充左右欲执纯,中护军羊琇、 侍中王济佑之,因得出。充惭怒,上表解职。纯惧,上河南尹、关内侯印绶,上表 自劾曰:“司空公贾充请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饮酒过多。醉乱行酒,重酌于 公,公不肯饮,言语往来,公遂诃臣父老不归供养,卿为无天地。臣不服罪自引, 而更忿怒,厉声名公,临时喧饶,遂至荒越。礼,‘八十月制’,诚以衰老之年, 变难无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养老父,而怀禄贪荣,乌鸟之不若。充为三公, 论道兴化,以教义责臣,是也。而以枉错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乱仪度。臣 得以凡才,擢授显任。《易》戒濡首,《论》诲酒困,而臣闻义不服,过言盈庭, 黩幔台司,违犯宪度,不可以训。请台免臣官,廷尉结罪,大鸿胪削爵土。敕身不 谨,伏须罪诛。”御史中丞孔恂劾纯,请免官。诏曰:“先王崇尊卑之礼,明贵贱 之序,著温克之德,记沈酗之祸,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轨仪也。昔广汉陵慢宰相, 获犯上之刑;灌夫托醉肆忿,致诛毙之罪。纯以凡才,备位卿尹,不惟谦敬之节, 不忌覆车之戒,陵上无礼,悖言自口,宜加显黜,以肃朝伦。”遂免纯官。
又以纯父老不求供养,使据礼典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骠骑将军齐 王攸议曰:“凡断正臧否,宜先稽之礼、律。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 不从政。新令亦如之。按纯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废侍养。纯不求 供养,其于礼、律未有违也。司空公以纯备位卿尹,望其有加于人。而纯荒醉,肆 其忿怒。臣以为纯不远布孝至之行,而近习常人之失,应在讥贬。”司徒石苞议: “纯荣官忘亲,恶闻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刘斌议以为: “敦叙风俗,以人伦为先;人伦之教,以忠孝为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亲。 若孝必专心于色养,则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顾其亲,则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为 臣者,必以义断其恩;为子也,必以情割其义。在朝则从君之命,在家则随父之制。 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纯兄峻以父老求归,峻若得归,纯无不归之势;峻不得 归,纯无得归之理。纯虽自闻,同不见听。近辽东太守孙和、广汉太守邓良皆有老 母,良无兄弟,授之远郡,辛苦自归,皆不见听。且纯近为京尹,父在界内,时得 自启定省,独于礼法外处其贬黜,斌愚以为非理也。礼,年八十,一子不从政。纯 有二弟在家,不为违礼。又令,年九十,乃听悉归。今纯父实未九十,不为犯令。 骂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国典。圣恩恺悌,示加贬退,臣愚无所清议。”河南功 曹史庞札等表曰:
臣郡前尹关内侯纯,醉酒失常,《戊申诏书》既免尹官,以父笃老不求供养, 下五府依礼典正其臧否。臣谨按三王养老之制,八十,一子不从政;九十,其家不 从政,斯诚使人无阙孝养之道,为臣不违在公之节也。先王制礼垂训,莫尚于周。 当其时也,姬公留周,伯禽之鲁,孝子不匮,典礼无愆。今公府议,七十时制,八 十月制,欲以驳夺从政之限,削除爵土。是为公旦立法,还自越之,鲁侯为子,即 为罚首也。石奋期颐,四子列郡。近太宰献王诸子,亦有籓外。古今同符,忠孝并 济。
臣闻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饮多,遂至沈醉。尹醒闻知,悼恨前失,执 谦引罪,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而谓傲很,是为重罪过醉之言, 而没迷复之义也。臣闻父子天性,爱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义合,而求忠臣必于 孝子。是以先王立礼,敬同于父,原始要终,齐于所生,如此犹患人臣罕能致身。 今公府议云,礼律虽有常限,至于疾病归养,不夺其志。如此则为礼禁正直,而陷 人以诈,违越王制,开其殆原。尹少履清苦,事亲色养,历职内外,公廉无私,此 陛下之所以屡发明诏,而尹之所以仍见擢授也。尹行己也恭,率下也敬,先众后己, 实是宿心。一旦由醉,责以暴慢。按奏状不忠不孝,群公建议削除爵土,此愚臣所 以自悲自悼,拊心泣血也。
按今父母年过八十,听令其子不给限外职,诚以得有归来之缘。今尹居在郡内, 前每表屡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养不废。兄侍中峻,家之嫡长,往比 自表,求归供养,诏喻不听。国体法同,兄弟无异,而虚责尹不求供养如斯,臣惧 长假饰之名,而损忠诚之实也。夫礼者,所以经国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顺 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旧章。伏惟陛下圣德钦明,敦礼崇教,畴咨四岳,以详典 制。尹以犯违受黜,而所由者醉。公以教义见责,而所因者忿。积忿以立义,由醉 以得罪,礼律不复为断,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诛,而耻不伸于盛明 之世。惟蒙哀察。
帝复下诏曰:“自中世以来,多为贵重顺意,贱者生情,故令释之、定国得扬 名于前世。今议责庾纯,不惟温克,醉酒沈湎,此责人以齐圣也。疑贾公亦醉,若 其不醉,终不于百客之中责以不去官供养也。大晋依圣人典礼,制臣子出处之宜, 若有八十,皆当归养,亦不独纯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明不责醉, 恐失度也。所以免纯者,当为将来之醉戒耳。齐王、刘掾议当矣。”复以纯为国子 祭酒,加散骑常侍。后将军荀眅于朝会中奏纯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进。侍中甄 德进曰:“孝以显亲为大,禄养为荣。诏赦纯前愆,擢为近侍,兼掌教官,此纯召 不俟驾之日。而后将军眅敢以私议贬夺公论,抗言矫情,诬罔朝廷,宜加贬黜。” 眅坐免官。
初,眅与纯俱为大将军所辟,眅整丽车服,纯率素而已,眅以为愧恨。至是, 毁纯。眅既免黜,纯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时人称纯通恕。
迁侍中,以父忧去官。起为御史中丞,转尚书。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 年六十四卒。子旉。
旉字允臧。少有清节,历位博士。齐王攸之就国也,下礼官议崇锡之物。旉与 博士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等上表谏曰:
《书》称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国十有六人, 同姓之国四十人,元勋睦亲,显以殊礼,而鲁、卫、齐、晋大启土宇,并受分器。 所谓惟善所在,亲疏一也。大晋龙兴,隆唐、周之远迹,王室亲属,佐命功臣,咸 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吴、会已平,诏大司马齐王出统方岳,当遂抚其国家,将 准古典,以垂永制。
昔周之选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则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及 召、芮、毕、毛诸国,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轻也,未闻 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国者。汉氏诸侯王位尊势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赞朝政者, 乃有兼官,其出之国,亦不复假台司虚名为隆宠也。
昔申无宇曰“五大不在边”,先儒以为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也。又曰“五 细不在庭”,先儒以为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也。不在庭,不 在朝廷为政也。又曰:“亲不在外,羁不在内。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其少戒 之。”叔向有言:“公室将卑,其枝叶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谚所谓 芘焉而纵寻斧柯者也。
今使齐王贤邪,则不宜以母弟之亲尊,居鲁、卫之常职;不贤邪,不宜大启土 宇,表建东海也。古礼,三公无职,坐而论道,不闻以方任婴之。惟周室大坏,宣 王中兴,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后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诗曰“徐方不回,王曰 镟归”,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为家,将数延三事,与论太平之基, 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违旧章矣。
旉草议,先以呈父纯,纯不禁。太常郑默、博士祭酒曹志并过其事。武帝以博 士不答所问,答所不问,大怒,事下有司。尚书朱整、褚等奏:“旉等侵官离局, 迷罔朝廷,崇饰恶言,假托无讳,请收旉等八人付廷尉科罪。”旉父纯诣廷尉自首: “旉以议草见示,愚浅听之。”诏免纯罪。
廷尉刘颂又奏旉等大不敬,弃市论,求平议。尚书又奏请报听廷尉行刑。尚书 夏侯骏谓朱整曰:“国家乃欲诛谏臣!官立八座,正为此时,卿可共驳正之。”整 不从,骏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独为驳议。左仆射魏舒、右仆射下邳王晃等 从骏议。奏留中七日,乃诏曰:“旉等备为儒官,不念奉宪制,不指答所问,敢肆 其诬罔之言,以干乱视听。而旉是议主,应为戮首。但旉及家人并自首,大信不可 夺。秦秀、傅珍前者虚妄,幸而得免,复不以为惧,当加罪戮,以彰凶慝。犹复不 忍,皆丐其死命。秀、珍、旉等并除名。”后数岁,复起为散骑侍郎。终于国子祭 酒。
秦秀,字玄良,新兴云中人也。父朗,魏骁骑将军。秀少敦学行,以忠直知名。 咸宁中,为博士。何曾卒,下礼官议谥。秀议曰:
故太宰何曾,虽阶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严肃,显登王朝。事亲有色养之名, 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实得臣子事上之概。然资性骄奢,不循轨则。《诗》云: “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人具尔瞻。”言其德行高峻,动必以礼耳。丘 明有言:“俭,德之恭;侈,恶之大也。”大晋受命,劳廉隐约,曾受宠二代,显 赫累世。暨乎耳顺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国之租,荷保傅之贵,执司徒之均。 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侧。方之古人,责深负重,虽举门尽死,犹不称位。而乃 骄奢过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义言之,非惟失辅相之宜,违 断金之利也。秽皇代之美,坏人伦之教,生天下之丑,示后生之傲,莫大于此。自 近世以来,宰臣辅相,未有受垢辱之声,被有司之劾,父子尘累而蒙恩贷若曾者也。
周公吊二季之陵迟,哀大教之不行,于是作谥以纪其终。曾参奉之,启手归全, 易箦而没,盖明慎终,死而后已。齐之史氏,乱世陪臣耳,犹书君贼,累死不惩。 况于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强盛,而不尽礼。管子有言:“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 维不张,国乃灭亡。”宰相大臣,人之表仪,若生极其情,死又无贬,是则帝室无 正刑也。王公贵人,复何畏哉!所谓四维,复何寄乎!谨按《諡法》:“名与实爽 曰缪,怙乱肆行曰丑。”曾之行己,皆与此同,宜谥缪丑公。
时虽不同秀议,而闻者惧焉。
秀性忌谗佞,疾之如仇,素轻鄙贾充,及伐吴之役,闻其为大都督,谓所亲者 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国大任,吾将哭以送师。”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军 必败,故哭送其子耳。今吴君无道,国有自亡之形,群率践境,将不战而溃。子之 哭也,既为不智,乃不赦之罪。”于是乃止。及孙皓降于王濬,充未之知,方以吴 未可平,抗表请班师。充表与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佥以秀为 知言。
及充薨,秀议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异姓为后,悖礼溺情,以乱大伦。昔 鄫养外孙莒公子为后,《春秋》书‘莒人灭鄫’。圣人岂不知外孙亲邪!但以义推 之,则无父子耳。又案诏书‘自非功如太宰,始封无后如太宰,所取必己自出如太 宰,不得以为比’。然则以外孙为后,自非元功显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礼,盖可 然乎?绝父祖之血食,开朝廷之祸门。《諡法》‘昏乱纪度曰荒’,请谥荒公。” 不从。
王濬有平吴之勋,而为王浑所谮毁。帝虽不从,无明赏罚,以濬为辅国大将军, 天下咸为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晋启祚,辅国之号,率以旧恩。此为王濬无功 之时,受九列之显位,立功之后更得宠人之辱号也。四海视之,孰不失望!蜀小吴 大,平蜀之后,二将皆就加三事,今濬还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吴之未亡也, 虽以三祖之神武,犹躬受其屈。以孙皓之虚名,足以惊动诸夏,每一小出,虽圣心 知其垂亡,然中国辄怀惶怖。当尔时,有能借天子百万之众,平而有之,与国家结 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实皆甘之耳。今濬举蜀、汉之卒,数旬而平吴,虽举吴人之财 宝以与之,本非己分有焉,而遽与计校乎?”
后与刘暾等同议齐王攸事,忤旨,除名。寻复起为博士。秀性悻直,与物多忤。 为博士前后垂二十年,卒于官。
史臣曰:齐献王以明德茂亲,经邦论道,允厘庶绩,式叙彝伦。武帝纳奸谄之 邪谋,怀绍终之远虑,遂乃君兹青土,作牧东籓。远迩惊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 膺教义,方轨儒门,蹇蹇匪躬,慺慺体国。故能抗言凤阙,忤犯龙鳞,身虽暂屈, 道亦弘矣!庾氏世载清德,见称于世,汝颍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谋甫素疾佞邪, 而发因醉饱,投鼠忌器,岂易由言。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子玄假誉攘善,将非盗 乎!
原文
①韦福字敬远,京兆杜陵人也。弱冠,被召拜雍州中从事,非其好也,遂谢疾去职。前后十见征辟,皆不应命。(魏)太祖经纶王业,侧席求贤,闻秆高不仕,虚心敬悦,遣使辟之,虽情逾甚至,而竟不能屈。弥以重之,亦弗之夺也。所居之宅,枕带林泉,付酝媲偈椋萧然自乐。
②明帝即位时,晋公宇文护执政,广营第宅。尝召钢琳,访以政事。秆鍪悠涮茫徐而叹曰:“甜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护不悦。有识者以为知言。
③弟孝宽为延州总管,钢林萦胄⒖硐嗉。将还,孝宽以所乘马及辔勒与浮敢云浠饰,心弗欲之。笑谓孝宽曰:“昔人不弃坠履者,恶与之同出,不与同归。吾虽不逮前烈,然舍旧录新,亦非吾志也。”于是乃乘旧马以归。
④缸迎,行随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宽子总复于并州战殁。一日之中,凶问俱至。家人相对悲恸,而干裆自若。谓之曰:“死生命也,去来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抚之如旧。
⑤建德中,敢阅昀希预戒其子等曰:“吾死之日,可敛旧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车载柩,坟高四尺,圹深一丈。其余烦杂,悉无用也。吾不能顿绝汝辈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吾常恐临终恍惚,故以此言预戒汝辈。”宣政元年二月,卒于家,时年七十七。
(选自《周书•卷三十一》)
译文
韦槭俏ば⒖碇兄,字敬远,京兆杜陵人。二十岁时,被征召为雍州中从事,因为不合心意,就称病离职。先后有十次被征召为官,均不出仕。当时太祖筹划大业,求贤若渴,听说韦楸3指呱兄窘冢不愿当官,心中非常敬佩,(魏太祖)派使者前往征召他,尽管情感表达感人至深,但最终不能使韦榍服(屈身、屈就)。(太祖)因此更加敬重他,也不强迫改变他的志向。韦榈淖≌,环绕着树林清泉,他对林泉而鼓琴读书,怡然自得。
明帝登基后,当时晋公宇文护执掌朝政,大建宅第。曾征召韦榈阶约赫第,询问政事。韦檠鍪哟筇茫缓缓叹息道:“沉湎在美酒和音乐之中,住着高峻华丽的宅第,即使二者只占其一,恐怕也未必不会灭亡。”宇文护很不高兴。有识之士认为此话很有远见。
韦孝宽担任延州总管,韦榈街莩怯胛ば⒖硐嗉。回来的时候,韦孝宽把自己骑的马以及鞍具、 送给韦椤N榭吹桨熬咧钗镒笆位贵,不想接受,就笑着说:“前人不丢弃遗落的簪子和坠落的鞋子,是由于怀旧之情。我虽然不及前贤遗风,但舍弃旧物而换用新物,也不是我的心意。”于是仍然骑着旧马返回。
韦橹子韦代理随州刺史,患病而死,韦孝宽之子韦总又在并州阵亡。一天之内,噩耗俱至。家里人相对悲恸,而韦樯裆如常。他对家人们说:“死生由命,人间常事,有什么值得悲伤的”若无其事地拿过琴弹起来,同往常一样。
建德年间,韦橛捎谀昀希预先告诫儿子们说:“我死的那一天,可穿上旧衣安葬,不要另制新衣。让棺材能够放下尸首,用牛车载运灵柩,坟高四尺,墓穴深一丈。早晚祭奠更加麻烦,我不能一下子断绝你们的思念之情,可以每月的初一、十五祭奠一次。我常常担心临终时精神恍惚,所以预先把这话告诫你们。”宣政元年二月,在家中去世,当时七十七岁。
注:更多精彩文章请关注查询栏目。
原文
古者包羲氏(即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法象,现象)于地,视鸟兽之文(文,错画也。象交文。今字作纹)与地(一说为“舆地”,即“与”之繁体“与”通“舆”,“ 与地”即“舆地”。“舆地”,以车喻地,即大地之意)之宜(通“仪”,仪象,或法度),近取诸身,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示也;《康熙字典》:又布也;留传,留传后世)宪象(观测推算天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众多)业其繁,饰(假托、掩饰)伪(作伪、虚假)(饰伪,即巧饰伪诈)萌生。黄帝之史(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háng,兽迹也)之迹,知分理(即文理)之可相别异也(悟出纹理有别而鸟兽可辨),初造书契(即文字)。“百工以乂(yì,治理),万品以察(分辨、明察),盖取诸夬(guài,《说文》分决也,即断决、分辨)”;“夬扬(扬:传播)于王庭”(这句意思是:万物分辨明晰了,然后在王者朝廷上予以传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说的是文字是在国王朝廷宣明教化的工具),君子(王臣百官)所以施禄及下(下层庶民),居德(蓄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孳乳:繁殖,泛指派生)而浸(一作寖,渐也)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如:《说文》从随也。一曰若也,同也)也。以迄五帝(指黄帝、帝颛顼(zhuānxù)高阳、帝喾(kù)高辛、帝尧、帝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武)之世,改易(改变)殊体(不同的形体)。封于泰山者七有二代,靡(无)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官名)教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先以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jiéqū,弯曲),日月是也。三日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喻也)相成,江河是也。四日会意。会意者,比(比合、组合)类(字类、字群)合谊(义之本字,义乃谊之假借字),以见指撝(指向)(二句言组合字群而会合其义,以表现所指向之物事也。),武信是也,五日转注。转注者,建类(造字类)一首(统一其部首),同意相受(加也),考老是也。六日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谓与仓颉之古文稍有不同)。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厥,其也,指示代词;厥意,文字构成之义)可得而说(说明)(这几句意思是:直到孔子编写六经,左丘明写春秋传,都用古文,字的意义还能够说明)。其后诸侯力政(政,即征。力政:以武力相征伐),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讨厌礼乐妨害自己),而皆去(废弃)其典籍(典章书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始天下,丞相李斯乃奏(上奏)同(同一、统一)之,罢(删除)其不与秦文合作(相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采用)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或者有很大的简化改变),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指焚书坑儒),涤除(废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以求简便),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的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刻于符信之体),四曰虫书(象鸟虫之形,书写旙信之体。旙信,即旗帜之类),五曰摹印(规摹印章之体),六曰署书(题署之体),七曰殳书(殳,兵器;殳书,刻于兵器之体),八曰隶书。(注:自刻符以下《汉书艺文志》谓之六技,其中除隶书外,大约都是大篆、小篆之艺术体)。
汉兴有草书(段玉裁曰:“按草书之称起于草稿……其各字不相连绵者曰章草,晋以下相连绵者曰今草。”草书之特征有二:—简化,二连绵)。尉律(廷尉之法律):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讽,背文也;籀,紬绎理解之意。讽籀者谓讽诵理解也。有人说:籀书九千文,是用籀文所写之文长达九千字,也通);又以八体试之(试用秦之八体使之书写之)。郡移太史并课(并试),最者(成绩最优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以法纠有罪也)之(这两句意思是:吏民上书,书写如不合规格者,即举而纠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文字之学谓之小学者)不修,莫达(明白)其说(文字构形之说)久矣。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谓李斯所作仓颉篇之说解。读,即说解)者,张敞从受之(从之受业);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馀人令说文字未央廷(未央宫)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采,采取,采取会议讲学讨论之结果)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亡新,指王莽。摄,摄政,指王莽代汉自立),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大司空,官名。甄丰,人名)之部。自以为应制作(谓应王莽之命而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壁中书者(壁中书,以古文出于壁中故谓之璧中书。晋人谓之蝌蚪文,则以周时古文头粗尾细,有似蝌蚪之故),鲁恭王坏孔子屋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不可之意)版复见远流(此言虽不可再见远古文字之流变,然其构字之详尚可说明),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大加非议),以为好奇者也,故诡(变也)更正文,乡(向,先前)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常行,通行之书,即指隶书),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言依秦隶书之形体牵强解字释经),喧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曲也,误也)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诃之假借字,斥责也)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翫(wàn,玩弄)其所习(指隶书),蔽(不明之意)所希(稀)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谓构字之条例),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通达)圣人之微恉(恉,意也)。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言学童承师之教告,而俗儒鄙夫因后世有“君命曰诏”之义,因说“仓颉篇”为古帝所作),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古代的记载)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xié,同邪,不正也)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经传子史)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博,广也;通人,学识渊博的专家),至于小大,信而有证(信、可信也。证、证据也)。稽撰(稽,稽考;撰,诠释)其说,将以理(解释)群类(字类),解廖误,晓学者,达神恉(深奥之旨,此谓文字结构之神妙意义)。分别部居(部类),不相杂厕(置也,放置)。万物咸覩(睹),靡不(无不)兼载(尽记也)。厥(其也,代词)宜不昭(昭,明也),爰明以谕(谕,告也)。其称(称,举也,犹今言征引,引证)《易》,孟氏,《书》;《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阙,即缺;阙如,即阙略不言之意)也。
译文:
古代庖羲氏统治天下的时候,上则观察星象于天,下则观察现象于地,又看到乌兽的纹理和地理的形状,近则取法于身,远则取象于物,于是开始作了八卦,用它来表示法定的图象。至神农时代,用结绳的办法记录事物,诸事繁杂,饰伪的事情不断发生。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乌兽足迹,知道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始创造了文字。“百官以乂,万民以察,大概取象于分别,”“分别了,扬于王庭,”这就是说,文字是在王者朝廷里宣教明化的,是百官用以对下布施教化,增修德行,明白禁忌的。仓颉在开始创造文字的时候,大抵是依照事物的形象画出它们的图形,所以叫做“文”。后来形旁声旁相互结合就叫做“字”。“文”是表示事物的本然现象,“字”就是由文孳生出来而逐渐增多的。写在竹帛上的叫做“书”,“书”就是“如”的意思。到了五帝三王的时代,文字逐渐改变成不同形体。在泰山祭天地的有很多朝代,使用的文字竟然没有相同的呢。
周朝的制度,儿童八岁入小学,保氏先用“六书”来教育王室的子弟。第一种叫做指事。所谓指事,就是一见就可以认识,细致观察就可以了解它的意义,==(上下)二字就是这样。第二种叫做象形。所谓象形,就是画成那个东西,随着它的形体而曲折,日、月二字就是这样。第三种叫做形声。所谓形声,就是根据事物造字,再取一个近似的声符配合而成,江、河二字就是这样。第四种叫做会意。所谓会意,就是组合两个以上的字,表示一个新的意义,武、信二字就是这样。第五种叫做转注。所谓转注,就是说造这种文字要统一部首,用一个同义的字展转注释,老考的关系就是这样。第六种叫做假借。所谓假借就是本来没有这个字,借用一个同音字来表示这个概念,令、长二字就是这样。到周宣王的时候,太史官名叫籀的作大篆十五篇,跟古文稍有不同。直到孔子编写六经,左丘明写春秋传,都用古文,字的意义还能够说明。此后,各国诸侯互相征伐,不服从周天子,他们讨厌礼乐妨害自己,于是都废弃旧时的典章书籍。当时天下分为七国,各国田亩划分的制度不同,车路轨道的宽窄不同,法律制度不同,衣冠形式不同,语言的声音不同,文字的形体也不同。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丞相李斯就上书建议把这些混乱现象统—起来,废除那些跟秦朝文字不同的书写形式。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都是取史籀大篆,或者稍微进行一些改变或简化,这就是所说的小篆。这个时候,秦王朝烧毁了经书,废除了过去的典籍,大量发动隶卒,兴起役戍,行政事务,监狱案件一天天繁杂起来,开始产生隶书,以求简便,于是古文使从此不用了。自此以后秦国文字有八种体式:一叫大篆,二叫小篆,三叫刻符,四叫虫书,五叫摹印,六叫署书,七叫殳书,八叫隶书。汉朝初年,出现了草书。廷尉的法律规定:学童十七岁以上才得应考,能讽诵理解九千宇的文章才能允当史官;同时也要考秦代八体的写法。地方送到朝廷去会试,成绩最好的录取为尚书史。书写有不正确的就检举处分他。现在虽然还有廷尉的法令,可是不考试了,小学也不讲求,一般人早就不懂得文字的道理了。孝宣皇帝的时候,召集了精通《仓颉篇》的人,派张敞跟他学习;此外,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也能够讲授文字的知识。孝平皇帝的时候,征聘爰礼等百多人,在未央宫中讲述文字,封爰礼作小学博士。黄门侍郎扬雄采集他们所讲的编成《训纂篇》。合计《仓颉篇》到《训纂篇》共十四篇,合计五千三百四十字,各书所记载的文字大致都保存着。到王莽摄政的时候,派大司空甄丰等人校正文字。甄丰自以为奉命而作,对古文有些改定。当时有六书:第—种叫做古文,就是从孔壁中得到的文字。第二种叫做奇字,就是古文的异体。第三种叫做篆书,就是小篆。第四种叫做左书,就是秦时的隶书,秦始皇命令下杜人程邈所作的。第五种叫做缪篆,是用来摹刻印章的字体。第六种叫做鸟虫书,是用来写在旗帜或符节上的。
壁中书,就是指武帝时鲁恭王拆孔子住宅而得到的《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有北平侯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各地又往往在地里挖掘出钟鼎彝器,上面的铭文就是前代的古文,它们的字体都相类似。虽然不能从这些材料看出文字的流变,但是造字详情还是可以大致说明的。然而当时的一些人对于这些古文,大加非议,认为这是好奇立异,故意变更正规文字,向着孔壁凭空虚构一些难以认识的东西,淆乱通行的文字来炫耀自己。。太学的学生都争着解说文字,阐明经义,妄称秦朝的隶书就是仓颉时代的文字。他们说,文字是世代相传的,怎么会改变呢?竞歪曲地说:“马头人”是“长”字,“人持十”是“斗”字,“虫”字是弯曲“中”字而成的。掌管法律的人说明法律,甚至根据隶书的字形判决案件,把“苛人受钱”的“苛”字说成“止句”,类似这种情况还很多。这些都同孔于壁中的古文不合,也不合于大篆。可是庸夫俗子玩弄他们的所学,不明了他们所少见的东西,没有看到宏通的学者,也没有明白文字的条例,把旧艺当作怪异,把野言当成宝贝,认为自己所知道的是非常奥妙的东西,认为自己透彻地领会了圣人的深意。他们又看到仓颉篇中有“幼子承诏”这句话,就说仓颉篇是古代帝王所作的,这里面还记载着神仙的法术哩!这样迷误不明,难道不是悖乱吗!
《尚书》说:“余想观看古人之象”,这就是说,必须遵守古代的记载,不应穿凿附会。孔子说:“我还看到过古史上的阙文,现在没有了啊!”这就是批评不懂不问,各逞己见,是非无定,巧言邪说,使天下学者疑惑的那些人。文字是经艺的基础,也是政治的基础,前人用它,将文化传给后人,后人用它认识古代文化。所以说:“基本建立了,其它事物才能产生”,“知道天下的深奥道理就不可错乱。”我现在编次小篆和古文籀文,广泛地采取通人的意见,至于各种解释,都是可信而有证据的。稽考诠释那些解说,目的在于拿它解释文字,剖析错误,告诉读者通达文字构造的深意。分别部类排列,不使杂乱。在这里,万事万物都可以看到,没有什么遗漏。那些意义不明的就清楚地加以说明。书中所引《周易》是孟氏本;《尚书》是孔氏本;《诗经》是毛氏本;《礼经》、《周官》、《左氏春秋》、《论语》、《孝经》都是古文经。至于那些还不清楚的,只好阙而不解了。
《太史公自序》原文:
作者司马迁 朝代汉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翻译:
太史公说:“我的父亲生前曾经说过:‘自周公死后,经过五百年才有了孔子。孔子死后,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修正《易传》,续写《春秋》,本于《经》、《尚书》、《礼记》、《乐经》的吗?’”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小子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曾听董生说过:‘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诸侯害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
孔子说:‘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明显。’《春秋》,从上而言,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政治原则;从下而言,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贬恶,崇敬贤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补救政治上的弊端,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
《易经》显示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相互关系,所以长于变化;《仪礼》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长于行动;《尚书》记载了上古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从政;《诗经》记载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长于教化;《乐记》是音乐所以成立的根据,所以长于调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
因此,《仪礼》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乐记》是用来激发和穆的感情的,《尚书》是用来指导政事的,《诗经》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的,《易经》是用来说明变化的,《春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有用了。”
内容品鉴:
《太史公自序》是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章,编为《史记》末卷。文章概述了作者的家族世系、家学渊源、著书经过及旨趣等,融作者的遭遇和志向于一炉,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
全文可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作者的生平家世和写作《史记》的时代条件、个人动机,以及受刑后忍辱著书的经历;第二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文章规模宏大,气势浩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创作的重要资料。
司马迁在元封三年(前108年)接替其父担任太史令,从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创作《太史公书》(后称为《史记》)。后因向汉武帝为李陵战败投降匈奴之事辩护而被捕入狱并处以腐刑,在形体和精神上遭受巨大的创伤。
出狱后任中书令,忍辱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太史公自序》既是《史记》的序文,也是作者的自传,编排在全书最后。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导之从子也,祖正,尚书郎。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 过江也,旷首创其议。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而异之。 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 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深为从伯敦、导 所器重。时陈留阮裕有重名,为敦主簿。敦尝谓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 减阮主簿。”裕亦目羲之与王承、王悦为王氏三少。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 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 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 以女妻之。
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累迁长史。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 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 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扬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劝 使应命,乃遗羲之书曰:“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至 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幸徐求众心。 卿不时起,复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开怀,当知万物之情也。”羲之遂报书曰: “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 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若 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 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汉末使太傅 马日磾慰抚关东,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
羲之既拜护军,又苦求宣城郡,不许,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时殷浩与 桓温不协,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因以与浩书以戒之,浩不从。及浩将北伐, 羲之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为姚襄所败。复图再举,又遗浩书 曰:
知安西败丧,公私惋怛,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 固以久矣,而加之败丧,此可熟念。往事岂复可追,顾思弘将来,令天下寄命有所, 自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 想识其由来也。
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 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 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追咎往事,亦何所复及,宜更虚己求 贤,当与有识共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 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任国钧 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 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
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 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今亟修德补阙,广延群贤,与之分任,尚未知 获济所期。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知言不必 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若必亲征,未达此旨,果 行者,愚智所不解也。愿复与众共之。
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知所厝。自顷年割 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
又与会稽王笺陈浩不宜北伐,并论时事曰:
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北面之道,岂不愿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载一时 之运?顾智力屈于当年,何得不权轻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 所忧乃重于所欣。《传》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 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 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议乎!
夫庙算决胜,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功就之日,便当因其众而即其实。 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一。且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 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今运无还期, 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 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张,令殷浩、荀羡还据合 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 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安危之机,易于反 掌,考之虚实,著于目前,愿运独断之明,定之于一朝也。
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未易。然古人处闾阎行阵之间,尚或干时谋国,评裁者 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末行,岂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决在行之,不可复持疑后 机,不定之于此,后欲悔之,亦无及也。
殿下德冠宇内,以公室辅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当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 者所以寤寐长叹,实为殿下惜之。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 游将不止林薮而已。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 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
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振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忧甚,羲之每上疏争之, 事多见从。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曰:
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 东海矣。
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 但当岁终考其殿最。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 降,令在疆塞极难之地。
又自吾到此,从事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错违背, 不复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纲纪,轻者在五曹。主者莅事,未尝得十 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卿方任其重,可徐寻所言。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史便 足统之,况以群才而更不理,正由为法不一,牵制者众,思简而易从,便足以保守 成业
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吾谓诛翦一人,其后便断,而时意不同。近检校 诸县,无不皆尔。余姚近十万斛,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
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 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 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又 有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成十年、十五年, 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 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 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今除罪而充杂役,尽移 其家,小人愚迷,或以为重于杀戮,可以绝奸。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 宜邪!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 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 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 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 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 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 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 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 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 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 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 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
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 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 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 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 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又尝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 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 姥如其言,人竞买之。他日,姥又持扇来,羲之笑而不答。其书为世所重,皆此类 也。每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曾与人书云:“张 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 及其暮年方妙。尝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叹
本文2023-08-05 08:34:20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198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