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装书局出版社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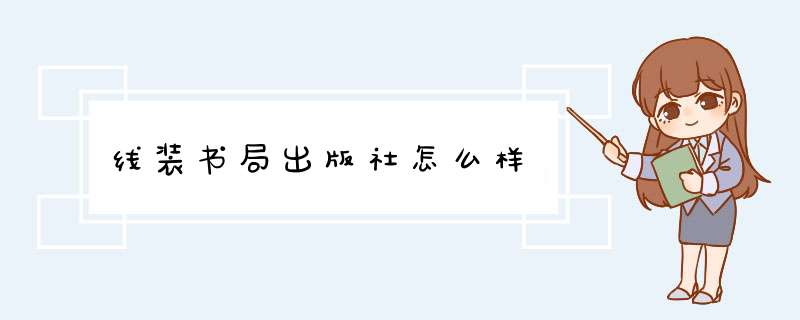
线装书局出版社详细介绍如下:
线装书局是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管、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 以出版国学典籍、社科专著、诗词书画、史志年鉴为主的国家出版机构,20世纪九十年代初成立。
已出版各类图书千余种,其中,以线装、精装大型精品书为主,兼出传统文化普及类平装书及特装国礼书。按照出书宗旨,线装书局陆续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版本价值、收藏价值的古籍书和当代著作,在国内外受到读者的欢迎。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线装书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南京图书馆孤本善本丛刊--明刊孤本方志专辑》、《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元珍影印丛刊--汉书》、《资治通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史记》、《永乐北藏》;
中英文对照丝绸版《孙子兵法》、《道德经》、《宋词一百首》;当代线装书有《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毛泽东诗词手迹》、《毛泽东选集》(全四卷)、《邓小平文选》(全三卷);
精装书《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古籍珍本游记丛刊》、《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等。这些经典、学术著作的出版,丰富了我国的文献宝库,使之版本品类更丰富,中国特色更浓,成为收藏之珍本、善本书。
按照出书宗旨,线装书局陆续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版本价值、收藏价值的古籍书和当代著作,在国内外受到读者的欢迎。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线装书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南京图书馆孤本善本丛刊——明刊孤本方志专辑》、《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元珍影印丛刊——汉书》、《资治通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史记》、《永乐北藏》;中英文对照丝绸版《孙子兵法》、《道德经》、《宋词一百首》;当代线装书有《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毛泽东诗词手迹》、《毛泽东选集》(全四卷)、《邓小平文选》(全三卷);精装书《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古籍珍本游记丛刊》、《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等。这些经典、学术著作的出版,丰富了我国的文献宝库,使之版本品类更丰富,中国特色更浓,成为收藏之珍本、善本书。
线装书局为传播、积累、保存民族文化遗产,抢救孤本善本,正在全力推出三项大型影印工程:一、《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二、《省市图书馆古籍善本集成》;三、《高校图书馆古籍善本集成》。
黄平(以下简称黄):“80后”文学多年来被各种印象式的观感所围绕,真切理解“80后”文学的前提,首先是梳理、辨析这些淤积的成见。
金理(以下简称金):对于“80后”文学最严厉的一种指责是过度市场化。其实“80后”的出场方式本就不同。有的与商业炒作、市场利润、网络、新媒体结合紧密,有的则通过传统文学机制登台,依然坚持以纯文学刊物作为阵地,以作协、主流文学奖、学院批评家为评价体系。只不过一般人的目光都被前者所吸引。还有就是一段时期内专业的文学研究没有及时跟进,无法在流行观念、传媒批评之外再提供一种考察视野。
在今天,如果我们依然持一种夸张“文学”与“市场”之间对立的看法,其实是很可笑的。前段时间有位媒体的朋友采访我,拟好的提纲里有一个问题是:当下“80后”作家群,似乎比他们的前辈们更具备市场意识,如关注作品的销量,在作品大卖后还会跟进一些衍生品。我的回答是,这一点不新鲜,如果回到现代文学史上,文学青年们利用、经营现代出版的经验,比如巴金、施蛰存、赵家璧等,足以让今人汗颜。只不过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今天可供利用的方式、阵地更新颖、多元。如果上面提到的那几位文学巨匠在今天这个时代重生,我想他们也会利用网络、微博发表诗歌、推广小说,一点不稀奇的。关键的问题是,当你在介入这个市场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文化理想?是仅仅满足于获取利润,还是借此传播、扩散自己的人文理想和精神能量?
黄:哪怕“市场化”的说法仅仅限定为针对郭敬明这样的作家,也只是过于表象的说法。无论是纯文学写作还是市场化写作,都存在着写作的交叠,一代人其实面对着类似的问题。比如城市化时代的青年无力把握自身命运的茫然之感,不仅在甫跃辉等人的小说中出现,也在郭敬明的小说中出现。《小时代》三部曲结束于“胶州路大火”,郭敬明安排他的所有人物在胶州路707弄1号聚会,时间是2010年11月15日。在现实世界中上海同一天同一地点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火灾,五十余人葬身火海。现实中的“上海”终于无比酷烈地闯进到“小时代”的世界中,将里面的男男女女焚烧干净。
这样一个猛烈而意味深长的结尾,提升了《小时代》三部曲的境界。同宿舍的四个女孩子组成了“小共同体”,以抱团取暖的方式,扮演着“大时代”的局外人、“小时代”的剧中人。然而,这种与历史疏离的态势无法持久,纸醉金迷的“上海梦”化为灰烬,宛如幻城一梦。郭敬明写完《小时代》最后一行,也许会想起十四岁时发表的处女作《孤独》,这首预言般的小诗结束于这一句:“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
金:记得三年前我们讨论过一次郭敬明。当时主要表达忧虑。最近我的想法有了改变。去年读完“90后”冬筱的一部长篇《流放七月》,小说并不是说写得多好,其实里面有很多青春文学的通病,但这个小说的奇特之处在于一方面写年轻人当下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在探究历史之谜--七月派的历史,当时的年轻诗人们如何在抗战烽火中聚集,如何在20世纪50年代遭逢炼狱……这个“90后”作者本人就是七月派的后人,再联想到相近的时间段里牛汉、化铁先生的辞世,感觉好像是文学传统的薪尽火传。但需要注意的是,《流放七月》这部小说最初是在《最小说》上连载,单行本由“最世文化”、长江文艺推出,冬筱是郭敬明旗下的作者。让我诧异的地方就在这里:原先我觉得肯定是两种立场、两股道上的力量,现在看来他们的分野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即便我们把郭敬明看作一种商业文化的代表,但他周围其实有着不同的“光圈”。像旗下笛安(《文艺风赏》主编)、林培源(《最小说》主办“文学之新”大赛全国十二强选手之一)的创作风格就偏向文学性。而当下最优秀的几位年轻的科幻作家陈楸帆、宝树、飞氘都是郭敬明的签约作者。
我在网络论坛上发现,郭敬明的许多粉丝并不怎么接受冬筱向历史致敬的写作风格。其实这才是值得追踪的话题:接下来,是郭敬明式的趣味全面改造冬筱的小说;抑或,冬筱、飞氘们拓宽年轻读者的阅读视野?我的意思是,在今天面对这样复杂的文化环境,与其固守二元对立,还不如抛弃成见,尤其当年轻人在商业市场和个人探索之间寻找回旋余地的时候,我们应该努力去感知他们在多方博弈的间隙里那种“借水行舟”的尝试。与其去区分市场、文学,或者再把文学划分为雅、俗,还不如去关注各种版块的缝隙间,是否存在着产生新意义与可能的空间,尽管目前这些空间也许还很暧昧、不稳定,但我想,这正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去珍重的空间。
肤浅而匮乏经典意识?
黄:对于“80后”文学的第二点批评,是往往认为“80后”对于经典作品与前辈作家缺乏足够的阅读,是处于文学传统之外的浅薄浮泛的写作。这种批评往往流于观感,缺乏资料的支持与对于“80后”作家的真实了解,而是主要依据流行的青春文学的美学特征来推衍。2014年开始,我们二人和杨庆祥在《名作欣赏》上联合主持“一个人的经典”栏目,请一些同龄的作家来谈自己的经典阅读,目的之一就在于纠正这类偏见。我们发现“80后”作家所推崇的经典,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吴承恩,和前辈作家很相似。与其争论“80后”作家读书多不多,不如具体讨论每个作家选择读什么,其阅读怎么构成他的写作资源。
金:一般人可能过于夸大青年作家将**、美剧、动漫等元素编织入创作,却忽略了青年人同样在向经典致敬,所以我很看重“一个人的经典”这个栏目。“经典”也可能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经典谱系。有些问题不必争论,类似“作家读书少”“作家不懂外语”之类的断言都是似是而非的,因为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反证;不如具体讨论作家的阅读资源。“经典”需要漫长的时间来过滤,所以我选择用“阅读资源”这个词。
选择某种阅读资源,绝不仅仅是出于文学趣味,而是生活感受在背后左右。这一期《名作欣赏》专号中让我眼前一亮的是飞氘的《蝴蝶效应》,它杂糅了至少三种资源:首先是当下的流行趣味,例如引入西方科幻大片;其次是中国古代历史、神话与典籍,比如有三章分别以逍遥游、沧浪之水、九章算术命名;第三是现代中国的思索与抗争,尤其通过鲁迅这个意象表达出来。《蝴蝶效应》中有不少关于鲁迅的“故事新编”,比如在“异次元杀阵”的题名下再写了“无物之阵”的故事,我想飞氘之所以起意致敬,肯定是共感到了鲁迅式“铁屋子”的困境和绝望中抗战的勇气。我的意思是:今天我们青年人和鲁迅相遇,不是说要取法某种文学技巧、接续某种文学传统,而是置身当下的生活感受,逼使我们摸索到了鲁迅这一份经典的资源。
黄:“80后”作家所身处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推动他们重构自身的写作资源。现代人情绪上的无根与迷幻,内心的漂泊与孤独体验,已经变成一种跨国性的元叙事。民族国家的区隔已经渐渐失效,让位于阶级的、地域的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习得上的区隔,比如,一位上海青年作家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位东京青年作家,与西北的青年作家交流起来,反而会有更多障碍。宇文所安在《他山的石头记》中举过一个形象的例子,对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一个韩国或日本或越南的知识分子,甚至一个博学的犹太人,都可能比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农民或商人与他们更好地分享传统文学。”
同时,我们的青年作家也要警惕将生活感受完全普世化,忽视了“中国特色”的影响。我个人看法,“80后”青年的孤独与迷茫之感,一方面是作为“现代人”的后果,一方面是作为“中国人”的后果。二者的辩证博弈,才能完整地诠释什么是现代中国,什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地说,卡夫卡的文学与鲁迅的文学,对我们同样重要。
专业主义?
黄:对于“80后”文学另外一个维度的批评是专业主义。这种批评主要针对“80后”批评家,也针对一部分传统文学体制中的“80后”作家。这种观点的持有者,往往强调一个道德化的现实主义立场与宗教式的知识分子精神,可谓近年来对于“纯文学”反思的一部分。
就“80后”这代人的文学批评而言,确乎是比较学院化的,但学院化并不等于脱离现实。指责“80后”批评家专业主义,其前提是一种朴素的反理论的态度,觉得文学理论尤其是学院派普遍侧重的西方文论不过是空对空的概念游戏,坦率讲这完全是缺乏文学理论训练的误读。我觉得比较客观的说法是,文学批评领域确实存在着大量对于西方文论的生硬复制,很多时候确实流于空泛的文字游戏,但这不能推论出西方文论本身就是空洞无物的,以及学院派批评都是封闭的知识循环。成熟的西方文论,必然是深切地回应了理论大家创制时所面对的重大文学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提供了普遍性的思考与解读的范式。换句话讲,一流的学院派批评一定是从彼时彼地的现实出发的,专业的解读范式,是为了更深地抓牢现实,切入现实,以及最终穿透现实。相反,前理论的印象式批评,确实不那么专业主义,然而不专业,往往流于对于现实的模式化梳理与教条化感慨。故而,今后与其再讨论“80后”批评家是否专业主义,不如具体讨论其理论工具运用得是否准确合理,其理论分析是否有效地展开了文本的内在脉络,是否深入地呈现了文本的历史语境。
同样,对“80后”作家而言,和先锋文学的父辈作家相比,他们的作品反而有更多的现实主义的特征,有的时候我这个尊崇现实主义的研究者,甚至觉得太现实主义了,“故事”--带着情绪或愤怒的故事--压倒了“文学”。指责他们专业主义,我估计是完全没读过作品,只是凭借先入为主的印象,揣测他们不过是纯文学作家的徒子徒孙。
金:如何通过更加有效的叙事来重建与复杂现实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反思“纯文学”是有启发性的。但是在我这样一个以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为文学启蒙资源的读者来说,反思“纯文学”的过程中其实有不少“泼水同时倒掉孩子”的问题。当时由“纯文学”这一概念所组织出来的各种文学思潮,如现代派、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极大程度地动摇了教条的文学观念,为其后的文学实践开辟了空间。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思潮在对抗某一种政治话语及其附属的写作方式时,往往隐匿了自身携带的意识形态特性,并将其抽象化在“文学性”“纯文学”“向内转”“返回自身”之类的表述中;但是,当时对“形式”的追求“本身就蕴含着对现实的评价和批判”。在反思“纯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窘境时,如果连带着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主流视作脱离现实、拒绝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学,则是误解。
在上述“反思”的语境中,“80后”写作往往被视作个人化、拒绝对时代发言的代表。其实在这个时代里,无论再怎么沉湎于“个人生活”,只要作家认真地生活,真诚地感受世界,那么其文字中总会折射出时代、环境的力量,以及与这力量相碰撞、发自心灵深处的欲望与感受。这些“碎片”中的心灵信息,暗藏着向现实社会提供的、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思想表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写作者承担时代责任的具体方式。
至于“学院化”,你之前的梳理已经表明,确实和我们这代人的出场方式有关,这样的痕迹是无法抹除的。问题在于,何种意义上的“学院化”?其实在我看来,我们还根本够不上真正的“学院派批评”,就像你说的通过专业的解读范式来“更深地抓牢现实,切入现实,以及最终穿透现实”,我们心向往之却还不能至。今天我们讨论“80后”文学,之所以要以驳论的方式展开,正是因为此前我们大多都是通过娱乐新闻、粉丝心态、流行观察等渠道去认识“80后”,由此积聚了大量似是而非的陈腐看法,正是因为“学院派批评”缺位或不受重视的缘故。我很佩服周作人的“十字街头的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既要“眼观六路”,也要“静得下心”。如何认真读书、提高理论素养,如何借助媒体、网络等便捷多元的传播渠道表达自己的声音,将学术研究成果转换成社会的精神能量,这几者间如何营造理想、健康的互动--这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无历史感?或“反讽”的美学
黄:和前面的几种说法相比,我觉得对于“80后”文学缺乏历史感的指责,倒是一个能够打开问题视域的批评,隐含着真正有力量的交锋。李陀先生在《“新小资”和文化领导权的转移》一文中,勾勒“小资”的历史谱系,指出当今的文化领导权控制在小资一代手中,“小资文化”外在的追求是中产阶级想象,骨子里则是虚无主义。随即杨庆祥发表《80后,怎么办》一文,将李陀对于小资的讨论,落实到对于“80后”与“80后”文学的具体分析之中。杨庆祥认为:“如果非要为‘80后'的阶级属性作一个界定,似乎再没有比‘小资产阶级'更合适的了。”而“80后”的小资产阶级之梦不过是全球化资本秩序加之于我们的一种规划和想象。在这种资本秩序的迷梦中,“80后”一代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真实有效的关联点,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这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以及“搞笑”“油滑”的艺术特征,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和语气来嘲讽和戏谑。
李陀与杨庆祥的讲法,很大程度上契合我的生活实感,这种虚无的美学看起来像是“搞笑”或“油滑”,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反讽”。但我不同意对于这种生活实感的理论收纳,“80后”一代的历史性,不是“搞笑”“油滑”这种印象式的描述可以架空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当杨庆祥用“局外人”来描述“80后”时,他背后隐隐可见的分析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我用“局外人”来描述“80后”时,想到的是加缪的《局外人》,以及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的《论反讽概念》。“80后”一代有深刻的历史性,只是这种历史性只有从妥帖“80后”的理论框架中才可以发现。
金:“小资产阶级”这样的词,背后粘附着太多的概念层累与操作痕迹。在没有对概念演变与出场语境作细致梳理的前提下,我个人觉得使用这样的词语应该谨慎。将“80后”一代的立场诊断为“无历史感”,进而号召“重新回到历史现场”,显然是有自己鲜明的反拨对象的。问题是,对这些“对象”是否有充分的把握,尤其是如何把握这些“对象”在彼时语境中的意义?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时刻,“反讽者”登场,虚无主义重临,“地下室人”被召回?是什么样的历史动能,让喊着“世界,我不相信”的一代从历史和共同体中“回收自我”(借庆祥的用语)?如果今天“80后”的立场是“重回历史”,那么:首先,我们如何看待此前那代青年人“出走”的姿态?他们在刘索拉、王朔、王小波、朱文、卫慧等人笔下不绝如缕地出现,他们心怀质疑,在主流价值观边缘上徘徊,对于这些“问题青年”所呈现的意义,今天可以一笔勾销?是因为他们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选择了错误的姿态,以致我们今天要承担这笔历史性的“债务”?我们今天要重回的“历史”,就是他们曾经试图告别的“历史”吗(是一个东西吗)?其次, 我们如何看待今天的现实?到底是“80后”拒绝进入世界,还是世界拒绝、闭合了“80后”的进入?
黄:这就是我所谓的“参与性危机”,我们无法有效地参与到自身的生活之中。“参与性危机”视野下个体与共同体的疏离,是“80后”一代热衷于“反讽”的现实根源。克尔凯郭尔认为反讽是与“虚无”的游戏。很容易指责这种状态犬儒,但我对这种状态抱有历史的同情。虚无与小资是两回事。我反对虚无走向小资,但我理解虚无走向反讽。
与之对应,对于“80后”无历史感的批评,其对历史感有隐含的限定,是指向阶级反抗的历史感,大致是一种“左翼文学”视野下的认识装置。不符合这套定义的历史感就不是历史感。坦率地讲,反讽就是我们并不陌生的一套历史大叙事崩溃后的产物,不检讨往昔“左翼”所限定的历史感的经验教训,而在外部空间中--地缘政治与全球资本秩序--审视内在于中国当代史的“80后”一代的历史感,无法真切地进入“反讽”的脉络内部来讨论。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虚无的“小资”可以追溯到“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波动》,并不是偶然的。比如,王朔反讽的顽主们,就是虚无的小资的前身,而王朔恰恰是反中产阶级文化的。当然,我同意李陀与杨庆祥的地方在于,尽管虚无并不必然是中产阶级想象的结果,并不必然由资本秩序所催生,但是虚无却可以被资本秩序所收编,转化为对于微小的、具体的、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把握的小物质与小情感的执迷。
金:看过李敬泽、李洱、邱华栋等几位前辈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一本对话录,对话围绕的主题是他们这代“60后”人的文学。我发现,当年他们努力辨析的几个关键词,比如“个人化写作”,比如“日常生活”,在今天来看,不但已经成为描述那代人美学经验的标识,而且进入了文学史成为“文学史概念”。文学史经验告诉我们: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的指认,往往都是通过一两个精简而有效的关键词来“落实”的。也许是因为创作所呈现的美学面貌的模糊,也许是因为评论的阐释力不够,讨论“80后”,我就觉得很难提炼出前人那样的关键词。不过你所说的“反讽”倒是很具启发性。
就好比“五四文学”“知青文学”只是泛指某一时代、代际的文学,而“问题小说”“伤痕文学”就大致关联着某一时代文学中较为主流的美学风貌;同样,“80后文学”只是某种“自然史”的命名,暂时还看不出自觉的美学反应。所以我很关注你近年来关于“反讽”的系列研究。文学提供的是一种美学中介,我们更关注的,当是青年文学对当下时代的一种独特的反应。这种“更上一层”的关切,“反讽”这一议题能够带出来,这里面有“形式的能动性”。当然,“80后”的美学特征并不就是“反讽”所能涵盖的,我们今天探究什么是“80后”文学,只是打开讨论的空间,其中自然不乏构造的痕迹,我们期待“80后”的文学创作能够摇曳多姿,甚至期待这一创作未来的丰富性能够校正、超越我们今天的理论探讨。
延伸阅读:
金理:1981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学者、批评家,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另在《文汇读书周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书评60余篇,主要著作有《历史中诞生--一九八〇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同时代的见证》《从兰社到〈现代〉》等。
黄平:1981年生于辽宁,200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讲师,兼任《现代中文学刊》责任编辑,”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评委。主要著作有《贾平凹小说论稿》《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合著,论文集)等,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曾获《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度优秀论文奖。
本文2023-08-05 08:49:50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19979.html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