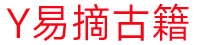古今主要字典有哪些?词典又有哪些?

古代字典和词典的编纂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早在周宣王时,就产生了我国见于著录的第一部字书《史籀》,也是当时教育儿童的一种识字课本。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配合统一文字的政策,特令李斯等用小篆编撰字书《苍颉篇》、《爱历篇》和《博学篇》。汉初,民间有人把上述三篇合为一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仍取名《苍颉篇》。以后,陆续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等。不过,以上这些原只是一般的识字读本,诸如《急就篇》,也是经庸人颜师古作注、宋王应麟补注,才使它具有查考字词的作用。真正奠定了我国古代字书基础的著作,还要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该书以小篆为主体,兼收古文、籀文,全书分为十四篇,收单字九牛五百四十三个,用读若法注音,按文字形体及偏旁构造分成五百四十部,创立了按部首收字的体例。它还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六书”理论,创立了较为系统的解释文字的方法,并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和汉代以前的文字训诂,对我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晚清以来关于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的研究,正是在《说文解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总之,在我国古代字书史上,它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晋朝吕忱的《字林》,是继承《说文解字》编纂的又一部字书名著。在唐代以前,人们还把它和《说文解字》并称,可惜不久就失传了。据《封氏闻见记》,《字林》的部首与《说文解字》相同,收字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个,较《说文》为多。《魏书·江式传》说;该书“文得正隶,不差篆意”,可见是我国第一部用隶书写成的字书。梁顾野王的《玉篇》,则是我国第一部用楷书编成的字书。今本《玉篇》虽非原本,但可知其对《说文解字》有所增订,也是一本较好的字书。
自隶书、楷书代替篆书通行以后,文字的形体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字和俗体也日益增多,于是就有人注意研究文字的异同,从而产生了唐颜元孙的《干禄字书》、辽释行均的《龙龛手鉴》、宋郭忠恕的《佩觿》及李从周的《字通》。这些字书对于我们认识一个字的异体,辨清许多形体相似的字,还是有用的;其中《字通》创建了按笔画排字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宋代的字书主要有王洙等相继修纂的《类篇》,它继承了《说文解字》和《玉篇》的体例,着重探讨字源,说明文字形体之变化并吸收了大量的新字(共收字三万一千三百十九),讲古音、古训,在字书史上有一定贡献。元戴侗撰《六书故》,改变了《说文解字》的部首编排,分为数、天文、地理、人、动物、植物、工事、杂、疑九部,每部之下各分若干细目,按字义排列。但戴侗攻击许慎用小篆作本字,使人“不知制字之本”,所以他的《六书故》采用钟鼎文字,钟鼎文没有的 字才用小篆。《四库全书总目》曾指出该书“非今非古,颇碍施行”。不过书中解释文字,也有精详的考证,作为研究古代文字训诂的工具书,还是有用的、不能一笔抹杀。
明代梅膺祚的《字汇》,是我国一部较为通俗而编排方法也比较进步的字书。它收编单字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九个,包括俗字,而僻字则一律不收,并把《说文解字》的部首简化成二百十四个,均按笔画多少排列。注音方法是先反切,后直音。对字义的解释,也较为清楚。全书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集,连首卷及附录共十四卷,每卷用表注明各部首及其所在页码,末附检字表以便查找不易辨别部首的字。这种编排方法是字书发展中的一大改进,后世多沿用。该书在明末曾风行一时,给它作补编或用其名新编的字书也很多,其中流传较广的则是张自烈的《正字通》。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张玉书等奉命撰《康熙字典》,这是我国字书第一次用字典的名称。该书继承了《字汇》和《正字通》的体例,分为二百十四部,共收字四万七千○三十五,用反切注音,释义旁征博引,可以说是我国封建时代纂修字书的一个高峰。当然,该书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乾隆时王锡侯著《字贯》一书,就对《康熙字典》的错误有所指摘和议论;但因此冒犯了康熙“御定”的威严;又因该书没有“避讳”,落了个作者满门抄斩,其著作也全部被销毁(事见《掌故丛编》)!直到道光七年(1827年),王引之奉皇帝之命,著《字典考证》,才校正了该书引书的错误二千五百八十八条。显然,错误当不限于此。第二节还要介绍清代以后人们的评论,这里从略。
我国古代专门汇集经史中文字训诂的字书有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清阮元的《经籍籑诂》,集释佛经音义的著作有唐释玄应的《一切经音义》、释慧琳的《一切经音义》,研究虚字的有清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等,都是价值较高的专著。
所谓“训诂”,就是解释词义;解释词义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用当代普通话的词语说明古代词、方言词的意义,这叫“诂”;一是说明词的定义和应用范围以及它和同义词、近义词的分别,这叫“训”。
《尔雅》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第一部训诂书,也是我国古代训诂书的代表作。此书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四库全书总目》说:“大抵小学家缀辑旧文。递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托之词。”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大约该书产生较早,春秋到汉初这一时期内,经过不少人的增补,到汉代才定型。今本《尔雅》按收录词汇的内容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等十九篇。它的内容丰富;不仅涉及到古代的一般词汇,还涉及到古代社会的人事、天文、地理和生物等方面的知识,分门别类进行了解释,是研究和查考先秦词汇的重要资料,在我国语言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这部词典成书较早,不少内容若没有后人的解释,也难以看懂。汉代以来,为《尔雅》作注的不少,但大多已失传,现存晋郭璞的注和宋邢昺的疏,即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的《尔雅注疏》。此外,宋代还有陆佃的《尔雅新义》、郑樵的《尔雅注》,清代研究《尔雅》的著作更多,最著名的有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
《尔雅》一书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被列为儒家的经典,对后世训诂书的影响颇大。后世训诂书,有的补充《尔雅》内容,有的仿其体例,且多以”雅”字命名。其中旧题孔鲋的《小尔雅》,是最早的一部补充《尔雅》之作。此后有汉刘熙的《释名》,除对字词进行简单的释义外,并进一步探求语源。魏张揖的《广雅》,则博采群书,以补《尔雅》训诂之缺。宋代补《尔雅》之作有:陆佃的《埤雅》,罗愿的《尔雅翼》。明代朱谋■的《骈雅》,专门收录冷僻深奥的词汇;方以智的《通雅》,特点在于探讨语源。清代吴玉搢收录形音歧异而意义相同的词,撰为《别雅》;史梦兰集叠字,撰《叠雅》。总之,以上诸“雅”,都是收录古籍书面语言的词典。
我国第一部专门收编各地群众口头语言的词典,当推旧题扬雄撰的《方言》(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汉末至晋初的人都说此书是扬雄所作,如应动的《风俗通义》和常臻的《华阳国志》。但是,《汉书》的《艺文志》和《扬雄传》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所以宋代洪迈便怀疑起来,以为扬雄作《方言》之说出于依托。《四库全书总目》断为“真伪皆无显据”。但该书自问世以后,研究它的名家,颇不乏其人,晋郭璞的《方言注》,更多所阐述,贡献较大,且流传至今,王国维在《书尔雅郭注后》、《书郭注方言后》曾给予分析、比较和肯定。清代学者为《方言》作校勘疏证工作的主要有:戴震的《方吉疏证》,钱绎的《方言笺疏》,王念孙的《方言疏证补》。但是,集大成之作,还是周祖谟的《方言校笺》(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续《方言》及收编方言俗语的专著还有不少,如:汉服虔的《通俗文》;唐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阙名的《释常谈》、龚颐正的《续释常谈》、李翊《俗呼小录》、明李实的《蜀语》等。
清代续《方言》的著作主要有:杭世骏的《续方言》,程际盛的《续方言补正》;考证一地方言的有: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专集诗词中方言的有:李调元的《方言藻》,专集常言俗语的有: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的《恒言录》、钱大昭的《迩言》等。
近代、现代字典和词典的编纂
近代、现代的字典和词典,是在古代这一类工具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华大字典》,编者陆费逵、欧阳博存等,中华书局1915年初版。全书收单字四万八千余,稍多于《康熙字典》,还纠正了后者的错误二千多条。尽管该书的缺点和错误也不少,但因它收字较多,在新的大型字典出版以前,还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字典。
在词典方面,《辞源》是编辑最早、规模较大的一部,该书由陆尔奎、方毅、傅运森等任编辑,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正编、1931年出版续编,后来又多次重印再版。全书收词目约十万条,内容包括普通语词、成语、典故和人名、地名、书名以及专科术语等等,按字头部首编排;每个字头先用反切注音,并附直音,再标明声韵,解释字义。词条按词头首字排列在字头之后。该书在内容和编排体例上,都吸收了前人的成果,注音简易,词条较多,引证丰富,释义明了,至今仍不失为有使用价值的词典。它的缺点是,第一、文史方面的条目多根据唐宋以来的类书,没有核对原文,往往发生错误和遗漏,而且引书不注篇名,难以查对,第二、摘引原文不标明删节,容易产生断章取义的错误;第三、有的词条去取失当;第四、没有使用新式标点;第五、一些释义上的立场、观点也有问题。
继《辞源》之后的百科性词典应数《辞海》,舒新城、张相等编,1936—1937年由中华书局分三册出版,后又再版。全书收录词条的数量和编制体例大致上与《辞源》相同。当然,《辞海》对《辞源》所存缺点错误有一些改正,如引书注了篇名,还采用了新式标点,但是,除此以外,前面所举《辞源》的缺点、错误,在《辞海》中仍多存在,特别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二书有不少共同之处,读者查考时应当注意。《辞海洲辞源》二书收编的条目不尽相同,可相互参照,取其所长。
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性的字典和词典,如杨树达的《词诠》、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朱起凤的《辞通》、符定一的《联绵字典》、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等等,至今也还有参考作用。
解放后,字典和词典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三十年来,先后编辑、出版了《新华字典》、《同音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汉语小词典》、《四角号码新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和一些专门性的字典和词典,并开始新编《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此外,还有《辞源》、《辞海》的修订、改编。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学术界协作努力下,《辞海》(1979年版)已于1979年9月出版,精装三巨册。新版《辞海》收单字一四八七二个,复词九一七○六条,插图二千余幅,计一千三百余万字。这是一部百科性辞书,主要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在改编、修订过程中,除上述1979年的新版本外,从1961年起,《辞海》还曾印刷过四种本子:(1)《辞海·试行本》,1961年出版,按学科编排,平装十六册,附总词目一册。(2)《辞海·试排本》,1963年印,供征求意见用,按部首笔画编排,乎装六十册,精装合编成三册。(3)《辞海·未定稿》,1965年出版,按部首笔画编排,精装二册。(4)《辞海》分册,按学科编排,共计分册,装订成甘八本,分两种版本:“修订稿”,已出版廿三本,1980年出齐;“修订本”已出六本。
《辞源》的修订定稿工作也于1979年完成,共四个分册,将于1981年出齐。修订后的《辞源》是一部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供文史研究工作者参考。收词限于古典文史范围,而且一般止于鸦片战争;旧《辞源》中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全部新词则一律删去。单字下注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并加《广韵》(间采《集韵》等)的反切,标出声纽。释义简明确切,并注意语词的来源及其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全部书证加注了作者、篇目和卷次,有些条目之末还附了参考书目。
宋代都市生活繁华,市民文化也随之勃兴,相继出现过众多市井文娱活动,其中有一项“说话”伎艺——也就是说书、讲故事——尤其受到士庶民众的广泛欢迎。然而因为品类繁杂琐屑,加以载籍纷歧不一,历来都缺乏缜密而详审的研讨。以所谓“南宋说话四家”为例,王国维、鲁迅、胡适、陈汝衡、王钟麟、孙楷第等近现代学者,或因所据文献不尽相同,或对资料释读存有分歧,便先后产生过各种说法;至于每一家说话流派内部所包含的具体细目,也同样聚讼纷纭,难有定论。钩稽排比相关史料,居然还牵扯到不少中外学者延续数十年之久的争论,能够从学术史的视角发现一些有意思的话题。
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作品颇感兴趣的诗人戴望舒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写过一篇《谈〈东京梦华录〉里的一个句读问题》(收入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吴晓铃编《小说戏曲论集》),就涉及“说话”伎艺中“讲史”一派艺人的家数问题。他在文中述及自己写作的缘起,乃是因为“最近读到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东方学报》第十四册第二分册。内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吉川幸次郎先生的《元杂剧之构成》那一篇。吉川幸次郎先生是日本少壮的中国学家,近年从事元曲研究,于学术界贡献甚巨”。他提到的这一期《东方学报》出版于1944年2月,此时的吉川幸次郎刚届不惑之年,但已经在日本汉学界崭露头角,数年之后还凭借《元杂剧研究》获得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此次发表的正是其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戴望舒对吉川的研究近况显然极为关注,然而在礼节性的称赞致意之后,随即就提及,他的论文中“也有一个小小的错误,那便是关于引用《东京梦华录》的句逗问题”。南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中曾经详细开列过一份包括“说话”在内的民间艺人名单,近现代学者在考察“说话人”家数的时候经常会加以征引和分析。戴望舒认为其中一段文字应当标点为“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而吉川幸次郎居然掐头去尾地读成了“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为了证明自己判断无误,戴望舒还从《东京梦华录》原书当中寻找到了重要的佐证:“同书卷六《元宵》条有‘尹常卖:《五代史》’等语,即可为吉川先生误读之证。”通过前后文的比勘互证,来坐实吉川在研读中确实存在断句失误。
平心而论,《东京梦华录》中有不少内容确实很难读懂,尤其是涉及市井民俗的部分,由于缺乏相关资料作为参考,有时几乎难以索解。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耗费二十余年时间校注此书的历史学家邓之诚就曾经大叹苦经:“断句以《伎艺》《饮食》为最难,其他讹夺俱难强解。虽力求不误,而误者必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东京梦华录注·自序》)戴望舒对此应该也深有体会,所以并没有对吉川幸次郎的误读多加苛责,而是相当体谅地说:“《东京梦华录》是一部极可爱而又极不易读的书,而遇到这种地方,文字之连上读或接下读又是毫无标准的,读错了原无足怪。”兴许是为了宽慰对方,他又附带批评道,即便是中国学者也难免会出现类似的谬误:“赵景深先生曾把‘尹常卖:《五代史》’读为‘尹常:卖《五代史》’;孙楷第先生读此节时句逗的错误又完全和吉川先生一样。”所述赵景深的断句失当,留待下文再予细说。先来看孙楷第的讹误,源自他发表在1930年《学文》创刊号上的《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其中引录《东京梦华录》此节文字,标点作“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子”,两相对照,确实和吉川幸次郎的理解相仿。据邓之诚所述,他在整理《东京梦华录》时曾经得到过孙楷第(字子书)的慷慨襄助,有不少资料“皆友人孙子书举以告我者”(《东京梦华录注·自序》),可见孙氏对此书素有研究,颇多蓄积,然而在细节方面仍不免略有疏失,足证戴望舒所说的“读错了原无足怪”,洵非虚语,并无客套。
孙楷第的这篇论文此后经过润饰,相继收入其《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以及《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等论文集中,最初在刊物上发表时所出现的那处断句错误都已经改正无误。不过仔细考察缘由,促使他修订疏漏的恐怕还未必是因为戴望舒的指摘,而是俞平伯在1931年4月发表于《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创刊号上的《〈东京梦华录〉所载说话人的姓名问题》(后收入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燕郊集》)。文章指名道姓与孙氏商榷:“考《梦华录》此节之文,极其凌乱,有联上读者,亦有联下读者。……乃孙君悉以属下,遂致所记名字悉误。”在示范了正确的断句方式应当是“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之后,俞平伯又在文章最后的附记中提到:“此文甫毕,在同书卷六‘元宵’条,歌舞百戏下有‘尹常卖五代史刘百禽虫蚁’可证。”同样通过书中的内证来判定对方的误读。孙楷第当时正供职于北平图书馆,同时还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职,就常情而言,应该很容易留意到同样在北大兼课的俞平伯的批评,据此修正自己的误读自然也顺理成章。
毫无疑问,若就文句之联上抑或属下,乃至寻求原书内证而言,早在戴望舒之前,俞平伯就已经解决了问题。不过再仔细推敲一番,宋人究竟如何“说话”的问题,实际上仍存待发之覆,即戴望舒在文章中还提到赵景深曾将其中一句读作“尹常:卖《五代史》”,可见“卖”字在上下文中到底该如何归属,依然存有分歧——邓之诚在《东京梦华录注》中将此句标作“尹常卖五代史”,便索性不予细究,含混敷衍过去了——赵景深的误读见于1940年《宇宙风(乙刊)》第二十九期上发表的《南宋说话人四家》一文,他根据孟元老的叙述,用图表的形式来展示当时说话人的家数分类情况,将“说三分:霍四究”与“卖五代史:尹常”并列,作为“讲史”类的两大派别。论文后来收入其《银字集》(永祥印书馆1946年)中,内容一仍旧贯,并无丝毫改动。究其原委,大概正如戴望舒在另一篇与这场争议相关的文章《释“常卖”》(亦收入《小说戏曲论集》)中所言,当是认为在《东京梦华录》原文中“‘说《三分》’与‘卖《五代史》’相对成文,尹常是姓名,固无可非难者”。其实类似的理解并不仅见于赵景深此文,在此之前,热衷于考证传统小说的胡适也注意到“宋代‘说话’的种类,各书说的不相同”,并在日记中通过列表的方式来比较《东京梦华录》与《都城纪胜》《梦粱录》和《武林旧事》等文献中的记载,以便考察“说话人”的流派分合。在《东京梦华录》一栏之中,就赫然列有“卖五代史”一项(参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胡适日记全编》1922年10月21日条),可见他也同样将“尹常”视作该艺人的姓名,其断句方式和赵景深完全一致。
赵景深、胡适等人依循上下文句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做出的判断似乎言之成理,不过戴望舒对这样的标点方式仍然持有异议。他在《释“常卖”》中认为“此未考‘常卖’系一专门称呼之误也。‘常卖’系一种专业之特称,今人称质库司事为‘朝奉’,称卖针线花粉者为‘货郎’,‘常卖’一辞,亦即类此”。他还特意摘录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中“方言以微细物博易于乡市中,自唱曰常卖”的记载,并进而推论说:“意者尹某原为行贩,及改业小说人,仍袭其旧称也。”强调“常卖”意为走街串巷贩卖日常货品,是当时的行当名称,不能拆开分释,而“尹常卖”则是由姓氏加职业而构成的特殊称谓。这一结论无疑是信而可征的,直到此时,这个涉及宋人“说话”的问题才算得到较为圆满的解答。
在戴望舒之后,另一位俗文学专家叶德均又写了一篇《释常卖》(收入中华书局1979年版《戏曲小说丛考》),同样批评“近人论小说的专著和文学史之类,就有把‘卖’字当着‘卖唱’、‘叫卖’之类的‘卖’字看,和前面‘说’字作对待的。因而把‘尹常’二字当作人名,在旁边加个人名号,如赵景深先生《南宋说话人四家》(见《银字集》)一文”。而他的意见与戴望舒完全相同,即认为“尹常卖”才是对这位“说话人”的正确称呼。除了戴氏先前所举证的《云麓漫钞》之外,他又征引了《铁围山丛谈》和《中吴纪闻》这两部宋人笔记中的记载,进一步证实“‘常卖’一辞,是宋人习用的方言,指街市叫卖零星什物者。……常卖既是做小买卖的称谓,而尹氏又以常卖为名,当是未入瓦市说《五代史》以前,曾经做过‘常卖人’,因而称之为尹常卖”。由于增添了新的例证,使得戴望舒所作的推论更显得坚确不移。戴望舒曾在四十年代主编《星岛日报·俗文学》周刊,约请过众多学者撰文助阵,叶德均也在受邀之列;而在吴晓铃蒐集整理戴氏遗稿的过程中,叶德均也提供过参考意见(见《小说戏曲论集》中《读〈李娃传〉》一篇编者附记),足见两人在学术上颇有交谊,叶氏在考证“常卖”一词时或许受到过戴氏的启发也未可知。至于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中华书局1964年版)、许政扬《宋元小说戏曲语释》(收入中华书局1984年版《许政扬文存》)、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等论著中也都列有“常卖”条目,各家结论基本相同,而考释更为详赡;甚至还有学者如戴不凡在《小说识小录》(收入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小说见闻录》)中,进一步寻绎宋人笔记中留存的蛛丝马迹,推测“尹常卖”的本名或为“尹昌”。尽管他们未必都参考借鉴过戴、叶两位的论文,但就时间而言,均已在两人之后了。
直接卷入这场争论之中的学者,当然会认真参考戴望舒等人的考释结果,以便修正自己的讹误。吉川幸次郎的博士论文《元杂剧研究》在1948年正式出版,其下编的第一、二两章《元杂剧の构成》就是根据此前在《东方学报》上发表的那篇论文修订润饰而成。在引录《东京梦华录》的那段内容时,吉川将原文转译为“霍四究が说三分、尹常卖が五代史”(据岩波书店1954年第二版),显然已经意识到自己先前的误读而及时加以补救。可惜的是,在六十年代初问世的郑清茂中译本《元杂剧研究》中,却不知道是由于什么缘故,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将这段文字恢复为汉语时,竟然在“尹常”旁添加了专名线(据台湾艺文印书馆1987年第四版)。据郑清茂在《译后记》中自述:“我对元杂剧虽有偏爱,但自认没有什么深刻的研究。”又说:“我翻译本书时,最感棘手的是书中所引中文资料的还原工作。”他或许并不知晓此前围绕着这段文字的标点所发生过的一系列争议,在检覈《东京梦华录》原文时又疏忽失察,没有仔细参酌吉川的日译,反而以不误为误,最终导致吉川幸次郎的一番苦心付诸东流。郑氏在《译后记》中还郑重提到:“胡适之先生、郑因百先生、董同龢先生、陈世骧先生、牟复礼先生、严一萍先生、罗锦堂学长、郑再发学兄,他们对本书的翻译和出版,都曾直接或间接地给我指示或协助。”他将“尹常”视作人名,倒是和胡适先前所作判断如出一辙,不知是否受其影响。列入这份致谢名单之中的郑骞(字因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撰有《永嘉室札记》(收入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龙渊述学》),其中有一条专门考释《东京梦华录》中“常卖”一词,依据《孙公谈圃》《云麓漫钞》和《志雅堂杂钞》等宋人笔记中的记载,指出“常卖为当时一种行业,或出入人家第宅,或沿街巷,或自设店铺,以贩卖杂货为生者也”,虽然未曾言及戴望舒、叶德均等人,可最后的结论倒是不谋而合。从其所举例证来看,又有溢出戴、叶两家范围之外的资料,想来并非有意掠美,而是无心暗合。只是在十年前郑清茂着手翻译《元杂剧研究》之际,郑骞还没有对这个问题做过仔细考辨,未能给予有针对性的指点。而对于大部分只能阅读中译本的读者而言,在这个细节上终不免被译者误导。
另一位当事人赵景深在晚年整理部分文稿,汇为《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一书,那篇出过纰漏的《南宋说话人四家》也被收入并经过了修订。赵景深与戴望舒过从甚密,在结婚时甚至还盛邀对方出任过男傧相;和叶德均之间则有师生之谊,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主持整理过叶氏的遗著,对他们两位的意见当然会格外留意参考吸取。虽然已经事隔多年,但能够亡羊补牢,避免谬种流传,还算为时不晚。
更有意思的是,在邓之诚的《东京梦华录注》由商务印书馆于1959年正式出版之后不久,与吉川幸次郎合作研究过元代戏曲的日本学者入矢义高便在日本《书报杂志》上撰写长篇书评给予极其严厉的批评。此文竟然旋即被翻译过来,刊登在《古籍整理出版动态》上,其内容“略谓校订失多于得,句读误至五十余处,注释有当注不注、注而不切,且注错者甚多。因定为低下之书,其疏漏之严重为近来中国出版注释书中所罕见”,言辞犀利刻薄却又有真凭实据,惹得自视极高的邓氏耿耿于怀,“夜中遂不寐,信心平气和之难耶!”“气坠,起坐良久,乃知又受凉矣!”(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邓之诚文史札记》1959年9月8日条)为了一探究竟,邓之诚立即致函日本友人杉村勇造,托其代为寻觅入矢义高的原文(同上,1959年9月14日条)。甚至在日本发生地震时,他还像小孩子斗气一般说道:“闻日本又遭海啸,名古屋最甚,骂我之入矢义高谅不致受虚惊也。”(同上,1959年9月27日条)而等到接获入矢义高的原文之后,他又评价说:“其辞极奚刻,指摘甚当,然亦有说可两存者。其人颇称许邓广铭、王利器、周祖谟,服其精审。予老矣!不欲与少年争得失,撰为此注颇有托意,时人恐未必能解也。”(同上,1959年9月29日条)尽管心有不甘而欲极力辩解,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存在失误。看到邓广铭等年轻一辈的学人受到对方推崇,又颇有几分失落怅惘,但也只能强作宽慰之词,聊以排遣抑郁。一个月后,他在日记中又留下一笔:“《光明日报·史学》载邓广铭等四人所为文,袭用入矢义高语句,盖赏其能骂我也。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诚然!”(同上,10月29日)指的应该是当天发表的由邓广铭、田余庆、陈庆华、张寄谦四人合作撰写的《十年来的中国史研究概述》,文中特别列有“古籍整理”一项,介绍“我们在古典历史文献的整理、注释、校勘、今译和标点断句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作为宋史专家,邓广铭对《东京梦华录注》自然会特别注意,对《古籍整理出版动态》上转载的那篇书评当然也不会错过,而批评起来也正如入矢义高那样并不客气(此文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邓广铭全集》第十卷中,涉及《东京梦华录注》的内容已经删削殆尽)。面对入矢义高和邓广铭等人桴鼓相应的批评,理亏的邓之诚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在日记中发泄一通。
入矢义高胆敢撰文批评邓之诚这样的知名史家,自然是有备而来,绝不会率尔操觚。实际上,他从1949年开始就召集同好逐字逐句地研读《东京梦华录》,所指摘的讹脱疏漏无疑都经过细致深入的考辨。历经数十年持之以恒的积累,入矢义高最终联手另一位日本宋史专家梅原郁合作译注《东京梦华录——宋代の都市と生活》,此书最先由岩波书店于1983年出版,后转由平凡社于1996年推出修订第二版,并在1999年出版了修订第三版。比起邓之诚的《东京梦华录注》来,无论是史料征引,还是文句考订,入矢义高和梅原郁的译注本都显得更为精审翔实。一方面固然是他们多年以来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结果,另一方面其实也充分借鉴了其他学者所作的考订辨析。尽管全书使用日语撰著,却非常值得翻译成汉语以供参考。而在笺注卷五中那段涉及宋代说话人家数的文字时,他们特别指出“尹常卖五代史”一句,曾经被不少学者误读为“尹常が五代史ヲ売ル”,意即“‘尹常’售卖‘五代史’”。两人随即参考戴望舒、叶德均两位的考证,对“常卖”一语加以详尽确切的注释——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论争中,这大概也算是中国学者又扳回了一局吧。
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科学。它包括古音学、今音学、北音学、等韵学等学科。
音韵学和语音学不同:语音学是对语音的客观描写,有时还利用各种实验方法,来征明语音的生理现象和物理现象;音韵学则是把语音作为一个系统来观察,它研究各种语音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语音学既然把语音当作生理现象或物理现象来研究,因此有所谓普通语音学,讲述发音器官的作用、各种语音的构成,那是适用于全人类的,只是每一个民族的具体语言还有自己的一些语音特点罢了。至于音韵学,则不可能有“普通音韵学”,因为音韵总是属于一种具体语言的,它具有很显著的民族特点,甲语言的语音系统决不可能跟乙语言的语音系统相同。
但是,音韵学又是跟语音学有密切关系的。不能想象,一个人不懂发音的道理而能把音韵学研究好。因此,我们又可以说,语音学是音韵学的基础。
汉语音韵学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传统,它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术语。我们应该用现代的语音学的理论和术语去说明它。我们不能抛开古代的理论和术语不管,因为我们必须把音韵学这份文化遗产继承下来。
研究目的
我们研究现代汉语音韵学,是为了了解现代汉语语音的严密的系统性,以便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的语音,有利于语言实践。
我们研究古代汉语音韵学,因为它是与汉语史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语言学部门。必须先深入研究了古代汉语音韵学,然后有可能研究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
音韵学也跟文字学有密切关系。有狭义的文字学,有广义的文字学。前者专门研究文字的形体;后者则研究字形、字音和字义。从广义看,音韵学又包括在文字学之中。文字学的旧名是“小学”,原来是一种识字的功课。古代的学者认为读书必先识字,因为有些古书的时代距离现代很远了,书中的文字,无论从字形方面看,从字音方面看,从字义方面看,都有许多是我们所不认识的了。而且汉字的形、音、又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假如不懂古音,则古代的字形和字义也会不懂,或者是懂得不透彻。古人把文字(字形)、音韵(字音)、训诂(字义)看成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所必备的基础知识,那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传统音韵学一向被认为是艰深的学问,甚至称为是“绝学”。其实古代的一套音韵学理论和术语,如果拿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术语来对比,加以说明,也就变为比较易懂,甚至是很好懂的东西了。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在传统音韵学中,也有一些含胡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论,和一些玄虚的,缺乏科学根据的术语,我们在这一本小书中,或者是提出来批判,或者是索性略去不提。我们力求把汉语音韵学讲得浅显一些,同时也不能因为要求浅显而损害它的科学性。希望这一本小书能够沟通古今,使读者对汉语音韵学能够得到比较个面的基础知识。
音韵学的功用
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汉语方言学、训诂学、考古学、校勘学、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古代文献学以及古籍整理等学科都有密切的联系,其作用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谈谈汉语音韵学的功用。
一、汉语音韵学是建立汉语史的前提
要研究汉语语音,指出汉语语音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指导汉语的学习和使用,以保证汉语朝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就不能不建立汉语语音史。要建立汉语语音史,首先必须研究出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声、韵、调系统,例如先秦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何,隋唐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何,元明清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何等等。只有把这些不同历史时期声、韵、调系统的面貌弄清楚,并探寻出其间的联系和发展规律,才谈得上汉语语音史的建立,而要知道汉语各个时期声、韵、调的状况,就得依靠音韵学的研究。王力先生的《汉语语音史》就是在汉语音韵学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写成的,其突出的特点是比较详细地展示出了汉语各个历史阶段的声、韵系统及拟音,指出了汉语语音发展的某些规律。
二、音韵学是进行方言研究的必备知识
汉语方言学是研究汉语各地方性口语的一门科学。要对方言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能不牵涉到方言的历史,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找出方言特点的根据,才能弄清方音的来龙去脉,才能对方音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作出合乎科学的解释;因此,要从事方音研究,就必须具备一定的音韵知识。例如“幕”字,北京话读作〔mu�〕,而广东梅县话则读作〔m�k�〕,北京人和梅县人对“幕”字的读音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异只要有点音韵学知识就会知道,原来北京话和梅县话都源自隋唐古音。在隋唐时,“幕”属于入声“铎”韵,带有塞音韵尾〔k〕,拟音为〔mɑk〕。北京人所以会把“幕”读成〔mu�〕,这是因为到元代时大部分北方话的入声韵尾发生了脱落,随着韵尾的脱落,其韵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梅县人所以会把“幕”读成〔m�k�〕,是因为入声韵尾脱落的这一现象在梅县话中至今也没有发生,由于塞音韵尾的稳定作用,其韵腹的变化很小。要进行方言研究,一般少不了进行方言调查,搞方言调查,需要亲自到方言区去口问、耳听、手记,做静态的分析描写工作,这同样需要具备音韵学知识。凡是有关方言调查的书籍,都免不了要讲述音韵学的基础知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方言调查字表》,采用的就是中古音系,目的在于古今对照,说明今音特点的历史根据和演变规律。
三、音韵学是训诂学的工具
训诂学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文字意义的一门传统学问。与训诂学关系密切的学科有音韵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文献学等,其中音韵学与训诂学的关系最为重要,是训诂学的得力工具,因为训释词义,往往需要通过语音说明问题。凡是有成就的训诂名家,无一不精通音韵学知识或本身就是音韵学大家,如清人戴震、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今人杨树达、杨伯峻、周祖谟等。《吕氏春秋·重言》中有这样一个著名的例子,足以说明音韵对于训诂的重要: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少顷,东郭牙至。……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君呿而口金,所言者莒也。”
东汉高诱对其中呿 、口金 的字注道:“呿,开;口金 ,闭。”“莒”的读音现在为jǔ,韵母ü属于闭口高元音,为什么高诱的注却说桓公发莒音时口形是张开的呢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要借助先秦古音的知识。原来“莒”在先秦属“鱼”部字,根据今人的构拟,其读音为〔kǐ 〕,韵腹〔 〕是个开口低元音,这难怪东郭牙说齐桓公发“莒”音时的口形是“开而不闭”了。如果不是靠先秦古音来说明,高诱“呿,开”的这个解释反而会使人感到莫明其妙,成为千古之谜。
在大量的古代文献中,通假字是随处可见的。所谓通假字,今天来看就是古人写别字。通假字产生的客观原因是由于它与本字的读音相同或相近,所以在写本字时才容易写成通假字(仿古另当别论)。训诂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出通假字的本字。由于语音在发展变化,有些通假字与本字的读音今天不相同了,如果不懂得古音,就很难将它们联系起来。例如:
《荀子·非十二子》:“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
其中“佛”字用“仿佛”或“佛教的创始人”去解释都不通,显然是个通假字,其本字应为“勃”。唐人杨 “佛,读为勃。勃然,兴起貌。”“佛”与“勃”的今音差异不小,一个声母是f,一个声母是b,一般人是很难将它们联系起来的;但是站在古音的角度看,二者不但韵部相同,而且声母也是相同的。怎么会知道“佛”与“勃”的声母是相同的呢这就涉及到音韵学上一个重要的结论“古无轻唇音”。根据这一结论,上古没有f这类轻唇音,凡后代读作f的轻唇音上古均读作b、p一类的双唇音。由于佛、勃在上古的读音完全相同,所以古人将“勃”写作“佛”就不足为怪了。有时候,通假字与本字之间有声转现象,不懂音韵学的人就更难想到其间的联系了。例如: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
心之忧矣,如匪瀚(一作浣)衣。
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诗经·邶风·柏舟》五章
其中“如匪瀚衣”一句,自毛亨以来的注释家多解释作“像没洗涤过的脏衣服”,比喻心中忧愁之至就像穿着没有洗过的衣服让人难受。这种解释在逻辑上讲不通,喻体和本体之间没有相似点,与下文的“静言思之,不能奋飞”也联系不起来。事实上“匪”应是“篚”的古字。《说文解字》:“匪,器似竹筐。”“瀚衣” 应即“翰音”。“瀚”、“翰”上古音同属“元”部、匣纽,“瀚”通“翰”没有问题。“衣”、“音”声母相同,均属“影”母;但是韵部不同,衣属“微”部,音属“侵”部。根据王力先生的拟音,“微”部读音为〔�i〕,“侵”部读音为〔�m〕。二者声母、韵腹均相同,韵尾不同,一个属元音韵尾,一个属鼻音韵尾,为什么“衣”会通“音”呢这就牵涉到音韵学上一个重要的音变规律“阴、阳对转”。原来在作者的方音中二字的读音是相同的,故可以通假。从通语的角度看,此二字的读音在作者的方言中发生了对转,即由阳声韵变成了阴声韵。“翰音”就是鸡。《礼记·曲礼下》:“凡祭宗庙之礼,……羊曰柔毛,鸡曰翰音。”后世遂将翰音作为鸡的代称。张协《七命》(见《文选》):“封熊之蹯,翰音之跖。”吕延济注:“翰音,鸡也。”清陈梦雷《周易浅述》卷六:“鸡鸣必先振羽,故曰‘翰音’。”“匪瀚衣”中的“匪”用作动词,义为“关……在笼子里”。全句的意思应是“如同关在笼子中的鸡”,这样喻体和本体之间才有了相似之处:不能自由自在。同时和下文的“不能奋飞”也有了照应1。
四、音韵学是学习和研究古代诗歌声律的基础
中国古代诗歌很讲究节奏和押韵,富于音乐感。特别是唐代的格律诗,为了极尽诗句乐感的抑扬顿挫、曲折变化之妙,有意将平上去入四声分成平仄两类,规定了严格的交替格律。因此,如果没有一定的音韵学修养,对古代诗歌就无法做到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欣赏,学习不好,更谈不上研究。例如:
青青子佩〔bu 〕,悠悠我思〔si�〕。
纵我不往,子宁不来〔l�〕
《诗经·郑风·子衿》二章
这章诗今天看来并不押韵,不懂音韵的人会误以为它原来就不押韵,其实在先秦是押韵的。“佩”、“思”、“来”三字同属一个韵部(之部),如果按照后面的拟音去读这章诗,其韵味马上就显现出来了。又如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t�ia〕!�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a〕!
这首诗今天看起来更不押韵,事实上在中古时期也是押韵的。“者”、“下”二字在平水韵中同属上声“马”韵。现在很多人喜好唐代的律诗,然而要真正懂得律诗的格律,学会调平仄,就非得具备一些音韵学的基础知识不可。例如古代属于仄声的入声字有相当一部分今天已变成了平声字,如果按照今天的调类去分析律诗的平仄,肯定就会出错,此以白居易的五律《草》为例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其中“一”、“接”、“别”三字在普通话中分别读作阴平和阳平,在中古都是入声字,属仄声。如果按照今音将此三字作平声对待,就会误以为“一枯荣”、“接荒城”都是三平调,“满别”与“萋萋”没有作到平仄交替。
如何辨认入声字,这成了现代人特别是北方人学习诗律的一大难关,但是只要懂得点音韵学,入声字的辨识就容易多了。
音韵学的代表人物--樊腾凤
樊腾凤(1601-1664年),邢台隆尧县西良前村人,我国著名的音韵学家 以创著《五方元音》闻名全国。樊腾凤是一秀才,清兵入关后,他积极参加反清活动,自为军师,联合本村人高唐、高殿,邻村人梁路头、贾二杆杖等人,拥载邻村人叫赵二疯子的为皇帝,抗击清兵。后来失败,赵二疯子等被杀。樊腾凤在地窖里藏了三年,写成了《五方元音》。这种字典用的是反切法,用十二进个韵母和二十个声母来拼音。十二个韵母是:一天、二人、三龙、四羊、五牛、六獒、七虎、八驼、九蛇、十马、十一豺、十二地。二十个字母是:梆、匏、木、风;斗、土、鸟、雷;竹、虫、石、日;剪、鹊、系、云、金、桥、火、蛙。用这种方法查字很方便。
《五方元音》原以木版本刊出。他的后代将木版卖给山东省东昌府一家,此人把木版带到上海用石印翻印,流行全国。上海锦章图书局印行的石印本,封面题“五方元音大全,樊腾凤先生原本”,这种版本流传很广。
非天
尚书音韵学比较难学,这和音韵学的学科特点有很大的关系。音韵学是研究古代汉语各个历史时期声、韵、调系统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传统学问。语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加之古代也没有一套科学的记音工具,是用汉字拼合去标注语音和分析语音,因而给我们今天的学习带来了很多困难。但是只要有决心,有毅力,并且方法正确,坚持练习,就一定可以掌握这门比较陌生的学问。
首先,要真正弄懂音韵学的名词术语,牢记基本概念,并且要背诵一些重要的材料,这是学好音韵学的基础。
其次,要建立“历史”的观念,要认识到古今音是不同的,并把握住语音的演变规律,正象明代陈第在《毛诗古音考》中指出的那样,“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学习音韵学,不仅要知道上古有多少声母韵母、中古有多少声母韵母等,更重要的是要清楚从上古到中古、从中古到现代的演变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把握汉语语音的特点和发展方向。
最后,学习音韵学要注重实践,除了要认真做一些音韵学作业外,还应将学的音韵学知识与方言调查、训诂、校勘、诗词格律等科研与创作活动联系起来,学以致用,这样既起到了巩固音韵学知识的作用,又可以从中感受到音韵学这门知识的实用价值。
四、音韵学的基本内容及学习要点
传统音韵学分为三个部门,即今音学、古音学和等韵学。今音学是研究中古时期 (隋唐时代)汉语声、韵、调系统的一门学问;古音学是研究上古时期(先秦两汉)汉语声、韵、调系统的一门学问;等韵学是用“等”的概念分析汉语韵母及声韵配合规律的一门学问,它通过韵图的形式展示某一历史时期的声、韵、调系统。等韵图类似于现代汉语中的声、韵配合表。到了元代以后,在传统音韵学三个部门之外,又兴起了一个新的部门“北音学”,北音学旨在研究元明清时代以北方中原话为基础的语音系统。
在学习中古音、近代音、和上古音之前,需要掌握一些音韵学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主要有声纽、字母、声类、五音、七音、清浊、等呼、韵类、韵母、韵部、摄等。声纽、字母、声类都是关于声母的概念,五音、七音是关于声母发音部位的概念,清浊是关于声母发音方法的概念,等呼、韵类、韵母都是关于韵母的概念,韵部是对韵母的归纳,摄则是对韵部的归纳。
(一)中古音
中古音是指隋唐时期汉语的语音系统。研究中古音的材料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广韵》,一项是反映《广韵》韵音系统的等韵图。
韵书是将同韵字编排在一起供写作韵文者查检的字典。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韵书是隋陆法言所撰的《切韵》。《切韵》成书于隋仁寿元年 (公元601年),全书分韵有193个之多。到了唐代,《切韵》被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韵书,其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为《切韵》增字作注的人很多。到了北宋初年,陈彭年、丘雍等人奉皇帝的诏令据《切韵》及唐人的增订本对《切韵》进行了修订。修订本于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完成,于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改名为《大宋重修广韵》,简称《广韵》。这是第一部官修性质的韵书,是《切韵》最重要的增订本。《广韵》分206韵,收有 26194字。《广韵》撰成后,一直流传到今天,《切韵》及唐人的增订本则在宋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失传,直到清代末年才陆续在敦煌石室、新疆吐鲁番及故宫等地被发现,且大多数都是一些残卷。《广韵》虽非《切韵》,但由于其未改变《切韵》的音系,所以在完整的《切韵》未出现之前,它就成了研究中古音最重要的材料。
《广韵》是一部韵书,它并没有直接展示中古的声母和韵母,但它所收的每个字都是用反切注音的,中古的各类声母和韵母自然就都包含在这些反切上下字中。所以通过对这些反切上下字进行研究,就可以得到中古的声母和韵母。清人陈澧第一个找到了通过《广韵》反切上下字求得《广韵》声母和韵母的方法——系联法,系联法的基本依据就是反切的原理,即反切上字与别切字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及声调相同。陈澧在《切韵考》一书中通过系联将《广韵》 452个切上字归纳为40个声类,将1195个切下字归纳为311个韵类。后来的学者又使用系联法对《广韵》的反切上下字进行了进一步的系联,并对系联结果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最终研究出了《广韵》的声母和韵母。本书综合前人的研究结果,将《广韵》的声母确定为37个,韵母确定为142个。《广韵》的声调有四个,分别为平、上、去、入。《广韵》的列韵本身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
为了直接展示中古音的声韵面貌,古人在撰写韵书之外又专门编制了一种等韵书,这种等韵书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声韵配合表。《韵镜》就是其中最早并且是最重要的一种,可看作是《广韵》的姊妹篇,它与《广韵》互为补充,互相参证,是考察中古音的另一重要材料。《韵镜》以七音为经,通过“清、次清、浊、清浊”等术语将七音中所含的声母区分开来;以 206韵为纬,通过四个格子将韵中所含的韵母区分开来。在声、韵交叉处便是音节代表字。这样就将中古汉语的声韵调(韵本身包含声调)及其配合规律展示出来。《韵镜》将中古声母确定为38个,韵母确定为139个。
在《广韵》和《韵镜》之后,还出现了几种和《广韵》同属一个语音系统的韵书和韵图,其中颁行于北宋的《集韵》和南宋刘渊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以及南宋郑樵的《七音略》比较重要。《集韵》是《广韵》的增修本,由皇帝诏令修订,修订的宗旨是“务求该广”,共收字 53525个,比《广韵》多出一倍多;《新刊礼部韵略》将《广韵》注明同用的邻韵进行了合并,使206韵变成了107韵。在此以前,金人平水书籍(官名)王文郁著《平水韵略》,根据同样的原则将《广韵》合并为106韵,此后出现的各种诗韵,分韵都是106韵,简称“平水韵”。唐诗的用韵和平水韵是一致的。《七音略》是一部等韵书,在性质上与《韵镜》相同,基本上反映的是《广韵》的声韵系统,在体例上与《韵镜》大同小异。
中古音的知识除以上所介绍者外,还涉及到近体诗的用韵和平仄。近体诗用韵的特点是要合于“平水韵”,或者说要符合《广韵》独用、同用的规定,要使用平声韵,并且要一韵到底,不许中途换韵。清代所编的诗韵常见的有张书玉等人的《佩文韵府》、周兆基的《佩文诗韵释要》、汤文潞的《诗韵合璧》、余春亭的《诗韵集成》和汪幕杜的《诗韵合璧》等。近体诗平仄的特点是一句之中平仄相间,一联之间平仄相对,两联之间平仄相粘,押韵句末字用平声,非押韵句末字用仄声。所谓相间、相对和相粘都是以节拍为单位的。律诗的节拍除句末一字外均由两个字所构成。
中古音是学习音韵学的基础,学习中古音首先要掌握研究系联反切上下字的系联法,这是研究中古音的基本方法;其次要熟悉《韵镜》或《七音略》的体例,再其次要比较熟练的掌握 36字母、《广韵》的声母、韵部、韵母。除此以外还应对律诗的用韵和平仄以及《集韵》、《平水韵》等韵书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
(二)近代音
近代音指元明清时代以北方中原话为基础的汉语共同语语音系统。反映近代音的韵书主要是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和明代兰茂的《韵略易通》。元代时,近代音的基础已经形成。元代以后,近代音虽有所发展,但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中原音韵》是以元代中原实际语音为依据的一部韵书,因此,它所包含的声、韵、调大体上反映了近代音的面貌。《中原音韵》共含有 20个声母,46个韵母,四个调类,其中四个调类分别是阴平、阳平(周氏于平声中分阴、阳二类)、上声、去声,它与今天北京话的四声完全一致,只是具体的归字有所不同而已。
近代音的研究虽为时较晚,但非常重要,因为从中古音到今音的许多重要变化都是在近代发生的,近音的声韵系统在近代已基本完成,如全浊声母的消失、 [ f ]、[ t t ]、[ t t á ]、[ t ]、[ t § ]、[ t § á ]、[ § ]声母的产生、零声母的增加、四呼的出现、相近韵母的合并、[- m ]尾韵并入[- n ]尾韵、入声韵的消失、平声分化为阴平和阳平、全浊上声字变为去声字、入声字分别派入到其他声调等等。上述这些变化也正是学习近代音的重点所在。学习近代音不仅要掌握近代音的声韵调,同时更要掌握上述变化的结果和规律。此外,还应了解如何根据音变规律将古代反切转换成今音的常见方法。了解这些方法不仅有助于掌握学过的音韵学知识,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切出古书上一些反切的今音。
(三)上古音
上古音是指以《诗经》、《说文解字》为代表的先秦两汉的语音系统。上古音或称古音 ,它是相对隋唐时期的中古音而言的。
研究上古声母主要依据的是先秦两汉古籍中的异文、声训、注音、重文、通假字、联绵字等材料。其方法一般是通过这些材料反映的事实证明中古的某些声母在上古是否存在。研究上古声母的几项重要结论有: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喻三归匣;喻四归定;照二 (庄组)归精说等。
研究上古韵部的材料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先秦韵文;一个是《说文解字》中的谐声字。研究上古韵部的方法是首先通过系联方法归纳出先秦韵文的韵部,然后通过《说文》中的谐声字去印证先秦韵文归纳出来的韵部并扩大每一韵部的归字。清代是上古韵部研究的鼎盛时期,先后出现的古韵学家有二三十家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有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广森、王念孙和江有诰等。上古韵部主要就是由他们逐步建立、完善起来的。清代以后研究上古韵部的学者主要有章炳麟、黄侃、王力、罗常培、周祖谟等人。顾炎武研究上古韵部的结论是 10部,江永是13部,段玉裁是17部,戴震是25部,孔广森是18部,王念孙和江有诰都是21部,章炳麟是23部,黄侃是29部,王力是29部或30 部,罗常培和周祖谟是31部。
关于上古声调清人的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三派:一派以顾炎武、江永为代表 ,他们都是用中古的四声去看待上古的声调;一派以段玉裁为代表,他认为上古没有去声;一派以王念孙、江有诰为代表,他们主张上古有平上去入四个调类。今人关于上古声调的观点主要可分为两派:一派以王力先生为代表,认为上古没有去声,一派以周祖谟先生为代表,主张平上去入四声在上古既已存在。
根据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我们将上古的声母和韵部分别确定为 31个,将上古的调类确定为平上去入4个。
上古音的研究除了声、韵、调外,一般还涉及到“阴阳对转”和“因声求义”这两项内容。所谓“阴阳对转”是指汉语的一种演变规律,即阴声韵和阳声韵(也包括入声韵)在发展过程中会发生相互转化的现象。这一规律是由孔广森首先提出,由章太炎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因声求义”是对音韵学知识的运用,它是透过字形的外表通过字音去探求字义的。这种方法所以能够成立,一方面是由于汉语特定的声音往往表达了特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是由于古籍中通假、声训、错字等现象的出现主要都是由于读音相同或相近所造成的。因声求义是清人对训诂学的重大发展,由于这一方法的出现,使古籍中的许多千年疑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
学习上古音应熟练掌握前人关于上古声母的重要结论,牢记上古声母和韵部的名称,如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喻三归匣、喻四归定、王力及本书所确定的上古声母和韵部等。这些都是学习上古音的重点所在。除此以外,还应了解阴阳对转和因声求义的基本内容。
北大中文系学生应该读哪些书籍呢下面是我精心为您整理的文学系必读书目,希望您喜欢!
语言学
1,美国结构语言学 (American linguistics)
参考书目:Hockett 《现代语言学教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Sapir 《语言论》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Bloomfield《语言论》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实验语音学 (phonetics)
参考书目: 吴宗济 林茂灿 《实验语音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PB邓斯 EN平森著 曹剑芬 任宏谟 译
《言语链——听和说的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理嘉,《音系学基础》,语文出版社
3、汉语音韵学
参考书目: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耿振声 《音韵通讲》, 河北教育出版社
唐作藩,《汉语音韵学常识》,上海教育出版社
王 力,《汉语音韵》,中华书局
《宋本广韵&永禄本韵镜》,江苏教育出版社
余乃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辞书出版社
周祖谟,《广韵校本》,中华书局
丁声树、李荣,《古今字音对照手册》
李新魁,《韵镜校正》,中华书局
杨军,《韵镜校笺》,浙江大学出版社
4、汉语史(上)
参考书目: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
——《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
何九盈《音韵丛稿》(版本原文未注明)
下面的著作只研究某一时期的语音情况:
上古:李方桂 ,《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最好将李、王、何三家对比阅读)
何九盈、陈复华,《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何九盈,《上古音》,商务印书馆
龚煌诚 ,《汉藏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唐作藩 ,《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工具书)
中古:李荣,《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最好读1956年版)
邵容芬,《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好将邵、李两家对比阅读)
张渭毅,《中古音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周祖谟,《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近代: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
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汉语音论》,商务印书馆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
5、汉语史(下)
参考书目: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
向熹,《简明汉语史》(语法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
太辰田夫(著)蒋绍愚、徐昌华(译)《中国与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
——《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宋绍年,《马氏文通研读》,北京大学出版社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6、《切韵》导读
参考书目:余乃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辞书出版社
周祖谟,《广韵校本》,中华书局
李荣,《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最好读1956年版)
邵容芬,《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现代汉语
参考书目:北大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商务出版社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
——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8、古代汉语
参考书目:
郭锡良等,《古代汉语》,商务印书馆
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
王力(主编
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