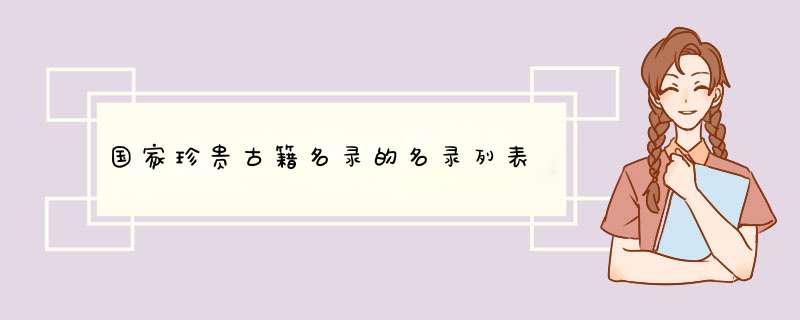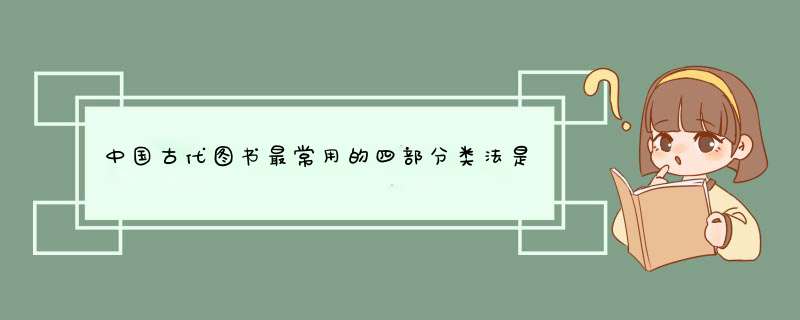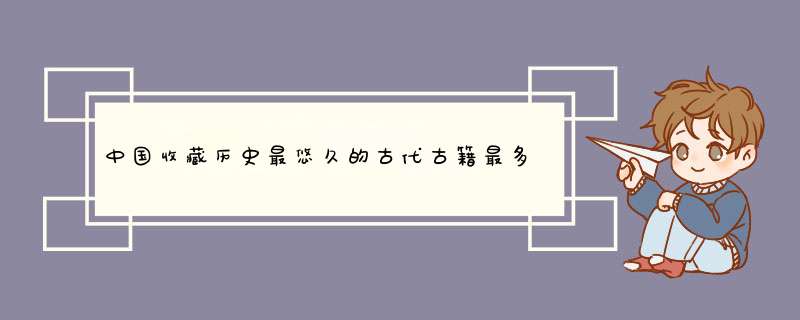中国著名文献古籍有哪些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
《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编纂说明 楚辞类 别集类 汉魏六朝之属 唐五代之属 宋代之属 金元之属 明代之属 清代之属 清前期 清中期 清后期 总集类 丛编之属 各体 《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编纂说明 楚辞类 别集类 汉魏六朝之属 唐五代之属 宋代之属 金元之属 明代之属 清代之属 清前期 清中期 清后期 总集类 丛编之属 各体 通代 断代 分体 通代 断代 通代之属 断代之属 郡邑之属 氏族之属 尺牍之属 课艺之属 诗文评类 词类 丛编之属 别集之属 总集之属 词谱之属 词韵之属 词话之属 曲类 诸宫调之属 杂剧之属 传奇之属 散曲之属 俗曲之属 杂调 鼓词 八角鼓 子弟书 马头调 木鱼歌 弹词之属 宝卷之属 曲选之属 曲谱之属(附身段谱、锣鼓谱、脸谱) 曲律之属 曲韵之属 曲评曲话之属 曲目之属 《中国古籍总目》藏书单位简称表
一、检寻图书的钥匙。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面对书籍的海洋,从何下手?这就要借助于古籍目录。
二、研究学问的向导。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目录学之所以被视为学中第一紧要,就因为它是引导治学的门径。目录学家著录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后来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使后人明确自己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向哪一方面继续探索,以免走弯路。
三、指示读书的门径。读书必须利用目录。我国古代目录学家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在编写目录的同时写序和提要。这些序和提要为我们今天阅读古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它告诉我们每部书的大致内容、性质、特点、优劣得失,使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哪些只需稍稍涉猎,哪些书中的精华值得吸取,哪些书中的糟粕应当扬弃。当然,古人衡量书籍优劣的标准不能和我们同日而语,但古人在彼时彼地的见解,对我们无疑是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四、考证学术源流。古籍目录通过小序、提要以及分类,表现一家一派之学,师承授受关系,使学术源流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有助于读者由委溯源。通过目录还可以了解古代各种学术兴衰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
五、鉴别书籍的真伪。历代的目录都是根据当时的藏书情况著录的。这就提供了鉴别书籍真伪的依据。
六、考证书籍的存亡。某些书籍大约在什么时代佚失,历代目录提供了考证的线索。 粗知一些目录学方面的常识,了解一些常见古籍目录的特点及用法,对于深入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化遗产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古籍总目》作为反映中国古籍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最全面、最重要的成果,其编纂特点如下: 一、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第一次将中国古籍书目著录为约二十万种。历来称誉中国古籍“浩如姻海”、“汗牛充栋”,但“海”和“栋”究竟有多大?八万种、十万种、十五万种,众说纷纭。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代流传的典籍,渐次由私人收藏转为公共收藏。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绝大部分的存世中国古籍,已成为国家及各地公共图书馆、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图书馆的馆藏。参与《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国内各大图书馆,所收藏古籍已涵盖现存古籍百分之九十以上品种,编纂中又吸收图书馆历年编纂的丛书、方志、家谱等联合目录成果,所录古籍收藏机构已逾干家,可以说参与“总目”编纂工作的同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对现存中国古籍,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今天可以给出约二十万种的统计数字,这是这次编纂工作的最大贡献。 二、著录了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稀见品种。现存中国古籍的总目录,理应反映全球收藏的中国古籍信息,限于人力物力,此项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古籍总目》已利用知见的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古籍收藏目录,采录大陆图书馆未见著录的古籍品种,并为稀见品种增补了海外收藏机构名称。 三、著录了现存中国古籍的主要版本。中国古代典籍的撰着与流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宋元以来,历代典籍屡经写抄刊刻、汇编选辑,版本极为复杂,人称书囊无底,难以穷尽。《中国古籍总目》的版本著录,不仅包括历代公私写抄、刻印、排印、影印之本,又综录佛道二藏,旁搜秘本僻书,兼及批校题跋,囊括所有版本类型。至如丛刻单刻、汇印选印、增刊补版、抄配补本等版本特征,形式多样,著录歧异,整合归并,多费斟酌。《中国古籍总目》对于所著录古籍的版本描述,已具初步清理之功。 四、依据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并有所突破。《中国古籍总目》沿用四部分类法类分古籍,并参酌《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增损类目,部居类分,有条不紊。如照应现代图书馆编目及庋藏实际,将“汇编丛书”单列为“丛书部”,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形成五部分类,《中国丛书综录》收录的“类编丛书”,则分归四部之首。又如明清以来方志、家族谱编纂兴盛,清季新学流行,相关译着及著述繁多,遂因书设类,特于史部增设“方志类”、“谱牒类”,子部增设“新学类”,汇录相关书籍,以便读者即目求书。 五、在编纂过程中注重人才培养。文献整理与研究中,书目指导的重要作用,久已成为共识。古籍编目似易实难,人才培养须经多年历练。近代以来,图书馆界曾涌现大量古籍编目专家,为历次全国性古籍联合目录编纂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持续多年,参与其事者多经磨练,造就了一批古籍编目骨干。然而,面对全国数千家古籍收藏机构所藏的数千万册古籍,古籍编目力量仍嫌薄弱。而古籍书目编纂是一项逐步积累、不断完善的事业,书目收罗的完备与著录信息的精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校核修订,迄无止境。《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完成,不仅为古籍整理与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书目工具,在编纂过程中,又为古籍编目队伍培养了后继人材,其中所积累的经验,有深远的意义。 六、吸收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古籍总目》初稿完成,编委会即分邀各学科专家学者参与审稿。参与审稿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来自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军事、地理、医学、科技、艺术、出版等领域,遴选及于台湾及海外。各科专家学有专长,熟精文献,认真审阅,悉心校核,拾遗补缺,多所匡正,及时反映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新成果,由此提高了《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质量,促进了学术界与图书馆界之间的交流。
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辞海编纂委员会辞海:第6版[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3]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 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周礼[M]台北:三军大学出版社,1986
[5]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6] 礼记[M]崔高维,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7] 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 郑樵通志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0] 刘昫,张昭远,贾纬,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 脱脱,张起岩,欧阳玄,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 王尧臣崇文总目[M]钱东垣,辑释上海:商务图书馆,1937
[14] 尤袤遂初堂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 张廷玉,万斯同,王鸿绪,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M]瞿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8] 永瑢,纪昀,陆锡熊,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9] 赵尔巽,柯劭忞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目录学·理论研究
中国历史上不仅产生了各类型的书目著作,而且在书目实践的基础上,也比较重视目录学理论的研究。南北朝时期,阮孝绪在《七录·序》里详细地论述了书目大小类目分类的观点及以往分类中存在的问题。如对王俭在《七志》中将历史图书附于“经典志”中的“春秋类”给予了批评:“刘氏(刘歆)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唐代毋煚在《古今书录·序》 中较充分地论述了目录学的意义,他说:“夫经籍志,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而去圣已久,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流,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将使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以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其愈乎!”这段文字一直影响着后世书目的编撰和目录学研究,怎样才能“剖析条流,甄明科部”,使学者“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免于“孤舟泳海,弱羽凭天”之苦。
南宋郑樵编撰的《通志·校雠略》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理论研究著作,他从理论上阐述了图书分类、图书收录及图书注释的观点,这些观点又在“艺文略”、“图谱略”中得到实际的应用。郑樵关于图书分类的思想,其主旨在于详明图书类例,以完成书目剖析学术源流的任务。他在《编次必谨类例论六篇》中提出了很有见解的分类原则,阐明了学、书、类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类例不明,图书无纪”,指出图书类例是否区分清楚,关系到图书的存亡和学术的发展。郑樵分类思想包含以下几个内容:一是明类例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图书,并借以保存图书的确实记载。他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学贵专门,才能世守;图书不专,泛览无归; 要做到 “人守其书”,必须做到 “书守其类”,以其“专”来区分类例。他认为,图书集中在一起就容易保管,分散就容易丢失,图谱书之所以多有亡佚,就是因为历代书目不立专类。郑樵的这种详明图书类例,把“专”作为图书分类的理论是有远见的。二是明类例可以提供学术发展情况,辨别图书内容,考察其源流演变。他说:“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类例既分,学术自身……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尽管郑樵过分地夸大了分类的作用,但他这种独到见解是值得肯定的。他批评刘歆,“七略所分,自为苟简”;批评四部分类法,“四库所部,无乃荒唐”。这种敢于批评前人疏漏的精神,对当时学术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三是注重图书分类的严谨细密,把明类例看得像治理军队一样。他说:“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主张图书应细分,有其学必有其类。郑樵根据这种思想及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不因袭旧法,创立了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算术、医方、类书、文十二类百家四百三十二种的分类体系,用于编撰“艺文略”。他的这种分类体系冲破当时盛行的四分法,把经部下的礼、乐、小学分别立类,与经书并列;把子部下的天文、五行、艺术、医方也分别独立成类,与诸子并列。他的这些做法都反映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等分类思想。四是对某些类目名称进行解释,以方便人们认识类目。如对“周官”的解释:“汉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礼,唐曰周礼,推本而言,周官则是。”对类目的解释也是为他明类例及发挥类例作用服务的。五是明确提出图书分类的原则。他认为图书应按性质各自立类,不可混杂,不同类别的书不能混杂在一起;各类图书的排列先后应有次序;同一作者的不同图书,应按图书内容各入其类。郑樵的这些原则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郑樵关于图书收录范围的思想,其主旨是通录古今存佚之书,详今略古。郑樵通录古今,是他变天下之书为一书及“会通”史学观点在目录学中的应用。他说:“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群书会记”指郑樵费“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群书会记、作校雠备论、作书目讹论”(郑樵《夹漈遗稿》卷 二)中所编的书目,这部书目即是《通志·艺文略》的初稿。郑樵关于图书收录的思想主要表现在记录亡阙图书; 记录古今所有图书,但是要详今略古;记录图谱。为了阐明他记录亡阙图书的思想,郑樵专门撰写《编次必记亡书论三篇》,他说:“自唐以前,书籍之富者,为亡阙之书有所系,故可以本所学而求,所以书或亡于前而备于后,不出于彼而出于此。”记亡书可便于后世求书,但是,“及唐人收书,只记其有,不记其无,是致后人失其名系”。他又说:“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记录亡佚之书可使源流有序。为了达到记录图书完备无遗的目标,郑樵作《求书之道有八论》一篇,提出了著名的求书八法: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尽管这套求书方法行之有效,但先秦古籍很难收集齐备,鉴此,郑樵认为应详今略古,“今有记者,欲以记百代之有无。然汉晋之书,最为希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于今为近,故差详。崇文、四库及民间所藏,乃近代之书,所当一一载也”。郑樵不仅主张记录图书,而且还要记录图谱,并专门编《图谱略》。他说:“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认为书与图各有其作用,两者不可偏废,并举出十六种书没有图不可用,如天文,非图无以见天之象;地理,非图无以见地之形;宫室,非图无以作室,“为学者而不知此,则章句无所用。为治者而不知此,则纪纲文物无所施”。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评论说:“自古提倡图画表谱,意识最清,出力最大,固未有逾于郑樵者。”郑樵关于图书注释的思想,其主旨是“泛释无义”。他认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何必再对每一种图书再加注释提要。为此,他专写《泛释无义论》一篇,主张“经入经类,何必更言经史入史类,何必更言史但陈其凡目,则其书自显。惟《隋志》于疑晦者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今《崇文总目》……每书之下必著说焉。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是繁矣,何用一一说焉。至于无说者,或后书与前书不殊者,则强为之说,使人意怠”。郑樵在这里反对的是不管需要与否一律编写提要的作法,并不是说凡书都不必注释。他又撰《书有应释论》一篇,论述其中的道理。“如史家一类,正史编年各随朝代易明,不言自显。至于杂史,容有错杂其间,故为之注释,其易知者则否。惟霸史一类,纷纷如也,故一一具注。盖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而论。按《唐志》有应释者而一概不释谓之简,《崇文》有不应释者而一概释之谓之繁。”郑樵的这种关于图书注释的思想,在《艺文略》中得到较好的应用,有的在书名下指出作者的时代及官阶,有的解释书名含义,有的简介其内容或真伪。总之,郑樵关于图书注释的思想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直至今日,仍有重要借鉴和参考价值。此外,郑樵还认为书目编撰人员应专职久任,“马司迁世为史官,刘向父子校雠天禄,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令狐德棻三朝当修史之任,孔颖达一生不离学校之官。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为了保证书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用的发挥,郑樵还提出了专人治专书和有一人总负责的书目编撰组织方法。他认为学术分工,各有其长,非其所长,不只会事倍功半,而且容易出错。他对刘向校书编目的分工组织方法深表赞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刘向、刘歆父子总负责,“出于一人之手,成一家之学”。郑樵对于中国目录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创造性地提出的新的目录学见解值得今天研究借鉴。专门研究郑樵目录学的著作有《郑樵校雠略研究》(徐家麟著,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等。
清代章学诚编撰的《校雠通义》是中国历史上继郑樵《通志·校雠略》之后的又一部目录学理论专著。章学诚生活在考据盛行的乾嘉时代,其代表作是《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前者主要体现了他的史学思想,后者集中反映了他的目录学思想。章学诚在总结刘向、刘歆以来目录学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代表了封建社会目录学方法和理论的最高成就。对目录和校雠工作来说,章学诚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仅仅是简单的分类编目,主要是通过揭示文献的思想内容、作者学术成就和师授渊源,阐明学术思想的源流和发展情况,使人们通过使用书目,深知学术之门径,探讨学术之源流,区别学科的范围,达到读书治学的目的。他赞同刘向、刘歆的学识和思想,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刘向父子能上溯源流,总结上古以来的学术思想,把学术史的内容赋予书目之中。他认为:“《辑略》……最为明道之要。……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学,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概言之,章学诚主张无论分类、编目、著录,都必须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章学诚关于书目分类的思想,强调类目应适应学术与图书发展的需要,有利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认为,分类应随时代和学术的变化而变化,“《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己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 《春秋》学家,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诸家,后世不复有其支别,四部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炽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抄辑之体,即非丛书,又非类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评点诗文,亦有似别集而实非别集,似总集而又非总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章学诚还特别重视分类的“论辨流别”作用,通过分类部次图书,使人能因类求书,因书求学。以类书为例,章学诚认为有两个种类,“其有源委者,如《文献通考》之类,当附史部故事之后;其无源委者,如《艺文类聚》之类,当附集部总集之后,总不得与子部相混淆。或有择其近似者,附其说于杂家之后可矣”。章学诚关于书目体例方面的思想,特别强调了类序和提要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的作用。他称赞《七略》的类序,“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甲乙纪数之需”。关于大、小类序的作用,他认为可起到记述学术源流、解释类名意义范围、说明类与类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作用。鉴此,一部书目必须有大、小类序,否则无法“辨章流别”。对于提要的撰写非常重视,反对南北朝时期那种“仅计部目”、“甲乙簿注”的做法。他认为只有编写提要,才能把作者的学术思想充分反映出来,“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所言有物而行有恒者,则一切无实之华言,牵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几辨章学术之一端矣!”关于提要的内容,章学诚要求具备书名的考异、作者的介绍及内容的评判等要点。他的这种关于提要的见解,值得今天目录学研究者及书目工作人员学习。章学诚关于书目著录方面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互著、别裁两个方面。为了使九流百氏之学,“绳贯珠联,无少缺逸”,他强调使用互著、别裁之法,以补充分类著录的不足。在分类著录过程中,一种书著录在某一类里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在现实中往往一种图书兼有其它学科的内容,“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记录,于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章学诚专门撰写《互著》、《别裁》两篇,对互著、别裁的概念、方法及意义作了阐述。关于互著,他说:“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表面看来,互著是个著录方法问题,实际上它不仅提高了图书分类的质量,便于考察学术发展源流,而且也发挥了图书的作用。关于别裁,章学诚说:“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这段论述极其精要地阐明了别裁的意义,分析出一种书中的某一篇章,不仅使某篇内容得到充分反映,而且对读者利用书目查检也很方便。别裁后,对原书没有任何影响。因为裁篇别出后说明原来的出处,从中也就可看出学问的流别。章学诚对于互著、别裁的论述,是对中国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贡献。关于互著、别裁两种著录方法的起始,历来有分歧意见。《七略》中有互著、别裁两种方法,但刘向父子没有这种思想,而是当时图书散乱、分工编目造成的一种失误。此后班固发现这个问题,在《汉书·艺文志》中给予纠正,删去了重复著录的图书。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中使用了互著的方法,明代祁承㸁使用了两种方法,而且简述了“通”、“互”的意义。历史上第一次详细明确地论述互著、别裁,并把两种方法提高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高度,是清代的章学诚。自此之后,学术研究人员及书目编撰人员才有了明确的思想和依据。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另一表现是关于对索引的理论和方法的论述。他说:“窍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以谓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总类。”这段论述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索引工作的研究。章学诚当时所说的只是编制图书的人名、地名、学名、官衔名的索引,此后出现的汪辉祖编的《史姓韵编》、阮元的《经籍纂诂》就是从人名、字词角度做的索引。章学诚对图书资料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有切实的评说,他利用 “道”与 “器”的关系来阐述这一问题,他说:“《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这里的 “道”指自然规律,“器”指客观事物。章学诚把这一哲学思想引入目录学中,在书中提到“六经皆掌故”、“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这里的“掌故”、“政典”、“器”都是指图书资料。人们通过阅读这些资料可得到学问,也就是得到“道”。这就是说,学术研究必须以资料为依据,这些资料“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答客问》)。他还把图书资料与学术研究比喻为“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这些精辟的见解常被后世看作重视资料工作的典范。综上所述,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是在广泛分析研究前代的书目及目录学著述的基础上形成的,为后世建立了科学的目录学理论和方法体系,不少目录学著述受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影响。
本文2023-08-03 19:51:1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23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