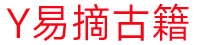和尚为何要吃素不吃肉呢?这个规定是怎样来的?

自从佛教从古老的印度传入中国,佛教的种子便在中国生根发芽,开始修建庙宇,铸造佛像,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僧人,也有很多的国人愿意信奉佛教,相信佛祖的因果轮回,人们心中也认为是要吃斋念佛,印象中那种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和尚是很少的,为什么和尚一定要吃素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在佛教之中有记载,不食三不净肉,这个原因和一位君王有关,那就是梁武帝,他有心中的推崇,推行素食,规定所有的和尚都必须食素,不得吃任何肉类的食物。
佛经中记载着和尚不能吃肉
在早期的佛教中,记载着不时三不净肉,就是亲眼见到此肉为自己所杀,亲耳听到此肉为自己所杀,见到有动物被杀的痕迹,在《梵网经》中也写到,如果佛教徒吃了肉,那么就会破坏他自己宽广的胸襟,延误自己的修行,也会使世间的凡人远离自己,在《入愣伽经》中也写到,这世间的生死流转,怨恨相互连结,都是吃肉所导致的,同时还会增长贪婪。
爱好佛教的梁武帝规定了和尚必须食素
梁武帝虽然是一代皇上,但他却信奉道教,同时它还是一个忠诚的佛教徒,史书中曾经记载,梁武帝信奉佛教,而且她非常爱学习,精通各种佛教书籍,后来还给各种佛教书籍做注释,有时还去寺庙中给和尚做讲座,在《广弘明集》中,记载了梁武帝是如何推行素食,梁武帝下诏禁止用动物作为祭祀品,要求佛教徒吃素,所以我国的一些僧人食素的习惯便一直流传了下来。
所以,从佛教古籍中的记载,到梁武帝推行吃素,僧人吃素的这个传统便一直保留了下来。
本书作者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肯尼斯•罗伊•诺曼(Kenneth Roy Norman , 1925— )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印度学家、佛教语言文献学家之一,他的专长主要是研究中古印度雅利安语。这类语言又称印度俗语(Prakrit),是相对于印度古婆罗门教与印度教的经堂语梵语(Sanskrit)而言。在学生生涯之中,他就师承可能是20世纪最为伟大的一位,同时也必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剑桥大学梵文教授贝雷爵士(Sir Harold Walter Bailey,1899 – 1996)。
贝雷爵士的学术成就其实应该专文介绍,此处只是简单提一下,即使传说他能够阅读五十多种语言的说法实在无法证实,但文献可征者,至少他可以阅读的语言中包括英、法、德、俄、意大利、西班牙、拉丁、古希腊、泰米尔、阿拉伯与日语,而由于他教书的关系,又可以说是“非常精通”梵语、巴利、犍陀罗、于阗、阿维斯塔等诸多古印度雅利安语族的语言。
与这样一位专攻伊朗语支,却同时可称为通才的老师不同,诺曼教授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之中主要专攻公元前阿育王石刻铭文的语法、语音及其语言学特性,与此同时,诺曼教授也是目前存世最为伟大的巴利语专家之一。他一生中校勘或翻译了巴利语圣典《长老偈》、《长老尼偈》、《经集》、《法句经》、《波罗提木叉》等。1983年,他还出版了典范性的著作《巴利文献》(Pāli Literature,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83)一书。
他学术生涯中的大量单篇研究文章,后来被收入巴利圣典学会(Pali Text Society)结集出版的著作集之中,达整整八卷之多。正是因为他对佛教文献学,尤其是巴利文献整理的巨大贡献,所以自1981-1994年间,他成为了具有百年历史的巴利圣典学会的会长。而且,作为英国人文学科学界的最高荣誉,他也是历史悠久的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顺便提一句,目前对汉语佛教文献学界作出空前成就的日本学者、创价大学佛教高等研究所所长辛嶋静志教授也曾在20世纪80年代到剑桥大学学习,当时其指导教授就是诺曼。并且,据辛嶋老师本人多次回忆,诺曼教授的研究风格对他的一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1994年3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邀请诺曼教授以“佛教传道协会访问教授”的名义,举行了一系列的演讲。此一演讲共分十讲,主要是从一位佛教语言文献学家的角度来谈佛教研究之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这些演讲内容,后来就结集成书(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 SOAS, London; reprinted by Pali Text Society),本译就是以此结集所成为底本。
诺曼这一系列演讲的纲领性重要程度还在于,作为一位佛教语言文献学最为顶尖的学者,他试图将本领域之中极为深奥的问题,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来向“普通读者”作一番细致入微的阐述。不过,我想预先提醒一下,即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不小的耐心与知识储备,尤其是古印度的语言知识,方能“完全读懂”这本小书之中的不少内容。
在这十讲之中,诺曼教授谈了从语言文献学角度来如何看待佛教起源的一些重要问题,着重研究了书面文字书写之前佛教文献的口传传统,并指出这种传统对后世佛教文献形成的重大影响。诺曼还在演讲中谈到了佛教与各个印度区域方言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上的佛陀究竟是讲述何种方言这一类问题的学术研究情况。后来,佛教文献被书面写定下来,而这种书面写定不仅使得比如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圣典被固定了下来,诺曼还试图表明,与此同时,这还为新的大乘经典提供了方便之门。公元前,佛教就逐渐从开始时的拒绝梵文的态度,慢慢回归到了梵语化的道路之上。但在这种梵语化的过程之中,就实际操作而言,却出现了各种文献的扭曲。诺曼正是通过各种精细的案例分析,让我们看到这些文献错误形成的原因及其过程。
阿育王是早期佛教由地方性宗教走向泛印度次大陆的宗教并最终实现国际化的一个关键。诺曼教授就同样从佛教语言文献学的角度,来分析过去关于阿育王的诸种传说,并参以有实实在在文献纪录(阿育王摩崖铭文与石柱铭文)的那个阿育王,看看何者更为真实。在整个演讲系列的最后,诺曼还以大量详实的资料来阐述佛教文献最终编纂为藏经圣典,以及整个圣典的巴利注释书传统对佛教未来的诸种影响。
从上面的简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虽然是一部概论性的普及读物,并且诺曼本人也一直在用一种更为明晰、简洁的方式来阐述佛教语言文献学的研究,但此书的信息量却同样巨大。因此它可以说是诺曼教授一生研究的一个缩影或标本,是一部真正的“大家小书”。我相信通过这本书的阅读,我们会发现,原来有些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简单问题,其实在佛教文献学家的眼里却有着完全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比如“四圣谛”、“辟支佛”、“菩萨”、“法华经”等基本概念,我们佛教界甚至包括佛教学术界都对之有着不小的误解。在很多情况下,“庸俗词源学”并非只是外行与民科的专利,即使在学界之中,它也还有很大的市场。
关于本书的翻译,我先说一下题名之中的philological以及philology的汉译问题。此一系列,我与世峰在本书之中都统一翻译为“文献学的”与“文献学”。但对此词,汉语世界则有“语文学”、“历史语言学”、“文献学”等多种翻译法,究其根底还是因为此词的原始意思难以找到完全合适的汉译对应。2017年3月14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陈怀宇教授在私人交流中建议我译为“语文学”或“语言文献学”,以与作为textual criticism的“文献学”相区别。对此问题,我其实有自己的考虑,早在2013年4月15-20日台湾佛光大学举办的“汉传佛教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研讨会上,我就发表了题名为“汉文佛教文献学的现状与未来”一文。其中我提到:
目前受西方佛教文献学的影响,很多都把佛教文献学等同于佛教学研究中的Philology。我这里稍微作一点说明。关于这个词的汉语对应翻译,有些直接对应为“文献学”,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英语中,它本来就有“语言与文献的研究”(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这一义项。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之下,这个词又会被译为“语言学”、“语文学”,因为这个词也有“古典语言、文献与历史的研究,但是目前最普通的义项是语言的科学”,而且更多的时候加上一个“比较”(comparative)的限定词,这样其语义就相对明确一点了,即有“比较语言学”的意思(The New Webster Dictioary,New York:Grolier,1968,p623)。
我在后面的西方佛教研究介绍中会提到,整个西方的佛教文献学研究,主要其实是佛教经典语言的研究,以梵、巴、藏以及其他一些包括古代汉语在内的古典佛经语言为载体的佛经的校勘、翻译以及比较研究最为核心。
正是因为西方佛教学的研究基础是一些Philology的工作,所以我在后面介绍西方的文献学研究述评方面也仅涉及这种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但是Philology并不完全等同于我所说的佛教文献学。前面已经提到了Philology还有很强烈的语言学的倾向,尤其涉及到语言学史与发展等方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的佛教文献学家,大多数都是精通佛教的古典语言如梵、巴、藏等等,并主要从事这些古典佛教文献的翻译和校订,并对这些古典语言的文法结构、发音特点、语词训诂等作全方位的探讨,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已经进入了语言学的范畴。
虽然我们看到在佛经的翻译和校订过程中,这些西方的佛教文献学家(即Philologist)也会探讨佛经的不同版本,但他们不会象汉文佛教文献学家那样把这些版本的特征与归类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只是利用这些来作为辅助工具。这可以以《法句经》的研究为例,欧洲最初是将巴利语《法句经》欧译,在中国的新疆发现梵语和犍陀罗语《法句经》以后,更激起了佛教文献学家们的研究激情。
他们做的最多的一项工作就是对这些不同文本中的平行段落(parallel passages)作一种比对性研究,比如不同语种的《法句经》之间的比较研究,这非常类似传统中国文献学中的不同版本的对勘;或者对不同文本中具有相关系的条目作交互的参考(cross-references),比如在研究《法句经》时引用古注或古书来加以辨析,这又非常类似于中国传统文献学中的他校。但有一点十分明显,我们看到佛教的Philologist(文献学家)所做的主要是在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和校订,而在传统的汉文佛教文献学中则基本不属于其工作的领域。
同样的道理,有的时候,这些Philologist也会编制一些目录,但大多数只是为了翻译和校订的方便,而不会把这些目录学本身当作一门学问。除了编制目录以外,汉文佛教文献学者还会研究中国古代佛教经目的历史演变和未来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这也是西方佛教Philologist一般所不会涉足的领域。
相比较而言,汉文佛教文献学所特有的研究范围,则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佛经的版本学,就大端而言有大藏经本的研究、藏外单刻本的研究等;佛教的目录学研究,这包括佛教的目录学史研究,佛教经目和版本书目的整理出版等;佛教的校勘学研究,这包括佛教校勘特殊情况以及处理等;佛经的辨伪研究,包括佛经的真伪辨别,产生年代、地点以及宗教背景等;佛经的辑佚研究,包括从内外典类书、总集和其它经典中辑出已经佚失了的佛教文献等。
所以我们看到在传统“汉语文献学”架构范围内的“汉语佛教文献学”就是一种以中华传统研究方法为依托,并且主要是在“汉语”这单一语种内的文献学研究。而这种单一语种内的文献研究,正如我一直在强调的,在面对佛教文献这样一种涉及到从源头的印度语言再到汉语、藏语等一系列分支语的复杂局面时,就难免会受巨大局限。
故而,虽然我已经非常明确表述了西方的philology一词与我们汉文世界之中的“文献学”有着不小的差距,前者更为倾向于语言学,尤其是“比较”语言学的学科建制。但在此我还是决定选用“文献学”这一译语,其原因如下。首先,将此词翻译成“文献学”确有成例,也是学术界的常用作法之一;其次,西方的这种(佛教)语言学研究取向,完全可以被纳入整体的、一个更大的佛教文献学研究框架之中,而且也确实应该将此东西方研究方法作一个整合。而最近一些特别优秀的汉文佛教文献学家,如辛嶋静志、左冠明(Stefano Zacchetti)等,他们的研究本身也其实是在整合了东西方两种佛教文献学研究的传统。
尤其是在左冠明的研究之中,除了传统的欧洲比较语言学血统之外,他还对汉文大藏经的版本、佛教校勘学等达到如数家珍的地步;第三,也同样是出于受众更为容易接受的角度来看,佛教“文献学”起码要比佛教“语文学”或“比较语言学”等看起来更为可亲一点,不至于那么异类而拒人千里之外。嗯,实话实说吧,本来这种干巴巴的纯学术书籍我就怕没多少人愿意看了,何况还弄上这么一个吓死人的名字呢。
这几位杰出的汉语佛教文献学家所做的,或者说是我们所梦想追求的目标,就是能在汉语佛教研究界中强化作为佛教经堂与圣典语言的梵语、巴利语、犍陀罗语,以及藏语、蒙古语、回鹘语、满语等的语言学学习,同时用这些语言为参照系,充分利用传统汉语文献学中的版本、校勘、目录、辑佚学方法,重新审视佛教文献的词义、语法等,在真正弄清楚佛教文献中的“意思”之后,再逐步开展佛教哲学、历史、文献、艺术等一系列其他研究。我真诚希望,有更多开设佛教研究相关的硕士、博士课程的学校,会将这些语言中的一种或数种当成是每位学生的入门必修课之一。
当然,我并非是说一定要每位从事佛教研究之人都精通这些文献学的基础,但毫无疑问,我们汉语佛教研究界中从事这些基础研究之人并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而这方面的重要性,又实在是无法更加强调了。比如现在大藏经之中归到安世高名下的《大安般守意经》(T602),是众多学者用以分析安世高以及早期汉语禅定文献的重要标本,但左冠明的研究就表明这根本就不是安世高所译,甚至就不是一部佛经。而真正的安世高所译,则藏在日本的金刚寺之中。那么,回过头来再看我们那些以此经作为“安世高译经”并以此为基础所作出的众多推论,又有多少价值呢?
毋庸讳言,过去国内汉语佛教界中,语言文献学,尤其是印欧语言文献学,除了以季羡林、王邦维、段晴、叶少勇等为代表的北大东语系传统,以及最近一些年来也渐渐发展起来的人民大学(惟善法师等)与复旦大学(刘震等)等少数院校之外,则可以说是大陆佛教研究的一个相当边缘的领域。
但就事实而言,正如此书之中所不断强调的,佛教文献学(当然也包括佛教汉语文献学)是过去、现在与将来一切佛教研究的基石。如果我们连佛经或佛教基本文献本来的意思都无法弄懂或真正弄懂,那又如何来谈其历史、哲学等其他问题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本小书的出版,稍微介绍一点西方最为优秀的佛教语言文献学成果。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以这个小册子为起点,将更多优秀的西方印度学、佛教学与文献学著作带到汉语学术圈子之中来,并且能够吸引更多的学子加入佛教文献的研究队伍之中。
说到此书的翻译,最早我阅读此书大概是在2008年。我在复旦之时所受的基本是传统的汉语文献学训练(我要感谢我的导师陈允吉先生与教过我文献学的陈尚君、吴格二位先生,虽然我学得很糟糕),2006年出国之后感觉眼界大开,大概以每年浏览近百本的速度囫囵吞枣地快读了不少西方佛教研究专著,也领略到西方佛教文献学研究的风采,这其中也包括此本小册子。
除我之外,这本书的主要译者是陈世峰博士,我与他是2013年9月起认识的,他是原籍新加坡的澳洲籍华人,后移居澳洲近三十年。其专业本为农学(1987年昆士兰大学农学博士),却于2007-2008年在澳洲国立大学这座佛教研究的重镇系统地修学了一年梵文,在此之后,他长年不懈地继续学习梵文与巴利文。2014年开始,他翻译了多篇诺曼教授的研究文章,我们之间的通信也主要是讨论一些专业问题。
这一年的2月18日,世峰给给巴利圣典学会的办公室主管温兰(Karen Wendland)**发信询问一篇诺曼教授论文的翻译版权事宜,次日他就收到了现在全权负责诺曼先生版权的普瑞特(William Pruitt)教授的同意电邮。普瑞特教授,圈内人都知道,也是一位成绩卓著的佛教文献学家。因此我也与普瑞特本人获得了联系,并于3月4日去信询问是否可以获得诺曼本书的翻译授权,次日他就回信说没有问题,并告诉我当年8月他会借着给缅甸政府整理缅文藏经目录的机会来新,到时候我们可以一面。后来出版社需要一个更为正式的授权,又由世峰去信获得了他们的书面首肯。
我们虽然拿到了授权,但因为2014年上半年我一直在忙于翻译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的名著《大乘佛教》(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一书,所以此书,就和我无数如空中楼阁一样的研究计划一样,拖了下来。而此年,我相信,对世峰而言也是一段在澳洲、新加坡与广州间不断奔波而忙碌的时光。
整个2015年我在教书之余,也在忙着准备几篇会议论文,9月又给左冠明编了一个汉译佛教文献学的作品集,中间除了一个月被拉去临时帮忙之外,至2016年3月总算译完了十篇文章约三四十万字的草稿,但很快又有其他一些杂事不断冒了出来。也就是在这年的11月,世峰手头上的事闲下来后问我诺曼一书的翻译情况并提出与我合译。
我当时提出一人译一半并由我统筹汉文译稿、编制译语索引,同时优先寻找国内出版社,如果不行,就由我主编的《新加坡佛教研究学刊》(The Singapore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以专刊的形式出版。这样,可同时提供网上免费下载并向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直接寄送赠刊的形式也可以起到广为流通的目的。但后来感到教书、行政,再加上杂事不断,分身实在乏力,就由世峰译完了第3-10章。所以说这本书的译成,绝大多数都是世峰的功劳,而我只不过给此书开了个头而已。
世峰的第3-10章,他在2016年9月29日就发给了我初译稿。而我的两章译稿则拖到今年2月才译完。之后我就全力将全部译稿校对了一遍并开始编制译语索引,一直到5月15日。我以修订模式给全部译稿加上意见之后发给了世峰。这份译稿,世峰斟酌之后于8月14日发还给我,我在此基础上打印出来又读了一遍,修订了一些明显的错别字、语法性错误与误译等, 于8月25日发回世峰再审,9月7日世峰的部分定稿,我们全书才算基本告成(仍待清样出来后,我再编制一个术语索引)。
世峰可能是汉语学术译界中相当少有的一位,他的母语虽是汉语,但汉语则相对他的英语程度要稍弱一点。因此他真正的强项是汉译英,就在今年年初,他只用了三四个月就译完了我几年前近7万字的长文《疑伪问题再研究》(《福严佛学研究》,2012,卷7:115-182)。其中不仅涉及到了佛教文献学的专门知识,还有海量的专用术语与技术名词,他却在如此短的时间完成了英译,实在让我吃惊。所以,他的英文理解很少会有错,而我的主要工作是对他的汉语表达作修饰与改译。当然,错译与错误表达之处肯定还是会有,在此我们真诚地欢迎任何批评意见,并将以此为鞭策,为下一版的改进作好准备。
在我对全书进行校订之际,3月10日我在新浪微博上发了一条简讯,询问有没有国内的学术出版社有兴趣。在第一时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刘赛先生就与我联系出版事宜。虽然最后此书未能在上海古籍出版,但刘先生的高情厚谊,我实在是无法忘怀,并且对没能积极回应刘先生的主动提出帮助感到万分的抱歉。
几乎与此同时,浙江大学的林晓光师弟发来信息,说他已经与中西书局的李碧妍博士联系,李博士对此书很感兴趣。11日早上复旦陈引驰师也给我发来短信,告之此书出版如有问题,他可以帮忙。3月12日午夜,北京大学的陆扬教授发来短信,强烈推荐李碧妍博士与中西书局,他的原话是:“……中西(书局)目前是国内出印度学佛教学最好的出版社,李碧妍更是最好的编辑。辛嶋的书在那里刚出。你不妨考虑独立弄一个系列,将 Norman 的两本都列入其中。我强烈推荐中西(书局)。……”3月14日,李碧妍博士就给我发来了邮件询问出版的具体事宜。
就在同一天,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陈怀宇教授也向李碧妍博士推荐出版本书。3月17日,北京大学的叶少勇教授向我推荐,并介绍了中西书局印度学系列出版情况。如果有人还嫌这些师友的推荐不够份量的话, 3月26日我在山西参加“从襄垣到锡兰:汉僧法显其生平与遗产”研讨会时,与严耀中老师饭后散步,他听说我们这本书的出版之事,也向我推荐李碧妍博士。也正是在此会议期间,北京大学王颂教授知道此书未签出版社后,提出他可以帮忙解决出版事宜。到了4月13日,复旦刘震兄发来邮件问此书是否有着落,如果没有,则可以纳入他主持的译丛。
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竟然惊动了如此多的师友,实在让我非常汗颜。同时也想借此机会真诚感谢这些师友的无私帮助,当然更要感谢李碧妍博士的学术激情、伍珺涵老师专业精细的编辑校订与中西书局对学术冷门的不懈支持,让我们这些有“特殊癖好”之人能够找到一小块自留地。
纪赟 2017年9月8日 新加坡碧山
自考/成考有疑问、不知道自考/成考考点内容、不清楚当地自考/成考政策,点击底部咨询官网老师,免费领取复习资料:https://www87dhcom/xl/
1、《搜神记》
是一部记录古代民间传说中神奇怪异故事的小说集,作者是东晋的史学家干宝。原本已散,今本系后人缀辑增益而成,20卷,共有大小故事454个。主角有鬼,也有妖怪和神仙,杂糅佛道,所记多为神灵怪异之事,也有一部分属于民间传说。
大多篇幅短小,情节简单,设想奇幻,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影响深远。
其中《干将莫邪》、《李寄》、《韩凭夫妇》、《吴王小女》、《董永》等,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残酷,歌颂了反抗者的斗争,常为后人称引。其中的大部分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想感情。
它是集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之大成的著作,搜集了古代的神异故事共四百一十多篇,开创了我国古代神话小说的先河。
2、山海经
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3、洞冥记
通过天堂地狱的鬼神生活,展示了清末民初在革命风潮中死不悔改的封建地主阶级借助鬼神迷信自我麻醉的惶恐心态。该书攻击义和团、辛亥革命,意欲将进步人士、开明学者及军械学家皆以鬼神法力打入地狱。
又鼓吹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欲等待真命紫微天子下世,以重造一个地主们所期望的中世纪圣贤国度。
4、中国神话
是由王新禧所编写,2010年5月1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这本好书主要介绍了中国传统神话里的故事和人物。暮霭昏沉的夜晚里,温暖而迷蒙的灯下,老人们徐徐道来的一个个充满奇情幻想的精彩故事,勾勒出我们儿时最美丽的梦。穿越神话的天空,在云之彼端,一个神话就是莲花一朵,一个神话就是明珠一颖。
中华神话就如一本读不完写不尽、博大精深的书,令人一世痴迷,一生探究。
5、佛门故事 神异篇
收入了历代僧人在传播佛教的过程中,或为拯救危困,或为教导行善,或为阐扬佛法,或是救人治病,或是祈福兴雨,或是预言世事,所留下的一百余则神奇事迹,均是典籍中影响深远的故事。全书分为五辑,每辑二十余个故事。文字流畅,内容通俗。
70
宗派经典
《楞伽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等经典对禅宗有较大影响。《六祖坛经》是禅宗代表性经典。
1、《楞伽经》
本经说明清净心、如来藏及阿赖耶识之教义,是禅宗以及法相宗(唯识宗)的重要经典之一,中观学派论师清辩亦援引本经解释中观空义。在印度、在中国的佛教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金刚经》
佛教经典,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由于篇幅适中,得到广泛传播,三论、天台、贤首、唯识各宗都有注疏,特别受到慧能以后的禅宗重视。
3、《大乘起信论》
《大乘起信论》,略称《起信论》,是大乘佛教的一部论书,法性宗的提纲挈领之作,相传为马鸣菩萨依据《楞伽经》所造,依据真谛三藏之弟子曹毘为其所作传记,此论为真谛于太清四年(公元550年)译。篇幅凡一卷,是自隋、唐起对汉传佛教影响很大的一部论著。
4、《六祖坛经》
《六祖坛经》,佛教经典,亦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简称《坛经》。禅宗六祖慧能说,其弟子法海集录。是禅宗的主要经典之一。
扩展资料:
禅宗思想与修行
禅宗创始于南北朝来中国的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他以佛教释迦牟尼佛“人皆可以成佛”的基础上,主张“人皆有佛性,透过修行,即可获启发而成佛”,后另一僧人道生提出“顿悟成佛”说。
唐朝初年,僧人惠能承袭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并将达摩的“修行”理念进一步整理,提出“心性本净,只要明心见性,即可顿悟成佛”的主张。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亦主张道在生活中,故世俗活动照样可以正常进行。禅宗认为,禅并非思想,也非哲学,而是一种超越思想与哲学的灵性世界。禅宗思想认为语言文字会约束思想,故不立文字。
禅宗认为要真正达到“悟道”,唯有隔绝语言文字,或透过与语言文字的冲突,避开任何抽象性的论证,凭个体自己亲身感受去体会。
禅宗为加强“悟心”,创造许多新禅法,诸如云游等,这一切方法在于使人心有立即足以悟道的敏感性。禅宗的顿悟是指超越了一切时空、因果、过去、未来,而获得了从一切世事和所有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自由感,顿见本来面目、本地风光,从而“超凡入圣”,不再拘泥于世俗的事物,却依然进行正常的日常生活。
禅宗不特别要求特别的修行环境,而随著某种机缘,偶然得道,获得身处尘世之中,而心在尘世之外的“无念”境界,而“无念”的境界要求的不是“从凡入圣”,而更是要“从圣入凡”。得道者日常生活与常人无异,而是精神生活不同。在与日常事物接触时,心境能够不受外界的影响,换言之,凡人与佛只在一念之差。
参考资料:
所谓“佛经”就是佛所说的话,佛灭度后由弟子们集结并记录下来,以供后人修行之用,你说释迦摩尼佛在世时并没有佛经传世,那就对了,因为佛祖还没灭度呢,他的法还没传完呢,弟子们也就没有整理记录他所讲的经文,当然就没有佛经喽。
好,第二个问题。佛像崇拜,以下资料是佛像的由来希望对你有帮助:
在很久很久以前,佛祖释迦牟尼佛曾居住在波斯匿王的国土上,并受到波斯匿王虔诚的供养。
一天,佛陀升上忉利天,去为其生母摩耶夫人讲法,以报答母亲养育之恩。这一去,就是九十天。
波斯匿王是极其虔诚的佛弟子,一连九十天没有见到佛陀,未听到佛陀说法,他感到怅然若失,心中似乎无依无靠。波斯匿王思念佛陀,吃不下,睡不着,急切地盼望着能早日见到仁慈的佛陀。
波斯匿王实在忍不住了,便用珍贵的牛头旃檀雕了一尊如来像。此佛像雕得精致无比,容貌神态与佛陀维妙维肖,双目慈悲地注视众生,如同佛陀在为众生说法一般,且芳香四散,沁人心睥。波斯匿王见到这尊如来像,就如同见到了佛陀一样,心生欢喜。
波斯匿王将雕好的佛像置于佛陀的座位上,每天供养、礼拜。如此,他想念佛陀之心才得到了安慰。
却说佛陀释迦牟尼在忉利天宫为母亲说法,不觉一晃就过去了九十天。其母劝佛陀赶紧回去,因为众生不能离开佛陀的教诲。佛陀深以为然,便辞别摩耶夫人,回到自己的精舍。
佛陀一进房门,只见一尊佛像离座起身,前来迎接。佛陀用法眼观这佛像来历,心中释然,便恭敬地对佛像说:“请您坐回原来的座位吧。”
随即,释迦牟尼佛对众弟子宣布道:“我涅檠后,此佛像可以为四部弟子,即此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做法事。”
佛陀说完,那佛像便坐回原来的座位。
这尊佛像就是众佛像之始祖。后人凡做佛像,均仿效这尊佛像。
之后,佛陀不再住原来的精舍,而将佛像安置于精舍之中,自己则移到一边的小精舍中居住,与佛像相距二十步左右。
释迦牟尼佛的祗洹精舍本有七重,渚国崇敬佛法,争先恐后供养佛,来听佛讲法之人络绎不断。
有一天,精舍有一老鼠偷灯油,碰翻油灯,引燃幡盖,大火遂起。一刹时,熊熊烈火便吞没了七重精舍。诸王及臣民见状,无不捶胸顿足,痛心不已。众人只道那殊胜的旃檀佛像必毁无疑,日后再也雕不出第二尊如此美好的佛像了。
大火接连烧了五天。火灭后,众人惊喜地发现,东边小精舍竟幸免于难,一点儿也没有燃烧的痕迹。众人推开小精舍之门,那旃檀佛像仍端坐无恙,毫无损伤。
众人均以为是奇迹,心生大欢喜,遂礼拜供养,重新建造精舍。那尊佛像又被安置在精舍中。
——据《出外国图记》
小乘佛教的主要经典(以汉译名称)有:《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等。大乘佛教的主要经典则有:《大般若经》、《妙法莲华经》、《华严经》、《大涅盘经》、以及《大智度论》、《中论》(龙树造)、《瑜伽师地论》(传为弥勒造)、《摄大乘论》(无着造)、《唯识三十论》(世亲造)等等。
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