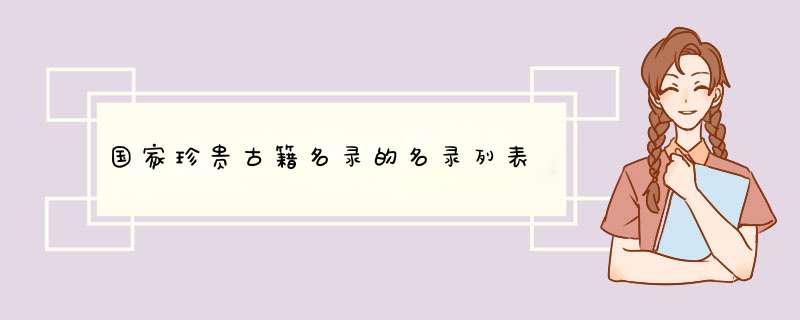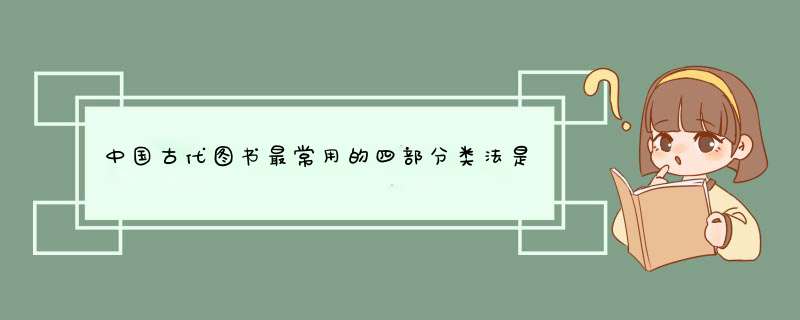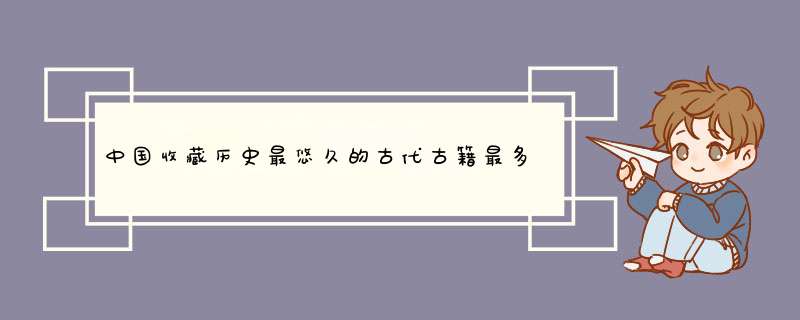具体介绍明清古籍善本版本

你这题目也太大了,给的钱也忒少了。
给你说几个
《十三经注疏》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开化纸印本
明末清初汲古阁刻十三经、十七史流传颇广,但大多是入清以后的竹纸刷印本,其实早在明末版片刚刚雕成之际,毛老太爷就用最上乘的开化纸印过一批《十三经》和《十七史》,印量极少,而且文字和后印竹纸本有不小的差别。
《说文解字义证》清道光间杨尚文连筠簃刻本
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在其生前一直没有出版,直到道光年间,杨尚文请著名小学家日照人许瀚以连筠簃的名义主持刊刻,版片刻成后放在日照许家,适逢捻军进攻日照,版片随即全毁,在此之前仅仅用此版片刷印百十来部,因此连筠簃刻本《说文义证》传世极少,向称善本,清末在京城一部连筠簃刻本卖到200两白银。
版本学·三
清末民国初年,随着西方科学思想的传入,近代图书馆在各地相继建立,古籍也成为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模式的图书馆应从1903年建浙江图书馆开始,其后陆续建立起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等,这些馆最早的基本藏书就是古籍。其中有些馆就是以收藏古籍著称的。如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以北京图书馆为例,其前身是初建于1910年的京师图书馆,它承继了清代内阁大库的藏书,珍善本颇富,既有宋元旧本,又有敦煌古写本。后补进了国子监南学藏书,并经南北访求,得南陵徐氏积学斋、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馆藏古籍日益丰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徐森玉、赵万里等先后主持善本部工作,为搜求古籍,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建立起善本甲库、乙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善本入藏更加丰富,最早一批就是 “赵城金藏”。建国之初,政务院 (即国务院) 公布了保护文物和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办法,并付诸实施。同时,文化部文物局对各地图书文物的调查、保护和收集工作也逐步进行。这一工作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各地收藏家纷起向文物局和各级人民 捐献珍贵的图书、文物,北京图书馆入藏古籍数量激增,质量优异,如周叔弢捐赠全部珍藏善本,凡七百余种,傅忠谟、翁之熹、潘氏宝礼堂、瞿氏铁琴铜剑楼、张约园、邢之襄、刘少山、赵元方等捐赠的均为一生精力所聚的宋元精本、名刊名抄。正是有了这些珍善本,才使北京图书馆与 “国家图书馆”这一称谓名实相符。
中国古籍特指1911年以前产生的图书。清王朝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完结,作为那个时代产物的中国古籍,就只有再发现,而不会再产生。从这些古籍由藏书楼转入图书馆起,图书馆古籍工作也就逐渐开展起来,其内容主要是对古籍进行鉴定、著录、分类、典藏并提供阅览,这其中就包括了版本目录学的内容。为了揭示馆藏,编出本馆的古籍书目或善本书目就成为当务之急。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即“文革”爆发前),陆续出现了反映各馆收藏的善本书目和古籍书目,代表了当时版本学的研究水平。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著录古籍,在著录项目、内容、次序、格式甚至用语等都有规定,但其成果,即版本目录,则大多数只是形式划一,质量则参差不齐。于版本目录功力深厚者,该馆的目录质量就高些,如《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又称“善本甲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等,反之,则多有未当之处。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对前人版本目录缺乏检验却仍沿用前人的经验、各家各馆之间缺乏交流、版本实践过程中缺乏总结等。
除各馆书目外,还有一些颇有价值的版本目录出版:
(1)《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作者孙殿起在北京设通学斋书店,经营古籍贩卖事业历数十年之久,他将目睹手经的书册逐一进行详细记录。由于所录基本上是清代以来的著作,其作用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续编。目中所录,一般地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的姓名、籍贯、刻版的年代等项目,如果卷数和版刻有异同,作者姓氏需要考订以及书籍内容有待说明的也偶有备注。
(2)《中国丛书综录》。1959年,上海图书馆将全国四十一个大型图书馆所藏古籍丛书编成《中国丛书综录》出版。这部《综录》吸收了旧时代各种汇刻书目和丛书目录的长处并有所发展。全书共分成三巨册:第一册为反映丛书书名的《总目分类目录》,收丛书计2797种,以其所订分类表分类。每项下列丛书名 (包括异名)、编纂者时代和姓氏、版本、子目书名及著者时代和姓氏、版本。末附《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第二册为丛书的 《子目分类目录》。第三册为丛书的《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有了这部《综录》,旧时代各种丛书目录基本上可以置之不顾了。
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版本学家有张元济、傅增湘、赵万里、王重民等。
张元济(1868—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并积极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受到 “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从1903年起,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直到逝世。他认为整理文献,非有丰富的善本书不可,便十分重视图书馆的建设,积极搜购善本书,并构筑了东方图书馆,又别辟专室,以珍藏宋元明旧刊和抄校本,名为涵芬楼。截至1932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东方图书馆藏书已达五十余万册,藏书之富居全国之冠。他在拥有这样丰富图书的环境中,开始了整理文献的工作,从1916年影印《涵芬楼秘籍》开始,连续辑印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道藏》、《续道藏》、《道藏举要》、《学津讨原》、选《影宛委别藏》、《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元明善本丛书》、《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大部头图书。除《学津讨原》据清张氏刻本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据文渊阁影印外,其余诸种版本,都是由他亲自别择、校定、整理付印的。凡经张氏校勘过的古籍,一般都有题跋,从书的内容、篇卷、版式、行款、刻工、讳字、前后序跋、文字异同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简要的考证和比较。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等,四川江安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选庶吉士。五四运动后,专心从事收藏图书和校勘图书的工作,所著主要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宋代蜀文集要》、《藏园群书经眼录》、《清代典试考略》等。他每得一书,就撰写题跋一篇,每见一善本,也写一书录,辨版本之异同,校字句之讹误,穷搜宋代刻工姓名、避讳等资料,以资鉴别版本之佐证。《藏园群书经眼录》十九卷,著录了他三十多年访书、购书、读书过程中所见各公私藏书之精品,共收录善本四千五百余种。由于这部版本目录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也就成为检验当时版本学水平的主要著作。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浙江海宁人,早年肄业于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1925年任教于清华大学,担任国学研究所王国维先生的助教,并进行诗词、戏曲和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工作。1928年至1948年,历任北平图书馆善本考订组组长、中文采访委员会委员、采访组组长、善本部主任等职。建国后,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善本特藏部主任。他在江、浙、闽、粤等地收集了不少宋元旧本和明清罕见善本。由于他见多识广、功力深厚,于版本目录有很高的造诣,他编辑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和《中国版刻图录》,出版后得到了中外学者的极大重视和高度评价。
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河北高阳人,自192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后,即任职于京师图书馆,专攻目录学。1934年由北平图书馆派往法国国家图书馆作交换馆员,后来又转往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该馆所藏中文善本图书。1947年回国后,任北京图书馆研究部主任,兼在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曾短期代理北京图书馆馆长职务,1957年起,一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他的目录学研究成就斐然,《中国善本书提要》则体现了其版本目录的造诣。1939年至1949年,他先后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宋、元、明刻本及校抄本撰写提要,总计四千四百余篇(包括补遗),汇成此书。书中所录,凡《四库全书总目》已有提要者即不再编写,惟于所缺略者补充之、错误者釐正之,更侧重于著录图书版刻或文字增删的学术价值,详录每书行格、版心尺寸、卷端题名、刻工名氏、序跋简目等,更便于检核。其着力处在考订著者爵里生平、编刊始末及与它本编次的同异,就事论事,信笔为录。介绍特定藏书版本状况,固属功力之作,用于同书版本检索,却嫌特征揭示不足。
相对于大量的版本目录来说,这一时期有关版本学的专著不够丰富,主要有钱基博《版本通义》、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毛春翔《古籍版本常谈》,从整体来说,缺乏突破性的成就。“文革”期间,像版本目录学这样的传统学术研究已不可能进行,版本学研究一片空白。
《菜根谭》是以处世思想为主的格言式小品文集,采用语录体,揉合了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和释家的出世思想的人生处世哲学的表白。《菜根谭》文辞优美,对仗工整,含义深邃,耐人寻味。是一部有益于人们陶冶情操、磨炼意志、奋发向上的通俗读物。作者以“菜根”为本书命名,意谓“人的才智和修养只有经过艰苦磨炼才能获得”。正所谓”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菜根谭》现存有大体两种不同版本--清刻版与明刻版,明刻版来自三峰主人于孔兼的题词,系日本内阁文库昌平坂学问所的藏本,据说当初刊载于明代高濂编辑的《雅尚斋遵生八笺》中。书分前后两集,前集225条,后集135条,共360条。清刻版以光绪丁亥年氧扬州藏经院木刻本为主,参以二十三年佛学书局排印本。
古籍版本决定了古籍价值,同一本书,刻的年代和刻的人不同,其价值也不同。我们常常会好奇,同是《史记》,有的价值上万,有的就值几百。其实这和我们现代的出版物是一个道理,好的出版社出的书,价格自然高,因为人家纸质好,印刷好。古籍也同理。宫里的版本通常在质量上要比民间的坊刻本好很多,因为人家财大气粗。民间的不同刊刻人和作坊(相当于现在的出版机构)之间也有差别,所以版本很重要。
工具/原料
热爱阅读
热爱古书
方法/步骤
1.从版刻的风格特点初步鉴定版本
书籍的刊刻风格依托于当时的文化政治背景,刊刻的风格有着非常强烈的时代气息,所以,掌握一个时期刻书的风格特点,对于版刻时地的考定和版本学的研究大有裨益。如宋代刻书从版式上讲,前期多白口四周单边,后期则出现细黑口,版心有鱼尾,版心常镌有本版的字数、书名的简称、卷次、叶码、刻工姓名等,早期刻本卷端多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官刻书多在卷末刻有校勘人衔名,私刻本则卷末多有题记或牌记。宋代四川、两浙、建阳、江西等四大刻书地,在用纸、字体上也各自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特征。四川崇颜体、浙江崇欧体、建阳崇柳体、江西兼而有之。而从现存古籍看,用纸方面建阳多竹纸,其他地区则多为皮纸。
2.根据原书序跋鉴定版本
依据原书的序跋断定版刻年代是常用而且比较可靠的方法,序跋书写的年份、序跋中记载的有关刻书人、时、地的情况,均可作为断定版刻年代的参考。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判定版本必须结合版刻特点等其他因素,避免重刻而保留旧序旧跋的误导,造成判断错误。
3
3.根据书牌、木记鉴定版本
古人刻书特别是坊肆刻书,常常在书前内封面镌雕牌记,与现在出版物的版权页有相近之处,注明了书名、著者、批点评论者、刊版年月、雕版的斋室堂名等。这种牌记如果不是后人故意作伪,应该是鉴定版本最直接的根据。如,国家图书馆藏《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原来根据版刻风格等诸因素,断定为宋本。20世纪70年代,山东朱檀墓出土一部此书,与国家图书馆藏本比对,应为同版,而此书有牌记称“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有明确的刊刻时间,足以帮助我们断定此书并非宋刻,而是元刻,纠正了前人编目的错误。但也经常会有后人因书版易主更改牌记或书商故意剜改旧牌记以冒充早期刻本的情况,也还有牌记写为“╳╳╳藏版”,应区分刻版处和藏版处的不同。
在古籍善本领域,如果说某种版本类型被世人误解最深,长期饱受污名,但是又深受当下古籍收藏界的重视,那恐怕非明代内府刻本莫属了。
顾名思义,明代内府刻本就是明代皇家的刻书。作为皇家的刻书,明代内府刻书上承五代、两宋国子监刻书和元代兴文署刻书,下启清代内府(武英殿)刻书,是中国古代中央官府刻书这一链条上重要的一环,也是古籍版本领域极为重要的版本类型之一。由于明代内府刻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由司礼监下属之经厂负责,所以内府所刻之书往往又被称为“司礼监本”或者“经厂本”。
周易
但是,就是这样重要的一种版本类型,却一直饱受世人非议,将其视为司礼监太监所刻,认为内府本的质量不高。事实上,关于明代内府刻书的研究,诚如古籍版本学家、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先行先生所言“真正对经厂本深入研究者并不多”,以致长期以来大多数版本学家、古籍收藏者对明代内府本的认识都还远远没有达到全面深入的程度。
明代版刻述略http://wenkubaiducom/view/2634c9d63186bceb19e8bbf4html这个链接是全文,一万字不止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殿堂的一株璀璨夺目的奇葩。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遗存两相印证,可知至迟在唐代初叶,雕板印刷术就已经出现并应用于书籍的镂版施印了。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于极盛。其间所刻,无论规模之巨、数量之大、拟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不知凡己。本文即略述明代版刻的源流递嬗,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斧正。
一、明代版刻大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无庸置言,中国古籍刻印史的鼎盛时期出现于明绝非偶然,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结果,是社会需要的必然。具体些说,其原因大抵有四:
1、明王朝文制政策的需要
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众削平群雄,驱逐元统治者至漠北,在金陵(今南京)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建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
明太祖出身于农家,苦无学术。但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他深谙“武定祸乱,文治太平”这一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在国事初定的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诏谕中书省:“朕恒谓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行教化,施教育,在此可以说是作为基本国策而颁示的。欲行此道,图书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明洪武时期,屡次下诏颁《四书》、《五经》、《通鉴纲目》、《说苑》等有补“教化”的书于学校。朱元璋只能说粗通文墨,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助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冀使明王朝能“永延帝祚”的书。如洪武六年(1373年)成《祖训录》,垂训子孙说:“后世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违祖训,亡无日矣!”在这里,图书成了教育其后代恪守祖宗成法,以使帝位罔替的重要手段。
其实,早在明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对图书事业显现出了极大兴趣。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一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发兵攻灭陈有谅,即下令访求遗书。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则云:“徐达入北京,封其库府图书宝物。”由此可见,对图书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视,对明太祖来说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是其大政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元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国近百年,文化事业相对落后,书业亦然。据统计,现存元人旧刻不过六、七百部,仅及两宋所遗之太半,就很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明太祖历百难千劫始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大业,通过重振书业复兴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其统治政策的需要,也是摆在明王朝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亦即明代书业极隆极盛的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明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有利于书业发展的举措,就是上述政策的具体化。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同时免去税收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可见在明太祖心目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业,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上的。二十三年冬,则“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亦见《明会要》)前者是通过让利于民来刺激书业的发展,后者则是由中央政府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图书刊刻活动。从官购图书予民刊刻而言,又颇有点民办官助的味道。明王朝对书业的重视,可以说不遗余力了。明享国270余年,自洪武至崇祯历十七帝,其间固然不乏昏庸糊涂,乃至胡天胡地的皇帝,对书业却基本上采取保护、扶持政策,这对明代书业的发展、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
2、学术发达,著述丰富,出版政策相对宽松
文祸不断,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书史的一大特色。类似事件,明代也时有发生。但查诸史籍,除了攻讦程、周、张、朱之学的“惑世”之说,或直接与政治斗争有牵连的著述,如明成祖诏令焚毁有干靖难的史料就是一例,对于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明政府干涉并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剧增加,丛书、类书的编辑亦十分活跃。清黄稷虞《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15,725种,而合诸家书目所载,元人著述不过三千余种。其因除明代立国时间较长外,与元代书禁森严亦不无关系。《元史•刑法志》载:“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大明律》中则看不到这样的禁令。明万历间,廷臣冯琦借焚毁李贽著作之机,上《正士习疏》,建议:“一切坊间新说,皆令地方官杂烧之。”疏进不纳,才使祖龙之火,未见于明,亦可看出明朝的文禁远不似元及清前期苛峻。著述大增,图书编辑活跃,使书业成为有源之水;文禁松施,则为书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
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比较于元代也是相当宽松的。据清蔡澄《鸡窗丛话》所记:“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明代则不然,不仅没有这样的繁文缛节,层层把关,逐级审查的图书出版制度,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无论官府、私宅、坊肆,拟或达官显宦、读书士子、太监佣役,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以至“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没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长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多则以滥,不能不说是一个弊病,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刻书之盛。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2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数,没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出版政策,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
3、经济发达,图书消费市场活跃
明太祖出身于农家,了解下层百姓疾苦,建立明王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的政策,就如他所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至洪武十八年(1385年),粮食产量已是元时的两倍。永乐时经济发展更快,“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栗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库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四方百货,倍于往时”。保证了生存需要之后,才谈得上更高层次的图书消费。
明中叶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扩大,通贩贸易活跃,成为刺激书业发展的催化剂。其对书业的影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明显的表现:
其一: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图书消费群体更为广泛,相对而言这部分人在经济上较为充裕,有余资购读书籍。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增多,为图书提供了更多的相对集中稳定的集散地。
其二:图书是商品。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便捷的交易手段,图书贸易也更为活跃。明嘉靖《建阳县志》载:“书坊街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说明当时的图书行业,已经出现了专事贩运,贸易的商贩。坊肆除了坐店销售自己的图书外,也干起了批发的生意。如织的贩者,大抵类似于今天的书商,在图书流通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三:市民阶层扩大,促使市民文化蓬勃发展。明嘉靖之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也可以说是“市民文学”的锓梓激增,成为书业中最主要的品种之一,就是以市井细民的需要为基础的。而在嘉靖之前,此类书鲜见梓行,其中当然有市场的规律在起作用。
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陆容为明成化间进士,以明时人记明时事,应该是可信的。如果说明初是书业的恢复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其中又以嘉靖、万历为极盛。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之后的出现和缓慢成长,对书业的发展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
4、制书材料生产进步,为书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所说的“器”指的是纸、墨、笔、砚等关系书业兴衰的物质材料,也是书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举例来说,现今所能见到的元代旧刻,以建宁所出为最多,其地造纸原料丰富,纸张产量较大是一个重要原因。进而论之,元代纸、墨、笔、砚的生产远逊于两宋,书业之不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和图书有关的材料制作业和书业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材料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书业的需要,书业兴盛又会刺激材料业的进步。明代,两者之间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互动的。
明代纸、墨、笔、砚的制作,无论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丰富,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以笔而言,明笔一改元时笔毫软散的习尚,硬毫成为时兴。明陈继儒《泥古录》称:“笔有四德,锐、齐、圆、健”,强调的就是笔毫要劲健有力,富有弹性。元及明初刻书,盛行赵(孟頫)体,尤其元中叶之后,有刻几全为赵字风范。明中叶之后,仿宋刻本蔚然成风,字多为欧、颜体。赵体纤弱,笔毫宜柔;欧、颜体遒劲有力,笔毫宜硬。可见,制笔工艺的改革,实则就是当时书法风格的反映,当然也影响到刻书的用字。
生产规模扩大,分布地域广泛,新品名笔后来居上,是明代笔业的又一特点。其时,元代始崛起的湖笔如日中天,湘笔之盛,几可与湖笔并驾齐驱。与此同时,京笔异军突起,成为北方笔业的中坚,时人称“南有湖笔,北有京笔”,即此之谓。名笔佳品增多,书家誊稿,根据所书字体需要对笔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明代尤其是晚明有不少精美的写刻本传世,和笔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
明代制墨业一扫元代颓势,制墨名家倍出,流派众多,墨质精良,墨式新奇,有人将此比喻为诗之盛唐,词之宋时,诚不为过。中国古代有关墨的代表性专著,如程君房的《墨苑》、方瑞生的《墨谱》、李孝美的《墨谱》、万寿祺的《墨志》,皆诞于明,足征其时墨业之盛。以晚明印本而论,距今已逾三个半世纪,不少传世之本墨色仍显莹润亮泽,宛若新印,可见墨质之佳。明代的制砚业,亦颇发达。入明之后,传统的名砚如端砚、澄泥砚等枯木逢春,再入佳境,一些新开发的砚材亦负盛誉,如北京的潭柘紫石砚、东北长白山的松花石砚,四川的嘉陵峡砚等,名色繁多,无复一一列举。
书之所以为书,正赖纸张为其载体。明代造纸业的发展,更可谓盛况空前。清康熙《上饶县志》记明时江西上饶县石塘镇“纸厂槽不下二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十人。”也就是说,一地纸坊用工,多达三百至六百人,推及全国,纸业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明代不仅民间造纸,宫廷内府也造纸。据万历《大明会典》等书载,司礼监有制纸匠六十二人,所制纸品名色有宣德纸、大玉版纸、大白版纸、大开化纸、毛边纸等。
造纸业的大发展,为明代书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明刘若愚《明宫史》载《佛经一藏》的用纸情况:共需用白纸45,023张,黄毛边纸570张,白户油纸10,395张。明人喜编印大型的丛书、类书、文集,动辄一部书数百卷上百册。明代产生的一些大型著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白话长篇小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医药、农业著作;《筹海图编》等军事著作,都是页数以千计的鸿篇巨制。没有纸张的大量生产,这类图书锓梓传世根本无法想象。
明人对印书用纸颇有研究,或者正因为书业之盛,才引起学者的关注。明朝的大学问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就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闽中纸短窄熏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值最廉。”明代纸的名色很多,大约逾百种,但除明初承元余绪,有过少量的黄白麻纸本外,主要分绵纸、竹纸两类。绵纸以桑皮为主料,竹纸则采用竹子的纤维为原料。
明代刻书,早期常见用白、黄绵纸,嘉靖、隆庆间用白绵纸多,也有少量竹纸印本,晚明则多用竹纸。一般来说,嘉靖之前的绵纸质佳,纸质莹洁,有如玉版,韧性亦佳;隆庆之后,所制则较为粗厚。竹纸薄且易老化,但绝少虫蛀。明谢肇淛说:“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所谓“丑恶极矣”,指的就是竹纸。相对于绵纸而言,竹纸质较次而价亦廉。明中叶之后,国用不足,民生凋敝,易绵而用竹,正是物力艰难在书业上的反映。明嘉靖之后,坊刻本大行于世,坊肆为降低成本而用竹纸,是图书商品化的必然结果,谢氏以书论书,以纸论纸,未免有些偏激了。
本文2023-08-05 20:02:53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246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