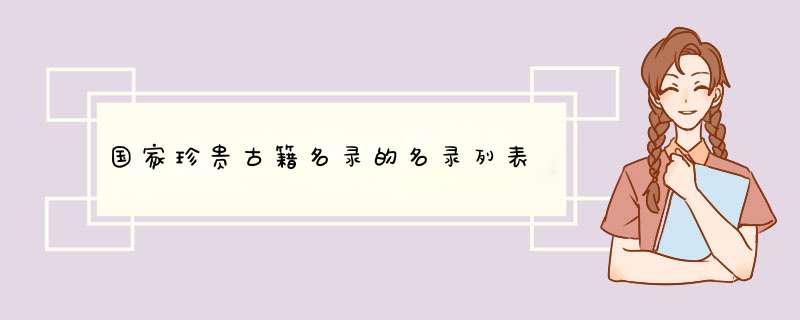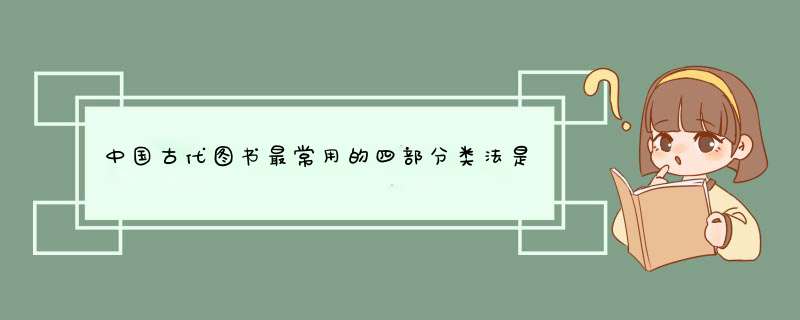经典的书?

古代百科资料必读书
北堂书钞
(隋)虞世南编
艺文类聚
(唐)欧阳询等编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
初学记
(唐)徐坚等编,中华书局1962年整理出版,1980年重印
太平御览
(宋)李等编,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出版
册府元龟
(宋)王钦若、杨亿等编,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出版,1982年重印
玉海
(宋)王应麟编,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据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影印出版
三才图会
(明)王圻、王思义父子编纂,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古今图书集成
(清)陈梦雷等编,1980年中华书局、巴蜀书社联合出版
中国历代文献精粹大典
门岿主编,学苑出版社,1990年
查考古籍必读书
古籍流传
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1933年编印,中华书局1960年重印
现存古籍
四库全书总目
清永溶等撰,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出版
古籍丛书
中国丛书综录
上海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59至1962年出版,共3册
四部丛刊书录
孙毓修编,商务印书馆,1922年
四部备要书目提要
中华书局1936年编印
丛书集成初编目录
商务印书馆编,中华书局1983年重印
古籍版本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
清邵懿辰撰、邵章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重印
亭知见传本书目
清莫友芝撰、莫绳孙编,上海扫叶山房,1923年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6年、1990年分别出版其经部和丛部
善本提要
中国善本书提要
王重民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古籍辨伪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55年
伪书通考
张心编撰,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
查考传记资料必读书
日记
清代道咸日记知见录
陈左高编,刊《文教资料》1990年第5期
三十五种近代日记书录
丁丁编,刊《文教资料》1988年第6期
现当代日记篇目选录
乐齐编,刊载《文教资料》1989年第5期
现代外国日记译作书目提要
孙继林辑,刊载《文教资料》1990年第5期
年谱
中国历代年谱总录
杨殿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来新夏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疑年录
疑年录汇编
张惟骧编,1920年小双寂庵刻本
历代名人生卒年表
姜亮夫纂定,陶秋英校,初版于1937年,中华书局1956年重印
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
吴海林、李延沛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释氏疑年录
陈垣撰,中华书局,1964年
传记资料
二十五史人名索引
中华书局1935年初编,1956年重印
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
张忱石、吴树平编,中华书局,1979年
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
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编撰,中华书局,1982年
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增订本)
昌彼得等编,王德毅增订,台北鼎文书局1977年至1980年出版,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出版
元人传记资料索引
王德毅、李荣村等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于1979年至1982年出版,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出版
明人传记资料索引
昌彼得等编,台北中央图书馆,1978年
四朝学案人名索引
世界书局,1936年
宋元方志传记索引
朱士嘉编,中华书局,1963年
北京天津地方志人物传记索引
高秀芳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清代碑传文通检
陈乃乾编,中华书局,1959年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朱保炯、谢沛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人物图像
中国历代名人图鉴
苏州大学图书馆编著、瞿冠群、华人德执笔,上海书画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人画像汇编
林明哲编,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年
清代学者像传
第一集由清代叶兰台撰绘,商务印书馆1930年影印出版;第二集叶恭绰编绘,商务印书馆1953年影印出版
明清人物肖像画选
南京博物院供稿,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编辑出版
历代古人像赞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无双谱
清代金古良绘,中华书局1961年
晚笑堂画传
清上官周编撰,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
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
第一届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
《东方》(魏巍)
《李自成》(第二部)(姚雪垠)
《将军吟》(莫应丰)
《冬天里的春天》(李国文)
《芙蓉镇》(古华)
第二届
《黄河东流去》(李)
《沉重的翅膀》(修订本)(张洁)
《钟鼓楼》(刘心武)
第三届
《少年天子》(凌力)
《平凡的世界》(路遥)
《都市风流》(孙力、余小惠)
《第二个太阳》(刘白羽)
《穆斯林的葬礼》(霍达)
《浴血罗霄》(萧克)
第四届
《白鹿原》(修订本)(陈忠实)
《战争和人》(王火)
《白门柳》(刘斯奋)
《骚动之秋》(刘玉民)
第五届
《抉择》张平著群众出版社
《尘埃落定》阿来(藏)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长恨歌》王安忆著作家出版社
《茶人三部同》(1、2)王旭烽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鲁迅文学奖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1997-2000年)
各单项奖获奖作品名单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
《鞋》 刘庆邦 《北京文学》
《清水里的刀子》石舒清 《人民文学》
《吹牛》 红 柯 《时代文学》
《厨房》 徐 坤 《作家》
《清水洗尘》 迟子建 《青年文学》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
《梦也何曾到谢桥》叶广芩 《十月》
《被雨淋湿的河》鬼 子《人民文学》
《永远有多远》铁 凝《十月》
《吹满风的山谷》衣向东《橄榄绿》
《年月日》阎连科 《收获》
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
《落泪是金》何建明《中国作家》 中国青年出版社
《远东朝鲜战争》王树增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西部的倾诉》梅 洁 《报告文学》
《中国863》李鸣生《北京文学》山西教育出版社
《生死一线》 杨黎光 《深圳特区报》《报告文学》
全国优秀诗歌奖获奖作品
《羞涩》 杨晓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曲有源白话诗选》 曲有源 作家出版社
《地球是一只泪眼》 朱增泉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西川的诗》 西 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
《纯粹阳光》 曹宇翔 明天出版社
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获奖作品
《大雅村言》 李国文 东方出版中心
《山居笔记》 余秋雨 文汇出版社
《精神的归宿》 朱铁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张抗抗散文》 张抗抗 解放军出版社
全国优秀理论评论奖获奖作品
《"五四"文化革命的再评价》 陈 涌 《文艺报》
《一九O三:前夜的涌动》 程文超 山东教育出版社
《12个:1998年的孩子》 何向阳 《青年文学》
《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 韩子勇 百花文艺出版社
《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 钱中文 《文学坪论》
1995-1998年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获奖作品
《济慈诗选》 屠 岸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堂吉诃德》 董燕生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奥德赛》 王焕生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秧歌》 董 纯译 法国"中国之蓝"出版社
《圣殿》 陶 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中国作协(1998-2000)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
长篇小说
《中国免子德国草》《吹响欧巴》《大绝唱》《属于少年刘格诗的自白》
中短篇小说集
《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 《永远的哨兵》
童 话
《笨狼的故事》
散 文
《中国孩子的梦》《小霞客西南游》《怪老头随想录》
诗 歌
《我们去看海》《笛王的故事》
幼儿文学
《幼儿园的男老师》
寓 言
《美食家狩猎》
科学文艺
《非法智慧》
传记文学
《严文井评传》
纪实文学
《黑叶猴王国探险记》
青年作者短篇佳作
《村小:生字课》(诗歌) 《单纯》(小说)
将其他单位藏书误标为河南省图书馆藏书
(1)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书目中,书名编号9508的《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宋章如愚辑,元延祐七年圆沙书院刻明修本),其收藏单位的代号有:0101,0201,2201(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检索表》,以下此类情况不再进行说明)。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2201指代的是河南省图书馆(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中“0101”原指“北京图书馆”,以下行文统称为“国家图书馆”)。经查河南省馆藏书和目录,却并无此书。查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正式出版前的《征求意见稿》对藏书单位的标示,该书为代号2261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又请河南省社科院图书馆确认,此书的确是其所藏。可以确切地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2261误为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9508 0101,0201,2261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编号8868的[万历]《山西通志三十卷》(明李维桢纂修,明万历刻本),标示有四家单位收藏,其中河南省只有一家,即河南省图书馆。经过一番查找求证,确认河南省馆没有收藏此书。查《征求意见稿》,又查当年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河南省内各单位著录各自所藏古籍善本、而后汇总到河南省馆的善本目录卡片(注:由于时间、地点、人事变化等的缘故,笔者没能见到这部分善本目录卡片的全部。以下行文中称其为“善本目录卡片”),均显示该书为河南省南阳市图书馆收藏,又与南阳市馆核对无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错将南阳市图书馆的代号2210印成了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8868 0101X,0201X,0581,2210X
(3)《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代号9165的[顺治]《西华县志八卷》(清左国桢、王鼎镇等纂修,清顺治刻本),标示只有河南省图书馆一家收藏,为孤本。经过对河南省馆藏书的追究,又查《征求意见稿》和善本目录卡片,该书的收藏单位实为南阳市图书馆,经过联系,南阳市馆也对此书予以了确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错误与上述[万历]《山西通志》的错误相同。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9165 2210
(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书目中,书名编号2734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宋范纯仁撰,元刻明修本),标示国内有三家图书馆收藏,河南省图书馆为一家,另两家分别为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征求意见稿》的标示同上(注:《征求意见稿》集部宋别集类中,该书名编号为551)。但遍查河南省图书馆现有的古籍目录,却未见有对此书的著录。查善本目录卡片,关于元刻本的范纯仁文集,只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一张“二范集四十四卷”的目录卡片(归入集部宋别集类)中,显示有“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位于其父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之后,版本著录为“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中,先后著录有范氏父子的集子。书名编号2355的为“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宋范仲淹撰)遗文一卷(宋范纯仁、范纯粹撰)年谱一卷(宋楼钥撰)年谱补遗一卷祭文一卷诸贤赞颂论疏一卷论颂一卷诗颂一卷朝廷优崇一卷言行拾遗事录四卷鄱阳遗事录一卷遗迹一卷褒贤祠记二卷义庄规矩一卷”(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一书,在其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可以找到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且标示其所藏书残缺;《征求意见稿》著录相同,只是未标示残缺且书名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略有差异(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192)。而在所有的元刻本(包括元刻明修本)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书名编号从2732至2735)的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却都没有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只有在书名编号2734《范忠宣公文集》(元刻明修本)的藏书单位代号中,有河南省图书馆的代号2201。又查《征求意见稿》(该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551),藏书单位的标示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相同。综上所述,可以推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编纂过程中,将原本是郑州大学图书馆藏书《范忠宣公文集》误标成河南省图书馆的藏书了。如果笔者的这种推论不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于郑州大学图书馆所藏范氏父子的这两种书籍的残缺情况、版本等方面的认定与著录,与郑州大学图书馆原来的判断和著录也是有所不同的。河南省图书馆现存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二范集四十四卷”的另一张目录卡片,它与前面所提到的那张卡片著录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在卡片背面多出了对于书籍行款、版式、序文、牌记、印鉴等方面的描述文字,文字的旁边还有铅笔批字:“据纸张墨色看,系元刻明印本。”这一点似乎也能从另一方面佐证笔者的上述判断。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2734 0101,0201,2241
图书馆高度重视突出学校自身特色的馆藏资源积累,已经形成以教育类和文史类重点学科领域文献为主的多种类型、多种载体形式的综合性馆藏体系,为教学与科研提供较为完备的图书文献信息保障。馆藏中外文实体文献280万册(件)。其中,开架书库藏书80万册,中外文报刊2400余种。馆藏中外文数据库90余个,电子图书100余万册,电子期刊11万余种,学位论文3万余篇。馆藏古籍为藏书重点,以文史类为主,侧重明清时期,突出地方性特点,珍本荟萃,常用古籍齐全,涵盖经史子集各类。其中,旧平装书7000余种、27万余册;古籍线装书1万余种、12万余册;善本书 700余种、 7500余册。278种古籍被列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经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管理中心(CALIS)批准,成为国家教育部“211工程”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E读应用服务示范馆”、“外文期刊网应用服务示范馆”、“馆际互借应用服务示范馆”。与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及天津市19所高校图书馆建立了长久性馆际互借关系。
经过多年的努力,图书馆已经形成了网络资源、镜像服务站和本馆资源等多元化的虚拟文献资源服务体系。图书馆利用磁盘镜像服务器建立了本地数据镜像站点,为读者提供中外文电子文献全文数据库检索服务。图书馆有各类数据库 40 个,其中已购置使用权的数据库 33 个(中文数据库 14 个,外文数据库 19 个),在线试用数据库 5 个,自建《心理与行为研究特色资源数据库》和《天津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 个。此外,还自行研发了《信息参考咨询服务平台》及其《交互性在线咨询系统》等 8 个子系统,为读者提供互动式在线实时咨询等多种服务。图书馆虚拟文献资源主要包括中外文图书、期刊和专题数据库三大类,覆盖文史、理工、综合等学科。馆藏电子图书 78 万多册,另有外文电子期刊(全文) 8536 种。
图书馆为学校教学、科研和学生素质教育服务的文献保障体系十分健全,涵盖了学校开设的教育、政治、经济、管理、文史、心理、外语、艺术、计算机、数理化、生物、地理、环境、体育等学科的全部 56 个专业。业已形成的文献资源与办学规模相适应、传统文献资源与数字化文献信息相结合、学科教育与素质教育相融合的馆藏体系,能够满足学校教师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以及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各类人才的需要。
武王《几铭》“口”非阙文证补
明钟惺、谭元春辑《古诗归》卷一周武王《几铭》:“皇皇惟敬口,口生,口戕口。”钟惺评云:“读‘口戕口’三字,悚然骨惊,觉《金人铭》反饶舌。”谭元春评云:“四‘口’字叠出妙语,不以为纤。‘皇皇’二字,郑重异常。”〔1〕自晚明以来,钟、谭此书常遭到学者的讥评,这两条批语尤为“暴谑之资”,而铭中的“口”字是非,则为数百年来学林的一公案。
清初周亮工于此尝大加讥评,其《因树屋书影》卷二有云:“古逸书如《穆天子传》、《汲冢周书》类,凡阙字类作囗。武王《几铭》:‘皇皇惟敬囗,囗生垢,囗戕囗’,亦阙文也。钟、谭目‘囗’为‘口’字,友夏云:‘四口字叠出妙语,不以为纤。’伯敬云:‘读口戕口三字,竦然骨惊。’不知《几铭》与四口字何涉!可发一噱。”〔2〕又在《与林铁崖》中云:“伯敬、友夏只是好新,落笔遂不顾所安耳。他且勿论,即如《穆天子传》、《汲冢周书》,凡缺类作囗;武王《几铭》‘皇皇惟敬囗,囗生垢,囗戕囗’,亦缺文也。两君目‘囗’为‘口’字,(中略)不知《几铭》与四‘口’字何涉,岂三代时便学作钟、谭诗耶?即此已可笑,何况其他?”〔3〕文字与前略相同,而口气更加轻蔑。
近人大抵视周说为定论,即为钟、谭诗学作持平论者,亦认此为无可辩解之讹谬〔4〕。有人论及明代的唐诗选本,也特地引及周亮工对《诗归》的这个批评,用以说明“明代学风空疏,且好以己意改窜古书”,说:“竟不知‘囗’为阙文符号,读为口字,鲁莽灭裂,可见一斑。”〔5〕明人学风空疏,自为无可讳辩,好以己意改窜古书,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此处所说的妄改公案,却非不可翻的定谳,确切说来,错的还并非是钟、谭,恰相反,正是以纠错正讹自居的周亮工。
钱锺书于此早有详确考辨。其《管锥编》中,曾引清王应奎、严元照、张宗泰等,驳之云:“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诗归》评周武王《几铭》,以为四“口”字叠出妙语,周亮工、钱陆灿皆辨其谬。近见宋板《大戴礼》,乃吾邑秦景旸阅本,是“口”字,并非方空圈’;严元照《蕙櫋杂记》:‘几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周盖未尝读《礼》。“口生”作“口口生”,则误也’;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八《再跋〈因树屋书影〉》:‘编录金石文字,遇有缺文,则以方空代之,而经、传不闻有此也。武王《几铭》载在《大戴礼·武王践祚》篇,历代相传;乃指数“口”字为缺文,可乎?’足息三尺喙矣。”〔6〕据此可知,钱锺书不以周、钱的非笑为然,而同意王、严、张三家之辩,其态度与判断都是十分明确、毫不含糊的。
近人王欣夫亦有辩证,其说较钱锺书为稍早,而所辩说实可比观互照。王在其《文献学讲义》中,于论及“阙文和穿凿”时,曾引《诗归》“口”为阙文为例。王氏亦不以周说为是,不过未下明确断语,其于引王应奎《柳南随笔》驳周说后,复引卢辩《大戴礼记》注:“,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又:“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而加以甚为谨慎之申说:“倘使这囗形真是阙文而不是口字,那么,穿凿的应该是卢辩。在没有北周以前写本发现,没有可信的证据时,宁可保留它的原状。”〔7〕又谓:“钟谭是文学家,他们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认为是口字,而且这口字用得非常之妙。明人虽好窜改古书,也不能不问情由,硬加在他们头上。”〔8〕这个说法似乎稍欠明清,但以《诗归》所录之铭并非钟、谭“妄改”,则其为钟、谭辩冤也是明显的。
从王、钱二家的考辨看,自不可再以钟、谭为“妄改”,而近人仍沿周亮工之误,其故当是未读王、钱之书。不过,细究王欣夫的辨说,此一问题仍留有些许疑问,有待于作进一步的考辨分疏。王欣夫于引王应奎《柳南随笔》后说:“王应奎所据是宋版,宋版本来不是完全正确的,何况囗之于口,凡是刻板多容易互混。(中略)王应奎只看见下面的注,不能提出更有力的证据也是读书的疏忽。不过铭的是几,而内容却强调了口,好像没有多大联系,虽则卢注补充了说:‘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这句话兜了一个圈子,究竟是不是正确?还有研究的余地。”〔9〕据此可知,王欣夫虽不以作“口”为钟、谭的“妄改”,因为其文实自北魏卢辩注始;而王应奎之所谓“宋版作口”,亦没有作为版本证据的价值,因为宋版不是绝对没有错误,所以未必便为铁证;且囗之于口,刻板多易互混,辨识也未必可保绝对真确无误。而其最主要之疑问则为:“几铭”与“口”之间,缺少直接必然的联系。他认为卢辩注的那个解说尚嫌迂回牵强,不足以弥“几”、“口”之间的罅缝。
钱锺书的解释可祛王氏之惑。钱同样亦引卢辩注,并辨析云:“按几固如严元照说,乃人君出令所依,故‘口’即言语;顾古人食虽据案,而《说文》曰:‘案,几之属’,赵怀玉《亦有生斋集·文》卷一一《几席考》谓后世以椅代古之席,以桌代古之几。《全后汉文》卷五〇李尤《几铭》云:‘昔帝轩辕,仁智恭恕,恐事之有缺,作倚几之法’,盖即《国语·楚语》上所谓‘倚几诵训’,故‘口’乃口舌之‘口’;又云:‘肴仁饭义,枕典席文,道可醉饱,何必清醇!’,则‘几’正同案,可据饮食,‘口’复为口腹之‘口’。口腹之‘口’,则‘生’者,‘饮食之人,人皆贱之’也,而‘戕口’者,‘病从口入’、‘烂肠之食’也。《易·颐》:‘慎言语,节饮食’,足以移笺‘口戕口’之两义兼涵矣。”〔10〕揭橥“几”“口”之义极为透彻。钱锺书的这个阐释,重点不在版本考索,而在义理的圆通无碍,这恰可以释王氏的疑惑。据钱锺书的考证,“几”与“口”的内在联系,实有两点:一,“几”乃“倚几”之“几”,古人“倚几诵训”,其事与“口”相关,故“铭几”以慎“言语”;二,“几”又为“案”,“案”为古人据以饮食之具,故“口”又指“口腹”之“口”,诫“口”即是节“口腹之欲”。这样,“几”、“口”之间,就不是缺少关联,而相反,正是严丝合缝、语义双关!王欣夫《讲义》的撰述,在钱氏《管锥编》之前,迨《管锥编》出版时,王欣夫已经故去,所以不可能见到钱氏的解说。
据上面的考述,《几铭》之“口”非阙文,已可论定,自无须再节外生枝。但若于其首尾详加覆按,则知其间仍有待补之疏漏,而钱锺书所考间亦有误,必待补证、纠正,始可以称为圆满。这一待补之疏漏,主要表现在版本上,即:《几铭》出《大戴礼记》,而严元照、张宗泰、王欣夫诸家,却都不从《大戴礼记》版本作考辩,这实际是不合常理的。而钱锺书引张宗泰云:金石文字遇阙文,始用方空圈代之,儒家经传则不用此。而《几铭》载于《大戴礼记》,历代相传,并非金石或出土文献,故不必使用方空圈。这一判断自是正确的。但也很难证实,因为,“说有容易说无难”,儒家经传从不用方空,也没有证据证明。而且,张宗泰的这一说法,又与王应奎之说凿枘不合。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云:“近予见宋板《大戴礼》,乃秦景旸阅本,口字并非方空圈。”〔11〕既云“宋板作口”,言下之意,则《大戴礼》当日的通行本,“口戕口”都确乎作“囗戕囗”,否则,若通行本俱作“口”字,王应奎也就不必引“宋板”为辩说,只须径称“《大戴礼》正作‘口’字”,便可驳倒周亮工而雪钟谭之冤了。而王欣夫继王应奎之后,又以“宋版不尽可据”,持蓄疑待考之两端论,一似《大戴礼记》中真有“口”作阙文之事。而一考《大戴礼记》的版本源流,就知其实从未有过“口”为阙文之说,有之,则自周亮工讥讪钟谭《诗归》始。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知明代《大戴礼记》通行本,十之九俱附有卢注,白文本实极罕见〔12〕。而卢注为今传宋以前唯一的旧注。其传本可考之最早者,为宋淳熙年间韩元吉刻本,元明刊本大都据其覆刊或重刊。而其中通行于世影响最大的,则为明嘉靖十二年(1533)袁氏嘉趣堂刻本和万历程荣刻《汉魏丛书》本〔13〕。据此两明本《大戴礼记》卷六《武王践祚》引《机铭》云:“口生。卢注:‘,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詈也。’口戕口。卢注:‘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14〕知卢辩于作注时,所见之本必非“口”作阙文;如卢辩所见“口”作阙文,则注必不云“口能害口”,“以言语为戒”;因卢辩这两句注,其与阙文,实无任何意义关联。由此更可推知,当日卢辩注《大戴礼记》,所参考罗列诸本中,当无一“口”作阙文者,揆诸古人注书通例,经有异文,则注者于注必有所说明。
又考清人专治《大戴礼记》者,有名于世凡十数家,若戴震、孔广森、汪照、汪中、王聘珍、孙诒让等,其治学均以谨严不苟称,而其校注概未提及阙文之说。即以戴震校本言之,其所参校之本极为广泛〔15〕,而其校语于“口生,口戕口”下未列异文〔16〕。又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卷六于“口生”后注云:“,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詈也。注‘’有两训,疑记文本作‘生’,故卢意谓君有耻之言,则致人之詈也。王本‘敬’下多‘口口生敬’四字,恐后人所加。”〔17〕“,耻也”后为卢辩原注,“注有两训”后为孔氏补注。其于“口戕口”后,则仅录卢注“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无任何校补。又汪中《大戴礼记正误》校云:“口生,注可不慎乎。喜孙案:卢注此本各本有‘,詈也’四字,先君校去,与戴校聚珍本合。”〔18〕于“口戕口”亦未出校语。故知此处并无异文。汪照《大戴礼注补》卷六“口生”注:“原注:‘,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案别本又有‘,詈也’句,一注两释,疑后人所加。”又“口戕口”注:“原注:‘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集解:《太公金匮》: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戒,随之以身。几之书曰:安无忘危,存无忘亡。孰惟二者,必后无凶。照补:《书·大禹谟》:唯口出好兴戎。《鬼谷子》:口可以食,不可以言。傅元《口铭》:病从口入,祸从口出。”〔19〕引《书》、《鬼谷子》、《口铭》等,以笺“口戕口”,亦未尝言其有异文。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六“口生,口戕口”注:“《少仪》曰:‘言语之美,穆穆皇皇。’,谓诟病羞辱也。《书》曰:‘惟口起羞。’戕,害也。《大学》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卢注云:‘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20〕亦不言有“口”为阙文之说。晚清孙诒让《大戴礼记斠补》卷中“皇皇惟敬,口生”校云:“孔云:‘王本“敬”下多“口口生敬”四字。’严校云:‘《续笔》引亦有“口口生敬”四字。’案:洪、王本是也。此读‘皇皇惟敬口’五字句,‘口生敬’、‘口生’,皆三字句。与诟声同字通,言惟敬慎其口,慎则见敬,不慎则招诟辱也。”〔21〕并皆不及“口”作阙文。
据此则不难推知,清代治《大戴礼记》诸家,于武王《几铭》未尝睹“口”作阙文者,若其曾见有作阙文之文,其于注中,必当有校语说明。又照清人治经之法,诸家治《大戴礼记》,于版本亦必竭力搜求,而据此六家之所目睹者,竟未有一本作阙文者,则谓传世之《大戴礼记》“口生,口戕口”未尝有异文,亦可谓不中不远。而细究周亮工所云,谓“古逸书如《穆天子传》、《汲冢周书》类,凡阙字类作囗。武王《几铭》云云,不知《几铭》与四口字何涉”,则其意中实视《几铭》为古逸书,与《穆天子传》、《汲冢周书》等类齐观。据此,则又不难推知,周亮工本不知《几铭》出自《大戴礼记》,为自汉以来传而未绝之经书,与《汲冢周书》等佚而复出者,本不可同日而语,只因其为武王之铭,遂望文生义而生臆说,误以“口”为古逸书的方空。所以,周亮工的这个说法,虽然其流传甚为广泛,而清代治《大戴礼记》诸经师,未尝引之以为版本依据。
而迨至晚清,又有俞樾、叶大庄二家,据孔广森疑“口生”作“生”,而提出“口”为“囗”、二“口”皆为“”之说。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五“阙字作空围而致误例”条云:“校书遇有阙字,不敢臆补,乃作囗以识之,亦阙疑之意也。乃传写有因此致误者。《大戴记》‘武王践祚’篇:‘机之铭曰:皇皇惟敬,口生,口戕口。’卢注曰:‘,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詈也。’孔氏广森补注曰:‘疑记文本作“生”,故卢意谓君有耻之言,则致人之詈也。’按此说是也。惟其由生,故谓之‘口戕口’。今作‘口生’,盖传写夺‘’字,校者作空围以记之,则为‘囗生’,遂误作‘口生’矣。”〔22〕按俞氏治经故多勇改,此一据注疑经之说,较孔广森更进一步,疑“口生”之“口”,本为“”,传写夺去而代以空围,但此与周亮工说仍有本质区别,即:俞氏只以“口生”之“口”为阙文,而周亮工则以四“口”字皆为阙文。而更为重要的是,俞氏疑传世之本“口”为空围,则其实已承认传世之本作“口”,其作空围者疑不知佚于何时耳;周亮工则以传世之本本作空围,钟、谭二人不学无知,故妄改为“口”。盖亦以此故,俞氏虽于经有所疑,但并不引周氏为说,即并不以周氏为是。而考俞氏之所疑,其于理实亦欠通,因卢注紧接经文之后,经文中夺去“”字,后人可以据注疑经,前人岂不能据注校经。若经文之“”漫漶难辨,校者可据其下注文“,耻也”,容易辨出经中“”字,而不致以空围代之。俞氏又著有《大戴礼记平议》,不用《举例》“口”为阙文之说,当以《举例》为举例以明理,可以得鱼忘筌,所重不在具体所举之例;而《平议》为解经之书,当谨严不苟,大胆假设之说,固当在摈弃之列。
又叶大庄《大戴礼记审议》卷一云:“口生,口戕口。大庄案:孔氏补注:‘有两训,疑记文本作‘生’,故卢意谓君有耻之言,则致人之詈也。’若依孔说作‘生’,上训耻,下训詈,犹言‘耻生詈’,殊觉无义。此记本作‘口生,戕口’,上训耻,下训詈,上下相承,文同义异,古书多有此例。故卢注有两训,是其明证。‘,詈也’四字,疑本在下文‘口能害口也’之上。‘口能’之‘口’亦疑作‘ ’。盖缘记文‘ ’字脱省为‘口’,遂以‘、詈也’四字与‘口戕口’意不相属,因移置于上文注末,而又改注中‘‘字作口,以应‘口戕口’之义,不然卢君作注,何以有此四字,固为横分两义耶。汪氏《大戴正误》校去此四字,非也。今试重次之云:‘口生。注:“,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戕口。注:“ ,詈也。言能害口也。机者,人君之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如此则经注均无碍矣。”〔23〕叶氏不以经学名家,其所假说推论,亦据孔广森《补注》而来。其与俞樾不同之处,则在俞所疑在“口生”,而叶氏所疑在“口戕口”,而仍然只疑及一“口”字,与周亮工之说固区以别。至其移上文注入下文,实难逃蹈空轻率之讥,当不为乾嘉经师所许。
总上之说,即令俞、叶二家假说近是,而二家亦未有版本为据,又诸家校语概未著异文,是则《机铭》从未有口为阙文之说,则可以大致论定。据此从可推知,上文所引严元照、张宗泰云云,谓周亮工未尝读《礼》,徒凭肊说而致讥钟、谭,亦为事实。又据王应奎“宋板”云云,王欣夫“宋板亦不足据”云云,其所疑问,至此亦不复有意义,而钱锺书所谓“足息三尺喙”者,则确可视为定谳而结此公案。
钱锺书考辩偶疏处顺笔纠正。《管锥编》引《蕙櫋杂记》谓:“几固如严元照说,乃人君出令所依,故口即言语”云云。不知此并非严元照语,而为严元照所引卢辩《大戴礼注》注文。严氏《蕙櫋杂记》原文较长,为便比勘,具引如后:“周亮工《因书屋书影》云云,(中略)予按《大戴礼·武王践祚篇》:‘机之铭曰:皇皇惟敬,口生,口戕口。’卢景宣(辩)注‘口生’曰:‘,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又注‘口戕口’曰:‘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周盖未曾读礼,强改古先王成语为阙文,而大书深刻,可称大胆。(‘口生’作‘口口生’,此则误也。)”〔24〕据此,知钱氏致误之由,当是笔记节抄时删去过多,而于临文考辩之际,未覆案《蕙櫋杂记》,又未核检《大戴礼记》卢辩注,故忘前后而混淆宾主,以致误断严元照所引卢注的起迄。
《管锥编》又云:“武王器物诸铭,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五《题太公〈丹书〉后》始标举之,洪迈《容斋续笔》卷九继之。”〔25〕云云。按洪迈《容斋续笔》卷九“太公丹书”条云:“太公丹书今罕见于世,黄鲁直于礼书得其诸铭而书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读《大戴礼·武席践祚篇》,载之甚备,故悉纪录遗好古君子。”〔26〕又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五云:“山谷以太公所诵丹书及武王铭,书于坐之左右,以为息黥补劓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写《武王践祚》一篇,以为左右观省之戒。”〔27〕据此知,钱所云实本洪、王,其语固有所袭。或谓山谷标举《机铭》,其事至钱锺书始为考出〔28〕,亦为未探其本而误断。又王书似亦本诸洪氏,王年代晚于洪,王生时洪已死二十年,疑王读洪书而著此条,而钱氏所以未引王书,当以王书晚于洪故。清翁元圻注《困学纪闻》,未引洪书以明其朔〔29〕,后来张嘉禄撰《困学纪闻补注》,于此亦无增注〔30〕,是并当补引以纠其疏漏。
〔注释〕
〔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闵氏刻本,集部第1589册。又,明万历刻本“”作“垢”,后引周亮工《与林铁崖书》亦引作“垢”,所见当即万历本。
〔2〕《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康熙六年刻本,子部第1134册。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校点本,第43-4页作:“皇皇惟敬,囗囗生垢,囗戕囗。”标点不妥。又“戕”作“”,误;“囗生”作“囗生垢”,则是周氏所据或为万历刻本。
〔3〕见《赖古堂集》卷二〇,《清人别集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4〕王恺:《关于钟、谭〈诗归〉的得失及其评价》,《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5〕陶敏、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第135-6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6〕第85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7〕第2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8〕同注7。
〔9〕第285-6页。
〔10〕同5,第856页。
〔11〕第11页,王彬、严英俊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1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第20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3〕黄怀信:《〈大戴礼记〉传本源流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1期。
〔14〕《四部从刊》影印明袁氏嘉趣堂刊本,又明万历程荣刻《汉魏丛书》本。
〔15〕据其校语所及,有元至正刘庭干本、明朱养纯本、沈廷芳《五礼经传目》本、袁氏嘉趣楼本、程荣《汉魏丛书》本、朱轼句读本、方苞评点本、傅崧卿《夏小正戴氏传》本、杨简《先圣大训》本等。
〔16〕《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17〕《顨轩孔氏所著书》本。
〔18〕《江都汪氏丛书》本。
〔19〕《清经解续编》,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3册。
〔20〕第105页,王文锦点较,中华书局1983年版。
〔21〕第214页,雪克点校,齐鲁书社1988年版。
〔22〕《春在堂全书》本。
〔23〕清玉屏山庄刻本。
〔24〕清光绪11年(1885)新阳赵氏刻本,又赵诒琛辑《峭帆楼丛书》本。钱氏所引颇有删节。
〔25〕同6。
〔26〕第3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7〕《四部丛刊三编》本。
〔28〕敏泽:《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29〕《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道光五年翁氏守福堂刻本,子部第1142册。
〔30〕《四明丛书》
(刊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2期)
目录学·专科书目
专科书目是指围绕某一学科系统全面地收集文献而编制的书目。西汉初年,张良、韩信编制军事方面的书目,从众多的图书中选取了三十五家。汉武帝时,军政杨仆在整理兵书的基础上,编制了《兵录》。这部书目是中国第一部有文献记载的专科书目。在专科目录中,目录学成就最高的一是佛经书目,另一是经学和史学书目。
佛教历经东汉、三国的发展,至南北朝时期,非常盛行。佛经的数量超过了儒家图书的数量。为了管理上的方便,一些著名僧侣编制了一批佛经目录,据统计,佛经目录有四十余种。这批目录各有特点,并积极创新,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南北朝时期重要佛经目录是道安编撰的《综理众经目录》和僧祐编撰的《出三藏记集》。《综理众经目录》成书于东晋(374),是中国较早的一部佛经目录。僧祐说:“爱自安公,始述名录,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斯人。”道安的目录已佚,但从《出三藏记集》中可看出它的成就和特点。《综理众经目录》把佛经书分为七类,一是经论录、二是失译经录、三是凉土异经录、四是关中异经录、五是古异经录、六是疑经录、七是注经和杂经。经论录著录汉至西晋时的十七家经书,排列顺序以译经人生卒年代先后为序,并注明翻译的年代和异名。后附一篇文字,介绍译人的姓氏、评论翻译质量的高低等。失译经录著录了一百三十四部不知道译者姓名的经书。凉土及关中异经录著录的是只知道翻译地点,而不知道译著姓名的经书。古异经录著录了九十二部书,多是经书摘译的单行本。疑经录著录的是真伪难辨的图书,计二十六部。注经及杂经著录道安自注的众经和杂经。从上述七类内容看,它与综合性书目的体例大不相同,梁启超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载《图书馆季刊》1926年第1卷第1期)一文中认为这种体例有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纯以年代为次,使读者可知经学发展的源流和各家的派别; 二是不知译者姓氏的单独立为一类;三是摘译经书列为一类,并以书的性质分别,眉目清楚;四是真伪难辨的书单独为一类,精神最为忠实;五是注解的书别自为部不与本经混合,主从分明。僧祐《出三藏记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佛经书目,陈垣在《中国佛教史概论》一书中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三藏”指经、律、论,即佛教经书的总称。该书目是根据定林寺所藏经书,并在《综理众经目录》基础上增辑而成的。它们的编撰体例是“一撰缘记、二铭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所谓“缘记”,即佛经及译经的起源。所谓“名录”,指历代的书名经目,把经书分为十二录,其次序为:经论录、经缘录、律录、古异经录、失异经录、凉土异经录、关中异经录、失译杂经录、抄经录、疑经录、疑经伪撰录、注及杂经录。所谓“总经序”,即各经的前序和后记,共约一百二十多篇。所谓“述列传”,即译经人的传记,共录二十二个外国人及十个中国人的传记。《出三藏记集》的四个组成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名录”,袭用《综理众经目录》并有所增补,其余三部分都是僧祐的创新。其成就和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借书目保存了各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如叙述佛典的来历及翻译方面,记录了当时名僧事迹,抄录了经序和后记,这些资料对于研究该学科都是非常珍贵的。二是在目录学方法上开创了广搜经序的方法,借此可使读者了解一种图书的始末源流。这种广泛搜集评论资料汇集成篇的方法为后世辑录体提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也为后来尤其是清代的专科书目广泛采用。三是详细叙述译者的传记,并专列为一个部分,经书质量的优劣与译者有重要关系,叙述译者事迹对于读者了解经书内容有一定关系,列传与目录相互补充,可更好地发挥书目的作用。四是在类目上根据图书实际情况而增设。在道安书目的基础上增列了“抄经”等类,节抄的经书不与原书放在一起是有一定道理的。总之,僧祐的书目无论书目编制体例,还是目录学的成就都为后世所推崇。隋开皇十四年(594),法经等人编撰《大隋众经录目》,它不以译经特征编目,而按佛经内容分类,把经、律、论分开,又把“大乘”、“小乘”各列一录,三藏以外的书分为抄录、传记、著述三录,每录又分西域与中国两类,其组织体系较为严密。稍后,费长房编有《历代三宝记》,又称《开皇三宝录》,全书十五卷,在现存经录中规模较大,共著录经书六千二百三十五卷,比《大隋众经录目》五千二百三十四卷多著录一千多卷图书。前三卷为年表。四至十二卷著录汉代至隋代所译经书,以年代及译人生卒先后为序,每人先列所译著经书,然后附以小传。十三至十四卷为大小乘入藏目,十五卷为序传。梁启超认为,《历代三宝记》“最可观者实惟前三卷之年表,虽考证事实,舛误尚多,然体例固彼所自创也”(《图书馆季刊》1926年第1卷第1期)。佛经目录在唐代又有新的发展,较著名的有道宣编撰的《大唐内典录》和智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大唐内典录》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创立“众经举要转读录”,梁启超说:“盖佛典浩如烟海,读者本已穷年莫殚,加以同本异译,摘品别行,叠屋支床,益苦繁重。宣公本篇,于异译别行诸经,各择其最善之一本以为代表,例如《华严经》则举佛陀跋陀罗译之六十卷本,而异译异名之十部,皆该省略焉。……诸如此类,裨益于读者实不少,著书是以备学者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同上)。智升《开元释教录》基本上仿照《大唐内典录》编撰而成,其不同之处一是经论分类更加细密,二是提要较为详细。最为称道的是它对目录学的独特见解,“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伦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开元释教录》卷一)。此后,宋代有惟白编撰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和王古编撰的《大藏圣教法宝标目》,明代有智旭编撰的《阅藏知津》。宋代两部书目提要较为详明,明代智旭的书目改进了佛教图书的分类,又使用符号以识别图书的优劣、缓急,借以指导阅读。综观佛经书目,在目录学上的成就有以下几点: 首先,各部经目在体例上勇于创新,各具特点,僧祐以道安的目录而成,但在类目上超出道安目录五个类目; 隋代法经编的书目改编以前从经书特征编排的旧例,转向从佛经内容分类,这些不因旧法的编目方法值得今天借鉴。其次,在著录方法上灵活具体。佛经是从外国文字翻译过来的,“有译乃传,无译乃隐”。各部佛经书目特别注意翻译事项的著录。如道安的目录于各家经目下注其异名、译出的年月、译人姓氏、翻译始末、译笔优劣等。僧祐的“缘记”、“列传”、“经序”三部分也是为读者了解经书而采取的灵活方法。这些方法不同于综合性书目,都是根据佛经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这种因书而宜的方法值得今天书目工作发扬。第三,在提要编写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僧祐在“经序”中专辑佛经译本的前序和后记,“列传”部分记述名录的译者事迹,两部分虽然独立,实际上起到提要的作用。前序、后记是现成的资料,利用这些资料作为提要的素材,不仅是佛经目录的一种创新,也是中国目录学上的一大发明。此后,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广泛采用广搜序跋等文字的方法,形成了辑录体提要的一大体例。
中国古代特别重视经学和史学的研究。较早的经学书目是郑玄编的 《三礼目录》,后来李肇编有《经史释题》、欧阳伸编有《经书目录》。最有成就的书目是清代朱彝尊编的《经义考》和章学诚编的《史籍考》。《经义考》把图书分成二十六类,每种图书除著录著者、卷数等项目外,并各注明 “存”、“佚”、“阙”、“未见”四项,然后辑录原书的序、跋及古今学者的论述,照录原文,不加评论,继承了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以来辑录体提要的写作方法。陈廷敬在《经义考》的“序”中说:“今古经具在而学术如此,经之其存其佚皆不可得而知矣。兹先生所著《经义考》至于三百卷之多,虽其或存或佚者,悉载简编。余以为经先生之考定,存者固森然其毕具,而佚者亦绝其穿凿附会之端,则经义之存,又莫有盛于此时者矣。微竹垞博学深思,其孰克为之”这些赞誉是符合实际的。它的影响不仅及于后代,也影响到海外,日本丹波元胤在其影响下编撰了《医籍考》。章学诚《史籍考》继承了《经义考》的体例,在分类、著录方面提出了古逸宜存、家法宜辨、剪裁宜法、逸篇宜采、嫌名宜辨、经部宜通、子部宜择、集部宜裁、方志宜选、谱牒宜略、考异宜精、版刻宜详、制书宜尊、禁例宜明、采摭宜详等十五种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其它学科历代也编有不少书目。西晋的荀勗编有《文章叙录》,此后挚虞编有《文章志》、傅亮编有《续文章志》、沈约编有《宋世文章志》等文学书目。宋代高似孙编有《史略》和 《子略》两部书目,其中《史略》者录十三世纪以前的史学图书。在医学、数学方面,明代殷仲春编制了《医藏书目》、清代梅文鼎编有《勿庵历算书目》等。专科书目集中收录某一学科的文献,或广泛搜集,详细著录,给人们查询利用专科文献提供方便;或详加考订,注明真伪存佚,为后世的整理利用提供依据。其中,《经义考》、《史籍考》等书目,把辑录体提要的方法发扬光大,不仅为后世书目的编撰树立了典范,而且也为读者留下了一种图书的多方面评论资料。
中国古典书目中,还有一种指导读书的推荐书目。这类书目又叫导读书目。现存最早的是唐代末年编的《杂钞》。它以问答形式给青年开列了一部包括数十种书的书目单。元代初年,程端学把朱熹、真德秀以来在书院书塾教学中所创造的读书方法,结合当时实际情况,编写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对明清产生很大影响,被称为“读书工程”。清代道光年间(1847),湖北学政龙启瑞编撰了《经籍举要》,开列了经史子集以及经济、考试方面的图书。推荐书目中影响最大的是光绪年间 (1876) 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不少学者从书目中得到教益。鲁迅先生曾说:“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 《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 ( 《而已集·读书杂谈》) 余嘉锡先生曾对陈垣先生说,他的学问是从《书目答问》入手的。张之洞当时编撰书目的目的,是要回答当时的青年人“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清代中叶,目录学一时成为“显学”,对于《四库全书总目》,张之洞非常推崇,说“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但《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图书太多,不易读书人阅读,所以他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重要图书加以选择,收书二千二百种左右,编成《书目答问》,以书目形式回答全国生童的读书问题。综观书目,其成就及特点有以下几点。首先,在分类方面,它突破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四分法,在经、史、子、集之外,新增“丛书”一部为五部。他认为丛书“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丛书类的增设表现了清代学术的发展,自此以后,许多书目都采用五分法组织图书,今天集中全国各馆善本图书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就采用这种分类体系。部下分类,类的分合也不拘守《四库全书总目》,如经部增列“正经正注”一类,以反映清代经学研究成果;史部增列“古史”一类;子部为周秦诸子立“古子”一类,以别于后世诸子,天文算法类分为“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既反映了当时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和中西学术的交融,同时又将天文算学书籍独立为类,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集部对清代人的别集按各家学派分别立类,如“古文家集”下分“不立宗派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家”、“阳湖派古文家”三个子目,并加注语说:“国朝人集,流别太多,今为分类列之,各标所长,以便初学寻求。”为了更好地发挥图书的作用,张之洞在分类著录上采用了互著的方法,并明确指出“《汉书·艺文志》有互见例,今与相类关者,间亦互见,注其下”。总之,《书目答问》从基本大部的划分,具体类目的设置,以及前人互著方法的应用,都体现了张之洞的见解和创新。其次,在图书的收录方面,规定了严格的选书标准。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规定了五不录原则:凡无用者、空疏者、偏辟者、淆杂者不录;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 注释浅陋者、妄人删改者、编刻伪谬者不录;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旧刊旧钞,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同时,张之洞也规定了收录标准: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丛书举多存古书、有关实义、校刊精审者。从上述收录标准中,可看出《书目答问》重在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重在今人著作,实事求是,不炫奇示博,以多为胜。综上所述,张之洞在书目中对于图书的取舍贯彻了推荐书目所独有的有其书未必尽录、无其书未必不录的原则。第三,在图书版本的著录方面,不追求古本,讲求质量和实用。张之洞在“略例”中强调,“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关于善本书的标准,他认为首先是足本,无阙卷,未删削;其次是精本,精校、精注的本子;再次是旧本,旧刻旧钞。在书目中对于版本的著录,刻意做到这样几点,一是方便读者,易买易读;二是比较各本,指出优劣;三是考述沿革,稽核篇卷;四是注明分合,标识异同。张之洞在书目版本的选择中表现出的不追求宋椠元刻,从读者方便需要考虑的思想,值得今天借鉴。第四,在图书的注语方面,力求做到简明,有必要解释的则解释,没必要解释的则以类举。注语的内容较为广泛,有的介绍图书内容,评论得失,有的考证作者,辨别真伪,有的则注明学术渊源。总之,寥寥数语,体现了指导读书治学的精神。《书目答问》成书于光绪初年,时间愈久,原书中的错漏就愈觉明显,因此范希曾撰 《书目答问补正》(1931年出版)。“补正”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纠正了《书目答问》原来的错误,其中包括书名、作者、卷数、版本等;二是补记了原书漏记的版本以及成书后的版本; 三是补收了一些和原书性质相近的图书。一些书下还写了按语,说明利弊。因为《书目答问》是一部推荐性质的书目,所以它的指导读书的方法跨越时代,一直影响到今天,不少报刊开设“书目答问”专栏,用以开列青年人必读的书目。受《书目答问》的直接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编制推荐书目的 。1923年,胡适首先在 《晨报副刊》上发表了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自称“只为普通青年欲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者设想,并不为已有国学根底者设想”,所以“用历史的线索为国学天然的系统,而其书目顺序,也就是下手的法门”。对于胡适的书目,梁启超有不同意见,同年也编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推荐书目,把所收之书分为: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它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隋时涉猎书类。每类列举数十种要籍,每种图书简单说明内容及其读法。附录最低限度的必读书二十八种,并说“若藏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人矣”。继胡、梁开列国学书目之后,李笠编制了《国学用书撰要》、章太炎编制了《中学国文书目》、支伟成编制了《国学用书类述》、吕思勉编制了 《经子解题》、吴虞编了《青年研究中国文学宜选读之书》、王浣溪编了《中国文学精要书目》、陈伯英编了《国学书目举要》、曹功济编了《国学用书举要》等。根据各家开列的国学图书,商务印书馆经过整理,编印了《国学基本丛书》。鲁迅先生对胡适等开列的书目持不同意见,认为“书目开的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所以他开列的三种文学推荐书目非常简要。1982年,复旦大学教授蔡尚思在编写《中国文化史要论》开列“中国文化基础书目”的基础上,开列了一份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书目,计二十种(载《书林》1982年第5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历史沿革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11月,1958年3月,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为上海地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1978年1月改为今名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立之初便已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及诗词散文等不同文学门类的作品选读、选辑,加以通俗的解说、详尽的注释。有的更用现代汉语翻译。精选历代名篇,加上说明、注释,以单篇或合订本形式,出版《中华活页文选》。还有古代重要典籍的今译,如《四书》、《五经》、老庄诸子,以及《孙子兵法》等,语译而外,有的还附原文。并出版一部分高等学校的文科教材。出版当代老中青著名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的学术论著,如陈寅恪、郑振铎、郭绍虞、钱钟书、饶宗颐、吕思勉、岑仲勉、俞平伯等著名学者,或编为文集,或作为专题论著。此外,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有选择地出版《海外汉学丛书》。1962年起出版了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已成系列的有《文化春秋丛书》、《三百题系列新刊》、《十大系列丛书》、《生活文化丛书》、《文物鉴赏丛书》、《中华文明宝库》等等。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出版了《中国丛书综录》、《诗韵新编》、《变文字义通释》等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已设立了影印组。历年来影印的有《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集成》、《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大型的《四库全书》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下设5个编辑室和1个编辑组。第一编辑室负责文学类;第二编辑室负责除文学以外的哲学、经济、军事、历史、艺术、科技等类以及《中华文史论丛》;第四、第五编辑室分别负责敦煌吐鲁番文献和《续修四库全书》,此外的影印工作由第三编辑室负责;一个编辑组负责临时性或突击性的某些书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由李俊民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自1959年3月至1966年12月,由金兆梓任主任,总编辑一直是由副主任李俊民兼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后先后担任社长、总编辑的有李俊民、戚铭渠、魏同贤、钱伯城、李国章、赵昌平。
组织机构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主要组织机构有:党委办公室、社长、总编办公室、编审室、一编室、二编室、三编室、四编室、五编室、六编室、七编室、美编室、校对科、出版科、发行一科、发行二科、文化经营部、宣传信息科、人事科、财务科、行政科、储运部。
主要业务大型集成性文献丛刊与古籍整理
《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已出:《俄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17册)、《法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34册)、《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4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北大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7册),以及《俄藏黑水城文献》(已出11册),别外还推出《俄藏敦煌艺术品》(已出5册),《英藏黑水城文献》(全4册)等。中国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工程《续修四库全书》,1800册于2002年全部出齐。
大型集成性资
本文2023-08-05 20:42:45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24927.html
- 105840-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子部類書類之名賢氏放族言行類稿11 .pdf
- 105841-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子部類書類之名賢氏放族言行類稿12 .pdf
- 105842-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子部類書類之名賢氏放族言行類稿13 .pdf
- 105843-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子部類書類之名賢氏放族言行類稿14 .pdf
- 105844-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子部類書類之名賢氏放族言行類稿15 .pdf
- 105845-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子部類書類之名賢氏放族言行類稿16 .pdf
- 105846-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子部類書類之名賢氏放族言行類稿17 .pdf
- 105847-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子部類書類之名賢氏放族言行類稿18 .pdf
- 105848-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子部類書類之名賢氏放族言行類稿19 .pdf
- 105849-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子部類書類之名賢氏放族言行類稿20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