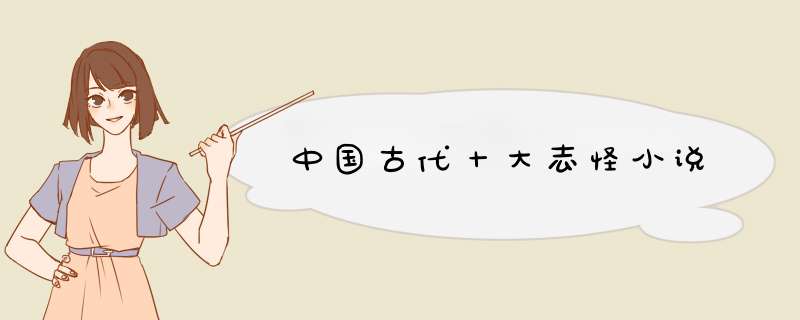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情义

北京六部口,30年代的崇德中学有一双童年时期的好朋友,大两岁的是杨振宁,小两岁的是邓稼先,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和哲学系教授邓以蛰的孩子。数十年的友谊是从逮知了的大树上,从弹玻璃球的泥地上开始的。这友谊一直延伸到了大洋彼岸。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即将回国的邓稼先与杨振宁、杨振平兄弟俩分手在芝加哥市。此后二十年,邓杳无音信。
1972年,杨振宁第二次来华。有关部门批准邓稼先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他童年的朋友。旧家具被人匆匆搬走。上面特地派来木工,把邓稼先的一个旧书橱打磨赶制,又匆匆装上一面穿衣镜,使之一天之内就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大衣柜;破旧的地板上了蜡,又有人从办公室扛来沙发,送来了良种西瓜、巧克力和一箱汽水。仿佛是在戏台上置景。邓稼先默认了。
杨振宁来的那天晚上,大院里特意放**,把人们都引到**场上。楼里显得别样的清静。杨振宁一进屋门,环视片刻,便径直向书架走去。这已是一个纯粹的医学专家的书柜,除了最显著位置上的两本毛泽东著作和厚厚一叠特意摆放的祖国风光明信片。
杨振宁回过头来,含笑的眼睛颇有意味地盯着他的朋友。早在1964年,他就从美国报纸上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报道中看到了邓稼先的名字。他不愿点破,只是微微地点点头,像在说,你收拾得很干净。
这次会面的气氛比1971年的第一次会面要自然和活泼得多。那一次是在宾馆,大概这一次毕竟是在家中。杨振宁吃着西瓜,喝着汽水,一会儿直言不讳地评论中国“不能调动人的进取心”,一会儿说起他在美国搜集的中国“文革”街头小报,一会儿又谈开了联邦调查局。忽然,他问:“这是你们的家吗?”
“是,是,”邓稼先用事先统一过的口径回答,“是许鹿希医学院的宿舍。”
“怎么没有儿子的床?”杨振宁聪明过人。
儿子的床的确在布置“客厅”时拆了。邓稼先没料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会看得如此精确。还是许鹿希反应敏捷,她忙打掩护:“儿子在爷爷家住。”
后来邓稼先又请杨振宁吃了一次烤鸭。和他在一起,邓稼先总感到有点紧张。他害怕童年时代的朋友会突然问起他的工作。可是杨振宁像是忘了这桩事。两个物理学家都在有意选择非物理学的话题。
这出戏直到杨振宁离北京去上海时才结束。邓稼先去机场送行,当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机坪时,杨振宁回转身,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问:“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搞的,他叫寒春,这是真的吗?”邓稼先的神情惊愕起来,他激动地张了张嘴,可是立刻又把嘴唇咬住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先上飞机吧。”
飞机腾空不久,邓稼先马上向上级报告并请示了他遇到的提问。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激动万分的邓稼先迫不及待地写了封信,立即交专人乘民航班机赶往上海。杨振宁是在上海市“革委会”为他饯行的宴会上接到这份急件的。当他拆开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邓稼先的笔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时,泪水夺眶而出。
1957年,当杨振宁赴瑞典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评委会要他提供一份英文的演说稿。杨振宁回答:“不,我要用中文写。”评委会说:“中文演说稿无法排印。”他坚定地回答:“那就请复制我的手稿。”
杨振宁常常从美国飞来。邓稼先的家是他平静而温暖的港湾,在邓稼先的身边是自由的。
———你给我找辆自行车!
———干什么?
———我们一块儿到香山去玩!
———我可不敢。人家能让吗?!
———真遗憾。那我们谈点什么吧,宇宙不守恒定理?规范场论?
常常,他俩的谈话就是一张纸一支笔。
那天在仿膳,席间,轻松的谈话之余,杨振宁忽然问:“稼先,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七年,苏联人用了三年多,英国人用了四年,法国人用了八年,为什么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邓稼先没有说话。他的神色突然变得严肃了。他知道这是杨振宁在心中憋了许久的一个问号,一缕歉意在他心中浮沉,但他无法满足朋友的探究心愿。这不是一个人的秘密,是一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秘密。沉默,这是渴望理解和渴望被理解之间的沉默。
出仿膳,邓稼先夫妇陪同杨振宁到北京图书馆,杨振宁要查阅一本古籍珍本。许鹿希后来隐约记得,那是一本中国古代哲人的著作。杨振宁查阅完毕,在许鹿希的小本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似至晦实至明似至难实至易似至繁实至简。1986年5月30日下午,杨振宁去医院看望术后不久的邓稼先。当他滔滔不绝地对邓稼先谈起世界前沿科学的进展情况时,邓稼先的额上正沁出一粒粒虚汗。
6月13日,是杨振宁离北京回美国的日子,他又一次来到医院。两双手———打墙球的手,写物理公式的手———握紧又握紧———是真正的告别,不再是“再见”了。
1有关清华的诗词
有清华二字的诗句: 清华水木,浴火凤麟。
——《清华赋》青溪水木最清华——周必大《记金陵登览》秋色正清华——杜牧 《题白苹州》清华公子笑相邀——曹唐 《萧史携弄玉上升》梦绕清华宴地深——李山甫 《谒翰林刘学士不遇》方与清华宫——李沇 《醮词》长爱清华入诗句——李建勋 《雪有作》天阵清华野——许敬宗 《奉和执契静三边应诏》清华两辉映——张九龄 《胜,因并坐其次相得甚欢,遂赋诗焉,以咏其》月色清华——谢逸 《采桑子·冰霜林里争先发》料唤赏、清华池馆——吴文英 《花犯·小娉婷》问清华姓字——陈允平 《八声甘州·两台帘对卷》徒爱清华秋——张籍 《城南》山深水木清华——元好问 《清平乐·村墟潇洒》天质自清华——苏轼 《三月二十日多叶杏盛开》。
2我们为什么要读唐诗
中国的孩子尚在襁褓之中时,父母就很自然地边拍着宝宝边轻念几句“床 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父母们或许也不知道为 什么要让孩子们知道唐诗,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这样做,并且从没有停止过,也 许父母们自己也未必知道:就从这几句唐诗开始,他们就已经在孩子纯净空廓 的心田播种下了善良的种子。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也曾建议教育部要求小学毕业生要会背一百首唐 诗宋词,因为会背诗词有很多的好处。事实也即如此,鲁迅。
巴金、杨振宁、丁肇中等很多人都在少儿时代背诵了大量的诗词。唐诗于中国人真可谓家喻户 晓,是每个孩子的必修的“童子功”,然而,究竟什么是唐诗呢?仅是文学作 品吗?在唐诗中,蕴涵着什么更多、更深远的东西呢? 关于这个问题,叶嘉莹教授引用了中国现代著名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的四 句话,诗其实就是“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
她 说,这是关于诗的最精彩的一句定义了。诗其实就是人心的苏醒,而这种心灵 的苏醒,古今皆相通。
她认为“苦难的打击可以是一种催伤,但同时也可以是一种锻炼。而诗歌 的写作也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种抒发和缓解。”
唐代的诗人们,如果伤心 失恋了,会说“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然后哂然一笑,便心 情好起来了。 如果曾经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又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便会说: “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潇洒豪迈之情溢于言表。
而这些诗句,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哪里能找寻出一丝隔阂?正是这古今相通的人性,使 得唐诗虽然和我们相隔了一千余年的距离,却仍然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心中。 唐诗道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始终蕴含着一种生命的感动和召 唤。
人生百年,几多曲折,其中的得失利害、波澜起伏我们又能控制多少?当 你的人生面临着彷徨,甚而陷于困顿时,如果能有一种活泼开放的精神,那将 是无尽的愉悦和美的享受。在这样一份跨越时空的共鸣中,积蓄了古代伟大诗 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无疑“能够使得一个人超越小我生 命的狭隘和无常,把目光投向更广大、更恒久的向往和追求,并且给予你坚强 的力量和坚定的信仰”。
转眼千年已逝,浪漫的大唐王朝已经远去,如今已是物非人亦非„基本知识 积累不足,阅历不够丰富,理解有偏差等原因,使我们现代人学起唐诗来,会有 坠入重重迷雾之感,虽然背诵了一定数量的唐诗,却总不能触类旁通,理解到唐 诗的内涵和精髓。学无常法而必有法,方法得当则事半功倍。
《唐诗鉴赏知识实 用百科》把唐诗中的基本常识,全部整理出来,配上插图和解说,以易读精美的 方式展现给读者,使读者抓住学习唐诗的突破口,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有关唐诗 的最多知识。同是,本书还附有一些宋词鉴赏知识,希望本书可以成为读者学习 诗词的首选必读读物,带领大家领略诗词的绝代风采。
3介绍一两本唐诗宋词赏析 比较权威的书
《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 我看的是北京出版社的 有一定的点评 胶装本 比较容易坏 但是封面很不错 其他的鉴赏辞典也见了不少 都是很厚 而且封面、排版都不好看北京出版社的这本从书的装帧来说算不错
但是要论点评的好坏 那鉴赏辞典一类的书是很一般的 因为只是给中小学生做题目用 讲解只是为了让人了解意思而已
要看唐诗宋词 肯定不可以错过 《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这样的启蒙性读物 虽然某些佳作没有收录 但对于初学者来说 是了解唐诗宋词的不错的途径
唐宋诗词选释(俞平伯)比较权威
唐宋词欣赏 夏承焘 浙江古籍出版社 为普通读者写的书 平常买书 要么是唐诗 要么是宋词 但实际上 宋诗 唐词中也有不少精品 这本唐宋词欣赏 收录了唐宋名家词 对普通人而言 是比较实惠的 书里有词的创作背景、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很值得一读
读词常识 夏承焘,吴熊和 中华书局 也是夏老的作品 深入浅出 学词应该准备好这样一本书
人间词话 王国维 其实人间词话这本书 虽然是极好的 但是不适合现在的初学者 主要是王国维先生是新旧社会变革时期的人 而那时的语言习惯和现在大有不同 如果不熟悉此段时期语言风格的人 很容易把作者的意思理解错 而且 王国维先生是以西方哲学为基底写成的书 不了解康德 叔本华的人 很能把王国维先生的意思理解透 好在 市面上有较多的 人间词话评注 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但是 选评注也要小心 不要被忽悠了
国人必知的2300个唐诗鉴赏常识 万卷出版公司 国人必知的2300个宋词鉴赏常识 这两本书都挺厚 装帧一般 但是挺不错 有条件可以买 但也不必执着
我知道的书不多 在这里写出来 希望对你有帮助 在问问 问这种问题很难得到有效的回答 因为我也试过 结局很杯具 但是也许能撞到不错的回答。看运气。 希望你采纳我的答案 这是我自己打的 打了快一个小时。
这两个网站上有不错的诗词和鉴赏 你可以看看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 《诗词十六讲》(朱自清 吴梅 闻一多) 图文版 很不错 但是忍受不了半文言式风格的话就不要买了 会把人脑袋看晕的。
4清华北大状元门的各方评价
新华网:清华北大争“状元”不如争学术
事实上,公众也不想知道谁是“录取状元数”的老大。在争状元上,北大第一还是清华第一,其实并 不重要。这些年来,北大、清华早就成了国人心目中的最高学术殿堂,状元纷纷报考这两所学校,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笔者认为,倘若“状元”们纷纷弃两校而去,那才是北大、清华最应该挠头的事情。
北大清华的面子,到底应该体现在何处?还原到本质上来,当然还是学术。当下,没有人知道北大清华在争状元上谁是老大,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公众更关心两校在学术上谁是老大。
成都商报:抢状元 北大喜讯+清华捷报:今年招的状元>;全国总和
“清华北大”、“北大清华”,这样的排序问题,在旁人看来似乎无关紧要,但在北大、清华大学的招生老师那里,这个微妙的变化却非常重要。“谁是中国最高学府”的“暗战”已延续了近一个世纪。近日,因为高考录取优等生的数据“打架”,清华和北大这两所中国知名学府再次被拉进公众视野。一个是绝对领先,一个是全国第一,两校录取的状元相加,比例已远远大于100%。是谁在撒谎?还是你已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文字游戏当中? 中国的大学啊怎么看怎么像公司招人!中国的下一代啊!
北大与清华招生竞争毒瘤已蔓延至各市县中学,这个时候,各中学也抛出招生的优厚政策以吸引中考成绩较好的学生,于是一些学生就成了大爷,真搞不明白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78988e69d8331333361303130,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教育……
可笑之极,度量一所大学的标准不是看录了多少状元;如果状元全被你录取了,结果四年以后出来成废物,那么这所大学是好是坏呢?
说多了都嫌浪费口水!就是把全球的状元都给了他们,我看也捣鼓不出来一个诺贝尔得主!
建议,清华大学并入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大学并入北京**学院,反正如今都在娱乐大众,索性全进娱乐圈。
邓稼先是安徽怀宁县人,而杨振宁的父亲曾在安徽怀宁县一所高中任教过,杨振宁的“宁”就取自怀宁,所以他们算是半个老乡了;北京六部口30年代的崇德中学有一双童年时期的好朋友,大两岁的是杨振宁,小两岁的是邓稼先,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和哲学系教授邓以蛰的孩子。数十年的友谊是从逮知了的大树上,从弹玻璃球的泥地上开始的。这友谊一直延伸到了大洋彼岸。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即将回国的邓稼先与杨振宁、杨振平兄弟俩分手在芝加哥市。此后二十年,邓杳无音信。
1972年,杨振宁第二次来华。有关部门批准邓稼先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他童年的朋友。旧家具被人匆匆搬走。上面特地派来木工,把邓稼先的一个旧书橱打磨赶制,又匆匆装上一面穿衣镜,使之一天之内就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大衣柜;破旧的地板上了蜡,又有人从办公室扛来沙发,送来了良种西瓜、巧克力和一箱汽水。仿佛是在戏台上置景。邓稼先默认了。
杨振宁来的那天晚上,大院里特意放**,把人们都引到**场上。楼里显得别样的清静。杨振宁一进屋门,环视片刻,便径直向书架走去。这已是一个纯粹的医学专家的书柜,除了最显著位置上的两本毛泽东著作和厚厚一叠特意摆放的祖国风光明信片。
杨振宁回过头来,含笑的眼睛颇有意味地盯着他的朋友。早在1964年,他就从美国报纸上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报道中看到了邓稼先的名字。他不愿点破,只是微微地点点头,像在说,你收拾得很干净。
这次会面的气氛比1971年的第一次会面要自然和活泼得多。那一次是在宾馆,大概这一次毕竟是在家中。杨振宁吃着西瓜,喝着汽水,一会儿直言不讳地评论中国“不能调动人的进取心”,一会儿说起他在美国搜集的中国“文革”街头小报,一会儿又谈开了联邦调查局。忽然,他问:“这是你们的家吗?”
“是,是,”邓稼先用事先统一过的口径回答,“是许鹿希医学院的宿舍。”
“怎么没有儿子的床?”杨振宁聪明过人。
儿子的床的确在布置“客厅”时拆了。邓稼先没料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会看得如此精确。还是许鹿希反应敏捷,她忙打掩护:“儿子在爷爷家住。”
后来邓稼先又请杨振宁吃了一次烤鸭。和他在一起,邓稼先总感到有点紧张。他害怕童年时代的朋友会突然问起他的工作。可是杨振宁像是忘了这桩事。两个物理学家都在有意选择非物理学的话题。
这出戏直到杨振宁离北京去上海时才结束。邓稼先去机场送行,当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机坪时,杨振宁回转身,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问:“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搞的,他叫寒春,这是真的吗?”邓稼先的神情惊愕起来,他激动地张了张嘴,可是立刻又把嘴唇咬住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先上飞机吧。”
飞机腾空不久,邓稼先马上向上级报告并请示了他遇到的提问。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激动万分的邓稼先迫不及待地写了封信,立即交专人乘民航班机赶往上海。杨振宁是在上海市“革委会”为他饯行的宴会上接到这份急件的。当他拆开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邓稼先的笔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时,泪水夺眶而出。
1957年,当杨振宁赴瑞典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评委会要他提供一份英文的演说稿。杨振宁回答:“不,我要用中文写。”评委会说:“中文演说稿无法排印。”他坚定地回答:“那就请复制我的手稿。”
杨振宁常常从美国飞来。邓稼先的家是他平静而温暖的港湾,在邓稼先的身边是自由的。
———你给我找辆自行车!
———干什么?
———我们一块儿到香山去玩!
———我可不敢。人家能让吗?!
———真遗憾。那我们谈点什么吧,宇宙不守恒定理?规范场论?
常常,他俩的谈话就是一张纸一支笔。
那天在仿膳,席间,轻松的谈话之余,杨振宁忽然问:“稼先,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七年,苏联人用了三年多,英国人用了四年,法国人用了八年,为什么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邓稼先没有说话。他的神色突然变得严肃了。他知道这是杨振宁在心中憋了许久的一个问号,一缕歉意在他心中浮沉,但他无法满足朋友的探究心愿。这不是一个人的秘密,是一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秘密。沉默,这是渴望理解和渴望被理解之间的沉默。
出仿膳,邓稼先夫妇陪同杨振宁到北京图书馆,杨振宁要查阅一本古籍珍本。许鹿希后来隐约记得,那是一本中国古代哲人的著作。杨振宁查阅完毕,在许鹿希的小本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似至晦实至明似至难实至易似至繁实至简。1986年5月30日下午,杨振宁去医院看望术后不久的邓稼先。当他滔滔不绝地对邓稼先谈起世界前沿科学的进展情况时,邓稼先的额上正沁出一粒粒虚汗。
6月13日,是杨振宁离北京回美国的日子,他又一次来到医院。两双手———打墙球的手,写物理公式的手———握紧又握紧———是真正的告别,不再是“再见”了。(王X摘自《蔚蓝的思维———科学人文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钱钢)
北京六部口,30年代的崇德中学有一双童年时期的好朋友,大两岁的是杨振宁,小两岁的是邓稼先,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和哲学系教授邓以蛰的孩子。数十年的友谊是从逮知了的大树上,从弹玻璃球的泥地上开始的。这友谊一直延伸到了大洋彼岸。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即将回国的邓稼先与杨振宁、杨振平兄弟俩分手在芝加哥市。此后二十年,邓杳无音信。
1972年,杨振宁第二次来华。有关部门批准邓稼先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他童年的朋友。旧家具被人匆匆搬走。上面特地派来木工,把邓稼先的一个旧书橱打磨赶制,又匆匆装上一面穿衣镜,使之一天之内就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大衣柜;破旧的地板上了蜡,又有人从办公室扛来沙发,送来了良种西瓜、巧克力和一箱汽水。仿佛是在戏台上置景。邓稼先默认了。
杨振宁来的那天晚上,大院里特意放**,把人们都引到**场上。楼里显得别样的清静。杨振宁一进屋门,环视片刻,便径直向书架走去。这已是一个纯粹的医学专家的书柜,除了最显著位置上的两本毛泽东著作和厚厚一叠特意摆放的祖国风光明信片。
杨振宁回过头来,含笑的眼睛颇有意味地盯着他的朋友。早在1964年,他就从美国报纸上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报道中看到了邓稼先的名字。他不愿点破,只是微微地点点头,像在说,你收拾得很干净。
这次会面的气氛比1971年的第一次会面要自然和活泼得多。那一次是在宾馆,大概这一次毕竟是在家中。杨振宁吃着西瓜,喝着汽水,一会儿直言不讳地评论中国“不能调动人的进取心”,一会儿说起他在美国搜集的中国“文革”街头小报,一会儿又谈开了联邦调查局。忽然,他问:“这是你们的家吗?”
“是,是,”邓稼先用事先统一过的口径回答,“是许鹿希医学院的宿舍。”
“怎么没有儿子的床?”杨振宁聪明过人。
儿子的床的确在布置“客厅”时拆了。邓稼先没料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会看得如此精确。还是许鹿希反应敏捷,她忙打掩护:“儿子在爷爷家住。”
后来邓稼先又请杨振宁吃了一次烤鸭。和他在一起,邓稼先总感到有点紧张。他害怕童年时代的朋友会突然问起他的工作。可是杨振宁像是忘了这桩事。两个物理学家都在有意选择非物理学的话题。
这出戏直到杨振宁离北京去上海时才结束。邓稼先去机场送行,当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机坪时,杨振宁回转身,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问:“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搞的,他叫寒春,这是真的吗?”邓稼先的神情惊愕起来,他激动地张了张嘴,可是立刻又把嘴唇咬住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先上飞机吧。”
飞机腾空不久,邓稼先马上向上级报告并请示了他遇到的提问。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激动万分的邓稼先迫不及待地写了封信,立即交专人乘民航班机赶往上海。杨振宁是在上海市“革委会”为他饯行的宴会上接到这份急件的。当他拆开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邓稼先的笔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时,泪水夺眶而出。
1957年,当杨振宁赴瑞典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评委会要他提供一份英文的演说稿。杨振宁回答:“不,我要用中文写。”评委会说:“中文演说稿无法排印。”他坚定地回答:“那就请复制我的手稿。”
杨振宁常常从美国飞来。邓稼先的家是他平静而温暖的港湾,在邓稼先的身边是自由的。
———你给我找辆自行车!
———干什么?
———我们一块儿到香山去玩!
———我可不敢。人家能让吗?!
———真遗憾。那我们谈点什么吧,宇宙不守恒定理?规范场论?
常常,他俩的谈话就是一张纸一支笔。
那天在仿膳,席间,轻松的谈话之余,杨振宁忽然问:“稼先,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七年,苏联人用了三年多,英国人用了四年,法国人用了八年,为什么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邓稼先没有说话。他的神色突然变得严肃了。他知道这是杨振宁在心中憋了许久的一个问号,一缕歉意在他心中浮沉,但他无法满足朋友的探究心愿。这不是一个人的秘密,是一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秘密。沉默,这是渴望理解和渴望被理解之间的沉默。
出仿膳,邓稼先夫妇陪同杨振宁到北京图书馆,杨振宁要查阅一本古籍珍本。许鹿希后来隐约记得,那是一本中国古代哲人的著作。杨振宁查阅完毕,在许鹿希的小本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似至晦实至明似至难实至易似至繁实至简。1986年5月30日下午,杨振宁去医院看望术后不久的邓稼先。当他滔滔不绝地对邓稼先谈起世界前沿科学的进展情况时,邓稼先的额上正沁出一粒粒虚汗。
6月13日,是杨振宁离北京回美国的日子,他又一次来到医院。两双手———打墙球的手,写物理公式的手———握紧又握紧———是真正的告别,不再是“再见”了。(黄艾华摘自《蔚蓝的思维———科学人文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钱钢)
北京六部口,30年代的崇德中学有一双童年时期的好朋友,大两岁的是杨振宁,小两岁的是邓稼先,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和哲学系教授邓以蛰的孩子。数十年的友谊是从逮知了的大树上,从弹玻璃球的泥地上开始的。这友谊一直延伸到了大洋彼岸。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即将回国的邓稼先与杨振宁、杨振平兄弟俩分手在芝加哥市。此后二十年,邓杳无音信。
1972年,杨振宁第二次来华。有关部门批准邓稼先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他童年的朋友。旧家具被人匆匆搬走。上面特地派来木工,把邓稼先的一个旧书橱打磨赶制,又匆匆装上一面穿衣镜,使之一天之内就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大衣柜;破旧的地板上了蜡,又有人从办公室扛来沙发,送来了良种西瓜、巧克力和一箱汽水。仿佛是在戏台上置景。邓稼先默认了。
杨振宁来的那天晚上,大院里特意放**,把人们都引到**场上。楼里显得别样的清静。杨振宁一进屋门,环视片刻,便径直向书架走去。这已是一个纯粹的医学专家的书柜,除了最显著位置上的两本毛泽东著作和厚厚一叠特意摆放的祖国风光明信片。
杨振宁回过头来,含笑的眼睛颇有意味地盯着他的朋友。早在1964年,他就从美国报纸上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报道中看到了邓稼先的名字。他不愿点破,只是微微地点点头,像在说,你收拾得很干净。
这次会面的气氛比1971年的第一次会面要自然和活泼得多。那一次是在宾馆,大概这一次毕竟是在家中。杨振宁吃着西瓜,喝着汽水,一会儿直言不讳地评论中国“不能调动人的进取心”,一会儿说起他在美国搜集的中国“文革”街头小报,一会儿又谈开了联邦调查局。忽然,他问:“这是你们的家吗?”
“是,是,”邓稼先用事先统一过的口径回答,“是许鹿希医学院的宿舍。”
“怎么没有儿子的床?”杨振宁聪明过人。
儿子的床的确在布置“客厅”时拆了。邓稼先没料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会看得如此精确。还是许鹿希反应敏捷,她忙打掩护:“儿子在爷爷家住。”
后来邓稼先又请杨振宁吃了一次烤鸭。和他在一起,邓稼先总感到有点紧张。他害怕童年时代的朋友会突然问起他的工作。可是杨振宁像是忘了这桩事。两个物理学家都在有意选择非物理学的话题。
这出戏直到杨振宁离北京去上海时才结束。邓稼先去机场送行,当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机坪时,杨振宁回转身,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问:“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搞的,他叫寒春,这是真的吗?”邓稼先的神情惊愕起来,他激动地张了张嘴,可是立刻又把嘴唇咬住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先上飞机吧。”
飞机腾空不久,邓稼先马上向上级报告并请示了他遇到的提问。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激动万分的邓稼先迫不及待地写了封信,立即交专人乘民航班机赶往上海。杨振宁是在上海市“革委会”为他饯行的宴会上接到这份急件的。当他拆开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邓稼先的笔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时,泪水夺眶而出。
1957年,当杨振宁赴瑞典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评委会要他提供一份英文的演说稿。杨振宁回答:“不,我要用中文写。”评委会说:“中文演说稿无法排印。”他坚定地回答:“那就请复制我的手稿。”
杨振宁常常从美国飞来。邓稼先的家是他平静而温暖的港湾,在邓稼先的身边是自由的。
———你给我找辆自行车!
———干什么?
———我们一块儿到香山去玩!
———我可不敢。人家能让吗?!
———真遗憾。那我们谈点什么吧,宇宙不守恒定理?规范场论?
常常,他俩的谈话就是一张纸一支笔。
那天在仿膳,席间,轻松的谈话之余,杨振宁忽然问:“稼先,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七年,苏联人用了三年多,英国人用了四年,法国人用了八年,为什么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邓稼先没有说话。他的神色突然变得严肃了。他知道这是杨振宁在心中憋了许久的一个问号,一缕歉意在他心中浮沉,但他无法满足朋友的探究心愿。这不是一个人的秘密,是一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秘密。沉默,这是渴望理解和渴望被理解之间的沉默。
出仿膳,邓稼先夫妇陪同杨振宁到北京图书馆,杨振宁要查阅一本古籍珍本。许鹿希后来隐约记得,那是一本中国古代哲人的著作。杨振宁查阅完毕,在许鹿希的小本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似至晦实至明似至难实至易似至繁实至简。1986年5月30日下午,杨振宁去医院看望术后不久的邓稼先。当他滔滔不绝地对邓稼先谈起世界前沿科学的进展情况时,邓稼先的额上正沁出一粒粒虚汗。
6月13日,是杨振宁离北京回美国的日子,他又一次来到医院。两双手———打墙球的手,写物理公式的手———握紧又握紧———是真正的告别,不再是“再见”了。(黄艾华摘自《蔚蓝的思维———科学人文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钱钢)
邓稼先和杨振宁交往纪事
北京六部口,30年代的崇德中学有一双童年时期的好朋友,大两岁的是杨振宁,小两岁的是邓稼先,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和哲学系教授邓以蛰的孩子。数十年的友谊是从逮知了的大树上,从弹玻璃球的泥地上开始的。这友谊一直延伸到了大洋彼岸。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即将回国的邓稼先与杨振宁、杨振平兄弟俩分手在芝加哥市。此后二十年,邓杳无音信。
1972年,杨振宁第二次来华。有关部门批准邓稼先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他童年的朋友。旧家具被人匆匆搬走。上面特地派来木工,把邓稼先的一个旧书橱打磨赶制,又匆匆装上一面穿衣镜,使之一天之内就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大衣柜;破旧的地板上了蜡,又有人从办公室扛来沙发,送来了良种西瓜、巧克力和一箱汽水。仿佛是在戏台上置景。邓稼先默认了。
杨振宁来的那天晚上,大院里特意放**,把人们都引到**场上。楼里显得别样的清静。杨振宁一进屋门,环视片刻,便径直向书架走去。这已是一个纯粹的医学专家的书柜,除了最显著位置上的两本毛泽东著作和厚厚一叠特意摆放的祖国风光明信片。
杨振宁回过头来,含笑的眼睛颇有意味地盯着他的朋友。早在1964年,他就从美国报纸上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报道中看到了邓稼先的名字。他不愿点破,只是微微地点点头,像在说,你收拾得很干净。
这次会面的气氛比1971年的第一次会面要自然和活泼得多。那一次是在宾馆,大概这一次毕竟是在家中。杨振宁吃着西瓜,喝着汽水,一会儿直言不讳地评论中国“不能调动人的进取心”,一会儿说起他在美国搜集的中国“文革”街头小报,一会儿又谈开了联邦调查局。忽然,他问:“这是你们的家吗?”
“是,是,”邓稼先用事先统一过的口径回答,“是许鹿希医学院的宿舍。”
“怎么没有儿子的床?”杨振宁聪明过人。
儿子的床的确在布置“客厅”时拆了。邓稼先没料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会看得如此精确。还是许鹿希反应敏捷,她忙打掩护:“儿子在爷爷家住。”
后来邓稼先又请杨振宁吃了一次烤鸭。和他在一起,邓稼先总感到有点紧张。他害怕童年时代的朋友会突然问起他的工作。可是杨振宁像是忘了这桩事。两个物理学家都在有意选择非物理学的话题。
这出戏直到杨振宁离北京去上海时才结束。邓稼先去机场送行,当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机坪时,杨振宁回转身,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问:“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搞的,他叫寒春,这是真的吗?”邓稼先的神情惊愕起来,他激动地张了张嘴,可是立刻又把嘴唇咬住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先上飞机吧。”
飞机腾空不久,邓稼先马上向上级报告并请示了他遇到的提问。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激动万分的邓稼先迫不及待地写了封信,立即交专人乘民航班机赶往上海。杨振宁是在上海市“革委会”为他饯行的宴会上接到这份急件的。当他拆开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邓稼先的笔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时,泪水夺眶而出。
1957年,当杨振宁赴瑞典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评委会要他提供一份英文的演说稿。杨振宁回答:“不,我要用中文写。”评委会说:“中文演说稿无法排印。”他坚定地回答:“那就请复制我的手稿。”
杨振宁常常从美国飞来。邓稼先的家是他平静而温暖的港湾,在邓稼先的身边是自由的。
———你给我找辆自行车!
———干什么?
———我们一块儿到香山去玩!
———我可不敢。人家能让吗?!
———真遗憾。那我们谈点什么吧,宇宙不守恒定理?规范场论?
常常,他俩的谈话就是一张纸一支笔。
那天在仿膳,席间,轻松的谈话之余,杨振宁忽然问:“稼先,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七年,苏联人用了三年多,英国人用了四年,法国人用了八年,为什么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邓稼先没有说话。他的神色突然变得严肃了。他知道这是杨振宁在心中憋了许久的一个问号,一缕歉意在他心中浮沉,但他无法满足朋友的探究心愿。这不是一个人的秘密,是一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秘密。沉默,这是渴望理解和渴望被理解之间的沉默。
出仿膳,邓稼先夫妇陪同杨振宁到北京图书馆,杨振宁要查阅一本古籍珍本。许鹿希后来隐约记得,那是一本中国古代哲人的著作。杨振宁查阅完毕,在许鹿希的小本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似至晦实至明似至难实至易似至繁实至简。1986年5月30日下午,杨振宁去医院看望术后不久的邓稼先。当他滔滔不绝地对邓稼先谈起世界前沿科学的进展情况时,邓稼先的额上正沁出一粒粒虚汗。
6月13日,是杨振宁离北京回美国的日子,他又一次来到医院。两双手———打墙球的手,写物理公式的手———握紧又握紧———是真正的告别,不再是“再见”了。(王X摘自《蔚蓝的思维———科学人文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钱钢)
本文2023-08-06 00:18:01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26591.html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