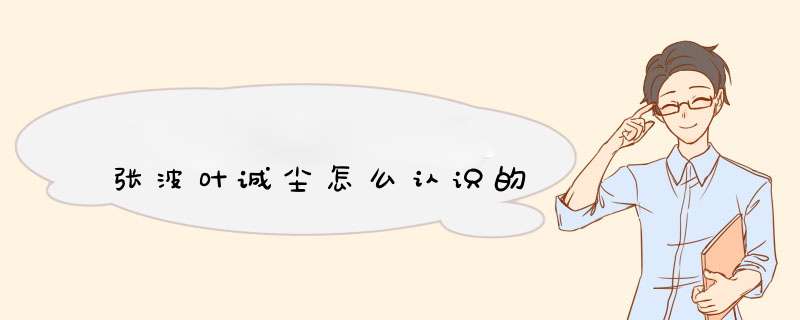“祝尤古术”老先生,给你讲述濒死体验

我第一次去香港是在九几年的时候,那里很小,在地图上看还没有指甲盖大;那里也很大,大到人与人的关系都都相隔万里,触不可及。
当时在做外贸生意,一个港商拉上我出境兜了一圈,才转机到的香港。那年月国内闭塞,香港是名副其实的花花世界。不出半月,我就背叛了与青梅竹马的誓言,连六旬老母也抛在脑后,整日泡在夜总会和马场。
在国内一年都挣不到的钱,只要和几个港商大佬跑跑颠颠就轻易到手。
可财悖而入,必悖而出。
好景不长,两年后我就被一个此前的手下骗光家财,差点露宿街头,经朋友介绍我到一家商行打工,勉强解决温饱。
那段时间每天都浑浑噩噩,整个人都麻木了,没什么知觉。
我记得是一天早上,刮台风,风雨很大,我落水了,在海水里扑腾着,长时间的熬夜,再加上没怎么好好吃饭,我很快就没有力气了。
海水从我的鼻孔和嘴巴灌进喉咙,好一会我才想起喊救命,可是周围一个人没有。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濒死体验,我的意识脱离,我感受不到我的身体了,脑海里像走马灯一样闪过以前的画面。
画面庞杂,甚至是我还没有记忆的婴儿时代,父亲再高出望着我笑,画面连绵不断。
还有几岁时的老家院子,我在院子中间,站在母亲给我晒的一盆温水里洗澡。
直到某些片段时,突然戛然而止,有股力量,迅速让你做出“决定”。
诬陷另一个小朋友偷走我的零用钱,他被妈妈拖走一顿暴打,我看见他脸颊的水肿,还有鼻血流出来。
这像是一场拷问,你一生的亏心事的拷问,如何处理,怎么解决。
随着画面闪现,画面里我的年龄也越来越大,随后浮现的是伶伶,接着是母亲。
后来我听人说,不同宗教对这种现象有不同的叫法,教会说这是来自主的“审判”;而在佛教中,这被叫做“了缘”,就是在你濒死的时刻,迅速做出反应,一件一件每一件你都要迅速做出抉择,一是忏悔,二是如何报偿。
对我而言,采访过程里,小会议室中弥漫着一股灵异、猎奇的味道。
面前的人,头发白了大半,但依旧精神抖擞,他的故事让我十分好奇,甚至有时候忘记了要主导采访。
这个爱上死亡的男人,叫严树。从那之后,他就像魔怔了一样,只身一人回到内地,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徒步之旅。
说漫长的徒步,并不足以形容严数的那段生活。
他从蝉鸣鼎沸的南方,一直走到冰天雪地的东北,一路乞讨,一日一餐。
从南走到北,并不是歌里的歌词,那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可他却只能一带而过的形容。
那是因为严数也不大清楚,他究竟是怎么过来的,从哪来,途径了什么地方,他一概记不起来了。
直到他遇见“四舅姥爷”。
他说他入夏的时候进的山海关,行到吉林小山村时,已经入冬了,他的鞋子还是单鞋,还有一只烂了,没有针线,只好用绳子缠了一圈又一圈。
“四舅姥爷”家中已经收留了两个人,一个叫做墨迹,一个叫少语,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所有人都管他叫四舅姥爷,可能是因为一开始和他生活的人,真的是他远房亲戚。
“你的魂儿呢?”四舅老爷捧着一碗热粥给他,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四舅老爷目光凌厉。
严数说,他好像有电流通过,就像医生抢救时电击心脏一样,他好像被唤醒了。
“喝吧。”四舅老爷把粥递到他手里,坐在凳子上望着他。
严数只觉得要来不及了,他慌忙放下粥,跪在地上猛的磕头不停。
好一会,“行了,你起来,住下吧。”四舅老爷说道,“把魂找到再走。”
就是这不可思议的对话,严数留了下来。
四舅老爷是个农村中医,平时来看病的人不多,也不是什么活都接,除非是老头子觉得该治的,他才会给人号号脉、摸摸骨。
更多时候,四舅老爷对乡民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这病我不治,去县医院看。”
严树留下来后,平时干农村杂活以外,没有什么事,剩下时间,按照四舅老爷教他的法子打坐、看书。
磨叽坐在炕沿上小声嘟囔着,像是自言自语,“县里的大夫水平也来越差,不知道医书都是怎么读的,没几天了,还不得都被他们害死”磨叽的喃呢声越来越小。
严数早就习惯了磨叽的小声嘟囔,有时候磨叽能前五百年、后五百载的说个遍,有时候又说村子里各家各户的闲言闲语,还有时候不知道在和什么人对话,一开始严数实在是不胜其烦,嘟嘟囔囔的像苍蝇赶都赶不走,但后来他慢慢习惯了,会仔细听磨叽在说什么。
严数敢肯定磨叽之前肯定是个知识分子,因为磨叽时不时会冒出几句古文,《诗经》、《大学》、《资治通鉴》,还有《毛选》,磨叽都背过。
可再后来,严数就挑自己愿意听的听点,不愿意听的就分散注意力,干点别的。
就像现在,他勾着炉火,准备加煤呢,丝毫没有在意磨叽说些什么。
外屋,少语在收拾碗筷,饭桌上放着他准备要缝制的棉布垫,收拾完碗筷,少语就会开始想女人一样缝制棉布垫了,不知道他在哪寻来的碎布头,缝好几十个之后,他就会把他们卖掉,一个能卖到1块多,来补贴平时的开销。
少语之所以叫少语,是因为四舅老爷在几年前告诉他,要持“止语戒”,要求除非不得已,否则不要讲话,少语最信四舅老爷,所以“不得已”在少语那里,变成了“绝对不”,自打严数来到这他从未听少语说过一句话。
严数说,这并不是他的夸张说法,而是真的;他甚至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偷偷观察少语,希望听听少语的声音,可这家伙睡觉从不说梦话,连呼噜都不打。
不过还好,这穷乡僻壤,也没什么事好沟通的,除了下地做活,就是日常杂活,几个人话虽少,但一个眼神就都懂了。
就是这几个性情古怪的人,组成了这个奇怪的家庭。
要说家里的家长——四舅姥爷,恐怕是最忙的了。
“都啥时时候了,也不知道哪去了,今天可是个好日子,月儿圆,野史古籍上说武则天”
磨叽正说着,四舅老爷推门回来了。
四舅老爷每逢十五都会喝的醉醺醺的回家,磨叽连忙从武则天的故事里收回思绪,从床上捧出被物,开始忙活起来。
但凡村民有什么异病、怪事都会来找四舅老爷,四舅老爷慢慢在村里被传得神乎其神,可四舅老爷好像有些避之不及,唯恐别人来烦他。
严数就曾亲眼见过,四舅老爷曾特意批卦、算事的时候有所保留、甚至故意算错。
可每逢十五,与四舅老爷喝酒的是村里的村长,不知道两人为何如此投缘,每个月都要醉上一回。
“别忙活了。”四舅老爷坐在炕沿,好像彻底醒酒了一样,除了一身酒气、脸色微红以外,没有一丝醉意。
几人忙停下手中的活,齐刷刷的看着四舅老爷,好像在等待着什么神圣的事情。
“少语,你持止语戒多少年了?5年?6年?”四舅老爷轻轻皱着眉头,望向一旁的少语。
少语想了想,用手比划了一个6,又比划了一个4。
四舅老爷把脸扭向一旁,眼神空洞,“真快啊,6年零4个月,真快啊。” 说着,四舅老爷好像想起什么来一样,转向磨叽,笑着说道:“你呢?多久了?”
“和他差不多,也5、6年了吧。”磨叽说道。
“我第一次见的的时候,你都没了个人样,一身的泥巴,浑身恶臭,可我看见你的心还是很干净,你身上虽然没有什么大伤,可我眼睛里你已经奄奄一息了。”
“那年我想死,死了几次都没死成。”磨叽说。
“我不知道这世道究竟怎么了,你又是怎么了。人活一世,草木一秋,都说出来能让你少受点罪,算是分散一下苦难吧。”四舅老爷说着,严数好想明白为什么磨叽整日嘟囔的缘由了,四舅老爷接着说,“几年没犯了?”
“上次是4年前。”严数突然不怎么适应磨叽一脸专注的说话。
“快了。今年把你的劫数过去,估计下次再犯就是又一个五年,我恐”四舅老爷顿了顿,“少语啊,我今天再和你说一遍,为什么让你止语。”
少语皱着眉头,面露悲色。
“止语一开始,可能会让你的其他感官放大,眼、耳、鼻的功能会扰乱你的心,但之后会让你达到真正的清净,身口意的真正清净。你到这个阶段了么”
少语点了点头。
四舅老爷转向严数,“你呢,怎么样?”
“我我不知道。”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就像他们俩的法门,人之道,补不足而损有余,你得靠你自己慢慢找回你的魂儿。”四舅老爷从柜子里取出一本红色的塑料皮笔记本,交给严数,“明天开始我开始正式教你祝尤术,你自救吧。”
“我可以拜你为师么?”严数赶忙跪在地上。
“你起来!”四舅老爷有些生气的皱着眉头,“你们都记着,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你们,修行在于自己,我这辈子连自己都没修好,还说什么救人?还说什么做你们师傅?你们把我当成什么都行,师傅、长辈、朋友、家人,都无所谓,记住,过的好过些,比什么都强。”
少语把头扭向一边,眼眶有些湿润,磨叽若有所思,整个人僵在那里。
“也就这几天吧,我估摸着。卦上说,应该是这个月,你们陪磨叽把劫渡了,保证有个人一直在他旁边。”
夕阳如血,缓缓隐藏入山。
少语和严数的汗水已经把身上的衣服浸湿了,也不知道磨叽怎么会有这么大力气,发起狂来两个人壮年男人都摁不住他。更别说磨叽了,口水、汗水、泪水流的一身都是,但总算了过去了。
磨叽用手摩挲了一把脸,抽了抽鼻子。
少语探了探头,轻挑眉毛,用表情问道:“好了?”
“嗯”,磨叽挤出个微笑,向两人点了点头。
接着,磨叽望着四舅老爷说道,“我去做饭。”
四舅老爷明显身子骨老了,面露疲惫,扶着香案点了点头。
不一会,严数听见厨房传来声音,“这劈柴的纹理不好,一看就是新木头,也不知道潮不潮,要是潮可不好生火”严数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
在中国,儒释道是不分家的,四舅姥爷就是这么个融汇的人,用看似不同的方法,去给不同的人解决问题,是他奇怪也拿手的本事。
不出半年,严数的祝尤术算是小成了,除了必要的时候,问问四舅姥爷,其他时候可以独自给人看病了。
祝尤其实是中医的一个偏门,逐渐被人们慢慢遗忘,除了基本的号脉、施针以外,还有符咒。
又过了不到半年,毫无征兆的,一场急病,四舅姥爷撒手人寰了。
临走前,四舅老爷把几个“家人”叫到炕边,“别哭了,没什么可哭的,我等这天很久了。”四舅姥爷气若悬丝,“时辰不多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我挺放心你们,以后的日子你们随自己的心意,各自去了吧。”
“但是,磨叽,你先不能走,你还有个五年劫数,你就留下打点打点,过了在走。”最后,四舅姥爷说道:“别废修行,活的自在些。”
说完就咽气了。
打点完四舅姥爷的后世,三人打了几斤酒,伶仃大醉了一场。
第二天,一切向没发生过一样,磨叽忙完农活,又开始坐在炕上开始嘟囔,严数洗涮完毕开始捧着红皮笔记本翻看着。
这时,少语拿了个绿色的帆布双肩包不知道收拾着什么,好一会,磨叽一边嘟囔一边转过头看着少语,严数也合上了书,站起身。
三个人开始一起帮少语收拾了起来,那是在帮少语收拾行囊,少语要走了。
两人都没有问少语去哪,他们只是把少语送到院门口。
少语往院门里推了推两人,示意别送了,接着转身要走。
两人再也忍不住了,“弟弟。”磨叽喊道。
“师兄。”严数喊道。
“你得保重啊。”
“咱们还能再见么?”
两人的眼泪喷涌而出。
少语转过身,走到磨叽身边,点了点头,“嗯。”少语从嗓子里发出的声音,像是在说,你也得保重。
又走到严数身边,说道:“嗯。”像是在说,肯定会见的。
接着头也不回的走向远处。
那是严数第一次听见少语说话,只有两个“嗯”字,却无比珍贵。
十天后,严数觉得自己也该启程了,上路去找魂儿。
他走到炕边,看着磨叽,磨叽停下叨咕,转头看着严数,还没等严数说话,磨叽就叹了口气,起身开始忙活起来,两人又开始无言的收拾行囊。
“我去做饭,吃饱好上路。”磨叽给严数收拾完背囊,说道。
“都走啦,这福地就剩我老哥一个了,看看今天弄点啥好吃的”
那天,磨叽忙活了一下午,一边嘟囔,一边给严数弄了一桌好菜。
严数离开四舅姥爷的小屋后,又开始行脚,这次他开始往家的方向走,一路上,用四舅姥爷传授的祝尤术给人治病,养活自己。
到老了家,严数去母亲的坟上祭拜之后,又开始重新上路。
严数因为每次给人看病,只瞧些陈年顽症,都是大医院束手无策,患者又寻路无门的病。治病手段又不是常规中医,有时甚至还用朱砂画符,开坛作法。但往往病者都会药到病除,取了诊费后,严数就会再次上路。
病者都觉着这个性情古怪的大夫医术高明,再寻时却只能望尘兴叹。
逐渐,严数的声名鹊起,名声和医术被人口耳相传。
说是声名鹊起,也不过是被瞧过病的人对他赞不绝口,众人都说,有一个行脚神医,可遇不可求,行脚、治病皆是他的修行。
也有不少人领着亲戚、孩子来找严数拜师,还有虔诚者找他询问修行法门,
严数说,他不想收徒,他的修行也区别于其他门派。
若遇诚心坚持询问的人,严数就会在纸上誊写一个地址,上面是一个东北的偏远小庙。还会对他说,修行在哪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一再坚持让我教,不如去这家小庙看看,若是有缘,主持自然会点化。
兄弟几人几年后又见面了,在之前的老屋中,老屋一点没变,磨叽日日打扫,虽显得有些破败,但依旧让人心驰神往。
少语修为更上一层楼,已经不用持戒了。
“时间快啊,5年了,眼看磨叽师兄的大关将至了。”严数说道。
少语从自己的双肩背里拿出来两个大酒瓶,说道:“自家酿的,尝尝?”
少语和严数两人双双把目光投向磨叽,磨叽心领神会,“有何喝不得,来,给我满上,这一桌子的菜,你们可别糟蹋喽,咱们边喝边吃,可不许剩。”
“酒能乱性,佛家忌之;酒能养性,仙家爱之。”严数眼神黯淡,若有所思的说道。
“有酒修道,无酒礼佛。”少语和磨叽异口同声的说。
之后几人笑作一团,这句话是四舅老爷常说的一句话,据说出自苏东坡,老人家融会贯通,随性而为。
几日后,严数和磨叽两人先把少语送走了,磨叽对严数说,我这有一个虔诚的老香客来求医,说他家族女性前些年都患上跛脚症。
“还有这样的怪病?”严数皱眉问道。
“是,你能不能替我去跑一趟?”
“人在哪?”
“回老家了,在河南。”
“没问题,反正都是行脚。”
“好,我一会去通知他,到了河南让他接引你。”
严数到了河南,见到了家属。宗族姓雷,果然家族女性10几人都有跛脚。严数诊了脉,又问了病情,断定这不是身子的问题。
在严数要求下,一行人到了雷家祖坟。
祖坟在后山山腰处,呈三角形排列,在祖坟旁不远处有一新坟,碑上的语焉模糊,只说是雷袁氏。
严数看了一圈祖坟,并没有发现什么要紧的问题,最后他走到不远处的雷袁氏的坟旁,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这个坟是你们雷家的吧?”严数问道。
周围的一行人似乎有些难言之隐,互相扫视,一语不发。
好一会,“有啥不能说的,这女人是我们雷家的,是自杀,祖上有规矩不能纳入祖坟。”说话人是一个30出头的壮年。
按理说,民间习俗,夭折、横死、自杀都不该纳入祖坟,也无可厚非。
一旁的长者瞪了一眼那壮年,说道:“严先生,这都我们家内的私事,本不该说,但您是先生,说了也就说了,袁木玲这女人的命苦啊。”
严数像是惊醒一般,猛的转身问道:“她多大?”
“死那年应该35吧,要是活着今年得37、8了。”
“袁木玲,木可是如沐春风的沐?”严数有火急火燎地问道。
“是啊,没错。”
严数神态紧张,一字一顿的接着问道,“玲可是伶仃的伶?”
“哎呀,先生,您是咋知道的?”
严数立在原地如五雷轰顶。
严数在河南村子的第二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一个身着破衣的男人来找他,他们在山坡上的一颗杨树下坐着,两人一见如故,男人从破烂的上衣口袋,掏出一个深红色的木铃系在严数腰间,严数掩面痛哭,而男人站起身,挥挥手,佝偻着腰走开了。
严数猛的惊醒,坐在床边,等待天亮。
严数说,他知道梦里的男人是谁、男人想要说什么、要干什么,都很好猜。
天一亮,他就到了沐伶坟前,设坛作法,打算把沐伶的骨灰带回老家。
可他这半辈子都没遇见这么奇怪的事。
给沐伶上的三根香中,一根刚烧个头就熄灭了,另两个根倒是燃着,可以燃烧速度相差极大,一根快要燃尽,一根却还有大半。
严数刚写好的黄符怎么也点不燃,火机点不燃蜡烛,蜡烛点不燃黄符,折腾了很久。
严数跪在地上,浑身颤抖,眼泪和鼻涕不自觉的流了一脸,他只觉得自己的劫数要来了。
很明显,沐伶并不愿意同他离开。
“我对不起你,沐伶啊,我来晚啦”严数垂着头,一边流泪,一边咧嘴嘟囔着。
不一会,严数的身后传来脚步声,“严先生,起的怎么早啊?”说话人是雷家宗族的长者。
严数偷偷拭去眼泪,起身说道,“你去把宗族所有人叫来,我有大事说。”
不一会,雷家男女老少都来了,得有三四十人。
“各位,你们的腿疾有两三年光景了吧?是不是每到黎明前疼痛最重?”严数说道。
雷家女眷都纷纷点头。
“各位,那是因为被你们害死的人,就是在黎明时分自缢的。这只是开始,还只是女眷,还只是瘸腿;不销半年,整个雷家都会鸡犬不宁,小孩子都会遭殃。”严数说完,大家都嘀咕起来。
“严先生,你得救救我们啊,我们雷家全族,都会感您大恩大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说是不是?”其中一个老者说道。
“那是佛家说的,我不信佛,我救不了你们。我叫你们来是想告诉你们,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你们好自为之吧。”说完,严数佯装要走。
“哎哎哎,严先生,别别别,您道法通天”家族人围了上来,几个腿疾严重的已经跪下了,最后大家纷纷下跪,“严师傅、严先生,您救救我们吧。”
严数把沐伶嫁到河南后的事大致的说了一遍,还特地说了几个细节,上吊的时间、上吊绳的颜色,众人听后无不颤栗,对严数言听计从。
9
本来严数是要带着两人的骨灰回老家下葬的,但后来他决定还是带回吉林,老家已经没人能照顾他们的墓了。
现在老房子里,严数重新干起了四舅老爷的工作。
道心孤绝。
严数对这四个字深以为然,现在他不仅继承了四舅老爷的工作,还继承了四舅老爷常说的那句话:
“这病我不治,去县医院看。”
故事本来到这就应该结束了。
就在我第二天整理采访稿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有些事由和过程对不上,于是再次联系严数。
几十年前的香港,严数在海中险些丧命,生前的一幕幕如走马灯一样,在眼前晃过,迅速地“了缘”,一次次严肃的审判等他回复,他并不只是重新体验了自己的人生,还有别人的。
他看见沐伶在屋门内举起农药,仰头而尽,她的全部心绪、情感、悲喜,这一刻严数全部心灵相通,一幕一幕真实而残酷。
他还看见沐伶站在凳子上,腥红的绳子勒在她白皙的脖子上,紧接着她踹开了凳子。
这时,时间停止,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在质问严数,你拿什么偿还?
我用我这辈子还,这辈子还不上,下辈还,下辈子还不上,还有下下辈子。
这是严数心里想的,之后他得救了,莫名其妙的活了下去。
他一直以为那是个意识和神经错乱的玩笑,是死前生理系统的一次胡乱反映,直到他到了河南。
本文2023-08-06 06:03:28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285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