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出自哪里合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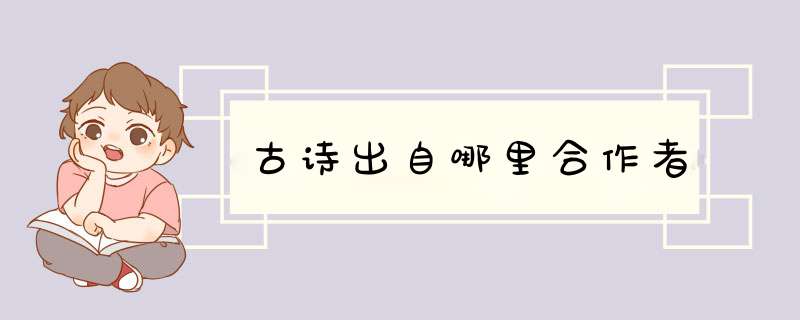
吴地文化从考古发现来看,已有上万年的历史。吴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必然是伴随着当地初民的生产劳动,祭祀习俗,和生活娱乐活动而发生发展的。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在没有文字之前,很难寻觅它的遗迹。如今要想找到古代吴歌的真貌,寻找它的源头,已经是一件十分困难和复杂的事。
在晋以前“吴歌”一词,未见诸文字。在汉魏歌谣中也没有吴歌之目。春秋战国时代,有“吴歈”“歈”又作“愉”,有人解释,俞,是独木舟,欠,是张口扬声,合起来即是船夫唱的歌。之说,见屈原的《楚辞·招魂》:“吴歈蔡讴,奏大吕些。”汉代王逸注:“吴、蔡,国名也。歈,讴,皆歌也。大吕,六律名也。”左思《吴都赋》云:“荆艳、楚舞、吴愉、越吟,此皆南方之乐歌,为《诗三百篇》所未收者也。”那时把吴国人唱的歌曲统称为吴声歌曲。当时吴国的疆土领域常有变化。古吴国要从泰伯、仲雍建立句吴算起。因此有人说:“江南文化始泰伯,吴歌似海源金匮。”(无锡旧名金匮,梅里有泰伯墓)此说法的根据是泰伯、仲雍从中原来到江南,把中原文化带到荆蛮地区,江南文化才得以开发,因此吴歌发源于此。这个说法值得推敲,从考古发现长江文化的历史,已推前到七千年到一万年,吴越地区的先民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创造了稻作文化,吴歌和稻作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最早的歌谣总是伴随着劳动产生和发展的,中原文化不可能代替当地的土著文化,反之,泰伯、仲雍到了江南,不入乡随俗,断发纹身,也是无法生存的。当然,他们带来了中原文化,对江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果说某一首歌,是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吴歌的源头根本不可能是外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吴歌来源于“越”,或者发于“南音”。这是因为有一篇《越人歌》,或《越人拥楫歌》,见西汉末年刘向著《说苑·善说篇》,记载着春秋时期楚康王公元前559-545之子皙泛舟于新波之中,刘向曾照越国的原音记录过一首百越歌,文字无法看懂,译成楚文,即:“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从内容来看,反映的是当时臣子取悦于王子的歌。这种上层社会吟唱的歌并不少见。吴吟的出典也是楚国使者陈轸,为讨好秦王而“为王吴吟”,他唱些什么内容没有流传。据《世说新语》记载,晋武帝曾问被掳的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你是否会唱﹖”孙皓即席应唱,歌词是: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这显然是用民歌曲调填词的五言四句,接近民歌,但无吴语特色。
战国吴越之争的时代,吴国曾战败越国,越后来又灭了吴。吴、越两国均在江南接土邻境,“习俗同,言语通”,“同音共律”,因此吴愉越吟是基本相同的。楚破越后,吴、越之地大部分为楚所占,称为“吴楚”或“荆吴”。因此,这段历史时期的吴歌,很难用现存的区域划分来说明。不是有人说“四面楚歌”,应当是“四面吴歌”吗?虽然项羽的时代已非吴楚之时,但楚歌、吴歌也一定不像我们划分得如此清楚。
据有的专家学者引证,“春秋战国时期的吴愉、越吟,是夏、商、西周时期南方夷蛮音乐声歌'南音'的继承和发展。”其主要根据是说虞夏时有南方涂山氏之女歌唱的“南音”,即古称的《侯人歌》。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篇》列入最早的乐府歌曲,说:“涂山歌手《侯人》,始为南音。”此说来源于《吕氏春秋·音初篇》中引述的关于大禹的传说记载。《侯人歌》的歌者涂山氏的故地尚不明,《野客丛书》说:“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又一说在九江,一说在绍兴,虽同属江南,但是否属吴愉、越吟之类尚存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吴地的中心是在建业(后称建邺、建康,即今南京),“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晋书·乐志》)这时所指的吴声歌曲,后来被人统称之为“吴歌”。可以说吴歌当时即是吴声歌曲的缩写。吴声歌曲初期的作者多属无名氏,说明是在民间流传中采录的。吴歌在此之前见诸文字的很少,文学家和史学家都从乐府中找到吴歌的端倪。特别是《诗经》上的十三国风,只辑录了北方的歌谣而没有吴歌的记录,吴声歌曲补上了这一空白,其价值很高。但对吴声歌曲也要作具体分析;南朝乐府初期采录了吴地歌谣,是徒歌,比较纯朴,在《子夜歌》等吴声歌曲中保留了这种素质,但当“徒歌“被以管弦,上了大雅之堂以后,许多文人纷纷仿作,成了上层社会的行乐之词,这种吴声歌曲和民歌(吴歌)已相距甚远,但在文学史上却一直统称为“吴歌”。
其实,历史上文人记载的资料,仅仅是吴歌的“流”,溯流寻源,研究吴歌的流变,这些资料当然非常珍贵,但是要找寻吴歌的真正源头,要靠扎实的田野作业,从劳动人民口口相传,世代相袭的口头文学中去寻觅,经过科学论证,才会有所发现。
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文字记录,最早用吴语记录的山歌,是唐末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鏐唱的一首即兴的山歌。这首山歌原载于宋吴僧文莹《湘山野录》,五四以后研究吴歌的先辈容肇祖先生,曾于1936年北大《歌谣》周刊第二卷第七期上,发表了《一千年前的一首吴音山歌》一文,介绍了这首最早的吴音山歌,容先生引证《学海类编》本的《湘山野录》,记下了这一条的全文,如下:
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梁太祖即位,封钱武肃(鏐)为吴越王。时有讽钱拒其命者。钱笑曰:“吾岂失为一孙仲谋耶?”拜受之。改其乡临安县为临安衣锦军。是年省茔垄,延故老,旌钺鼓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钓之所,尽蒙以锦绣。或树石,至有封官爵者。旧贸盐肩担,亦裁锦韬之。一邻媪,九十余,携壶浆角黍迎于道。鏐下车亟拜。媪抚其背,犹以小字呼之,曰:“钱婆留,喜汝长成。”盖初生时光怪满室,父惧,将沉于丫溪矣。此媪酷留之,遂字焉。为牛酒大陈乡饮,别张蜀锦为广幄,以饮乡妇。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岁已上玉樽。时黄发饮玉者尚不减十余人。鏐起,执爵于席,自唱还乡歌以娱宾。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临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爱日辉。父老远近来相随,家人乡眷兮会时稀。斗牛光起兮天无欺!”时父老虽闻歌进酒,都不之晓。武肃亦觉其欢意不甚浃洽。再酌酒,高揭吴喉,唱山歌以见意。词曰: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侬心子里!歌阕,合声赓赞,叫笑振席,欢感闾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
这段笔记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一千多年前,吴越王钱鏐衣锦还乡到临安(今杭州)的情景,他仿照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高兴地唱起来,但乡亲们都听不懂,不能尽兴,于是他“高揭歌喉,唱山歌以见意”,山歌虽然只有三句歌词,但却是乡音土语,立即引起共鸣,“叫笑振席,欢感闾里”。从这三句歌词来看,确实是全部用吴语记录下来的山歌,加上注释更加确切地反映出吴音的特点,使人感到非常亲切。它比六朝吴声歌曲记录的吴歌,更加朴实、通俗,乡土气息特别浓厚。研究吴歌的学者们,把它作为用吴语演唱并完全用吴语记录下来的第一首吴歌。在顾颉刚先生七十年前写的《吴歌小史》中,引用了它,关德栋先生在为冯梦龙的《山歌》作序时,也说它是“吴中山歌最初的记载”(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明清民歌时调集》上)。原记述者的最后一句话:“今山民尚有能歌者”,说明北宋时还有人能唱这首歌,关德栋先生进一步引证南宋人袁耿《枫窗小牍》也叙及此事,其后并说:'至今狂童游女,借为奔期问答之歌。'”可见此歌流传久远。并进一步明确吴歌主要即是“山歌”,这就和冯梦龙时代收集的山歌,和现代流传于广大农村的山歌,一脉相承。
历史对民间文学是这样的不公平,生长在田野里的民歌,靠口口相传,代代相袭,文字记载却寥寥无几。经过文人笔录记载下来的民歌,又常常是被改造过了,其中不乏人民性很强的作品,但已非民间口头文学的本来面目。
吴歌历史源远流长。传说殷商末年,周太王之子泰伯从黄土高原来到江南水乡,建了勾吴国并以歌为教,从那时算起,吴歌已有3200多年历史。 《楚辞·招魂》即有“吴蔡讴,奏大吕些”的记载。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时将吴歌编入《清商曲辞》的《吴声曲》。明代冯梦龙采录宋元到明中叶流传在民间的大量吴歌,辑录成《山歌》、《挂枝儿》。清代是长篇叙事吴歌的成熟繁荣时期,经书商刊刻、文人传抄和民间艺人的口传,保存了大量长篇叙事吴歌。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发起了歌谣运动,《晨报副镌》于1920年起连载吴歌,其后陆续编辑出版了《吴歌甲集》(顾颉刚)、《吴歌乙集》(王翼之)、《吴歌丙集》(王君纲)、《吴歌小史》(顾颉刚)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辑成《吴歌丁集》(顾颉刚辑、王煦华整理)、《吴歌戊集》(王煦华辑)、《吴歌己集》(林宗礼、钱佐元辑),大量吴歌得到搜集、整理和研究。特别是长篇叙事吴歌的发现、挖掘和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歌谣卷的编纂出版,使大量的吴歌得到了抢救性的搜集和保存。
进入21世纪,有关部门又编辑出版了《白茆山歌集》、《芦墟山歌集》、《吴歌遗产集粹》和《吴歌论坛》等几百万字的吴歌口述和研究资料。中国传统民间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吴歌如今也逐渐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 作为吴歌的3个里程碑,安·比雷尔的《汉代民歌》和《玉台新咏》把南朝的吴声歌曲译成了英语,科奈莉亚·托普曼翻译出版的冯梦龙的《山歌》把明代的吴歌译成了德语,荷兰学者施聂姐出版的《中国民歌和民歌手--江苏南部的山歌》则研究和翻译了部分现代吴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传统民歌保存情况考察团曾于1994年到苏州、常熟考察吴歌的保存情况。这说明了中国传统民间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
在长期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生活条件下,农村交通闭塞,农民生活贫困,文化生活非常贫乏,那时唱山歌就是他们唯一的自娱形式,除了劳动场所外,夏天乘风凉,冬天围炉取暖,以及农闲时逛庙会,都唱山歌以自娱,这不但可以自由地抒发胸臆,而且可以施展人们的创作才能,表现人们的聪明智慧,丰富人们的劳动生活知识。当然,对于青年男女来说,唱山歌会给他们带来爱情的欢愉,或者成为婚姻的媒介。所以山歌成为农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和娱乐工具。有的歌乡山歌代代相传,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歌手。有的歌手常在赛歌会上通过对歌、赛歌,大显身手,远近闻名。有的歌手从小即在自己的亲属身边学唱山歌,有超群的智慧和惊人的记忆力。过去家庭传承是山歌传承的主要方式。这样便形成了农民自己的未经雕琢的自然形态的文化。它和其他文艺形式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的口头性、变异性、传承性和自娱性和职业艺人有明显的区别。这种文化现象和民俗事象,被称为天籁之声,生动地记录了江南农民和下层人民的生活史,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十分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
顾颉刚先生在他写的《吴歌小史》中说道:所谓吴歌,便是流传于这一带小儿女口中的民间歌曲。这一带,大致是指长江三角洲的吴语地区。由于历史上历代区域划分不同,早期吴是吴国领域的概念,甚至包括现在的南京和扬州等地。现在所说的吴,是指吴语区,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市,即是江浙沪等地的同一个吴语区语言文化圈,同属传统吴文化范畴。无锡恰在它的中心地位,它是一座享誉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采集吴歌,也以它为中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寻邬文献丛刊(7卷)》简介
《寻邬文献丛刊(7卷)》一共七卷,它们分别为:
一、《石溪词辑注》
二、《民国乡土教材三种》
三、《长宁县志辑注》
四、《泛梗集笺注》
五、《邱簬村诗全集笺注》
六、《寻邬碑刻与契约文书》
七、《民国书刊寻邬文献选辑》
据寻乌县历史文化研究会消息,江西省首部县域古籍文献丛书——《寻邬文献丛刊》第一批书籍正在江西人民出版社排印。《寻邬文献丛刊》第一批书计有清邱上峰《邱簬村诗全集笺注》(上下二册)、清《长宁县志辑注》、民国邝摩汉《石溪词辑注》、《民国乡土教材三种》(内含谢竹铭《寻邬乡土志》《应酬从俗》及刘淑士《寻邬应酬须知》)。由于该丛书不公开发行,需要书籍的朋友可与责任编辑李月华联系。《寻邬文献丛刊》后续书清吴之章《泛梗集笺注》《寻邬碑刻与契约文书》《民国书刊寻邬史料选辑》将于明年春出版。
丛书主编:黄志繁,男,1972年生,江西石城人。1991年毕业于赣南师范学院。1995年师从南昌大学邵鸿教授,1998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8年师从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2001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1年起进入南昌大学历史学系工作。2002年至2004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工作,师从曹树基教授。2005年11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为访问学者。2006年破格评为教授。2010年4月赴香港中文大学为访问学者。现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特别重视对江西区域社会的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项、省部级项目2项。获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3次。获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三等奖1次。代表作为《“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明史学会理事,江西省历史学会副秘书长等。
执行主编:刘承源,男,1966年生,江西寻乌人。曾任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客家方志项目领衔专家、《江西地方珍稀文献丛刊(10卷)》副主编、广东客家文化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先后承担清康熙十二年《长宁县志》、清乾隆十四年《长宁县志》校注工作,承担清光绪三十三年《长宁县志》校勘工作,参与清光绪二十七年《长宁县志》、明祝枝山《正德兴宁志》、明嘉靖《赣州府志》、明嘉靖《虔台续志》、明天启《重修虔台志》、清道光《定南厅志》的整理工作,参与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客家珍稀谱牒文献丛刊(100卷)》、广东省重点图书《客家山歌大典(10卷)》等项目的策划编纂工作,撰有《长宁县志纂修历史及版本考略》《邝振翎事迹考略》《我是寻邬第一郎:曾有澜事迹编年考》《江湖未是风波恶:明代黄乡叶氏历史初探》等见诸《江西文史》《江西地方志》。
责任编辑:李月华,女,江西人民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编辑、副主任。
阴法鲁先生(1915-2002),山东省肥城县人,著名古典文献学者和音乐舞蹈史专家。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1939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毕业。1942年昆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首届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历任昆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助教,武昌华中大学(迁滇)副教授,北京政法学院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京市音乐舞蹈协会副主席,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诸职。主要论著有《唐宋大曲之来源及其组织》、《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与杨荫浏先生合著)、《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从音乐和戏曲史上看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古文献中不同语言的译语校注问题》等,结集有《阴法鲁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阴法鲁先生参加中华书局本廿四史的整理工作,具体负责《隋书》的点校定稿。此外,还主编有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化史》,荣获教育部、北京大学等各项奖励。
阴法鲁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和中国文化史,侧重古代音乐舞蹈研究,在古代音乐与文学交叉领域的研究有突出贡献。1939年,阴先生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之后,即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与逯钦立、马学良、周法高、杨志玖、王明、任继愈等成为该所西南联大时期首届研究生。阴先生的研究生导师为罗庸(庸中)、杨振声(今甫)先生,两先生为其确定的研究方向为“词之起源及其演变”。罗庸先生还拟订了详细的研究工作指导说明书,并提示三点研究进阶:其一,唐五代宋词调之统计及时代之排比;其二,就各调之性质分类,溯其渊源;其三,依性质及时次,重编一“新词律”,主要在调名题解及说明其在文学史上之关系,不重在平仄律令之考订。罗庸先生把随身携带的清万澍《词律》和清徐本立《词律拾遗》两书交由阴先生剪贴,编成《词调长编》,另外编集《乐调长编》,然后以两长编为条目,归纳门类,辑录资料,强调要“从乐曲之见地,溯其渊源,明其体变”。在扎实的文献工作基础上,阴先生得以进入唐宋音乐与文学关系领域的探究,并认识到研究古代诗歌体裁的发展嬗变,首先必须研究当时乐曲形式的发展嬗变。循此思路,阴先生在罗庸先生指导下,撰写完成毕业论文《词与唐宋大曲之关系》。大曲是燕乐之一种,每曲由十余乐章组成,结构颇为复杂。其为唐代梨园法部所用者,谓之“法曲”;如仅截取其后半部分,则称为“曲破”。大曲盛行于唐宋时期,且堪称两代音乐最高之典制。大曲影响所及,不惟产生若干词调曲调,即宋之杂剧,金之院本,元之杂剧,亦莫不承其余绪,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王国维先生著有《唐宋大曲考》,开大曲研究之先河,然所论仅限宋代,唐代大曲较少涉及,宋代部分亦失之简略,且颇有可商榷之处。阴先生论文在王国维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梳理大曲的来源与组织结构,进而深入分析词调与大曲之关系,大曲曲词之特征,探究词的起源问题。因为相关研究植根于深厚的音乐史背景,且视角独到,故其论述推理缜密,结论颇具说服力。
阴先生的研究结论,澄清了唐宋大曲及其与文学关系研究的许多关键问题。如唐梨园法部所演奏之法曲,实即大曲,或有以为古代之遗音者。清儒凌廷堪《燕乐考原》即指法曲出于清商三调,“天宝法曲即清商南曲”。阴先生条分缕析,多方举证,论定凌说之非,法曲不能等同清商,遂为定谳。至于大曲的来源,阴先生认为,既有对清商乐“相和大曲”的继承,又有传自西域者,还有根据西域音乐自造者。唐宋大曲的特征有三:即多遍,具备序、破之组织,配舞,缺一不可。遍,亦作“徧”“片”,虽为乐曲单位名称,然所指范围有大小之别。大曲包括的许多可以独立之小曲,相对于整部大曲而言,谓之“大遍”;而就其中一节而言,则有排遍、遍、衮遍诸称,此“遍”也有称“叠”者,大致相对于西方音乐中的乐章,而所谓“小遍”,即指大曲中可以独立之乐章;每遍所包括之小曲,也有不止一曲者。此种小曲,或亦谓之“遍”,或谓之“叠”,或谓之“阕”,源光圀《大日本史·礼乐志》谓之“帖”。大曲虽有多遍,但结构大致为三部分,即白居易《霓裳羽衣歌》描述之散序、中序和破。王国维《唐宋大曲考》云:“顾大曲虽多至数十遍,亦只分三段:散序为一段,排遍、、正为一段,入破以下至煞衮为一段。”此正可与白氏散序、中序、破相对应。散序部分没有拍子,也不配以舞蹈,然别具一种悠扬婉转之情调。大曲自“排遍”开始有拍。“排遍”亦称“叠遍”,因大曲各遍内包含小曲不止一曲,而尤以排遍为多,故谓之“排”“叠”。任二北《南宋词之音谱拍眼考》认为“排遍之排谓排匀也”,恐失之穿凿。王国维《唐宋大曲考》云:“唐以前,‘中序’即‘排遍’,宋之‘排遍’亦称‘歌头’。”然唐大曲之中序与宋大曲之歌头,两者虽地位相当,仍有可区别之处。宋大曲虽然歌者自排遍起,但与歌头得名之由来,无甚关涉。根据文献记载,唐五代已有“歌头”之说。排遍起歌,则歌头必为排遍之第一遍,可由宋人作品证明。大曲多遍繁复,故至于宋代,管弦家在普通演奏时,已多截取某一部分。此截取之部分,即谓之“摘遍”。摘遍之法盛行,影响有二:即词家选择大曲之摘遍以填词,曲家就摘遍衍生创制性质不同之独立乐曲。
虽然治学继承了注重文献的朴学传统,但阴先生的学术视野并未局限于此,而是接受了现代史学的进步理念,非常重视古文献资料与文物资料的结合,与社会调查资料的结合,以及中国材料与外国材料的结合。他认为,文献记载虽是研究古代音乐文化史的主要资料,但古文献中有记载过于简略、不周密、不具体或疏漏、错误、伪托的情况,需要用文物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来加以补充、澄清和订正。如商代甲骨文中有“乐”字,像木板上张着丝弦,有学者认为其原来就是一种弦乐器。阴先生认为,木板上张着丝弦,还必须有共鸣器,才能发出较高的音响。甲骨文中就有一个带底座的“乐”字,底座大概同时就是共鸣箱。这种乐器可能就是古琴的原型。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琴,琴面板的背部有槽,和另一块有槽的底板相合后,才能构成共鸣器,这是商代以来的遗制。当时因限于工艺水平,还不能做出固定的中间保留较大空间的共鸣器。古文字和古文物的实证反映出一种乐器形成发展的过程,可以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阴先生还对敦煌石窟壁画和藏经洞文献研究倾注了极大热情,先后撰写了十余篇论文,利用敦煌壁画资料,结合文献记载与传世文物,考察唐代的乐器、服饰、舞姿,解读舞谱,描摹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的盛况。阴先生的敦煌艺术研究成果,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开创之功。
社会调查是近世学术颇为倚重的研究手段,阴先生较早地将其引入音乐文学研究领域。比如他注意到各地民歌,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山歌,许多都采取唱和形式,即领起部分和应和部分相结合的形式。而古代许多入歌作品,亦有此例。遂参照分析中国古代诗歌的唱和形式。西安及其近郊流行一种传统的民间音乐,称为“鼓乐”。据学者研究,鼓乐保存着某些唐宋大曲的遗迹。阴先生认为这是极有价值的资料,推测鼓乐中所用的独奏、轮奏、合奏等演奏方式,应存在于唐宋大曲之中。鼓乐演奏时还有穿插乐段、变奏、加花等手法,乐谱之外有口传心授的部分。依例可以想见,唐宋大曲在演奏时,于乐谱之外,或有即兴穿插补充之处。1959年,阴先生与历史研究所的同事参加西藏文物调查,历时四个月,遍览西藏重要寺庙。其间,他特别关注各寺庙残存的乐器、壁画和经书文献,并据此考察吐蕃文化与敦煌文化的关联,西藏文化与内地文化的联系。此类研究,当时还很少有人涉足。
对于国外材料的利用,阴先生在敦煌音乐舞蹈艺术研究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他在考察敦煌壁画描摹的乐器、服饰、舞蹈时,穷究其地域背景,并引用不同文种的文献和社会调查资料予以佐证。如考察敦煌壁画乐器时,即引用到日本宫内省存藏的腰鼓、羯鼓实物,日本信西古乐图描绘的羯鼓、揩鼓,以及亚述的铜铙等国外材料。论及“答腊鼓”,则联系到新疆维吾尔族仍在使用的名为“答普”的手鼓,并引用唐代张祜《周员外席上观柘枝》诗句“画鼓拖环锦臂攘”为例,指出类似形式的鼓,法文称“昙不腊”,英文称“昙波铃”(tambourine),阿拉伯人称“塔波儿”,都是源于同一语根。类似的考证事例再如:商代甲骨文“龠”字是一种编管乐器,至战国时代称为“箫”或“籁”。用竹管排比而成,即指排箫。至今国内外有些民族语言称管乐器为“奈伊”(nay),和“籁”的读音相近。如维吾尔语称笛为奈伊,中亚各族语称管乐器为奈伊,特别是匈牙利语和罗马尼亚语,就称排箫为奈伊。在古代汉语中,有些方言l和n往往不分,因此,nay很有可能是“籁”的音译。阴先生还对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史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撰写了《丝绸之路上中外舞乐交流》《唐代中国和亚洲各国音乐文化的交流》《从音乐和戏曲史上看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历史上中国和东方诸国音乐文化的交流》《古代中国与南方邻国的音乐文化交流》《明清时代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利玛窦与欧洲教会音乐的东传》《近代澳门与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等论文,学术贡献卓著。
综观阴先生的治学经历,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他在学术切入点和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明显具有现代学术的眼光,而在研究方法上,则既崇尚传统朴学工夫,强调文献基础,同时又接受现代史学重视文物考古和社会调查资料的先进理念。因此,他的研究选题虽然角度不大,对象冷僻,但立论甚高,视野开阔。阴先生并不是一位书斋型学者,他的学术追求都是尽力与实践相结合,服务于现实。他为校外音乐舞蹈史学界培养的不少人才,都成为指导古代音乐舞蹈实践的骨干。他本人还与著名音乐史家杨荫浏先生合作,研究南宋词人姜夔,解译其词曲乐谱,令宋时的吟唱再现于七八百年后的舞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驰名中外的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其辉煌成功的背后也有艺术顾问阴先生的一份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本文2023-08-06 06:39:09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28816.html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