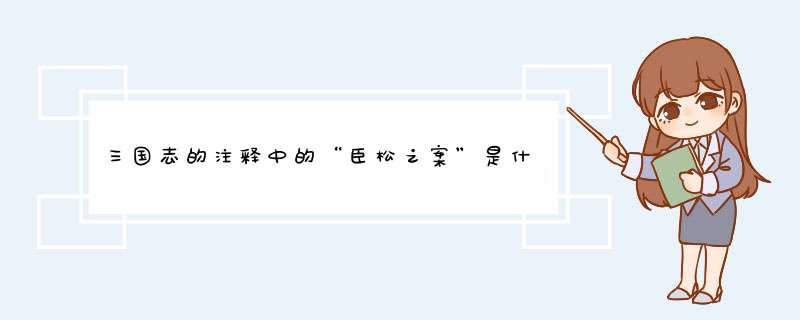中国姓氏里面有姓是的吗?

中国姓氏中有来姓。
来姓源于姒姓,出自古代夏王朝缔造者大禹之裔孙伎来,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据史籍《氏族典》第十一卷记载,黄帝第五代骆明生伯鲧,伯鲧生禹;禹建夏王朝,娶涂山氏,生子二人:长子启,次子均。
启为继夏帝世系者。次子均生固,固生伎来,伎来生循鞈。在伎来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来氏,世代相传至今。
扩展资料:
来姓的字辈排行
济南市西郊大饮马庄来氏一脉,有族谱记载的已有九世。为家族延续,行辈有序,且同莒县族谱保持一致,从第十世起,为顺、继、恒、恩、久、传、诗、圣、美、新、科、育、高、才、子、彦、建、洪、业、春、晖、敬、星、群,
一九九三年五月续定的勤、文、树、振、清、继、金、耀、昌、泽十字取消。望族人切记以上二十四字顺序,为子孙取名,以防伦乱之误。
安徽阜阳市颍泉区伍明镇来氏字辈:“天立金振永洪文继” ,天字辈之前的不详,继字辈之后的有个立字辈的私塾老先生曾经排过一次:“继启明升大兆”,但是未得到推广与应用,继“继字辈”之后已经有两代人了,取名都没有遵循辈份。
-来姓
自古以来,行政性收费一直都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行政性收费起初就带有税收的性质,实质上是税收的一种补充,但由于缺乏规范和有效的监督,乱收费、滥收费现象便相伴而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痼疾。乱收费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农民不堪重负,逃亡奔命,造成国家失去大量纳税户,田赋收入也随之减少;国家财力分散,分配秩序紊乱,终致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削弱中央集权,助长地方势力膨胀。正因为乱收费、滥收费危害重重,所以历代统治者对此都极为重视。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也出现过三次比较著名的税费改革运动——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地。这三次税费改革在历史上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着的农村税费改革也很有借鉴意义。所谓“以史为鉴”,将历史上三次税费改革的经验,与当前农村税费改革进行参照对比,对于我们了解现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能否成功,或者怎样才能成功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
一、历史上的三次税费改革
(一)唐代中后期杨炎推行的两税法
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适即位,以杨炎为宰相。杨炎面临着土地兼并严重,吏治败坏,农民负担沉重,国家财政面临危机等情况,因而上书请作“两税法”。唐德宗采用了杨炎的建议,在全国推行两税法,首开了中国费改税之先河。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包括:(1)“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就是以户为片收单位,不论主户、客户,一律在当时居住的地区登记,编入户籍。按各户土地财产的多少确定应纳税额,这是户税;以公元799年垦田数字为依据,按田亩多少征收田亩税,这是地税。商人是流动的,没有常居地,所在州县纳其财货三十分之一的税。(2)“人无中丁,以贫富为差。”即是不分丁男,中男,都要按拥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来纳税。(3)“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每年的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4)“量出以制入”。杨炎在制定两税法时,明确地规定实行“量出为入”原则,即先预算出国家财政支出的数额,然后量出制入,确定出国家财政收入总额。意在限制滥征苛敛,减轻人民的负担。
两税法归并了税目,把混乱繁杂的税种规并为户税和地税两种,集中了时间,一年分为夏秋两次;收费全部改为正税,一同并入两税之中。两税法改革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它改变了过去“科敛之名数百”和百姓“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中央统一控制了税费征收大权,强化了中央财政的集中性和控制力,抑制了地方为所欲为的收费行为。
(二)明代中后期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
明代中后期官府的暴敛、豪强的兼并,已使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激发,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神宗万历初年,张居正为首辅,全面整顿军事、政治和经济,在财政上实行一条鞭法。
明代的“一条鞭法”是继唐代“两税法”实施八百年后又一次较大的税费改革。“一条鞭法”把各种徭役、田赋和各种杂费,并为田赋一种,以田亩为对象,一次征收。并将扰民最重的役并入田赋之中,征课的田赋一律折合成银两交纳。另外,税费统一改为交银后,不再由地方的“里长”、“粮长”办理征税管理,而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后解缴国库。“一条鞭法”改革化繁为简、税费合一,达到了统一税制、省费便民、稳定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增加了明朝的中央财政收入,出现了“太仓所储,足支八年;公私积储,颇有盈余”的状况,加强了中央财政的集中统一,限制了地方政府越权收费和地方官吏强取豪夺的腐败行为。
(三)清朝前期康熙雍正推行的摊丁入地
明末一条鞭法夭折之后,豪绅富家凭借特权逃避编丁,土地兼并加剧,无地农民苦于丁银负担,大量逃亡。于是一些地方进行了丁银均入田赋中征收的税制改革,称之为“随粮代丁”、“丁随田办”。公元1721年,清政府宣布“添丁不加银”,这就为“摊丁入地”的实施提供了政策保证。康熙五十五年,清政府首先大广东省试行丁银摊入地亩征收。至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已经开始大规模推广,“摊丁入亩”改变了过去地丁并行的税制,简化了征税手续,放松了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尽管田赋重了,但免去了人头税。这对无地贫民而言,无疑是带来了一丝福音。“摊丁入亩”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到雍正末年,国库存银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加到六千多万两。
二、历史上三次税费改革的经验教训
历史上的三次税费改革既规范了收费管理,扩大了税基,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加强了中央财权的集中统一,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政府越权收费和地方官吏巧立名目、强取豪夺的腐败行为,有利于整顿吏治。然而,这三次税费改革由于皇权社会政治经济的局限性和改革措施本身的一些不科学和不完善,最终都未能解决好乱收费、滥收费问题。
历史上有许多的学者针对这一现象进行过研究,比较典型的理论有“黄宗羲定律”。黄宗羲是明末的思想家,有“启蒙思想家”之称。他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讲,历史上的田赋有“积累莫返之害”。即赋税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将杂征变为正税,以后又出现新的杂征。这样下去税负就不断加重了。他举例说:两税法并庸调于租,但宋代在两税之外又征了丁身钱。明中期一条鞭法已将各种杂税归并,但后来又有杂役、旧饷、新饷、练饷。明末户部尚书倪元璐将三饷合并,又成为固定的税收。“黄宗羲定律”反映了历史上赋税不断加重的客观实际,它的进步意义是揭示了历史上的统治阶级贪得无厌、诛求无已,希望统治者不要横征暴敛。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封建统治下三次税费改革的失败之处,“黄宗羲定律”实际上成了专制王朝时代进行税费改革的一个怪圈。
历史上的三次税费改革从短期来看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清理整顿了吏治。但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三次税费改革中没有一次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好乱收费、滥收费问题。三次税费改革大多只是昙花一现,人亡政息。笔者认为,历史上的三次税费改革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1、历史上的三次税费改革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需要,并不是要真正地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历史上三次税费改革,毕竟都是地主阶级的政策,有其阶级的局限性和欺骗性。他们实行税费改革,并不是发自内心地要为人民减轻负担,更多地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增加财政收入。当税费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阶级矛盾得到缓和时,他们的贪欲又暴露无疑,苛捐杂税死灰复燃也是自然的事情。
2、历史上三次税费改革带有很强的“人治”色彩,改革没有形成制度化。历史上三次税费改革在短时间里能迅速得以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当朝皇帝强悍的作风和专断独行的权力,改革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制度上去。一旦皇权出现更替,改革就很有可能随之夭折。
3、历史上三次税费改革措施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无论是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还是清朝的摊丁入地,其改革措施的本身都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唐代两税法规定征税时以货币计税,但在唐德宗时,征税时又要人民折成实物交纳,但在折合过程中,人民的负担又有所加重。明代一条鞭法将各种随田起征的赋役合并征收,手续固然简便,但纳税人无从确切知道所纳何税,致使贪官污吏得以随意摊派增减,弊病百端。清朝摊丁入地在征银时增征“耗羡”等,更是额外的剥削。
赋圣司马相如曾以《子虚》《上林》《大人》三篇赋作而三度震惊“汉主”,又以《长门赋》复得“千金”之重,以《哀秦二世赋》讽“秦政”以喻“汉政”,皆闻名赋坛,至于其《美人赋》一篇,属意为何,颇有疑义,且成一流传久远的公案。据葛洪《西京杂记》卷二记载:
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
将“美人”落实为卓文君,赋意为“自刺”,缘由在相如患“消渴疾”(糖尿病)。因《美人赋》不载汉代史书,《文选》未收,赋文初见唐人类书《艺文类聚》与《初学记》,收载北宋发现之《古文苑》,故作者真伪在龙蛇间。然学界亦多考实之论,如简宗梧先生《〈美人赋〉辨证》(收录于《汉赋史论》)从音韵学考述其为西汉之文法,即为一例。当然,对《西京杂记》所载相如为此赋的动机,简文也不以为然,可是相如之“病”,却于史书有证。
有关相如“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有五处记述,其一,“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其二,“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其三,“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其四,“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其五,“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可见“称病”“病免”乃至“病死”,“病”成了书写相如人生的常用词,而最后一则“家居茂陵”,指相如“拜为孝文园令”后的经历,因此相如病在后世也就习称“文园病”。如“我惭衰病似文园”(陈镒《次友人见寄》)、“我抱文园渴”(边贡《答罗兖州》)、“一自文园移疾后,遂令玄草出人间”(徐中行《哭梁公实》)、“仆抱文园之疾”(张居正《与吴川楼给谏》)等,皆以“文园病”自拟与自嘲。最有意思的是徐珂《清稗类钞》记载洪钧贪恋美色而死的趣事,几乎是《西京杂记》所述的翻版:
有傅彩云者,久著艳名,一曰曹梦兰,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沪。吴县洪文卿侍郎钧初得大魁,衔恤归,一见悦之,以重金置为室,待年于外。祥琴始调,金屋斯启,携至都下,宠以专房。文卿持节使英,万里鲸天,鸳鸯并载……俄而文园消渴,竟夭天年。
相如贪“文君”之色而“亡”,洪钧贪“彩云”(或“梦兰”)之色而“亡”,况且“祥琴始调”,也是摹写相如“琴挑文君”故事。所不同者在于相如留下了文案,就是《美人赋》。
这篇署名相如的《美人赋》究竟与“文园病”有否关联,还是应阅读该赋的文本。今存赋文大体可分为两节,赋首“司马相如美丽闲都”到“臣弃而不许”为前节,主要是相如对梁王辩解自己“不好色”的缘起,并以东邻之女“望臣三年”“臣弃而不许”事情加以说明;从“命驾东来,途经郑卫”到赋末为后节,通过主人公在“上宫闲馆”经历“美人”挑逗而坚拒的叙述,得出“不好色”的结论。仅此,就有两点与《西京杂记》所述不符:一是该赋书写“客游梁”之事,故有答“梁王问”,而相如“琴挑文君”史事在“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之后,二是全赋写“不好色”,与好色“自刺”内涵不符。当然,赋家可以假托为词,交错时空,以致有戴仲纶之惊呼“长卿长卿,据尔所言,鲁男子不啻也。其在卓氏前邪,后邪?由前则行不掩言,由后则言不顾行”(邓伯羔《艺彀》卷上),然勘进于赋旨,宜观赋中最重要的一段描写:
途出郑卫,道由桑中,朝发溱洧,暮宿上官。……臣排其户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黼帐高张。有女独处,婉然在床。奇葩逸丽,淑质艳光。睹臣迁延,微笑而言……玉钗挂臣冠,罗袖拂臣衣……于是寝具既设……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亵衣,皓体呈露,弱骨丰肌,时来亲臣,柔滑如脂。臣乃脉定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
这是假托赋者对“梁王问”的话语,所叙自投“艳网”,又“高举”“长辞”,这种既非人性,又不合逻辑的自述之词,实则是对前人诗赋创作的摹写与夸饰而已。
如果追溯此赋渊承,前人多谓取法宋玉《讽赋》与《登徒子好色赋》,论其“好色”旨意,其创作更近于后者。宋玉《好色赋》收载《文选》,赋中不仅如写宋玉“体貌闲丽”及叙事谓“东家之子”“登墙窥臣三年”的模式完全为《美人赋》取法,而且前引《美人赋》一段描写,书写思想及方式也完全等同《好色赋》中“章华大夫”的言说:
臣……从容郑卫溱洧之间。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仓庚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臣观其丽者……于是处子恍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复称诗曰……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
尽管比较而言,《美人赋》而临 写得更暴露些,然其所述男女遇合的发生地“桑中”与“上宫”源自《诗·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与《登徒子好色赋》的“郑卫溱洧”属同一区域。而对“桑中”“溱洧”诗的名义,毛诗序一谓“刺奔”,一谓“刺乱”,皆与以“郑风”为代表的情诗相关。于是再拓展来看宋玉《高唐》与《神女》两赋“云梦”情事及人神遇合的描写,诚如《墨子·明鬼》所谓“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就是闻一多《高唐神女传统之分析》考证的祭祀生育女神的圣地。
对此“桑林”文学传统,可观三篇考述文字:一是清人惠士奇《惠氏春秋说》卷八引述《墨子》说阐释云:“盖燕祖齐社,国之男女皆聚族而往观,与楚、宋之云梦、桑林同为一时之盛,犹郑之三月上巳士与女合会于溱洧之濒观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志在女”说,意味深远。二是近人陈梦家《高禖郊社祖庙通考》依据《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女,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会不禁”、《礼记·月令》“仲春之月”“祠于高禖”的记述,论证祭祀媒神以及与“祈雨”求嗣的关系。三是法国汉学家桀溺《牧女与蚕娘》一文梳理从郑卫“桑间”之词到汉乐府古辞《艳歌罗敷行》以及晋唐以降的众多拟作,得出桑园文学主题有“两种形式,即自发产生于春祭活动中的情歌和道德裁判家的谴责,可以说是这一主题发展的两个极端”的结论(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正因为“志在女”所显示的“奔会不禁”的情之原欲,以及与以孔子为代表之道德家批评“郑声*”的礼教精神,构成了后世仿效“春祭”遗俗之作品的内在矛盾,形成某种欲说还休,或戛然而止的写作特征。《美人赋》的“女”之情态与“臣”之高举,既荒悖,又滑稽,但却合理地表现了“两个极端”的有机统一。所以在该赋之前,有“高唐”“好色”诸赋,之后诚如王楙《野客丛书》卷十六所列“蔡邕又拟之为《协和赋》、曹植为《静思赋》、陈琳为《止欲赋》、王粲为《闲邪赋》、应玚为《正情赋》、张华为《永怀赋》、江淹为《丽色赋》、沈约为《丽人赋》,转转规仿”,加之张衡《定情赋》、蔡邕《检逸赋》与陶潜《闲情赋》之同类作品,写作宗旨无非是“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闲情赋序》)。缘此创作传统,某年我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邀约作学术演讲,拟题“诗赋创作与乐教传统”,意从“桑中”诗说起,邀约方得题后以为太朴素,恐不能吸引听众,于是我将其讲题改为“祭坛情歌”,内容不变,立即获允。又某年某学术会议,我将此讲稿增饰成论文宣讲,开场言及当时改题事,对座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插言:此题若改作“相爱在公元前”更好。当年笑谈,余音在耳,试想那遥远的相爱,如何发展成原欲的抗拒,《美人赋》作为桑园文学传统中的一篇(或一发展阶段),乃模拟之文,非新创之篇,固然与耽色“自刺”说不伦类,然其中是否确有“病”症?
回到《西京杂记》的“自刺”说,记述者以为相如刺而未休,以致于死,于是“文君为诔”。考文君《司马相如诔》初见明人梅鼎祚编的《西汉文纪》,作者难为信谳,诔文中写道“忆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怜才仰德兮,琴心自娱;永托为妃兮,不耻当炉;生平浅促兮,命也难扶”。文字杂取于《史记》本传及《玉台新咏》中的《琴歌》,然“雍容孔都”与“怜才仰德”两句,或可折射出《美人赋》中的“文园病”。考《史记》本传所述相如五次“病”例,关乎人生行为和情感者主要有二,一则“因病免,客游梁”,导源其因,在相如不满意当时的工作,即传中所谓“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这是相如一生的心病,或谓“士不遇”情怀,也是古代文人的通病。如果说体现于《美人赋》中,则如其间“女乃歌曰”所唱的歌词:“独处室兮廓无依,思佳人兮情伤悲。有美人兮来何迟?日既暮兮华色衰,敢托身兮长自私。”这种怀才不遇的心病,在相如被委派作“孝文园令”尤为明显,他的《大人赋》与《长门赋》中也无不包含了这种心态的书写与隐喻。二则“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其“病”在有良知的文士不能与俗浮沉的幽兰白雪的情怀,以及与世道龃龉的冷落与悲凉,这是汉赋家对屈原辞赋中“宁昂昂若千里驹”“宁与骐骥亢轭”“宁与黄鹄比翼”而不“与鸡鹜争食”(《卜居》)之精神的传递,在《美人赋》中则体现于对相如“美丽闲都”的形容,与赋者“鳏处独居”“莫与为娱”的自怜或自诩,所谓“韩囚而马轻”(《文心雕龙·知音》),堪称其“自洁”与“不遇”的一体化的写照。
读《美人赋》,倘着相于“好色”,则如吴子良所说“宋玉《讽赋》……大略与《登徒子好色赋》相类,然二赋盖设辞以讽楚王耳。司马相如拟《讽赋》而作《美人赋》,亦谓臣不好色,则人知其为诬也”(《荆溪林下偶谈》卷三),若不限于“好色”与否,又如诸论家将此赋归于宋玉《讽赋》旨趣,而另有深意在。近人金秬香认为:“是赋首言臣非好色之徒,及慕义东来之故;中乃用宋玉《讽赋》之意,抚《幽兰》《白雪》之曲,摹玉床横陈之词,其词丽以*;末言‘臣乃气服于内……’谐戏中又说得极庄雅。……太史公《相如传赞》曰:‘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旨哉斯言。”(《汉代词赋之发达》第九章《汉代词赋之种类·抒情类》)如此评说,或得正解。只是赋中寄“讽”,为何要以男女为喻,或许人云“万恶*为首”(《增广贤文》)?抑或孔子所言“吾未闻好德如好色”(《论语·子罕》)吧。当然,“桑林”文学的摹写所形成的传统力量并导致的赋文模式化,这也算是赋坛一“病”,然在 与乐教之间所渗透的作者怀抱,却不乏新义而可供寻绎、玩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本文2023-08-06 11:09:28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308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