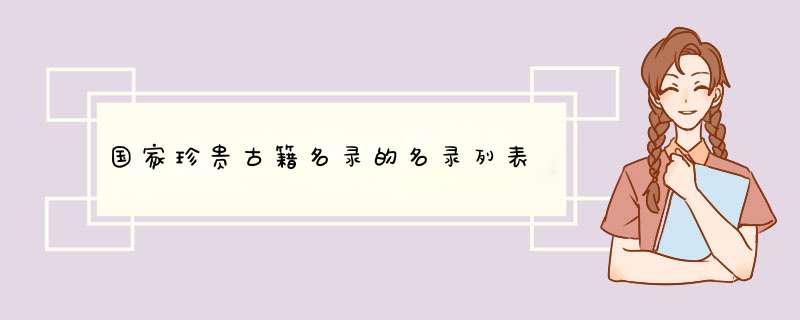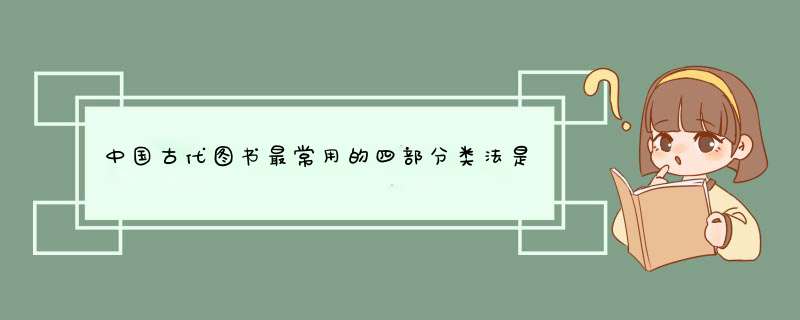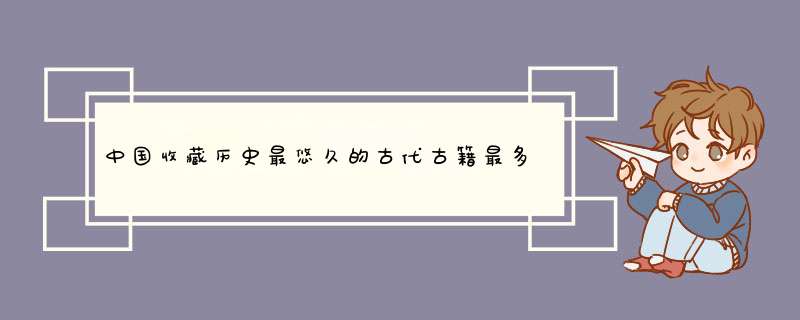如何评判古籍善本的价值?

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投资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评判古籍善本价值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 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二、各种古籍善本的市场价格
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三、古籍善本的几种作伪手法。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它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将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二类是用“旧纸新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张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留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收藏者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籍,并可请专家一起鉴定,应注意去伪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购古籍物有所值。
送綦毋潜落第还乡
[唐]王维
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
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
既至金门远,孰云吾道非。
江淮度寒食,京洛缝春衣。
置酒长安道,同心与我违。
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
远树带行客,孤城当落晖。
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
关于“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
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曰:“第三段四句,是写送行和还乡,是说饯别之后,我不久也将乘船去访问你,足见两人交情的真挚。”(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按:此二句语意,紧承上句“同心与我违”,主语明显是“同心”,即心心相印的朋友,指綦毋潜。因此,它是说綦毋潜就要乘船还乡,不久便可到家,而不是说“我不久也将乘船去访问你”。綦毋潜的家乡在荆南,而王维是河东人,此时在京城长安。荆南在今湖北;河东在今山西,长安在今陕西,与荆南均相距甚远。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诗人一般不会轻易地作出这样的承诺。
唐王昌龄《别刘谞》诗曰:“天地寒更雨,苍茫楚城阴。一尊广陵酒,十载衡阳心。倚仗不可料,悲欢岂易寻。相逢成远别,后会何如今。身在江海上,云连京国深。行当务功业,策马何骎骎。”刘长卿《送王端公入奏上都》诗曰:“旧国无家访,临歧亦羡归。途经百战后,客过二陵稀。秋草通征骑,寒城背落晖。行当蒙顾问,吴楚岁频饥。”高适《河西送李十七》诗曰:“边城多远别,此去莫徒然。问礼知才子,登科及少年。出门看落日,驱马向秋天。高价人争重,行当早著鞭。”韩翃《送李司直赴江西使幕》诗曰:“敛版辞汉廷,进帆归楚幕。三江城上转,九里人家泊。好酒近宜城,能诗谢康乐。雨晴西山树,日出南昌郭。竹露点衣巾,湖烟湿扃钥。主人苍玉佩,后骑黄金络。高视领八州,相期同一鹗。行当报知己,从此飞寥廓。”李益《送常曾侍御使西蕃寄题西川》诗曰:“凉王宫殿尽,芜没陇云西。今日闻君使,雄心逐鼓鼙。行当收汉垒,直可取蒲泥。旧国无由到,烦君下马题。”李端《送宋校书赴宣州幕》诗曰:“浮舟压芳草,容裔逐江春。远避看书吏,行当入幕宾。夜潮冲老树,晓雨破轻。鸳鹭多伤别,栾家德在人。”孟郊《送淡公》诗十二首其二曰:“坐爱青草上,意含沧海滨。渺渺独见水,悠悠不问人。镜浪洗手绿,剡花入心春。虽然防外触,无奈饶衣新。行当译文字,慰此吟殷勤。”张籍《送郑秀才归宁》诗曰:“桂楫彩为衣,行当令节归。夕潮迷浦远,昼雨见人稀。野芰到时熟,江鸥泊处飞。离琴一奏罢,山雨霭馀晖。”皆送别之作,而诗中“行当”云云,皆叙被送者将如何如何,其例正同,可以参看。
宿建德江
[唐]孟浩然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关于“江清月近人”
刘永济先生《唐人绝句精华》曰:“第三句写远景,野旷则似天低于树。第四句写近景,江清则觉月近于人。合观之有辽阔凄寂之感,所谓‘客愁新’也。诗家有情在景中之说,此诗是也。不可但赏其写景之工,而不见其客愁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
按:此句中的“月”,当指月亮在江中的倒影。月影在水,客船也在水,所以说“月近人”。此句在全诗中的作用,恐非加倍渲染“客愁”,而是适度消减“客愁”:有“月”与诗人相亲近,其孤寂的感觉便不至于太浓重。从章法上来看,“日暮客愁新”句一推,此句一挽,乃有收放自如之妙;若“日暮客愁新”句一推,此句又一推,放而不收,似略嫌平直。
春望
[唐]杜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关于“烽火连三月”
宋赵次公注曰:“考此诗作于天宝十五载之正月。盖禄山反于十四载之十一月,至是则烽火连三月。”(宋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卷一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九曰:“考是诗作于天宝十五载正月之末。盖安禄山反于十四载之十一月,至是则烽火连三月矣。”(《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70页)
宋黄鹤注曰:“天宝十五载正月,明皇未幸蜀,方且命嗣吴王只季随李光弼等讨安禄山,安得谓之‘国破’?是时公携家在奉先,五月方入鄜,道路未绝,书非难达。赵注以十四载之十一月至次年正月为三月,失于不考。当是至德二载三月陷贼营时作,‘三月’者,直指三月而云。”(宋黄希原本、黄鹤补注《补注杜诗》卷一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三之一曰:“自禄山祸起,至此已一年馀。鹤(按:黄鹤)说良是,但如此则不成句法矣。考史,上年之春,潼关虽未破,而寇警不绝。此云‘连三月’者,谓连逢两个三月。诗作于季春,故云然耳。”(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册,第363页)
萧涤非《杜甫诗选注》曰:“这是至德二载(七五七)三月所作。……三月,指季春三月。连三月,连逢两个三月,是说从去年一直打到现在的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2—73页)
按:尽管赵次公、蔡梦弼等对杜甫此诗系年有误,但他们以“连三月”为连续三个月的理解,却没有错。《杜诗言志》及俞陛云《诗境浅说》亦持此见,可谓有识。“连数月”这样的用法,在唐人文集里也有例证,如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按:牛僧孺)墓志铭》曰:“敬宗即位,与武士畋宴无时,征天下道士言长生事。公亟谏曰:‘陛下不读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静养生。彼道士皆庸人,徒夸欺虚荒,岂足师法!’未一岁,请退,不许。连四月日间以疾辞,乃以鄂、岳六州建节号武昌军,命公为礼部尚书、平章事,为节度使。”此“连四月日”,明显是说连续四个多月。又,宋李弥逊《与似表弟游石门怀蹈元时中用高字韵》诗曰:“病来避酒连三月,春半寻山等一遭。”曾几《郡中迎怀玉山应真请雨得之未沾足》诗曰:“悯雨连三月,为霖抵万金。”陈渊《答李光祖书》曰:“渊入台已四月馀,日日益多事,几无顷刻之暇。以连三月宿斋,故得尽答亲知之书。”周紫芝《次韵远猷东池晚思》诗曰:“多事冯公子,含情不奈秋。……烽尚连三月,诗应拟《四愁》。”洪适《祭南海庙文》曰:“章贡叛黥婴城连三月矣,生齿何辜,沦胥涂炭!”范成大《秋雷叹》诗曰:“向来夏旱连三月,吁嗟上诉声满屋。”吴泳《小雪》诗曰:“卧病连三月,起来几半人。”刘黻《旱》诗曰:“一雨连三月,当秋乃亢晴。”释文珦《苦雨》诗曰:“秋雨连三月,愁吟野水。”俞德邻《病中谢亲友》诗四首其四曰:“一病连三月,肥甘宁得知?”凡此“连三月”,也都是说连续三个月。宋世去唐未远,语言习惯当无大的改变。在唐代语言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宋代语言资料的参考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黄鹤关于杜甫此诗系年的考辨,或许近是。但他以“三月”为具体月份的说法,却不能成立。浦起龙、萧涤非先生说“连三月”是“连逢两个三月”,错得更为离奇。只要对照笔者上文所举诸多书证,黄、浦、萧诸说之误,便可一目了然。
自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发生,到肃宗至德二载(757)春,已一年多。天宝十五载(756)六月,玄宗仓皇奔蜀,安史叛军占领长安。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杜甫闻讯,将家小安顿在鄜州,只身赴灵武欲投肃宗,中途被叛军俘获,押往长安。自此到至德二载春,也已半年多。因此,我们对他这首诗中的“三月”,不应坐得太实。作“好几个月”来理解,似较圆通。因为这是一首五言律诗,囿于格律,“月”字前面的那个数字,必须用平声字。而从一到十的十个数字中,只有“三”字是平声,故诗人不可能有其他选择。
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
[唐]白居易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
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
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
关于“一篇长恨有风情”
王汝弼先生《白居易选集》注曰:“风情,风人(诗人)之情。《诗集传》:‘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白氏自认其诗有风人之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按:“风情”是古代诗歌中的常用词,义项虽不止一端,却偏偏没有“风人之情”“风人之旨”的意思。考察白居易同时代人的诗歌,权德舆《奉和许阁老酬淮南崔十七端公见寄》诗曰:“芳讯风情在,佳期岁序徂。”刘禹锡《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诗曰:“眼前名利同春梦,醉里风情敌少年。”姚合《寄送卢拱秘书游魏州》诗曰:“蓟门春不艳,淇水暖还清。看野风情远,寻花酒病成。”凡此“风情”,或曰“芳讯”“佳期”,或曰“醉里”“少年”,或曰“看野”“寻花”,似皆谓风流或风雅情致。而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中,“风情”一词凡十五见。除本篇外,卷一七《蔷薇正开春酒初熟因招刘十九张大夫崔二十四同饮》诗曰:“瓮头竹叶经春熟,阶底蔷薇入夏开。似火浅深红压架,如饧气味绿粘台。试将诗句相招去,倘有风情或可来。明日早花应更好,心期同醉卯时杯。”又《湖亭与行简宿》诗曰:“浔阳少有风情客,招宿湖亭尽却回。水槛虚凉风月好,夜深谁共阿怜来?”又《三月三日怀微之》诗曰:“良时光景长虚掷,壮岁风情已暗销。忽忆同为校书日,每年同醉是今朝。”又《题峡中石上》诗曰:“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于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又卷二〇《湖上招客送春泛舟》诗曰:“欲送残春招酒伴,客中谁最有风情?两瓶箬下新开得,一曲《霓裳》初教成。排比管弦行翠袖,指麾船舫点红旌。慢牵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镜上行。”又卷二四《奉和汴州令狐令公二十二韵》诗曰:“眷爱人人遍,风情事事兼。犹嫌客不醉,同赋夜厌厌。”又《题笼鹤》诗曰:“经旬不饮酒,逾月未闻歌。岂是风情少?其如尘事多。”又《酬刘和州戏赠》诗曰:“钱塘山水接苏台,两地褰帷愧不才。政事素无争学得?风情旧有且将来。双蛾解佩啼相送,五马鸣珂笑却回。不似刘郎无景行,长抛春恨在天台。”又卷二六《忆梦得》诗曰:“齿发各蹉跎,疏慵与病和。爱花心在否,见酒兴如何?年长风情少,官高俗虑多。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又卷二七《想东游五十韵》诗曰:“驿舫妆青雀,官槽秣紫骝。镜湖期远泛,禹穴约冥搜。预扫题诗壁,先开望海楼。饮思亲履舄,宿忆并衾裯。志气吾衰也,风情子在不?”又卷二八《座中戏呈诸少年》诗曰:“衰容禁得无多酒,秋鬓新添几许霜。纵有风情应淡薄,假如老健莫夸张。兴来吟咏从成癖,饮后酣歌少放狂。不为倚官兼挟势,因何入得少年场?” 又卷三一《侍中晋公欲到东洛先蒙书问期宿龙门思往感今辄献长句》诗曰:“功成名遂来虽久,云卧山游去未迟。闻说风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时。”又卷三四《酬梦得以予五月长斋延僧徒绝宾友见戏十韵》诗曰:“禅后心弥寂,斋来体更轻。不唯忘肉味,兼拟灭风情。”又卷三五《梦得前所酬篇有炼尽美少年之句因思往事兼咏今怀重以长句答之》诗曰:“昔饶春桂长先折,今伴寒松取后凋。生事纵贫犹可过,风情虽老未全销。”又卷三七《寄黔州马常侍》诗曰:“闲看双节信为贵,乐饮一杯谁与同?可惜风情与心力,五年抛掷在黔中。”所谓“风情”,亦多以饮酒赏花、游山宿水、听歌观舞、题壁赋诗等为言,仍指风流或风雅情致。 据此类推,则 “一篇《长恨》有风情”云云,也应是诗人自负其名篇《长恨歌》甚有风流情致。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人物志》曰:“轻诺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无效,进锐似精而去速,诃者似察而事烦,诈施似惠而无终,面从似忠而退违。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有大权似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内明,博爱似虚而实厚,正言似讦而情忠。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得其实也?”)
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知于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长,音竹两反。),有顺懁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焊(音汗)。”
太公曰:“士有严而不肖者,有温良而为盗者,有外貌恭敬、中心欺慢者,有精精而无情者,有威威而无成者,有如敢断而不能断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有倭倭迤迤而有效者,有貌勇狠而内怯者,有梦梦而反易人者。无使不至,无使不遂,天下所贱,圣人所贵,凡人莫知,惟有大明,乃见其际。”此士之外貌而不与中情相应者也。
(桓范曰:“夫贤愚之异,使若葵之与苋,何得不知其然?若其莠之似禾,类是而非是,类贤而非贤。”扬子《法言》曰:“或问难知曰:‘太山之与蚁蛭,江河之与行潦,非难也。大圣与大佞,难也!于乎!唯能别似者,为无难矣!’”)
知此士者而有术焉。微察问之,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谋,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远使以财,以观其廉(又曰:委之以财,以观其仁;临之以利,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又曰:悦之以色,以观其不。);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又曰:告之以危,而观其勇。又曰:惧之,以验其特。);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又曰:醉之以酒,而观其则。又曰:醉之以酒,观其不失。)。
《庄子》曰:“远使之,而观其忠(又曰:远使之,以观其不二。);近使之,而观其敬(又曰:近之以昵,观其不狎。);烦使之,而观其能(又曰:烦之以事,以观其理。);卒然问焉,而观其智(又曰:设之以谋,以观其智。太公曰:事之而不穷者,谋。);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太公曰:使之而不隐者,谓信也。);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又曰:纵之以视,观其无变。)。”
《吕氏春秋》曰:“通,则观其所礼(通,达也。);贵,则观其所进(又曰:达,视其所举也。);富,则观其所养(又曰:富,视其所与。又曰:见富贵人,观其有礼施。太公曰:富之而不犯骄逸者,谓仁也。);听,则观其所行(行则行仁);近,则观其所好(又曰:居,视其所亲。又曰:省其居处,观其贞良;省其交游,观其志比。);习,则观其所言(好则好义,言则言道。);穷,则观其所不爱(又曰:穷,则视其所不为非。又曰:贫,视其所不取。);贱,则观其所不为(又曰:贫贱人,观其有德守也。)。喜之,以验其守(守,慎守也。又曰:喜之,以观其轻。);乐之,以验其僻(僻,邪僻也。又曰:娱之以乐,以观其俭。);怒之,以验其节(节,性也。又曰:怒之仇,以观其不怨也。);哀之,以验其仁(仁人,见可哀者则哀。);苦之,以验其志(又曰:检之,以观其能安。)。”
《经》曰:“任宠之人,观其不骄奢(太公曰:贵之,而不骄奢者,义也。);疏废之人,观其不背越;荣显之人,观其不矜夸;隐约之人,观其不慑惧;少者,观其恭敬好学而能悌(《人物志》曰:“夫幼智之人,在于童[齿乙],皆有端绪。故文本辞繁,辩始给口,仁出慈恤,施发过与,慎生畏惧,廉起不取者也。”);壮者,观其廉絜务行而胜其私;老者,观其思慎,强其所不足而不逾。父子之间,观其慈孝;兄弟之间,观其和友;乡党之间,观其信义;君臣之间,观其忠惠(太公曰:付之而不转者,忠也。)。”此之谓观诚。
(傅子曰:“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设所修出于为道者,则言自然而贵玄虚;所修出于为儒者,则言分制而贵公正;所修出于为纵横者,则言权宜而贵变常。九家殊务,各有所长,非所谓难。所谓难者,以默者观其行,以语者观其辞,以出者观其治,以处者观其学。四德或异,所观有微,又非所谓难也。所谓难者,典说诡合,转应无穷,辱而言高,贪而言廉,贼而言仁,怯而言勇,诈而言信,而言贞。能设似而乱真,多端以疑暗。此凡人之所常惑,明主之所甚疾也。君子内洗其心,以虚受人,立不易方,贞观之道也。九流有主,贞一之道也。内贞观而外贞一,则执伪者无地而逃矣。夫空言易设,但责其实事之效,则是非之验立可见也。”
故韩子曰:“人皆寐,盲者不知;人皆默,喑者不识。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穷矣。发齿吻,视毛色,虽良、乐不能必马;连车蹴驾,试之行途,则臧获定其驽良。观青黄,察锻销,虽欧冶不能必剑;陆断狗马,水截蛟龙,虽愚者识其利钝矣。是知明试责实,乃圣功也。”)
《人物志》曰(凡有血气者,莫不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着形。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也。):“骨植而柔立者,谓之宏毅。宏毅也者,仁之质也(木则垂阴,为仁之质。质不宏毅,不能成仁。)。
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火则照察,为礼之本。本无文理,不能成礼。)。
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为信之基。基不贞固,不能成信也。)。
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金能断割,为义之决。决不勇敢,不能成义也。)。
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达,为智之原。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
故曰:直而不柔则木(木强侥讦,失其正色。),劲而不精则力(负鼎绝髌,失其正劲。),固而不端则愚(专己自是,陷于愚戆。),气而不清则越(辞不清顺,发越无成。),畅而不平则荡(好智无涯,荡然失绝。)。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神者,质之主也。故神平则质平,神陂则质陂也。),明暗之实在于精(精者,实之本。精清则实明,精浊则实暗。),勇怯之势在于筋(筋者,势之用也。故筋劲则势勇,筋弱则势怯。),强弱之植在于骨(骨者,植之机。故骨粗则植强,骨细则植弱。),躁静之决在于气(气者,决之地也。气盛,决于躁;气冲,决于静。),惨怿之情在于色(色者,情之候。故色悴由情惨,色悦由情怿也。),衰正之形在于仪(仪者,形之表。故仪衰由形殆,仪正由形肃。),态度之动在于容(容者,动之符。故哀动则容哀,态正则容度也。),缓急之状在于言(言者,心之状。故心恕则言缓,心偏则言急也。)。
若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崇容直,则纯粹之德也。”
夫人有气。气也者,谓诚在其中,必见诸外。故心气粗讼者,其声沉散;心气详慎者,其声和节;心气鄙戾者,其声粗犷;心气宽柔者,其声温润。信气中易,义气时舒,和气简略,勇气壮立。此之谓听气。
(以其声,处其实。气生物,物生有声。声有刚柔清浊,咸发乎声。听其声,察其气,考其所为,皆可知矣。)
又有察色。察色,谓心气内蓄,皆可以色取之。夫诚智,必有难尽之色(又曰:诚智,必有明达之色。);诚仁,必有可尊之色(又曰: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难慑之色(又曰:诚勇,必有矜奋之色也);诚忠,必有可观之色;诚絜,必有难污之色;诚贞,必有可信之色。质色浩然固以安,伪色曼然乱以烦。此之谓察色。
(《人物志》曰:“夫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仁目之精,悫然以端;勇胆之精,晔然以强。夫忧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疢之色,乱而垢理;喜色,愉然以怿;愠色,厉然以扬;妒惑之色,冒昧无常。是故其言甚怿而精色不从者,中有违也;其言有违而精色可信者,辞不敏也;言未发而怒色先见者,意愤溢也;言已发而怒气送之者,强所不然也。”凡此之类,虽欲违之,精色不从,威愕以明,虽变可知也。)
又有考志。考志者,谓方与之言,以察其志。其气宽以柔,其色检而不谄,其礼先人,其言后人,每自见其所不足者,是益人也。若好临人以色、高人以气、胜人以言,防其所不足,而废其所不能者,是损人也。(太公曰:“博文辩辞,高行论议,而非时俗,此人也。王者慎勿宠之也。”)
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饰其美、不隐其恶、不防其过者,是质人也。(又曰:与之不为喜,夺之不为怒,沉静而寡言,多信而寡貌者,是质静人也。议曰:太公曰:“朴其身头,恶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得,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之。夫质人之中有如此之伪者也。”)
若其貌曲媚,其言谀巧,饰其见物,务其小证,以故自说者,是无质人也。(议曰:晏子云:“谗夫佞人之在君侧,材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诚于中者,必谨小诚于外,以成其大不诚。此难得而知也。荀悦曰:“察人情术,观其言行,未必合道,而悦于己者,必佞人也;观其言行,未必悦己而合于道者,必正人也。”此察人之情之一端也。)
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烦乱以事而志不惑,深导以利而心不移,临慑以威而气不卑者,是平心固守人也。(又曰:荣之以物而不娱,犯之以卒而不惧,置义而不迁,临货而不回者,是果正人也。议曰:孔子称:“取人之法,无取健。健,贪也。夫健之弊有如此者矣。”)
若喜怒以物而心变易,乱之以事而志不治,示之以利而心迁动,慑之以威而气恇惧者,是鄙心而假气人也。(又曰:若格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诺而不决者,是情弱之人也。)
设之以物而数决,惊之以卒而屡应,不文而慧者,是有智思之人。(议曰:太公云:“有名而无实,出入异言,扬美掩恶,进退为功,王者慎勿与谋。夫智思之人,弊于是矣。”)
若难设以物,难说以言,守一而不知变,固执而不知改,是愚佷人也。(议曰:志士守操,愚佷难变。夫不变是同,而愚智异者,以道为管也。何以言之?《新语》云:“夫长于变者,不可穷以诈;通于道者,不可惊以怪;审于辞者,不可惑以言;达于义者,不可动以利。故君子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学问欲博而行己欲敦。目不炫耀之色,耳不乱阿谀之辞。虽利以齐鲁之富而志不移,设以松乔之寿而行不改,然后能一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观其道业。”此其所以与愚佷异也。)
若屏言而勿顾,自私而不护,非是而强之,是诬嫉人也。(议曰:刘备以客见诸葛亮而贤之,亮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忤数。形外露,邪心内藏。必曹氏刺客。”后果然。夫人容止,大抵如是。
何晏、夏侯玄、邓扬等,求交于傅嘏而不纳也。或怪而问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也;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败衅,妒前而无功。以吾观此三人,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后皆如嘏言。夫妒者之行,有如此者。)
此之谓考志。
(《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质欲懿重,志欲宏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堪物侄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诗》咏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以色,心小也;‘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论之,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心大志大者,豪杰之隽也;心大志小者,傲荡之类也;心小志小者,拘懦之人也。”)
又有测隐。测隐者,若小施而好得,小让而大争,言愿以为质,伪爱以为忠,尊其行以收其名。此隐于仁贤。(孙卿曰:“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言霸道者,何也?彼非本政教也,非服人心也,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桀耳,曷足称大君子之门乎?”)
若问则不对,详而不穷,貌示有余,假道自从,困之以物,穷则托深。此隐于艺文也。(又曰:虑诚不及而佯为不言,内诚不足而色亦有余,此隐于智术者也。《人物志》曰:“有处后持长,从众所安,似能听断者;有避难不应,似若有余而实不解者;有因胜情错失、穷而称妙,似理不可屈者。此数似者,众人之所惑也。”)
若高言以为廉,矫厉以为勇,内恐外夸,亟而称说,以诈气临人。此隐于廉勇也。(议曰:太公云:“无智略大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将。”此诈勇之弊也。)
若自事君亲而好以告人,饰其见物而不诚于内,发名以君亲,因名以私身。此隐于忠孝也。此谓测隐矣。(《人物志》曰:“尤妙之人,含精内真,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违。而人之求奇,不以精微测其玄机,或以貌少为不足,或以瑰姿为巨伟,或以真露为虚华,或以巧饰为真实。”何自得哉?故须测隐焉。)
夫人言行不类,终始相悖,外内不合,而立假节以惑视听者,曰毁志者也。(《人物志》曰:“夫纯讦性违,不能公正,依讦似直,以计讦善;纯宕似流,不能信道,依宕似通,行傲过节。故曰:直者亦讦,讦者亦讦,其讦则同,其所以为讦则异;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则同,其所以为宕则异。观其依似,则毁志可知也。”)
若饮食以亲,货赂以交,损利以合,得其权誉而隐于物者,曰贪鄙者也。(太公曰:“果敢轻死,苟以贪得,尊爵重禄,不图大事,待利而动,王者慎勿使也。”)
若小知而不大解,小能而不大成,规小物而不知大伦,曰华诞者也。(文子曰:“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诚其大略非也,闾里之行,未足多也。”)
又有揆德。揆德者,其有言忠行夷,秉志无私,施不求反,情忠而察,貌拙而安者,曰仁心者也。有事变而能治效,穷而能达,措身立功而能遂,曰有知者也。有富贵恭俭而能威严,有礼而不骄,曰有德者也。(议曰:鱼豢云:“贪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处所然耳。”是知别恭俭者,必在于富贵人也。)有隐约而不慑,安乐而不奢,勋劳而不变,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有恭敬以事君,恩爱以事亲,情乖而不叛,力竭而无违,曰忠孝者也。此之谓揆德。
(桓范曰:“夫帝王之君,历代相踵,莫不慕霸王之任贤,恶亡国之失士。然犹授在凶愚,破亡相属,其故何哉?由取人不求合道,而求合己也。”故《人物志》曰:“清节之人,以正直为度,故其历众材也,能识性行之常而或疑法术之诡;术谋之人,以思谋为度,故能识策略之奇而或失遵法之良;伎俩之人,以邀功为度,故能识进趋之功而不信道德之化;言语之人,以辩析为度,故能识捷给之慧而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驳,莫肯相是。凡此之类,皆谓一流。故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矣。”又曰:“夫务名者不能出陵己之后,是故,性同而材倾,则相援而相赖也;性同而势均,则相竞而相害也。此又同体之变,不可不察也。”)
夫贤圣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识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又曰:夫天下之人不可尽与游处。何以知之?欲观其一隅,则终朝足以识之;将究其详,必三日而后足。何谓三日而后足?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然则何以知其兼偏而与之言乎?其为人务以流数,抒人之所长,而为之名目。如是者,谓兼也;好陈己善,欲人称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谓偏也。)是故,仲尼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爱物,蔽在无断;信者露诚,蔽在无隐。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率此道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易经》是如何一部书?如今已是众说纷纭,且不管如今如是说,但是对一个想要学习《易经》的人,首先应该明确一点:《易经》是占卜之书。
自孔子之后,南宋大学者朱子(熹)应该为易学研究集大成者,为此,文韬武略的康熙帝曾誉之为:“易之本义,朱子独得”。朱子曾为《易经》定义:“易乃卜筮之书”。为此清朝初期在统编《御纂周易折中》一书时,康熙也御笔亲批:“易学之广大悉备,秦汉而后无复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来,周邵程张阐发其奥,唯朱子兼象数天理违众而定之,五百余年无复同异,宋元明至于我朝,因先儒已开之微旨。或有议论已见,渐至启后人之疑”。上述简言之,康熙大帝之意为:本朝有关《易经》之论,均以朱子之意为准。由此可见《易经》为占卜之书,已是自古的定义,已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易经》的学者有意无意间在回避这一问题,似乎一提《易经》占卜,总有大逆不道,怕染封建迷信之嫌。为此,当代易学大师刘大均也曾有言:“当今国内易学研究,言理者多,言象数者少,言占者更少”。
国学浩繁,号称“十三经”,但不是每部经都具备占卜功能。唯有《易经》,除能以通天达地的意志内涵和精义入神的思维境界,以及修齐治平的人文思想,稳居群经之首外,又能以其特有的占卜功能,深受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的崇拜和喜爱,以至历经几千年苍桑仍经久不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的文化特性,而在于它的趋吉避凶,度人教化的占卜功能。《易经》之所以避过秦始皇焚书之火,就因为他是一部占卜之书,故古籍《隋书》云:“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
其实,就人类生存意义而言,所谓文化并不重要。远古之人,没有今人的文化,但他们的生存历史远远比今人长久得多,他们尚道德,重吉凶,在意自身的一切,能否遵天守地而不至灾害。于是《易经》产生了,他们力求以占卜的方式与天地沟通,以达到自身的生存意义。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到,那时人们的心灵是如何的纯净。那种原生态的生活是多么的悠然自得。
在这之后的古人,他们自认为比以往的古人进步了,有文化了,同时也变得有些贪婪了,灾难也随之增长,但他们也仍然视《易经》为法宝,将占卜行为运用到更广泛的行动中。他们从《易经》占卜中获得巨大智慧。成就了令后人引为骄傲的千秋大业,以此同时,他们也将《易经》研究推向更广泛的文化境地。
如今,随着科学时代的到来,《易经》的发展到了新的时代,易经社会学、易经哲学、易经天文学、易经地质学、易经系统学等等不断出现,科学以其特有的优势,在证明着易经的博大和精深。但这一切多是对《易经》本体的研究,并不会改变《易经》的占卜性和《易经》的占卜的运用,相反更能证明《易经》占卜是建立在《易经》本体的科学性之上。
人类生活无论处在任何时期,都无法离开精神的需求,人类的一切生存行为中都必须面对吉凶的选择。灾难、死亡和罪恶,将始终是人类生活所要面对的现实,而现代化的生活,将加剧人类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为此,我们重提《易经》的占卜性是一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易经》的占卜性应为当今喜爱《易经》、学习《易经》之人的第一要义。这是华夏远古神灵留给我们的生存法宝,是“圣人”的功德所在,是天地造物者对苦难人类的一种恩泽。试想,如果《易经》失去它的占卜功能,失去趋吉避凶的意义,而只是一种似有非有的文化,《易经》存世还有多大意义!
(本文为易经占卜自学堂教材)
本文2023-08-06 17:15:50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337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