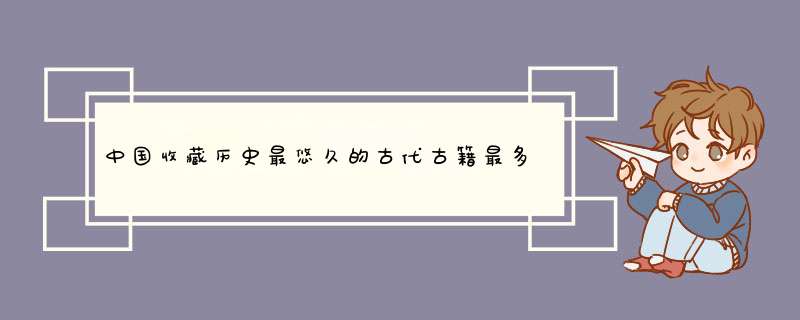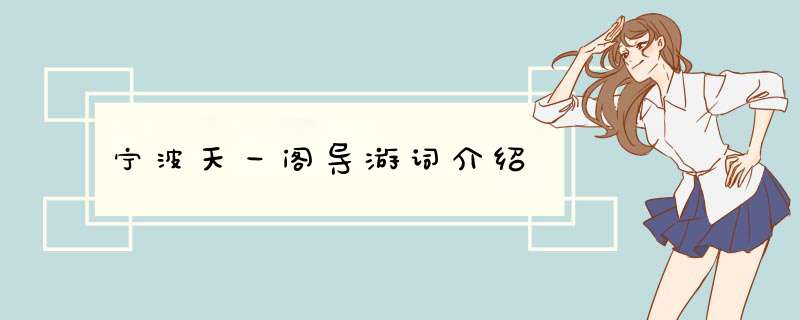古书收藏的知识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
最有智慧的古书排名
《周易》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我国最古老、最有权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一名《易》,又称《易经》,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本是占筮
《菜根谭》、《幽梦影》、《小窗幽记》、《围炉夜话》《颜氏家训》、《朱氏家训》,到后来的《曾国藩家书》、《左宗棠家书》,再到解放前鲁迅许广平的《两地书》、《闻一多家书》;解放后的《傅雷家书》、《沈从文家书》等 国外的如英国培根《人生论》,
NO10 锏 锏,(铁)鞭类,长而无刃,有四棱,长为四尺(宋制四尺为一米二), 后来才有了杨家枪和杨家将的故事NO3 矛 有古书上也说矛=枪, 但从一些小说和文
中国最神秘的一部古书
很多,例如:《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各有文章81篇,内容非常广泛《黄帝外经》37卷,据说内容也很丰富,可惜失传了 《连山》、《归藏》 周易的分支 《明心宝鉴》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辑录者或整理者是范立本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收藏有1368年刊印的《校正删补明心宝鉴》,其善本室则藏有1553年刊印的《重刊明心宝鉴》(二卷)和1621年刊刻的标明“范立本集”《新刻音释明心宝鉴正文》(二卷),普通古籍室还收藏有《新镌校正明心宝鉴正文》,扉页上题“官板正字明心宝鉴”,“桥村庄三圣堂行”国家图书馆同时收藏有明万历皇帝《御制重辑明心宝鉴》二卷(根据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影印),成书于1585年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内容包括一些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和一些远古神话和传说
十三经 《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 、《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中国十大旷世古书
按古籍影响 周易、论语、诗经、史记、资治通鉴、本草纲目、伤寒论、四库全书、六艺十三经、孙子兵法 以下是按古籍年代 唐咸通九年刻本《金刚经》唐成都府BIAN家刻本《陀罗尼经咒》宋杭州猫儿桥刻本《文选五臣注》宋刻本《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史记集解索引正义》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元至正五年刻本《金史》元大德三年《稼轩长短句》按古籍类别: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 总之门类繁多,不可细数
很多,例如:《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各有文章81篇,内容非常广泛《黄帝外经》37卷,据说内容也很丰富,可惜失传了 《连山》、《归藏》 周易的分支 《明心宝鉴》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辑录者或整理者是范立本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收藏有1368年刊印的《校正删补明心宝鉴》,其善本室则藏有1553年刊印的《重刊明心宝鉴》(二卷)和1621年刊刻的标明“范立本集”《新刻音释明心宝鉴正文》(二卷),普通古籍室还收藏有《新镌校正明心宝鉴正文》,扉页上题“官板正字明心宝鉴”,“桥村庄三圣堂行”国家图书馆同时收藏有明万历皇帝《御制重辑明心宝鉴》二卷(根据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影印),成书于1585年
中国古书:《三字经》、《黄帝内经》、《山海经》、《资治通鉴》、《道德经》、《奇门遁甲》、《孙子兵法》《易经》、《增广贤文》、《论语》、《史记》、《汉书
中国人十大必读古书
1、中国先秦时期的百科全书 《诗经》 孔子 2、兵家韬略之首 《孙子兵法》 孔武 3、垂范千古的儒家经典 《论语》 孔子及其弟子 4、中国道家学说的开山之作 《老子》 老子5、最爱中国人推崇的英雄传奇 《水浒》 施耐庵 6、包含处世权谋与人生智慧的杰作 《三国演义》 罗贯中 7、东方世界的《堂吉诃德》 《西游记》 吴承恩 8、成就人生事业的大学问 《菜根谭》 洪应明9、不会做诗也会吟 《唐诗三百首》 孙洙,徐兰英 10、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 《红楼梦》 曹雪芹,高鹗
如下:《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史记》,《论语》,《孟子》,《孙子兵法》,《道德经》,《诗经》
《太平广记》 全书按题材分为92类,又分150余细目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如 明代拟话本有的据古书记载敷演成篇,如《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咏菊花事,出自《
中国十大经典古籍
1、《论语》:《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 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其
如下:《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史记》,《论语》,《孟子》,《孙子兵法》,《道德经》,《诗经》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
"Without grammar very little can be conveyed,without vocabulary nothing can be conveyed"
出自:DAWilkins,"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下面是引用:citation ,页码不是很重要,只要MLA 的各是正确就行了:Wilkins,DA1972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The MIT Pres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Massachusetts
英国的巨石阵是英国著名的史前遗迹,与神秘的复活岛石像和古埃及金字塔媲美,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大家都惊叹于古代的人是如何建造这样一个超前技术的巨石阵的?并且被因为什么原因而建造感到困惑。
正是因为种种谜团,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有人还将巨石阵与神秘的外星人联系到一起,认为巨石阵是外星人建造的,从而展开了诸多脑洞大开的推测。但是在不久之后,英国人就承认巨石阵并不是古物,巨石阵是假的,这到底是为什么?
早期的考古学家根据计算得出,巨石阵建造于公元前4000年至2000年。这个计算引发了考古界的争论,一直到2008年,一考古小组称他们测量的建造巨石阵的时间在大约公元前4000年至4200年是最为准确的时间。
不过近年来有人多人质疑巨石阵,认为是英国人对世界撒的谎,是伪造的。它的历史并没有上千年,而是只有65年。
巨石阵是由重量达几十吨的大石头组成的,在英格兰威尔特郡的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矗立着。它早已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是世界上最为神秘的纪念碑之一。从它的排序来看,有的人认为它是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将其比作秘鲁的“众神之门”。最近有几组巨石阵的照片曝光再次引起民众的质疑。
这一组照片在网络流传。在照片中,人们使用一下现代的运输工具如起重机、拖拉机等来搬运巨石阵中的巨石。似乎都还未完成建造。这一组照片于1954年拍摄,它也确确实实是巨石阵。
照片很明显地显示出巨石阵确实是当时英国人所伪造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外界声音开始怀疑英国的麦田怪圈也是当地人为了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而故意建造的。在一些古籍上似乎并没有提到过巨石阵。因此,看过这些照片的人都断言,巨石阵并不是什么古老遗迹,其真正历史仅有65年。
倘若是英国人的目的是为了拉动旅游业的发展而伪造了巨石阵,那么很显然他们做得很成功。每年到达巨石阵参观的游客人数已经超过一百万。当然,还是有人不相信巨石阵的伪造的这一结论。他们不懈努力,翻阅无数资料,找到一些巨石阵在1954年前就已经存在证明。用此证据证明巨石阵不是后人伪造,而拥有几千年的历史。
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都参与到这件事情来,事实上,巨石阵的建造记录确实可以追溯到14世纪,并不是人们所相信的后来才被伪造,确确实实有存在的历史记录。在1986年巨石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我们不可否定,毕竟如果这是假的,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早已揭穿了英国人的谎言。
而对于网上广为流传的照片,考古学家表示,这只是对巨石阵进行了一项修复工作,类似于大规模的修复在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多次。但是英国并没有对这组照片做出任何解释和发出任何声明,这也引起了网民的躁动。
我不知道弗洛伊德会对这怎么解释,反正有30多年时间,我最幸福的梦都是关于旧书店的: 一些我从前根本不认识的书店或者我正在光顾的熟悉的老书店。其实那些熟悉的书店肯定已经不存在了,我很不情愿地得出这个结论。在巴黎,离火车北站不远的一个地方,对于那里一条上山的长街尽头的一家书店,我有着非常生动鲜明的记忆。那是一家有着许多高高书架、门进很深的书店(我得用梯子才能够到那些书架的上头)。至少有两次我搜寻遍了它的每一个书架(我想我在那儿买到了阿波利奈尔的《法尼·西尔》的译本),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我去那里寻找那家书店的努力却是归于徒然。当然,那家书店可能已经消失了,甚至那条街道本身也不在那儿了。此外在伦敦有一家书店,非常频繁地出现在我的梦中: 我能够非常清楚地记得它的门面,但是却记不得它内部的情况了。它就坐落在你来尤斯顿路的路上,在夏洛特街后面的那个地区。我从来没有走进去过,但是我肯定如今那儿再也没有这么一家书店了。我总是带着一种幸福和期待感从这样的梦中醒来。
在我生活的各个不同时期,我一直坚持写关于我的梦的日记,在我今年(1972)的日记里,在前7个月的日记里就包括有6个关于旧书店的梦。相当奇怪的,是第一次。它们都不是快乐的梦;也许这是因为我的一个亲爱伙伴在1971年底去世了吧,我曾经和此人一起去淘书,在二战刚刚结束之后,我和此人一起,开始去搜罗维多利亚时期的侦探小说。同样在今年的一些梦中,出现过一本我打算送给我的朋友约翰·苏特罗作圣诞礼物的有关铁路的旧书(他曾经在牛津创建了铁路俱乐部),当我从书架上把它抽出来的时候,书皮却已经掉了一半: 甚至那些旧的红色纳尔逊7便士丛书(那么没道理地受到乔治·奥威尔的中伤,尽管它的初版太昂贵了,但我仍然很喜欢拥有它)结果都是不同版本的。在所有这些梦中,似乎没有什么好到值得一买的书。
我的朋友戴维·洛是一个书商,他的收藏品曾经使我的思想天马行空,放荡无羁,不止是通过一些梦,而是通过长达50年的淘书中的无数小小探险和在其中结下的友谊。(在17岁上我就变成了查林克罗斯路上的一个漫游者,唉,现在我很少叨扰那里了。)
旧书商们在我以往认识的各种人物中是属于那种最友好又最古怪的人。如果我没有成为一个作家,那么他们的行当一定会成为我最喜欢选择的行当。在他们那儿有书籍发霉的气味儿,在那儿有寻宝探宝的感觉。由于这个缘故,我宁愿到码放得最混乱的书店,在那种地方,地形学和天文学的书籍混放在一起,神学和地质学的书籍混放在一起,一堆堆没有分类的书籍乱堆在楼梯间里,正对着一个标着“旅游图书”的房间,而在这个房间里可能包括一些我所喜欢的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失去的世界》或者《克罗斯科的悲剧》。我害怕走进马格斯书店或者夸里奇书店,因为我知道在那种地方不可能作出什么个人的发现,在那儿书商不会犯任何错误。从戴维·洛的收藏中我意识到我害怕去威廉四世大街的巴恩斯书店是多么错误。但是现在来补救我的这个错误未免为时太晚了。
一个人要想真正进入这个充满机会和冒险的魔幻世界,就必须既是收藏家又是书商。我本来宁愿做一个书商的,但是由于二战我失去了机会。在德国人大规模空袭伦敦期间,我碰巧和戴维·洛(我已经和他很熟了)和小科尔是隶属于同一个哨所的临时防空员,小科尔在那些日子是一个书“贩子”。我和科尔的第一次侦察任务是去搜寻一个伞投炸弹,有人说它挂在布鲁姆斯伯里一个广场的树上。我们根本没有找到它,就给自己放了假。科尔领着我去看了一趟他的房间: 我记得破旧的书籍堆得到处都是,甚至床底下都堆着书,我们俩一致同意,如果有一天我们俩都能在战争中幸免于难,我们就一起经营旧书。后来我离开伦敦到西非干别的工作,我们失去了联系。我已经失去了成为旧书商的唯一一次机会。
要成为收藏家相对比较容易。你收藏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你有入门的钥匙。收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寻求的乐趣,是你遇见的那些人物,是你结交的朋友。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的时候,就初次尝到了购买收藏南极探险作品的滋味,我对北极不感兴趣。那些书籍都已经不在了。那些书现在会有一些价值,但是谁会在乎呢?在战前,我收集查理二世复辟时期的文学作品,因为我当时正在写一部罗切斯特传记,这本书直到30多年以后才得以出版。那些书并不是最早的版本(我当时买不起);那些书也已经不在了: 其中有些书是在德国人对伦敦大轰炸的时候遗失的,也有一些是在我离开英国的时候很遗憾地放弃的。
现在我依然在收藏维多利亚时期的侦探小说: 在40年代的弗伊尔斯书店,我曾经一次花半克郎找到多少书呀!虽然约翰·卡特在10年后推出了著名的斯科里布纳目录,它到处造就了无数收藏家。
对于收藏家来说,毫无疑问,比起那种寻找的兴奋,比起有时这种寻找把你带到的那些神奇陌生的地方来说,收藏品本身价值的重要性倒变得次要了。就在最近,我和我的兄弟休(他收藏的侦探小说的范围包括从维多利亚时期到1914年,所以我们经常结伴淘书)曾经在倾盆大雨中穿过坐落在一片废弃地区中的令人忧郁的利茨街周围,那地方简直就是格里尔森绝望的纪录片的一部分。我们寻找着一家书店,它曾被收入一本很可靠的指南。但是随着我们在那些废弃的工厂之间身上变得越来越湿淋淋的,我们对那本指南的信任也变得越来越少了。然而,当我们终于到达那家肯定曾经存在过的书店时,那里一扇挪了窝儿的门上挂着一个招牌“书店”,其中“书”字的前三个字母都不见了,所有的窗户都破碎了,地板上神秘地乱扔着一些孩子的靴子和鞋,还有一些好鞋。难道这是什么小孩黑手党的聚会地点吗?好像是在那类地方,发现了一些新酒吧和过去从来没有尝过的啤酒,倒也是对淘书者的某种奖赏。
这和皮卡迪利大街上那家年代久远的书店完全是不同的世界,那家书店有古籍旧书部,我最近还到那里去消磨过时间,如果偶然问起他们是否有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伦特的什么著作,他们就会问:“他写什么,先生?小说吗?”
我想戴维·洛对于这些昂贵的书店太宽厚仁慈了,但是我想,一个人如果干这行,他就不得不对那种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衣着讲究的坏蛋作出友好的姿态。我避开那些新开的大学书店,那儿都是红砖和玻璃,塞满了二手的学术书籍,那些书即使在它们初次问世的时候就很沉闷无聊。唉,至于狄龙**的书店,它躲过了扔在商店街周围的所有炸弹幸存下来,但是它今天也没有昔日的那种魅力了。有时候,戴维·洛在讲礼貌上做得过分了: 对于那位邦珀斯书店的大名鼎鼎的威尔逊先生来说,“精”是一个褒义的形容词,我倒是宁愿说他“滑”。
不,比起查林克罗斯路来,伦敦西区现在再也不是我的魂牵梦萦之地了,但是感谢上帝!塞西尔短街依然保持着塞西尔短街的样子,即便是戴维·洛已经搬到牛津郡去了。
在一个开心的日子里,我从戴维那里买到一份奇怪的18世纪的手稿,封面由白色皮纸制成,上面有一个手写的标题《赫尔顿尼亚纳》。它花了我5个畿尼,在30年代这是很大的一笔钱,但是在经过一些研究之后,我靠着在《旁观者》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把这个书价挣回来了。文章谈到这样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一连串残酷的骗局使一个名叫赫尔顿的不得人心的商人大受其苦,很显然这个故事是他的敌人写的。我拥有这份手稿,一直到一封有趣的来信“插入进来”,信中谈到手稿里提到的一些18世纪的伦敦商店名,信是由安布罗斯·希尔爵士写的。这使我很高兴,靠这种方法,在《赫尔顿尼亚纳》上面我除了付出了一点劳动之外什么钱也没花。
也许我最看重的是淘到了《复活节前一周的任务》,由沃尔特·柯卡姆·布朗特翻译,1687年出版,配有7张霍拉版画,封面是同时代压印的红色摩洛哥羊皮。它被献给英格兰女王。“英格兰的女王、王后们又称圣了,”布朗特写道,“结果无限伟大,于是人们发现通往天堂之路就是效忠宫廷之路。”他在一年后就不会写这些话了,因为荷兰的威廉来到了。他将不得不在国外出版这本书,或者根本没有出版家的印刷,没有在坐落于海霍尔本羊羔街的马修·特纳书局公开出版。这本漂亮的书让我在克拉彭公地的盖洛普先生的书店里花了半个克朗,我在那儿买我的安东尼·伍德作品。盖洛普先生的书店是二战的牺牲品之一,它在同一天里和两百码以外的我的房子一样“上天了”。
但愿戴维·洛在书中包括一个被炸弹和建筑师们毁掉的已亡书店名单。例如原坐落于威斯特本园林的那家消失了的我喜欢的旧书店,还有坐落在金克罗斯车站对面三角地的消失了的小书店,在那里我曾经买到《探险记》和《夏洛克·福尔摩斯回忆录》的首版本,花的是在那个时候看来过分的价格五英镑。那是淘书的令人难过的一面,与新书店的开张相比,更多得多的书店消失了。甚至布莱顿也不是它当年的样子了。
(邹海仑 译)
注释:
查林克罗斯路: 在伦敦市中心,是伦敦旧书店最集中的地方。
罗切斯特(1647—1680): 即罗切斯特二世伯爵,本名约翰·威尔莫特,17世纪著名英国诗人,查理二世的朋友。
格里尔森(1898—1972): 英国纪录片运动的创始人。拍有纪录片名片《漂网渔船》(1929),1948—1950任英国中央资料馆影片审计官。
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伦特(1840—1922): 英国诗人,诗集《海神情歌》是其代表作,另有《我的日记》(1919,1920)两卷。
畿尼: 英国旧金币单位,等于21先令。
荷兰的威廉(1650—1702): 即大不列颠的威廉三世,初任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执政(1672年起),后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国王(1689年起)。
安东尼·伍德(1632—1695): 英国古物收藏家、学者,著有《牛津大学历史及其人物》、《牛津学苑》等。
赏析
本文是格林在1973年为好友戴维·洛《带着所有的错误》一书所写的序言,是一篇反战题材的散文。作者通过对战前战后旧书店的对比和与旧书商们友谊的描述,表达了浓重的反战情绪;通过对在旧书店淘书的乐趣的回忆,凸显出战争的破坏性,从而深刻地反思战争带给人们的伤痛。
旧书店让格林魂萦梦牵,而这些曾给他带来过无比乐趣的地方,经过战争的硝烟炮火,已经不复存在。作家只能在梦中去寻找这些书店的影子。格林伤感地写道,在30多年的时光中,“最幸福的梦都是关于旧书店的”,即使醒来时也带着“一种幸福和期待感”。
旧书店让人留恋,因为作家能够在那些散发着霉味的、混放的书籍中,找到一些无法在正规书店中找到的书,比如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失去的世界》或《克罗斯科的悲剧》等。这种乐趣就好比探险家在探险。那种在经历艰难险阻和重重障碍后,最终发现自己寻找已久的宝物时的惊喜与兴奋,是没有过淘书和探险经历的人所难以体会到的。旧书店让人留恋,也是因为那里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与同样懂得淘书乐趣的旧书商们通过讨价还价结下深厚的友谊,比如和书商戴维·洛。然而,所有这些乐趣都被战争的到来剥夺了。作家以前经常去淘书的伦敦西区,经过战争的洗礼,现在已经面目全非,里面充斥着新开的大学书店和沉闷无聊的二手学术著作。查林克罗斯路和塞西尔短街仍然维持旧貌,但是昔日好友戴维·洛已经从那里搬走了。曾买到过《复活节前一周的任务》的盖洛普先生的书店,也已经成为二战的牺牲品,在飞机的轰炸下,“它在同一天里和两百码以外的我的房子一样‘上天了’”。“原坐落于威斯特本园林”的小书店,“坐落在金克罗斯车站对面三角地”的小书店等等,所有这些作家喜爱的小书店,一个个地消亡在战争的阴影中。
战争不仅仅破坏旧书店、淘书的乐趣和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它更是扼杀人们理想的刽子手。作者原本向往成为一名书商,并和一位兴趣相投的伙伴相约,如果能在战争中幸免于难,就要共同经营一家旧书店。结果最后他们失去了联系,作者也就失去了成为书商的唯一一次机会。虽然格林在写作时用了幽默甚至调侃的手法,但是我们仍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失去朋友和理想破灭的复杂心理,切身感受到战争带给人们的伤痛。作家还有一个理想,那就是成为一名收藏家。然而,他精心收藏的有关南极的书籍,有的在德国人对伦敦的轰炸中遗失,有的在作者逃命时被遗弃,于是,这个理想也不得不被放弃。
战争改变了一切。在战争的硝烟与战火中,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放弃友谊、乐趣甚至是理想,而即使是生存,在这时也变得可望而不可即。在生命都已经被忽视的日子里,人们只能用回忆来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是的,战争带来的不仅是对物质的摧毁,更是对精神的毁灭。这一切,格林都通过对旧书店的描写,忠实而客观地记录了下来。整篇文章弥漫着一股无奈的伤感气息和自我解嘲的幽默与调侃,读来让人心酸,又让人回味。
(王 坚)
编者按: 牛津大学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之一,曾被用来拍摄《哈利·波特》系列**中魔法学校的部分场景。记者近日访问了这座著名
牛津大学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之一,曾被用来拍摄《哈利·波特》系列**中魔法学校的部分场景。记者近日访问了这座著名的“知识宝库”,负责接待工作的是对该馆了如指掌的依莎贝拉**。从她口中,记者探听到不少有关图书馆的“独家秘闻”。
女王无权借走馆内藏书
据依莎贝拉介绍,牛津大学图书馆现有藏书800万册,其中很多都是古籍珍本,论级别仅次于大英图书馆。馆内藏书只能阅览,不能外借,对女王也不例外。此外,很久以前牛津大学就立下规矩:在成为该馆新读者前必须宣誓。誓词大意是:不得偷拿、损毁、玷污书籍,不带火种进馆,严守馆内各项规定。早年间,这种誓言是要用古老的学术语言拉丁语讲出的。依莎贝拉表示,临时参观者就不要求宣誓了,但必须严守其他规定,例如不得拍照等。
牛津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记者看到,在图书馆二楼可开架阅览的图书,很多是三四百年前的珍贵资料。进馆之前记者还被告知,如要在笔记本上做摘录,只能使用铅笔。因为不论是鹅毛墨水笔,还是钢笔、圆珠笔、签字笔,一旦污损了这些珍贵书籍,损失将是不可挽回的。因此所有阅览者都老老实实地使用最可靠的铅笔。
值得一提的是,从今年开始,牛津大学图书馆又添了一项新规定,就是放在书架最上层的书籍禁止利用梯子拿取。原来,馆方打算将图书馆内的古董书籍保留在其历史位置不再移动。另外考虑到图书馆的栏杆很低,使用梯子也不安全。那真需要看这些古书怎么办?依莎贝拉耸耸肩说,只有到英国别的图书馆看这部书的其他版本了。
世界各地抢着向其捐书
依莎贝拉骄傲地告诉记者,该图书馆的馆藏近70%是靠出版社缴存,真正购买的书籍比例不高。牛津大学是英国书刊缴存制度的开创者,早在1610年就与伦敦出版业协会达成协议,该协会成员每出版一部新书,就向牛津大学缴存一部。这样的图书缴存制度,历经沧桑保持至今。目前,来自英国和世界各地的捐赠图书源源不断地涌进图书馆。依莎贝拉说,图书馆每周收到的新书达到5000册。
“800万册的馆藏加上每周5000册的新书,如何安排得下呢?”记者不禁问道。依莎贝拉似乎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她说,牛津大学城到处都是古建筑,不可能建新的现代化高楼用来藏书,唯一的出路就是转入地下了。现在这个图书馆地下方圆几平方英里都挖空做了藏书之所。如果将地下的图书取出放在书架上,那么这个书架会有190多公里长。
图书馆曾为抵抗纳粹立功
图书馆无疑是防火重地,那么牛津大学图书馆是怎样幸存于二战时期纳粹德国轰炸之下的呢?为此,记者特意向莫德林学院的老教授请教。原来,当年不列颠空战时期,纳粹并没有轰炸牛津大学。据教授讲,纳粹德国的如意算盘是在占领英伦三岛后,将牛津作为英国的新首都。该图书馆不仅因此躲过一劫,还协助收藏了很多从伦敦转移过来的珍贵书籍。
作为中国人,记者自然关心图书馆收藏的中文书籍情况。依莎贝拉告诉记者,牛津大学图书馆向来重视汉学,早在中国明朝时就委托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购买明朝刻印的书籍。目前馆里有几万册中文古籍,主要是明清小说。如果算上后来收藏的中文书就更多了。另外,图书馆中文部还学会了一个绝活,就是用中国古法修复中文古籍。
可以说,记者了解到的这些“秘闻”,其出发点都是对知识、对文化的尊重。就如同牛津大学图书馆取名为博德利图书馆一样,博德利本是牛津大学16世纪的校友,当年他为建立图书馆出钱出力、四处奔波。热爱知识的人自然会赢得爱戴,这座图书馆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钱钟书先生在牛津读书时,是这座图书馆的常客。不过饱学的钱先生没有将这个图书馆按发音直译成“博德利图书馆”,而是译为“饱蠹楼”。恐怕这种形神与发音兼备的翻译,也只有钱先生那样的书虫想得出来吧。
有!英国对汉学的研究比法国、德国和俄国都要晚。在18世纪的英国,除了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这个大汉学家,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个人。琼斯爵士大概在他21岁的时候便已经开始接触汉语,阅读了柏应理和殷铎泽等人译的拉丁文版的《大学》、《中庸》、《论语》。从此,他对儒家学说和孔子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读完《大学》后,还写了一篇议论教育的文章,流传至今的只有文章的大纲。琼斯通过阅读这些儒家经典,加强了自身道德教育的信念,开拓了思想的领域。同时,《大学》中引用的《诗经》中的若干诗篇也使他初次接触到了中国的古典诗歌。琼斯曾经将《卫风·淇奥》中的一节分别用直译和意译的方式译成拉丁文,与其通信的波兰梵文学者瑞微兹基(Rivicski)看到他的译文后,十分赞赏,称其十分高雅和不同寻常。大约在1785年和1788年之间,琼斯担任亚洲学会的会长,发表了一篇关于《诗经》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选有琼斯根据《大学》翻译的三节《诗经》中的诗,它们分别是:《淇奥》、《桃夭》和《节南山》。翻译时他参考了柏应理的拉丁文译本。他的译文比之前的珀西的译本准确多了。
法国汉学家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在1736年和1738年曾分别由布鲁克斯(R Brookes)和凯夫(E Cave)译成英文,英语读者由此最早接触到了其中收录的《诗经》和《书经》。“1829年,英国汉学家戴维斯(J F Davis)在其专著《汉文诗解》里以《诗经》和先秦至六朝民歌为例论述中国诗歌格律,开创了《诗经》原文英译的先河。”
第一部英译本的《论语》的翻译者是顾利(David Collie),“他曾担任过马六甲的英华书院的汉语教授,英华书院印行过他的四书译本,书题为《通常被称之为四书的中国经典著作集》(1928)。”
四书 The Four Books:
《大学》the Great Learning
《中庸》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孟子》Mencius
五经 The Five Classics:
《诗》The Book of Songs
《书》The Book of History
《易》The Book of Changes(或:I-ching 易经的音译)
《礼》The Book of Rites
《春秋》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本文2023-08-06 18:34:23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344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