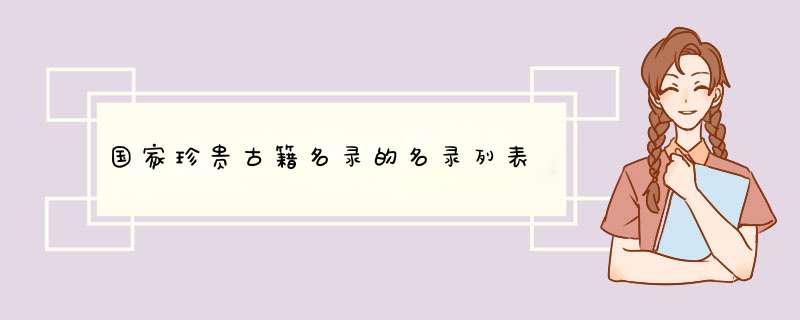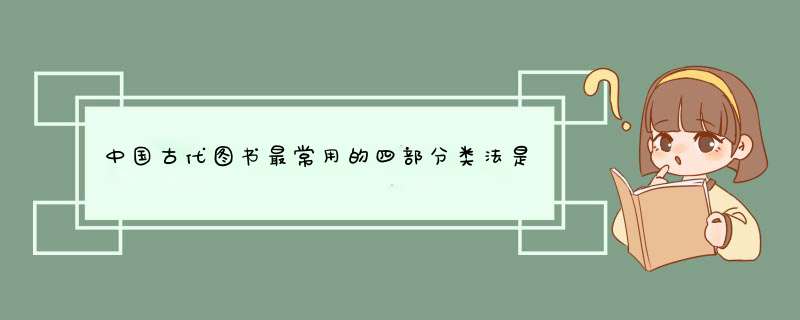中医古籍 [侵华日僧曾掠走大批中国古籍]
![中医古籍 [侵华日僧曾掠走大批中国古籍],第1张 中医古籍 [侵华日僧曾掠走大批中国古籍],第1张](/aiimages/中医古籍 [侵华日僧曾掠走大批中国古籍].png)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文献记载历数千年而未中断。中华民族的典籍文献,夙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数量之丰富,内容之深厚,举世无双。这些丰富的典籍不仅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且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深刻影响,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文化遗产。保护并继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要求今人对现存中国古籍作系统整理与研究,首先需要对文献资源作全面调查与清理。在中国历史上,像编纂《中国古籍总目》这样在全国图书馆界、学术界对古籍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清理,尚属首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具有开创性与总结性,堪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重大成果。
编纂全面反映中国古代文献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总目录,是文献学界、图书馆界多年的共同理想。中国历代有编纂史志目录、公私藏书目录的传统,并重视书目编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指导作用。史志与公藏目录多反映各朝皇家或官府的典籍积累,私家藏书目录则较多反映民间的文献收藏,两者各有局限,互为补充。收罗完备、着录详明、体例精严的总目录,惟有文献典籍大多归于公藏,各地区、各系统图书馆开展联合编目的当代,才有可能产生。近代以来,各大图书馆逐步积累的馆藏古籍记录与各学科专家合作编纂的专科目录,是《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大型书目,为《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提供了文献调查与收集、书目汇总与校订的成功范例。
一百多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270余万册馆藏实体文献基本形成了以适应师范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为主,覆盖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各学科门类的藏书体系。馆藏中拥有线装古籍文献17万余册,古籍善本2200余种12600余册,拥有《四库全书》、《中华大藏经》、《申报》、《晨报》、《民国日报》及解放前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影印本等特种文献。除了大量的实体文献外,数字信息资源的建设也呈迅速增长之势,近些年先后引进了中外文数据库近20个,其中包括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硕论文数据库、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高校管理决策参考数据库、中宏数据库、中国基本古籍全文数据库、爱迪科森网上报告厅、北大法律网、新东方网络课程,外文数据库:数学评论期刊全文库、德国Springer 外文期刊数据库、美国LexisNexis Academic学术大全数据库、美国物理研究会AIP&APS期刊全文数据库、荷兰Elsevier SDOS期刊全文数据库、美国EBSCO教育心理学数据库、英国皇家物理学会的IOP数据库等,另有方正数字图书馆、超星图书馆和美星外文数字全文库的电子图书近100万册。
本文2023-08-06 19:38:08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349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