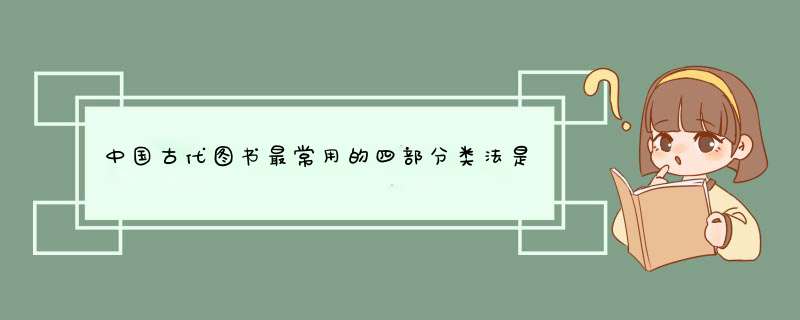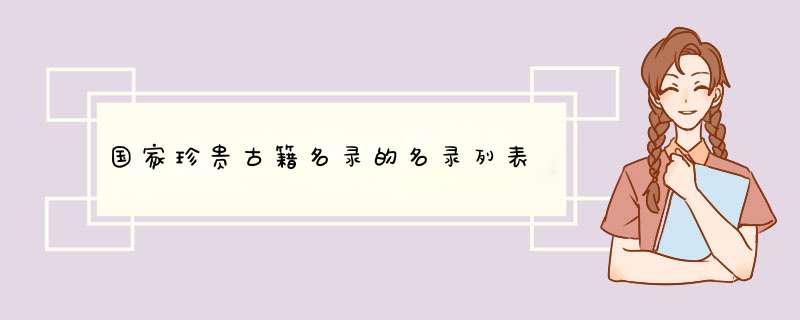唐朝的古籍

金刚经
《金刚经》是早期大乘佛教经典,属于《大般若经》的第九会,是宣说般若空义的代表作之一。中国依鸠摩罗什译本为流行本,一般所说的《金刚经》都指罗什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科判则依昭明太子的三十二分法。《金刚经》古来依无著和世亲的论释为中心被理解,尔后由三论、天台、华严、法相、禅、真言等各宗的观点加以理解和发展。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等,无论提到哪一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古籍都是让人羡慕无比的瑰宝。
当阿里达摩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四川大学的文史专家们的牵线搭桥下。终于在汉典重光平台上回归了首批数字化的古籍,包含40余种宋元刻本、写本,共有20万页。让我们不禁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国古籍流失最严重是主要原因是战乱。当时许多所谓的外国科考队趁着混乱的局势,肆无忌惮的盗挖、偷运、走私、贸易。导致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众多古籍珍本纷纷流落海外。更有甚者连流落何方都无从得知。让国人为此感到心痛不已。
而在全球许多博物馆内都可以看见这些中国古籍的身影。让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经发出无奈的感慨:“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国家政府对这些流失海外的古籍也极其高度重视,但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我国想要全部追回这些古籍原件的难度非常大。有很多时候也是凭着爱国人士的一腔热忱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让古籍回家。
这些古籍都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载体。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了更详尽清楚的路径。为了避免这些古籍再次流失遭受毁坏。我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运用传统的修补技艺来修补受损的古籍外。还通过数字化这种科学技术让这些珍贵的古籍得到长久的保存。每一本能传承至今的古籍都是无数前人耗费心血或牺牲生命保留下来的,而我们必须更好的将这些传承给后世子孙们。
先说说你说的第一句话:看史记,感觉古代文人尽玩“文字游戏”,对自己思维能力提升没有帮助。
这个“文字游戏”,我想应该是指善用典故或春秋笔法。
《史记》其何以见长?述通古今,不虚美不隐恶,辞练文采。这些尽是道德文学修养,岂能比于侦探逻辑小说?想通过读《史记》来提升自己思维能力?可见你读书不得其道了。若论春秋笔法,我觉得实是史书必须。中国古时是极讲求道德伦理,有一定地位的人死了会定諡号,通常都是为了概括其为人,暗含褒贬,目的就是为了扬善贬恶,风行教化。
史书的目的,当然不只是为了记述事实。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賊子惧,可见其目的也是为了评判是非,扬善贬恶。史官自已在叙述事实时,要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又不能因个人观点或情感歪曲历史,就不得不用词隐讳,暗含褒贬,才会有“郑伯克段于鄢”这样言简意赅评判得当的历史记述,所谓阐幽发微。后代史家常运用此种笔法,并不是后人的过度解读。
(其实,我窃以为也可能有不得以而为之。众所周知,史笔如铁。然而这样一件极需要执论公允的事情又常会因为犯讳而面临杀身之祸,往往只能是本朝修前朝史,所以才会产生类似于躲避言论审查的用词讲究。)
很多人不区分“读书”一词的内涵,只是简单地以为是获取知识,而不知有修身筑基之说。
如果读书只是从功利效率出发,直接使用Google搜索就行了,有目的性的获取知识,这好像才是最值的方法。
“中国古籍还值的阅读吗”这种问题形式早已在其它地方讨论过好多次,比如有人会问“拉丁文古籍还值得阅读吗?”、“《修昔底德历史》还值得阅读吗?”、“《荷马史诗》还值得阅读吗?”。如果撇去文学修养的需求,还可以换成这样:“《几何原本》还值得阅读吗?”、“《九章算术》还值得阅读吗”、“亚里士多德还值得阅读吗?”,如果历史再跳到五百年后的未来,估计还会有人问:“《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还值得阅读吗?”、“《晶格动力学理论》还值得阅读吗?”
这类问题归根到底其实是这样的一种问题:我们在学习知识时,是否还值得去了解它产生的历史。
对于科学更是如此,数学教科书更是深有此弊病,直接告诉你公式结果,而对于其产生的历史过程我们则知之甚少,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学生没有必要再去了解过去的大师走过的弯路了。
显然,我是属于支持学术与学术史一齐学习了解的。我的论点并不新奇,早已有人论述过。前时读《高观点下的初等数学》与《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时,其中的教育观点更引为知音。
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要问“中国古籍还值的阅读吗”,那就从另一些近代批判书籍中寻找答案吧,以上可供参考。
引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爱心斗士」中一段文字: 让我们首先考察历史,因为在几个方面,历史是教育的核心。这一点无需我来争辩,正如西塞罗所云:“如果你对你出生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这就意味着,你永远只是幼稚的孩童。”只提一点就足以说明历史的重要性:历史是我们“提高觉悟”的最强大的思想手段。不过,关于历史和历史教学还是有一点要强调,因为它们在学校里常常被忽略。历史并非众多必须传授的课程之一;每一门课都有历史,生物学、物理学、数学、文学、音乐、艺术都有自己的历史。我在这里建议,每一位老师都必须是历史老师。比如,只传授今天所知的生物学而不教过去所知的生物学,那就是把知识贬低为纯粹的消费品,那就使学生无缘了解我们知识的重要性,使他们无从知道我们的知识是如何得到的。倘若教学生原子而不提德谟克里特,教电学而不提法拉第,教政治而不提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利,教音乐而不提海顿,那就是不让学生参与 “伟大的会话”。再者,那就是斩断了他们知识的根基。目前,其他的社会机构对知识的本源都不太感兴趣。了解你的根基不仅仅是了解自己的祖父从何而来,不仅仅是了解他吃过什么苦。你还要知道你的思想从何而来,你为何相信这些理念;你还要了解你的道德感和审美体验从何而来;你还要了解你的世界从何而来,而不仅仅是知道你的家庭从何而来。为了完整展示上文开始的西塞罗的思想,我们再引他的一句话:“除非人的生命融入了祖先的生命,除非人的生命置入历史语境中,否则人生又有何价值呢?”当然,西塞罗所谓的“祖先”并不是指母亲的姑母或姨母。
据此我建议,每一门课程都要当做历史教。这样,学生在初小时就知道,知识不是固化的物体,而是人类发展的某一阶段,有过去也有未来;可惜现在的学生不了解这一点。让我们回头说一说创世论的问题,我们想要说明,四千年前产生的思想不仅在时间上传到今天,而且在意义上发生了变化,这些思想从科学变成宗教暗喻,又从宗教暗喻变成科学。古希伯来人在沙漠帐篷里神奇的思辨,和现代麻省理工学院教室里神奇的思辨,两者之间一以贯之的联系是多么亲切、多么深刻啊!我想要说的是,学科的历史使我们学会其中的联系;历史教育我们:世界并不是每天都被重新创造的,每个人都站在他人的肩头上。题外,引用《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一文中的一段话以概述史学对于人文的重要:
一般说来,一个有着道德感的人,自是一个有着内心敬畏感的人。反之,一个内心无所畏惧的人,一个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无信仰者,自是一个缺乏道德感的人。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前者的宗教意识与后者的历史意识,虽对象不同,但功能相近。
有一些中国学者(多为中青年学者)在比较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时,既发出叹息:中国人缺乏宗教感;又发出呼吁:中国人应亲近宗教,应陶冶出宗教感来。
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有些偏颇:
只看到中国人缺乏诚挚的宗教感,未看到中国人富有醇厚的历史感,即能在某些方面替代宗教感的历史感;
只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巨大差异,未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着一些共性,即都有着内心敬畏感。
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简单的事实,就是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并已延续数千年了,不可能不在中国人的心底酿出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只是这种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在今天变得有些淡薄了。
(我们民族通过著史来维系社会公正这一途径,在不同社会层面有不同表现形式,在主流社会有正史,在民间社会有家谱、墓志、说唱……--从略)
根据上述看法,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其他许多看法,至少还可以引申出下面一些看法。
其一,传统中国史学兼容并包事实判断系统和价值判断系统--传统中国最为丰富的事实判断系统和传统中国最为基本的价值判断系统,因而拥有我们民族最为深厚的精神资源。
正因如此,我们民族拥有一句其他民族不大可能拥有的名言:"史不亡国亦不亡",即史为国本,史为民族精神之根本。
宋刻本《后村居士集》、北宋《金粟山大藏经》写本、清文澜阁《四库全书》零等20万页古籍以数字化的方式回归了。这些古籍古迹历史非常久远,时至如今还能回归这中间的困难喝阻碍难以言喻。据了解,这些古籍的数字化回归离不开一位年近七旬老人数年的奔走。那么,这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
这位老人是中央文史馆馆员、四川大学的教授,两年间里,奔走于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让收藏在此的文化古籍可以通过技术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经过这名老学者的不断努力和奔走,终于20万页古籍以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回归并且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这定是有着非凡的信念和坚定的信仰。并且有这么一项技术能够运用在这20万页古籍上,使之以数字化形式呈现,那么在未来肯定也可以运用到其他的文物或文化典籍的恢复和回归上。这不仅是对文化典籍恢复有重要影响,对于科技上来说也是非常显著的一项进步。
当然,我想说的并不仅仅只是这个故事和这项技术,我更想呼吁的是能够有更多的像这位教授一样的学者出现,每个人都应该以中国文化而感到自豪。我们目前古书典籍的修复现状其实是不容乐观的,专业人才的缺失,修复的难度系数高都让这项事业难以前进,我们应该惋惜但更应该珍惜。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其中的文化瑰宝数不胜数,历史长河中消逝不见的也大有其在。但不论是保存至今的还是丢失不见都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并且创造。我们是历史文化的见证者更加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葛剑雄教授曾在一个讲座上说中国古籍能保存至今,是先贤不惜生命代价传承下来。现在,这名年近七旬的教授用行动告诉我们,中国古籍的保存不仅只有先贤的贡献,我们也是同样可以为之做出贡献的。
1、《东京梦华录》,《东京梦华录》是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创作于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是一本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俗人情的著作。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1102-1125)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古籍。
2、《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再现了北魏都城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轶闻,内容相当丰富,书中亦有不少志怪故事,如“法云寺”条中所载之田僧超吹茄、刘白堕酿酒、孙岩娶狐女等。
3、《唐代的外来文明 》,本书选取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朝代——唐代为研究对象,详细研究了当时的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引进。内容涉及了唐朝生活的各个方面,家畜、野兽、飞禽、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品、纺织品、颜料、矿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共18类170余种,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无所不包。此书不仅展现了大唐时期的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的生动画面,为认识唐朝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也是了解中华文明和文明交流史的必读书籍。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本文2023-08-06 22:02:04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360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