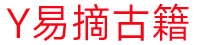竹木简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并普及?哪些古书是用竹木简的?一本书又有多少卷?大约有多重?

竹木简
将字写在用竹、木削成的片上,称“竹木简”,如较宽厚的竹木片则叫“牍”。竹木简是古代用竹简和木简写成的书,是我国最早的书籍。竹子和木头都是常见而易得的东西,古代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在上面写字著书。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每根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多少不一,最多的有40多字,最少的只有一二字,一般写20多字。
现在的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竹木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3尺,最短的只有5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书了。编连竹木简多用麻绳,也有的用丝绳(称“丝编”)或皮绳(称“韦编”)。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现在的“册”字,就是一个象形字,很像一根根简用绳子编连起来的样子。
《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典”指的就是用竹木简做成的书。商代的甲骨文中,也有这样形状的字“〓”,即“册”字。可见,竹木简书籍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了。约春秋、战国之际,还出现了写在丝织品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所以帛书不及竹木简书普遍。东汉时出现了用纸抄写的书籍,纸既轻便又易于书写,价格也比较便宜,于是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代,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戊申年是哪一年
膳夫山鼎历日改写西周元年历史
文/毛天哲
导读摘要:此文直接了司马迁的”元年”说,将改写中国历史。通过膳夫山鼎历日的推求校真,得以证实,周厉王奔彘在三十七年;西周行年数为三年,而不是司马迁所说的十四年。如果一定要为共伯和行政确立一个历点的话,公元前830年才是真正的”元年”。
关键词:元年,膳夫山鼎,铜铭历日,周厉王,奔彘年,前841年,共伯和,三正,金文断代,月相,岁首,年首
㝬簋,亦称厉王簋
周厉王及的纪年是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遗留难题。史家有关周厉王在位年数及行政的相关问题,历来颇多争议,至今未有定论。厉王在位年数,《史记•周本纪》为三十七年,而《卫世家》、今本《竹书纪年》均不足三十年。
所谓”元年”的””二字,司马迁认其为周公、召公相与行政之义,今之史家均已不认同其说。但目前史学界对元年是前841年的说法,还是普遍认同的。
梁启超在1922年所撰的《最初可纪之年代》一文中说:”若采最谨严的态度,当宗《史记》,以西周之元年(注:庚申)为断,其年当西纪前八百四十一年。”
稍微学过点历史的人,应该都记得前841这个特殊的年份,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有了确切纪年,这要归功于司马迁的整理。有人提出,”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这个历史年代概念是怎么来的?根据何在?却似乎一直没有人探究过,令人费解。
其实不难理解,《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明周宣王元年为甲戌年,以西历纪年上推,是可以推溯得出宣王元年为西纪前八百二十七年。而司马迁年表记有十四年,元年干支在庚申,则上推”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正确无疑的。
1904年,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十四年》,将“周召”界定为“贵族”
问题在于,在汉之前的典籍中,”元年”这个概念仅见于《史记》,可以说是司马谈迁父子的一家言说。2003年陕西眉县新出土的铜器群反映出并不单独纪年,这就对司马迁的十四年说,以及断代工程所拟定的西周后期王年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由《竹书纪年》及出土铜铭(至今尚未发现带年号者)来看,年间周王室仍承续厉王纪年,并未废止。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史记》中言之凿凿的纪年,在当时很可能是不存在的,至今也没有十足的证据证明现有的西周晚期器物存在纪年器。
之事,按《史记》的说法是,在周厉王专利山泽之后,国人,厉王出奔于彘,然后有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这个历史叙事,相信为大多数人熟知。但是从目前的史学研究和考古证据来看,所谓行政并不是召公、周公的”二相行政”。
最早把这个问题搅浑的记录是西晋时期出土于河南汲县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称:
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事(原注:号为。)
此说不光存于今本《竹书纪年》,亦见于古本《竹书纪年》佚文中。这就提供了另一个完全迥异的历史叙事,所谓””并不是”二相行政”而是指共伯和执政。《竹书纪年》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官修史书,时代比司马迁更接近西周晚期,所以这一则与《史记》完全不同的记录就引起了史家的重视。
古本《竹书纪年》已经散佚,今辑校本《纪年》不以单独纪年,而是列入厉王的纪年内,这点是清楚的。其文之末虽然也记有”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云云一条,而出自《太平御览》卷897所引”史记”,未必是古本《纪年》本文,王国维先生的校语也只说”《史记》无此文,当出《纪年》”。
司马迁
今本《纪年》则明确无疑地不以纪年,而以十四年为厉王二十六年,亦即厉王实际在位只有12年。李仲操先生认为厉王奔彘前年数为23年,是竹书参考了鲁国世系修正了鲁历公的年数,增加了2年,却把鲁献公的年数错减去了11年。故推至元年,发现周、鲁年数相差11年,而以下的历史纪年已成定论,无法更改,故竹书从厉王奔彘前23年中减去11年,使前的厉王年数变为十二年。(具体见李仲操《周厉王年数释疑》一文)
李仲操先生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哲非常认可。西晋学者在整理汲冢竹书时,势必参考了《史记》等文献。但要指出的是,周厉王奔彘前年数或是26年,这三年的差值 于西晋学者在整理汲冢竹书时的错断。也即周昭王死于十六年,并不是死于十九年。故《竹书纪年》所推,自周穆王以下,龚、懿、夷诸王的在位元年就已经错位了三年。
由此为基点分析,今古本《纪年》所推所记厉王年数盖皆为二十六年。不过因受《史记》十四年说的影响,今本竹书将厉王奔彘前年数移位错订为十二年,将厉王元年误系为戊申年(西历前853年)。如果我们将厉王奔彘前二十六年数,加上司马迁误说的十四年数,则周厉王元年至于宣王即位(含共伯和干政),概有四十年。这就合了《周本纪》厉王三十七年奔彘的说法。
《十二诸侯年表》元年下,记这年当卫厘侯之十四年。参考《卫世家》:”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顷侯立十二年卒,子厘侯立。厘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于彘,行政焉。二,周宣王立。”卫顷侯元年至卫厘侯十三年(厉王奔彘年)共计二十五年,这其中 周夷王年数和周厉王奔彘前年数。按常理,顷侯得立后方能厚赂周夷王,那么厉王奔彘前在位年数下限为十三年,上限至少在二十四年。这和史马迁公的三十七年奔彘的说法就产生了龃龉。
竹书纪年
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这一年份应有来由,它当是汉初尚传的厉王在位年数。从《史记》相关记载可以看出,司马迁并不认为厉王奔彘后年份 于周厉王在位年数。梁玉绳《史记志疑》谓:”按厉王在位之年,汉初已无可考,故史公作表断自。而据《本纪》所书是三十七年流彘,五十一年崩,后人皆从之。”
然厉王在位年数加奔彘后年数长达五十一年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知王在位有四十六年之久,则厉宣父子在位总年数长达九十六年,这是超乎常理的。夏含夷先生质疑认为:”父子相袭,按照常理,父在位长,则子在位就短;子在位长,则父在位就短。”夏先生的这个推说虽然也会存在例外,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司马迁《史记》厉王奔彘时,国人围召公家索太子静。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
但这事经不起推敲。如果厉王奔彘前已在位三十七年,则太子静应已成年。然依史记所言,厉王奔彘时宣王尚年幼,此一不也。
十四年的时间,从年幼到,男子相貌变化是很大的。召公立太子静,则国人能不疑乎?此二不也。
出土㝬簋表明,厉王是个愿意有所作为的,文献金文都记载了厉王曾亲自征伐鄂侯、南淮夷之叛,且北抗犬戎的袭扰,表明了周厉王并不是隔甘于平淡的庸主,共伯和干政长达十四年,周厉王能安心流彘乎?此三不也。
召公谏言周厉王
行政和周公摄政虽然有点类似,但本质上还是有所不同。西周奉行父死子继的宗法制度,父在子不得继位。天无二王,厉王奔彘后,尚在世则宣王不得立(不管长幼)。但天又不可无主,于是畿内贵族就推举了共伯和摄政。以大臣代王行政是权宜之计,史官记录必然还是以厉王为纪年。
周公摄政是因成王年幼不能践祚,故周初确实存在过周公摄政纪年,传统文献和出土铜铭及《竹书纪年》隐约有类似的记载。司马迁或许是参考了周初的情形,才认定厉王奔彘后不在王位,故把厉王三十七年全当做了奔彘前年数。
但凡司马迁能反自检下其所著”卫世家”篇,当能自省其所断之误。所谓”元年”、”周召二相”、”年数长达十四年”说,皆出自司马谈、迁父子的一家之言。传统文献、出土战国竹简、青铜铭文等材料都不支持这类说法,那么有理由相信,元年应该是司马迁为方便整理史料而自定的一个历点而已,他取的就是厉王奔彘后一年。
今学者多认为,周厉王在位年数必是包括了十四年在内的三十七年。如果司马迁”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说确有所据,那么可以推论厉王元年到其去世必然还应再多加数年,这个数年才是共伯和行政年数。司马迁认为有十四年,所以他以宣王元年(甲戌)上推,得出了元年历点在庚申年(前841年)。
问题在于,司马迁何以认定有十四年之久?遍查先秦两汉文献,皆找不到出处。今古本《竹书》中倒有类似说辞,但哲以为,那是西晋学者参考了史记而作的整理,并不是出土文字的原貌。那么,司马迁所自定”元年”历点的正确与否是值得怀疑的。
14年与厉王的37年是该并存接续还是合并,这个问题我看司马迁当时也搞不清楚了,所以陈梦家先生说:”此说史公亦不自信,故其《十二诸侯年表》不始于厉王。”哲以为,厉王奔彘之年距太子静得立,相距时间可能没十四年之久。这个年数超过了孝王、夷王、幽王的在位年数,理论上来说不大可能。
其次共伯和只是代行王事,没资格重建元年,所以共伯和即使执政,颁布的历法纪年应该依然是周厉王纪年,而不应该是从元年开始重新纪年。也就是说,共伯和执政的头一年就不可能是”唯王元年”,至于是周厉王几年,这是一个至今未解的学术难题。
清华楚简《系年》
2008年,清华大学入一批战国楚简,其中首次公布的被命名为《系年》的简书应为楚国官修史书,其中记载的”共伯和代行执政”与《竹年》完全一致。以此可见,司马迁的《史记》在 “周召二相”这点上,确实错了。既然”周召二相说”确定是错误的,那么司马迁所定的元年历点也存在错误的可能。
孤证不立,而另一条历史记录更为哲的这个判断增添了新的证据,也表明司马迁的十四年说并非空穴来风。司马迁可能见过这类相似的材料,但遗憾的是,可能他错解了史料,也可能是误信了。 这一条,楚简《系年》是这样记载的:
至于厉王,厉王大疟于周,卿李(士)、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宋(宗)。
这就很清楚了,在战国时楚国的主流历史叙事中,所谓””就是指共伯和在位的时期。青铜器铭文与魏国、楚国的官修史书同样将””指向了”共伯和摄政”,虽然仍然无法完全否认掉史记的记录,但是也足够有说服力了。
值得指出的是,此条记录中,”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今人多认为是共伯和在位十四年的证据,可佐证史公的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哲以为不然。从文意上理解,此”十又四年”并非指共伯和行政年数,而是指周厉王十四年生宣王,是史官对太子静生年的解释。
假如理解为共伯和当政十又四年,厉王始生宣王。宣王得立岂非在襁褓之中,那是绝无可能的,文献并不支持。今人有这样的误读,哲相信古会存在。这就能解释司马迁公为何不定元年为三年、五年、十年,而偏偏是十四年。
相信战国时楚地流传的这则史料到了司马迁年代,或口头,或文字,一定还有所传续。只是有可能错讹为年数有十四年之久,司马迁采信了这个说法,故才有了”元年”历点的错误推算。
国人 西周
那么所谓的”元年”历点,也就是说,周厉王奔彘之年以及真正的共伯和干政的始年具体在哪一年呢?出土青铜器膳夫山鼎铭文或许能告知我们答案。
膳夫山鼎,通高45、口径42、腹深21厘米,重281公斤。前在陕西永寿县好畤河出土,现陕西历史博物馆。立耳圜底蹄足,口沿下饰重环纹及弦纹一道。铸铭文121字(其中重文2)。
铭文释文:隹(唯)卅又(有)七年正月初吉庚戌,王才(在)周,各(格)图室。南宫乎入右譱(佑膳)夫山,入门立中廷,北卿(向)。王乎(呼)史□令(命)山,王曰:”山,令女(命汝)官(司饮)献人于□,用乍(作宪)司贮,(毋敢)不善;易女(锡汝)玄衣、黹屯(纯)、赤巿(韨)、朱黄(衡)、(銮)旗。”山拜稽首,受册,佩(以)出,反入堇章(返纳瑾璋)。山(敢)对(扬)休令(命),用乍(作)朕皇考吊(叔)硕父(尊)鼎,用(祈)匃眉寿,□□(绰绾)永令(命)霝冬(灵终),子子孙孙永宝用。
膳夫山鼎 拓片
该鼎铭文首句载历日词语,其中年、月、日干支月相俱全,且为长篇记事铭文,纪年又是三十七年,是已知西周金文纪年更高的一例。该件高纪年器物年代的确定,对于西周青铜器以及西周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其确切年代 问题一直有所争论,至今亦无定论,主要有夷、厉、宣三种说法。
陈梦家、日本学者白川静持夷王说,他们是将膳夫山鼎和毛公鼎相对比,认为其属于夷王时器。据哲考证,周夷王在位年数仅有九年,毛公鼎的命书年代确实在周夷王元年,但铸造或在厉王初年。故是说可以排除。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朱捷元、黑光二位先生详细分析了膳夫山鼎的造型、纪年、铭文内容及书体,并且以和其共出的琱生鬲为参照,认为该鼎铸造于周宣王三十七年。虽然其后的刘启益、王世民也信从此说,但对学界的影响不大。
有影响的主要是李学勤先生力主的厉王说。据李学勤先生研究,从如下五方面考虑,可将膳夫山鼎定在厉王期:1)膳夫山鼎形制、纹饰近于宣王初的毛公鼎;2)山鼎铭文字体、格式类似宣王三年的颂鼎;3)山鼎所见图室见于宣王早年的无惠鼎;4)山鼎所见南宫乎作有编钟,钟的形制、纹饰均似厉王未年的虢叔旅钟;5)虢旅其人又见厉王三十一年的□攸从鼎。
李学勤先生认为,厉王执政之年,文献记载有异。《周本纪》以为37年,而《卫世家》、《齐世家》《陈杞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则在14年至24年之间,今本《竹书纪年》仅13年。据晋侯苏钟已知,厉王在位年必超过33年。现据膳夫山鼎37年,可证《周本纪》载厉王37年奔彘说可信。今取厉王三十七年即元年说(为当年称元),查张表,公元前841年,正月建丑壬子朔,初吉庚戌先实朔二日。
西周月相规制蠡测
李说晋侯苏钟为厉王三十三年器,对此哲并不同意。据哲考证,晋侯苏编钟历日正合张培瑜《先秦史历表》中的宣王三十四年,而周历的王正月实际为上年的夏历十三月,真正的年岁是以春王正月起始的。也就是说,晋侯苏编钟铭文历日确实在宣王三十三年(丙午年)。膳夫山鼎历日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后文详解)。
虽如此,李学勤先生对膳夫山鼎的年证,哲还是非常认可的,认为是周厉王器无疑。哲和李先生稍有的分歧点,主要在于该鼎铭文历日的推定上。李先生是以初吉为月朔为推,出发点就是错误的。金文中的初吉概指二、三日,并不在朔日。何况其说”前841年,正月建丑壬子朔,初吉庚戌先实朔二日。”可知铭文历日偏离实朔有二日之多,要说铭文合历谱恐怕过于空疏了。
哲通过多年的研究认为,金文月相不但是定点的,而且是有规律的。朔、望、上下弦月乃月相之四分矣,类节气之二分二至。古先哲以朔不可见,转而以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以代。
生霸死霸即上下弦月,初吉即胐日。因大小月影响,初吉在二日,则既生霸在十日,既望在十六,既死霸在廿四;初吉在三日,则既生霸在十一日,既望在十七,既死霸在廿五。古人制定月相称谓必指月之特定某日,而非王国维所说四分。明白了古之月相的其中关节,则用以考求铜铭历日无不中的。
月相词语各家观点
膳夫山鼎铭文首句已载历日:”隹(唯)卅又(有)七年正月初吉庚戌”。初吉在庚戌,则朔日在戊申或己酉,正月为大月,则初吉在戊申。查张培瑜《先秦史历表》,自周懿王元年(前900年)下查,有三个年份合。一为前897年1月2日,一为856年1月26日,一为前830年1月10日。之一个年份在周懿王四年,自可排除。第二个年份下距司马迁元年(前841)十五年,似有可能。但其距懿王元年(前900年)为四十九年。若以此为厉王三十七年,则懿孝夷三王年数被压缩到12年,故此年份也可排除。
那么铭文历日最有可能是在前830年1月12日。此年下距宣王元年为三年,若以此为厉王三十七年,则年数可视为三年。这样的话,共伯和干政仅为二、三年的光景。这个结论应该是合历史事实的。
毛氏西周断代年表2022 0920
依据毛氏西周断代年表,周夷王元年为前876年,厉王元年在公元前867年,此结论能为铜铭历日校雠确定。如此鼎:隹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可考求历日在前851年11月3日,此器为周厉王器,据此可推周厉王元年。
师询簋也是元年器,铭文历日为”隹元年二月,既望庚寅。”且铭中有”古亡承于先王”,表明此簋所记史实是西周中晚期王位更迭中,某王承位并非是父死子继,而是由大臣力主下得以继承。这样的现象仅发生在周夷王、宣上。搞清此簋的年代则能确定其王世 。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何景成先生对师询簋的年代做过精湛的考证。他认为,西周时期”亡承于先王”的唯有夷王而非传统旧说的宣王。宣王前虽有行政之说,但宣王是在历王死于彘地后嗣位的,并不合该铭史实。故其比较研究后认为,师询簋必是夷王器无疑。
哲对其说深以为然。结合铭中历日以推,既望在庚寅,则得朔日在乙亥。以张培瑜《先秦史历朔日表》查对校真,并结合哲所拟定毛氏西周断代年表,则求得公元前876年2月22日(即周夷王元年周正二月既望庚寅日),正是师询簋所记史实发生之日。
孝王元年可据曶鼎历日:”隹(惟)王元年六月既朢乙亥”,求得在前884年。如此,孝王在位年数为八年,周夷王在位年数为九年。《御览》八十四引《史记》:「周孝王七年,厉王生,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此记载或为史实,则可推厉王12岁即位。
历始革典
周夷王时,王室衰落,且与诸侯国之间矛盾激化。夷王用鼎烹杀了齐哀公,并立其弟齐胡公为新任齐侯,齐胡公继位后将齐国的都城从营丘自己的封邑薄姑。但事后不久,齐哀公同母弟姜山又发动击杀胡公,自立为齐君,称齐献公,把都城从薄姑迁到临淄。此次齐国事变表明,周的权威已大大削弱。
与此同时,周朝的外患问题非但没有被以往的征伐平息,反而愈发严重。尤其是南方的楚国,楚君熊渠叫嚣”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封其三子为王,公然反判周。周夷王面对楚人这一明显的挑衅行为却只能默不作声,毫无办法,只得任其放肆无礼。周厉王即位以后为了扭转王朝江河日下的局面,下定了革除旧典、实行新制的决心,大刀阔斧实行,史称”厉始革典”。
㝬簋为厉王十二祀年器,铭文可谓是厉王的内心独白。此年厉王23岁,作为一个锐意的孤家寡人,面对周夷王留下的烂摊子,难以冲边一群阳奉阴违的既得利益者构筑的藩篱,只能孤独地向祖先祈求力量和勇气。
结合前面所说,”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表明厉王25岁生宣王,至三十七年奔彘时,宣王大致为23岁;三年后被立,为26岁;在位四十六年,则年寿为73岁。周厉王三十七年流彘,三年后崩,自元年即位到崩年为40年,加上在位前11岁,年寿盖为51岁。
需要细说的是,膳夫山鼎铭文历日在前830年1月12日(周正月初吉庚戌),貌似在周厉王三(辛未年),其实不然。
周人年岁的划分亦是以立春日为起始的,铭文历日的干支年是在庚午。和晋侯苏编钟一样,周王正月实际是当年的夏历十一月。西周春秋时期,王公即位皆在春王正月(夏正月),始称元年。夏曰岁,周曰年,商曰祀,所指者同一也,皆从夏正月起算。可见,所谓周王正月,就是当年夏岁的十一月。
《尚书大传》曰:”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所谓三正,实际上是司天者对本年和下年的调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也。夏人是以立春日为一年(卒)始。商认为,确定了大寒日,则可推溯出立春日,故以大寒日为殷正月之始。而周认为,确定了冬至日,则可推溯出立春日,故以冬至日为周正月之始。
逸周书《周月解》说,”周正岁首,数起于一而成于十,次一为首,其义则然。”所以周人取夏岁的十一月间的冬至日为岁首。《史记·历书》有云:”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于终,事则不悖。”这个原则,哲相信在年历的规制中也存在,就是三正的真正含义。
通俗点说,就是金文中的周王正月,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为周王年之始。西周时期,年的概念和我们今人是一样的,是以立春日为年岁之始。我们现在也是以立春日为干支年的始分点,立春日前一日归于上一干支年。
史记周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而膳夫山鼎的历日在厉王三十七年的夏历十一月(周之正月),可以推知,国人就发生在周厉王命膳夫山之后,更大的可能就是发生在周厉王三十七年的夏历十二月间,也就是厉王三十七年周正二月内。
可以定论,《史记》所谓的元年在庚申,是司马迁误信了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年数有十四年”的,由宣王元年上推十四年所得,并非是真实的共伯和干政始年。通过对膳夫山鼎历日的考证校真,证实了周厉王确实在位有三十七年。周厉王三十七年奔彘后,王位三年,由大臣共伯和代执政。周厉王四十年,王崩于彘,在共伯和下,”乃率诸侯会二相而立宣王,共伯归共国。”西周行年数为三年,而不是司马迁所说的十四年。如果一定要为共伯和行政确立一个历点的话,公元前830年才是真正的”元年”。
毛家小子天哲写于浙江金华
二〇二〇年九月初稿
参考文献:
[1]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M]:中华书局,2004290
[2](日)白川静吴卫国译西周断代与年历谱[G]
[3]李学勤 膳夫山鼎年世的确定[J]文物, 1999(06):54-56
[4]李学勤 膳夫山鼎舆周厉王在位年数[J]中华文史论丛, 2011
[5]李仲操 周厉王年数释疑[J] 文博(5期):36-38
[6]张富祥 《竹书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的比较研究[J] 史学月刊, 2006, 000(001):20-28
[7]王宏 膳夫山鼎年代再议[J] 史志学刊,2009(6)
[8]彭裕商 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精)[M] 巴蜀书社, 2003
[9]梁玉绳 史记志疑[M] 中华书局, 1981
声明:本文极具学术价值,由毛天哲 首发于微信 和今日,严禁抄袭或洗稿,有报刊想刊登的可 本人。
简介
以上就是与戊申年是哪一年相关内容,是关于周厉王的分享。看完宣统戊申年是哪一年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
要知道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的错误,首先要了解古书是以何形式流传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
一、古藉简介
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说文》:“古,故也。”故古籍又称故籍、故书、载籍等。古代文献,最早见载于甲骨、金石,“甲骨卜辞”也称“殷墟书契”。作为最早的正式书籍,为用竹木及缣帛记录文献之简牍、帛书。晋太康二年(公元280年)汲群魏襄王墓出土之《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之《秦律》等简策,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老子》、《经法》、《战国纵横家书》等帛书,为传世之最早古籍。汉代纸问于世,遂有手抄、唐写、宋元明清刻印书籍。据国务院古籍小组的规定,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断限,凡辛亥革命以前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通称为古籍。据古籍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贩书偶记》以及佛藏、道藏、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录等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10万多种。
二、古籍类别与版本
善本: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又,珍贵难得之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亦称为“善本”。
孤本:仅留存一份之书本。一部书之某一书本,未刻之手稿,碑帖之旧拓本,在现世间仅有一份流传者,均可称为孤本。
蓝本:谓著书或刊书所依据之旧本。《居易录》:“今方修一统志,似当以旧通志为蓝本。”凡是重刊或校勘,必以最精之本子为蓝本。
刻本:又称“椠本”、“刊本”,雕板印成之书。我国雕板印书始于隋唐,至宋而大盛。按刻书之不同情况及刻本之不同类型,可分各种不同型式:以时代区别,有宋、金、辽、元、明、清刻本;以地域区别,有浙江、福建、江西、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各地刻本;以刻书者区别,有官刻、私刻、坊刻等;以版式区别,有九行本、十行十八字本、四周单栏本、左右双栏本、竹节栏本、白口本、黑口本、两节本、袖珍本、巾箱本等;以字体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宋体字本、软体字本(亦称写刻本)、篆字本、梵文本、满文本、满汉文合刻本等;以墨色区别,有朱墨印、几色套印等;以纸张区别,有皮纸本、麻纸本、棉纸本、竹纸本、开化纸(亦称桃花纸)本、宣纸本、毛边纸本、毛太纸本、罗纹纸本、连史纸本等;以装订形似区别,有经折装(亦称梵夹装)本、旋风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毛装本、金镶玉本等;以刻书先后区别,有原刻本、重刻本、仿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以内容及价值区别,有足本、残本、增订本、删节本、繁本、简本、批点本、评本、单疏本、集解本、重言重意本、纂图互注本、绣像本等。
祖本:一种书最初刻印之本。一种书在不同时期往往刻有多种本子,难免产生讹误,而祖本则保持其本来面貌,因此为人所重。
原本:第一次写成或刻成之书本。为对增订、修改和重刻、改版而言。原始稿本和最初刻本与增订、重刻之本往往有很多不同。可供查考一种著作之发展过程。
定本:一书之最后确定之本。指自己编撰或整理前人之著作,在一定时间内,已经整理完毕,最后确定,准备发表之本子。
副本:同一书籍抄出之副本。为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稀见图书,依样重写,储作副本。《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书三阁,限写五十副本”。今亦指国家对内或对外文件之正式签署之副本,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别本:同书同一来源之另一本子。亦称“副本”。《南史·刘孝绰传》:“又写别本封至东宫。”又,同书另一来源之本子。亦称“异本”。因所根据之来源不同,内容也有出入。如:书有《别本十六国春秋》,帖有《黄庭坚别本》。
仿刻本:摹仿原版字体版式刻印之书本。宋无刻本,多以擅长书法者上版,加之雕印精湛,明清两代刻书往往予以摹仿,故有“仿宋本”、“仿元本”之称。
影刊本:照原书版式影刊之书本。珍贵之古籍,为存原书面貌,以适应研究之需要,清乾、嘉以后,常用影刊方法加以传布。如黄丕烈所刻《士礼居黄氏丛书》,其法大都先照原书影摹,然后上版开雕。摄影术发明后,亦有用原书照相雕版者。刻成之后,与原刻相仿,精工者几难识别。自影印兴,影刻之书渐少。
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之书本。习惯称唐以前为“写本”,唐以后称“抄本”。宋以后,雕版虽以盛行,但抄本与之并行,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皆为抄本;有些较为专门或需要不广之著作,仍靠抄本流通。更有抄书者系著名藏书家或学者;除书之内容外,其手迹也值得珍重。故抄本图书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藏书家以精抄本与宋元刻本相次比。对于不详年月之抄本,约在清嘉庆以前者通称“旧抄”,晚清者称“近抄”,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对于确定为明代或清代之抄本而无从断其年月者,则统称“明抄”或“清抄”。
朱墨本:用朱、墨两种颜色套印之书本。最早为元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之《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沿至明末,吴兴(今湖州市)闵齐吉、凌檬初两家盛用两色套印,墨色印正文,朱色印评语及圈点。
珍本: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类别科学价值之珍贵罕见之写本或刻本。
初印本:书版刻成后第一次印刷之书本。特点是字画清晰,赏心悦目,故为藏书家与读者所重。
后印本:历次再版印刷之书本。其字迹漫漶,版断框歪,墨色暗淡,故不受人喜爱。
重刻本:一种书重新刻印之本。相对原本而言。不但字体版式与原本不同,在文字内容上也往往有所修改,多在序文凡例中加以说明。
道藏本:根据道藏刻印之书本。同样,佛经中亦有“碛砂藏本”、“嘉兴藏本”等称呼。
卷子本:用卷轴装订之书籍。唐以前抄写书本均用长幅纸,卷成一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状,收藏家谓之卷子本。”
百衲本:用百种不同版本之残卷零页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之书本。“百衲”取僧衣破敝补缀之称。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百衲本资治通鉴》、《百衲本二十四史》。
残本:内容残缺不全之书本。
配本:一部书因有残缺,用其它版本之同一种书予以配全,故称。
三朝版:经过三个朝代修补之书版。南宋杭州国子监,所藏各种书版多有残缺。元朝时,将这些版片转入西湖书院,加以修补印行。至明洪武八年,书版又移至南京国子监,再次进行修补印刷。对这部分递经宋、元、明三朝修补之书版,后人称为“三朝版”。
活字本:用活字排版印刷之书本。活字印刷为宋仁宗庆历时(1041——1048年)毕升所发明。其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使坚,排版印刷。为中国之伟大创造,早于欧洲活字印刷400多年。元代又创木活字。明弘治时创铜、铅活字,为我国近代铅字印刷术之前导。
影印本: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方法印成之书本。有胶印、大石印、珂罗版(即玻璃版)印、铜版印等。稀少、罕见之图书资料,为研究之需,常用原书影印,以广流传。
石印本:以药墨书写于特种药纸上,用石制版印刷之书本。用摄影制版石印之书,则称“大石印本”。
排印本:用活字排印之书本。为区别版本,通常称铅字排印之书为“排印本”,而其它活字排印之书则分别称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等。
拓本:即摹拓金石彝器碑碣印章之本。用红色拓者称“朱拓”,黑色拓者称“墨拓”,最早拓者称“初拓”。初拓字迹(或图案)清晰,墨色匀净,较为珍贵。
稿本:即作者之原稿。作者亲笔写定者称“手稿本”,经过整理誉清者称“清稿本”。
影写本:用纸覆于原书上影写成之书本。其点画行款,一依原本。一般专指影写宋、元善本,如明末常熟毛晋及古阁据宋本影写,非常精工。
校本:根据不同本子和有关资料核对过之书本。取某书之一本子作底本,搜罗一种或几种不同本子及有关资料相核对,发现其讹误衍脱,即在底本上加以批注。如只传抄他人所校,则称为“过录校本”。
内府本:明、清两代宫廷内部刻印之书本。校勘,刻印,都较精良。清昭梿所撰《啸亭杂录续》有内府刻书目录一卷,可资检览。
藩刻本:明代分封各地之藩王所刻印之书本。因有些藩王、子孙及其门客颇有学问,而且刻印之书所据底本多为御赐宋、元善本,故其版本价值较高。
聚珍本:清代以木活字排印之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后来中华书局创制仿宋体铅字,就名为“聚珍仿宋版”。
闵版: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蒙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所印之书。其选择经、史、子、集各类凡士人习用书籍,专辑前人评论批点,使用方正宋体字和优质白纸,作朱墨两色或兼用黛、紫、黄各色套印,后人称为“闵版”。特点为词义显豁,脉络分明,行疏幅广,光彩夺目。近人武进陶湘,编有《明吴兴闵版书目》。
麻沙本:南宋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书坊刻印之书本。因该地盛产榕树,木质松软,易于雕版,故书坊集中,于当时图书流通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书贾射利,校勘粗疏,刷印低劣,故《石林燕语》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说。
蜀本:四川刻印书本之总称。宋代眉山为四川刻书中心。刻书多为大字颜真卿体,故又有“眉山本”、“蜀大字本”之称。
浙本:浙江刻印之书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衢州本、台州本。宋代浙本大都字体方整、刀法圆润,为宋版之上品。
闽本:亦称“建本”,即福建刻印之书本。又分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
宋本:宋代刻印之书本。雕版书至宋代而大盛,杭州、建阳、眉山等都为当时刻书中心。公私所刻,有监司、家塾、坊肆等。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多仿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白口居多,至南宋中后期出现细黑口;避讳较严。所印书籍,校勘精审、雕印精美者颇多,往往为后世刻本所依据,为学者所重视。
金本:金代刻印之书本。金代雕版中心在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其地产纸丰富,书坊很多,设有管理出版机构。所刻著名者有《刘知远诸宫调》、《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此外,山西运城所刻之《藏经》及河北所刻之经书、音韵学书,也颇有名。
元本:元代刻印之书本。元代雕版中心在杭州、建阳、平水等地。公私所刻,无论校勘与雕印,不乏精品,堪与宋本媲美。其风格、字体大都摹仿赵孟頫书法,扁方圆活,常用简体字,黑口、双鱼尾居多,初期行字疏朗,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趋向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
明本:明代刻印之书本。明代雕版之普遍,出版量之庞大,前所未有。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为明代雕印技术发展之辉煌成就。但有些刻本校勘不精,删节不当,甚至妄改书名、伪造古书,后人多有批评。明初刻书犹沿元代风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间,出现仿宋风气,白口为多,字体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显得板滞。万历以后,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直重;部分家刻及坊刻本出现软体字,较为美观。
高丽本:亦称“朝鲜本”,指朝鲜刻印之中文古籍。我国印刷术很早传入朝鲜,朝鲜刻印之书流入我国也很多。无论刻本或活字本,均为软体大字,皮纸精印,书品宽大,醒人眼目。
东洋本:亦称“日本本”,即日本刻印之书本。我国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其次为日本。日本所刻古籍,多用美浓纸精印,近似朝鲜本,但在字体与装订等方面,下朝鲜本一等。有些书行间注以平假名或片假名,较容易识别。
越南本:越南刻印之书本。越南之印刷术也从我国传入,故刻印风格及装订形式与我国基本一致。流入我国之书籍,大都在相当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刻印,未见有更早印本。
官刻本:历代各类官方机构刻印之书本。如宋代秘书监、转运司、茶盐司、公使库、郡庠、县斋以及州府县学,元代国子监、各路儒学、府学、兴文蜀,明代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所刻之书,都属于官刻本。
监本:历代国子监刻印之书本。监本始于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命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以后国子监都印图书,以经、史为主。明朝南北两京设立国子监,都有刻书,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称。
家刻本:私人刻印之书本。亦称“家塾本”。私家刻书为宋代以来雕版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校勘、刻印俱精,版本价值颇大。其中著名者,如宋陆遹刻《渭南文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元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明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清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等。
坊刻本:简称坊本,指书铺刻印之书本。因以营利为目的,一般雕印不如官刻本之精,校勘不如家塾本只审。但也因地因人而异,如宋代临安陈氏书棚本,校印精湛,极为人所重;福建麻沙本,讹误较多,人多不贵之。因坊刻本面向大众,许多医书、民间文学赖以流传,故颇受人们喜爱。
三、主要错误
辑佚(缺失):由于古藉承载物有甲骨、简、金石、帛等形式,在某种情况下都会受到损坏,造成句字缺失,甚至整本整卷残缺不全,虽然后人会整理出“辑佚本”,辑佚本几乎一定会有错漏、误解。辑佚可能是古藉传出错最大的原因。有时不是整段缺失,会少写少抄一字,往往被称为“脱字”。
错字(别字):古人在誊刻、誊写、排字等过程中由于疏忽、误读、误认、通假字等原因造成错字。有些错字是关键字眼,甚至会造成后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四中提到:“朱淑真词,自来选家列之南宋,谓是文公侄女,或且以为元人,其误甚矣。淑真与曾布妻魏氏为词友。曾布贵盛,丁元以后,崇宁以前,大观元年卒。淑真为布妻之友,则是北宋人无疑。李易安时代,犹稍后於淑真。即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沈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池北偶谈谓淑真玑图记,作於绍定三年。绍定当是绍圣之误。绍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隶辇毂久矣。记云:‘家君宦游浙西。’临安亦浙西,讵容有此称耶。”由上文可见,绍定是绍圣之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这也是一个古藉出错的主要原因。
误解:中国文字几千年来词意变化很大,早期古文又十分简练,会造成后人在阅读时产生不同的理解结论,如果流传载体同时有缺失,后人在整理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误解。
张冠李戴:同在以上《蕙风词话》同一卷中,指出欧阳修的一首词误入朱淑真集。
以讹传讹:古人读书人少,写书人更少,当一专家泰斗在书中写出错误结论时,很少有人去怀疑其正确性,后人引用此论,导致以讹传讹。
标点错误:古书没有标点,后人在标点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理解,不一定是古人的愿意,甚至有可能完全是相反的意思。
标音错误:在校勘过程中,注音也是工作内容之一,校勘者对原文注音的理解不同,也会造成一定错误。
年代错误:对古藉出现、整理或作者生存年代的误认。
以上为几种主要错误,由于本人不是这方面专家,只是对此感兴趣的“票友”,答案不能作为专业使用,仅供参考。谢谢!
在下认为我们应该补习繁体字,港澳台地区的同胞应该补习简体字。
我们由于长年用简体字,一时间再学习繁体字有问题。可我们不一定要会写繁体字,只要会看就行了。
我们看TVB的连续剧时,时繁体字字幕的。当引进到内地时就变成简体字字幕了。这大可不必,反正已经配音配成普通话了,大多观众也不太需要看字幕了,那内地的电视台大可保留原有的繁体字字幕使得我们久而久之,潜移默化中,能“看”繁体字就行了。就好比我们在内地看凤凰台、TVB、ATV等港澳台电视台时,他们都是用繁体字的,只要我们会看了,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们在引进港台书籍的时候,可以审查,可以删减,但应该保留原著的繁体字印刷嘛,反正现在都是电脑印刷的,不存在什么技术问题。保留繁体字印刷,可以最大限度保持书籍的完整性嘛。(不会出现现在大陆唯一的繁体字书籍是中华书局的古籍)。
同理,港澳台地区引进内地书籍或内地电视剧时,都保留简体字字幕,使得港澳台同胞能渐渐接触和认识简体字嘛。
长此以往,就算两岸三地的官方用字维持不变,但三地群众在文化交流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因用字的问题而产生的隔膜了。“繁简之争”的问题也不存在了。那时我们也大可答应台湾,共同编著一本中华大辞典了。
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