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遗民谈迁历尽千辛万苦变成的史书 差点就被清朝给乱改了

满清于1644年入关,第二年,就嚷嚷着说要纂修《明史》。
可是,这部书,直到乾隆四年(1739)才正式刊行。前后历时九十四年,成为了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例!
花了将近百年的时间修史,可知其灌注心血之多、打磨力度之巨,用功之精细。
毫无疑问,从书的总体质量上来说,《明史》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洁,编排得当,完全称得是二十四史中的上乘之作。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颇为客观地评价说,“《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 《金史》呢,虽然“行文雅洁,叙事简括”,也只是“稍为可观”而已。要论“完善”,没有一部比得上《明史》。
不过,作为一部官修的正史,《明史》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清廷统治者一向自诩大清得天下为历朝历代最光明正大者。以雍正皇帝为代表,其颁行的《大义觉迷录》曾将汉魏晋唐宋元明贬了个遍,说汉朝是建立在死人堆上的,魏晋唐宋都是欺负孤儿寡妇篡位而来,元呢元灭宋,那是 裸的强盗行径;而明本是元之臣民,臣民犯上,雍正愤然骂道:“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对于大清得国,雍正正气凛然地说:“赶出明之主人者,流贼李自成也。我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
基于清廷统治者这一说法,由清廷统治者牵头编修的《明史》就出现了最大的一个缺点:不仅完全隐没了建州女真先世与明朝的臣属关系,也完全隐没了清入关之后南明弘光、隆武、绍武、永历诸朝廷存在之事实。
老实说,自古以来,以后代修前代史,凡涉及到新朝与旧朝之关系,免不了要有所掩饰,但象《明史》这样“一隐没而遂及一代史(建州史)之全部”的,绝无仅有。
单就这一点来说,后人要研究明史,特别是要研究满洲的兴起及清军入关前后等等历史问题,就必须参考其他著述。
但是,经过清廷血腥文字狱的摧残和洗劫,这样的著述已经是百不存一了。
大历史学家吴晗在《灯下集》曾提到自己做这方面工作时的艰辛,说:“二十五年前,我在北京图书馆读《明实录》,抄朝鲜《李朝实录》,想从这两部大部头书里,找出一些有关建州的史料,写一本建州史。因为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这三百年间的历史都隐没了,窜改了,歪曲了,为的是好证明清朝的祖先从来没有臣属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进一步强调建州地区从来不属于明朝的版图等等政治企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把明人有关建州的真实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办法多种多样:一种是毁版,禁止流通;一种是把书中有关地方抽掉,弄成残废;一种是把有关文字删去或改写。推而广之,连明朝以前有关女真历史的著作也连带遭殃,不是删节,便是被窜改了。这样做的结果,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中期这一段期间的建州史实,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成为空白点,我们对建州的社会发展、生产情况、生产工具、社会组织、风俗习惯、文化生活、部落分布等不是一无所知,便是知道的很少。这是个历史问题,应该解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吴晗先生把《明实录》翻来覆去地读,读出了许多困难;没办法,只好下苦功,用笔抄,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抄出有关建州和中朝关系的史料,一共抄了八十本。
后来,吴晗偶然触及了一本堪与《明史》相媲美的明代史书——谈迁的《国榷》,不由得激动万分地说:“由于当时(《国榷》)并未刊行,因而也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乱改。……对研究建州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
《国榷》是一部编年体的明史,按年、月、日记载明朝一代的重要史实,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凡四百三十万字,记叙了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
书中对《明实录》中避而不谈的明朝史实敢于直言不讳,对建州女真的史实也不回避、不掩饰,全部如实地加以叙述。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也在《明实录》没有记载的情况下,尽力根据邸报、方志、其它史家著述,以及一些官吏、遗民的口述,加以补编,使有明一代的历史达到了相对的完整。
就因为《国榷》没有印本,得以避开了“四库馆臣的乱改”,成为了现在研读《明史》的重要补充。
1958年,海宁张宗祥根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还有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互相校补、勘正,交由古籍出版社分精装六册出版。
吴晗欣喜地说:“想望了二、三十年,如今头发都白了中华书局排印了这部六大厚册,五百万字的大书,怎能叫人不高兴,不感激,不欢欣鼓舞!”
可以说,《国榷》的刊行,是一件史学界的盛事。
则《国榷》的著者谈迁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九泉矣。
明清以降,私人撰修国史之风长盛不衰。单就嘉靖至万历年间,就有邓元锡的《明书》,薛应旃的《 录》,郑晓的《吾学编》,陈建的《皇明通纪》等等。
谈迁此人,“生平无他好,惟好书”,尤其喜爱子史百家之言。他在翻阅了上述史家著述之后,深感这些史书见解肤浅,史实错误,观点荒谬。而他在研读《明实录》时,也发现了很多记载并不完全可靠,甚至还有许多缺漏及掩饰之处,便立志要写出一部明朝信史留传后世。
原本,谈迁也参加了好几次乡试,但次次铩羽。有了著史之想后,就彻底抛弃了科举仕途,博集群书,披阅采摘,专心于历史的编撰。
谈迁家境贫寒,既无钱买书,借书不容易,却凭坚忍不拔之志,六易其稿,写成了元末明初到天启朝的历史初稿,共一百卷。谈迁自称“集诸家之书凡百余种”,勒为一编,名《国榷》。但谈迁并不满足于此,多方结交文友,利用一切机会收集史料,对原稿进行修改和补充。
该过程中,对谈迁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张慎言、高弘图。
张慎言时任南京吏部尚书、高弘图时任南京户部尚书,想那谈迁不过一个落第秀才,但张、高二人并不以世俗眼光相待,反而十分赏识谈迁的才学,“相与为布衣交”。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十三日,京师失守的消息传到南京,留守南京的大臣方寸大乱,一时不知所为。
谈迁撰史治史,眼光自然高出常人许多,连夜上书高弘图,建议派员急往淮阳阻止发往北京的漕舟。
福王朱由崧监国,谈迁又及时地指出南京礼部主事吴本泰所制《监国仪注》的种种不当。
张慎言认为谈迁高才有识,很想推荐他为礼部司务;高弘图也想荐谈迁任中书舍人,但谈迁却以自己不过一介布衣,不忍乘“国之不幸”博求官职,断然拒绝,只在高弘图幕下担任记室。
不久,高弘图遭马士英等人排挤,谈迁建议高弘图辞去。
次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克扬州、镇江,南京危急。
谈迁跟随高弘图前往杭州劝浙江巡抚张秉贞、总督张凤翔抵抗清兵。看到张秉贞等人口不言兵,谈迁知事不可为,便告别了高弘图,回到海宁家中,一门心思著述明朝历史。
明亡以后,为完成崇祯、弘光两朝历史,谈迁不遗余力地寻访明朝降臣、遗民、阉宦、贵戚等,大量查阅邸抄、见闻,使一部《国榷》成为完备的编年体明史。
这其中,发生了一件让人撕心裂肺的事: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已经成书的《国榷》竟然被小偷偷走!
谈迁欲哭无泪、悲愤莫名。
没办法,只好咬着牙,从零开始,重新再写。
在重写第二稿过程中,谈迁得到了朱之锡、吴伟业、曹溶、霍达等人热情帮助。《国榷》所记史事也在一改再改中不断求真。
1657年,《国榷》终于写成。
也在这一年夏天,谈迁西游平阳(今山西临汾),专门到好友张慎言墓前祭奠。
张慎言在弘光朝覆灭后不久便含恨病死,棺柩安葬在故里山西阳城。
原本,谈迁还想撰写一部纪传体明史,但到了平阳,已是寒冬,年事已高的他突感风寒,于该年十二月十二日病逝于平阳旅舍,终年六十有四。
校勘古书不能轻易更改古书内容,否则,古书会失去原来的面貌。
中国具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华文化的传承除通过传统习俗的传承,最主要是依靠图书的传承,古代图书起了重要作用。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大量中华文化的灭失,而不能往下传承。清朝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图书会出现版本不同、破损等现象 ,需要后人对其进行校勘。古代图书的校勘,应该以保持图书原貌为原则,不能轻易更改图书内容。如果确实需要更改,应该在注释等相应位置进行说明,说明更改的依据是什么,以免产生歧义、以讹传讹等现象。
例如,由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在收录《论语•季氏将伐颛臾》一文时,有一句“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虽然出现文字互误,但是没有进行更改,而是以注释的形式进行说明:这两句文字互误。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初六”按:寡、贫二字,传写互易,此本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贫‘以财言,’不均‘亦以财言?不均则不如无财矣,故’不患贫而患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不安不如无人矣,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可据以订正”。
如果你的顺利传承指的是大公子扶苏即位,那么的确大秦的文学会与众不同,扶苏先是以贤人的形象出现,因其反对焚书坑儒,而被秦始皇派往上郡监军,希望他能够行事果敢,扶苏不负秦始皇所望。若是他能够成为帝王可开真正的大秦万世基业,儒家的文化必有一席之地,因为儒治是帝王权力的工具,从伦理纲常上制约官员的行为;法治不可缺,大秦以此强国定天下,更何况李斯不会同意,他本人也是在法家的环境下长大的;道家的无为而治不适合在帝国诞生之后的前100年出现,四百年的分崩,人心不是那么容易积聚的,所以道家文化是不会在朝堂上出现的,黄老之学如果兴盛,那么大秦蜀中和汉中及关中的统治基础就会薄弱,因为大秦的士兵之所以会悍不畏死,是因为军功的累积是出人头地的保障,在生产技术并不发达的先秦时期,道家与黄老之学的兴起无疑会使普通人失去生活的目标;由上述总结,诗经的诗歌会继续传唱,其内容应涵盖大秦的人民歌颂扶苏的仁政,始皇威武的军功。
阅读文学古籍,也可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相结合。古籍是传统文化的载体,非物质文化则是靠记忆和口头传承的艺术或技能,二者往往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在阅读宋元话本的时候,就借助于听书的经验,解决了一些困惑的问题。现存的话本或详或略,或雅或俗,总的说都不会是实况录音的记录。因此有的被认为是拟话本,如鲁迅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宣和遗事》的判断。有人认为话本只是故事的代称,如日本的增田涉等学者。还有人不承认宋元话本的存在,认为都是明代人改写的小说。其实,说话人一般有底本,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北方的评书艺人,把提纲式的简本叫做“梁子”,把语录式的繁本叫做“册子”,但也不会是实况的记录。如现代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岳飞传》的时候,每天要写上万字的稿本,但还是要加上许多临场发挥。我在参观苏州评弹博物馆的时候,注意到收藏的弹词话本,一般只有唱篇,没有表白;有的虽有表白,也很简略。也有已整理成书的,一般也不像场上说唱的那么详细生动。
当然,也有老艺人自己整理成比较详备的底本,或徒弟继续加工的繁本,那是很少见的。例如苏州评话老艺人陆耀庭和顾宏伯,都有说《三国志》的脚本,是自己编写的抄本,都把一部分脚本送给了学生王忠元。王忠元自己又整理了一个脚本。2015年5月18日,王忠元遗孀华琦把三种脚本都捐赠给了苏州评弹博物馆,成为一时佳话(何兵《留住名家珍贵史料,三部手稿展现戏痴情怀》,据《古代小说研究网》转载2015年5月20日《姑苏晚报》)。师父整理了自己的底本,最后送给了徒弟,这是曲艺界常有的事,有些话本大概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因此就有了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形成了世代累积型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到宋元时期的特定背景,文化重心逐渐下移,特别是元代一度停止科举,文人没有出路,走向民间,出现了不少书会才人。他们为艺人编写脚本,杂剧、散曲是大宗的,都见于《录鬼簿》。但编写话本的只见陆显之《好儿赵正》一例。“腹笥有文史”的朱桂英女士,讲的是“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则是讲史家(见杨维祯《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但有无话本留传,亦未可知。现存的《宣和遗事》则是收集了许多史料的一部话本,编者掌握不少史传和诗词的资源,文化修养较深,应该说是当时的“才人”。但《宣和遗事》可能并未全部付诸场上演说。我认为这也是话本的一种类型。因此我提出了讲史平话的多样性问题,对古代作品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但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有些艺术性不强的本子,却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意义,如《宣和遗事》就是。
清代的话本如《清风闸》《飞跎子传》也是艺人自己整理的,但比较简略,又没有才人帮他润色。俞樾虽然对《三侠五义》作了一点修改,但没有仔细加工,所以没能像《水浒传》那样成为杰作。
苏州评弹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许多世代累积型的话本和多种流派的唱腔。我作为苏州评弹的老听客,很关心它的保护和传承。在探讨近体诗的格律及吟诵问题时,觉得苏州评弹在雅化和格律化的过程中,曾深受近体诗的影响,特别是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珍珠塔》和马调系统的唱腔,最能体现传统的吟诵方法。因此写了《苏州评弹与格律诗的吟诵》等文章,希望能以吟诵的方式来扩展传统诗词的传承,包括对诗词格律的普及。另一方面,也希望苏州评弹的艺人,能继承并发展前人的经验,适当借鉴传统诗词的格律,提高评弹的艺术性。反过来,吟诵家也可以借鉴曲艺家的唱腔,适当改进吟诵的音乐性。例如平起式的七言诗,如果结句是“平平仄仄仄平平”的,在苏州评弹里一般都是在第六字上延长行腔,而在第七字时却很快收束,与其他剧种大多在末字上延长行腔迥然不同。我觉得近体诗的吟诵,也可以适当夸张第六字的长音,显示“二四六分明”的平仄反差。最近在电视上听到上海陆锦花女士指导、培养的小学生,用苏州评弹唱腔吟唱的唐诗,比较准确地体现了平长仄短的声调,也很好地给少年儿童传播了古典诗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诗教方式,值得重视和提倡。
“常州吟诵”已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赵元任先生的吟诗方法为代表的。在目前百花齐放的吟诵流派中,我认为“常州吟诵”可以代表吴语地区及大多数方言地区的传统吟诵方法,以“平长仄短”的声调和两字节、三字尾为基本节奏,是和近体诗的格律相适应的,完全可以作为“非遗”保护并传承下去。其他流派的吟诵,是否分别列入“非遗”,还有研究讨论的必要。至于以音阶高低为艺术手段的歌唱方法则是在探讨和试验中的创新,同样可以为传统诗词的传播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本文2023-08-06 23:27:17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36805.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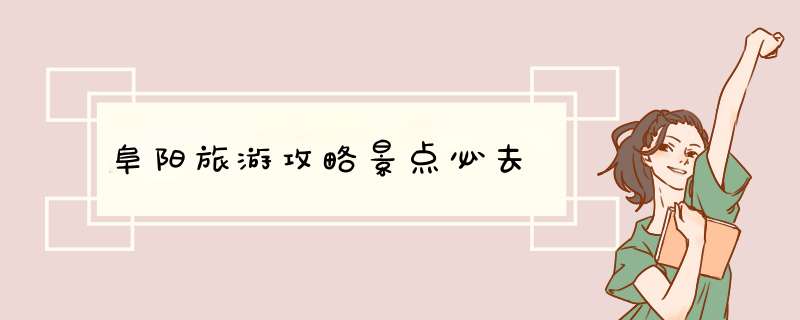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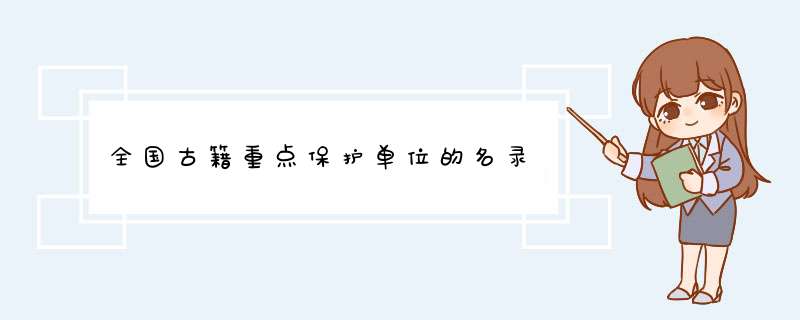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