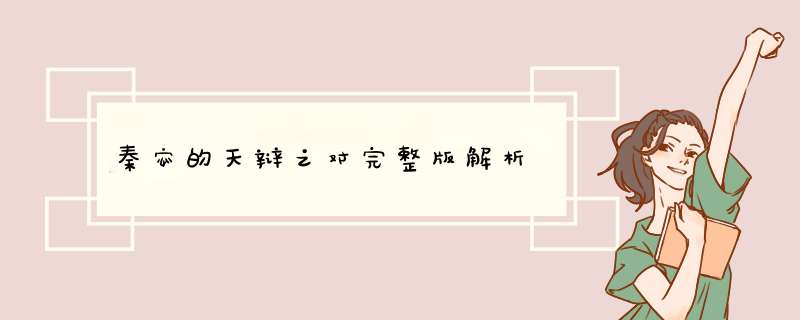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是否参考了中国古籍

记得2013年《读库》某期中有文章提及,但记得是“受XXX思想影响”,而不是科学研究和学术写作意义上的完全的参考。你再找找民国期间,严复翻译英国科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部分(《天演论》)一书和他人评价时好像也提及。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达尔文在奠定进化论、论证人工选择原理的过程中,曾参阅《本草纲目》,并将其称之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
“老实话好听”,建议搜一下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之类的资料。
liuxue86com 2012年11月30日 10时讯 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为英国主要汉学研究重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剑桥大学、以及牛津大学)之一。剑桥大学卓越的研究机构、丰富的典藏资源、以及优秀的汉学研究学者,为英国的汉学研究注入了新生命,也充份展现了剑桥大学汉学研究的历史及优良的学术传统。剑桥大学主要汉学相关书籍,分别收藏于以下机构: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Chinese Collec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东方研究院图书馆(Faculty Library, 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及同位于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等等图书馆。本文将重点介绍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要珍贵的收藏。
剑桥大学图书馆为世界知名大型图书馆之一,而其中的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所收藏的汉学文物,不仅为世界上少有的珍藏,数量上也同样非常惊人。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所收藏的珍贵文物,包含了为数丰富的十三世纪甲骨文、各类善本珍籍、手抄本、手稿、绘图、拓本及其它重要文物。
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所收藏的第一本中文书籍,为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于1632年赠与中文部的藏书。之后,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更获得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威妥玛(Thomas Wade, 1818-1895)所慷慨捐赠的4,304本珍贵中文书籍。这些中文书籍,为威妥玛教授于中国担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等等职务时的四十年间,陆续获得的私人收藏。这些书籍主要为历史、法律、外交类书籍,同时也包含了许多宝贵的善本珍籍,如十七世纪《明实录》手稿(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Ming Dynasty)、十五世纪的《异域图志》(Illustrated Chronicle of Strange Lands)等等。
二次大战后,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的中文藏书为洛克哈特爵士(Sir J H Stewart Lockhart)、阿拉巴斯德先生(Ernest Alabaster)、汉学教授莫尔(Arthur Christopher Moule)、汉学教授哈隆(Gustav Haloun)所拥有的私人收藏捐赠及采购。1952年获得由金璋先生(L C Hopkins)捐赠生前收藏的约八百多片甲骨文。因这些甲骨文皆承载了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目前为剑桥大学图书馆内最古老的典藏文物。
此外,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的珍贵收藏还包含清德宗于1908年赠与伦敦中国协会(the China Society of London)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Imperial Encyclopaedia)。《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规模最大也最完整保存的类书(注1),由清康熙年间即开始编撰,至雍正四年编成,并开始排印。《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收录了清初以前历代典籍,总数约有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除文字记述外,也包含了大量的附图及图表,图文并茂,实为汉学家查询古代文献重要的依据。《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依分类及主题编目,主要结构包含三个层次:「汇编、典、部」。其中,「汇编」分成六大类,包含历象汇编(记天文、历法等)、方舆汇编(记地理等)、明伦汇编(记百官、家族等)、博物汇编(记动植物、农业、医学等)、理学汇编(记经学、文学等)、经济汇编(记教育、经济、律法等)。汇编以下,还分类成32「典」,以及6117「部」。由于分类清楚详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可视为查询汉典古籍文献的百科全书,不仅为汉典古籍集大成之作品,也成为汉学学者经常使用的查询工具,为一优良的索引工具书。
而近年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也持续从国际其它机构得到的许多慷慨赠书,例如于1986年,大陆捐赠4,468册中文书籍。1988年,台湾故宫博物院捐赠了重要古籍-《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Imperial Compendium of Literature)共五百册。《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为撷取《四库全书》中菁华所编汇而成。由于《四库全书》为清乾隆三十八年开始修编,但高宗已届高龄,唯恐生前无法目睹《四库全书》的完成,故下令将《四库全书》中菁华部份(约全书的七分之一)编汇成《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荟要》共有手抄本两部,一部已于英法联军时被烧毁,另一部置放于摛藻堂供高宗阅读,后由故宫博物院典藏,为现存海内外唯一孤本。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收录菁华全书的部份,除了较《四库全书》更加简约菁粹外,也因其本质为「专供御览,毋须钻营于不利清廷之思想着作之芟减汰除,更能保存原书内容之真实性」(注2),至今仍为汉学学者研究古籍的重要参考依据,拥有极高的历史及学术意义。
综合以上,剑桥大学的中文馆藏涵盖领域相当多元,而其中该校图书馆中文部收藏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善本珍籍及宝贵文物,提供了英国汉学研究学者相当重要的参考资源。除此之外,该校近几十年来也陆续出版了许多的重要汉学着作,为国际汉学研究相当重要的参考依据,强化了国际汉学研究的深度。
注1:根据郑恒雄所述,「类书相当于今日的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是颇具特色的一种工具书」。
注2:请参考徐小燕,〈学问的渊薮〉,第5页。
资料来源: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A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Mind', http://wwwlibcamacuk/About/journeypdf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Collections, http://wwwlibcamacuk/deptserv/chinese/introhtml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he Chinese Collections, http://wwwlibcamacuk/deptserv/chinese/catalogueshtml
郑恒雄,〈钦定古今集成资料库新献〉, http://wwwgooglecouk/urlsa=t&rct=j&q=&source=web&cd=8&cad=rja&ved=0CGgQFjAH&url=http%3A%2F%2F19219213178%2Fbook%2Fbookdoc&ei=ylqdUPLKE-ei0QWe-4GoBQ&usg=AFQjCNEcMZEn-Q9hGKUm_pHDOU9MUpFAFA
徐小燕,〈学问的渊薮〉, http://wwwlibscuedutw/pub/s19/19-1pdf
世界书局,〈四库全书荟要〉, http://wwwworldbookcomtw/web/SelfPageSetupcommand=display&pageID=11333&_fcmID=FG0000002786000004_0_2
(wwwliuxue86com)
钱钟书(1910.11.21-1998年12月19日)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教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仁中学。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回家探亲时,因沦陷而羁居上海,写了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围城》已有英、法、德、俄、日、西语译本。散文大都收入《写在人生边上》—书。《谈艺录》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与此同时,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中央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执教或任职。1953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所著多卷本《管锥编》,对中国著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我不知道弗洛伊德会对这怎么解释,反正有30多年时间,我最幸福的梦都是关于旧书店的: 一些我从前根本不认识的书店或者我正在光顾的熟悉的老书店。其实那些熟悉的书店肯定已经不存在了,我很不情愿地得出这个结论。在巴黎,离火车北站不远的一个地方,对于那里一条上山的长街尽头的一家书店,我有着非常生动鲜明的记忆。那是一家有着许多高高书架、门进很深的书店(我得用梯子才能够到那些书架的上头)。至少有两次我搜寻遍了它的每一个书架(我想我在那儿买到了阿波利奈尔的《法尼·西尔》的译本),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我去那里寻找那家书店的努力却是归于徒然。当然,那家书店可能已经消失了,甚至那条街道本身也不在那儿了。此外在伦敦有一家书店,非常频繁地出现在我的梦中: 我能够非常清楚地记得它的门面,但是却记不得它内部的情况了。它就坐落在你来尤斯顿路的路上,在夏洛特街后面的那个地区。我从来没有走进去过,但是我肯定如今那儿再也没有这么一家书店了。我总是带着一种幸福和期待感从这样的梦中醒来。
在我生活的各个不同时期,我一直坚持写关于我的梦的日记,在我今年(1972)的日记里,在前7个月的日记里就包括有6个关于旧书店的梦。相当奇怪的,是第一次。它们都不是快乐的梦;也许这是因为我的一个亲爱伙伴在1971年底去世了吧,我曾经和此人一起去淘书,在二战刚刚结束之后,我和此人一起,开始去搜罗维多利亚时期的侦探小说。同样在今年的一些梦中,出现过一本我打算送给我的朋友约翰·苏特罗作圣诞礼物的有关铁路的旧书(他曾经在牛津创建了铁路俱乐部),当我从书架上把它抽出来的时候,书皮却已经掉了一半: 甚至那些旧的红色纳尔逊7便士丛书(那么没道理地受到乔治·奥威尔的中伤,尽管它的初版太昂贵了,但我仍然很喜欢拥有它)结果都是不同版本的。在所有这些梦中,似乎没有什么好到值得一买的书。
我的朋友戴维·洛是一个书商,他的收藏品曾经使我的思想天马行空,放荡无羁,不止是通过一些梦,而是通过长达50年的淘书中的无数小小探险和在其中结下的友谊。(在17岁上我就变成了查林克罗斯路上的一个漫游者,唉,现在我很少叨扰那里了。)
旧书商们在我以往认识的各种人物中是属于那种最友好又最古怪的人。如果我没有成为一个作家,那么他们的行当一定会成为我最喜欢选择的行当。在他们那儿有书籍发霉的气味儿,在那儿有寻宝探宝的感觉。由于这个缘故,我宁愿到码放得最混乱的书店,在那种地方,地形学和天文学的书籍混放在一起,神学和地质学的书籍混放在一起,一堆堆没有分类的书籍乱堆在楼梯间里,正对着一个标着“旅游图书”的房间,而在这个房间里可能包括一些我所喜欢的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失去的世界》或者《克罗斯科的悲剧》。我害怕走进马格斯书店或者夸里奇书店,因为我知道在那种地方不可能作出什么个人的发现,在那儿书商不会犯任何错误。从戴维·洛的收藏中我意识到我害怕去威廉四世大街的巴恩斯书店是多么错误。但是现在来补救我的这个错误未免为时太晚了。
一个人要想真正进入这个充满机会和冒险的魔幻世界,就必须既是收藏家又是书商。我本来宁愿做一个书商的,但是由于二战我失去了机会。在德国人大规模空袭伦敦期间,我碰巧和戴维·洛(我已经和他很熟了)和小科尔是隶属于同一个哨所的临时防空员,小科尔在那些日子是一个书“贩子”。我和科尔的第一次侦察任务是去搜寻一个伞投炸弹,有人说它挂在布鲁姆斯伯里一个广场的树上。我们根本没有找到它,就给自己放了假。科尔领着我去看了一趟他的房间: 我记得破旧的书籍堆得到处都是,甚至床底下都堆着书,我们俩一致同意,如果有一天我们俩都能在战争中幸免于难,我们就一起经营旧书。后来我离开伦敦到西非干别的工作,我们失去了联系。我已经失去了成为旧书商的唯一一次机会。
要成为收藏家相对比较容易。你收藏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你有入门的钥匙。收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寻求的乐趣,是你遇见的那些人物,是你结交的朋友。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的时候,就初次尝到了购买收藏南极探险作品的滋味,我对北极不感兴趣。那些书籍都已经不在了。那些书现在会有一些价值,但是谁会在乎呢?在战前,我收集查理二世复辟时期的文学作品,因为我当时正在写一部罗切斯特传记,这本书直到30多年以后才得以出版。那些书并不是最早的版本(我当时买不起);那些书也已经不在了: 其中有些书是在德国人对伦敦大轰炸的时候遗失的,也有一些是在我离开英国的时候很遗憾地放弃的。
现在我依然在收藏维多利亚时期的侦探小说: 在40年代的弗伊尔斯书店,我曾经一次花半克郎找到多少书呀!虽然约翰·卡特在10年后推出了著名的斯科里布纳目录,它到处造就了无数收藏家。
对于收藏家来说,毫无疑问,比起那种寻找的兴奋,比起有时这种寻找把你带到的那些神奇陌生的地方来说,收藏品本身价值的重要性倒变得次要了。就在最近,我和我的兄弟休(他收藏的侦探小说的范围包括从维多利亚时期到1914年,所以我们经常结伴淘书)曾经在倾盆大雨中穿过坐落在一片废弃地区中的令人忧郁的利茨街周围,那地方简直就是格里尔森绝望的纪录片的一部分。我们寻找着一家书店,它曾被收入一本很可靠的指南。但是随着我们在那些废弃的工厂之间身上变得越来越湿淋淋的,我们对那本指南的信任也变得越来越少了。然而,当我们终于到达那家肯定曾经存在过的书店时,那里一扇挪了窝儿的门上挂着一个招牌“书店”,其中“书”字的前三个字母都不见了,所有的窗户都破碎了,地板上神秘地乱扔着一些孩子的靴子和鞋,还有一些好鞋。难道这是什么小孩黑手党的聚会地点吗?好像是在那类地方,发现了一些新酒吧和过去从来没有尝过的啤酒,倒也是对淘书者的某种奖赏。
这和皮卡迪利大街上那家年代久远的书店完全是不同的世界,那家书店有古籍旧书部,我最近还到那里去消磨过时间,如果偶然问起他们是否有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伦特的什么著作,他们就会问:“他写什么,先生?小说吗?”
我想戴维·洛对于这些昂贵的书店太宽厚仁慈了,但是我想,一个人如果干这行,他就不得不对那种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衣着讲究的坏蛋作出友好的姿态。我避开那些新开的大学书店,那儿都是红砖和玻璃,塞满了二手的学术书籍,那些书即使在它们初次问世的时候就很沉闷无聊。唉,至于狄龙**的书店,它躲过了扔在商店街周围的所有炸弹幸存下来,但是它今天也没有昔日的那种魅力了。有时候,戴维·洛在讲礼貌上做得过分了: 对于那位邦珀斯书店的大名鼎鼎的威尔逊先生来说,“精”是一个褒义的形容词,我倒是宁愿说他“滑”。
不,比起查林克罗斯路来,伦敦西区现在再也不是我的魂牵梦萦之地了,但是感谢上帝!塞西尔短街依然保持着塞西尔短街的样子,即便是戴维·洛已经搬到牛津郡去了。
在一个开心的日子里,我从戴维那里买到一份奇怪的18世纪的手稿,封面由白色皮纸制成,上面有一个手写的标题《赫尔顿尼亚纳》。它花了我5个畿尼,在30年代这是很大的一笔钱,但是在经过一些研究之后,我靠着在《旁观者》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把这个书价挣回来了。文章谈到这样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一连串残酷的骗局使一个名叫赫尔顿的不得人心的商人大受其苦,很显然这个故事是他的敌人写的。我拥有这份手稿,一直到一封有趣的来信“插入进来”,信中谈到手稿里提到的一些18世纪的伦敦商店名,信是由安布罗斯·希尔爵士写的。这使我很高兴,靠这种方法,在《赫尔顿尼亚纳》上面我除了付出了一点劳动之外什么钱也没花。
也许我最看重的是淘到了《复活节前一周的任务》,由沃尔特·柯卡姆·布朗特翻译,1687年出版,配有7张霍拉版画,封面是同时代压印的红色摩洛哥羊皮。它被献给英格兰女王。“英格兰的女王、王后们又称圣了,”布朗特写道,“结果无限伟大,于是人们发现通往天堂之路就是效忠宫廷之路。”他在一年后就不会写这些话了,因为荷兰的威廉来到了。他将不得不在国外出版这本书,或者根本没有出版家的印刷,没有在坐落于海霍尔本羊羔街的马修·特纳书局公开出版。这本漂亮的书让我在克拉彭公地的盖洛普先生的书店里花了半个克朗,我在那儿买我的安东尼·伍德作品。盖洛普先生的书店是二战的牺牲品之一,它在同一天里和两百码以外的我的房子一样“上天了”。
但愿戴维·洛在书中包括一个被炸弹和建筑师们毁掉的已亡书店名单。例如原坐落于威斯特本园林的那家消失了的我喜欢的旧书店,还有坐落在金克罗斯车站对面三角地的消失了的小书店,在那里我曾经买到《探险记》和《夏洛克·福尔摩斯回忆录》的首版本,花的是在那个时候看来过分的价格五英镑。那是淘书的令人难过的一面,与新书店的开张相比,更多得多的书店消失了。甚至布莱顿也不是它当年的样子了。
(邹海仑 译)
注释:
查林克罗斯路: 在伦敦市中心,是伦敦旧书店最集中的地方。
罗切斯特(1647—1680): 即罗切斯特二世伯爵,本名约翰·威尔莫特,17世纪著名英国诗人,查理二世的朋友。
格里尔森(1898—1972): 英国纪录片运动的创始人。拍有纪录片名片《漂网渔船》(1929),1948—1950任英国中央资料馆影片审计官。
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伦特(1840—1922): 英国诗人,诗集《海神情歌》是其代表作,另有《我的日记》(1919,1920)两卷。
畿尼: 英国旧金币单位,等于21先令。
荷兰的威廉(1650—1702): 即大不列颠的威廉三世,初任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执政(1672年起),后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国王(1689年起)。
安东尼·伍德(1632—1695): 英国古物收藏家、学者,著有《牛津大学历史及其人物》、《牛津学苑》等。
赏析
本文是格林在1973年为好友戴维·洛《带着所有的错误》一书所写的序言,是一篇反战题材的散文。作者通过对战前战后旧书店的对比和与旧书商们友谊的描述,表达了浓重的反战情绪;通过对在旧书店淘书的乐趣的回忆,凸显出战争的破坏性,从而深刻地反思战争带给人们的伤痛。
旧书店让格林魂萦梦牵,而这些曾给他带来过无比乐趣的地方,经过战争的硝烟炮火,已经不复存在。作家只能在梦中去寻找这些书店的影子。格林伤感地写道,在30多年的时光中,“最幸福的梦都是关于旧书店的”,即使醒来时也带着“一种幸福和期待感”。
旧书店让人留恋,因为作家能够在那些散发着霉味的、混放的书籍中,找到一些无法在正规书店中找到的书,比如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失去的世界》或《克罗斯科的悲剧》等。这种乐趣就好比探险家在探险。那种在经历艰难险阻和重重障碍后,最终发现自己寻找已久的宝物时的惊喜与兴奋,是没有过淘书和探险经历的人所难以体会到的。旧书店让人留恋,也是因为那里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与同样懂得淘书乐趣的旧书商们通过讨价还价结下深厚的友谊,比如和书商戴维·洛。然而,所有这些乐趣都被战争的到来剥夺了。作家以前经常去淘书的伦敦西区,经过战争的洗礼,现在已经面目全非,里面充斥着新开的大学书店和沉闷无聊的二手学术著作。查林克罗斯路和塞西尔短街仍然维持旧貌,但是昔日好友戴维·洛已经从那里搬走了。曾买到过《复活节前一周的任务》的盖洛普先生的书店,也已经成为二战的牺牲品,在飞机的轰炸下,“它在同一天里和两百码以外的我的房子一样‘上天了’”。“原坐落于威斯特本园林”的小书店,“坐落在金克罗斯车站对面三角地”的小书店等等,所有这些作家喜爱的小书店,一个个地消亡在战争的阴影中。
战争不仅仅破坏旧书店、淘书的乐趣和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它更是扼杀人们理想的刽子手。作者原本向往成为一名书商,并和一位兴趣相投的伙伴相约,如果能在战争中幸免于难,就要共同经营一家旧书店。结果最后他们失去了联系,作者也就失去了成为书商的唯一一次机会。虽然格林在写作时用了幽默甚至调侃的手法,但是我们仍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失去朋友和理想破灭的复杂心理,切身感受到战争带给人们的伤痛。作家还有一个理想,那就是成为一名收藏家。然而,他精心收藏的有关南极的书籍,有的在德国人对伦敦的轰炸中遗失,有的在作者逃命时被遗弃,于是,这个理想也不得不被放弃。
战争改变了一切。在战争的硝烟与战火中,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放弃友谊、乐趣甚至是理想,而即使是生存,在这时也变得可望而不可即。在生命都已经被忽视的日子里,人们只能用回忆来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是的,战争带来的不仅是对物质的摧毁,更是对精神的毁灭。这一切,格林都通过对旧书店的描写,忠实而客观地记录了下来。整篇文章弥漫着一股无奈的伤感气息和自我解嘲的幽默与调侃,读来让人心酸,又让人回味。
(王 坚)
应该是《枪管的膛线理论》其实这个不现实的,弹头是和膛线的阳线齿合的,弹药击发后膛线使弹头高速旋转,从而使弹头精度变高,在空中弹头不会出现翻滚现象,但是膛线和弹头之间的巨大摩擦力会产生高温,纸张肯定要燃烧掉的,所以这个不现实的,有一点是真的任何枪管射出来的弹头膛线痕迹都不会和别的相同的。
拉丁语是古罗马的语言,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由于各蛮族语言不统一,而且罗马教廷是用拉丁语作为基督教的法定语言的,所以,各国本身都没有什么文化积淀,所以,拉丁语成了他们的公用语言。各国的文字都是在拉丁语的基础上创造的。
刻本也就是版本类型。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经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盛。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
石印本指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 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体字,易于辨认。
影印本:分线装和平、精装两种形式。过去的影印本,大都采用线装,保持中国古书古雅的特色;但当代的趋势,要求影印的古书采用平装、精装的形式,这样价格可以低廉,又便于插架。影印的古籍也可以加以断句或校勘,有部分影印的古籍已是断句本或校勘本。
扩展资料
中国近代的石印文献,内容以古籍为多,遍及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丛书、通俗小说、唱本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商务印书馆石印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石印的《古今图书集成》等。此外,地图、画刊、报刊和时人新作等也大量地以石印的方式出版。
影印图书大约有3种方式:珂罗版影印,石印,胶印。工序基本上都是先照相,而且是依原本照相。影印本在古籍中很普遍。
-刻本
-石印本
-影印本
①G布朗:《怠工行为》,1977年英文版。
②GDH柯尔:《劳工世界》,1913年英文版。
③M杜波夫斯基:《我们要作世界的主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历史》,1969年英文版。
④B霍尔顿:《英国工团主义1900—1914》,1976年英文版。
⑤AD刘易斯:《工团主义和总罢工》,1912年英文版。
⑥SG佩恩:《西班牙革命》,1970年英文版。
⑦FF里德利:《法国的革命工团主义》,1970年英文版。
⑧DD罗伯茨:《工团主义传统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1979年英文版。
⑨W韦斯特加德—索普:《走向工团主义国际──1913年伦敦会议》,
载《社会史国际评论》,英文版1978年第XX II卷。
⑩GA威廉斯:《无产阶级秩序》,1975年英文版。
本文2023-08-07 05:40:0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400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