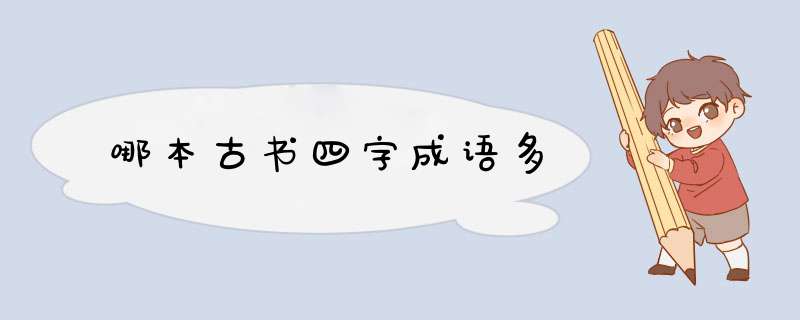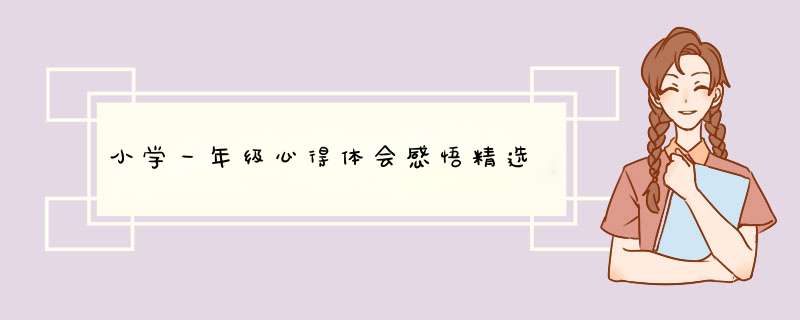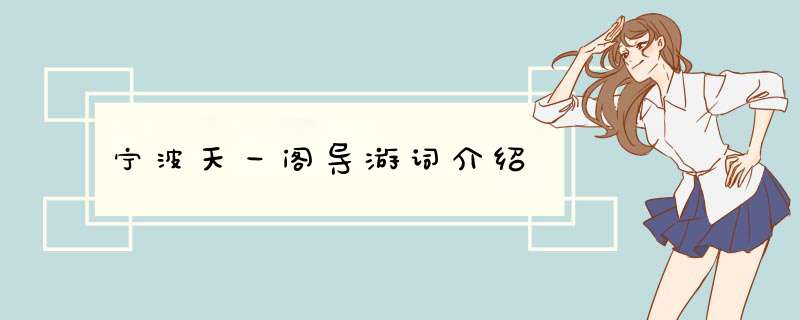嘉业堂藏书楼及小莲庄位置在哪里

嘉业堂藏书楼及小莲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嘉业堂藏书楼与小莲庄毗邻,因清帝溥仪所赠“钦若嘉业”九龙金匾而得名。该楼规模宏大,藏书丰富,原书楼与园林合为一体,以收藏古籍闻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之一,系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
解放后,原书楼主人捐赠给浙江图书馆,现在的藏书楼正以公共图书馆和旅游景点的双重身份接待来自-的读者和游客。
嘉业堂藏书楼坐落于南浔的鹧鸪溪,与小莲庄隔溪相望,有小桥通连。藏书楼掩映在园中,楼外有园,园中有池。
顺着荷叶形的莲池前往,可见太湖石堆垒的假山,形如十二生肖。池的左右有“浣碧”、“障红”两亭,与池中孤岛上的“明瑟”亭构成鼎立之势。西南有一块三米多高的“啸石”、石上有小孔,吹之如虎啸,系南浔三大奇石之一。
藏书楼的创始人是号称“江浙巨富”的刘承干。刘承干,曾是晚清秀才,是刘镛的孙子。建藏书楼以“嘉业”命名,是因清末刘承干曾捐巨资助修光绪陵墓,宣统曾赐以“钦若嘉业”的匾额,他以此为荣,故以“嘉业”命名。
书楼为一座回廊式的两层建筑物,由七间两进和左右厢房组成,共有书库52间,中间有大天井。
书楼收藏书集有两大特点:一是不仅专重于宋元刊本,更着眼于明清两代;二是广收地方志1200余种。其中可称“海内秘籍”的珍本就有62种。
刘承干还以雕版印书蜚声海内,共刻书200余种,版片3万多。刻印了不少被清廷列为-的古藉,如《安龙逸史》、《闲渔闲闲录》等。鲁迅在《病后杂谈》一文说:“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用处的人物。”
背景介绍:
刘承干(1881—1963),字贞一,号翰怡,南浔人,清末秀才。他的祖父刘墉(1825—1889)经营蚕丝致富。然轻富重文,竭力鼓励子孙念书做官。父亲刘锦藻(1862——1934)精文史之学,光绪二十年(1894)中进士,撰有《续皇朝文献通考》、《南浔备志》、《坚匏庵诗文抄》等著作。
刘承干秀才出身。从小受到诗书艺文的熏陶,及长与著名考古学者王国维、罗振玉、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缪荃孙等相交往,爱好古籍赏鉴,并有承袭其父史学及继父刘安澜(刘锦藻的长兄)藏书遗志。
刘承干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开始聚书,凭着他雄厚的资财,加上嗜书如命的癖好,手持巨资,肯出高价,“凡书商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之”。
书商闻风不远千里而来,不数年他花资近30万元之巨,“几有万家之势”,先后收购了甬东卢氏“抱经楼”、独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结一庐”、丰顺丁氏“持静斋”太仓缪氏“东仓书库”等十数家的藏书。故刘氏藏书几萃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地藏书家之精华,得书60万卷,共16万册。
南浔镇:南浔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江南古镇,地理座标位于东径120°25’-120°26’,北纬30°52’-30°53’20”,地处太湖之滨,与苏州接壤,是湖州接轨上海浦东的东大门。长湖申航线和318国道横贯其中,地理环境优越,水陆交通便利。全镇区域总面积1413平方公里,辖51个行政村,10个居民社区,总人口116万人,耕地面积1225万亩。2000
印章的出现和使用大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说文解字》释“印”曰:“印,执政所持信也。”传世印文最早的有战国时“上师之印”。在印章出现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印章只是作为权利的象征和取信的实物,随着社会发展,印章的功能不断增加,而用于藏书是其多种功能中最具文化特色的一种。
藏书印是钤印在图书上的,能够体现藏书所有关系或表达特定的思想内容。古代藏书家多有印,因其制作形式、蕴含内容、价值作用等十分丰富,成为藏书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关于古代藏书印起源,近代学者叶德辉说:“吾尝忆及古人藏书印记,自唐至近世,各有不同,而亦同为不达而已。”(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藏书家印记之语》,广陵书社2007年版)味其语,似乎是说私家藏书印始于唐代,而事实上,早在东晋时期,已有人在收藏的名画上加盖印记,唐代学者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诸好事家印,有东晋仆射‘周顗’印,古小雌字。”(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公私印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其中的“古小雌字”,指的是用唐以前的古体字所作的白文。现存最早的藏印为敦煌写本《杂阿皮昙心经》上的“永兴郡印”,永兴郡为南齐郁林王萧昭业隆昌元年(494)所设,因此此印当为南齐时代之物。到了唐代,私家藏书普遍使用印章,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其高祖张嘉贞藏印为“河东张氏”,曾祖张延赏藏印为“乌石侯瑞”。(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公私印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诗人皮日休《鲁望戏题书印囊奉和次韵》诗云:“金篆方圆一寸余,可怜银艾未思渠。不知夫子将心印,印破人间万卷书。”(《全唐诗》卷六百一十五,中华书局1960年版)可知这方印使用频率非常高。更有寻常人家“偶获图书,便即印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公私印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反映出唐代藏书家用印已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了。
宋代私家藏书蔚为大观,藏书印使用也超越前代,大多数藏书家习惯在藏书上加盖印章,以取信于人。宋人藏书印在形制和内容上都远超唐人。宣和年间(1122年前后),文士钤章用印于书画藏品风行一时,受此影响,藏书家开始镌刻钤印自己的藏书印,宋室南渡后,此风仍不衰,主要有名号印、室名堂号印、纪事印、鉴赏印、校读印、箴语印、诗文印、纪年印等。明清时期,私家藏书风气更盛,再加上文人刻印的流行,藏书印遂成了藏书家必备的征信之物,每位藏书家几乎都有几方乃至十几方、上百方印,每得好书,把玩欣赏或阅读之余,必钤印书上,成为那时的时尚。
叶德辉在《藏书十得·印记》中说:“藏书必有印记,宋本《孔子家语》以有东坡折角玉印,其书遂价重连城。晋家明文庄公菉竹堂藏书,每抄有书,钤以历官关防,至今收藏家资以考证。”(叶德辉:《叶德辉书话》,李庆西标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叶德辉所强调的正是藏书印的价值。
古代私家藏书印内容多样,部分印语体现出特定时期的藏书风尚和藏书家的藏书思想,是研究古代历史文献承继传播、藏书事业发展变化以及藏书文学的主要依据之一,亦可资古代篆刻艺术史的研究。晚清苏州学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所记古代藏书家的藏书印最多,这是因为叶昌炽本人尤好金石学,他先后撰著《语石》和《邠州石室录》等,与金石学关系至密的印章学,自然也在其研究范围之内。此外,今人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体例上最类叶书,于藏书印记载亦多。今略述二书所载藏书印文化内涵。
宋元之际著名书画家赵孟书斋名“松雪斋”,他对书籍非常爱护,谆谆告诫子弟谨为保守,不少藏书流传至今,如所收藏的宋刻本《汉书》《后汉书》一直为明清藏书家所称羡。赵孟藏书最大的特点是喜欢钤盖名氏印和闲章,所用印章成为判断宋元刻本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常用印章有“赵”字方圆二印,还有“松雪斋”“赵孟印”“赵氏子昂”“大雅”“水晶宫道人”“天水郡图书印”等。关于“水晶宫道人”之印的来历,《藏书纪事诗》记载说:“孟以湖州四面皆水,自号水晶宫道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二《赵孟文敏》引《天禄琳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赵孟是文学和书法大家,传世的史料文献颇多,故其生平比较清晰。但是,在其众多的别号、别署中,“水晶宫道人”或“水精宫道人”,争议颇多。虽一字之差,但是涉及鉴定赵孟书画真伪的问题。许慎《说文解字》说:“晶,精光也。”从文字学来说,“精”与“晶”并非通假字,不过,“水晶”与“水精”倒是可以通用。水晶亦称水玉,东晋郭璞注《山海经》云:“水玉,今水精也。”水玉还是玻璃的别称。《本草纲目·金石部》:“(玻璃)本作颇黎;颇黎,国名也。其莹如水,其坚如玉,故名水玉,与水精同名。”赵孟《题苕溪绝句》中有云:“我居溪上尘不到,便当家在青玻璃。”故“水晶宫道人”亦可写作“水精宫道人”,似无疑义。但在书画鉴藏史上,究竟是“水晶宫”?还是“水精宫”?一直喋辩不休,至今犹聚讼未息。曾有学者和鉴定家认为,凡署款或钤印“水晶宫道人”者皆伪。但是,在传世的古代书画中,伪赝之作要远远多于真迹,前人的鉴定结论未必可信。(万君超《水精宫道人漫笔》,《翰墨真赏》,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藏书纪事诗》的记载,虽不能给史上这桩笔墨聚讼做出裁断,但至少为后人研究提供一种佐证。
明末清初江苏常熟藏书家黄翼一生性好古铜瓷器及宋元版书,搜访把玩,视如美人好友,乐此不疲。黄氏爱用藏书印,常用的有“黄子习读书记”“印溪黄子习氏藏书记”等。此外,还有一方比较特殊,曰“有明黄翼收藏”,钤在宋本《林和靖诗》卷首,圜朱记。卷尾跋称该书为“戊子夏”收购而来。关于这方藏书印中的文字,叶昌炽解释说:“戊子为顺治五年(1648)。子羽国变后,杜门不出,此跋仅题戊子,而无纪元,图记冠以‘有明’二字,盖犹有故国故君之思焉。”(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黄翼圣子羽》“昌炽案”)其时虽在清朝,但是身为明遗民,黄翼通过藏印隐含故国之思,因惧怕清初残虐的文字狱,而只好隐晦如此。
藏书印是藏书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因而印文内容对藏书事实多有反映,可以藉此研究藏书家的藏书喜好及情趣。如清代居住在阳湖(今常州)的汉军镶黄旗藏书家杨继振收藏甚富,主要是金石和图书,自称藏书有数十万卷之多,皆卷帙精整,标识分明。其藏书楼名较多,有“石筝馆”“苏斋”“雪蕉馆”“星风堂”等,至清末,因贫困潦倒,相继将藏书出售,叶昌炽曾得零散本数种。杨氏酷爱藏书印,印文主要有“石经厂”“古燕杨氏星风堂鉴藏”“承寿双碑之馆”“宏农杨氏世家”“又云”“继振”等。其中一枚为长方印,文曰:
予席先世之泽,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自少及长,嗜之弥笃。积岁所得,益以青箱旧蓄,插架充栋,无虑数十万卷。暇日静念,差足自豪。顾书难聚而易散。即偶聚于所好,越一二传,其不散佚殆尽者亦鲜矣。昔赵文敏有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静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予谓吴兴数语,爱惜臻至,可云笃矣,而未能推而计之于其终,请更衍曰:“勿以鬻钱,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星凤堂主人杨继振手识,并以告后之得是书而能爱而守之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六《杨继振幼云》“昌炽案”)
全印195个字,不啻一篇小品文,堪称巨印。在这篇印文中,杨氏自述藏书因由,并引用了赵孟(文敏)的藏书箴言,敷衍爱书情状,谆谆告诫,用心良苦。
清代秀水(浙江嘉兴)学者、藏书家朱彝尊精于金石文史,游大江南北,所到之处无不搜剔考证。曾先后收购李延昰、项元汴藏书,又到曹溶、徐乾学等家借抄,所藏益富,自称拥书8万卷。朱氏藏书处曰“曝书亭”“古藤书屋”“潜采堂”等。所用藏书印有“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梅会里朱氏”“潜采堂藏书”“七品官耳”“我生之年岁在屠维大荒落月在橘庄十四日癸酋时”“秀水朱彝尊锡鬯氏”“南书房镝史记”“南书房旧讲官”“小长芦钓鱼师”“得之有道传之无愧”“别业在小长芦之南毂山之东东西峡石大小横山之北”等。其中一方尤为独特——“七品官耳”,关于此印来历,朱氏自述说:“予中年好抄书,通籍以后,见史馆所储,京师学士大夫所藏弆,必借录之。有小史能识四体书,日课其传写,坐是为院长所弹去官,而私心不悔也。”(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朱彝尊锡鬯》引《曝书亭集·鹊华山人诗序》)因为偷抄史馆藏书而丢官,可为藏书一痴,但是朱氏并不后悔,“七品官耳”,一语道破心中重书轻官之意,十分难得。朱氏还撰《书椟铭》称:“予入史馆,以楷书手王纶自随,录四方经进书。纶善小词,宜兴陈其年见而击节,寻供事翰苑。忌者潜请学士牛钮形之白简,遂罢予官。归田之后,家无恒产。聚书三十椟,老矣,不能遍读也。铭曰:‘夺我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朱彝尊锡鬯》引《曝书亭集·书椟铭》)同样洒脱。
晚清近代藏书家叶德辉有一印曰:“长沙叶氏郋园藏书处曰丽廔,藏金石处曰周情、孔思室,藏泉处曰归贷斋,著书处曰观古堂。”(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卷七《叶德辉焕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印文交代自家四个藏书室的不同功能:藏书、藏金石、藏古币和藏著述,叶氏果真如此富有?非也,此为叶氏以藏书印表明一心向古,从事学术之心态。历史上,叶德辉学问很大,历仕三朝,骨子里反对维新,反对社会变革,所以对这方印章要辩证看待。
藏书家用印并非一枚,一般都有多枚,众多藏印更能反映出他们丰富的藏书心态。明代常熟藏书家毛晋建汲古阁广收天下图籍,从事刻书和藏书工作,其藏书印众多,大致有如下几类:(一) 钟爱宋元刻本者,如“宋本”“元本”;(二) 表明藏书所有者,如“玈溪”“弦歌草堂”“仲雍故国人家”“汲古主人”“汲古得修绠”“毛晋秘箧审定真迹”“毛氏藏书”“东吴毛氏图书”“汲古阁世宝”;(三) 告诫子孙精心保存,如“子孙永宝”“子孙世昌”“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等;(四) 提倡阅读,如“开卷一乐”“笔研精良人生一乐”,等等。(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毛晋子晋》引《东湖丛记》)众多藏印有助于对毛晋及其汲古阁藏书研究。
古代藏书印文,多明藏书之艰,要后人妥为保守。明代山阴(今浙江绍兴)藏书家祁承建藏书楼曰澹生堂,藏书9千多种,10万多卷,这个规模在当时比天一阁藏书还多3万余卷。为了不让藏书流失,祁氏曾与儿辈订立《澹生堂藏书约》,并撰写藏书铭镌刻于印,文曰:“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祁承尔光》)
无独有偶,清代青浦(今属上海)藏书家王昶,建藏书室曰“蒲褐山房”,富于藏书。其有一藏印说:
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剧劳勚。愿后人,勤讲肄。敷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勿废置。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述庵传诫。(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五《王昶德甫》引《东湖丛记》)
告诫子孙不可变卖藏书,用语严厉,甚至用上了诅咒和恐吓。纵然藏书家们苦口婆心,但是,自来藏书不过三世,子孙能够永守者鲜有其人,如祁承死后十几年,即发生明末战乱,澹生堂藏书开始散失,入清,藏书楼不复存在。
清代浙江临海藏书家洪颐煊一生读书、为官,性喜聚书,曾广购岭南旧本至3万余卷,碑版彝器多世所罕见,致仕归里后,聚书更多,为防子孙不守,刻多枚藏书印,谆谆告诫,有“子子孙孙永为宝”“子孙宝之”“子孙世守”“鬻及借人为不孝”“子孙保之”(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卷三《洪颐煊》)等,用心极为良苦。
当然,《藏书纪事诗》在收集各类用印情况时,也不忘批评史上藏书家乱用藏书印的恶习。如明代秀水(浙江嘉兴)藏书家项元汴家资雄厚,收藏大量的法书名画,建有天籁阁储之,其藏书印主要有“世济美堂”“传家永宝”“神游心赏”“古檇李狂儒墨林山房史籍印”等。但项元汴有个恶习,每得珍贵典籍、书画,必在上面钤满累累的印章,这一习惯众人皆知,而不忍卒睹的是,其印章又多出于俗手所制,手法恶劣,粗俗不堪,时人给以“美人黥面”“佛头着粪”之喻。针对项元汴乱用藏书印一事,叶昌炽给以诗说:“十斛明珠聘丽人,为防奔月替文身。紫茄白苋秋风里,一度题诗一怆神。”(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项元汴子京》)语虽尖刻,却是切中肯綮。
藏书印在藏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它是鉴定古籍版本的重要依据之一,借助藏书印,研究者可以了解一部书的收藏及流传过程。后人品味前人藏书印,明古人之思,探古人之幽,解古人之情,小中见大,趣味丰饶。而一部古书,因为有了古人的藏书印,给人以返璞归真的历史气息,当然,一部古籍往往也因为钤有古代著名藏书家的印而身价百倍。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新书架
《皇清奏议》
《皇清奏议》为罗振玉在搜集整理内阁大库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全书68卷,正编64卷、续编4卷,收入了清顺治元年至乾隆六十年和嘉庆元年至十年的中央官员及督抚学政等地方高级官员的奏疏,反映了清初至清中叶政局的变动、政治生态的演变、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本次整理以民国二十五年墨缘堂石印本(据罗振玉“内府精写本”影写)为底本,国家图书馆藏《皇清奏议》(不分卷)和清华本《皇清名臣奏议》为主要参校本。
《皇清奏议》(全三册),张小也、苏亦工等点校,繁体竖排,精装32开,凤凰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定价320元。
《世说新语》 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记述后汉至南朝刘宋人物的遗闻轶事的杂史。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撰,梁刘峻(字孝标)注。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该书原名《世说》,后人为与刘向书相别,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今名。全书原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隋书·经籍志》将它列入小说家。该书所记个别事实虽然不尽确切,但反映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
刘义庆门下聚集不少文人学士,他们根据前人类似著述如裴启的《语林》等,编成该书。刘义庆只是倡导和主持了编纂工作,但全书体例风格大体一致,没有出于众手或抄自群书的痕迹,这应当归功于他主编之力。有的日本学者推断该书出于刘义庆门客、谢灵运好友何长瑜之手。
刘孝标原是南朝青州人。宋泰始五年(469)北魏攻下青州,他随例被迁到平城,在那里出家,后又还俗。齐永明四年(486)还江南,曾参加翻译佛经。该书的注,是刘孝标回江南以后所作。他采用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办法,进行补缺和纠谬的工作。孝标征引繁富,引用的书达四百余种。后人注释该书的,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谔《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日本德川时代的学者著有几种《世说新语》注。还有马瑞志的英文译本、目加田诚等的多种日文译本和法文译本。
《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宋刘义庆编撰。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类,每类收有若干则,全书共一千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从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 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於传闻,不尽符合史实。此书相当多的篇幅系杂采众书而成。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前人的记载。一些晋宋间人物的故事,如《言语篇》记谢灵运和孔淳之的对话等,则因这些人物与刘义庆同时而稍早,可能采自当时的传闻。
德行第一 言语第二
政事第三 文学第四
方正第五 雅量第六
识鉴第七 赏誉第八
品藻第九 规箴第十
捷悟第十一 夙惠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羡第十六
伤逝第十七 栖逸第十八
贤媛第十九 术解第二十
巧艺第二十一 宠礼第二十二
任诞第二十三 简傲第二十四
排调第二十五 轻诋第二十六
假谲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俭啬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谗险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纰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世说新语》主要记述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我们明确的看到了所谓「魏晋清谈」的风貌。
此外,《世说新语》善用对照、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
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影响尤其大。
从《世说新语》的某些分篇中,可以看出刘义庆编著此书时的倾向性。如《德行》、《政事》、《方正》、《雅量》等篇,作者对其中的人与事大抵采取肯定的态度;《任诞》、《简傲》、《汰侈》、《尤悔》、《惑溺》等篇,则对所写人与事多持否定态度。其他各篇,虽然从题目中看不出明显的态度,但行文中仍有其倾向性。大体来说,刘义庆对汉末一些名士,都是歌颂或赞赏的;对魏晋的清谈家则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如他比较赞赏的晋代乐广等人,尚清谈而又不违背“名教”;至於象阮籍等蔑视“名教”的人,则被斥之为“狂诞”。对有些历史人物,他虽然并不赞成,但对他们某些行动,却又持欣赏的态度。如对西晋末年“清谈误国”的王衍,有时也赞赏他不和人计较的“雅量”;对桓玄则称其早慧。总的来说,他还是依据世族士大夫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人物的。
《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人物言行,往往是一些零星的片断,但言简意赅,颇能传达人物的个性特点。如《雅量》篇写祖约和阮孚两人的优劣,只通过祖约料理财物和阮孚为木屐上蜡的两个细节,显示出一个是吝啬的守财奴,一个只是出於对木屐的癖好。淡淡几笔,人物性格就跃然纸上。《忿狷》篇写王述性急,吃鸡蛋时用筷子刺不破壳就发怒,以至用脚踩,还放口中嚼破后吐掉,寥寥数语,把他当时暴怒的状况生动地表达出来。
在《世说新语》中,记言论的篇幅比记事的更多些。记言方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往往如实地记载当时口语,不加雕饰,因此有些话不很好懂。如《政事篇》记载王导对几个“胡人”弹著指头说“兰阇兰阇”,就是一句“胡语”;《排调篇》又记载他当著刘惔的面说“何乃渹”,“渹”是吴语冷的意思。此外象“阿堵”、“宁馨”等当时的俗语也屡次出现。它在记言方面的另一个特点,是常常能通过几句话,表现人物的性格。如《简傲篇》写桓冲问王徽之做什么官,他回答说:“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又问他有几匹马,死了多少,他都答不上来,却用《论语》中的话来答对,活画出世族士大夫们狂放而不切世情的特徵。《尤悔篇》载桓温自言自语地说:“作此寂寂,将为文(晋文帝司马昭)景(晋景帝司马师)所笑。”接著又说:“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这几句话,也活画出一个野心勃勃的权臣的心理。后一句话是内心自白,很可能出於传说和想象。书中还有一些反映人物心理的语言,也很生动传神,如《忿狷》篇写王恬对王胡之发火,王胡之握著他手臂说:“汝讵复足与老兄计耶?”王恬拨开他的手说:“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言语间表现出一个很冷静,一个在狂怒,都很形像。
《世说新语》的文字,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几如口语,而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读,其中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
《世说新语》有梁刘孝标注本。刘注的特点是收集许多其他古籍材料,与原文参证,这些材料多已亡佚。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宋刊本。国内影印的日本“金泽文库”藏宋刊本,附有日本所发现的唐写本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嘉趣堂刊本等。近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是本书最好的笺释,有中华书局排印本。
《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有关东汉到南朝刘宋人物轶事的杂史。作者是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公元403年~公元444年),梁朝的刘峻(字孝标)作注。在汉代时,刘向曾写《世说》,但已散失。《世说新语》原名也是《世说》,所以为和刘向的区别,又叫《世说新书》,宋代之后改为现在这个名字。
编著者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宗室,袭封临川王,曾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等职。《宋书‧宗室传》说他“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著有《徐州先贤传赞》九卷及《典叙》、志怪小说《幽明录》等。刘义庆以前的志人(轶事)小说有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均已散佚。《世说新语》虽被保存了下来,但近代学者根据唐写本残卷考证,亦经后人删改,与原貌已有很大出入。
《世说新语》通行本为 6卷,36篇。分德行、语言、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等36门。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於传闻,不尽符合史实。此书相当多的篇幅系杂采众书而成。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前人的记载。一些晋宋间人物的故事,如《言语篇》记谢灵运和孔淳之的对话等,则因这些人物与刘义庆同时而稍早,可能采自当时的传闻。
原文阅读:http://wwwmy285com/gdwx/xs/bj/ssxy/indexhtm
古书拼音
注音: gu shu
古书解释
意思:古代的书籍或著作。
古书造句:
1、别把这些古书弄坏了,我可赔不起。
2、贵族们或拨弄乐器,或阅读古书,心情则凄凄惨惨戚戚,通常为逝去的亲人唏嘘不已。
3、这本古书研究的是人生命中的变化,易经相信通过了解变化的方式和周期可以为未来的事件做好准备,并且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决策。
4、古书描述了此病的'具体症状。
5、买卖收藏品——从古书到泰迪熊,这里面有很多商机来买进和卖出收藏品。
6、这本福音书是三份装订在一起的古书中的一份。
7、然而,分析气体的技术实现了非侵入性研究古书。
8、一本古书散发出来的熟悉的霉味源于纸张或其它如装订线等材料发出的数百种不同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9、《算命大全》是一本厚厚的古书,就摆在她手边的一张桌子上,因为经常装在口袋里,它已经十分破旧了,边儿都磨到了文字的边上。
10、这些拉丁原稿也许早在几百年前便已被书写成文,而后人们或直接在古书行与行或页边空白之间添加这些解释的集注。
11、为震慑朋友和同事,他们把名片印成折页状,仿佛中国的古书,上面的字也小到必须用放大镜才能看清。
12、当代中国人厌倦了斗争和内乱,几乎自动地对这样的言辞产生反应,呼唤古书《礼记》中大同的乌托邦理想。
13、我买了好多古书,它们被到处堆放,因为我喜欢看过去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行为,我想我将找时间读完每一本书。
14、于古书辨伪实践中,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古代著作权人的精神权利。
15、据古书记载,神秘、醇香的蒸汽从地面升起,皮提亚就中了阿波罗的咒语。
16、这些事实收藏在一些古书里。
17、在古书里对我显示你的肖像。
18、这样,阅读古书时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19、有些古书及古旧抄稿配有各种装饰。
20、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性恋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中国古书上也有断袖之癖的记载。
21、有时候字或它们的意义甚至不存在而只在古书里可找到。
22、中国古书中有一段记载说,一位学者因为朋友不愿把一种植物的新枝送给他,便实行偷窃,结果被捕入狱。
23、我们在读一本古书,或阅一幅古画时,我们其实不过是在观看那作家的心灵的流动。
24、根据协议,日本将向韩国移交殖民统治期间夺走的一批古书。
25、这在瑜伽古书中已经交代的非常明确了。
26、所有这些古书古画都标了价。
研究古文字的风气是在汉代开始形成的﹐汉代人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有3种。一种是先秦铜器的铭文﹐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里说﹐各地“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西汉张敞“好古文字”﹐宣帝时美阳(今陕西扶风)出土古铜鼎﹐他曾释读其铭文﹐事见《汉书‧郊祀志 下》。一种是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的字书《史籀篇》的抄本﹐汉代人所说的籀文﹐就指《史籀篇》的字﹐其字体属于大篆﹐一种是所谓古文经﹐即秦始皇焚书时被藏匿起来的一些儒家经籍抄本﹐如汉初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得到的《尚书》﹑《礼》﹑《论语》等书。这些经籍抄本的字体既不是隶书﹐也不是小篆和籀文﹐汉代人多称之为古文。推崇古文经的经学家如许慎等人﹐认为这种字体比籀文还要早。但是据后人研究﹐所谓古文其实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指秦以东各国)的文字。汉代推崇古文经的那一派经学家﹐后人称为古文学家。另一派经学家﹐反对古文经﹐只相信世代相传的本子﹐后人称为今文学家。古文学家为了读通古文经﹐必须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古文﹐所以往往同时是文字学家。他们进行了收集古文并把古文跟当时使用的文字相对照的工作﹐有些人还进一步对汉字的构造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今字》和《隋书‧经籍志》等著录的后汉卫敬仲(即卫宏)撰的《古文官书》等书﹐是前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说的建立是后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属于古文经系统的《周礼》。不过据近人研究﹐把六书解释为“造字之本”﹐大概是汉代古文学家的创造。公元 1世纪末﹐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为古文学家对文字的研究作了出色的总结。
《说文》收字的体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字形以小篆为主﹐同时收入一些写法跟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在解释文字的时候﹐许慎依据六书理论﹐尽可能结合字形指出字的本义。所以即使按照不以小篆为古文字的传统文字学的观点来看﹐许慎的工作也是带有古文字研究的性质的。可惜许慎等古文学家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时代都比较晚。在当时虽然古铜器铭文已经受到了有些人的注意﹐但是蒐集﹑研究这种资料的风气却还没有形成﹐学者们很难加以利用。《说文》叙提到了鼎彝上的“古文”﹐但是书中所收的古文看来全都出自古文经﹐实际上只是战国时代的文字。籀文的时代也不算很早﹐而且许慎等人所看到的《史籀篇》是屡经传抄的本子﹐有些字形显然已经讹变。这些古文字以及小篆的字形往往不能反映本义。因此许慎对古文字的发展过程缺乏正确的认识﹐他对字形的解释和所指出的本义也往往不可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缺点是很难避免的。 从魏晋一直到宋初﹐古文字的研究没有很大的进展。这一时期最受重视的早于小篆的古文字﹐仍然是古文学家所说的那种古文。曹魏正始年间将古文学家传授的《尚书》和《春秋》刻石立于太学﹐每个字都用古文﹑小篆﹑隶书三体写刻。这就是所谓三体石经。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或谓在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或 281)﹐在汲郡(今河南汲县)的一个被盗掘的战国后期魏国大墓里发现了大量竹简书﹐共有75卷﹐10馀万字﹐字体跟古文经相类。这就是所谓汲冢古文。这批竹书被收入官府﹐先后由荀勗﹑和峤﹑卫恒﹑束皙等人加以整理﹐写定为今文。竹书原本早已不存﹐写定之本除《穆天子传》外也都已亡佚。据史书记载﹐南北朝时也间有古文简册发现﹐但是其内容一点也没有流传下来。在从魏晋到宋初这段时期里﹐仍有人继续做蒐集古文的工作﹐而且还有人用古文刻写碑碣或伪造典籍古本。他们所用的古文﹐有的有根据﹐有的则是杜撰的。五代末宋初的郭忠恕(~977)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古文资料编成古文的字汇﹐名为《汗简》。稍后的夏竦(985~1051)编《古文四声韵》(1044)﹐材料来源跟《汗简》基本相同﹐不过《汗简》是按部首编排的﹐夏书则是按韵编排的。这两部书虽然收入了不少杜撰的古文﹐大部分字形还是有根据的﹐是现代人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郭﹑夏之后﹐古文之学就逐渐衰微了。
在这一时期里﹐有铭文的古铜器也时有发现﹐可惜仍然没有形成蒐集﹑研究金文的风气﹐唐初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发现了重要的先秦石刻──石鼓文。唐代人对石鼓文很重视﹐讲字体﹑书法时往往提到它。由于石鼓文的字形跟籀文比较接近﹐当时人多附会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书。秦始皇巡行天下时所立的篆文刻石﹐在唐代也很受重视。南北朝时石经已有搨本﹔在唐代﹐秦刻石和石鼓也都有搨本流传。
唐代篆文书法家李阳冰曾整理过《说文》。他根据秦刻石改了《说文》的一些篆形﹐如改(欠)为等﹐受到后人的很多批评﹐李阳冰擅改古书是不对的﹐但是他根据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文字资料纠正《说文》﹐这却是值得重视的。他解释字形也时出己见﹐虽多荒谬﹐但也间有可取之处。例如许慎解释“木”字说:“从﹐下象其根”﹐他则认为整个字“象木之形”。 在宋代﹐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古文字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真宗咸平三年(1000)句中正等人考定乾州(今陕西乾县)所献“史信父甗”﹐这是宋人研究古铜器铭文之始。由仁宗朝到北宋末年﹐蒐集﹑著录﹑研究古铜器及其铭文的风气日盛﹐南宋时﹐关中﹑中原等发现古铜器的主要地区先后为金﹑元占据﹐蒐集新出土铜器的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但由于北宋学风的影响﹐南宋前期著录﹑研究金文的风气仍相当兴盛﹐到后期就衰落了。
宋代学者在研究金文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北宋的杨元明(南仲)﹑欧阳修(1007~1072)﹑吕大临(1046~1092)﹑赵明诚(1081~1129)和南宋的薛尚功等人。宋人编了不少古铜器和铭文的著录书﹐流传至今的有吕大临《考古图》(1092)﹑宋徽宗撰的《博古图录》﹑南宋赵九成《续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1144)﹑王俅《啸堂集古录》和王厚之(复斋)《钟鼎款识》。前3种兼录器形和铭文﹐后3种单录铭文。吕大临另编有《考古图释文》﹐按韵收字﹐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汇(或谓此书为赵九成所编﹐似非)。政和年间王楚撰《钟鼎篆韵》﹐绍兴年间薛尚功撰《广钟鼎篆韵》﹐材料较吕书增多﹐但皆已亡佚(王书实际上还保存在元代杨的《增广钟鼎篆韵》里)。
殷周金文是学者们最早接触到的早于籀文和古文的文字。宋代学者对金文的蒐集﹑著录和研究在古文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他们通过较古的金文已经认识到“造书之初”象形之字“纯作画像”﹐“后世弥文﹐渐更笔划以便于书”(《考古图》 4‧26上)。《考古图释文》的序对金文形体上的某些特点(如笔划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不一等)以及辨释金文的方法作了简明的概括﹐也很值得注意。宋人正确释出的金文﹐大都是比较容易认识的。不过他们有时也有很好的见解﹐如杨南仲释晋姜鼎铭文﹐疑“”为“旂”字﹐读为“祈”﹐就比近代古文字学名家吴大澄﹑罗振玉等人以“”为“祈”之本字的说法确切。
在石刻文字方面﹐石鼓文和秦刻石在宋代都继续受到重视。南宋前期的郑樵创石鼓文为秦篆之说﹐认为石鼓是秦惠文王以后始皇以前的刻石。时代稍后的巩丰认为是秦襄公至献公时的刻石。这在石鼓文的研究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北宋时还发现了战国时秦王诅咒楚王于神的刻石﹐即所谓诅楚文﹐欧阳修(1007~1072)﹑苏轼(1037~1101)﹑董逌等人都曾加以研究。
在宋人的六书研究中﹐可以看到金石学的影响。郑樵《通志‧六书略》对某些表意字字形的解释明显胜过《说文》。例如 《说文》说“止”字“象艹木出有址”﹐《六书略》则认为“象足趾”﹔《说文》说“步”字“从止﹑相背”﹐《六书略》则认为“象二趾相前后”﹔《说文》说“立”字“从大立一之上”﹐《六书略》则认为“像人立地之上”﹔《说文》说“走”字“从夭﹑止﹐夭者屈也”(从段注本)﹐《六书略》则说“夭”“像人之仰首张足而奔之形”﹐“步”﹑“立”﹑“走”等字一般都看作会意字﹐《六书略》却收在象形类里﹐郑樵对金石文字颇有研究(《通志》有《金石略》)。他能有上述那类见解﹐显然是由于受了金石文字中较古字形的启发。宋元间的戴侗作《六书故》﹐直接采用金文字形。由于金文字少﹐往往杜撰字形﹐因此受到后人的很多批评。不过戴氏说字颇有独到之处﹐这也是后人所承认的。如他认为是“星”的初文﹐“鼓”字所从的“”本象鼓形﹐就是很好的见解。 元﹑明两代是古文字研究衰落的时期﹐金石学方面值得一提的﹐只有明人蒐集﹑著录古印的工作。这项工作宋人就开始做了。但是宋元时代的古印谱大都已经亡佚﹐流传下来的如《说郛》所收的《汉晋印音图谱》﹐资料贫乏﹐用处不大。明人所编古印谱﹐如顾氏《集古印谱》(1571)﹐内容比较丰富﹐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在这一时期里﹐古文字字汇继续有人编纂﹐但是所收字形大都据前人之书辗转摹录﹐没有多大参考价值。元初杨桓《六书统》﹑明代魏校《六书精蕴》等书也都想根据早于小篆的古文字来讲六书﹐这些书“杜撰字体﹐臆造偏旁”之病甚于《六书故》﹐而见解则不及《六书故》﹐不为后人所重。 进入清代以后﹐金石学和小学复兴﹐古文字研究重新得到发展。清代古文字研究的水平是逐渐提高的。清初闵齐伋作《六书通》﹐后由毕弘述整理刊行﹐这是兼采古文﹑印文和钟鼎﹑石刻文字的一部古文字字汇﹐流传很广﹐但是内容杂乱﹐摹录失形﹐水平很低。乾隆时﹐清高宗先后命梁诗正﹑王杰等人仿《博古图录》体例对内府所藏古铜器加以著录﹐编成《西清古鉴》(1751)﹑《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及《乙编》4书 (后3书稿本民国时方印行)﹐其水平尚在宋人之下。从乾﹑嘉之际开始﹐清人在古文字研究上才有明显超过前人之处。道光以后﹐重要的金石收藏家辈出﹐陈介祺(1813~1884﹐号簠斋)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收藏的古文字资料在种类﹑数量﹑质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人。由于古文字资料的日益丰富﹐同时也由于小学﹑经学等有关学科的发达﹐古文字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到清代晚期同治﹑光绪时期达到了高峰。吴大澄(1835~1902)﹑孙让是高峰期最重要的学者。
清代古文字研究的重点仍然是金文。乾隆时﹐由于朴学的兴起以及《西清古鉴》等书的编纂﹐士大夫中对金文感兴趣的人逐渐增多﹐嘉庆元年(1796)﹐钱坫刻《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专收自藏之器﹐器形﹑铭文并录。九年(1804)﹐阮元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著录所收集的各家铭文﹐加以考释﹐以续《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此后出现了很多跟钱书或阮书同类的著作﹐影响较大的有吴荣光(1773~1843)《筠清馆金文》(1840)和吴式芬(1796~1856)《捃古录金文》(1895)﹐体例都是仿阮书的。
清代研究金文的主要学者﹐乾嘉时期可以上举的钱坫﹑阮元为代表﹐道咸时期有徐同柏(1775~1854)﹑许瀚(1797~1867﹐字印林)等人。徐同柏著《从古堂款识学》(1886)﹐许瀚曾为吴式芬校订《捃古录金文》﹐他在金文方面的见解多见于此书。同光时期﹐金文研究出现高潮﹐主要学者有吴大澄﹑孙让﹑方濬益(~1899)﹑刘心源(1848~1915)等人。吴大澄跟金文有关的主要著作有《说文古籀补》﹑《字说》等书。《古籀补》是古文字字汇﹐所录之字以金文为主﹐兼及石刻﹑玺印﹑货币和古陶文字﹐释字颇有出自己见者。此书一改《古文四声韵》以来按韵收字的体例﹐分别部居悉依《说文》﹐不可释和疑而不能定之字入于附录。所录之字皆据搨本慎重临摹﹐跟过去那种辗转摹录﹐字形失真的古文字字汇大不相同。后来的古文字字汇﹐在编排的体例上大都仿照吴书。孙让著《古籀拾遗》(1888)和《古籀馀论》(1929)﹐订正前人考释金文之误。方濬益著有《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1935)﹐但在他去世多年后才出版。刘心源的主要著作是《奇觚室吉金文述》(1902)。上述诸人对金文的考释有很多超过前人之处。
宋代以来多把春秋战国时鸟篆之类笔划屈曲奇特的金文视为夏商文字。龚自珍(1792~1841)曾疑王复斋《钟鼎款识》著录的﹑铸有这类铭文的“董武钟”是吴越器。方濬益明确指出:“若薛录之四商钟﹑王氏所录之董武钟﹐要亦周器﹐乃当时自有此一体﹐如秦之有缪篆﹑殳书者”(《缀遗》卷首《彝器说》中)。这是一种进步。在把铭文跟古籍中有关的历史资料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方面﹐清人也超过了前人。 货币文字真正成为古文字研究的资料是从清代开始的。蒐集﹑研究古钱币的风气开始得很早。但是宋代以来研究古钱的人大都把基本上属于战国的东周时代的刀﹑布等类钱币﹐说成太昊﹑尧﹑舜等古帝王和夏商时代的东西﹐解释币文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直到乾隆时撰的《钱录》(1751)﹐仍然停留在这种水平上。古币文字的研究出现转机﹐也在乾嘉之际﹐据蔡云《癖谈》(1827)﹐钱大昕曾说过“币始战国”的话﹐嘉庆时﹐初尚龄作《吉金所见录》(1819)﹐把古刀﹑布断归春秋﹑战国。先秦古币的研究自此渐上轨道。吴大澄《古籀补》收入了不少币文﹐刘心源在《奇觚》里也考释了一些币文。
乾嘉以后﹐玺印文字的研究也有相当大的进步。元明人不知古印中有早于秦代之物(明人古印谱中其实已收入不少战国印﹐但他们不明其时代)。乾隆五十二年(1787)﹐程瑶田为潘氏《看篆楼印谱》作序﹐释出战国印中的“私玺”二字﹐并说“‘玺’但用‘尔’者﹐古文省也”(《通艺录》卷八《看篆楼印谱叙》)。这是清人辨识先秦古印的先声。道光十五年( 1835 )张廷济(1768~1848)编《清仪阁古印偶存》﹐称先秦印为古文印。同﹑光间﹐陈介祺编《十锺山房印举》﹐在汉印之前列“古玺”和“周秦”印两类。按其内容﹐前者基本上是六国印﹐后者包括战国时的秦印﹑秦代印和汉初印。陈介祺本认为周秦印是周末与秦代之物﹐古玺是三代之物。光绪四年(1878)﹐他在致吴大澄的信中说:“……朱文铜玺﹐前人谓之秦印﹐不知是三代﹐今多见﹐亦似六国文字”(五册本《簠斋尺牍》第五册戊寅四月二十二日札)﹐对古玺时代的认识已接近实际。《古籀补》收入了一些玺文。在汉印篆文方面﹐嘉庆时就有桂馥《缪篆分韵》(1796)等字汇刊行﹐摹录印文比较谨严﹐胜于以前其他各类古文字字汇。 道光以后还发现了一些古文字资料的新品种﹐如封泥文字(即打在封泥上的印文﹐以汉代的为多)﹑古陶文字以及在清末才发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甲骨文。古陶文字首先于同﹑光间在山东临淄等地发现﹐稍后又在直隶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地发现﹐陈介祺是第一个鉴定“三代古陶文字”(实际上大都属于战国时代)并加以收藏的人。吴大澄第一个认真研究古陶文。他曾据陈介祺藏陶的搨本写过一些考释﹐还在《古籀补》里收入了不少陶文。
安阳殷墟的甲骨文(主要内容为卜辞)大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受到古董商的注意。次年﹐王懿荣(1845~1900)鉴定为三代古文并加以收藏。殷墟甲骨文资料丰富﹐内容重要﹐时代属商代后期﹐早于大多数铜器铭文﹐其发现在古文字学史上有重大意义。王懿荣在鉴定甲骨文的次年﹐就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自杀殉国﹐所藏甲骨后归刘鹗(1857~1909)。刘鹗选拓了一部分甲骨编为《铁云藏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版。这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刘鹗在序中已称甲骨文为“殷人刀笔文字”﹐次年﹐孙让据《藏龟》写成《契文举例》。这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此书遗稿由甲骨学的奠基者罗振玉在1917年印行。甲骨文发现后﹐古董商欺骗收藏家﹐把出土地点说成汤阴。罗振玉是学者中最早打听到真实出土地点的人﹐宣统二年(1910)﹐罗振玉作《殷商贞卜文字考》﹐考定甲骨出土之地是殷都故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遗物﹐把甲骨文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当时认为殷墟只是“武乙之墟”则是错误的)。此书印行的次年﹐清王朝就覆灭了。
清代金石学的发达﹐在专门研究《说文》的著作里也得到了反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字下引用金文的“勒”来作解释。桂馥本是金石学家﹐他在《说文义证》里屡次引用金石文字。王筠在《说文释例》里更是常常用金文的字形跟《说文》的字形作比较。
随著古文字研究的逐渐深入﹐《说文》的一些错误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吴大澄在《古籀补》自序里指出《说文》中古文的形体跟习见的铜器铭文不合﹐怀疑他们皆“周末七国时”文字。陈介祺也有类似看法(《古籀补》陈序)。吴﹑陈二氏还都对《说文》所收的籀文的时代表示了怀疑。从《古籀补》﹑《字说》等书中关于玺文﹑币文和陶文的一些话可以看出﹐吴大澄已经认识到这些文字资料基本上都是“周末”﹑“六国”时的东西。他在《古籀补》“二”﹑“钧”两字下﹐还明确指出《说文》中这两个字的古文的字形跟六国铜器铭文相合﹐应是“六国时”文字﹐不是真正的“古文”。可见吴大澄对《说文》古文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对战国文字的研究为基础的。对《说文》篆形以及许慎讲字形和本义的错误﹐吴大澄﹑孙让等人也时常根据古文字加以指出。《古籀补》凡例第一条就说:“古器所见之字﹐有与许书字体小异者……可见古圣造字之意﹐可正小篆传写之讹。”
孙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写成《名原》一书﹐从文字学角度总结自己研究甲骨﹑金文的成果。他指出文字“本于图象”﹐汉字最初“必如今所传巴比伦﹑埃及古石刻文﹐画成其物﹐全如作绩(绘)”﹐后来由于书写不便逐渐简化﹐“最后整齐之以就篆引之体”﹐才成为《说文》所载的那种文字。书中还很注意把同从一个偏旁的字放在一起来加以考察。《名原》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圈子﹐是古文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一部著作。 到了民国时代﹐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现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逐渐形成﹐古文字学也逐渐加强了科学性。
民国前期古文字研究的代表学者是罗振玉和王国维。罗振玉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于清末﹐不过他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民国时代进行的。罗氏对甲骨﹑铜器﹑金文拓本﹑玺印﹑封泥等古文字资料都有丰富的收藏。他既勤于著录﹑传布各种资料﹐也勤于研究﹑著述﹐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他的著作里﹐最重要的是在《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基础上写成的《殷虚书契考释》(1915)。此书在甲骨文字的考释和卜辞的通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为甲骨学奠定了初基。王国维是在罗振玉的影响下开始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他在甲骨﹑金文和古文﹑籀文的研究上都取得了成就。在甲骨文方面﹐王国维新识之字并不是很多﹐但往往对通读卜辞有重要意义。他的主要贡献是以甲骨卜辞与典籍互证﹐进行历史﹑地理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他在金文方面﹐著有《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和很多单篇文章。在古文﹑籀文方面﹐著有《魏石经考》﹑《史籀篇疏证》以及《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桐乡徐氏印谱序》等文章。他认为古文是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说法比吴大澄精确﹐此说现已成为定论。至于籀文究竟是不是战国时秦国的文字﹐古文字学界尚有不同意见。
罗﹑王都已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对旧的金石学有所不满。罗振玉主张把金石学改为古器物学(《云窗漫稿‧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王国维曾把前人对古铜器和铭文的研究称为“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国朝金文著录表序》)﹐还时常单独使用“古文之学”﹑“古文字之学”或“古文字学”的名称﹐可见他倾向于把金石学分为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客观存在的趋势。不过从罗﹑王的研究工作来看﹐他们还未能真正摆脱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
本文2023-08-07 09:56:17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421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