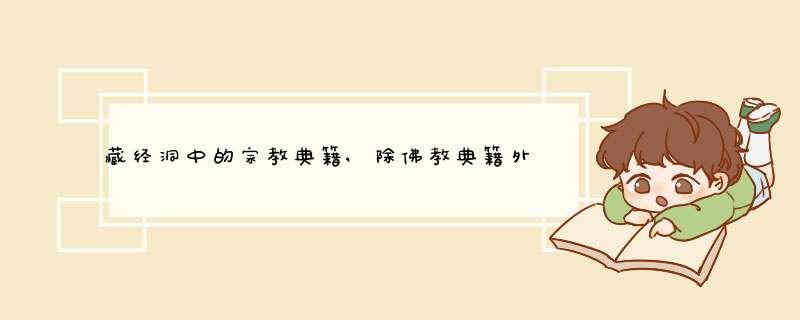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中华传统文化是以老子道德文化为本体、以儒家、庄子,墨子的思想、道家文化为主体等多元文化融通和谐包容的实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国5000年优秀文化的统领。而流传年代久远,分布广阔,被称为“汉文化圈”,文化是宇宙自然规律的描述,文化是道德的外延;文化自然本有,文化是生命,生命是文化;文化是软实力,是决定一切的内在驱动力;文化又是社会意识形态,是中华民族思想精神,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根本。
中华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包括思想、文字、语言,之后是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再后是生活富足之后衍生出来的书法、音乐、武术、曲艺、棋类、节日、民俗等。传统文化是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融入我们生活的,我们享受它而不自知的东西。
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古诗、词语、乐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清明节前后的寒食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活动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国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6)旋风装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学,诗歌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使唐代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唐代社会相应地产生并发展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备查检掌故用的类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代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也就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唐代书籍最通行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仍是单面书写的卷轴装。这样,在通行的装帧形式与要方便翻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续采用单面书写的卷轴装,翻检方便难以解决;突破卷轴装,另外采取更新的装帧形式,一时又难以创造出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打破卷轴装的外壳,又达到了方便翻检为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类书籍的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yu玉〕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这类东西,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了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描绘它是“龙鳞楷韵”,“是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态完全相同。
清朝初年的著名藏书家钱曾,也见过这类东西。《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是完全一样的。他将之称为“旋风叶卷子”。可见我们把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是不乏古人见证的。
且考自然界旋风的形象特征,亦是因某处气压低,四周空气向一处注流而形成的螺旋式旋转的风,其中大而强烈的,就是龙卷风。这种风的特点,就是空气分若干层次前后朝一个方向旋转。它的立体形象就仿佛若干张鳞次相积卷起的芦席,像个圆筒。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形式,内中书叶错落相积,朝一个方向卷收,外壳又保留着卷轴装的格局。装帧完毕,卷收起来,内中书叶很像空气分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的旋风。因此,我们认定这种形式才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不是经折装包粘一张整纸就成了旋风装,更不是经折装又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装的制约。它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经折装是对卷轴装的彻底改造,已由卷轴装过渡到了册叶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旋风装比经折装出现得要早。
(7) 蝴蝶装
(8)包背装
敦煌学·敦煌学的内容、意义及前景
随着国内外研究“敦煌学” 的兴起,引起了人们对敦煌学理论的深入探究。自八十年代起,中国学者对“敦煌学”的定义、内容等进行了争论和探讨,出现了几部专著,如刘进宝《敦煌学述论》、林家平等《中国敦煌学史》、胡戟等《敦煌史话》、荣新江《话说敦煌》等,都对敦煌学理论的研究提出了看法。目前,“敦煌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敦煌学是以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考古与艺术、敦煌史迹、敦煌学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考古、宗教、艺术、语言、文学、民族、地理、哲学、思想、科技、音乐、舞蹈、建筑、古籍校勘、中西交通等多种学科。它的目的是揭示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发展过程、内容、特点和规律;深入揭示敦煌、河西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中西交通等历史的本来面貌和发展规律,探索主要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促进现代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一个问题是,“敦煌学”是因地名学,它规定了这个学科的空间范围,是“敦煌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和标志。如中国文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如果运用敦煌文献资料研究中国文学问题,就属于敦煌学的范围,其他如历史、地理、考古、宗教、科技、民族等莫不如是。所以,“敦煌学”绝不是它所涉及的那十几门学科的简单综合,更不是把它所涉及的那十几门学科的内容统统包揽收容成一个多学科的联合体,它是一门运用敦煌提供的各种资料(地下出土文物文献,地上石窟、壁画、塑像、遗址、城址等)进行学术研究的特殊学科。因此,它与严格意义上的“××学”有别,而是约定俗成的一种已被学术界承认的学科。
研究“敦煌学”的意义何在呢周一良教授在《何谓 “敦煌学”》一文中用一长段论述来说明其意义:
敦煌壁画雕塑以及文献中的韵书等,我不敢妄论,现只就历史、文学、宗教三方面简单介绍利用敦煌汉文文献取得的若干成果,借以窥“敦煌学”粗略的一斑。
一、历史
甲 首先是旧史所不详的沙州地方历史。安史之乱后,787年(贞元二年,一说781或785年)吐蕃占领敦煌,到848年(大中二年)张议潮以河西十一州归唐,共六十余年。吐蕃赞普派“节儿”统治沙州,汉族官员苦闷屈辱,人民发动起义。唐蕃文化有所交流,敦煌禅僧入藏,多次与印度僧人展开辩论。张议潮归唐后,赐号归义军节度使,世代承袭。七十年后,920年曹议金取代张氏。1035年西夏取敦煌,而曹氏的地位可能维持到1055年。张曹两家统治敦煌前后二百年,与唐、五代、宋朝的中央政权虽保持受封与朝贡关系,实际处于半独立状态,曹议金曾自称大王。沙州境内有不少昭武九姓与鲜卑、吐谷浑等族人,他们从事力役兵役,与汉族杂居通婚。沙州统治者西与于阗、东与甘州回鹘通婚,以确保东西贸易的利润。这些都是靠综合变文、碑文、壁画供养人题名、造窟造像人题名以及各种文书得以考见的。
乙 唐代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历史。敦煌发现唐律及疏以外,还有令和格的残卷以及保存相当完好的水部式,亦即水利管理条例。从户籍簿、差科簿等可以了解徭役、兵役以及均田制实施的细节。学术界趋向于肯定均田制确曾实行,但受田并不足数,而徭役沉重。农民土地分割细碎,且存在所谓 “自田”。从 “社司转帖”得知民间存在称为社的互助组织;从书仪得知一些流行的婚丧礼俗。《氏族志》、《沙州图经》等提供了关于氏族和地理的资料。有名的《往五天竺国传》是新罗僧人慧超入唐后又经中亚去天竺的旅行记。他返唐后终于五台山,这部书是研究当时中亚和印度的重要史料。
二、文学
唐人记载中有所谓“目连变”、“昭君变”,过去不详究何所指。敦煌写本发现后,才解答了这个谜。原来变指变文,是一种兼有韵散、用于讲唱的通俗文学作品。敦煌还发现唐代曲子词《云谣集》。二者都是填补唐代文学史上空白的重要发现。王梵志的白话诗既谈佛理,亦讽时俗,当时颇有影响,为后来寒山子诗的先驱。过去记载中保存了若干首,敦煌写本出现后,才能略窥全豹。韦庄的《秦妇吟》是晚唐士大夫阶级诬蔑农民大起义的作品,但其中也保存一些可供参考的历史材料。过去只在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留下很能反映农民大起义威力的两句:“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敦煌石室中保存了此诗的完整写本,对于研究唐代历史与文学都大有裨益。
附带谈一下敦煌发现的经史子集四部书。虽然数量不多,但保存了某些已佚的古注,而且唐人手写旧本往往保存古字。唐人所写当时俗体字,有些还可以帮助了解后代刊本致误之由。这些都有益于古籍的研究与校勘。写本四部书都属于寺院所藏,史部特别少,反映当时寺院对此不很重视。十三经中只发现九经,没有 《周礼》、《仪礼》、《公羊传》和《孟子》。究属偶然未保存下来,抑或反映某种倾向,有待探讨。
三、宗教
甲 敦煌的佛教势力很大。日本学者估计,当时唐代敦煌县人口两万而僧尼约占一千人。寺庙十几座,十三个乡中至少每乡有一寺,还不算规模较小的“周家兰若”、“张家佛刹”之类。寺院役使沙弥、园子、“常住百姓”、奴婢,还有专门从事某一手工业的梁户 (榨油)、硙户 (磨米面)、酒户以及牧羊人等。寺院田地之外还拥有菜园、果园。从寺院公布的帐目看,收入除“念诵入”、“转经入”之外,最大宗是出借谷、麻、豆等等的“利润入”,半年即取息50%。足见寺院高利贷剥削之重。敦煌发现的佛经中,三方面的写本很有意义。一是大藏中未收的佚经,和不属译出而是中国本土根据当时当地需要杜撰的“伪经”。二是初期禅宗史料,即被主张顿悟的南宗所取代的主张渐悟的北宗的经典。三是短期存在的小宗派的经典,过去不为人所知,如三阶教的经典。
乙、道教 从文献看不出敦煌道观的记载,但石室发现的道教经典,有的钤有 “净土寺藏经”印记。西晋开始出现《老子化胡经》,说老子渡流沙入夷地,成浮屠以化胡人。六朝至唐出现多种化胡经,在石室中可以找到写本,有助于研究道教史和佛道关系。唐陆德明《经典释文》里提到《老子想尔注》,说“不详何人。一云张鲁,或云刘表”。敦煌发现想尔注残卷,学者们认为是张陵张鲁系统的五斗米道徒所注,是研究五斗米道教义和老子书与五斗米道关系的重要材料。
丙、其他宗教
三世纪波斯人摩尼在佛教、火祆教、基督教影响下创建的摩尼教,和五世纪涅斯托里斯在东罗马帝国创建、属于基督教一个教派的景教,唐时都曾传入中国,其经典都可在敦煌写本中找到。
以上仅就敦煌汉文文献在三方面的利用略作介绍,已可看出其内容丰富异常。
其实,敦煌文献及文物所涉范围十分广泛,但它们有着都与敦煌有关这一特点。即便是中原的公文、四部书、 颁发的写经,亦或是梵文、吐蕃文、于阗文、回鹘文等写本,莫不与敦煌的历史文化有关。而敦煌又处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各种文化相交汇,呈现出多彩多姿的状态,自然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敦煌文献的发现,改写和充实了许多学科的历史。在今天,许多学科中如果缺少了敦煌的资料,可以说是不完全的。
从七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及世界各地的敦煌学研究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的敦煌学研究队伍已经扩大到三百人以上,其中多数为中青年学者,其中有些人脱颖而出,已经在某一学科、某一专题有所发明、有所建树,受到了世界敦煌学界的重视。
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敦煌莫高窟列入“世界遗产清单”(中国同时列入的还有泰山、长城、故宫、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及秦兵马俑坑),敦煌莫高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敦煌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摆在敦煌学者们面前的任务仍然是极其艰巨的,而前途也是光明灿烂的。要想使“敦煌学”取得更大的成绩和更多的成果,有几项任务是必须着力进行的。
第一,对散落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要有一份尽可能完整、详细、准确的注记目录,这是进行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
第二,尽可能编定反映全世界敦煌学者研究成果的论著目录,是促进研究深入的重要方面。
第三,尽可能将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及文物刊布,以便使用。
第四,各种文献的分类整理研究成果,应尽量采用专题形式进行,以利各学科非敦煌学者使用。
第五,对敦煌文献、石窟壁画、题记、敦煌遗址及遗迹、传世文献进行综合性研究,找出和解决有关“敦煌学”的一些最令人关注的课题。
第六,加强与非敦煌学者的合作。
当然,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的增多,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中青年敦煌学者的崛起,相信不久的将来,“敦煌学”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它的明天会更加辉煌。
道士下山:曝敦煌遗书被发现时的灵异事件
什么叫敦煌遗书学术界的定义是敦煌出土的公元四至十一世纪古写本及印本,系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献——
发现时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
发现地点:敦煌莫高窟
发现者:一位道士,名王圆箓
然而,王道士这次发现,并没有人为之欢呼,也没有人表扬,文化名人余雨先生甚至曾称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未成功臣,反当罪人。为什么笔者想来原因很多,说到底就一句话:发现的不是时候!
●一个小道士的大发现
人们记得王圆禄,只因他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正由于他不经意间的发现,使他一下子成为名人。
历 史定格在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甘肃敦煌,一扇历史之门悄悄地被湖北麻城籍道士王圆禄偶然打开,被古人封存了近千年的 5-11世纪的珍贵写本得以重见天日,以至于20世纪的世界文化发现史上注定要记下这样的文字:王圆禄道士发现了敦煌藏经洞。而今密室已不再是密室,渐渐 地人们称它为“藏经洞”,而把藏经洞内的经卷文书称为“敦煌遗书”。敦煌遗书与甲骨文、汉简、故宫明清档案一起,被誉为近代中国四大学术发现之一,并被称 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
遗书发现者道士王圆箓
王 圆禄(1850-1931年)又作圆箓,多被称为“王道士”。湖北麻城人。《麻城县志》载,咸丰六年(1856年)夏天,麻城遭遇旱灾,庄稼几无收成。迫 于生计,王圆箓逃离家乡,来到酒泉一带,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退伍之后,为解决吃饭问题,王圆箓想出了一个妙法——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大约在光绪 23年(1897年),他西游来到敦煌莫高窟。其时,莫高窟虽已萧条异常,但因为有百姓的供养,寺院的香火依然时而接续。对已到不惑之年的王圆禄而言,这 个清静的所在正是他度过残生的绝佳选择。
王圆禄发现藏经洞的过程还颇具传奇色彩。开凿于鸣沙山东崖上的莫高窟,由于西北风的长年吹打,流沙 便从窟顶不断地蔓延下来,洞口甬道堆满了沙土,整个洞门都被封了起来。王道士雇了几个伙计帮助清除长年堆积的沙子。那一天,编号为16窟甬道的沙土已经渐 次清理完毕,一位姓杨的伙计发觉甬道北面壁裂一孔,怀疑暗藏石室,于是,王道士与杨某夜半破壁,一个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难得的惊人发现就这样被一个不知考古 为何物的道士发现了。
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唐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王道士面对这么多古代经本和画卷,思考着怎样利用它们来换取一些功德 钱。王道士最先赠送的对象是安肃道台兼兵备使廷栋,不料廷栋这位颇自负的满族官僚只是觉得这些古代写经的书法不如自己写的好,而没有对它们表示特别的兴 趣。但王道士不甘心,仍旧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赠送经卷,求得捐助,以至于甘肃的地方官绅有许多人都接受过王道士的经卷赠品。
1902 年3月,湖北人汪宗瀚出任敦煌县令,汪县令很快就得到了王道士送来的经卷和绢画。当这位进士出身、谙熟历史文化的县令见到经卷后,立即判断这些经卷不同一 般,并于1903年冬天,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兰州的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通过汪宗瀚,不仅获得了敦煌莫高窟留存的碑铭拓片,还收到藏经洞出土的佛画、 经卷和所藏石碑、梵文写本等。只是汪宗瀚所传递的消息极不准确,说洞中经卷只有几百卷,并且好像已经瓜分完毕。所以,叶昌炽虽然一眼看出藏经洞经卷的价 值,但始终没有踏上敦煌一步。倒是那位对王道士态度冷淡的廷栋,后来真的把藏经洞的消息上报了甘肃藩台,但甘肃藩台以敦煌到兰州的运费难以凑齐为由,仅给 汪宗瀚发了一张命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于是,汪宗瀚亲临莫高窟执行这道命令。这是第一次由政府出面对藏经洞进行封存。由于封存措施不力,王道 士表面应承,实际上仍不断地从洞窟取出经卷悄悄出售。直到藏经洞的藏品纷纷被运往国外,造成敦煌遗书的大量外流,当局仍一无所知。
虽然在外国人到达敦煌之前,中国曾有7年的时间可以妥善保护藏经洞写卷,但却一次又一次地失之交臂。接着发生的就是众所周知的西方探险家对敦煌遗书的大肆劫持。尤以英斯坦因和法伯希和为最。
斯 坦因第一次来敦煌是在1907年3月12日。由于不会说汉语,第一次与王圆箓沟通时,王圆禄只答应接受斯坦因的慷慨布施,想看一看书稿,想买几木书卷的请 求被委婉地拒绝了。通过观察,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对唐僧顶礼膜拜”。于是,在绘满出自当地画匠之手的唐僧传说的道观大殿里,斯坦 因向王圆箓大谈自己对玄奘的崇拜,他甚至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圆箓,以等候自己——一个从 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即“唐僧之徒”为名,骗取王圆禄的信任。显然,王圆禄被斯坦因“忽悠”了。虽然二人有了共同话题,但王圆禄仍然坚持不让斯 坦因进入藏经洞,而是亲自搬出一捆经卷到大殿的耳房供其翻阅。最终,他接受了斯坦因开出的条件,以40锭马蹄银(合200两银子)的代价出卖了所有被斯坦 因和蒋师爷选中的经卷、帛画,并且追加了6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当斯坦因离开莫高窟时,仅经卷文书装满了24箱子,精美的绢画和刺绣艺术品等文物 又装了5大箱。后经清理,卷文完整的有7000件,残缺的6000件,还有一大批其它文物,开创了敦煌遗书大量流向境外的先例。因为斯坦因不懂中文,他带 走的文件中有很多没有价值的东西。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时,又以500两白银的捐献,从王圆禄手中换去570部汉文写卷。这些卷子是王圆禄专门收集的,均为 完整的长卷,价值极高。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前脚刚走,法国人保罗伯希和又来到敦煌。伯希和不仅是汉学方面的专家,而且极富语言天才,至少会讲13种语言。对汉语犹为精通,古汉语中的文言文他都能看懂。
1908 年2月,伯希和到达敦煌。在此伯希和与王道士进行交涉,伯希和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而且,王道士从谈话中得知,伯希和并不知道他把一大批 写本出卖给了斯坦因,所以对这些洋人的坚守诺言感到满意。伯希和同样使用了金钱诱惑的办法,答应给王道士一笔香火钱。经过大约二十多天的交涉,在3月3 日,伯希和就被引进藏经洞,而且还允许他在洞中挑选。
这是外国人继斯坦因之后第二次走进藏经洞,伯希和经过三周调查了藏经洞的文件,最终伯 希和以500两银子(约90英镑),换得了藏经洞6600余卷写本精品和38幅大型绘画。虽然伯希和比斯坦因晚到藏经洞一年,但斯坦因并未能进入藏经洞内 挑选,未能看到全部藏品,而伯希和则不同,他不仅亲自进入洞窟翻检了所有藏品,而且他精通汉语,有着丰富的中国和中亚历史文献的知识,获取遗书的数量虽不 如斯坦因,但几乎全是精品。伯希和后来在一次演讲中称:“在近两万卷子中,只后悔看漏了一个。”
伯希和将获取的卷子从天津以海路运往巴黎 后,于1909年5月来到北京。得知清朝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正在“物色各种古籍,以保存国粹”,不知他出于炫耀或别的什么心理,伯希和随身携带一些敦煌 珍本,如《尚书释文》、《沙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碑赞合集》等在北京六国饭店展示。当时,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京师 大学堂经科监督柯劭忘、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江瀚、京师大学堂教习兼学部编译局次长王仁俊、京师大学堂教习蒋斧、国子丞徐坊、知名学者罗振玉、 董康等都前往参观。这些京城的官员和学者看到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尚书》死卷等珍品后,“惊喜欲狂,如在梦寐”,始得知甘肃敦煌有重大发现。
9 月4日,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者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还有董康、吴寅臣等,其中主要是京师大学堂的一批学者。在招 待会上,恽毓鼎在致词中,正式提出影印其中精要之本的要求,伯希和表示“自可照办”。具体实施者是罗振玉。罗氏又请端方襄助,敦请伯希和出售所携和已运回 国的四部要籍写本照片,伯氏如约,陆续寄到,端方分交罗振玉和刘师培考释。同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造访伯希和于苏州胡同,随即得知敦煌石室尚有卷轴约八千 轴,但以佛经为多。罗振玉立即报告了学部左丞乔茂楠,并由罗代拟电报,命陕甘总督、护理甘肃都督毛庆蕃立即查封敦煌藏经洞,并将所余遗书悉数解运京师。甘 肃方面接到学部电报后,甘肃藩司、代理巡抚何彦升刚刚到任,他命令敦煌知县陈泽藩点查剩余经卷,解运京师。而此时,距藏经洞发现已整整9年。
1910 年,劫余敦煌遗书从敦煌启运。陈泽藩派傅宝书、武相臣两人负责运卷大车的押运。事实证明,傅宝书、武相臣在押解途中,不尽心力,所经之地敦煌卷子任当地官 员抽取挑选,并擅自出卖,又为掩人耳目,一卷撕开充作两卷。之后,才移交学部,共18箱,编号计8679卷。然而,这种分裂经卷以充件数的行径很快就暴露 出来。当时,学部侍郎宝熙发现运送学部的卷子有问题,于是,他写了上告奏折,负责押运的傅宝书被扣留。只因辛亥革命起,清朝官人自顾不暇,不得已,将傅宝 书放回了甘肃,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因此,我们在理直气壮地指责外国探险家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不免多了一份伤痛和尴尬。
1931年,王圆禄80岁高龄死去。按道家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但王圆禄的弟子还是为他修建了一座很有气派的土塔,塔碑上记载了他发现藏经洞的过程。
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
确切地说,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
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
参考资料:
国家图书馆古籍资源的类型包括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西夏文献、赵城金藏、地方志、家谱、年画、老照片等。
我国的古籍:
1、《永乐大典》——百科类
《永乐大典》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占卜、戏剧、工艺、农艺等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2、《四库全书》——百科类
《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包括了我国几千年来的重要文化典籍,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
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3、《梦溪笔谈》——科学类
《梦溪笔谈》就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本书由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撰,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
我国古籍的价值:
1、文献价值。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旧抄本、古本、初刻本、精刻本以及各类活学本等版本的价值较高。
3、艺术价值。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写刻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短版、拱花、版画等。
4、学术价值。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录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刊元椠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人物生平
清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年),段玉裁出生于江苏省金坛西门外大坝头村,有一姐二弟一妹,父亲虽为塾师,但收入微薄。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执教,家务全由母亲史氏操劳。全家人衣着粗布,常年是大麦粥糊口,很少吃上白米饭,家境非常清贫。
乾隆一十三年(1748年),十三岁补诸生,曾至扬州安定书院就读。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十五岁中举人,任国子监教习,入都会试,屡不中。经人介绍,段玉裁在京就教职,获读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有意于音韵之学,遂边教边做学问,历时约10年。在京时,师事戴震,并结识了钱大昕、邵晋涵、姚鼐等学者。返里后,又得与刘台拱、汪中、金榜等人相交。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吏部铨授贵州玉屏县知县,两年后,调到四川省,先后任富顺、南溪和巫山县知事,仕宦期间,均携《六书音韵表》于身边,每每处理完公家事务至深更半夜,经常置灯于笼中,或以口气嘘物取暖,编著、修改文章。经10年,他以父母年迈多病、自身有疾为由,辞官归故里,卜居苏州枫桥,潜心著述和藏书,时年仅47岁。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二次入都,得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商讨音韵、训诂,颇为契合。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移居苏州阊门外之枝园。出身寒素的段玉裁,毕生铭记“不耕砚田无乐,不撑铁骨莫支”的祖训,一生以著述为乐事,他克服重重困难,潜心注释《说文》。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四月,不幸跌坏了右腿,从此成为残疾之人。当时的段玉裁曾对友人说,“《说文注》三年必有可成。可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段氏坏足,《说文注》成。”其后健康每况愈下,盖春夏秋三季多不适,而春季尤甚,疮烂疥烦,两眼昏花,心脉甚虚,稍用心则夜间不能安宿,又左臂疼痛不可耐。此时段玉裁最为担心的事,是注释《说文》能否完成,他曾对友人说,他身体旧病如故,担心《说文注》难成,加上精力不足。假如完成后死了,就很欣慰了。到段玉裁注释《说文》完成时,他对自己的学生说,他如春蚕一般,茧织成了,只待等死矣。
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完成的《说文解字注》30卷。嘉庆二十年(1815年)五月《说文解字注》全书刻成,为将此书刻成付印,他用去了全部积蓄。
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年),9月8日在贫病交加之中去世,卒年八十一。
主要成就 学术成果哲学思想
实事求是是乾嘉学派学人的共同旗帜和人生信仰。段玉裁是戴震的大弟子,他虽未能像他的老师那样写出一系列哲学著作,但在学术理想、路线方面基本遵循了戴震所开创的皖派学术风格,并有其独 献,特别是他在古典语文学研究中所贯彻的追求真知的精神,与戴震是相通的。他说:“凡著书者,将以求其是而已,非将以求胜于前人而要名也。将以求胜于前人而要名,则吾斯未信,而欲天下后世信之,无是理也。虽然,吾非以要名,吾非以求胜于人而诚求其是,则其书之成,宜必可信矣。”
在哲学立场上,段玉裁也继承了戴震反宋儒的观点,坚持“阴阳气化即道”、“必于物上求理”,反对“执意见以为理”。他在《十经斋记》一文中说:“余自幼时读四子书注中语,信之惟恐不笃也,即壮乃疑焉。既而熟读六经、孔孟之言,以核之四子书注中之言,乃知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与六经、孔孟之言大异。六经言理在于物,而宋儒谓理具于心,谓性即理;六经言道即阴阳,而宋儒言阴阳非道,有理以生阴阳,乃谓之道。言之愈精而愈难持循,致使人执意见以为理,碍于政事。”而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就反复批评宋儒视理为得于天而具于心的观点,认为宋儒执意见以祸国殃民,甚至造成“以理杀人”的恶果。
段玉裁在“求真”学术理念的支撑下,批评王应麟著《困学纪闻》和顾炎武著《日知录》的著书方法,认为这种著书方法有两种弊端,一是好为异说,二是剿说雷同,中无所得,仅邀名而已。王应麟与顾炎武都以博学著称,而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还曾接引段玉裁进入古典语言学。但段玉裁受戴震影响,领悟为学真谛,不再博学以夸能,而是以追求真知与十分之见为人生信仰。他说:“闻之东原师曰:知十而皆非真知,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洞彻其本末,剖其是非,核诸群书而无碍,反之吾心而帖然,一字一句之安妥,亦天地位,万物育之气象也。久能所说,皆得诸真知,故近以自娱娱亲,远以娱人,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其传世行后无疑也。”
不仅如此,段玉裁还认为,通过追求真知的活动,上可以神交古人,下可以神交后人,使人的生命存在超越时间限制,进入永恒的境界:“夫人有心得之处、超乎古人者,必恨古人不我见,抑余以为古人有言有为,未尝不思后人处此必有善于我者,未尝不恨后之人不可见也。”在追求真知的活动中寻求短暂生命的永恒意义,这一价值理想说明,乾嘉学者的学术活动并不仅仅是外在的政治压迫的结果,他们在考据学中找到了精神寄托。
段玉裁并未简单重复老师的观点,而是在“求是”的问题上发展了戴震的学说。他认为“追求真是”是一个历史过程,从原则上说后代胜于前代,后人通过研究不得已要与前人不同,是追求真理的一般规律所致,并非有意难为前人。他说:“著书者,固以天下后世信从真是之为幸,而非以天下后世信从未必真是之为幸。左氏非不乐公羊、谷梁之后出,杜氏非不乐刘炫辈之后出,朱子在今,必深幸诋议之有人。夫君子求为可信,不求人之信。求其真是,而亦不敢自必为真是。此真是之所以日出也。”与戴震所说的“十分之见”的自信相比,段玉裁更明白“真是”不易得,而且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研究的深入,“真是”也在不断发展。
经学研究
在“经学”研究方面,段玉裁没有写出系统的哲学著作,但他通过对《春秋》、《左传》、《大学》等经典文本中的具体字义、句子的辨析,尤其是对明世宗继统问题的系统研究,阐发了其政治伦理思想,也提出过一些突破传统经学思想的主张。晚年的段玉裁在写《十经斋记》一文时,对于训诂、名物、制度、民情物理四者三致其意,而且自称“不敢以老自懈”。段玉裁对于名物、训诂、制度的研究,主要表现出“求是”精神,而对于“民情物理”的关心,则表达了“求道”的理想。
段氏博大精深的小学是段氏经学的方法论支撑。清初顾炎武在回答什么是经学问题时曾说:“理学,经学也。”就是“舍经学即无理学”,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舍小学即无经学。段氏小学为解经服务,小学是治经的工具。段氏小学伟岸,经学成就亦因此富厚。经学史在段玉裁那里,实在是围绕群经的语学工具逻辑应用史,经学史是经书传注史。
《周礼汉读考》(1794年)对读经的语言逻辑指要。段玉裁《周礼汉读考》最重要的贡献是,为读懂《周礼》提出了汉代人注释《周礼》的体例:《周礼汉读考序》提出的“汉注正读”三式。段说:“汉作注,于字发疑正读,其例有三:一曰读如、读若;二曰读为、读曰;三曰当为。”这段文字,同样见于《说文段注》“读”字下,正可看做独立之古代语学移置于经学用作辞例。读如、读若:“拟其音也”,是用来拟比同音字、近音字的。读为、读曰:主要是用来指明意义的变化。当为:段说:“字误、声误而正之,皆谓之当为。”
《尚书》学领域建功勋。清初声讨伪古文《尚书》是有思想启蒙意义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之为“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尚书》为十三经之一,十三经为封建社会正统指导思想,揭露《尚书》伪作,当然是对封建统治思想的冲击。乾隆年间段玉裁研核今古文《尚书》,为揭梅赜伪作的余绪,意义不凡。
自然科学与读经。段玉裁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入经,章炳麟《检论清儒》曾说段玉裁以“十三经”为少,“宜增《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及《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皆保氏书数之遗,集是八家,为二十一经”,这样,段氏所增八经中有两经是数学书,足见段氏说经对自然科学的重视。
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就是段玉裁对今文经的包容态度。段玉裁曾特别要他的外孙龚自珍向古文经学者程瑶田学习。后来今文经学家龚自珍写成《明良论》四篇,揭露清代官僚政治的腐败,段玉裁80岁时读到此文,盛赞其“切中今病”,“髦(出类拔萃)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遗憾)矣。”
语言文字学
段玉裁主要继承、深化并细化了戴震的语言学研究,在声音与意义的关系、经典中“本字”的考订、 注经原则的发明等古典语文学方面,成就突出。
段玉裁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在语言文字学,主要成果集中在《说文解字注》一书中。“注释”是古人著书立说的重要体裁,如果说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重在经汉字字形揭示汉字的本义,清代段玉裁则重在用传世文献揭示汉语词的引申义。我们今天讲段注在词义学、词汇学上的贡献,主要是以段注引申义为基础的。段注把古今的字形、字音、字义都贯通起来,因而更显得体大思精。
段注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九千多个汉字安置于新的古音韵系统,一一标明各字的韵部。附于段注书后的《六书音韵表》就是九千多字的位置系统,即上古韵部系统。段玉裁古韵学成就可以归纳成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了一系列古音学的原理,成为古音理论的集大成者,特别是开辟了从谐声偏旁入手来研究古韵分部的新途径和新的方法系统。二是分上古韵六类十七部,超迈前人,启导后来。段玉裁、戴震论韵十五年成为学术史上的佳话。经过研讨,在上古“支、脂、之”三韵部分立问题上,双方达成共识。但在上古真部与文部的分立问题上,戴始终没有接受段的意见,今天,上古真、文分部已成定论,段是正确的。
段注的再一个重要贡献是,除了指出《说文》各部首内相关汉字之间的意义联系,使许慎《说文》变得井井有序,“如一篇文字”以外,还就全书范围内意义相关字不断勾稽指示,使之组合类化。
段玉裁高足弟子之中,长洲徐c、嘉兴沈涛、女婿仁和龚丽正(龚自珍之父)较为知名,长洲陈奂尤其得其学识真传。
个人著述文字训诂
段玉裁博览群书,著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在小学范围内,又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根基充实,深得体要。所著有《六书音均表》、《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汲古阁说文订》、《说文解字注》及《经韵楼集》等书。《六书音韵表》在顾炎武《音学五书》和江永(1681~1762)《古韵标准》的基础上剖析加密,分古韵为17部,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周祖谟认为此书“在
本文2023-08-07 12:04:2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431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