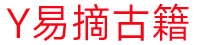万首唐人绝句书中的五绝六绝七绝各是多少首?

《万首唐人绝句》 中国唐代绝句诗总集。宋代洪迈编。迈(1123-1202),字景卢。洪迈辑唐人绝句5000多首,进呈宋孝宗后,复补辑备足万首之数。原本100卷,每卷100首。凡七言绝句75卷,五言绝句25卷。末附六言绝句1卷。此书汇集了唐代诸家诗文集、野史、笔记、杂说中的绝句诗,有保存资料的劳绩,但为凑满万首,不免滥收,窜入少数非唐人作品。并且有割截律诗为绝句,一人之诗分置几处等现象。《万首唐人绝句》有明代陈敬学仿宋刊本。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以影印,较为通行。清王士禛有《唐人万首绝句选》7卷。
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是宋代较为著名的一部唐诗选本,它的产生引起了一股宋人选唐绝句的热潮,许多不载于他书的唐绝句,赖此书得以保全。理清其版本情况是研究《万首唐人绝句》和唐诗的一项重要工作,但现在学术界在这方面还是一个空白,本文就其版本流传情况进行了探讨。
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开启了宋代专选唐绝句的热潮,许多唐人绝句藉此保存下来。版本刊刻较为复杂,洪迈二次刊刻此书,定为一百卷本。宋人吴格对其部分修正,宋人汪纲重刻此本,因另析出六言诗为一卷,改为一百一卷。此书宋本已佚,有明刻本两种存世。明嘉靖陈敬学据汪本重刻。明万历赵宦光因洪迈原编舛误较多,再作校订补充,重新编定,改为四十卷。
论文: 1王立民,叶昌炽研究述论,《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7期 2王立民、刘奉文,《沈石友题画诗留稿》笺释,《文献》2009年4期 3王立民、佘彦焱,钱曾藏书之来源概述,《图书馆杂志》2009年4期 4王立民, 叶昌炽字号及藏印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4期 5王立民,《缘督庐日记》稿本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3期 6王立民, 叶昌炽生卒年辩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5期 7王立民,从古代小说观的演变看先秦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吉林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4期 8王立民,师范院校毕业生教育实习面临的困境及对策,《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中国语言文学系教学研究专辑)2002年 9王立民,古代诗歌中格桐悲秋意象探源,《东方杂志》第一辑2002年4月 10王立民,读《诗经》说葫芦,《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3期 著作: 1《缘督庐日记》校点(第一册),吉林文史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5月。 2《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研究》(专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3 孟子译评(古籍整理)(国文珍品文萃),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7月。 编著: 1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文学艺术等部分,副主编),辽海出版社2007年9月 2中华文明实录(物质文明卷,参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 3中国文学史话(元代部分,参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 主持项目: 1晚清著名藏书家叶昌炽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B级) 编号:10BZS006,2010年7月开始,进行中。 2清人小说序跋与小说内容的相关性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与文学的发展”团队项目,三级子课题。进行中。(校内项目) 参加项目: 1吴格主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戏曲小说部分整理)(约15万字),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C级)2002年开始,接近完成。 2黄季鸿主持,《西厢记》研究史,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C级)2007年11月开始,进行中。(第三参加人) ,3裴丹莹主持,师范生职前实践能力培养研究,国际合作项目(C级),2007年12月开始,已结项。(第三参加人) 4陈向春主持,“大诗教”视野里的传统诗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规划基金项目(C级)2008年11月开始,进行中。(第一参加人) 5张洪兴主持,明清庄子学书目考,吉林省社科规划项目(省级),2009年5月开始,进行中。(第一参加人) 获奖情况: 1《缘督庐日记》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获第27届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 22010年,《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研究》,获东北师范大学第八届优秀社科著作一等奖。 32008年、2009年连续两年被评为东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生教育实习优秀指导教师。 4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并获得复旦大学第五批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资助。 52002-2003年度被评为东北师范大学学生档案管理工作先进个人。 61994-1995学年被评为榆树市实验中学先进个人。
一年写诗百多首
黑黑现为上海某中学初三学生,诗集名《天为神州降此童———黑黑癸未诗词存稿》是诗歌界人士专
为他题写的,诗集中收录了他2003年间的诗词作品,共有101首。
上海师范大学陈克艰教授认为,黑黑的诗作绝不是因为作者年幼,才显得好,他语汇的丰富、见解的精审,甚至可以追配古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严寿澄教授表示,黑黑的诗“融经铸史,出入唐宋,而自成为,黑黑之诗”。复旦大学吴格教授干脆认为黑黑无愧于前贤“江山代有才人出”的赞美。
《古文观止》读3遍就能背
该书责编、资深新诗评论家唐晓渡告诉记者,诗歌界所有已经阅读过黑黑旧体诗的专家学者,没有不使用这些极端的赞美之词的。
唐晓渡告诉记者,由于与黑黑的父亲早年相识,所以他知道黑黑从小就过目不忘,比如《古文观止》只要读一遍,85%的内容他都能记下,读3遍之后就能全文背诵。而且黑黑特别热爱古典文学,除了上学时间,他可能平均每天要花费10个小时看书,甚至没有任何别的少年的爱好。
上海古籍所欲破格吸收
“黑黑的阅读非常广泛,他读什么,家里人基本不管,只是有时候觉得他看书有些太费时伤神的时候,才劝他少读。”由于黑黑现在就读初三,课业负担其实相当重。黑黑的父亲程兆奇是上海社科院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研究的专家,他介绍除了学校规定的课程和作业外,家人没逼他在功课上花费时间。但是,程兆奇对黑黑的身体非常担忧,他告诉记者,这次黑黑的诗集封面照片其实是黑黑9岁时的照片,那时的黑黑十分健壮,可是由于大量读书,长期的睡眠不足,对视力、体力、精力的损害和消耗相当大,现在的黑黑不仅十分消瘦,甚至还有些驼背。“所以我们现在从来不给他任何压力。”据悉,上海古籍研究所甚至希望能破格吸收这个16岁的少年,不过被黑黑的父亲拒绝了。
心理:不应给孩子太大压力
一位心理专家表示,黑黑这种现象属于心理成熟期早,所以从开始就保持单一爱好,甚至会有不符合他年龄的惊人之举产生。但是孩子终归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们需要听到更多鼓励的声音,但是不意味要给他们强加一些头衔让他们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自动往那些头衔上去贴合,这样对孩子心理轨迹的铺设和健康成长并没有益处。
本书作者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肯尼斯•罗伊•诺曼(Kenneth Roy Norman , 1925— )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印度学家、佛教语言文献学家之一,他的专长主要是研究中古印度雅利安语。这类语言又称印度俗语(Prakrit),是相对于印度古婆罗门教与印度教的经堂语梵语(Sanskrit)而言。在学生生涯之中,他就师承可能是20世纪最为伟大的一位,同时也必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剑桥大学梵文教授贝雷爵士(Sir Harold Walter Bailey,1899 – 1996)。
贝雷爵士的学术成就其实应该专文介绍,此处只是简单提一下,即使传说他能够阅读五十多种语言的说法实在无法证实,但文献可征者,至少他可以阅读的语言中包括英、法、德、俄、意大利、西班牙、拉丁、古希腊、泰米尔、阿拉伯与日语,而由于他教书的关系,又可以说是“非常精通”梵语、巴利、犍陀罗、于阗、阿维斯塔等诸多古印度雅利安语族的语言。
与这样一位专攻伊朗语支,却同时可称为通才的老师不同,诺曼教授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之中主要专攻公元前阿育王石刻铭文的语法、语音及其语言学特性,与此同时,诺曼教授也是目前存世最为伟大的巴利语专家之一。他一生中校勘或翻译了巴利语圣典《长老偈》、《长老尼偈》、《经集》、《法句经》、《波罗提木叉》等。1983年,他还出版了典范性的著作《巴利文献》(Pāli Literature,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83)一书。
他学术生涯中的大量单篇研究文章,后来被收入巴利圣典学会(Pali Text Society)结集出版的著作集之中,达整整八卷之多。正是因为他对佛教文献学,尤其是巴利文献整理的巨大贡献,所以自1981-1994年间,他成为了具有百年历史的巴利圣典学会的会长。而且,作为英国人文学科学界的最高荣誉,他也是历史悠久的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顺便提一句,目前对汉语佛教文献学界作出空前成就的日本学者、创价大学佛教高等研究所所长辛嶋静志教授也曾在20世纪80年代到剑桥大学学习,当时其指导教授就是诺曼。并且,据辛嶋老师本人多次回忆,诺曼教授的研究风格对他的一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1994年3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邀请诺曼教授以“佛教传道协会访问教授”的名义,举行了一系列的演讲。此一演讲共分十讲,主要是从一位佛教语言文献学家的角度来谈佛教研究之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这些演讲内容,后来就结集成书(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 SOAS, London; reprinted by Pali Text Society),本译就是以此结集所成为底本。
诺曼这一系列演讲的纲领性重要程度还在于,作为一位佛教语言文献学最为顶尖的学者,他试图将本领域之中极为深奥的问题,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来向“普通读者”作一番细致入微的阐述。不过,我想预先提醒一下,即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不小的耐心与知识储备,尤其是古印度的语言知识,方能“完全读懂”这本小书之中的不少内容。
在这十讲之中,诺曼教授谈了从语言文献学角度来如何看待佛教起源的一些重要问题,着重研究了书面文字书写之前佛教文献的口传传统,并指出这种传统对后世佛教文献形成的重大影响。诺曼还在演讲中谈到了佛教与各个印度区域方言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上的佛陀究竟是讲述何种方言这一类问题的学术研究情况。后来,佛教文献被书面写定下来,而这种书面写定不仅使得比如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圣典被固定了下来,诺曼还试图表明,与此同时,这还为新的大乘经典提供了方便之门。公元前,佛教就逐渐从开始时的拒绝梵文的态度,慢慢回归到了梵语化的道路之上。但在这种梵语化的过程之中,就实际操作而言,却出现了各种文献的扭曲。诺曼正是通过各种精细的案例分析,让我们看到这些文献错误形成的原因及其过程。
阿育王是早期佛教由地方性宗教走向泛印度次大陆的宗教并最终实现国际化的一个关键。诺曼教授就同样从佛教语言文献学的角度,来分析过去关于阿育王的诸种传说,并参以有实实在在文献纪录(阿育王摩崖铭文与石柱铭文)的那个阿育王,看看何者更为真实。在整个演讲系列的最后,诺曼还以大量详实的资料来阐述佛教文献最终编纂为藏经圣典,以及整个圣典的巴利注释书传统对佛教未来的诸种影响。
从上面的简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虽然是一部概论性的普及读物,并且诺曼本人也一直在用一种更为明晰、简洁的方式来阐述佛教语言文献学的研究,但此书的信息量却同样巨大。因此它可以说是诺曼教授一生研究的一个缩影或标本,是一部真正的“大家小书”。我相信通过这本书的阅读,我们会发现,原来有些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简单问题,其实在佛教文献学家的眼里却有着完全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比如“四圣谛”、“辟支佛”、“菩萨”、“法华经”等基本概念,我们佛教界甚至包括佛教学术界都对之有着不小的误解。在很多情况下,“庸俗词源学”并非只是外行与民科的专利,即使在学界之中,它也还有很大的市场。
关于本书的翻译,我先说一下题名之中的philological以及philology的汉译问题。此一系列,我与世峰在本书之中都统一翻译为“文献学的”与“文献学”。但对此词,汉语世界则有“语文学”、“历史语言学”、“文献学”等多种翻译法,究其根底还是因为此词的原始意思难以找到完全合适的汉译对应。2017年3月14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陈怀宇教授在私人交流中建议我译为“语文学”或“语言文献学”,以与作为textual criticism的“文献学”相区别。对此问题,我其实有自己的考虑,早在2013年4月15-20日台湾佛光大学举办的“汉传佛教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研讨会上,我就发表了题名为“汉文佛教文献学的现状与未来”一文。其中我提到:
目前受西方佛教文献学的影响,很多都把佛教文献学等同于佛教学研究中的Philology。我这里稍微作一点说明。关于这个词的汉语对应翻译,有些直接对应为“文献学”,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英语中,它本来就有“语言与文献的研究”(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这一义项。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之下,这个词又会被译为“语言学”、“语文学”,因为这个词也有“古典语言、文献与历史的研究,但是目前最普通的义项是语言的科学”,而且更多的时候加上一个“比较”(comparative)的限定词,这样其语义就相对明确一点了,即有“比较语言学”的意思(The New Webster Dictioary,New York:Grolier,1968,p623)。
我在后面的西方佛教研究介绍中会提到,整个西方的佛教文献学研究,主要其实是佛教经典语言的研究,以梵、巴、藏以及其他一些包括古代汉语在内的古典佛经语言为载体的佛经的校勘、翻译以及比较研究最为核心。
正是因为西方佛教学的研究基础是一些Philology的工作,所以我在后面介绍西方的文献学研究述评方面也仅涉及这种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但是Philology并不完全等同于我所说的佛教文献学。前面已经提到了Philology还有很强烈的语言学的倾向,尤其涉及到语言学史与发展等方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的佛教文献学家,大多数都是精通佛教的古典语言如梵、巴、藏等等,并主要从事这些古典佛教文献的翻译和校订,并对这些古典语言的文法结构、发音特点、语词训诂等作全方位的探讨,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已经进入了语言学的范畴。
虽然我们看到在佛经的翻译和校订过程中,这些西方的佛教文献学家(即Philologist)也会探讨佛经的不同版本,但他们不会象汉文佛教文献学家那样把这些版本的特征与归类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只是利用这些来作为辅助工具。这可以以《法句经》的研究为例,欧洲最初是将巴利语《法句经》欧译,在中国的新疆发现梵语和犍陀罗语《法句经》以后,更激起了佛教文献学家们的研究激情。
他们做的最多的一项工作就是对这些不同文本中的平行段落(parallel passages)作一种比对性研究,比如不同语种的《法句经》之间的比较研究,这非常类似传统中国文献学中的不同版本的对勘;或者对不同文本中具有相关系的条目作交互的参考(cross-references),比如在研究《法句经》时引用古注或古书来加以辨析,这又非常类似于中国传统文献学中的他校。但有一点十分明显,我们看到佛教的Philologist(文献学家)所做的主要是在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和校订,而在传统的汉文佛教文献学中则基本不属于其工作的领域。
同样的道理,有的时候,这些Philologist也会编制一些目录,但大多数只是为了翻译和校订的方便,而不会把这些目录学本身当作一门学问。除了编制目录以外,汉文佛教文献学者还会研究中国古代佛教经目的历史演变和未来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这也是西方佛教Philologist一般所不会涉足的领域。
相比较而言,汉文佛教文献学所特有的研究范围,则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佛经的版本学,就大端而言有大藏经本的研究、藏外单刻本的研究等;佛教的目录学研究,这包括佛教的目录学史研究,佛教经目和版本书目的整理出版等;佛教的校勘学研究,这包括佛教校勘特殊情况以及处理等;佛经的辨伪研究,包括佛经的真伪辨别,产生年代、地点以及宗教背景等;佛经的辑佚研究,包括从内外典类书、总集和其它经典中辑出已经佚失了的佛教文献等。
所以我们看到在传统“汉语文献学”架构范围内的“汉语佛教文献学”就是一种以中华传统研究方法为依托,并且主要是在“汉语”这单一语种内的文献学研究。而这种单一语种内的文献研究,正如我一直在强调的,在面对佛教文献这样一种涉及到从源头的印度语言再到汉语、藏语等一系列分支语的复杂局面时,就难免会受巨大局限。
故而,虽然我已经非常明确表述了西方的philology一词与我们汉文世界之中的“文献学”有着不小的差距,前者更为倾向于语言学,尤其是“比较”语言学的学科建制。但在此我还是决定选用“文献学”这一译语,其原因如下。首先,将此词翻译成“文献学”确有成例,也是学术界的常用作法之一;其次,西方的这种(佛教)语言学研究取向,完全可以被纳入整体的、一个更大的佛教文献学研究框架之中,而且也确实应该将此东西方研究方法作一个整合。而最近一些特别优秀的汉文佛教文献学家,如辛嶋静志、左冠明(Stefano Zacchetti)等,他们的研究本身也其实是在整合了东西方两种佛教文献学研究的传统。
尤其是在左冠明的研究之中,除了传统的欧洲比较语言学血统之外,他还对汉文大藏经的版本、佛教校勘学等达到如数家珍的地步;第三,也同样是出于受众更为容易接受的角度来看,佛教“文献学”起码要比佛教“语文学”或“比较语言学”等看起来更为可亲一点,不至于那么异类而拒人千里之外。嗯,实话实说吧,本来这种干巴巴的纯学术书籍我就怕没多少人愿意看了,何况还弄上这么一个吓死人的名字呢。
这几位杰出的汉语佛教文献学家所做的,或者说是我们所梦想追求的目标,就是能在汉语佛教研究界中强化作为佛教经堂与圣典语言的梵语、巴利语、犍陀罗语,以及藏语、蒙古语、回鹘语、满语等的语言学学习,同时用这些语言为参照系,充分利用传统汉语文献学中的版本、校勘、目录、辑佚学方法,重新审视佛教文献的词义、语法等,在真正弄清楚佛教文献中的“意思”之后,再逐步开展佛教哲学、历史、文献、艺术等一系列其他研究。我真诚希望,有更多开设佛教研究相关的硕士、博士课程的学校,会将这些语言中的一种或数种当成是每位学生的入门必修课之一。
当然,我并非是说一定要每位从事佛教研究之人都精通这些文献学的基础,但毫无疑问,我们汉语佛教研究界中从事这些基础研究之人并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而这方面的重要性,又实在是无法更加强调了。比如现在大藏经之中归到安世高名下的《大安般守意经》(T602),是众多学者用以分析安世高以及早期汉语禅定文献的重要标本,但左冠明的研究就表明这根本就不是安世高所译,甚至就不是一部佛经。而真正的安世高所译,则藏在日本的金刚寺之中。那么,回过头来再看我们那些以此经作为“安世高译经”并以此为基础所作出的众多推论,又有多少价值呢?
毋庸讳言,过去国内汉语佛教界中,语言文献学,尤其是印欧语言文献学,除了以季羡林、王邦维、段晴、叶少勇等为代表的北大东语系传统,以及最近一些年来也渐渐发展起来的人民大学(惟善法师等)与复旦大学(刘震等)等少数院校之外,则可以说是大陆佛教研究的一个相当边缘的领域。
但就事实而言,正如此书之中所不断强调的,佛教文献学(当然也包括佛教汉语文献学)是过去、现在与将来一切佛教研究的基石。如果我们连佛经或佛教基本文献本来的意思都无法弄懂或真正弄懂,那又如何来谈其历史、哲学等其他问题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本小书的出版,稍微介绍一点西方最为优秀的佛教语言文献学成果。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以这个小册子为起点,将更多优秀的西方印度学、佛教学与文献学著作带到汉语学术圈子之中来,并且能够吸引更多的学子加入佛教文献的研究队伍之中。
说到此书的翻译,最早我阅读此书大概是在2008年。我在复旦之时所受的基本是传统的汉语文献学训练(我要感谢我的导师陈允吉先生与教过我文献学的陈尚君、吴格二位先生,虽然我学得很糟糕),2006年出国之后感觉眼界大开,大概以每年浏览近百本的速度囫囵吞枣地快读了不少西方佛教研究专著,也领略到西方佛教文献学研究的风采,这其中也包括此本小册子。
除我之外,这本书的主要译者是陈世峰博士,我与他是2013年9月起认识的,他是原籍新加坡的澳洲籍华人,后移居澳洲近三十年。其专业本为农学(1987年昆士兰大学农学博士),却于2007-2008年在澳洲国立大学这座佛教研究的重镇系统地修学了一年梵文,在此之后,他长年不懈地继续学习梵文与巴利文。2014年开始,他翻译了多篇诺曼教授的研究文章,我们之间的通信也主要是讨论一些专业问题。
这一年的2月18日,世峰给给巴利圣典学会的办公室主管温兰(Karen Wendland)**发信询问一篇诺曼教授论文的翻译版权事宜,次日他就收到了现在全权负责诺曼先生版权的普瑞特(William Pruitt)教授的同意电邮。普瑞特教授,圈内人都知道,也是一位成绩卓著的佛教文献学家。因此我也与普瑞特本人获得了联系,并于3月4日去信询问是否可以获得诺曼本书的翻译授权,次日他就回信说没有问题,并告诉我当年8月他会借着给缅甸政府整理缅文藏经目录的机会来新,到时候我们可以一面。后来出版社需要一个更为正式的授权,又由世峰去信获得了他们的书面首肯。
我们虽然拿到了授权,但因为2014年上半年我一直在忙于翻译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的名著《大乘佛教》(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一书,所以此书,就和我无数如空中楼阁一样的研究计划一样,拖了下来。而此年,我相信,对世峰而言也是一段在澳洲、新加坡与广州间不断奔波而忙碌的时光。
整个2015年我在教书之余,也在忙着准备几篇会议论文,9月又给左冠明编了一个汉译佛教文献学的作品集,中间除了一个月被拉去临时帮忙之外,至2016年3月总算译完了十篇文章约三四十万字的草稿,但很快又有其他一些杂事不断冒了出来。也就是在这年的11月,世峰手头上的事闲下来后问我诺曼一书的翻译情况并提出与我合译。
我当时提出一人译一半并由我统筹汉文译稿、编制译语索引,同时优先寻找国内出版社,如果不行,就由我主编的《新加坡佛教研究学刊》(The Singapore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以专刊的形式出版。这样,可同时提供网上免费下载并向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直接寄送赠刊的形式也可以起到广为流通的目的。但后来感到教书、行政,再加上杂事不断,分身实在乏力,就由世峰译完了第3-10章。所以说这本书的译成,绝大多数都是世峰的功劳,而我只不过给此书开了个头而已。
世峰的第3-10章,他在2016年9月29日就发给了我初译稿。而我的两章译稿则拖到今年2月才译完。之后我就全力将全部译稿校对了一遍并开始编制译语索引,一直到5月15日。我以修订模式给全部译稿加上意见之后发给了世峰。这份译稿,世峰斟酌之后于8月14日发还给我,我在此基础上打印出来又读了一遍,修订了一些明显的错别字、语法性错误与误译等, 于8月25日发回世峰再审,9月7日世峰的部分定稿,我们全书才算基本告成(仍待清样出来后,我再编制一个术语索引)。
世峰可能是汉语学术译界中相当少有的一位,他的母语虽是汉语,但汉语则相对他的英语程度要稍弱一点。因此他真正的强项是汉译英,就在今年年初,他只用了三四个月就译完了我几年前近7万字的长文《疑伪问题再研究》(《福严佛学研究》,2012,卷7:115-182)。其中不仅涉及到了佛教文献学的专门知识,还有海量的专用术语与技术名词,他却在如此短的时间完成了英译,实在让我吃惊。所以,他的英文理解很少会有错,而我的主要工作是对他的汉语表达作修饰与改译。当然,错译与错误表达之处肯定还是会有,在此我们真诚地欢迎任何批评意见,并将以此为鞭策,为下一版的改进作好准备。
在我对全书进行校订之际,3月10日我在新浪微博上发了一条简讯,询问有没有国内的学术出版社有兴趣。在第一时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刘赛先生就与我联系出版事宜。虽然最后此书未能在上海古籍出版,但刘先生的高情厚谊,我实在是无法忘怀,并且对没能积极回应刘先生的主动提出帮助感到万分的抱歉。
几乎与此同时,浙江大学的林晓光师弟发来信息,说他已经与中西书局的李碧妍博士联系,李博士对此书很感兴趣。11日早上复旦陈引驰师也给我发来短信,告之此书出版如有问题,他可以帮忙。3月12日午夜,北京大学的陆扬教授发来短信,强烈推荐李碧妍博士与中西书局,他的原话是:“……中西(书局)目前是国内出印度学佛教学最好的出版社,李碧妍更是最好的编辑。辛嶋的书在那里刚出。你不妨考虑独立弄一个系列,将 Norman 的两本都列入其中。我强烈推荐中西(书局)。……”3月14日,李碧妍博士就给我发来了邮件询问出版的具体事宜。
就在同一天,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陈怀宇教授也向李碧妍博士推荐出版本书。3月17日,北京大学的叶少勇教授向我推荐,并介绍了中西书局印度学系列出版情况。如果有人还嫌这些师友的推荐不够份量的话, 3月26日我在山西参加“从襄垣到锡兰:汉僧法显其生平与遗产”研讨会时,与严耀中老师饭后散步,他听说我们这本书的出版之事,也向我推荐李碧妍博士。也正是在此会议期间,北京大学王颂教授知道此书未签出版社后,提出他可以帮忙解决出版事宜。到了4月13日,复旦刘震兄发来邮件问此书是否有着落,如果没有,则可以纳入他主持的译丛。
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竟然惊动了如此多的师友,实在让我非常汗颜。同时也想借此机会真诚感谢这些师友的无私帮助,当然更要感谢李碧妍博士的学术激情、伍珺涵老师专业精细的编辑校订与中西书局对学术冷门的不懈支持,让我们这些有“特殊癖好”之人能够找到一小块自留地。
纪赟 2017年9月8日 新加坡碧山
自考/成考有疑问、不知道自考/成考考点内容、不清楚当地自考/成考政策,点击底部咨询官网老师,免费领取复习资料:https://www87dhcom/xl/
缅甸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1044年形成统一国家后,经历了蒲甘、东坞和贡榜三个封建王朝。英国于1824-1885年间先后发动了3次侵缅战争并占领了缅甸,1886年英国将缅甸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1937年缅脱离英属印度,直接受英国总督统治。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1945年全国总起义,缅甸光复。后英国重新控制缅甸。1947年10月英国被迫公布缅独立法案。1948年1月4日缅甸脱离英联邦宣布独立,建立缅甸联邦。1974年1月改称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88年9月23日改称“缅甸联邦”。 缅甸是著名的“佛教之国”,佛教传入缅甸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1000多年前,缅甸人就开始把佛经刻写在一种叫贝多罗树的叶子上,制成贝叶经。正如李商隐诗中提到“忆奉莲花座,兼闻贝叶经”。在缅甸5300多万人口中,80%以上信奉佛教。缅甸的每一个男人在一定时期内都必须削发为僧。否则,就会受到社会的蔑视。佛教徒崇尚建造浮屠,建庙必建塔,缅甸全国到处佛塔林立。因此,缅甸又被誉为“佛塔之国”。千姿百态、金碧辉煌的佛塔使缅甸成为旅游胜地。 缅甸
缅甸历史,可以上溯到5000年前。当时缅甸的伊洛瓦底江边的村庄已有人类居住。将缅甸划分成“上缅甸”和“下缅甸”是英国殖民统治后的人为划分。相传西元前200年骠人(Pyu)进入依洛瓦底江的上游地区,并掌控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通商之路。两世纪之後孟族来到锡唐河(SittangRiver)流域,而在849年缅甸人接管骠河流域并建立蒲甘城(Pagan)。 蒲甘王朝(1044年-1287年) 蒲甘王朝是由阿努律陀国王(KingAnawrahta,1044年-1077年在位)於1044年建立,为缅甸第一个统一的帝国,以小乘佛教为国教。阿奴律陀国王相继征服掸族和孟族,也不断扩展领土。在阿朗西都国王(KingAlaungsithu,1111年-1167年)掌政时,小乘佛教逐渐成为主流,并在13世纪初期达到顶盛。当时建造的3000馀座寺庙尚有100座保存至今。1287年元朝统治者忽必烈率领元军大举入侵而结束了蒲甘王朝。此後,缅甸进入了掸族时期。 东吁王朝(1531年-1752年) 1531年缅人莽应体(Tabinshwehti,1531年-1550年)二度统一缅甸,成立东吁王朝而自称为王,并於1546年建立首都勃固城(Pegu)。之後莽应龙(Bayinnaung)即位,因多次与实力犟大的泰族阿瑜陀耶王国(大城王国)(Ayutthaya)交战而耗尽了资源,最後因勃固城於1599年被阿卡族占领而迁都阿瓦(Ava)。东吁王国最终在1752年没落。1753年,缅人雍籍牙(Alaungpaya)出现,赶走当时攻占阿瓦的孟族人,并建立大光城。 贡榜王朝(1752年-1885年) 1782年-1819年是波道国王(KingBodawpaya)主政的专制时期,因其多次企图入侵泰国的野心,使得当时占有印度的英国不免忧心缅甸可能造成的威胁。 殖民时期(1885年-1948年) 英国和缅甸间的紧张局势在1824年-1826年以及1852年两次的英缅战争中达到高峰。英国在这两次的战争中均获得胜利,最後攻占勃固城并将此地称为下缅甸。在英国人进入缅甸後,上缅甸的经济也显著好转。1886年,英国再度赢得第三次的英缅战争,此时英国将缅甸纳为印度的一省,并将政府设於仰光。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缅甸的交通和教育获得大幅改善。英国人致力开发水路,使得无数蒸气船得以航行於依洛瓦底江。铁路和道路也获兴建和改善以弥补水路的不足。此时,大量的印度移民涌入导致劳工廉价,造成地方经济受到威胁。因此缅人开始产生对印度人的仇视,以致在1930年爆发反印度人的暴动。 1936年,在英国统治下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的选举中,巴莫博士(DrBaMaw)当选为英国控制下政府的首相,1937年,英国创建一套独特的缅甸宪法,同意缅人可以控制自国内政。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在1942年5月占领缅甸,成立以巴莫为首的缅甸执行政府。在日本的支持下,反对英国殖民政府、渴望独立的昂山将军(GenAungSan)组织了缅甸独立义勇军,1942年他率军与日军一起参加了对英军的战斗,然后在日军支持下宣布缅甸从英国独立。1943年,巴莫与昂山等人受邀访问日本,他们回国重组缅甸政府,昂山成为国防部长。1944年,昂山开始支持美英的同盟国一方,并组织「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以对抗日军。1945年日本投降後,宣布缅甸独立是有效的。战後的缅甸仍受英国控制,昂山则在1947年7月遇刺身亡。昂山的继承人德钦努(ThakinNu)继续领导独立运动,在英国议会1948年1月4日正式承认缅甸独立之后,於1948年初正式成立了缅甸联邦。
你好,我是在2011年1月15、16日参加的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我报的古代文学专业。第一,你在大学期间是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并且自己比较擅长哪个方面。比较擅长的话就会在复习的时候有信心并且压力不会很大。第二,如果你是跨专业考的,那么我建议你选择现当代文学,毕竟现当代文学跨度小,复习内容相对少一些。第三,考研究生其实很多学校都是按照专业课总分和英语成绩从高到低排名进入复试的,所以我建议你在复习的时候英语是要用心用力复习的。并且文学这一个专业的英语成绩在众多专业中和各个地区应该都是最高的。希望这些建议对你有帮助,祝你考研成功!
历代书目所载《万首唐人绝句》均为宋洪迈编,只是此书初题名不是《万首唐人绝句》,此名直至明代才有。《宋史·艺文志·总集类》卷二百九载:“洪迈《唐一千家诗》一百卷”宋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总集类》:“《唐人绝句诗集》一百卷。洪迈景卢编,七言七十五卷,五言六言二十五卷,各百首。凡万上之重华宫,可谓博矣。而多有本朝人诗在其中,如李九龄、郭震、滕白、王嵒、王初之属,其尤不深考者,梁何仲言也。”元马端临著《文献通考·经籍考·集部》卷七十五引陈振孙言及后村刘氏言:“《唐人绝句诗集》一百卷。后村刘氏曰:‘野处洪公,编唐人绝句仅万首。有一家数百首并取不遗者,亦有复出者,疑其但取唐人文集杂说,令人抄类而成书,非不有所去取也。’”洪迈对此书写有序言,后世刊本中均有,曰:
淳熙庚子秋,迈解建安郡印,归时,年五十八矣。身入老境,眼意倦罢,不复观书,惟时时教稚儿诵唐人绝句,则取诸家遗集,一切整汇,凡五七言五千四百篇,手书为六秩。起家守婺,赍以自随。逾年再还朝,侍寿皇帝清燕,偶及宫中书扇事。圣语云,比使人集录唐诗,得数百首。迈因以昔所编具奏。天旨惊其多,且令以元本进入,蒙置诸复古殿书院。又四年,来守会稽间,公事余分,又讨理向所未尽者。唐去今四百岁,考《艺文志》所载,以集著录者,几五百家,今堇及半而或失真。如王涯在翰林同学士令狐楚、张仲素所赋宫词诸章乃误入于王维集;金华所刊杜牧之续别集皆许浑诗也;李益“返照人闾巷,愁来与谁语”一篇,又以为耿𣲗;崔鲁“白首成何事,无欢可替愁”一篇,又以为张𧏖;以薛能“邵平瓜地入吾庐”一篇为曹邺;以狄归昌“马嵬坡下柳依依”一篇为罗隐,如是者不可胜计。今之所编固亦不能自免,然不暇正,又取郭茂倩乐府与稗官小说所载仙鬼诸诗,撮其可读者合为百卷。刻板蓬莱阁中,而识其本末于首。于绍熙元年十一月戊午,焕章阁学士、宣奉大夫、知绍兴军府事、两浙东路安抚使,魏郡公洪迈序。
越州所刻七言至二十六卷,五言至二十卷,而奉祠归鄱阳,惟书不可以不成,乃雇婺匠续之于容斋,旬月而毕,二年十一月戊辰迈题。
从序言可知,洪迈初编《唐诗绝句》是为教稚儿,作为教科书之用,后受宋皇鼓励授命,又搜得唐绝句百卷编为一书。此书在洪迈在世时自行刊刻,但分二次刻成,一次为洪迈守越州会稽间所刻,即迈序言中绍熙元年之“越州所刻七言至二十六卷,五言至二十卷”之本,初刻为四十六卷。再次刊刻为绍熙二年(1191),刻于鄱阳,即序中“奉祠归鄱阳,惟书不可以不成,乃雇婺匠续之于容斋,旬月而毕”之本。故洪迈自刻本一百卷,半刻于会稽,半刻于鄱阳。洪迈对此书的刊刻情况在《重华宫投进箚子》中交代更为详细,曰:“……臣以幺么余生,获安故里,窃恃隆恩,冒昧有陈。臣顷岁备数禁廷,得侍清间之燕,因及手写唐人绝句诗,即蒙盛旨许令进入,是时才有五十四卷。去年守越,尝于公库镂板,未及了毕,奉祠西归。家居无事,又复搜讨文集,傍及传记小说,遂得满万首,分为百卷。辄以私钱雇工接续雕刻,今已成书。……贴黄上件诗集七言二十六卷以前,五言二十卷以前,系绍兴府所刻,臣临行时仓卒印造,纸箚多不精,续后点检得有错误处,只用雌黄涂改。……”此文中绍兴府所刻即洪公言守越,尝于公库镂板之书,宋时改越州为绍兴府,故越州刻本又有绍兴府刻本之说,洪迈私钱雇工所刻本即鄱阳本。
现存《万首唐人绝句》明嘉靖陈敬学刊本,前有洪迈自序,另有宋嘉定吴格识语、宋嘉定汪纲跋及陈敬学跋。吴格识语曰:“右《唐人绝句》乃内相洪公手自采择,暨守会稽,尝以此刊之郡斋,后三十年格获继往躅,暇日取是书,伏而玩之,则岁月暨久,固已漫谬蠹阙多矣,因命工修补,以永其传,嘉定辛亥孟秋下浣新安吴格谨识。”以此推之,宋时还有吴格重修本,所修之本应为洪迈半刻会稽之本,而且不全,此在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明版集部》卷十中论之甚详,曰:“……乃书中又有吴格识语,以吴格亦为越守,后于洪迈先于汪纲,曾取会稽所刻一半之版修补之,而刻于鄱阳之一半不与焉。故其识语但称洪公守会稽,尝以此刻之郡斋,三十年格获继往躅,命工修补,以永其传。时为嘉定辛亥云云,不言卷数亦不言鄱阳续刻之事,以意考之,则止会稽一半之版也。……”汪纲跋曰:“《唐人绝句》诗凡一百一卷,半刻会稽,半刻鄱阳。嘉定癸未新安汪纲守越,遂拓鄱阳本并刻之,使合而为一,既毕工,姑识其末,是岁二月既望书于镇越堂”此跋中谓《万首唐人绝句》为一百一卷,汪纲已把洪迈的一百卷本变为一百一卷本,以据汪本翻刻的明嘉靖本与洪迈自刻之本比较,知汪本析六言另为一卷,故增多一卷。
由上论可知,此书宋代有三种版本行世。一为洪迈自刻之本,半刻会稽,半刻鄱阳,共一百卷;一为吴格重修本,据部分会稽刻本修补,卷数不详;一为汪纲刻本,合会稽鄱阳之刻,析六言另为一卷,共一百一卷。现此三种版本都已不存,只能在书目文献中可见有记载。傅增湘《雁影斋题跋》卷一所载《唐人万首绝句》(宋本)题跋曰:“此绍熙刊本也。自四十五卷后皆阙。前有洪文敏原序一首,自置复古殿以下亦阙,书贾补缀增一‘云时’二字,即接绍熙元年云云,而弥补无迹,亦善于欺人矣。查《万首绝句》在宋时即有三本,一本一百卷;一本一百一卷。一百卷者为文敏所自刊,半刻于会稽,半刻于鄱阳。一百一卷者为汪纲守越时刊合鄱阳会稽本而并刻之者也。又有吴格重修之本,则仅会稽初刻之一半。据文敏自题云:‘越州所刻七言至二十六卷,五言至二十卷。’此本正四十六卷,则汪舍人修补越府所刻之一半印行之本也。……”汪士钟编《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集部》载:“《万首唐人绝句》存三十六卷。”顾广圻撰,黄丕烈注《百宋一廛赋》(及其他二种)载:“洪氏之万首,残本《万首唐人绝句》,每半页九行,每行廿字,所存前后凡三十六卷,而序及目录,完好无恙,《敏求记》言,目录二卷,七言七十五卷,五言二十五卷,六言一卷,赵宦光所刊。统而一之,讥其好自用,诚哉是言也,明嘉靖时有覆宋本者,规模未改,胜赵宦光远甚,然终不若此之可宝。”汪士钟所记与黄丕烈所记应为一书,同为残卷三十六卷。此宋本应为迈自刊的绍熙刊本,据汪纲本翻刻的明嘉靖本为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此本半页九行,行二十字,此本应为绍熙本。《增注四库简明标注》中此宋本亦作半页九行,行二十字,但江标辑《宋元本行格表·集卷上》载为二十二字,曰:“宋残本《万首唐人绝句》行廿二字,百宋一廛赋注,简明目录批注本,作行二十字。”谁是谁非,现已无从考证。
明有嘉靖辛丑陈敬学仿宋本和明万历丙午赵宦光刻本,现存。另有明苏州府刻本,《百川书志 古今书刻》合刻本中明周弘祖撰《古今书刻》载:“南直隶,苏州府,《万首唐人绝句》。” 《晁氏宝文堂书目 徐氏红雨楼书目》合刻本中明晁瑮撰《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上诗词》载:“《万首唐人绝句》苏刻。”二书所载应同为一书,但今已不存。嘉靖辛丑(十九年)陈敬学仿宋本现存国内多家图书馆,《藏园群书经眼录·集部七·卷十八》、《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郋园读书志·集部·总集》、《爱日精庐藏书志·集部·总集类》、《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均有记载。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室所藏即为此本,此版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中缝下方有“德星堂”三字,五言卷十九下有“陈敬学校刊”几字,前有绍熙元年序、《重华宫投进箚子》、《重华宫宣赐白箚子》、《谢表》、《别奏箚子》、《奏耿柟不受书送箚子》、《谢南内奏状》。目录后有吴格识语、汪纲跋及陈敬学跋文,陈敬学跋曰:“《万首唐人绝句》诗自宋刻迄今,又多慢谬蠹阙矣,都宪陈公俾愚领校刊之任,愚虽三年劳于兹,亦乌能免伪舛之非乎哉!维昔始之以淳熙庚子,而今继之以嘉靖庚子,数之偶然有可识焉耳。辛丑人日,姑苏门生陈敬学书。”从中可知,陈敬学刊本历时三年乃成,此书一百一卷,当据宋汪纲本翻刻。《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中《涵芬楼烬余书录》载:
《万首唐人绝句》一百一卷,宋洪迈编 明嘉靖刊本,四十册,怡府旧藏。
卷首绍熙元年洪迈序,次《重华宫投进箚子》,又《重华宫宣赐白箚子》,洪迈《谢表》,又《别奏箚子》,又《奏耿柟不受书箚子》,又《谢南内奏状》。此据宋嘉定越州刊本覆刻,故提行空格,悉依旧式。目录分二类:前七言,凡七十五卷;后五言,凡二十五卷。附六言一卷。尚有二年洪迈题语,嘉定新安吴格、汪纲二跋,均佚。
藏印:“怡亲王宝”、“冰玉山庄”、“赐额忠孝为藩”、“纶音”、“好书犹见性情醇”、“徐开任印”。
张元济谓此嘉靖本据宋嘉定越州刊本覆刻,宋嘉定本只有吴格修补本和汪纲刻本,吴格修补本为不全之本,而此书为一百一卷全本,可见应据汪纲本覆刻。叶德辉也持此观点,《郋园读书志·集部·总集》卷十五载:“《唐人万首绝句》一百一卷,明嘉靖辛丑陈敬学仿宋刊本。宋洪迈《唐人万首绝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一百卷,与迈自序合。此为明嘉靖辛丑陈敬学仿宋刊本,作一百一卷,盖据宋嘉定癸未汪纲重刻本翻雕,与明钦《天一阁书目》及乾隆内府《天禄琳琅书目》所载合,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所云析六言另为一卷者也。天禄本即四库著录本,提要云九十一卷下注内府藏本,《简明目录》云佚其九卷者。”从此文知,《四库全书》即收录此明嘉靖陈敬学刊本,但为不全之本,只九十一卷,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二》卷一七八载:“《万首唐人绝句诗》九十一卷,内府藏本。”振铎曾得嘉靖陈本,是书藏于国图,上有郑振铎跋文,曰:“……此书常见者为万历赵宦光刊本,然多所改易,与原本面目全非。此嘉靖是本从宋本翻雕者,最为罕见,近来影印本即借北京图书馆珍藏此本付照。……”
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最为常见之本为明万历丙午赵宦光刊本,此本国图藏有,题为《宋洪魏公进唐人绝句》,四十卷,半页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前有万历丁未申时行《校刊万首唐人绝句序》、万历丙午赵宦光撰《万首唐人绝句刊定题词》、万历丁未黄习远《校刻万首唐人绝句引》,次洪迈自序,次重华宫投进箚子、重华宫宣赐白箚子、谢表、唐绝发凡,总目后有唐风四始考,之后有一行篆书“万历丙午秋九日寒山小宛堂编次”,卷一末有牌记,为“万历丙午秋日吴郡寒山校刻”。《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室》记载甚详,曰:“《宋洪魏公进万首唐人绝句》四十卷,目录四卷,宋洪迈辑;明赵宦光、黄习远补。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赵宦光刻本,六册。半页十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框高214厘米,宽138厘米。题‘明吴郡赵宦光凡夫刊定、灵岩黄习远伯传窜补’。前有万历三十五年申时行序、万历三十四年赵宦光序、万历三十五年黄习远序。凡例二十一则。绍熙元年(1190)洪迈序。重华宫投进箚子。绍熙四年洪迈谢表。唐风四时考。……”《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中《书录·总集类》也有记载。此书在日本被重刻,现藏于国图,半页十三行,行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书末在“四十卷终”下有字一行“文政六年刊”,后有几行大字,曰:“官版书籍发行所 东都横山町台丁目角 御书物师 出云寺万次郎。”可知赵宦光本曾于日本文政六年由官校刊刻行世。
赵宦光刻本改一百一卷为四十卷,卷数内容都作了很大变动。赵宦光《万首唐人绝句》刊定题词云:
时有魏公洪迈,出其手钞五千馀首,进之陛下以供挥洒之资。天颜粲然,都俞褒锡。既复搜讨,再得如前以献。于是陛下益喜,题曰:《万首唐人绝句》,颁赐文臣,垂之永久。惜于尔时洪公旋录旋奏,略无诠次,代不摄人,人不领什。或一章数见者有之,或彼作误此者有之,或律去首尾者有之,或析古一解者有之。至若人采七八而遗二三,或全未收录而家并遗。若此诖误,莫可胜纪。暇日与灵岩诗人黄伯传悉为厘正,削其十一,皆前失也。复讨寻四唐别、总集群,以及选摘稗官诸家,不遗余力,遂得洪氏阙略者数百篇,合一万若干首。虽去取略复相当,其视原本舛讹失所者,真可谓金枝迸海,草木皆明矣。……万历丙午秋日吴郡赵宦光撰
黄习远重刻《万首唐人绝句》跋曰:
原板一百一卷,半刻于会稽,半刻于鄱阳。嘉定辛未,越守汪公纲合鄱阳之刻于会稽,而加修补焉。迨我嘉靖庚子,陈中丞重校而梓之,然无有正其讹者。万历甲辰春日,予过寒山小宛堂,凡夫先生以兹集授予校雠,乃共芟其谬且复者共二百一十九首,补入四唐名公共一百一人,遗诗共六百五十九首,总得一万四百七十七首。诗以人汇,人以代次,厘为四十卷。凡三易寒暑而剞劂告成。予谓以魏公博赡犹有遗误。使我两人者,得称异代功臣,则耳目之外秘篇所载,尚冀后之君子佐其不逮焉。丁未端午灵岩黄习远伯传甫识于萧萧斋中。
从赵黄二人题跋可知,因洪迈所编《万首唐人绝句》多有讹误,而陈敬学并未订正,故二人得以阙者补之,伪者正之,总辑诗一万四百七十七首。此书李盛铎曾收藏,《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六上·集部八·总集类》载:“《宋洪魏公进万首唐人绝句》四十卷,宋洪迈编。明万历三十五年赵宦光刊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阑。李木斋藏。”清杨守敬为此本写有跋,《日本访书志》卷一三有载,杨守敬认为此本较原书实为精整。叶德辉撰《郋园读书志·集部·总集》卷十五也著录此书,但叶氏对此书颇有微词,谓“明人刻书不遵旧本,动以己意增删,刻一书而书亡不如不刻。”
近世有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明嘉靖陈敬学刊本影印,全书四册。又有1983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刘卓英校点的《万首唐人绝句》校点本,此书以明万历赵宦光刊本为底本加以校点。
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