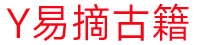不见于文献记载的西周「 ”曾国”,为何频频出土文物?

2010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湖北随州淅河镇蒋寨村叶家山村民在修整水渠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 ”大香炉”。随州市博物馆馆长黄建勋闻讯赶到现场,当他看了这件还有半截身子埋在土中、被村民称为「 ”大香炉”的鼎之后,不由得欣喜万分。从形制看,这件铜鼎至少是西周时期器物,而其巨大的体量,是随州西周考古所没有见过的。他朦胧地预感到随州考古将要轰动全国了。 随州考古的上一次辉煌,是1978年发现的曾侯乙墓。编钟、编磬、联禁铜壸、鹿角立鹤……琳琅满目的国宝,将墓主人曾侯乙的名字传扬天下。有曾侯便有曾国,但按史籍记载,这里却属于周代随国……一系列的疑问与猜想在随后的二十多年萦绕此地,学者们称之为「 ”曾国之迷”。这次,叶家山的发现会不会解开之前谜团呢? 他立即电话通知湖北省文物局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带领考古队员前来勘察。经过初步的清理,出铜器的地方是两座墓葬,为了保护文物,考古队员立即对这两座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按说年关将近、人心思归,可是队员们却都很兴奋,因为初步的勘察发现,在这两座编号为M1、M2的墓葬周围,沿着缓坡向南、向西还有不少墓葬,而且,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些墓葬保存完好,未曾被盗!初步的钻探结果显示,在其周围还有不少于50座墓葬。可以基本确定,叶家山是一处西周时期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它比曾侯乙墓早500余年,距今3100年。 从清理出土的大鼎上的铭文可知,这件器物与一个人有关。是谁,不知道。但要命的是,与大鼎一起出土的其它铜器上,我们却发现有「 ”曾侯”二字。这两个字再次打开了随州考古潘多拉魔盒,纠缠学界几十年的「 ”曾国之迷”又一次浮出水面。 随枣走廊,曾在哪里?随在何处? 熟悉中国先秦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先秦区域「 ”国家”中,最为神秘也最为有趣的莫过于「 ”随”国。 《左传》有「 ”汉东之国随为大”的描述,就是说,在汉水以东的所有诸侯国中,随国是最大的,在周代分封的诸多国家中,随的地位十分重要。随大致在今天的湖北随州市一带。 翻开河南与湖北省的地图可以发现,从河南进入湖北的道路,传统上有两条:一条大体沿今京广线南行,路径为驻马店一信阳一桐柏山与大别山一广水一云梦一孝感一武汉;另一条则从南阳盆地沿唐白河向南,到达襄阳,然后路分为二,一路在大洪山南麓,沿汉水南行至武汉;另一路则在大洪山北麓,由襄樊东行至枣阳,沿「 ”随枣走廊”,到达随州,之后可以沿着涢水南行至汉川、武汉。 大家可别小看这最后一条道路,这小小的随枣走廊,却关系着西周王朝的南方边境是否安定。也恰恰是这一区域,让商周考古学者又爱又恨。 众所周知,武王灭商之后,西周王朝为了镇守辽阔疆域、控制殷商后裔,便将兄弟叔侄以及立有战功的异姓贵族,派往各地担任诸侯。西周中叶,周昭王、穆王不断向淮夷、于越、荆楚等地用兵。为了巩固对南方的控制,夺取重要战略资源「 ”铜”,又把一些姬姓兄弟从山西、陕西移封至汉水以东、以北和江、淮间,组成一个庞大的姬姓封国集团,史称「 ”汉阳诸姬”。 按照清代经学家的考证,汉阳诸姬大体有「 ”唐、厉、随、贰、轸、郧、黄、弦、申、息、江、道、柏、沈”等15个国家。从分布区域看,大体在汉水北岸的冲积平原和大洪山两麓的地区,随国属于汉阳诸姬之一,分布区域最大、地望争议最小,核心区域就在今枣阳到随州一线的随枣走廊之中。然而蹊跷的是,北宋时,在安州(今湖北安陆县)出土了6件「 ”曾”器,史称「 ”安州六器”。铭文显示,它们与一个不见于文献的「 ”曾”国有关。在那之后,直到最近几十年,在这一地区及邻近的河南南阳盆地内,接连获取许多「 ”曾”国的青铜器,它们没有一件写有「 ”随”的字样。「 ”姬姓曾国”在文献里是完全找不到影子的。在记载江汉平原小国最详细的《左传》里,也没有「 ”曾”的身影。 这种出土发现与文献相矛盾的情况,一直没有合理的解释。一个是有史可据的「 ”随为大”,一个是查无出处、但却真实存在的「 ”曾”,到底是文献记错了,还是说考古人还没有发现那个神秘的「 ”随”? 直到1970年代末,随着湖北随县曾侯乙大墓的发现,一个自西周末年到战国时期的确存在过的「 ”姬姓曾国”,自此得到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 但是,有曾国,仍然无法解答随国在哪里的问题。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随就是曾,曾就是随,曾和随就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名字。这一说法很快得到了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因为在文献中,春秋战国时期的确有一个国家有两个名字的情况,比如,位于南阳盆地的吕国,又叫甫,在山东安国的州国,又叫淳于。 屡屡「 ”被食言”,商周考古学家又爱又恨之地 在曾侯乙墓发掘之后的20多年内,在随枣走廊,就如同打开了一个盛满铜器的库房大门一样,在大洪山南麓的漳河流域的苏家垅、檀梨树岗;滚水流域的段营、曹门湾、郭家庙;涢水流域的义地岗、擂鼓墩等地点,共发现了数百件青铜器它们无一例外都属于曾国。 令学者不解的是,这些青铜器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末期到战国时期,独不见西周晚期以前的铜器。 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徐天进教授,偶然在日本出光美术馆,发现了一件西周时期一个叫「 ”静”的人制作的铜方鼎,其中的铭文记载了一件事: 周昭王南征荆楚时,曾派静统辖驻扎在曾和鄂的王师部队。而前述「 ”安州六器”中的中上的铭文,提到了周王南征时,也有记录「 ”在曾”、「 ”在鄂师次(驻扎、停留)”。由此可知,当时的曾与鄂国相距很近。在文献的记载中,鄂就在今天的鄂州一带,而曾,似乎与鄂相邻。 这个鄂国在历史上可是赫赫有名。在金文中,鄂国往往被写作「 ”噩”,商代晚期,鄂侯与西伯昌(即周文王)、九侯一起,名列商纣王的「 ”三公”后来九侯的女儿成为商纣王的妃子,但是因为不喜欢纣王的 ,被商纣王给杀了,九侯也受牵连,被商纣王剁成了肉酱。鄂侯替九侯出头争辩,结果话说僵了,被商纣王给做成了肉干(脯)。《史记·殷本纪》记载的这一段历史里,称此事件为「 ”脯鄂侯”。 嗣后,在西周时,鄂国一直是周王朝在南方的桥头堡,周王朝向南征伐的时候,往往要借助鄂国的力量。所以,在西周中期前后记载周昭王南征的多件青铜器上,都曾记载有鄂。但鄂国又太过于强大,以至于到了西周晚期,它依仗自己的势力与周王朝时而交好,时而反叛。 在周厉王时期的「 ”鄂侯驭方鼎”铭文中记载,鄂国和周王朝通婚,在王朝征伐南淮夷、东夷的时候路过鄂国,还给了鄂国很高的赏赐与礼遇。但随后不久,鄂国就反周了。在另一个「 ”禹鼎”铭文中记载,鄂后来成为南准夷、东夷反叛周王朝的带头人,结果被王师攻灭。 根据中甗和静方鼎的铭文,有学者对曾国与鄂国的关系做出了这样的解释,认为鄂国在南边,其北部和曾国可能接壤,后来,鄂国被周王朝翦灭,曾国才进入南部鄂国的范围。所以,在西周晚期以前,两国一个在南一个在北,随州、枣阳一带,应该是两国的边界区域。这个说法,依当时的出土材料看,似乎是最合乎逻辑的,所以被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接受。 然而逻辑永远不能替代真相,各种相互有出入的文献记载,更不能替代地下的宝藏。没过三五年,又有新的发现挑战了这一认识。 叶家山PK羊子山,曾国崛起 2004年,随州博物馆的考古专家们通过编号为M4的墓葬随葬的一批青铜器,确认羊子山墓葬群属于西周早期到中期鄂国国君级别人物的墓葬。 李学勤先生针对羊子山的发现,就曾经感叹道: 「 ”(羊子山墓地)证明鄂国的中心就在汉东的随州一带,是我们想不到的”。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调和的意见: 「 ”由于随州与其周围记有曾国名号的青铜器,没有早于西周晚期的,而且形制、纹饰都近似周王朝器物。我觉得,这可能暗示我们,这里的曾国(即随国)是在鄂国已被攻灭之后才建立的,铭文中的‘曾’是沿用了鄂国的旧地名”。 谁料李先生这一精巧的推论刚刚提出,相距羊子山仅仅15公里的叶家山墓地就被发现。研究发现,它的时代恰恰属于西周早期。这样,先前以「 ”没有西周早、中期的曾国”为基础而推论出的种种假设又需要再次调整。 正因为长期以来,随枣走廊地区的考古发现不断改变着学术界对随、曾、鄂国问题的认识,有关曾国的来源和始封问题始终未成定论。大多数学者认为,曾国是在西周晚期周灭鄂之后立国的,但叶家山墓地所见铜器铭文表明,在西周早期,曾国不仅已存在,而且已称侯,已经发掘完的第65号墓是所见大墓之一,与之伴出的还有铜钺和铜面具等反映高等级身份的重器,极有可能就是西周早期的曾侯谏墓,说明曾国早在西周早期就已在汉东地区存在并已相当发达了。这一发现推翻了此前的所有认识。 新发现的铜器铭文,对于昭王南伐楚荆的诸多史迹的分析,都具有重要的辅证作用。对于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昭王伐楚事件,比如对于「 ”在曾”、「 ”在曾鄂师”等系列铭文,叶家山大墓的铜器铭文都可以重新诠释。 在四年前,随州羊子山鄂侯铜器群发现后,关于古鄂国的问题已渐趋明朗,此番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器群的再次面世,说明西周早期,曾、鄂应是同时并存于今随州地区的两个古国。从这次叶家山的发掘看,西周早期曾国并不大,似应仅局限于随州的漂水流域,而且与鄂相邻。到了西周晚期,鄂被周消灭,曾国才得以扩张,迅速地扩展至汉北及南阳盆地一带,替代鄂国成为名符其实的「 ”汉东第一大国”。 而随与曾的重合,似乎也成为必然推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发现,出土物上所见的「 ”曾”字,有两种。大体上商代与西周早期的「 ”曾”字「 ”下面不带‘曰’”,东周时期的「 ”曾”字「 ”下面带‘曰’字”。这反映了曾国历史演进中的重大变化(有学者猜测,这变化也许是联姻,也许是战争)。其原因,也许跟随的介入有关,而变化的时间,大体在西周中晚期。 就这样,早期曾国的发现,又一次改变了学术界对于西周早期汉东地区的政治版图认识。至于曾、随是否是一家,还是随灭曾之后改称为曾,曾、随的关系究竟如何,限于资料,目前尚未可知。 随枣走廊的发掘还在进行,曾国的故事仍将继续,众多未解或者争论极大的学术问题,仍将在随枣走廊的魔盒中不断露出端倪,正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所言,由叶家山墓地考古发现所衍射出的西周时期南方地区的政治形势可能仍然不及实际发生的那样复杂多变,但我们对于西周时期南方国家政治地理的理解,已经远远超出历史文献所能够为我们展现的。
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有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西晋时从古墓中发现的一部先秦纪年体史书。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汲郡汲县(今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时魏王的墓被盗,墓中沉睡了五百多年的一批古书得以重见天日。这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据说整整装了几十年。晋武帝对这一发现十分重视,命令将墓中出土的全部文物“藏于秘府”。
两年后,西晋朝廷征调了一批当时著名学者,对这批竹简古加以校读整理并将它们由古文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字体。
这批竹简是什么样子呢
据有关资料,竹简用素竹编联成册,每长度约为晋尺二尺,当战古尺二尺四寸,一简四十字,分为两行,每行二十字,用黑漆书写。简上文字为战国古文,即篆书,人们习称为科斗文。这种文字在秦统一后即已废弃,到了晋代、在当时人们看来简直茫光然若天书,且由于盗墓者的破坏,灯简散乱不全,所以整理起来十分困难。学者们整整花费了二十年时间,才大体整理完毕,计编校出古书十六种七十五篇,包括传世的《易经》《国语》等。
其中尤使人注目的是十三篇编年体史书,记载了夏、商、周、三代史事,西周灭亡后,即接晋国纪年,至战国三家分晋后,又用魏国纪年至
“今王二十年而止”,
所谓今据推算为魏襄王,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9年。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书记述的许多史事与儒家经典所言截然相反,如太甲杀伊尹,文王杀季历、幽王被逐等。以幽王时史事为例,史书称周、召二相共和,竹年称是共伯和执政,孰是孰非,这就在当时学术界中引起轩然大波,至今仍未得出定论。
唐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加强,与儒家经典不合的《竹书纪年》,为世人所漠视,经唐末五代战乱,到宋代仅剩残本三卷,约在宋末元初,连残本也流失了。
后代又出现了今本和古本。
今本是元末明清以来的通行本里混入了某些其它古书的内容。一些学者鉴于此,从古书中汇辑出竹书纪年的佚文,即竹书纪年的“古本”。古本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订正和补充一些史籍的失误和遗漏。如《史记》记战国自田成子杀简公自立为齐王,至秦灭齐,共历十世。但《纪年》则记为十二世,与《庄子·肤箧》
“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
的记载是一致的,纪年的记载是正确的。
其记越王朱句名,《史记》中不见。传世的与新发现的两柄越王州句剑铭文有
“越王州句自作自剑”
说明历史上确存在过一位名闩“朱句”的越王。又是《竹书纪年》的记载正确。
再如《尚书·无逸》篇提到商王中宗。《史记》认为中宗为太戊,《竹书纪年》则称“
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
殷墟卜辞出土后,人们发现甲骨文中有“中宗祖乙”四字连文,证实了纪年记载的正确性。
而今本竹书纪年,经著名学者王国维考证,为后人重编,有许多作伪的东西。
关于《竹书纪年》至今还有不少没有解开的谜。
其一、《竹书纪年》是不是晋之《乘》?
《孟子》曾提到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秦焚书坑儒后,除鲁之《春秋》外,其他诸侯国的史书差不多都失传了。那么《竹书纪年》按其用晋国纪年,是否与晋之乘有关系呢历代史学家就持有这一看法,并为许多学者赞同,但这仅是推测,无直接证据。
其二,所谓今本《竹书纪年》,究竟哪些为原文
哪些是混入的他书,仍然没有完全弄楚。
所以史学家没有绝对把握,是不会随引用今本《竹书纪年》的。
大量(匽)燕侯铭文青铜器的出土,充分证明这里就是燕国的始封都邑。据《史记》记载,周武王十一年(前1045)克商封召公于燕。而我们今天的首都北京,是和琉璃河董家林的燕都古城一脉相承的,于是北京建都建城的历史可以上溯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燕国,由此,此遗址被称为“北京城的发源地”。遗址包括古城遗址、生活区和墓葬区3个部分。其中,古城遗址约为南北向方形或长方形,北城墙全长829米,东、西城墙仅存300米左右。城外有深约2米的护城壕。宫殿区位于城址的北中部,附近有祭祀和生活遗址。 墓葬区位于城址的东南,被京广铁路分割为Ⅰ区、Ⅱ区。Ⅰ区为中、小型墓葬,随葬品少,多殉人、殉狗,是商遗墓地;Ⅱ区多大、中型墓,随葬品丰富、规格高,但极少见殉人、殉狗现象,可能是周人墓地。
两区中的大、中型墓葬多陪葬有车马,最大的车马坑陪葬有42匹马。出土文物数千件,以陶器、青铜器为主,还有原始瓷器、铅器、玉器、石器、玛瑙器、角器、骨器、牙器、蚌器、漆器、木器以及蚌壳等。陶器有壶、鬲、鼎、簋、罐等明器或实用器。青铜器包括礼器、容器、兵器、车马器、工具等类别。其中青铜礼器有鼎、簋、爵等,兵器有戈、矛、匕首等。1995年8月21日在遗址上建成了博物馆,并正式对外开放。馆内陈列有西周时期各类器物等300余件,这些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不仅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北京作为都城3000多年前的建城史及其灿烂的古燕都文化,更展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及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
墓葬:遗址保留的2座燕国贵族墓葬,其中有陪葬的燕国贵族使用的文物珍品和2处陪葬的车马坑等。
漆器:出土了罍、觚、盾等成组的漆器,并且大部分能够复原,在商周考古中尚不多见。
青铜器:遗址中出土了数件国家一级文物。其中,通高062米,重415公斤的堇鼎,是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的一件青铜器。
西安号称的西周都城其遗址只发现了渔网和粮食,更多的文献及遗址证明了成周洛阳宗周宝鸡的史实,而西安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小渔村罢了。
1.首要的证据是铸造于周成王五年、于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何尊。何尊铭文: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爯武王豊礼,祼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兹)辥(乂)民。”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爯武王豊礼”,明确了周武王迁都成周、周成王在成周称王的事实。
2、有50个出土文物金文和成周有关,有24个出土文物的金文和宗周有关,有22个出土文物的金文和莽京有关。但在出土文物和丰有关的仅有4个,和镐有关的出土文物金文尚未发现。
3、在和成周有关的金文中可以看出成周的建筑物有:大庙、大 室、京室、京宗、京大室、京宫、成大室、康宫、康昭宫、穆大室、康新宫、康夷宫、康刺宫;而与宗周有关的建筑物仅有大庙、穆庙、大师宫。
综上所述,洛阳作为西周的都城名正言顺,那为什么会有人认为西周首都是镐京而非洛阳呢,其实全来自这样一段话: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 。《史记》这句话就是说在司马迁那个时期人们认为西周周成王是迁都洛阳了的,这个从史记娄敬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这段话是娄敬劝说已经定都洛阳的刘邦迁都关中的话,如果关中的沣镐是西周首都,那么娄敬怎么会这样问。然而司马迁的西周都沣镐没有给出任何证据,只是个人臆测不应成为西周都镐京的证据,而他作为陕西人偏赞西安,私心杜撰也是有可能。可总有一些人奉司马迁的话为“金科玉律”,然而我们现在已经证实在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至少有两处错误,其一为“共和执政”实际为“共和伯执政”,其二就是广为人知的“烽火戏诸侯”然而烽火传信是汉朝才有的,在西周不可能烽火戏诸侯。所以司马迁认为西周都沣镐的话自然不能全信。
汉武帝东巡河洛,思周德,东周时周德已衰,汉武帝到洛阳思的不是东周,而是成王定都成周的成康之治。北魏孝文帝建都洛阳的原因: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经略四海,此周、汉之所以兴隆也。唐太宗攻东都之后作《古都感赋》“昔武王之克殷。筑王城而定鼎”,就是唐太宗思怀武王灭商在洛阳定都,宋太祖欲迁都到家乡洛阳,称循周汉故事,周汉故事就是指周武王与汉光武帝,并未建都关中,而是定都河洛。因此才有周汉(东汉)之兴隆。汉高祖、汉武帝、北魏孝文帝、唐太宗、宋太祖认为洛阳代表周朝之兴隆,或者直接称武王定都洛阳,依据的是周代文献,周开国成王受武王遗命定都洛邑在周代文献还是金文上都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记载。
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