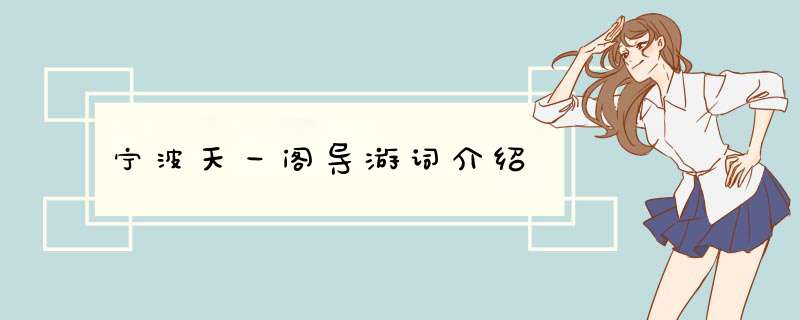季羡林:藏书与读书

有一个平凡的真理,直到耄耋之年,我才顿悟:中国是世界上最喜欢藏书和读书的国家。
什么叫读书?我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下定义。我们姑且从孔老夫子谈起吧。他老人家读《易》,至于韦编三绝,可见用力之勤。当时还没有纸,文章是用漆写在竹简上面的,竹简用皮条拴起来,就成了书。翻起来很不方便,读起来也有困难。我国古时有这样一句话,叫作“学富五车”,说一个人肚子里有五车书,可见学问之大。这指的是用纸做成的书,如果是竹简,则五车也装不了多少部书。
后来发明了纸。这一来写书方便多了,但是还没有发明印刷术,藏书和读书都要用手抄,这当然也不容易。如果一个人抄的话,一辈子也抄不了多少书。可是这丝毫也阻挡不住藏书和读书者的热情。我们古籍中不知有多少藏书和读书的故事,也可以叫作佳话。我们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古籍中寄托的文化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历千年而不衰,我们不能不感谢这些爱藏书和读书的先民。
后来我们又发明了印刷术。有了纸,又能印刷,书籍流传方便多了,从这时起,古籍中关于藏书和读书的佳话,更多了起来。宋版、元版、明版的书籍被视为珍品。历代都有一些藏书家,什么绛云楼、天一阁、铁琴铜剑楼、海源阁等等,说也说不完。有的已经消失,有的至今仍在,为我们新社会的建设服务。我们不能不感激这些藏书的祖先。
至于专门读书的人,历代记载更多。也还有一些关于读书的佳话,什么囊萤映雪之类。有人做过试验,无论萤和雪都不能亮到让人能读书的程度,然而在这一则佳话中所蕴含的鼓励人读书的热情则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
关于“四时读书乐”一类的诗,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可惜我童而习之,至今老朽昏聩,只记住了一句“绿满窗前草不除”,这样的读书情趣也是颇能令人向往的。此外如“红袖添香夜读书”之类的读书情趣,代表另一种趣味。据鲁迅先生说,连大学问家刘半农也向往,可见确有动人之处了。“雪夜闭门读禁书”代表的情趣又自不同,又是“雪夜”,又是“禁书”,不是也颇有人向往吗?
这样藏书和读书的风气,其他国家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据浅见所及,实在是远远不能同我国相比。因此我才悟出了“中国是世界上最爱藏书和读书的国家”这一条简明而意义深远的真理。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有极大一部分是通过书籍传流下来的。我们必须认真继承这个世界上比较突出的优秀传统,要读书,读好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上无愧于先民,下造福于子孙万代。
一、叶盛,明代著名藏书家,其藏书楼箓竹堂“藏书之富,甲于海内,聚书至数万卷”。叶盛经常告诫子孙要爱书读书。他说:“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教训童稚以给食,但书种不绝足矣!”
二、徐乾学,清初著名藏书家,从小就喜欢书,爱读书。针对当时很多人只想为儿孙们多留下点土地财产、金玉宝物、亭台楼阁等,他却对他的几个儿子说:“依我看,不论给后人留下什么财产,也难免会有失去的一天,不会长久享用不尽的。那么我给你们留传下什么东西呢?”徐乾学指着满屋子的藏书笑着说:“所传者惟是也!”并当即给藏书楼定名叫“传是楼”。很显然,在徐乾学看来,田产财物、珍宝玉器等物质财富总有用尽之时,而书籍里的知识是永远也学不尽用不完的。
三、清末藏书家张金吾藏书楼有诒经堂一处,系取“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义;杨以增的藏书楼名叫“海源阁”。他把书籍比作海洋,“学者而不观于海焉,陋矣。”然而,“观于海,久处其中,茫洋浩瀚不知所归,亦为学者之戒。学者应该涉海而探源,知源之所出。”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书籍它确实是一个知识的海洋,只要我们“涉海探源”,就一定会找到永不枯竭的知识之源的!
四、浙江宁波天一阁,建于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为面宽六间的两层楼房,楼上按经、史、子、集分类列柜藏书,楼下为阅览图书和收藏石刻之用。建筑南北开窗,空气流通。书橱两面设门,既可前后取书,又可透风防霉。
五、清朝北京故宫文渊阁,是专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的藏书楼,其房屋制度、书架款式等仿天一阁。
六、中国古代的官私藏书,总的来说,是供少数人阅读使用的,这同文化为少数人所掌握的历史时代是相适应的,而私人藏书也在很在程度上保护了文化。
现将主要辑本陈述如下:
(一)《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六卷。光绪十年潘祖荫编。据潘序云,黄氏士礼居藏书散出后多归汪士钟艺芸书舍,道光中又渐散失,初归聊城杨氏海源阁,后逸出者入吴平斋、陆存斋之手者亦多。潘祖荫一叔母嫁与汪阆源长子,因而潘得以从中抄录黄跋。后又得自吴、陆二家藏本之跋,并缪荃孙等赠送若干。于是按四部排列,编刊此书。卷一经,卷二史,卷三、四子,卷五、六集,凡六卷,收录题跋二百余种。此记有光绪十年吴县潘氏滂喜斋刻本。
(二)《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二卷。缪荃孙编。新收录荛圃题跋七十种:经七种、史九种、子十九种、集三十五种。这些黄跋皆由缪荃孙从归安姚觐元、德化李盛铎、湘潭袁芳瑛、巴陵方功惠、揭阳丁日昌等处观书抄录所得。光绪二十二年,由江标刻印,收入《灵鹣阁丛书》。
(三)《士礼居藏书题跋再续记》二卷。缪荃孙编。补录黄跋五十种:经二种、史六种、子十九种、集二十三种。据缪荃孙说,此册补辑在江标借刻《续记》时已编成,江不知有此册。民国元年,顺德邓实刻印此册,收入《古学汇刊》第一集。
(四)《荛圃藏书题识》十卷《荛圃刻书题识》一卷。缪荃孙、章钰、吴昌绶等编。民国八年,缪荃孙合“士礼居题跋三记”,复从乌程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和海盐张氏涉园、松江韩氏读有用书斋等处抄得黄跋补入。另由章、吴补得若干,总而编纂成此。此编一将刻书题识另卷分出,一则将确知版本流向的藏书处注明。民国八年江阴缪氏刻本。
(五)《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编》。孙祖烈编。民国间上海医学书局石印本。此编实取前编三记,加上张氏《适园丛书》中的《百宋一廛书录》。错误甚多。
(六)《士礼居藏书题跋补录》不分卷。李文裿编。辑得前编三记未录之黄跋二十八种。民国十八年冷雪庵铅印本。
(七)《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四卷《再续录》一卷。王大隆辑。大隆字欣夫,原籍浙江秀水,后迁苏州。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卒公元1966年。藏书室名“二十八宿砚斋”,著有《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等。此编刻于民国二十二年,与《思适斋书跋》合为《黄顾遗书》。
黄荛圃题跋与众不同的最大特点是喜谈藏书授受源流和得书经过。余嘉锡讥之为“卖绢牙郎”,对这种风格持批评或贬责态度的人不少,认为他与骨董商、掠贩家无异。其实黄跋的这方面独特内容和风格还是有意义和价值的。黄跋不仅喜详述得书经过,而且还尽情地表现自己的心态,以及日常生活起居中的琐事,多一时兴到之语,尽管无规无矩,但读毕细想,终究还是围绕着书在谈。 当然,黄跋对书本内容的提要、品评和考订比较忽略,但在学术上仍有较高价值。
其一,集中反映了黄丕烈的版本学研究方法、观点及理论。比如他判断、鉴别版本的方法,对宋元旧刻的总体认识,对明刻本、批校本价值的探讨,对重本、异本的重视,对稀见古籍的搜访、利用,都具有无可争辨的学术意义。黄丕烈是乾嘉学者中把版本研究推上专学的一位顶尖人物。因此,从版本学的学术角度来看,蕴含黄丕烈丰富版本学思想的《荛圃藏书题识》的学术价值,也不是晁、陈二志能简单相比的。
其二,黄跋对藏书源流的详细叙述,不仅留下了许多藏书史上的资料,而且还从商品流通的社会经济领域,为我们研究清代藏书史提供了难得的素材。那些被讥斥为骨董家言论的题跋,如果跳出传统治学方法的囿限去观察,就不会以为都是些无聊话了。至于它“可以考百宋一廛散出之书”的功用,就不必赘述了。
本文2023-08-09 12:46:44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518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