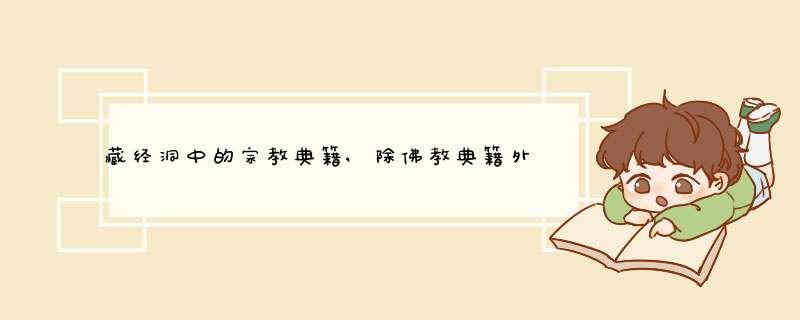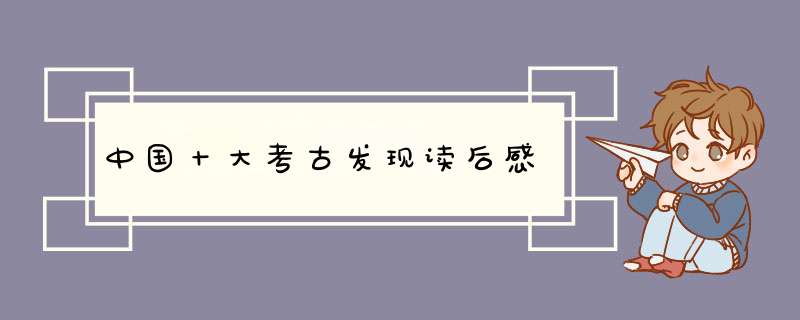守护莫高窟半生,与丈夫分居19年,敦煌女儿樊锦诗:只为一个嘱托

1963年,北大刚宣布完考古专业的分配名单,一个学生家长嚎啕大哭:“我只有一个儿子,你们怎么能把他分配到敦煌?”
当年,一起被分到“把人吓哭”的敦煌工作的,还有个瘦小的女生樊锦诗。
樊锦诗也不想去莫高窟,可为了老师的嘱托,她决心前往。
临行前,她和男友约定三年后就去武汉团聚。
没成想,自此她却守了莫高窟大半个世纪。
从青丝到白发,樊锦诗为何能一直坚守?她又为什么被称作敦煌女儿?
1938年,樊锦诗生于北平。但长在上海的她,更像个地道的上海姑娘。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父亲希望她今后饱读诗书,所以以“诗”命名。
樊锦诗也不负“父”望,虽自小体弱多病,成绩却一直不错。还特别喜欢看书。
中学时,樊锦诗读到过一篇关于莫高窟的课文。课文里说莫高窟有几百个洞窟。洞窟里面有精美的彩塑,还有壁画,是一座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
樊锦诗对此印象很深,特别是1958年她考上北大考古专业之后,总是想尽办法搜集和莫高窟相关的一切。
大学毕业前一年,樊锦诗还主动要求去莫高窟实习,然而她没想到的是,理想和现实之间,隔着漫天的黄沙。
刚到敦煌,鲜花般的上海姑娘樊锦诗就被风沙吹得灰头土脸。等她用香皂洗完头,头发上却留了一层洗不掉的白碱,黏糊糊地让人难受。
研究所里的前辈还告诉她,即便是这样又苦又涩的碱水,也得省着用。这是长在南方的她难以想象的事情。
不光缺水,这里食物也十分匮乏。蔬菜除了白菜、土豆就是萝卜,嘴馋时樊锦诗就盯着邻居树上的水果,却总也不敢去“偷”点解馋。
研究所种的水果成熟时,樊锦诗终于分得了一份,刚拿到手的那天晚上,她就一口气全吃光了。
时隔多年后,樊锦诗还感叹:“此生吃过很多水果,那晚的水果却是最好吃的。”
对樊锦诗来说,物资匮乏倒还可以将就,可怕的是那里的气候。不但干燥,温差还大,不服水土的樊锦诗几乎每天都失眠。
没过多久,樊锦诗就病倒了,身体虚弱到连走路都困难,老师怕她出事,急忙安排她回了北大。而当时距离实习期满还有三个月。
从此,樊锦诗提起敦煌就心有余悸。毕业分配时,一听说自己要去敦煌工作,樊锦诗又如何能欢喜得起来?
而且,当时樊锦诗已打算结婚,男友彭金章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教书。
樊锦诗知道两地分居意味着什么。
正当她踌躇间,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的一番话,让她下定决心去往敦煌。
苏秉琦先生郑重地对她说:“我要感谢你,你这次去敦煌,是要编写考古报告的,这考古界的二十四史,就交给你了。”
在当时,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叫:“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
近代以来,敦煌莫高窟不断遭到劫掠,仅1900年,藏经洞的文献就被英国人斯坦因拉走了十几车。
这些涵盖天文地理、习俗宗教、医学术疏、经济军事等的文献就如一部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而精华部分却早已经流落到日本、俄国、英国、美国……
敦煌的风雨历程成了几代学者的心头痛,而让敦煌学回到中国,也成为几代学者们最大的愿望。
听到恩师如此重托,樊锦诗眼窝发热,顿时觉得自己重任在肩。她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竭尽全力,用3-4年完成老师的嘱托。
临别时,男友彭金章轻声说:“我等你!”樊锦诗哽咽着安慰他:“很快,至多3、4年。”
然而,樊锦诗却失约了,他们足足分离了19年,才得已团聚。
樊锦诗到的时候,敦煌的风沙一如记忆中那般凛冽。而她的住处竟是一处破庙。
有一天,她想要去远处的土厕解手,刚一出门就看见一双绿眼睛,吓得她汗毛倒竖。
当时她第一反应便是,遇到了狼!
樊锦诗忙转身回来,插紧门心惊胆战地过了一夜后,才发现那“狼”其实是头驴。
这样的“笑话”却让樊锦诗笑不出来,反而感觉深深地悲凉。
为了不思念上海的生活,樊锦诗不敢照镜子,尽量不去想外面的一切。
可每到夜深人静时,樊锦诗都特别孤独:“我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了,老彭也把我忘了。”
1967年,当初的恋人彭金章,已成了丈夫“老彭”,而婚后,他们一个在武汉,一个在敦煌,隔着天南海北。
有第一个孩子时,樊锦诗与彭金章达成一致,准备临产时去医疗条件较好的武汉待产。
然而,迟迟请不到假的樊锦诗却不得不独自在敦煌生产。
好心的医生见她没有家人陪伴,给她出主意,说:“你快给你爱人发电报,说你生了个男娃娃。”
樊锦诗却苦笑道:“就算是个金娃娃他也赶不来。”
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彭金章正挑着两个筐子焦急地等火车。筐里放着早已准备好的营养品,以及孩子的衣服。
等他满头大汗地出现在病房门口,在惶恐中等了多日的樊锦诗顿时大哭失声。
彭金章看着虚弱的妻子,以及还没有衣服穿的儿子,也心疼得直抹眼泪。
之后,老彭又是炖鸡汤又是给孩子冲奶粉,体贴地照顾妻儿。
有丈夫的照顾,樊锦诗度过了一段温馨的日子。
可月子还没过完,老彭的假期已到,两夫妻又不得不再次分离。
他们在信中相约一定要尽快把工作调在一起,结束这种分居生活,可直到第2个儿子五岁时,他们的愿望还没有实现,一直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因为工作忙碌,樊锦诗没空管孩子。两个儿子不得不先后送到武汉,由彭金章照顾。
樊锦诗曾说:“我的心被撕扯成两半,一边是莫高窟,一边是老彭和孩子。”
其实,即便是备受赞誉,樊锦诗却不止一次想过要调离敦煌,去武汉好好照顾家人。
可樊锦诗的工作对莫高窟很重要,敦煌研究所不舍得放人;而彭金章在武大创建了一门考古专业,责任重大,武大更舍不得放人。
双方单位拉锯般争了多年,直到1986年时,甘肃有关部门特意派人去和武汉大学协调,武汉大学才松口表示此事交给彭金章个人决定。
不忍心看着妻子为难,年近50岁的彭金章,主动放弃了自己钻研已久的商周考古课题,到敦煌重新开始。
这对一个考古学者来说,是很难的抉择。为此,樊锦诗曾无数次对人说:“我不是个好母亲,更不是个好妻子。”
可于敦煌来说,樊锦诗却是个很好的守护者。
1984年,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
一次,负责档案编制工作的她,在查阅资料时,发现了一张法国人于1908年时拍下的《敦煌图录》。
对比同样的洞窟和同种文物的照片,樊锦诗发现,短短几十年间,许多壁画已经慢慢退化或者模糊。
“壁画在退化,壁画在退化……”这句话像魔咒般挥之不去。如何尽可能保护这些文物,成了萦绕在樊锦诗心头的一件大事。
苍天不负有心人,1989年时,樊锦诗终于等来了转机。
那年,樊锦诗去北京出差,无意间看见有人在用电脑。电脑上的色彩缤纷,一下子吸引了她的注意。
当得知图像数字化后可以储存,樊锦诗激动不已,当即开始筹划用计算机保存莫高窟档案。
但当时的计算机价格昂贵,中科院一台640K的处理电脑就卖到6480元,何况是大规模采购计算机,敦煌研究所根本拿不出来这笔巨款。
几经考虑后,樊锦诗硬着头皮找到甘肃科委。谁知,一番恳切交谈后,本不富裕的甘肃科委被深深打动,爽快下拨了30万,让他们用来研制敦煌石窟数字档案。
经过考古人员们的努力,洞窟、壁画、彩塑以及散落在世界各处的文献,先后用计算机汇集在一起,成了一个个永久保存的电子档案。
而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又接踵而至。
上世纪90年代,来敦煌莫高窟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光2001年,游客就超过了30万人次,且人数还在连年攀升。
有的游客大老远跑来看石窟,一出洞窟就感叹:“灰突突地有什么好看的?!”但即便是这样匆匆的一次参观,都会让莫高窟的微生态发生改变,使保护工作变得更加棘手。
为此,樊锦诗吃不下睡不着,不停地向有关部门写信建议停止莫高窟参观。
此举,引来了许多人不满:“要钱要支持时想到地方了,需要为地方做出贡献时,只知道死守着文物。”
樊锦诗也有过委屈,可转念想文物只有与时代相联系,才能增添活力,而如今的技术手段或可以解决莫高窟面临的困境。
为此,她呼吁在敦煌莫高窟保护区外建一所虚拟场馆。
2014年,敦煌数展中心正式运行,借助先进的数字和多媒体技术,千年前的洞窟如活过来了一般,不但缓解了莫高窟的压力,还给游客带去了很好的体验。
而樊锦诗也因对莫高窟的坚守与贡献,获得许多奖项,不断受到表彰。
可樊锦诗却说:“我原来并不懂文物保护的,我更想去完成苏先生交待的考古报告。”
面对越来越多的赞誉,樊锦诗认为荣誉应该属于莫高窟人,还将奖金都捐给了敦煌研究院。
2011年时,樊锦诗交出了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的第一卷,距离受苏秉琦先生嘱托那年,已经过去了整整48年。
其实,做学问何尝不是樊锦诗的梦想?可多年来,她从事更多的是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工作。
如今,彭金章先生已然辞世,而年过80的樊锦诗,又回到敦煌,为编撰敦煌考古的“二十四史”而努力。
在一代代敦煌学者的努力下,“敦煌学在外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坚守了敦煌几十年的樊锦诗终于完成了心愿。
敦煌莫高窟附近的宕泉河畔,长眠着许多为莫高窟做过贡献的学者。但樊锦诗却表示,这里不会再添新墓,包括她自己,因为“要保护敦煌莫高窟的整体风貌。”
活得通透的樊锦诗从不避讳生死:“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总有一天会走的,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有来生,我还会选择敦煌,选择莫高窟。”
几十年来,樊锦诗对莫高窟,困顿时坚守,需要时守护,为此,她牺牲了与亲人的相守,延迟了自己想做的学术研究。
甚至连为生命做出的最后打算时,都在考虑不破坏敦煌的环境。
人生最好的年华在哪里,哪里便成为生命中不可割舍的部分,敦煌对于樊锦诗来说,便是如此,她已然成为了真正的“敦煌女儿”。
坚守,是个力重千钧的词汇。靠得是身体力行,更需要热血铸就,而最后,要用每分每秒的时间去一点一滴践行。
-END-
作者:蕉下观雨
往期精彩文章推荐:
2016年贵州一局长被双规,录指纹时查出,他竟是18年前灭门案凶手
2015年,天津一家四口吃完饺子后3人离世,警察也差点中招
年前最后一篇散文
刚贴了一张膏药,在右侧肩胛骨的位置,也可能不是,好吧我不知道是哪,反正就是左手绕着脖子刚好能抠到的那个位置。缓了一分钟吧,那块儿我一趴桌子上准备码字就跳痛的筋骨肉好像受到了来自膏药地惊吓,一时忘记了咋疼,趁它还迷糊,我赶紧再敲一会儿。
我是个妥妥的宅女,一个行动派最想打倒的对象,如果硬让我选出几个特别想去的地方,前三个里,一定有敦煌。到敦煌一定是去莫高窟,当我看完《此生只为守敦煌》,我心说那好吧,算你狠,此生就先不去了,就此别过。开个玩笑,但是当真是敬畏,敬畏那里所有的无价的艺术品更敬畏那里的守护神常书鸿。当我第一次知道敦煌莫高窟的时候应该在 历史 教材里,印象不深,那时只顾埋头学习知识,丝毫不敢将心思放在学习文化上。后来,读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让我记住了一个破烂萎靡枯槁眼神空洞的王道士,大概的原话我都能回忆出来:是怎样一个苟延残喘地王朝会把一个民族最珍贵的宝库钥匙交到一个最没文化最目光短浅最舍本逐末最贪图蝇头小利的一个连知识都没有的半路出家的道士手里。在他的精打细算下,敦煌莫高窟封存的大量稀世经卷、壁画以及雕塑被几个洋人拿着几块儿廉价的马蹄银买走。至今,我们国内的白发苍苍的专家教授想要多了解一些莫高窟的 历史 ,都得漂洋过海买了票拿着放大镜脸贴着隔着冰冷地防弹玻璃看自家东西,那种屈辱感我想再有修养的人都会用国粹问候一句王道士。最滑稽的莫高窟里竟然还有一座道士碑,活生生的耻辱柱。同样是莫高窟的守护者,常书鸿却正大光明地被封为了神,且有碑传。
常书鸿先生,出生于1904年出生于杭州,家里是满清旁系且没落的贵族,他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拿到了庚子赔款的奖学金然后来到了法国巴黎学习绘画,很给国人挣脸,画作多次在欧洲展出并且在国际上获奖。本来已经在欧洲已经有了立足之地,就因为在巴黎见到了伯希和的《敦煌莫高窟图录》,从此就一眼“误”了终身,带着妻子和女儿就回到了祖国,辗转就来到敦煌。莫高窟里所有的艺术品即便是被打劫剩下的,在他眼里也是登峰造极高山仰止,已然开拓了眼界的他非常笃定莫高窟的艺术价值即便站在全人类 历史 的角度上也是会当凌绝顶的,于是他毫不犹豫的臣服于莫高窟,常书鸿像个疯子一样退去一身浮光掠影觥筹交错披上一件粗布麻衣就开始了他一生的莫高窟朝拜之旅,粗茶淡饭环境恶劣还不算什么,作为有官印的莫高窟的管理者,他不但经费无着而且还要被想办法抵挡军阀土豪们对莫高窟珍品的觊觎,尤其当地的县长寡廉鲜耻脸皮之厚不亚于那位王道士,本就是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常书鸿常常周旋于地痞流氓之间而疲惫不堪。
还好,他靠卖自己的画挣钱堵公家的亏空,而且有那些壁画陪着他,让他可以忘乎所以的日以继夜地临摹,但是也因此忽略了放弃大城市舒适生活陪他而来的太太,常先生第一任太太可以算的上是他的灵感缪斯,在国外拿奖的好几副画的模特都是她。我不知道为常书鸿先生写传记的作者叶文玲为什么要大书特书常先生第一任妻子与人私奔以及常先生骑马夜奔追妻的情节,这对本书来说没有丝毫的必要。她不是林徽因,绘画并不是她的专业敦煌并不是她的心之向往,从一开始鼓励新婚丈夫出国游学,在家里苦等数年才等到丈夫接她出国,并自学了法语,在丈夫身边时她还夫唱妇随去学习了画画,后来丈夫说要回到炮火连天的祖国她也放弃了国外安逸的生活回来了,再后来又要求她放弃大城市的教师岗位带着两个幼子到敦煌,而且来敦煌后也不见在身边的丈夫分出一点点温存给她,她终于扛不住了不是很正常的事儿么?我还觉得,她生育了常沙娜这么优秀的女儿,留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位敦煌研究者以及绘画天才艺术家,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真心觉得足够了,这个女人已经吃了很多苦了,没必要故意弄出一些情节放在书里,尤其是放在常先生的自传里。再说常先生最后还是找到了和他有共同理想也能够陪他吃苦的第二任妻子,也是幸福的一对。另外还有,写一个画家,写敦煌,就前面几张,插图全书就几张照片,实在有点不应该。
我不懂绘画也不懂艺术,我只是感性地认为莫高窟的珍贵不在于它里面的东西有多珍贵,而是背后的那些人和故事很珍贵,一千六百多年的 历史 很珍贵,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能够守护好他们的完整很珍贵,哪怕王道士顾的会计无意间发现洞窟墙壁后的夹缝的故事也很珍贵。更珍贵的,自然是常书鸿先生,冒死守护且将敦煌莫高窟带给世人的创举, 他让我知道一个人要是忠于一件事儿所爆发出的力量竟然有这么大,这是非信仰所解释不清的事儿。亚伯罕曾经为了向上帝表明自己的忠心,准备拿自己唯一的老来子斩杀献祭,上帝用一只羊替换了亚伯罕的儿子。常书鸿也是一样,他让自己年幼的女儿加入到了临摹的工作组里,没日没夜地训练和熏陶,再加上常沙娜那与生俱来的天赋与专注,十四岁时的临摹画作,竟然就可以让常书鸿拿着去痴迷绘画的县长那里换下一个被军阀定下的莫高窟里的一个精致佛头。后来,为了筹措保护莫高窟的资金,常书鸿筹备了一个父女联合画展轰动了全国,常沙娜也一时之间成了神童的化身,十七岁年龄一到,就被人资助去了美国深造,后又得到了林徽因女士的亲身教导,参与了新中国许多大型礼宾接待大厅的设计。
艺术造诣浅薄的我审美水平肤浅的我尽管内心戚戚,不过此生我还有机会,我女儿瑾瑜现在在学画画,那么,或许真有那么一天,我可以带着带着一双慧眼的女儿去朝拜莫高窟,我可以守着她临摹壁画,可以旁观她为国粹倾倒的样子。但愿有那么一天,可以打着她的名义,坦坦荡荡的朝敦煌进发,顶礼膜拜 历史 和璀璨的文化,也膜拜此生只为守敦煌的常书鸿先生。
回到本文开头,可能并不是膏药起了作用,是常书鸿教会了我,让灵魂去驾驭肉体,在困难中磨砺训练你的灵魂,让越来越强大的灵魂陪着你奔赴心之向往,才能在今生短暂的时间里,支撑你顺利度过彼岸。
名称
佛教诞生:古印度,迦毗罗一个小王国王子(现在尼泊尔),乔达摩悉达多(和孔子一个时代公元前565-公元前486)他的家族是释迦族,世人称 “释迦牟尼”
小乘:佛教中一开始 从个人解脱痛苦角度出发的一种修行
大乘: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佛,佛祖可以帮别人解脱、
释迦牟尼的顿悟,收徒、造佛像,一开始在孔子时代被我国人文无法接受,因为孔子倡导孝道等,到西晋短暂中国统一,之后的五代十国,战争导致人们精神寄托于外选择,产生信佛
敦煌莫高窟:壁画主要是反应佛教画像,加上中国神话故事,当前特别有名“飞天”、女娲和伏羲等
释迦牟尼故事:他的前世故事(前世尸毗王割肉产生的因果-侧面反应当时到处都是战争的血淋淋的战争,)
印度的佛祖像和中国佛祖像最大的区别:中国必须穿衣服不能暴露太多,但是印度佛像穿的比较少
佛祖的死:叫涅槃(超脱轮回),和尚死叫圆寂
敦煌藏经洞有哪些宝物:现在只有高僧像,原来有大约5万部经书,现在主要被英国、法国、日本获取,有《六祖坛经》《道德经》《孝经》 《孔子佳语》等等
这位1938年出生的奶奶说:只有你是个有心人,不懂的事物,可以请懂的人来帮你,但是这些基本原理你自己是绝对可以学会的,关键看你主观性和看出这些技术背后的原理是相通的。
老人家让我深刻的一句话:不该你拿的钱,一分都不能拿,但是你付出努力收获的钱,要坦坦荡荡的拿
朋友送了我一本《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初初一读,就被它真挚、质朴的语言吸引。没有浮丽的粉饰,没有豪言壮语,有的只是笔墨间流露的真挚情怀。千年岁月在眼前拂过,我在那漫漫飞舞的黄沙中看见千疮万孔也掩盖不住辉煌的敦煌莫高窟,看见在戈壁荒漠中跋涉的一代代信徒、开拓者、工匠,一代代守护人。
敦煌石窟是中华历史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我们历史的一道伤痕。东晋十六国前秦政权的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一名叫乐僔的僧人从中原远游到敦煌,一切皆天意,就因为夜幕降临时,他不经意地一望,对面三危山的佛光显耀,令他顿悟,决定留在这里坐禅修行。于是千年旷世石窟在他开始了第一凿。此后连续十个世纪,从未间断建凿、塑像、绘画的佛事活动,一代代僧人的虔诚还有后来的皇室宗亲,商贾以至普通百姓,以他们的追求、憧憬凝固成一个个石窟,一幅幅壁画,用千年的时光在一片荒芜中创化成宏大的佛教圣地,留下辉煌的艺术奇迹。
佛教的传播并不能阻止人类的战争。千年间,对敦煌的争夺不断,最终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都融汇进中华民族广阔的怀抱中。敦煌处于️中西方陆地交通要道,陆上丝绸之路门户,经济贸易发达,文化艺术也在这旺盛的宗教政治经济土壤中,兼容并蓄,吸收不同的养分,融合了中原、印度、希腊、伊斯兰文明的元素,蓬勃发展,孕育出独特的灿烂文明。
莫高窟就是敦煌文明的一颗光芒万丈,见证历史的璀璨明珠!莫高窟的历史是一部贯通东西方文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佛教发展和传播的历史,更是一部人类的心灵史。在那荒芜的黄沙之地,在战乱纷扰的岁月,它是人们的心灵故乡,安放人们的忧惧、悲苦、欢乐和向往。
后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敦煌渐渐失去东西方交通中转和西域门户的地位,莫高窟也渐渐衰落,直至明代嘉靖年间,嘉峪关锁关,莫高窟彻底被遗弃。之后的四百年间,无人管理,任人破坏。这个曾经的佛教文化艺术圣地,就这样渐渐颓败不堪,满目疮痍,湮没在历史的灰烟中。
直至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惊醒世人,敦煌石窟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重新回到历史的视野。可惜当时的中国,积弱落后,任人摆布,民不聊生。敦煌石窟的重现,引来的是一拨拨打着文化研究旗号的外国探险家的强取豪夺,其掠夺破坏程度,令人触目惊心。陈寅格的一句话把中国人的痛心说尽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这伤心,要用多少的努力才能抚慰?更甚的是,这饱经自然的岁月的人为的摧残的人类文化瑰宝如何修复如何续存?从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伊始,这份沉甸甸的使命落在一代代的守护者身上。
从第一代所长常书鸿启动,在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贫困,科技落后,又遭遇政治斗争风暴的形势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而樊锦诗,接过前辈的棒,承上启下,担起使命,为敦煌事业奉献了大半生,“此生命定,我就是敦煌的守护人”
樊锦诗,原本是一个身体柔弱的江南闺秀,或许是命运一早巳经暗中安排,少年时代,敦煌就是她的一个美丽向往,此生与敦煌的缘分从那时就萌芽了吧。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1962年她与另外三名同学被选择去敦煌毕业实习,当时敦煌是大家向往但几乎没有人愿意生活在那的地方。实习期间,她就因为水土不服被迫提前回京,没想到,她之后的人生却留在这个水土不服的地方!
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敦煌,她不想,找到校方,学校承诺两三年后会有新毕业生去替换她。就这样,抱着可以回来的希望,又带着内心对敦煌、对莫高窟的热爱,踏上了黄沙之地。但是,世事无常,不久文革开始,“三、四年后调离敦煌”的许诺无法实现,之后种种机会,也失之交臂,或许一切正如她说的“敦煌是我的宿命”
1963年的那天,火车行驶在河西走廊,经过武威、张掖、酒泉,穿过茫茫的戈壁,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到了柳园火车站,坐研究所的拉煤卡车走了一百三十多公里的路程,举目所见,只有一望无际的沙丘和戈壁。卡车开进一个长两千多米的山谷,到达莫高窟,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樊锦诗两腿发麻,两眼发晕,摇摇晃晃地下了车。
正值青春年华的她就这样来到荒凉寂寥的敦煌,伴着遗世独立的莫高窟,开始她的人生。
当时的所长常书鸿是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还有段文杰等专家、研究人员、职工,已经扎根大漠多年。那时的生活非常艰苦,几乎与世隔绝,住土房,地上是永远扫不完的尘土,喝的是咸水,冬天零下二十多度,夜晚寒风夹杂着狼的嚎叫。而且他们还忍受着与家人的长期两地分居,无法享受普通人的天伦之乐。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奔劳在风沙肆虐的尘土中,卷缩在洞窟里,修复、临摹壁画、研究、分析、整理、撰写,守护着这座文化遗产。
书中有一个情景让我记忆犹深,樊锦诗第一次见常书鸿是在她毕业实习到敦煌的时候,她想象,这个她慕名已久,放弃优越的生活,从巴黎回来的大学者,应该是风度翩翩的艺术家,然而站在她面前的却是几个衣衫陈旧,面黄肌瘦的老农。
从1944年至今,几十年弹指一挥间,一挥间,几代人的青春和一生就过去了,而原本危危可岌的千年艺术瑰宝却延续下来了。从最初的抢救性修复到八十年代后依托科技不断进步的“预防性保护”从敦煌艺术临摹拓展到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石窟图像、敦煌文献、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多领域研究,开展国际合作,逐步形成了国际水平的敦煌研究体糸,如今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内外最具影响力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
“我其实也想过离开”樊锦诗的自述是这么的朴素真实。时光一点点地流走,樊锦诗也如大部分普通人一样进行着个人生活的轨迹,结婚、生子,所不同的是,她赋予私人生活的时间和空间是那么的少。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独自在大漠中条件恶劣的医院生下第一个小孩。孩子无法带在身边,只能寄养在亲戚家。所以,回忆往事,她对丈夫、孩子始终抱有深深的遗憾和内疚“我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我其实也想过离开”“我应该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我应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应该有权利和自己的家人吃一顿团圆的晚饭”却难以实现。然而在她内心,已深深地爱上敦煌莫高窟,难以割舍。“我感觉自己已经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了,离开敦煌,就好象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象要和大地分离”所以当1986年,组织上终于松口的时候,她内心是如此留恋、不舍。是她的丈夫,彭金章,也是一名优秀的考古专家,最终放弃了自己在武汉大学已经颇有建树的事业,来到敦煌,两个儿子在兰州读初中,从结婚开始的十九年后,一家人才算是团聚了。知她者,莫如老彭,“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他们用爱和生命践行了这样一个神圣的誓言。
1984年,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这年她46岁。藉着时代的发展,敦煌事业也迈上新台阶。为了将十年文革磋砣的岁月补回来,樊锦诗和她的同事们夜以继日,扑到工作上,硕果累累:巜科学记录档案》将敦煌石窟的各种纷繁复杂的信息科学地汇集成册。参与或领导制订巜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巜敦煌莫高窟保护和管理条例》等一系例规章制度,不仅以法律形式规范对敦煌文物的保护,而且也启发、推动全国的文物保护思路。把握时机,积极寻求与国际合作,推动与国际保护研究机构关于莫高窟壁的保护合作。适应新时代人们文化生活需求,创建“数字敦煌”不但解决了保护与开放旅游的矛盾,而且为敦煌文化的弘扬开创了一条康庄大道。更在她古稀之年,完成了巜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巜莫高窟第266一275窟考古报告》这是莫高窟第一份考古报告,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当代成果,意义重大,不负四十年前宿白先生对她的重托。
从青春年少到成熟中年再到白发暮年,樊锦诗始终守护着敦煌。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她,在荒漠里度过大半人生?也许是莫高窟艺术的感召力和她赤子之心的契合铸造了她的精神支柱吧。她有过痛苦和迷茫,感到自己一无所有,离开家乡,举目无亲,就象一个漂泊无依的流浪者,在时代和命运的激流中,从繁华的都市流落到西北的荒漠中。每当心情烦闷时,她会一个人向莫高窟九层楼的方向走去,在茫茫的戈壁上,在九层楼窟檐的铃铎声中,尽情释放心中的苦闷。洞窟里美丽的飞天滋润她的心田,静谧安详的佛像启迪她的精神。她说,那尊禅定佛的笑容启示着她,活在当下,回归内心。在朝朝暮暮的相处中,她的人生巳经不知不觉地和莫高窟艺术融为一体了,无法分离。正如书中所说的“我突然明白了樊锦诗愿意一辈子留在敦煌的原因了。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在这里无需寻找。只要九层楼的铃铎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
最后分享一句樊锦诗的独白作为结束语“人生的幸福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而且是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他就可以面对所有困难,也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的那个自我。”
本文2023-08-19 02:50:28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546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