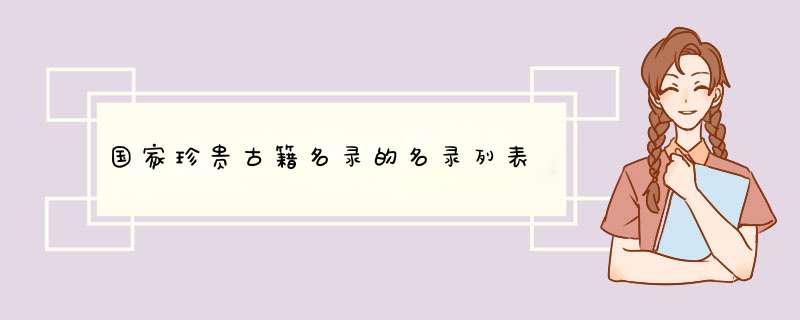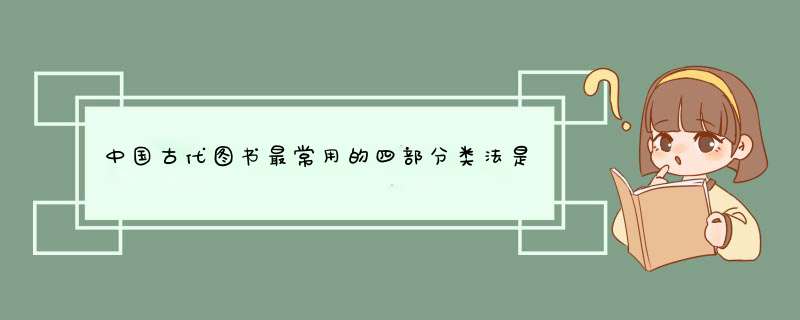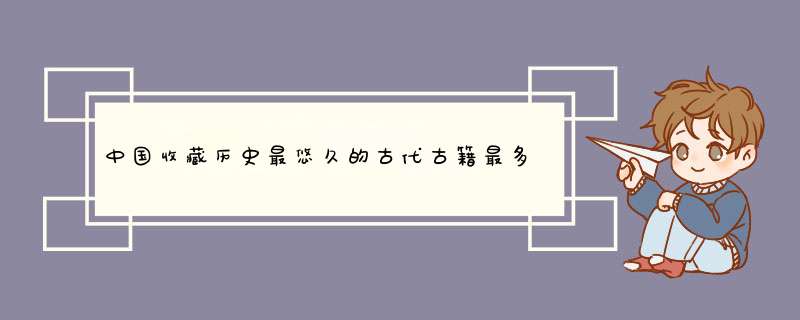古时候的人是怎样绘制地图的

在古埃及,每逢雨季,尼罗河洪水泛滥,带来肥沃土壤的同时,也冲刷了原本界限分明的田亩,为了声明对于土地的所有权,统治者不得不绘制地图,来确定自己所管辖的土地。
最早的地图,无关导航,而关乎占有,以及掠夺。
中国有记载的最古老的地图绘制在4000年前夏禹的九鼎上。相传大禹成功治水后,各部落与方国奉大禹为最高统治者。华夏遂分九州,大禹命人铸造九鼎,分别绘制各州的山川形势。鼎成后藏诸国都,普通百姓难得一见。九鼎上的原始地图,如同古埃及人的地图,都是一种对于土地所有权的声明。
谁拥有了地图,谁就能以“上帝视角”俯察这片土地,从此广袤的大地不再虚无缥缈,而是轻易地掌握在手中,并且可以在案上徐徐展开。这对于土地所有者而言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人对土地的欲望永远不知餍足,这赋予了地图一个天然的属性——扩张。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而当兵戎相见时,地图的身影再次显现。2000多年前的管子在《地图篇》中明确指出:凡是军事上的指挥者,必须首先研究和熟悉地图。(“凡兵主者,必先审之地图”)于是才有了许多向大王献地图的史事,譬如荆轲刺秦王,献上的是将军的人头与燕国地图。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两幅珍贵的古代军事地图: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和驻军图。这两幅图划时代地使用了比例尺的概念,前者约为1:18万,后者约为1:8万,分别描述了长沙国南部的山脉走向和驻军情况。西汉高后末年,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向长沙国南部发起进攻,朝廷及长沙国随即派兵征剿。这两幅图可能是墓主参与指挥此次征战使用的军事地图,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较早且较为精确的地图。地图给指挥将领带来了方便,不过可以设想,如果不幸落入敌手,长沙国将会陷入怎样的灾难之中。
所有的攻城略地落到纸上,都是为了将新的城池纳入自己版图,而地图上的每一次寸进需要付出多少的头颅与鲜血,这是在干干净净的地图上所看不到的。
士大夫的发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士大夫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君王丈量每一寸土地。
先行者是大禹的两名臣子,大章和竖亥,他们一个东西,一个南北,徒步为大禹丈量世界。“记里鼓车”出现在汉代,又叫大章车——大概就是为了纪念先驱大章——它大大减轻了丈量土地的劳动量。这种车分两层,每层有一个木人,车行一里,下层木人击鼓一次,车行十里,上层木人敲一下铃。驾车人只要记录鼓声和铃声次数便可以计算出马车行过的距离。
古人便是驾着这样的马车驶入未知的区域,凭借简单的定向设备确定位置,再将用肉眼观测到的地理信息记录下来,绘制到图上。
这种测绘最初全凭经验行事,久而久之,便有了一定的章法。西晋地官(专管国家的户籍、土地、税收和地图的官员),后官至宰相的裴秀将其总结为六项制图原则,也就是有名的“制图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分率就是比例尺,即确定面积和长宽的比例;准望就是方位,即校正地图各部分之间的相对位置;道里就是距离,即道路的里程;高下、方邪、迂直指的大体就是比较和校正不同地形所引起的距离偏差。
裴秀的制图六体为后世的地图测绘者所沿袭,在16世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带来西方制图理论之前,一直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制图传统。从唐代贾耽编制的《海内华夷图》,宋代沈括编制的《守令图》,到元代朱思本编制的《舆地图》,明代罗洪先编制的《广舆图》都能找到制图六体的影子。基于他的贡献,李约瑟称裴秀为“中国科学制图之父”。
在制图六体中,“分率”也就是比例尺问题,是科学制图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它关系到测绘者将以何种比例将庞大的山川河流、道路城邦“缩印”在绢帛或者纸上。裴秀的解决方案是“计里画方”,具体操作是先在地图上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绘成方格坐标网,以此来控制地图上各要素的方位和距离。
裴秀所绘的地图皆已失传,现存最早的“计里画方”实例是南宋石刻《禹迹图》,此图为全国地图,刻有山川、州郡等地理要素,横70方,竖73方,共5110格,方格边长11厘米,即“每方折地百里”,地图比例尺为1:500万,全图所涵盖的总面积为1278万平方公里。这是西方地图投影法和经纬度制图传入之前最科学的制图方法,其中的海岸线与黄河等河流的形状已经与现代地图极为相近。这一方法甚至在13世纪传到西方,被阿拉伯和意大利的地图学学者所采用。
认知的边界
一个时代的地图,反映的是一个时代对于世界的认知边界。地图延展到哪里,认知也就到了哪里,至于“画”外之境,对于所有绘图者来说都是一片空濛。
上古时代,人们只对眼前的溪流和田亩,至多还对远方障目的高山发生兴趣,他们用简单的符号记载了下来,这便是最早的地图。中国的文字是从象形符号发展而来,川字是流水,山字是三座山峰,田是分成小块的土地,这些古代的图形符号,或许就是最先在地图上标记的符号。
到了裴秀的时代,世界则广大得多,他以古时《禹贡》为依据,对山岳、湖泊、河道、高原、平原、坡地、沼泽、古代九州的范围以及当时十六州都作了核查,绘制了18幅《禹贡地域图》。而同样以《禹贡》为依据绘制的宋代《禹迹图》则涵盖了1278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他们的视野范围已经攘括海内,但这些以“计里画方”原则绘制的地图有个致命的缺陷,即测绘中心附近的相对准确,而离测绘中心越远则误差越大。误差产生的原因在于裴秀对于这个世界的错误认知:以为世界是平的。尽管张衡的“浑天说”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将这个世界描述成一个圆球,但绝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仍然固执地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扁平化的世界里。
裴秀的理论缺陷直到16世纪利玛窦来华才得到纠正。这位意在传教的意大利人,为了讨好官员与皇帝,尽情地展示着来自西方的“奇技*巧”,其中便有地图投影法,运用这种数学方法,可以将地球表面的曲面转换到地图的平面上而不发生误差。他还以西方的世界地图为蓝本,将东西方两个已知的世界汇编到同一地图上,这位“中国通”极为聪明地将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央,这幅图即是有名的《坤舆万国全图》。该图为我国首次刊行的世界地图,此后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一直沿袭这种布局格式。
这张世界地图带来的冲击像一记哑炮,空有声音,却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并没有激发士大夫知识分子探究外部世界的兴趣,或许他们甚至还陶醉于西方传教士制造的“中央帝国”的幻象之中。直到19世纪“蛮夷之邦”用真正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才有人开眼看世界。而世界早在300年前就以一种更为温和的形式呈现过,只不过当时的士大夫集体选择性失明,这不能不令人遗憾。如果地图不能引领人们去探寻未知,那么再精确的地图也只是画地为牢而已。
古籍中的昆仑山就是现在的昆仑山脉吗?昆仑山只有一处还是有几处?昆仑山究竟在何地?昆仑这个区域实在是太神秘了,以至它的确切位置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为此,歧说纷出,聚讼不断。
在《山海经》和《淮南子》中,昆仑山是黄河的源头,盛产玉石。因此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联系黄河源头来确定昆仑山的位置,并以出产玉石作为旁证。
最早确定昆仑山位置的是汉武帝。张骞“凿空”西域,了解到一些西北地理知识,回来报告黄河源头就在于阗(即今新疆和田附近),但他以为昆仑山还应在更西边的地方。以后汉武帝不断派使者到西域各国。《史记。大宛列传》说:“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于是,武帝断然拍板定案:昆仑即于阗的南山。此说一出和者甚众。我们今天地图上的“昆仑山脉”便由此得名。
但是,历代地理学者们对这个说法并不以为然,只是因为有了这一说,必要时姑且沿用而已。与武帝同时代的司马迁就认为于阗南山够不上高峻美丽的条件,不是昆仑山。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对于阗南山也仍叫南山,绝口不提汉武帝说的“昆仑”两字。后来有的学者则认为于阗并不是黄河的源头,从昆仑和黄河的联系上排斥了武帝的昆仑说。
《山海经》曾提到“海内昆仑之虚”。为《山海经》作注的东晋郭璞就此指出:“言海内者,明海外复有昆仑。”清朝的郝懿行在注《山海经》时继承了郭的说法,提出有大昆仑和小昆仑之分。由于古籍记载的问题,又由于对黄河源头看法的不一致,很自然地,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就有了几处昆仑山。
清人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一书中总计前人诸说,指出昆仑山共有七处:“一在海外,一在西宁,一在肃州,一、在新疆,一在青海西南,一在卫藏之北,一在北印度。”近几十年来,学者们渐渐趋向昆仑一元说。但是说法仍然不一。
岑仲勉针对陶保廉的统计,通过考订,得出结论:“海外、新疆、卫藏及北印之四昆仑,皆即古昆仑。非名称如一,地点亦未有异。西宁、肃州两昆仑者、古昆仑之东支,……唯青海之昆仑、则因真河源发现而层化。由是言之,昆仑之广义,实一元也。”岑认为古代昆仑是泛指现在的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以及青海地区的一些山脉。
吕思勉综合《禹贡》、《说文解字》、《十六国春秋》等资料,指出汉武帝之前人们以为的黄河源头是在今札陵泊、鄂陵泊处,昆仑山应是酒泉的南山(也就是在个祁连山附近)。至于把于阗当作河源并以此来确定昆仑山,那是汉武帝时君臣们的“自误”。
顾颉刚则以为在《山海经)中昆仑山只有一处。他说:“许多人不了解《山海经》有整体性,受了它分篇的名词的蒙蔽,以为在图和经里,这几个昆仑山不在一处,便说‘海内昆仑’怎样,‘海外昆仑’怎样,这是大误。”并指出昆仑山和黄河源头“可以不发生必然的连带关系”,但他也没确定昆仑山究在何处。
他说昆仑山或在甘肃,或在青海,或在新疆,三处都有点像,但又不完全像。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从神话传说的传播这个角度试图解释这一现象。古籍中记载的昆仑山究竟在何地,时至今日未有定论。或许昆仑山和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使我们不能指出它的确切位置。因此,昆仑山位置的千古之谜,看来要结合神话学等学科才能有一个较为完满的解答。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部,2008年3月1日公布;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个)名单,现予公布。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和利用好珍贵文献典籍,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公布为契机,加强科学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使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献典籍永泽后世。 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51个) 国家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省大连图书馆 黑龙江省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江苏省苏州图书馆 江苏省常熟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 安徽省图书馆 福建省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 湖北省武汉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 云南省图书馆 山东省青岛市图书馆 河南省图书馆 湖北省图书馆 贵州省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 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上海博物馆 山西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 河南大学图书馆 河南大学图书馆 苏州大学图书馆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516部,2013年3月8日公布。
国务院正式公布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上海图书馆藏北宋拓本《三藏圣教序》、徐州市图书馆藏南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青岛市博物馆藏清蒲松龄《鹤轩笔札》稿本等1516部古籍入选该名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浙江省西泠印社、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等16家单位成为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汉文古籍1218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286部,其他文字古籍9部,3种甲骨文。这是甲骨文首次进入《名录》。《名录》收录宋元拓本71种,明清稿本76部、抄本177部;收录舆图43种,其中,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地图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纸质地图,也是世界上最早用于书写的纸张实物,还是西汉初即已发明造纸术的有力证明;收录的民族文字古籍,涵盖藏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布依文等12种民族文字。
其中,西藏博物馆藏元刻本《释量论》,是继元刻《因明正解藏论》之后发现的第二部元刻本藏文古籍。这两部元刻本的发现,推翻了元代无刊印藏文文献和明代以前无藏文印刷实物的旧说。
在此次公布的16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中国嵩山少林寺、西藏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西藏自治区罗布林卡、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等5家为宗教、少数民族单位。
截至目前,共有11375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66家单位成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本文2023-08-19 16:01:04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566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