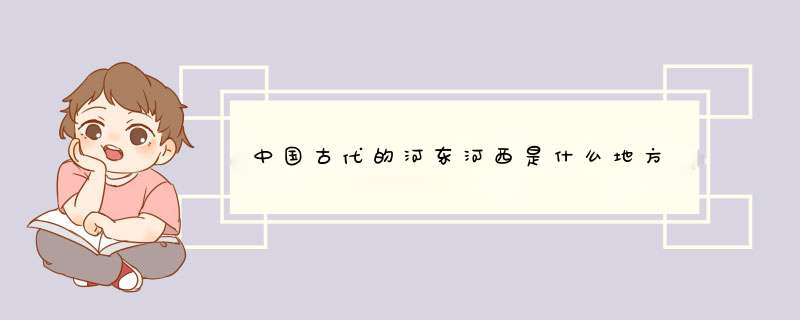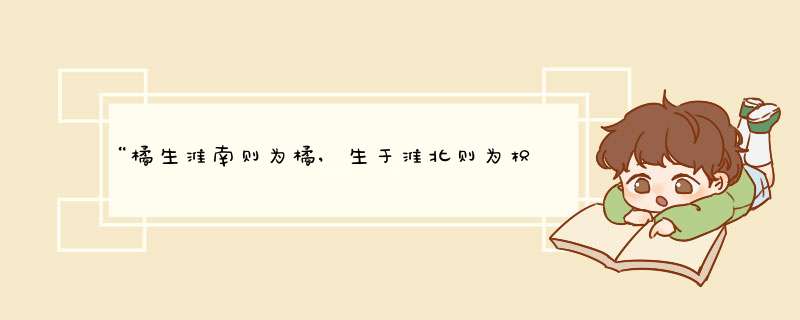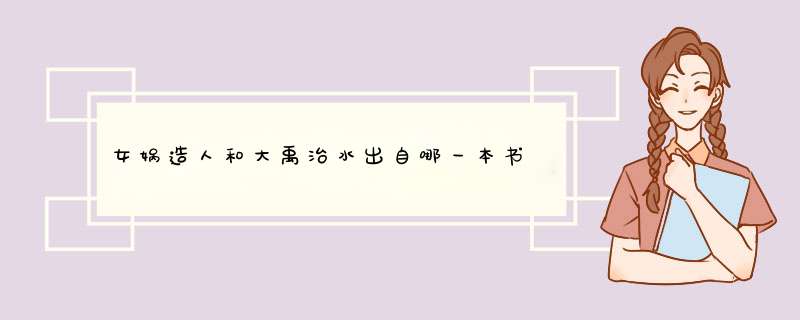贺绍俊《《淮水谣》,乡土文学的新开拓》

曹多勇是一位很有个性和特点的作家,他的写作极富有探索精神,同时又扎根于现实坚实的土壤。多年来,以家乡大河湾村为文学创作源头,曹多勇写出了一大批覆盖长中短篇体制的优秀小说作品。可以说曹多勇是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乡土文学的优秀代表。他生长在淮河流过的地方,他说过,淮河是他的母亲河。曹多勇热爱家乡、热爱土地、热爱淮河,这种爱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很突出。他在访谈中说,自己的作品有两类:一类写“历史”,一类写“当下”。写历史基本就是童年记忆,而写“当下”的作品同样也能看出记忆对他的影响。他的这些记忆其实都是关于淮河的记忆。他是在夯实乡土记忆的基础上,来写当下的乡土和生活,有厚厚的记忆底色。《淮水谣》就突出体现了曹多勇的这个特点。正如他在小说的后记里写的那样,这也是一本关于记忆的书。让人感到惊喜的是,作为乡土文学的《淮水谣》,既有着他小说固有的精神与特色,同时,又有着新的可贵的创新与探索,可以说是乡土文学在新时期的富有开拓意义和价值的优秀文本。
首先,《淮水谣》的结构极具艺术创新意味。刚接触《淮水谣》的读者,一开始可能会以为其结构比较老套,因为它是以小说中的十个人物为章节来结构小说的。猛一看,一个个人物像素描、特写、拼盘一样拼成了乡村图景。其实细心读进去,就发现不是这样的,这是一种凝结了作者深刻想法的结构。当然,这个结构并不是现代结构,从形态上说《淮水谣》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然而,尽管传统,却新意十足。曹多勇的《淮水谣》结构表面上看是一个形式问题,往深里追究,它与内容密切相关。如果只是为结构而结构,那它可能是纯粹的形式问题。但假如小说结构是作家在观察和剖析写作对象的过程中生发出的,这就不仅仅是个形式问题了。《淮水谣》的结构就是在观察和剖析写作对象中生发出的结构,是作家对小说总体精神与思想,经过深入思考和高度把握的结果,它反映着作家对小说中人物、命运、环境,甚至血脉与精神文化传统的精深考察与透彻领会。《淮水谣》写的是淮河边上的一个乡村家庭,先从第一辈的父母写起,再写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小女儿,然后辐射到儿媳、女婿等。我把它叫作从伦理上进行结构的小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结构是根系形态的,主人公韩立海、吴水月夫妇是根,从他们那儿发散开来。表面看来,是十个人物各自登场,各奔前程。而在更深层次,却是由近而远,由表及里,是一脉相承的,是血气相通的。这样的结构形式,形散而神不散,它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在变化无穷的人生舞台上,在各自命运的展开里,始终连接着韩立海、吴水月这根精神主脉,他们的命运遭际与生存轨迹,若隐若现地发散着来自乡土深处的人文气场、精神氤氲与风俗神韵。在曹多勇的《淮水谣》里,小说的结构就是这样与小说的内在肌理有着骨肉相连的关系,这样的独特结构就像是小说的骨架与筋脉,将小说的肉与血支撑起来,生动起来,丰满起来。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淮水谣》的主题内涵就包含了很多新的东西,是有着新的开拓的。但是他的这种“新”又藏得很深,有时候粗读可能没有发现。这里,只着重说一点,《淮水谣》其实写了一个普遍的观点——在乡村的人都想离开乡村。小说主要情节是写韩立海四个儿女包括韩立海自己其实都想离开乡村。小说每一章都写他们是怎么离开乡村的。小说最开始韩立海也是想离开乡村的,他到煤矿去,他差点离开了,因为有了吴水月以及其他原因,他留下来了。其实,但凡对农村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农村人都想到城镇去,有些农村的孩子在企业工作很辛苦,虽然很辛苦,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回到乡村。可以说《淮水谣》真实地写了乡村人的这种普遍的愿望:向往更好的生活,有着强烈的离乡愿望。《淮水谣》的深刻与新颖在于,他在写从乡村出走,也就是在写一个逃离的主题的同时,还有一个始终表现的主题:恋乡。这就使得《淮水谣》笼罩着一股浓浓的乡愁。这种将逃离乡村和乡愁、乡恋放在一起的写法,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饶有意味的互文关系。也就是说,在《淮水谣》里,离乡情结与恋乡情结是乡愁的一体两面。而当这二者会合到一起时,乡愁主题不仅出奇地完美,更具有着新时代所独具的复杂况味,有着一种当代乡村人,甚至是所有当代人精神深处扯不清剪不断的纠结与困窘。正是在这一点上,曹多勇的思索有了新的开拓,他使得乡土小说在精神包蕴上大大地丰厚了,具有了传统乡土文学所不具备的丰富性、新颖性与深刻性。似乎我们在以前的乡村小说中,没看到这样一种表现方式。当然,有的作家也会写到农村人想办法离开乡村,他们要逃避乡村的苦难,但这类小说多半是从另外一种角度去反映现代化进程的,是写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挤压,写乡村文明的崩溃,这种写作思路蕴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城市文明肯定比乡村文明要先进,城市文明终究要取代乡村文明,现代化的进程必然走到这一步。而这个思路是以一种高亢的声调来遮盖逃离乡土那挽歌式的怀乡与离愁,这种历史目的论支配下的乡土叙事,其实是无形中赋予了逃离乡村甚至是抛弃乡村的某种历史合法性。而在曹多勇的《淮水谣》,则有着更为深邃的思考和更为前瞻性与历史深远性的探究。《淮水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切入乡村历史与现实的新思路:人与土地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追求更好生活的问题,脱离土地逃往城市,也不是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更不是农民的理想归宿。一句话,逃离与乡愁绝不单单是先进与落后的问题。今天人们为什么还留恋乡土,向往乡村?为什么会有浓浓的土地情结?这是因为土地造就了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方式背后的文化定势,这与先进、落后没有关系。单纯地局限在先进和落后二元对立模式上,有时候会走极端;从先进与落后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会走到这样一个死胡同。《淮水谣》不回避这一点。小说告诉人们,其实乡村的人知道什么生活更美好、更舒服。所以,《淮水谣》绝对不是写两代人的差异,也不是写先进与落后的问题。绝不是说韩立海和吴水月留恋乡土,韩立海的后辈才想去城市,不是要构成两代人之间的对立关系。想离开乡村是人之共性,小说在写出这种人之共性的同时,还写出了对乡土的爱,对乡土的怀念,对乡土的坚守。这里面其实是有更深层的原因。《淮水谣》正是这样写出了土地造就的一种文化、人格与人性,当这种文化不仅铸就了你的生活方式,更铸就了真实的独特的个体的人。这样的人就会留恋这种生活方式,留恋这种生活方式所赖以存在的土地与乡村,留恋其背后更为深邃、复杂与奇妙莫名的感受、记忆、情绪、身份认同、价值认同与生存体验认同。所以吴水月死了都要葬在大河湾村,而韩立海那么穷都要养猪,使劲把孩子送往城市,但是他还留恋土地,留恋土地是因为他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他的文化性格。所以当孩子说把吴水月的坟迁到公墓里时,韩立海不同意,因为只有吴水月葬在这里,全家一年才能聚在一起。小说在这个层面上,又将对乡土的怀念与坚守与“家”联系起来,这就深深地触及中国人精神深处的“根”。差不多百年前,民国的那些乡土建设派就意识到:“盖中国民族,立国于亚洲大陆,自有历史以来,已四千余年,资以维持发展,历久不衰朽,几无一不家族是赖。”如此,我们说《淮水谣》里的一个个人物,最后其实塑造的是一个完整的形象,这个完整的形象就是“家”,它表达了曹多勇对“家”的理解,也表达了他对“家”的忧思。家,这个中国社会、乡土文化中最基本的元素,这个中华民族精神与魂灵的居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其凝聚力在销蚀,有着风雨飘摇的落寞感和荒凉感。而没有家或者远离家园的人是多么凄惶、迷惘与漂浮!《淮水谣》背后传达的就是这样一种忧思。这是一种源自血脉与骨髓深处的忧思,是发自“根”的期盼与召唤,是乡土中国数千年情绪记忆与精神积淀的苏醒、感应与喟叹。所以,我们说《淮水谣》在乡土叙事上有创新,不仅仅表现在形式上,也表现在思想主题上。
《淮水谣》作为乡土文学的富有开拓性的作品,之所以如此扎实而厚重,是源自曹多勇对淮河的深厚感情,更是源自他多年来潜心乡土文学的创作。几十年来,曹多勇写淮河的小说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很可观。可以这样说,曹多勇的小说创作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独有风格与特质。我以为曹多勇的乡土文学创作,堪称安徽乡土叙事的标示性文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以曹多勇为代表的安徽小说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乡土文学流派——皖派乡土文学?讲到乡土叙事,首先会想到陕西,陕西的确是很强大的,但安徽的乡土文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与独特的美学价值。陕西是在黄土高原上形成的乡土叙事,用一个“厚”字形容,就像厚厚的土,一吹就会扬起尘土。这种“厚”可能还和陕西乡土叙事中生存的艰难,生命主体常常是匍匐在黄土地上有关。但我读曹多勇的小说,我就要用“绵”来概括,绵软的绵,它有一种水的滋润,却又有水的韧性与执着。以曹多勇为代表的安徽乡土叙事里的生存也有艰难,但人与土地的关系是友好的。生命主体在安徽大地上往往是坚韧地顽强而乐观地抗争着的,是始终满怀希望的,是直立在土地上的。像《淮水谣》,显然也是一种现实主义传统。讨论现实主义传统时,我们会从各个方面去讨论,但《淮水谣》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用积极、乐观的姿态去面对乡村、面对叙事对象。这是中国现实主义传统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中国现实主义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的风雅颂。但后来我们谈现实主义传统,却只谈《诗经》中的风,好像风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传统,其实应该把三者看作统一体。风,是土风歌谣,来自民间,曹多勇的《淮水谣》就是谣,就是来自民间真实而苍凉的歌唱。同时,曹多勇的小说又是扎根于淮河大地的,写出了淮河人家真实的生存,写出了淮河养育的人们精神上的坚韧与倔强,本分与善良,深情与质朴……正是从曹多勇的小说里,人们开始真正接触和认识到,为一条伟大河流——淮河养育的人们是怎样在历史与现实中生存的,他们的生存又体现出怎样的精神与气质、性格与情怀、精彩与苦难、沉沦与梦想……还是著名评论家刘颋说得好,她说“曹多勇以他的小说绘制了一幅淮河文学基因图谱”。可以说,曹多勇的《淮水谣》是乡土文学的新开拓,也是为安徽的乡土文学做了开拓性与奠基性的工作。而这样的开拓性与奠基性的文学书写,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与深入研究。
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生卒年代不详,大约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属于同时代而略晚。孙子是齐国贵族和名将的后裔。他的祖先原是陈国的公子--陈完。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完便逃奔至齐国避难,改称为田完。田完的第五世孙田书(即孙子的祖父)曾经是齐国大夫,在攻打莒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战攻,齐景公便把乐安封给了田书,同时还赐“孙”为姓,以表示对田书嘉奖。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内乱,孙子便离开齐国,到了南方的吴国,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过起了隐居生活,潜心研究兵法。在吴国,孙子结识了伍子胥。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在诸候争霸中,南方新兴的吴国国君阖闾,为图霸业,欲攻打楚国,但是,一时难以选出合适的将领。伍子胥常与吴王论兵,他曾向吴王推荐说:孙子“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诚得此任为将,虽天下莫敌,何论楚哉!”经过伍子胥七次向吴王推荐,吴王便让伍子胥拜请孙子出山。
孙子晋见吴王之后,呈上所著兵书十三篇。吴王看后,赞不绝口。据有关资料记载,为考察孙子的统兵能力,吴王挑选了100多名宫女由孙子操练。这就是人们所传说的孙子“吴宫教战斩美姬”的故事。吴宫操练之后,吴王任命孙子为上将军,封为军师。从此,孙子与伍子胥共同辅佐吴王,安邦治国,发展军力。公元前506年冬,吴国以孙子、伍子胥为将,出兵伐楚。孙子采取“迂回奔袭、出奇制胜”的战法,溯淮河西上,从淮河平原越过大别山,长驱深入楚境千里,直奔汉水,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重创楚军。接着五战五胜,一举攻陷楚国国都郢。“柏举之战”后,楚国元气大伤,渐渐走向衰落,而吴国的声威则大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吴国不仅成为南方的强国,而且北方的齐、晋等大国也畏惧吴国。对于孙子的历史功绩,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写道:“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候,孙子与有力也”。
淮河以南适宜种植水稻,以北适宜种植小麦,以南是常绿阔叶林,以北是落叶阔叶林,以南降水多,适宜建设坡度较大的砖瓦房,以北适宜建设坡度较小的泥土房,选项BC叙述错误,不符合题意.
故选:A.
汴河,古称汳水。《水经》载“汳水出阴沟于浚仪县(今开封城西北)北”。郦道元《水经注》说“阴沟即蒗荡渠也”。汴河大致从今河南省开封城西北,向东南流经陈留、杞县东、宁陵县北、商丘、虞城县西南、安徽省砀山县、萧县,至今徐州市区东北汇入泗河。王国维《水经注校》提到留获渠和获水,实际与汴(汳)河是一条河流。因为,汴水经考城县称留获渠。
汴、泗合流,穿过徐州市区继续东南有沂、沭两河在其北侧相继汇入。沂河发源于今山东省沂源鲁山一带山区,大体南流,经今江苏省邳州市,至睢宁县古邳镇汇入泗河。沭河发源于今山东省沂水县北部山区,与沂河平行南流,至江苏省宿迁市西北处汇入泗河。泗河继续东南,在下相县故城东(今宿迁市城西南约七华里)接纳濉河至淮阴县汇入淮河。
隋统一中国,结束了东汉以来四百年的分裂局面。隋炀帝将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开挖了通济渠和永济渠,西通关中,南至江淮。
通济渠,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为了避开徐州、吕梁二洪之险,采取走宿州直接入淮的线路,即在今杞县以西与汴河分出一支折向东南,经商丘、永城、宿县、灵壁,至盱眙北入淮河。这支撇开徐州间的汴、泗运河径直入淮的河道,就是唐、宋时期的新汴河,亦称南汴河。但在此时成为汴河故道的汴、泗运河并未完全中断,因为,鲁、徐、淮、海一带,“水陆肥沃”,是漕粮主要筹集地。仍有舟楫通行要求。唐高宗武德七年(624年),即令尉迟敬德导汶、泗至任城(济宁)分水,建会源闸,治徐州、吕梁二洪,以通饷道。韩愈:“汴泗交流郡城角”和白居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就是对当时汴、泗两河在徐州汇流的真实写照。
五代后晋时,迁都汴京,曾“开济州金乡来水,西受汴水,北抵济河,南通徐沛”。周世宗时,形势大体稳定。显德二年(959年),以汴渠日久湮废,“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发民夫,因汴水故堤疏导之,东至泗上”。六年二月,命侍卫都指挥使韩通“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水”。至此,江、淮、河、汴舟楫复通。同治《徐州府志》载:“由淮入泗,由泗入汴者,此五代末之运道也”。
《淮系年表》记载了北宋仁宗庆历中(公元1045年前后),“浚任城、金乡之大义河,徐、沛之清河(泗水)以通漕”。又同治《徐州府志》载:“自宿、邳西溯泗流,经彭城又西接萧砀入归德(商丘)界,此宋至道前及熙宁间(公元1068至1077年间)之运道也”。北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对泗河航道上的徐州洪和吕梁洪,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即开月河、修筑石堤,上下两端置闸,设管理机构,按时启闭通船。公元1127年,宋室南迁,高宗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韦太后自金归,仍可“自东平舟行由清河(泗水)至楚州(淮安)”。这证明,虽然,从隋、唐、宋时期有了新汴河,但是,在徐州境内的汴河故道和泗河,做为运河的航道中断时间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
汴河成为通济渠的代称。按《宋史·河渠志》载:“汴河,自隋大业(605—618年)初疏通济渠,引黄河通淮,至唐改名广济。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阴县南为汴首,受黄河之口属于淮泗,每岁自春至冬,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重载为准,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故于诸水,莫此为重。” 汴河从汴京外城西水门入城,再入内城水门,横穿宫城前州桥、相国寺桥,出内城水门,然后向东南而出外城东水门。淳化二年(990年)六月,汴河在近城浚仪县的一段河堤缺了口,宋太宗赵光义亲自去视察,步辇行走在泥淖中,宰相、枢密院使等大臣连忙劝阻回驾,宋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于是下令调步卒数千来堵塞,直至看到缺口被塞住,水势稳定后,他才回宫。由此可见,汴河不但是当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且还是国家安全的系带,可以说是赵家王朝的生命线。
以下是举世瞩目的名画《清明上河图》相关描述文章中描写汴河喧闹、繁华的细节:
进入汴河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两艘重载的大船已经靠岸,正在往码头上卸货。从船身还吃水很深来看,被卸下的货物只是很小一部分。货物是用麻袋装的,老板正坐在麻袋上指挥工人们码放。扛袋的工人很吃劲,需要两个人帮他卸下,看来装的是粮食。北宋时代,属于国家的粮食储备仓库,大都集中在东南城沿汴河一带。《东京梦华录》“外诸司”记载:“诸米麦等,自州东虹桥元丰仓、顺城仓,东水门里广济、里河折中、外河折中、富国、广盈、万盈、永丰、济远等仓。”这些仓库的粮食,都是通过汴河从“江淮湖浙”运来的。粮食是一个物质需要,汴河又担负着运输粮食的重要任务,在图中我们第一眼就看到运粮船,这是毫不奇怪的。也可能是画家特意的安排,因为别的船只都遮盖着,只有在卸货过程中看它的包装形式才能了解是什么货物。
这个船码头正对着一条街道口。这是入城的第一条街,是沿着河岸走向的,可以叫“沿河街”或“沿河大道”,主要店铺是餐馆,以小吃为多。这很符合逻辑,因为它靠近码头,主要服务对象是刚入城的客人和一些苦力。如对街有一家小店,门前笼屉里摆着馒头,店主手持一个正在向挑夫兜揽生意。与之右邻的是一家小酒店。再过去的一家,铺面比较宽广,店前当路堆着纸盒类货物,路口竖着一块招牌,上书“王家纸马”。这是家专营纸人、纸马、纸扎楼阁和冥钱的铺子。按《东京梦华录》的记载:“清明节……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成楼阁之状。”画家在这个出城的路口画上纸马铺,除了与前面扫墓的队伍遥相呼应之外,同时又再一次点醒题目是“清明节”。
接下是一个大码头,街道宽阔平整,两边店铺也较为讲究,经营的主要是餐饮业,店铺里已经坐了不少客人。码头边一连停靠了五艘大航船。有一艘还在卸货,从伙计们爬在船篷上聊天来看,货物已卸得差不多了。有的船主卸完货以后,则邀客人到沿河酒店去喝上二两。沿河酒店的雅座,都向着河面敞开窗户,客人一边喝酒,一边可欣赏风景。在这一组航船中有一艘装潢特别华丽,清一色的花格窗子,前后有两个门楼,船舷也比较宽。透过窗子,可以看到舱内有餐桌之类的家具,知道这是一艘大客船,不但有舒适的客舱,而且还可以在船上用餐。船主可能上岸去了,留下四个伙计在忙活着收拾,等待着客人们到来。
在这一组船只外面,是一艘正在行进的大船。有五个人在岸上拉纤,船上可以看到有十一个人物。这是一艘客货混装的大船,因为它的船窗板中间与两头是不同的。前后舱的窗门是向里支开的,中间舱则向外支开。看来其货物除了装在底舱之外,中间的上层舱也堆放货物,所以这艘船载重量也很大。正由于货多船重,又行进在船舶密集的河道上,所以船主和船工们都很紧张。右舷上的三个船工,正轮流用篙将船往外推移,以免与停泊的船只碰撞,站在左舷和船头上的两个船工,手中紧握篙杆,准备随时使用,而船老大则在船头指挥,似在大声叫喊,提醒前面船上人注意。另外有三个是搭船的客人,第一个站在蓬顶的前部,在身后有一张小桌,放着杯盘之属,可能是他正喝着酒,看到前面有些紧张,便站起身来帮着叫喊;第二个在船尾敞棚里,背着双手,踱着方步,心情像是很急迫,也许他还嫌船走得慢哩;第三个在尾舱内露出大半个身子,快要到岸了,他是想出来看看。在船的前舱内,一个妇女带着小孩趴在窗口往外看,应当是船主的家眷,全船最没事的就是他们俩了。十一个人,各不重复,松紧张驰,各尽其态。画家对生活的熟悉和观察入微,我们不能不佩服。
这条船是在逆水而上,使我们知道是在汴河的西南岸。近岸边有一只小艇,船夫正在往外掏水。一艘大船刚从它身边驶过,大橹拨动的漩涡,一个一个向它袭来,使小艇的船身仿佛在晃动。大船是一艘有着双橹的载重船,船尾八个船工在使劲地摇着大橹。船头也有八个船工,只是被一棵大柳树把他们和船身遮挡住了,别以为画家在这里偷懒,省去画船上的各种细节的工夫,他是要让我们的眼睛稍事休息一下,因为后面还有更热闹的场面等着呢!
您好,您是想问江淮河汉指的是什么吗?江淮河汉指的是长江、淮河、黄河、汉水。
1、长江。属太平洋水系,是中国第一大河,长江干流自西而东横贯中国中部,数百条支流辐辏南北。
2、淮河。古称淮水,与长江、黄河、济水并称“四渎”,当代已被列为我国七大江河之一。淮河发源于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桐柏山太白顶西北侧河谷,干流流经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于江苏省扬州市三江营入江,流域地跨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五省。
3、黄河。是位于中国北方地区的大河,属世界长河之一,中国第二长河(也有称第二大河流)。黄河之“黄”,实为泥沙。古籍有载:“黄河斗水,泥居其七”。黄河泥沙九成来自黄土高原,黄土高原土质疏松,易蚀易散,每逢暴雨冲刷,则流失大量水土,奔入黄河。
4、汉水。汉江,又称汉水,汉江河,为长江最大的一条支流,现代水文认为有三源:中源漾水、北源沮水、南源玉带河,均在秦岭南麓陕西宁强县境内,流经沔县(现勉县)称沔水,东流至汉中始称汉水;自安康至丹江口段古称沧浪水,襄阳以下别名襄江、襄水。战国·邹·孟轲《孟子·滕文公》:“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
什么是淮河?这个问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答案。
在蒙昧初开的上古时期,人们认为淮河是由创世大神盘古的血液所化,与长江、黄河、济水同列“四渎”,是中华大地上最重要的四条大河之一。秦汉时,四渎各有祠庙供奉,帝王们祭祀名山大川时,淮河榜上有名。隋唐以降,将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和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在一起的京杭大运河横空出世,淮河作为衔接南北的重要通道,见证了无数繁华起落。
宋室南迁后,淮河成为宋金对峙的前线,诗人杨万里在《初入淮河四绝句》中写道:“……长淮咫尺分南北,泪湿秋风欲怨谁?两岸舟船各背驰,波浪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淮河以北成了回不去的故乡,也成了南渡士民心中的永痛。南宋中期,黄河决堤,滔滔黄水南下夺淮,巨量的黄河泥沙迅速淤塞了淮河河道,淮水漫溢,洪灾频繁,沿淮百姓犹如头悬水盆,800年间仓皇度日。
如今,鲜有人再提起淮河的洪灾,只有老一代人回忆属于他们的那个火热年代—出山店、王家坝、临淮岗、蚌埠闸……一座座水利工程驯服了肆虐的洪水。如今的淮河,又是什么样子?
苍翠桐柏山,神秘淮河源
桐柏山是秦岭大别山过渡带上的一段山峦,最高峰太白顶海拔1140米,这座并不算十分雄伟的山峰,却因坐落在豫鄂交界处而有了北视中原、南阅楚天的英姿。
云雾缭绕的山顶处,袅袅梵音不时从古老的云台禅寺中传出。寺院前后各有一口井,长年不枯,分别被称作大淮井和小淮井,它们是整个淮河流域的最高水位点,历来被视为淮河的源头。
走进桐柏山,游人会被郁郁葱葱的山林所迷醉,频频触动人心的,还有山中随处可见的飞瀑流泉。晶莹的溪水从岩壁上跌落,穿过巨石与枯木,在花草丛中时隐时现,潺潺不息。如果把溪流比作孩子,那么桐柏山的身上,就挂满了无数淘气的精灵。
明嘉靖年间,失意才子吴承恩曾到访桐柏山,他行至山脚下的水帘寺前,虔诚一拜,后循小路绕到寺庙后的山崖,只见一条白净如练的瀑布飘然高悬,宛若白龙吸水,洁净而蓬勃。瀑布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山洞,攀缘而上,可进入洞中,洞府与寺庙以水帘相隔,亦如世外天地。当地传说水妖巫支祁曾与大禹激战于此,最终被大禹制服,并被用铁链镇压在淮河之底。此地的风景和传说成为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灵感之源。后人推测,桐柏山的水帘洞是《西游记》中花果山水帘洞的原型,被大禹镇压在淮河底的水妖也正是被佛祖镇压在五指山下的石猴原型。
《西游记》是这样开篇的:“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而桐柏山也恰是著名的盘古之乡,古籍中记载:“盘古开天地,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河,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由此,作为淮河之源的桐柏山便和盘古关联起来。甚至当地人相信盘古开天辟地之后,最初站的位置就在桐柏山。桐柏山上有很多纪念盘古的遗迹,山下的城镇与村落里也广泛流传着与盘古相关的民俗与祭祀活动,这在其他地区是不常见的。
鲜为人知的淮河三峡
淮河出桐柏山,就进入了坦荡的华北平原,一路沉稳东去,出河南,过安徽,最终从江苏注入黄海,弯弯绕绕1000公里,却始终平淡无奇,鲜有急流险滩,所以稍有些波澜的地方,都会格外引人注意。
淮河三峡虽也有“三峡”名号,却和长江三峡的雄奇壮丽相去甚远。安徽淮南的八公山是淮河流出源区后穿过的第一座山,位于西侧山尾的硖山峡因此被誉为“千里淮河第一峡”。我身临其境却很难把它同峡谷联系起来—东西两岸只是两座浑圆的山丘,既不险要,亦无纵深,视觉上看更像是一座卡在河道上的石门。
蚌埠的荆涂山是淮河穿过的第二、三座山。荆涂二山相隔仅有600多米,淮水自南而北来,迎头撞上荆山,便连折两道大弯,从两山之间的夹缝中穿过,这就形成了淮河第二峡—荆山峡。比之于硖山峡,荆山峡在气势上要更胜一筹,我置身其中,感受到几分高山峻峡的压迫感。
第三峡浮山峡位于安徽与江苏的交界处。浮山只是一座矮小的赭红色山坡,紧邻淮河南岸,但河北岸却并没有一座与之相对的山峰,之所以称之为“峡”,大概是因为河道在山脚骤然收窄,船行至此犹如穿峡而过。
淮河三峡在景观上并不出众,但与之相关的 历史 和传说却不胜枚举。在尧舜时代,硖山峡狭窄闭塞,常因行洪不畅而洪水四溢,沿岸百姓叫苦不迭。大禹导淮时带领民众开山劈石,疏通峡口,大大缓解了洪涝之患。4000多年后的1991年,硖山峡又经人工拓宽了200多米。如今,只有河心孤岛上古老的禹王庙,默默诉说着曾经的险隘与洪涝。
和硖山峡类似,荆山峡最初也很窄,经大禹和后人的数次开拓后,才呈现出如今的样子。但荆山峡的故事更丰富,因为大禹在治水之外,还在这里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并召集天下诸侯会盟,奠定了夏王朝的根基。“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也发生在这里。涂山上有一块酷似人形的天然山石,临崖独立,遥望淮河,当地人说那就是大禹的妻子幻化而成的望夫石。
浮山峡给人最深刻的印记却是一段血泪史。北魏时,南朝梁武帝曾在此筑堰拦淮,欲以水代兵,击败魏军。然而,阻断大河并非易事,隆冬饥寒、盛夏疫病夺去了20多万役夫的生命。当高堰筑成时,上游150公里全被大水淹没;当年秋天,此堰被猛涨的河水冲垮,洪峰如雷,冲向下游的村落,无数百姓被洪水淹没。无辜百姓为梁武帝的倒行逆施付出了惨重代价。
人文荟萃的淮上故城
淮河不算太长,从河南桐柏山的太白顶开始,到江苏盐城的扁担港入海,干流总长度在1000公里左右,不及黄河的五分之一、长江的六分之一。但这1000公里的干流河面,犹如一条清晰的界线,把中国东部大陆划分出了地理意义上的南方和北方。
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就意识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暖温带与亚热带气候在淮河两岸各自展开,生发出绝然不同的农业生态和风格相异的民风民俗。介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淮河流域,因为南北文化的交织互融,自然成为中国思潮最活跃、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这片土地曾诞生过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一批奠定中华文化的思想家,也哺育过管仲、李斯、刘邦、曹操、朱元璋、周恩来等一批影响中国 历史 走向的实干家。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在没有洪涝灾害的时代,富庶的沿淮地区是人人向往的鱼米之乡。而在朝代更迭或南北对峙的时期,淮河一线又是冲突和战争最为频繁的区域。 历史 的浪潮在淮河两岸来回翻涌,催生出许多各领风华的天下名城。
河南信阳是淮河流经的第一座地级市,素有“淮河第一城”之称。美丽的浉河穿城而过,给这座城市点缀了几分灵动。城西有一座水域广阔的人工湖,湖畔的低山丘陵正是名茶信阳毛尖的主产地,青翠圆润的茶树林犹如毛茸茸的绿地毯,一眼望去绵延无尽。这里曾经是中原、荆楚和吴越文化交会之处,周天子在这一带设置了众多诸侯国。今天,不少诸侯国的痕迹依然可循,信阳境内沿着淮河可找到申国、息国、赖国、黄国、蒋国的故城遗址,这些古国后来慢慢演变成了众多中华姓氏的起源地,所以信阳还有“中原侨乡”之称。
安徽寿县古称“寿春”,坐落在八公山下,西邻淮河,北接淝水,是控扼南北的兵家形胜。寿春本是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的封地,后秦军攻楚时,楚王一路东遁,春申君就把此地献给楚王做国都,但楚国仅在这里延续了18年便被秦国攻灭。随后的 历史 中,寿春凭借襟山带水的地势又做了两次国都、10次郡治,无数风云往事在这里上演,大量文化遗存沉积于此,使其成为中国成语典故之乡和安徽省的文物宝库。寿春最为瞩目的文物是四面合围、高大坚固的城墙。这座城墙始建于宋,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防体系之一。墙高97米,底宽近20米,周长71公里,城开四门,四门各有瓮城,城北东西两隅巧妙设置了用以防洪排涝的泄水涵闸和月坝。千百年来,寿春城墙不仅承担着抵御来犯之敌的重任,也要拦截频繁袭扰的淮河洪水。正因如此,这座城墙才留存至今。从城门中缓步穿过,光滑如玉的青石板在脚下低吟着古城的沧桑。青檐古塔下,庙堂廊院中,居民们平凡朴素的烟火人生和络绎不绝的新鲜游客们和谐交融,而那些重见天日的金石器物则躺在博物馆的橱窗里熠熠闪光……
江苏淮安是周恩来总理的故乡,也是军事天才韩信和文学大师吴承恩的出生地。主城区位处京杭大运河与淮河的交汇处,明清时期曾与苏州、杭州、扬州并列运河四大都会。蓬勃数百年的漕运不仅带来了堆积如山的货物和川流不息的商旅,也带来了胜似江南的繁华富丽。“运河三千里,最忆清江浦”,清江浦是淮安里运河上的一个埠口商镇。在运河时代,这里是长江以北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有“九省通衢”之美誉,舳舫蔽水,市井稠密,亭台楼阁和园林酒肆鳞次栉比。而今,清江浦和里运河都已归于平静。为适应大型船舶的通航需求,人们在里运河以西开挖了新的河道,新运河从林立的高楼间穿过,宽阔的河面上依旧是百舸争流的繁忙景象,而古老的里运河则深藏功与名,摇身一变,成了美丽的城市景观。沿着里运河寻访,可依次观览屹立千年的镇淮楼、掌管天下漕运的漕运总督府和英才辈出的河下古镇,感受淮安最风光的那段记忆。
淮水入海,大河安澜
早在约2600年前的春秋时期,沿淮一带就出现了令人赞叹的水利工程—楚相孙叔敖主持修筑的大业陂和芍陂(在今天的霍邱和寿县),并一直被沿用至今。故而在相当长的 历史 时期中,淮河流域都是丰饶的天下粮仓,但这一切在1194年黄河决堤后戛然而止。
黄河的侵入,造成了淮河水系的全面紊乱,日益淤高的河床使上游来水难以宣泄,这些本该东流入海的河水逐渐汇聚在盱眙东部的平原,并将原有的大小水泽串联成片,广袤的洪泽湖由此而生。明代时,为保漕运畅通,又在洪泽湖以东筑起百里长堤,以蓄积湖水冲刷运河中的淤泥。堤坝越修越高,洪泽湖最终成了一座随时都有可能溃决的悬湖。1855年黄河北归后,洪泽湖以下的河道随之被淤废,淮河彻底失去入海通道,只能借长江入海。河道无法有效行洪,淮河也沦为一条灾害频发的祸河。据不完全统计,从1194年到1949年的755年间,淮河流域共发生316次规模较大的洪灾,平均每24年发生一次。每次洪水来袭,数千万亩耕地被淹没,无数城镇村庄被浊浪吞没,成千上万人沉溺水底……
1950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同时实施了两个重大举措,其一是抗美援朝,其二便是治理淮河。在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沿淮百姓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治淮事业中,经过近七十载的努力,共建成水库6300余座,堤防63万公里,水闸22万座,行蓄洪区27处,塘坝、机井、引水灌渠不计其数,淮河由此成为中国第一条被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
今天,当游人漫步在洪泽湖畔,一边是烟波浩渺的水面,一边是枝繁叶茂的防护林,敦实的大堤呈波浪状延展到天边,堤岸旁的村镇鲜花掩映,清净雅致,丝毫感受不到一点守着悬湖的忐忑。大堤东侧,3条人工河在辽阔的苏北平原上长驱并行,直通大海。黄河南下夺淮的800多年后,淮河终于又有了独属于自己的入海通道。淮水入海,大河安澜,这条古老河流的苦难史从此一去不返。
本文2023-08-20 23:39:49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614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