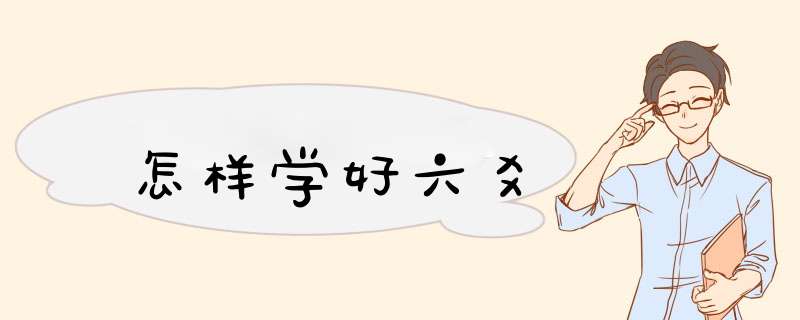中国古时候的书是从右往左竖排的,它是怎样演变为今天这个样子的?

我们现在的书写习惯与古代汉字竖排向左行的顺序是有极大差别的。其实,从古至今,世界各地各种文字的书写顺序是各有不同的,总体上分为左行、右行、下行三种,一直保留至今。左行如英文等;右行如阿拉伯文、希伯莱文等;下行如传统的蒙古文、中国古籍印刷、有时的日语等。
在中国古代,因为书写时是左手拿简,右手写字,一般是一根简一行字,并且为着左手拿简方便起见,空白的简是放在左边的。等到把一根简写完,写过的简为着和空白的简不相混,也就左手一根一根的向右边推去,并且排好。
在这种情形下排出的行款,总是写好的第一根简在最右,以次从右排到左,更由左手拿着的简是直立的,而一般人手执细长之物是与人指垂直的;于是中国字的行款,成为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了。
竹简与木牍是古代用于书写、记事的竹片和木片。简牍流行于东周至魏晋时期,可能在殷商时期就已出现。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是在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最晚则可延续到魏晋时期,而用少数民族文字如吐蕃文、西夏文等书写的简牍,在西北地区的唐宋墓葬中还有发现。
古代用竹简制成的书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官方的各种文书档案、私人信件、各种书籍抄件、历谱,以及专为随葬用的遣册等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是很珍贵的书法墨迹。对它们的发现和研究,是近代学术界的重要成果之一。
这些简都是每片简抄写一行字,所写的字数因简的长短而不等。另外还有一种简,宽约二厘米左右,每简上抄写两行字,这种简称为“两行”。竹简一般都是用丝纶或麻绳将零散的简编成册,是先编联,后书写,纶绳所过之处空而不写。
因为竹简与木牍制作繁复,而且书写字数有限、携带不便,所以缣帛成了秦汉时代的重要书写材料。用缣帛写成的书籍,称为帛书。后来,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简牍、帛书逐渐被废弃,纸最终成为书写的主流材质。
关于古籍结构的演变,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做过形象的比喻,“战国秦汉的古书像气体,种类和卷篇构成同后世差距很大;隋唐古书好像液体,虽然还不太稳定,但种类和构成渐趋统一;宋以后的古书则是固体,一切定型,变化多属誊写或翻刻之误”。 熊铁基在《刘向校书详析》说:后世流传乃至我们今日看到的西汉及其以前的古书,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是刘向他们校定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经过了他们的理解、认定乃至改造,当然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未得到充分认识,以为后世乃至今日所读的先秦古籍就是原来的样子,这就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得出与历史真实不符的结论。历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产生疑、辨,因而有指伪之作。从现存的《书录》及有关记载看,有的书完全是新编定的。如《列子书录》……可见刘向完全新编了一部《列子》书。
黄爱平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第八章《先秦至两汉:历史文献学的起源及奠基时期〈百家争鸣与诸子文献〉》中说:
先秦诸子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记载有“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而经过历史发展,尤其是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学说主导地位的确立,诸子思想被视为异端,其著作也大多湮没不传。流传至今的只有 20 余种,如《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文子》《列子》《尹文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
先秦诸子之书,初时多以篇行,如《韩非子》原有《孤愤》、《五蠹》等篇,后来才被集结成书,并以韩非的名字命名。并且,诸子之书的成书过程一般较为复杂,其著者一般习称自撰而成,但从其内容来考察,实际上有的是收集本派主要言论而成书,更多的是在师门传承过程中,由其后世弟子编辑而成。总之有可能是众手修成或者经过长时间的编纂、增补。正因为如此,诸子之书多传闻异辞、流传异本,有的还掺杂有他人的言论。这些都反映了早期文献的特点。
在中国学术史上,先秦是诸子百家争鸣、学术发展繁荣的黄金时代。各家代表人物以及诸多学人士子,或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或质疑辩难,既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发挥余地和想象空间。后人应该更好的保护与继承。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时代、地域,刻书者、刻版形体及印刷技术的不同,产生了许多型式各异的刻本。从时代上区别的有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民国刻本;因地域不同,有浙本(浙江地区刻本)、闽本(福建地区刻本,因以建宁府建安、建阳两县为中心,故又称建本)、蜀本(四川地区刻本)、平水本(山西平水刻本)等,具体又分为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等;按照书籍刻印的主体又分为官刻本(我国古代政府各机关雕版印行的书籍)、家刻本、坊刻本(指一般书商刻印的书),官刻本因所刻单位不同分监本、经厂本、藩府本、书院本以及各种名称的刻本,比如宋有崇文院本、秘书监本、茶盐司本、安抚使本、转运使本、仓台本、计台本、漕院本、公使库本、郡斋本、太医局本等。
坊刻和家刻都是私人刻书;从刻版形体上来区别的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黑口本、白口本、十行本、八行本、影刻本(又称影刊,其方法是先照原书影摹,然后在版上雕)、巾箱本(版本较小的古书,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策;因该书型特小可装在巾箱里,极便携带,故名)等;从印刷技术上区别的有写刻、朱墨印、几色套印等,因版印技术不同,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
因版刻印的早晚不同,有初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按书籍流通情况又有通行本、旧刻本、残本、善本、孤本等分别。刻本的出现和流通对保存、传播祖国文化遗产起了极大作用。
中国的古籍辨伪工作是伴随着文献研究工作的开展而产生的。早在战国时代,就有学者认识到,有必要在使用文献之前,对其立论、事实的真伪进行考辨。西汉末年,官府组织学者进行大规模的校理典籍工作,第一次全面地对当时所存文献中的依托和真伪掺杂现象进行了辨析在基本根据《七略》编成的《汉书·艺文志》中,有许多“依托”、“非古语”、“后世所加”之类的断语。此后历代学者对此都很关注,如东汉经学家马融在注《尚书》时曾遍考各篇的真伪;王充在《论衡》中系统地对当时一些经史要籍中记载的史实提出了质疑;隋代僧法经编纂的《众经目录》专立“辨伪”一门,著录在著者、内容和年代上有问题的经籍;唐代文学家韩愈在读书治学过程中,注意辨别古书之真伪,并根据伪书的不同性质对它们进行了初步的分类;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更写有《辨〈冠子〉》、《辨〈列子〉》等辨伪专篇。宋代疑伪考辨之风更为盛行,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欧阳修、吴、程大昌、王应麟、程颐、朱熹、晁公武等都进行过文献考辨,取得了较多成就。明代胡应麟在总结前人辨伪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古籍作伪的十几种情况,系统提出了辨析伪书的 8条基本方法;藏书家祁承在《澹生堂藏书约·鉴书》中也曾归纳了伪书的种种情况。清代是继宋以后辨伪工作的又一兴盛时期,学者们在提出问题的态度上更为慎重。在辨伪方法上更加细密,考辨深度也大大超过前代,确认了一批长期争论不休的典籍真伪。如确证古文《尚书》《孔子家语》今本《竹书纪年》系伪书等,即是这一时期辨伪工作的重要成果,阎若璩则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姚际恒所著《古今伪书考》一书是著名的辨伪著作。著名学者崔述在《考信录》一书中,对先秦典籍中史事立说的真伪进行了系统的考辨,基本总结了前人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工作经验,直接启迪了中华民国时期“古史辨”学派疑古辨伪学术活动的开展。清末民初的辨伪工作,不仅在具体文献的辨伪上有所收获,而且还在西方学术思想输入的背景下,依据前代学者的经验和成果,对辨伪方法进行了全面总结,基本确立了辨伪作为文献研究的分支学科的地位与方法。其中较著名的有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的审定史料真伪的 5条方法;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中归纳的辨伪公例等。近人张心辑《伪书通考》,基本上涵括了前人的辨伪成果和方法,是一部著名的辨伪工具书。
文物价值和使用价值可分为:孤本、秘本、珍本、善本、通行本等。根据加工不同可分为:过录本、校本、批本等。官刻本: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板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起,福建书坊续有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
本文2023-08-21 02:10:16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619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