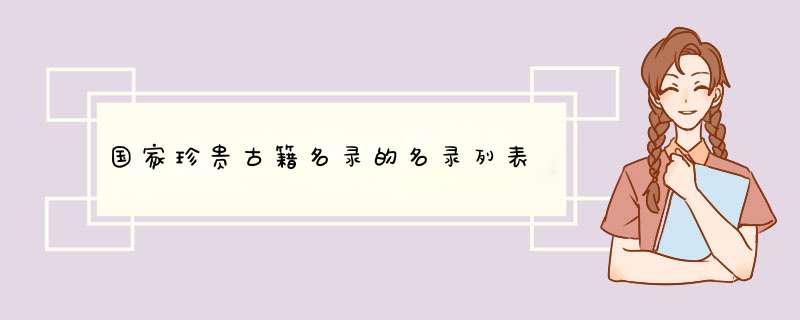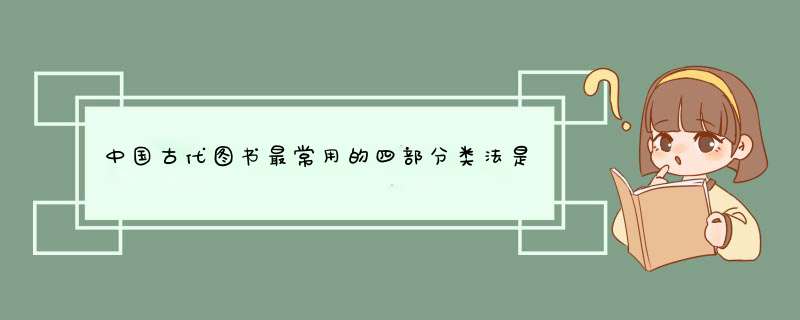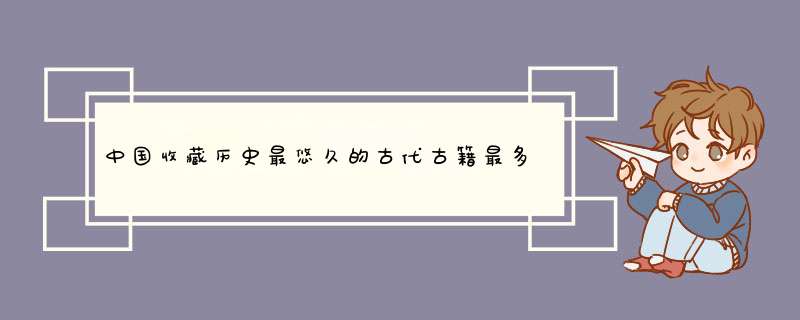如何评判古籍善本的价值?

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投资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评判古籍善本价值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 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二、各种古籍善本的市场价格
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三、古籍善本的几种作伪手法。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它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将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二类是用“旧纸新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张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留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收藏者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籍,并可请专家一起鉴定,应注意去伪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购古籍物有所值。
梵网经》云:“刺血为墨,以髓为水,析骨为笔,书写佛戒。”又《大智度论》卷十六云:“若实爱法,当以汝皮为纸,以身骨为笔,以血书之。”刺血写经有诸多步骤和讲究,前人多有论述。参见:几年前,山东省图书馆的古籍从大明湖分馆搬迁到济南二环路的新馆,在点库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了一部刺血写的佛经,见诸报章,一时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其实,这部书很早以前就已收藏在大明湖奎虚书藏的二楼书库中了,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上世纪70年代全国进行古籍普查,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当时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把它收到善本书目里去,但这部佛经的确是一部极其珍贵的文献 佛教强调读诵及书写经典的功德。向以经典为三宝中之法宝,甚加尊敬,而且通过写经来为人祈福,或求解脱,故书写经典时,态度颇为严谨。写经多以墨书写者,也有人以金银泥写经。刺血写经,是人们对佛经的最高供养形式。《梵网经》云:“刺血为墨,以髓为水,析骨为笔,书写佛戒。”又《大智度论》卷十六云:“若实爱法,当以汝皮为纸,以身骨为笔,以血书之。”刺血写经有诸多步骤和讲究,前人多有论述。 首先,古代人刺血,只从心脏以上取,或从舌头或从手指,或从手臂或从胸前处取血。刺血写经,有专门纯用血写的,也有合金、合朱、合墨、合水写的。如果用纯血书写,盛在清洁的器皿中,先用长针在血中尽力搅动,去掉血筋,这样血就不会粘笔,书写便会很流畅,如遇血凝,用生姜研磨后又可继续使用。刺血时,不可一时刺得太多。因为所采的血,久了就会发臭,无法再用来书写。如果是用手臂血,在刺后至多可接半碗。如果用不了晒干,再用水研开而用,或用血和朱红加胶做成血锭,经晒干后再用。其次,在刺血前,必须吃淡斋,减少吃食盐及大料调和品等。如果不是先戒食这些东西,就会使自己写的血经逐渐变黑发乌,而持戒所书,则字呈浅金**。第三,关于用纸。血性清淡,著纸即散,了无笔墨,成一血团。其纸必须先用白矾矾过,方可用。矾过之纸不渗,最省血。大纸店中有卖的,不需自制。另外在书写时,要一笔笔工整地用楷体书写,用行草来写经书是不提倡的。至于内容,刺血写经,目前存世的大都是《华严经》,其他还有《心经》、《金刚经》等。刺血写经对于历代的高僧们来说,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工程,一日十字或百字,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或几十年,是人生信念的艰苦跋涉。 山东省图书馆所藏刺血写本《华严经》函套内,有佛弟子如典跋曰:“此大乘法宝乃康熙年间四明嗣法沙门深湛大师刺血书《华严经》一部。奉佛弟子颜光南成就功德于道光十五年在济宁州南门里,估货摊工出卖时,有京师成庵潘居士输财请归,送至玉露禅林方丈供奉。愿后之高僧披阅者,珍重护持,永存常住,流传法宝。惟愿人人入毗卢性海,各各登华藏玄门。”简略说明了这部《华严经》的作者和流传的经过,至于何时被山东省图书馆收藏,已无从考证了。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华严经》从字迹上看,描笔迹象很明显,用手抚摸时,字痕凹凸分明,不是直接用毛笔手书的,可能是先用印书用的木版在宣纸上压出字痕,然后刺血填写的,字体工整俊秀,一丝不苟,虽经历300多年的沧桑,清晰依旧,字里行间透露书写人的虔诚和执著。书的每一卷前都有木版摹印的释迦说法图,非常精美。当时民间写经祈愿十分盛行,笔者猜测寺庙在卖香火法器的同时,也用印经典的雕版不沾墨印了一些书,卖给发愿写经的僧侣和信众们,供他们描摹书写。 在我国一些古刹名寺中,也都存有刺血写本的佛经。如江苏苏州西园戒幢律寺,现藏有元代善继以舌血书写的《华严经》一部,历时20余年写成。安徽九华山历史博物馆藏有明代无瑕禅师,刺血研磨银砂,历经28年才抄写成的《华严经》。在北京云居寺有明崇祯(公元1628年)时期的僧人祖慧7卷“舌血”《华严经》。江西庐山博物馆收藏海会寺普超和尚用血抄写的《华严经》,他历时15载,因出血太多,圆寂时年仅45岁。广东省潮州开元寺现珍藏有智诚法师血书《华严经》。在福建省福州涌泉寺内,现在还藏有血书《大乘般若波罗蜜多经》657册等。
提到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暴行,国人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等,但我们同样不应忘记,日军在烧杀奸*之外,还对中国文化万般蹂躏。所谓“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日本深谙其道,所造成的伤痛至今仍未平复——
就在不久前中国东南某省所谓的“反对课纲微调”运动中,还有自称“公平”的青年高呼:“毕竟当初是签约,台湾才变成他们的……在殖民这件事情上,他们是有一个法律条文存在的。我想对大家来讲,这是比较公平的事实。”仅此一例,便足见日本文化侵略给中国造成的危害是多么深重!
毁灭新文化
1932年1月29日,即“一·二八”事变次日上午,日军飞机从“能登吕号”水上飞机母舰起飞,向上海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总厂投弹,尽管投弹数量不多,但很快引燃了厂内的纸张等大量易燃物品。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皆中弹起火,全部焚毁,火势冲过马路,波及东方图书馆。
2月1日上午,日本浪人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直至傍晚,造型新颖、时为闸北最高的5层大厦焚毁一空。30多年收集所得的大量中外图书,积累多年的全部中外杂志、报章,极其珍贵的省、府、厅、州、县地方志及编译所所藏各项参考书籍与文稿均化为灰尘。
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海军少将说:“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传统文化典籍被毁令人痛心,但盐泽的着眼点落在“文化机关”上,可见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商务印书馆创建于1897年,到1932年,规模已超过包括日本在内的远东地区、甚至整个亚洲的所有出版企业,可与世界上任何大型出版社相媲美。当时,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闸北一带占地80余亩,有员工4500多人。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占全国出版物的52%,其中教科书占全国教科书总量的60%以上。商务印书馆被誉为“东方文化之中心机关”。
在学习西方的环境下,商务印书馆着力翻译介绍外国名著,其中以严复所译的《天演论》等八种影响最为深远。这些外国名著对开启民智、启蒙思想、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日本对中国此时顽强的文化抵抗恼怒不已,而商务印书馆作为这其中的代表,更是成为了中国当时新文化的象征。
正因如此,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才会在“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天就成为日军重点的空袭对象。当时日军将轰炸印书馆视作重大战果之一,日本在事变后发行的题为“上海战迹”的“军事邮便”中,至少有一张是当年上海闸北商务印书馆被炸坍塌的惨状。
被轰炸后的商务印书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全面入侵上海租界和香港,原本已经转移到上述几地开始重新生产的商务印书馆再次遭到打击。随着香港沦陷,商务印书社“影写版车间、纸栈房及油墨间中弹燃烧,房屋全毁,物资全部化为灰烬”。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后,工厂、分管、西环栈房全被查封。“财产损失极为严重,机器被运走120余台,铜模几十箱,铅字无算,栈房数百万册书籍和纸张一无幸存。”随着上海租界、香港和北京失守,商务印书社的主要厂房、机器和原料都无法使用。
不仅如此,商务印书馆于1932年8月重新开业后,再次接到了日本人投来的恐吓信。原文如下:“尔中国败孔道,立学堂,读些国语、三民主义,兴立共和,打倒帝国主义,恶劣之道行于天下,腐败尔国青年子弟,敌我日货,使我损款,修尔吉海,绝我南满。尔馆独销学校之书,印些腐败之物。上海毁烧尔馆,尔书馆还是恶习不改,仍印三民之书、党部之语。我国不忍旁观,所以毁尔书馆,今若不速改恶习,我军到处,是商务印书馆尽烧毁。我日国有言在先,那时莫悔。尔国若立颂道,读孔孟之书,不敌我日本之货,仍是好国。若不然,我日本虽小,将决一死战。”
从恐吓信里不难看出日军空袭商务印书馆的直接原因:共和反帝是抗日斗争的思想基础之一,引起了日本的疑惧。正是有了新文化的“启蒙”(当然还有帝国主义暴行本身的“教育”),鲁迅笔下那种麻木的、喜欢看杀头的中国人越来越少,如果他们都奋起抵抗,以日本的国力、人力,最终无疑将走上败途。同时,信中将所谓“孔孟之道”与三民主义、共和反帝等进步思想刻意对立,一方面使部分中国人拒斥新思想,另一方面标榜日本尊重中华传统,这也体现出某些日本人仿效满清入主中原的幻想。
这种对中国人自我启蒙的担忧,导致了日本在对待商务印书社这样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代表时,不吝采取最极端的手段加以剿灭。在1932年和1941年的两次对商务印书社的“扫荡”中,全国近40家商务分馆中有34家及各地工厂被日军轰炸、查封,机器设备大部分被损坏或掠走;“一·二八”事变中,日本没收了其出版的462万册图书,销毁了出版部全部的出版记录卡片;1941年后,更是有1520万册图书在几天内被查抄。日本宪兵只要看到“苏联”、“日本”、“国难”等词语,不论内容为何,一律抄没。
掠夺旧文化
消解新文化,阻止其激发中国民众,只是日本人在文化方面的第一招。受到中华文化长期影响,日本对中国的古代文明及其成就,大多数时候还是相当渴望的。不过由于近代日本的强大和中国的衰落,这种对中国文化的向往最终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展现出来,那就是掠夺。
“九·一八”以前,日本人在我国调查古代遗迹遗址和盗窃文物的事例就不下几十起。例如1905年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一直延续到1911年;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侵占济南,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淄县龙泉寺的2尊北齐石佛、2尊北齐菩萨雕像和2块石碑运往日本;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
日军侵占东三省后,对当地中国文化的掠夺更加直接。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随之而来,进行“考古调查”和盗掘,有些盗掘甚至在日军的直接保护下进行。
1931年至1934年,日本人原田淑人等领导的考古队,盗掘了黑龙江宁安县西南东京城镇的原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遗址,其中宫殿遗址6处、古寺遗址1处,陵墓遗址1处及禁苑、外城遗址数处,劫走一批珍贵文物。
1937年夏,原田淑人、驹进和爱带领考古队,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名义,盗掘了元上都遗址(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劫走一批出土文物,入藏于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同年,黑田源次盗掘了抚顺大官屯辽代瓷窑遗址,劫走大批辽瓷标本。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本人的盗掘活动向我国南方发展。1938年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了《江南踏查》报告,序中写道:昭和十二年(1937年)南京陷落,为了适应时局的发展,急需快速向中国派员进行学术调查以及古文化遗迹的发掘。为此,1938年5月庆应义塾大学派了三个“学术旅行队”,一队由大山柏率领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一队由柴田常惠率领赴中国中部;第三队是松本信广等赴中国江浙地区。
该报告书详细记录了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于1938年5月从东京出发,到达南京后,在日军的护卫下,“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挖掘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等活动。报告书中附有松本“旅行队”活动的照片,在发掘现场,日军荷枪实弹站在周围警戒,如临大敌,充分暴露了他们无视中国主权、肆意盗掘的丑恶嘴脸。
报告书的最后一部分是这次江南调查劫获文物的目录和实物照片,共计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如有孔石斧、玉戚、战国蟠螭纹有盖鼎、商周青铜戈、汉唐铜镜、良渚文化黑陶杯、汉代陶奁、女陶俑、越窑青瓷四耳罐、蚁鼻钱、五铢钱泥范、太平天国“天朝南昌宣抚使韦”印等,这些珍贵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
如在南京,自1938年3月起,日本上海派遣军动用367名士兵、220名特工人员,抓来830名中国人当苦力,劫掠南京图书文献。参与其事的还有满铁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等机构的工作人员。被劫掠的单位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省立国学图书馆等。被劫走的图书共计88万册,比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藏书还多3万册。这些图书文献,日军用卡车搬运了310辆次才搬完,后来全部被劫走。不但公家图书遭到劫掠,一些私人藏书家的古籍善本亦遭劫掠,如南京有名的私人藏书家卢冀野、古筱轩等,他们收藏的名遗善本,或被劫走,或被烧毁。此外,中央图书馆移藏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中四库全书等珍本也被劫运日本。据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数字,八年抗战中,被日军抢劫和焚毁的南京图书,总计达1815箱、2859套、148619册,其中不少是极为珍贵的古籍善本。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统计,中国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1000万册以上。1943年前,美籍人士实地考察,估计中国损失书籍在1500万册以上。
中国大量的博物馆也被侵华日军炸毁或劫夺,如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两批文物被劫,北平研究院在宝鸡发掘所获文物分藏北平部分被盗300多件。日伪先后从故宫博物院运走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等。更可恶的是,1942年伪北平市署搜刮故宫金缸的金屑,供日本侵略军用,简直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博物馆文物藏品大量被劫,对中国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
据1946年中国代表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递交的一份材料说:“全国博物馆,战前计有37所,工作人员110人。战争起后,故宫博物院所藏之文物珍品多迁至四川贵州各地妥藏。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亦迁四川李庄继续筹备。各省设立之博物馆则以战事影响,大多停办。1944年统计,全国仅存博物馆18所。”幸亏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不少文物珍品及时南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设想!
与此相应的,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话语权、解释权上的掠夺。南怀瑾在其《楞严经讲座》中提到,“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外国的学者、日本的学者有意地污蔑中国文化的传统,认为许多都是假的。尤其日本人很厉害,譬如说,认为我们的老祖宗尧、舜、禹,这些历史上的圣帝根本没有这个人。尧是个香炉,拿土做的腿翘起来的香炉,舜是个蜡烛台,庙子上插蜡烛的,禹是个大爬虫,在地上爬啊爬,把黄河长江爬出来的。人家有意污蔑我们的文化,是为了侵略。然后讲孔子呢?孔子——日本人!苏格拉底——日本人!好的都是日本人……”这种文化上的篡改与取而代之的妄想,正是日本对中国文化全面掠夺的重要证据。
建立殖民文化
除了对中国新旧文化的破坏,日本还竭力试图在占领的中国领土上推行自己的一套文化,即所谓的“皇民化教育”。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早稻田大学负责管理中国留学生的青柳笃恒就说:“多培养一名支那青年,也就是日本势力向大陆多前进一步。”当时“关东州”掌管学务的关屋贞二郎露骨地说:“新领土的教育方针,也就是统治方针。”
1932年“伪满”《建国宣言》中即宣称:新国家建设之旨——以顺天安民为主。1933年8月颁布的《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规定“伪满洲国”的教育“必须着眼于启发满洲国民自觉认识该国同帝国密不可分之关系,培养确保东亚和平之特殊的自尊心和五族共和之思想”。1934年刊行的《满洲国文教年鉴》指出:“今我国家以王道为施行教育之方针。”
日本在中国东北推行奴化教育,泯灭东北人民的祖国观念、民族意识和反抗侵略的精神。他们向学生灌输“日满亲善”、“大东亚共荣”等法西斯思想,把日语列为“国语”,就是为数不多的历史、地理课,内容也被篡改歪曲得面目全非,以使中国学生忘记自己的祖国;并且用愚民政策降低中国人的文化知识水准,从实用主义出发片面地强调职业教育,培养为日本侵略所需的劳动力。
日本特别重视对中国人普及日语,因为“日语学习带有潜移默化同化东北民族的特殊意义”。因此,在课程设置上,日语学习的课时超过其他任何学科,如公学堂的日语课时从每周6学时增到每周8学时。同时还规定:学校的日常用语全部用日语,如发通知、背诵、操练、口令、上学问好、下学再见等都不许说汉语。为强化日语学习,在高等公学校和公学堂高年级,除“满洲国语”这一门课用汉语外,其他课程全用日语,如历史、地理、修身、算术、珠算、唱歌等等课程,不准用汉语。学校聘请的教师,绝大多数也为日本人。
伪满洲国协和会发行的日语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占区进入战时状态,日本又在日占区推行皇民化教育政策。
日本殖民当局向中国学生进行“朝会教育”,即感谢皇恩和效忠日本天皇的教育,要求中国学生每天早晨集中在学校操场上,宣读日本天皇诏书,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面向东方遥拜日本天皇。
同时,日本侵略者还向中国学生进行“仪式教育”和“敬神教育”,要求中国学生注重日本节日的庆典。日本殖民当局把“天照大神”奉为“元神”,在东北各地的神社和纪念塔中供奉,要求中国学生按祭日前去参拜、祈祷。如每年每月8日要到旅顺白玉山的“表忠塔”(现已改为白玉山塔)、大连中央公园(今劳动公园)的“忠灵塔”(此塔已拆除)进行参拜。封建礼教成为日本侵略者奴化中国人的精神工具。
日本人安藤基平在《满人教育的使命和价值》一书中更是露骨地说:“对中国人的教育,首先要扮成神的使者,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到中国来拯救不幸的民族。通过教育取得中国青年的信任和理解,坚信与日本互相提携共建王道乐土。”安藤还直言不讳地表明,日本之所以大肆办学校,是“要从语言上打开缺口,让中国学生学会日语,再让他们作媒介以影响他们的父兄,减少他们对日本的仇恨,使他们从感情上同日本接近,感谢日本人,这样,从大连到满铁附属地,然后普及全东北,这对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是无法估量的”。
镇压新文化、掠夺旧文化,用殖民地文化和所谓“皇民化”来取代中国文化,可谓是日本侵华期间“文化战争”的“三板斧”,招招致命。这种系统性地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与蹂躏,甚至比军事行动本身,更能体现日本帝国主义的勃勃野心。
本文2023-08-04 03:55:19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62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