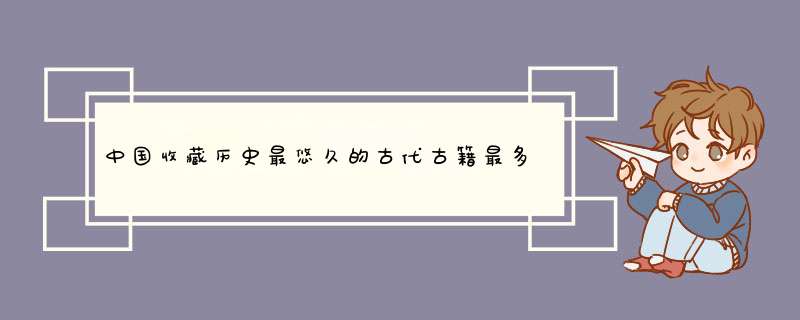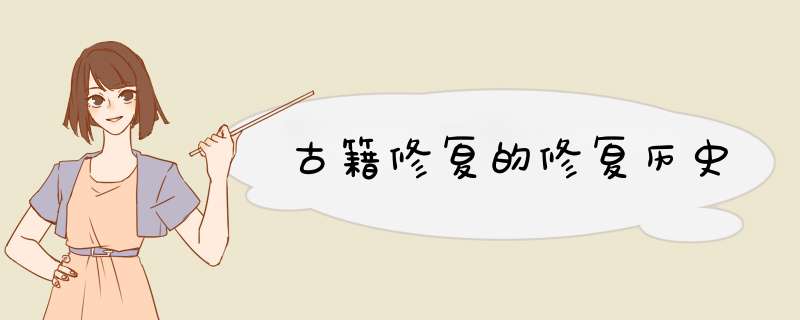卷轴制度有哪两种形式,各自特点是什么?

卷轴制度书籍,包括帛书和纸卷书两种形式,它们有共同之处,也有各自的特点,现分别论述如下:
(一)帛书的起源和历史
帛书是写在缣帛等丝织品上的书籍或文章,它的出现,晚于简册。简册虽然是我国最早的书籍形制,长时期内广泛使用,但有不少缺陷。除了因编绳散断,容易导致“脱简”、“错简”外;书籍也很笨重而不便阅读。如战国学者惠施,就曾用五辆车来运载笨重的书籍(《庄子·天下》);秦始皇每天批阅公文,“至以衡石(一百二十斤)量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西汉东方朔上书,用奏牍三千,汉武帝让两个壮汉尽力持举,从上方阅读,“二月乃尽”(《史记·滑稽列传》)。与这种简册相比,丝织品的帛书有不少优点:缣帛质地柔韧,吸墨性强,既便于书写,又可随意卷舒,阅读和收藏都比较方便;帛书的分量很轻,携带方便;帛书的篇幅宽长,书写时可据书籍内容长短裁剪,又不会有简册散断错乱的毛病。因此,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人用缣帛写书,并在很长时期内与简牍并用。
帛书究竟何时开始出现?目前尚难确考。不过在春秋末期至战国文献中,已时有记述。《论语·卫灵公》说:“子张书于绅。”“绅”,《说文》说是“大带”,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是下垂的带,总之是一种丝织品。《墨子·明鬼》说:“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韩非子·安危》篇也说:“先王寄理于竹帛”。《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说得更为明确:“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如果其言可信,那么在公元前七贷纪的齐桓公时代,就有帛书了。但由于丝织品比竹木更易朽坏,目前考古发现的帛书,大多出于汉代,先秦的较少。
秦汉以来,缣帛更普遍地应用于书写,《汉书·艺文志》中已有相当的图书用“卷”来统计,其他文献也常有反映。如西汉高祖刘邦,曾“书帛射城上”(《史记·高祖本纪》);扬雄《答刘歆书》说自己编纂《方言》时,“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一种光滑的白绢)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于椠”(《全汉文》卷五十二)。东汉末年董卓作乱,挟献帝西迁长安,把洛阳城内东观、兰台、石室等处所藏缣帛图书抢出,“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后汉书·儒林传》),“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隋书·经籍志》)。可见汉代朝廷收藏的帛书十分丰富。1973~1974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西汉初年帛书,包括《老子》甲、乙本和《战国纵横家书》、《周易》、《春秋事语》、《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二十多种书籍、文章,还有三幅古地图,更使得这个问题明朗化。
总起来说,春秋以来开始用缣帛写书、绘画,西汉时期普遍使用,魏晋以后仍然有人使用。但由于丝织品价格昂贵,不能像竹木及纸那样广泛普及,所以帛书始终未有一个独立使用阶段。它的前期伴随着竹木简册的盛行而兴起,后期则伴随着纸书的兴起而衰落,从公元前四五世纪到公元后三四世纪,大约有近千年的时间。
(二)帛书的形制
帛的长短不一,一般说来,标准尺度是40尺,所以在40尺内,不需缝接。但抄写书籍时,还要根据内容长短剪裁或缝接。唐人徐坚《初学记》卷二一说:“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截之”。所以帛书的长度,短的有一尺至数尺,长的则有数丈,东汉董卓的官兵因此用来做滕囊和帷盖。考古发现的帛书也是长短不一,如长沙子弹库的十二神像帛书,长38.7厘米,帛画长37.5厘米;陈家大山帛画长31厘米;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长约192厘米等等。
帛书的宽度,古籍记载以一尺为常制,但根据考古实物,实际上也并不一致。马王堆帛书,有一种是用整幅的帛来书写的,宽约48厘米,如《老子》等;另一种则用半幅的帛来书写,宽约24厘米,如《周易》、《战国纵横家书》等。子弹库的帛书、帛画分别为宽47厘米和28厘米;陈家大山帛画宽22.5厘米。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东汉初年级帛书信,其一约9厘米见方,另一件长15厘米,宽6.5厘米,可见帛书的宽度也是经常根据需要来裁截的。
帛书的书写格式,往往仿照简册。开卷一般留有空白,如同“赘简”。帛书文字也是由上而下书写,每行字数没有一定。为使各行文字书写整齐,有的帛书仿照简册形制,用朱笔或墨笔画上界栏。如马王堆帛书《老子》,各行间就有用朱砂画成的红色界行。帛书的界栏,早期大多为手画,当帛书盛行以后,为使用方便,也为了美观,于是有人用赤丝或黑丝事先在缣帛上织出界栏,如同今日稿纸,专门供书写之用,后人称之为“朱丝栏”、“乌丝栏”。
缣帛的质地柔韧,可以随意折叠或卷舒,所以早期的收藏方式是折叠与卷束并用。如子弹库十二神像帛书,就是经过8次折叠,然后放在一个竹匣中(商承柞《战国楚帛书述略》,《文物》1964年9期);马王堆帛书中,用整幅帛写成的,也是折叠成长方形,再放在一个漆盒下层的格子里;而用半幅的帛写成的,则用一长方形木片为轴,卷成一卷(晓菡《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文物》1974年9期)。折叠收藏的帛书,天长日久,折叠处难免破损断裂,所以后来的帛书,大多采用卷起来收藏的方式。一部书可以卷成一卷或几卷,所以“卷”就成为计算书籍篇幅的单位,一直沿用到今日。不过,古时所说的“卷”,最早指一册,今日也还有这种用法,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等,卷就是一册。但在旧印本书籍中,卷的篇幅往往比册小,一册中常有若干卷。
帛书的卷束,形式与简册不同。帛书与后来的纸卷,质软而薄,卷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轴,粘连在卷子的末端,以此为中心,从左向右卷。而竹木的简册,质硬且厚,最末一根简就起着轴的作用,所以无须另用轴。这也是卷轴形制书籍之所以不包括简册的原因之一。卷轴制书籍所用的轴,要比卷子的宽幅稍长,卷起之后两头在外。其质料早期不过是竹木片,后来通用漆木。皇帝及王公贵族,常用贵重的质料制轴,如琉璃、象牙、玳瑁、珊瑚、黄金等。除卷、轴之外,据古籍记载,卷轴制的帛书及纸卷,还有裸(包首)、带、帙(书衣)、牙签等附属品,以便保护书籍或便于查阅。但今日发现的秦汉帛书中却很少见到这类物品。它们很可能是草创于帛书卷轴,而大备于纸书卷子,所以我们放在下面“纸卷的形制”中一并说明。
(三)纸卷的形制
纸卷的形制初期是沿袭帛书卷轴,古代文献的记载和敦煌卷子等实物都证明了这一点。到了后期向册页制转化时,才演进为独特的形制,即经折装、旋风装。
纸卷如同帛书卷轴,以轴为中心,从左向右卷束。纸卷一般由多张纸连接而成。连接以后的卷子,长度通常9至10米,甚至数十米。每一卷是一个单位,一本书可以由一卷或几卷组成。
为了使字体整齐美观,写书纸上一般要画出界栏。四周的叫“边”或“阑”(也写作“栏”),各行字之间的直行叫“界”。唐人称之为“边准”,宋人称为“解行”。后人也有采用帛书中的名称,称为“乌丝栏”、“朱丝栏”。纸卷各行的字数也不固定,从实物看,十几字到几十字的都有。卷子一般是一面写,也有两面都写字的。如敦煌卷子里,经书的注疏往往抄在背面,叫“背书”。
书籍的注解有的不写在背面。写在正面天头上,叫作“眉批”;有的写在正文行间,叫“夹注”。写在正文行间的注释,为了有所区别,有多种形式:或者用大小两种字体分别写——正文用单行大字,注解用双行小字;或者正文顶格写,注解低一二格写;或者注文仍作单行,但字体略小,写在正文的下面。这后一种方法,抄书者一不小心,往往会使古书的正文与注解混淆,产生类似“错简”的错误。六朝以来还出现用朱、墨两种颜色写成的卷子,正文用朱笔写,注解用墨笔写,这是后代套色印刷的先驱。
纸卷写错了字,自然不能像简册那样刮削修改,古人或用纸贴,或用粉涂,效果都不理想,于是有人发明用雌黄来涂改。雌黄又名鸡冠石,可用作绘画颜料,用来涂写错字,不仅颜色与黄纸相仿,而且错字“一漫即灭,仍久而不脱”(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这种涂改法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有了,贾思勰《齐民要术》在“染潢及治书法”后,就有“雌黄治书法”一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也有“以雌黄改‘宵’为‘肎”’的记载。后人于是讥讽曲解古书、妄加评论者为“信口雌黄”。
纸卷的质地远不如缣帛柔韧结实,所以更需要保护。于是,在帛书卷轴上已开始采取的一些保护措施,到了纸卷时代,便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纸卷的卷头,除了自身留有空白“赘简”外,往往要加一块“包首”(后称“包头”),来保护书卷。包首或者用坚固的硬纸,或者仿效帛书,用绢帛之类的丝织品,古人又称为“裸”。裸的中间系上一根带子,用来捆扎卷子,叫“带”。带一般是丝织品,古代也是很讲究的。有人还用不同颜色的带子,来区分不同门类的书籍。有些大部头的书籍有许多卷,为避免与他书混淆,并保护卷子不受摩擦损伤,还要用“书衣”包裹,叫作“帙”,又写作“袠”。《说文》说:“帙,书衣也。袠,帙或从衣”。用帙包书,只包裹卷身,卷子两边轴头仍露在外,放在书架上,只看见轴头。架上的卷轴如果很多,为便于寻找,就在轴头上挂一个小牌子,上写书名和卷次,叫“签”。考究的用象牙制成,叫作“牙签”。唐代集贤院所藏四库图书,就分别用红、绿、碧、白四色牙签,区分经、史、子、集四部。一般的也有用木、纸或帛的。这样,褾、带、帙、签连同卷、轴,就构成了卷轴形制书籍的各个组成部分,这种卷轴形式一直沿用到唐代木年,才演化为折叠形制,如经折装、旋风装,并进而发展为散页装订,导致了我国书籍形制上的一次革命。
(四)卷轴形制的演进——由卷轴到折叠
卷轴形制适合于缣帛和纸的柔软特性,而且后来发展为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其缺点也就日益明显起来。卷子一般都比较长,甚至可长达数丈,这样长的卷子,阅读时要边拉开、边读、边卷,读完后再卷回去。倘若临时需要查阅其中的某些章节,就更为不便。特别是魏晋以至隋唐,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工具书,如类书、字书、韵书等。这类工具书一般不是从头到尾阅读,而是供人随时查阅,解决问题的。如果需要的资料不在卷子的开头,而是在中间甚至末尾,查找起来不胜其劳。于是有人对卷轴形制作了改进:不再把长长的卷子用轴卷起来,而是一正一反地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卷子的前面和后面加上较硬的纸,以免书籍损坏,这样就成了一叠书。这种折叠而成的“折本”,与从印度传来的梵文佛经的装帧形式有些相像,所以又称为“经折装”或“梵夹装”。经折装的书籍不用拉开和卷起,可以随时翻阅,比卷轴方便得多。这是书籍形制的一大进步,是由卷轴到册页的过渡形式。但经折装的书籍厚厚一叠,阅读时容易散开成而为长长的纸条,于是又有人将一张大纸对折,作为书皮,再把经折装书籍的首页和末页都粘连在书皮内,读时就不会散开了。用这种方法装成的书籍,从第一页可以翻到最后一页,还可再接连翻到第一页,回旋往复,不会间断;而且迅急如风,所以称为“旋风装”,它是经折装的改进型。
经折装和旋风装大约出现于唐代后期,一直沿用到北宋。由于它们都是折叠的形式,折叠后的长方形折子有点像树叶,所以又称为“叶子”或“叶”;折叠以后成为厚厚的一叠,又称为“册”或“册子”(“册”又写作“策”)。折叠形制的书籍启发了后来的散页装订,形式上也有些相像,所以书籍的册页形制,实质以经折装、旋风装为开端。“叶”、“册”这些术语,后来散页装订时依然沿用,不过“叶”字大多改写为“页”,意义上也由像树叶转变为单页、一页了。
崇祯自缢于景山,遗址至今犹存,且有石碑为证,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已是常识。但事实上,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1644年,李自成兵临城下,一场突发的瘟疫严重削弱了守城明军的战斗力,据史料记载,20万大军能登城的不过6000,且多为羸弱之卒。明北京内城墙12公里,外城墙14公里,就算皇城不布防,每名士兵平均也要守50米左右,绝无坚持的可能。 19日,农民军入城,遍搜皇宫无果,直到22日才在煤山(即景山)发现一具尸体,左手写“天子”二字,经太监辨认,系崇祯无疑。然而,对此说法,史家一直有争议,比如黄云眉先生认为崇祯自缢于北海公园,俞平伯先生则认为崇祯死于管园人的小屋。 “巍巍万岁山,密密接烟树,中有望帝魂,悲啼不知处。”这是清人哀悼崇祯的诗作,其中透露了两点疑问,首先,北海公园琼岛上也有一座“万岁山”,第二,自缢遗址,当时的人已经“不知处”。 至于“找到”自缢遗址,并“指出”究竟是哪棵树,甚至绘声绘色地称这棵树为“罪槐”,这是清政府为笼络人心干的事。清军以“为崇祯报仇”的名义入关,当然要做做样子,但并没有勒石立碑。 1931年,故宫博物院始立“明思宗殉国处”碑,沈尹默先生题写碑文,正值抗战前夜,故将“明”左半边故意写成“目”,以示对“日”不屑。此碑“文革”时被砸成两段,拉到原北京少年宫当井盖,北京少年宫即原景山寿皇殿,也有说法崇祯自缢于此。2003年,此碑回到原地。 1931年时“罪槐”已非原树,此时距崇祯自杀已280多年,从照片上看,那棵槐树胸径不过一尺,怎可能生长得如此缓慢?60年代中期,“罪槐”枯死,1971年伐去,1981年,栽了一棵小树,1996年,为渲染气氛,公园找了一棵树龄150年的歪脖老树,移栽于此,原本是建国门一带的道边树,就此成了“罪槐”。 1944年,甲申三百年祭,此处又立一碑,傅增湘撰文。傅是著名的教育家、藏书家,北洋政府时出任教育总长,在他的维护下,蔡元培得以施展“兼容并包”的教学理念,蔡元培辞职后,他也辞职了。1938年,傅参加日本人操纵的东亚文化协议会,并任会长等职,为时人所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派陈毅持亲笔函,专程拜访。陈毅未到,傅已抱憾长逝。傅增湘撰文的石碑曾于1955年被移走,后又在原地复立。 总之,“崇祯自缢处”不过是个象征,以表达后人对历史的一份敬畏而已,如果信以为真,未免贻笑大方。 本文资料引自《北京志·故宫志》等 来源:北京晨报
《山海经》是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神话、地理题材的书。它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山海经》还以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最有代表性的神话寓言故事有,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鲧禹治水等等可读性非常强的神话故事。具体成书年代及作者不详。
本文2023-08-03 18:57:35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1905.html
- 105392-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史部職官類之太常續考05 .pdf
- 105393-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史部職官類之太常續考07 .pdf
- 105394-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史部職官類之太常續考08 .pdf
- 105395-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史部職官類之土官底簿01 .pdf
- 105396-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史部職官類之土官底簿02 .pdf
- 105397-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史部政書類之政和五禮新儀01 .pdf
- 105398-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史部政書類之政和五禮新儀02 .pdf
- 105399-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史部政書類之政和五禮新儀03 .pdf
- 105400-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史部政書類之政和五禮新儀04 .pdf
- 105401-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史部政書類之政和五禮新儀05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