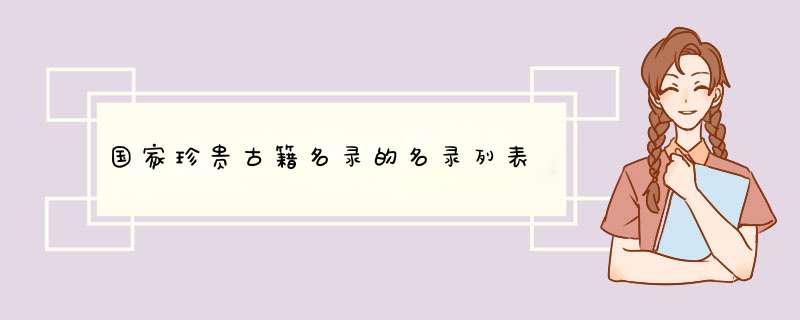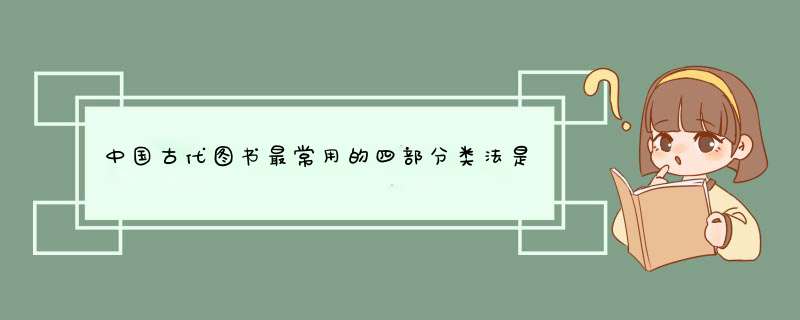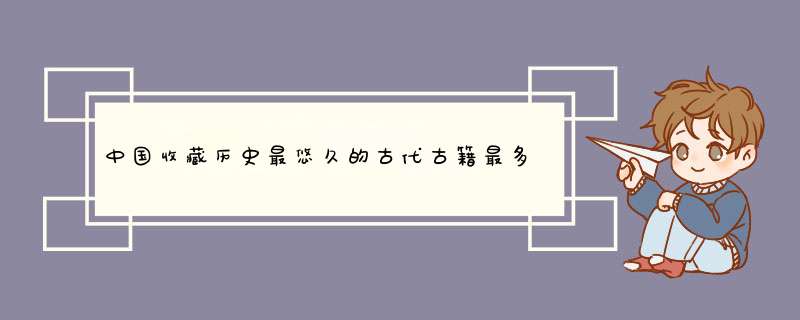清朝史学家、经学家王鸣盛简介,有传世之作《十七史商榷》

生平简介
王鸣盛,字凤喈, 一字礼堂,号西庄,晚年号西b,嘉定镇人(今上海市人)。官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
康熙六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1722年7月4日)生,幼奇慧,四五岁日识数百字,县令冯咏以神童目之。年十七,补诸生。岁种试屡获前列,乡试中副榜,才名藉甚。苏抚陈大受取入 书院肄业,东南才俊咸出其下。在吴门,与王昶德甫、吴泰来企晋、赵文哲损之诸人唱和;沈尚书归愚以为不下“嘉靖七子”。又与惠松岩讲经义,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服膺《尚书》,探索久之,乃信东晋之古文固伪,而马、郑所注,实孔壁之古文也;东晋所献之《太誓》固伪,而唐儒所斥为伪太誓者实非伪也;古文之真伪辨,而《尚书》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从得力矣。
乾隆十二年(1747),26岁时参加江南乡试中举。
乾隆十九年(1754),33岁时参加会试,中式;殿试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投翰林院编修。掌院事蒋文恪公溥重其学,延为上客。后迁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二十四年(1759),38岁即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不久出为福建乡试主考官,途中与一女子相识、纳为小妾,被御史罗典借题发挥,左迁光禄寺卿。
乾隆二十八年(1763),42岁时以老母去世,从此休官不做,安家于苏州。家居者三十年,闭户读书,从事著述,以汉学考证法治史,与惠栋、 研究经学。
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蛾术篇》百卷,其目有十:曰说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盖访王深宁、顾亭林之意,而援引尤加博赡。古文纡徐敦厚,用欧、曾之法,阐许、郑之学。诗早岁宗仰“盛唐”,独爱李义山,吟咏甚富,集凡四十卷。
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68岁时,两目忽瞽,阅两岁,得吴兴医针之而愈,著书如常时,嘉庆二年十二月二日(1798年1月18日)去世,得年七十六。
主要著作王鸣盛著述宏富。他用汉学考证方法研究历史,历时20多年,撰写《十七史商榷》共100卷。将上自《史记》,下迄五代各史中的纪、志、表、传相互考证,分清异同,互作补充,又参阅其他历史名著纠正谬误。对其中的地理、职官、典章制度均详为阐述,为清代史学名著之一。
所著《尚书后案》30卷及《后辨》1卷,专重东汉经学家郑玄之说,此书亦为继承汉代经学传统的重要著作。
晚年仿顾炎武《日知录》著《蛾术篇》100卷,对我国古代制度,器物、文字、人物、地理、碑刻等均有考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蛾术篇》原稿约百卷,王氏生前尚未有定稿,据姚承绪承《蛾术编跋》至道光中谋刻,有钞本九十五卷,而实刻八十二卷,其《凡例》曰《说刻》十卷,详载历代金石,已见王昶《金石萃编》,无庸赘述(实则《萃编》并未全收);《说系》三卷,备列先世旧闻,宜入王氏《家谱》。故所刻之本为八十二卷。分别为《说录》一四卷、《说字》二二卷、《说地》一四卷、《说人》一0卷、《说物》二卷、《说制》一二卷、《说集》六卷、《说通》二卷。为王氏平时论学之作之汇编。由迮鹤寿参校,校刻时核对原文,为注出处,出言过分者则稍圆其说,迮氏所注亦存书中。存世有道光二十一年世楷堂刻本(即此本)、《续四库全书》本等。
另有《续宋文鉴》80卷,《周礼军赋说》6卷。
史学思想王鸣盛强调“求实”,以考证“典制之实”和“事迹之实”为治史宗旨。中国史学发展到清代,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厚重积累,成就固然伟大,流弊也积重难返。每当一种史学思潮形成以后,都按其宗旨对前代的书籍加以整理和改造,这固然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种种人为的舛
误,出现古代史籍被歪曲和篡改的积弊。乾嘉时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识,对中国古代史籍做了一次全面清理。王鸣盛考史特点是首先对一部正史作总体评价,然后考证各种具体问题,最后论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史书。例如考证《汉书》,开端以“《汉书》叙例”、“《史》《汉》烦简”诸条作整体概括,关于《汉书》文字和历史事实的考订,末尾附带考证《汉纪》。再如考证两《唐书》,开端以“宋欧修书不同时”、“二书不分优劣”诸条作整体概括,以下考证新、旧《唐书》书法和历史事实,结尾附带考证《唐史论断》、《唐鉴》等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相比,成就突出表现在史书文字的考订、历史事迹的考订和地理、职官等典章制度的考订方面,为清理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贡献。
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的动机,表现出史家深刻的理性意识。他本着自任其劳、后学受益的理性精神,以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历史考证。他阐明撰写此书目的在于“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十七史商榷·序》)这种甘做后人阶梯的意识驱使王鸣盛不辞辛劳,知难而进,无怨无悔地投入历史考证事业,取得了丰硕的考史成果,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能够发千载之覆。例如他考证《新唐书》对《旧唐书·崔传》删削失实,同时指出宋代吴缜《新唐书纠谬》因不明唐代制度而致误。距离唐代时间较近的吴缜没能解决的问题,反而由千余年后的王鸣盛解决,恐怕不尽关乎个人能力问题,主要是有没有甘愿辛劳、嘉惠后学的意识。这种理性精神值得后人景仰。
王鸣盛史学的 理性 意识
王鸣盛史学的理性意识,在代表作《十七史商榷》一书得到反映。王鸣盛把考证清楚历史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史家治史鹄的,反对史家主观褒贬予夺和驰骋议论。他说:“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十七史商榷·序》)王鸣盛把记载和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历史事件的真实作为治史宗旨和考史原则提出来,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历代治乱兴衰正是通过典章制度反映出来,史家略去典制不载,后人就无法考察前代社会的利弊得失,史学也就失去了借鉴和经世的作用。《十七史商榷》一书的性质就是考察历代正史记载是否据事直书,把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记事失实恢复真相。王鸣盛这种注重考证而慎言褒贬的态度,表现出治史尊重客观事实的理性精神。《十七史商榷》中的“项氏谬计四”、“刘藉项噬项”、“陈平邪说”、“范睢倾白起杀之”等条,也议论历史人物和褒贬历代史迹,但褒贬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之上,议论是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并非空洞抽象地议论褒贬,与不顾客观事实而驰骋议论性质完全不同。这种历史评论的实质表现为尊重史实和客观评价的辩证统一,对中国古代史学方法论的发展至关重要。
王鸣盛把主要精力用于校注古籍、考证史事,正是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适应了中国传统文化总结时期的社会需要。他在治史实践中认识到:“古书传抄镂刻,脱误既多,又每为无学识者改坏,一开卷辄叹千古少能读书人。”(《十七史商榷》卷四二《黎斐》)倘若不先考证清楚史书舛误,而依据错误的史实著书,肯定没有学术价值。王鸣盛认为,当务之急是对古代史籍全面考误订疑,而不是忙于著述。他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十七史商榷·序》)他主张把考误订疑和立意著书合二为一,对撰写《十七史商榷》一书具有辩证认识:“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初未尝别出新意,卓然自著为一书也。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然则予盖以不著为著,且虽著而仍归于不著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他认为只有史实正确、内容征实的考史之作才是著作,而那些离开历史事实主观驰骋议论、褒贬予夺之作不是史书。王鸣盛的这种著书意识在乾嘉史家中最具代表性,反映出清代史家的著述价值观。
王鸣盛治史注重考辨史书记载真伪
王鸣盛治史,以“期于能得其实”为依归,故特重方法论的训练。积一生之治学经验,他总结出了一整套如何读书、如何校书、如何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方法。其中,以通晓目录之学为前提的读书、由此而打下广博的知识基础,乃是以“得其实”为依归的史学研究的必要准备;但在古书未经校勘、语多讹夺的情况下,读书又须与校书相结合,二者互为前提;由校书而展开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工作,读书、校书与辨伪又相互依存而密不可分。似乎可以说,他的读书法即校书法,校书法即辨伪法,一切都围绕着“期于能得其实”这一史学宗旨而展开。
王鸣盛如何校书?《十七史商榷序》说“余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w驳,以成是书,故曰商榷也。”在王鸣盛这里,所谓“校书”并不仅仅是通常所理解的文字勘误的工作,而且是一项包括史实考证在内、以据实恢复历史之本来面目的科学研究的工作。他之所以把他的史学着作题名为《十七史商榷》,主要的着眼点就是要在史实的真伪方面与以往的史书、特别是官修的正史“商榷”一番。校勘的过程即是认认真真地读书的过程:“既校既读,亦随校随读,购借善本,再三雠勘。”至于考辨史书记载的真伪,则需借助于正史以外的多重证据。
在王鸣盛搜集的各种史料中,约分两类:一类是文献记载,包括野史笔记、方志谱牒、诸子百家、诗文别集、佛道典籍等等;另一类是文物资料,包括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他认为这两类材料可以互相检照、互相印证,并且实际运用这两类材料进行“参伍错综,比物连类”的史学研究。这一方法,也就是后来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
王鸣盛治史强调“金石之有关史学”他认为古代的金石铭文资料,既可补充史书记载之阙,亦可纠正历史记载之讹。二者对于据实恢复历史的真相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利用金石资料补充史书记载之阙方面,他的发现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尤为重大。例如,《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没有记载杨国忠与李林甫互相勾结陷害名将王忠嗣之事,但这件事却与后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非同寻常的关联。“史有所漏,赖碑得见”。王鸣盛乃依据元载撰写的《王忠嗣神道碑》补充了这一被遗漏了的重要史实,说明了王忠嗣遭受陷害的经过,从而为全面解说安史之乱何以发生、唐王朝何以由盛而衰提供了又一不可忽视的证据。诚如王鸣盛所云:“忠嗣在唐名将中当居第一等,其老谋成算,体国惠民,尤不易得。横遭冤诬,身颓业衰。使忠嗣得竟其用,不但二边无扰,亦无禄山之难矣。唐人自坏长城,乃天下之大不幸也。”至于凭借金石资料以纠正历史记载之讹,王鸣盛亦多有发现。如依据《李良臣碑》《李光进碑》和《李光颜碑》的拓本,纠正了《旧唐书》误把李良臣在平息安史之乱中的战功附会为其子李光进的战功的错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王鸣盛治史重视野史笔记
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赵翼一样,王鸣盛也认为历代所谓《实录》有“为尊者讳”的弊病,转而重视野史笔记的史料价值。赵翼根据野史笔记中的真实可信的史料来订正历代官修史书的作伪失实之处,提出了“书生论古勿泥古,未必传闻皆伪史策真”的论断。王鸣盛的观点亦与此相似,认为“采小说者未必皆非,依实录者未必皆是”。这里所说的“小说”,即是指民间的野史笔记;而“实录”,则是由朝廷的史官所记载、作为官修正史之依据的历朝官方史料。王鸣盛认为,“实录中必多虚美”,例如五代诸实录“多系五代人所修,粉饰附会必多”,“盖五代诸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亦多讳饰”,而野史笔记中则多有真实可信者。所以他颇为公允地指出:“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这种以野史与正史相互参订以寻求历史真实的方法,也是合乎近代科学精神之要求的。
王鸣盛学术思想也有保守的一面。在经学研究方面,他有所谓“求古即所以求是”、“治经断不敢驳经”、“但当墨守 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之说。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吴派朴学的局限性的表现。然而,王鸣盛毕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所提倡的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实证方法,以及他的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贡献影响王鸣盛极为重视史籍校勘,对校勘的重要意义及必须具备的条件做出了科学的论断;并充分运用各种校勘方法校勘史籍;同时还注意结合探讨史籍致误原由,并进而归纳总结出“误例”,校勘方法全面,成果丰硕,对促进清代考据学日臻完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人整理研究古代史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史学宗旨上,王鸣盛坚决拒斥孔子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明儒家的“驰骋议论,以明法戒”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在史学方法论上,系统论说了“考其典制之实”和“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在史论方面,王鸣盛亦一反儒家传统观念,依据历史事实,为范晔、初唐四杰、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温廷筠和李商隐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
藏书之家性俭素,无玩好声色之嗜,唯左图右史,宋椠元刻明本亦多有收藏,黄丕烈、莫伯骥、丁丙、罗振常等藏家的书目中亦有其旧藏著录。研究《尚书》30余年,撰有《尚书后案》30余卷。著《十七史商榷》百卷,为史学经典名著之一。对金石、目录之学亦有研究。藏书丰富,多为治史所用,广泛搜集野史笔记,百家小说,碑帖鼎彝,藏书处曰“耕养斋”、“颐志堂”等,校勘精审。藏书印有“通议大夫”、“乙丑探花及第”、“西庄居士”、“西b居士”、“光禄卿之章”等。著述宏富,主要有《周礼军赋说》、《西b居士集》、《蛾术编》等。又选辑平生交游能诗者12家,编成《苔岭集》,自刻为《西庄始存稿》。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知识信息;
著作方式;
文字;
物质载体;
文字制作技术;
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明君治理国家的原则,像有若回答密子所说的那样,要有办法。君主听取言论时,一味欣赏说话人的口才,观察行动时,一味赞赏远离实际的作风。所以臣子和民众讲起话来,就高深莫测,做起事来就远离实际。
宓子贱治理单父,有若会见他说:“您为什么瘦了?”路子贱说:“君王不知道我没有德才,派我治理单父,政务紧急,心里忧愁,所以瘦了。”有若说:“从前舜弹奏着五弦琴,歌唱着《南风》诗,天下就太平了。现在单父这么个小地方,治理起来却要发愁,那么治理天下该怎么办呢?所以有了办法来统治国家,就是安闲地坐在朝廷里,脸上有少女般红润的气色,对治理国家也没有什么妨害;没有办法去统治国家,身体即便又累又瘦,也还是没有什么好处。”
楚王对田鸠说:“墨子是个声名显赫的学者。他亲自实践起来还是不错的,他讲的话很多,但不动听,为什么?”田坞说:“过去秦国君主把女儿嫁给晋国公子,叫晋国为他女儿准备好装饰,衣着华丽的陪嫁女子有七十人。到了晋国,晋国人喜欢陪嫁媵妾,却看不起秦君的女儿。这可以叫做善于嫁妄,不能说是善于嫁女。楚国有个在郑国出卖宝珠的人,他用木兰做了一个匣子,匣子用香料熏过,用珠玉作缀,用玫瑰装饰,用翡翠连结。郑国人买了他的匣子,却把珠子还给了他。这可以叫做善于卖匣子,不能说是善于卖宝珠。现在社会上的言论,都是一些漂亮动听的话,君主只看文采而不管它是否有用。墨子的学说,传扬先王道术,阐明圣人言论,希望广泛地告知人们。如果修饰文辞的话,他就担心人们会留意于文采而忘了它的内在价值,从而造成因为文辞而损害实用的恶果。这和楚人卖宝珠、秦君嫁女儿是同一类型的事,所以墨子的话很多,但不动听。”
宋王和齐国作对时,专为习武修建宫殿。讴癸唱起歌来,走路的人停下来观看,建筑的人不感到疲劳。宋王听说后,召见讴癸并加以赏赐。讴癸回答说:“我老师射稽的歌,唱得比我还好。”宋王召来射稽让他唱歌,但走路的人还不停地走,建筑的人也感到疲倦。宋王说:“走路的人还不停地走,建筑的人也感到疲劳,射稽唱得不如你好,这是为什么?”讴癸回答说:“大王可以检查一下我们两人的功效。”讴癸唱歌时建筑的人只筑了四板,射稽唱歌时却筑了八板;再检查墙的坚固程度,讴癸唱歌时筑的墙能打进去五寸,射稽唱歌时筑的墙只能打进去两寸。
良药苦口,但聪明人却要努力喝下去,这是因为他知道喝下去后能使自己疾病痊愈。忠言逆耳,但明智君主愿意听取,这是因为他知道由此可以获得成功
按刻书机构区分。计有:官刻本(包括国子监本简称监本、兴文署本、经厂本、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内府本、府学本、州学本、县学本、藩府本、官书局本、各地书院本)、家刻本、坊刻本等。
按雕版印刷情况分。计有:精刻本、写刻本、单刻本、丛书本、道藏本、祖本、原刻本、翻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递修本、百衲本、旧版、通行本、邋遢本、书帕本等。
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扩展资料:
古籍版本的历史说明:
春秋末战国时编定撰写的经、传、说、记、诸子书等是古籍的上限。下限则一般划到清代末年(这和史的分期有所不同)。
广义的下限是: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或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炉灶,例如旧体诗文集、对古籍所作的旧式校注之类,一般仍可以划入古籍范围。
应该算吧!因为专著即专业方面的著作。古代很多典籍写得非常简略,后人不断地加以注解,这些注解的文字专业性非常强。比如孔子的《春秋》,后代有不少人对其进行注解,最有名的是左丘明的《左氏春秋》,即《左传》。现代人对古籍的注解应该也是很专业的事情,形成的著作应该算专著。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中华书局曾经出版过郭象的《庄子注疏》((郭象/成玄英)。感兴趣的话,可以书店购买或者到大型图书馆借阅。
但个人感觉,郭象毕竟是儒家学派出身,他写的《庄子注疏》基本是以自己学术观点来发挥庄子的文字,所以大概率上并非是庄子本意(道家无为),可以当做参考,不能完全采信。之所以郭象这个版本一直为后世学者推崇,也是因为后世学者普遍都是偏向儒家的人士。
另外,中华书局对所有经典古籍都出版过各种校注版本,对《庄子》也不例外,有名的就有:
《庄子》(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译者: 方勇);《庄子集释》(郭庆藩);《庄子集解》(王先谦);《庄子补正》(刘文典);《庄子注疏》(郭象/成玄英);《庄子校诠》(王叔岷)。
你可以先从最浅显的现代人校注的《庄子》开始阅读,有所心得之后,再涉猎其他古籍(其他几本内容浩繁、相对较枯燥,建议当做文词工具书翻阅)。
本文2023-08-03 21:26:1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3052.html